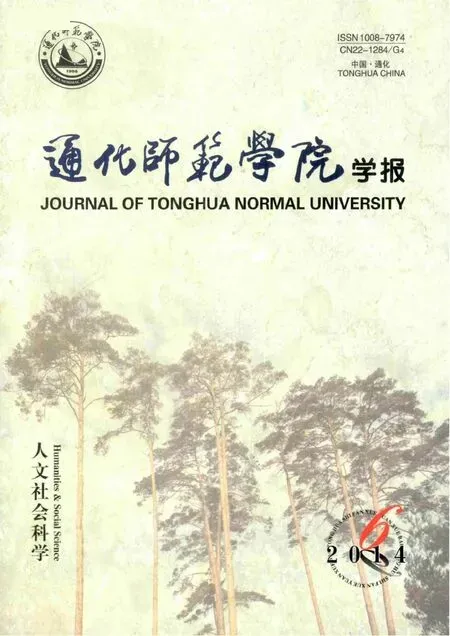《尚书·吕刑》中的“天德”意蕴阐微
2014-02-12李德龙
李德龙
(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3)
《尚书·吕刑》中的“天德”意蕴阐微
李德龙
(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3)
“天德”一词首现于西周中期的法律文献《吕刑》中,它的出现是随着西周政权的日趋巩固而进一步神化王权的必然结果,体现了统治者借助于“天德”的神圣性以论证王权至上的政治企图。“天德”具有哲学内涵,相当于“天道”,它直接引发了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规律、社会伦常以及人道性命的深刻思考,对中国古代哲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周中期;《吕刑》;天德;天道
“德”是贯穿于西周时期政治生活始终的一种政治理念抑或政治行为方式,在统治阶级对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任德尚贤等相关政治命题的反复申说与大力提倡下,使“德”成为今文《周书》十九篇中出现频率极高的重要字眼。然而,任何一种思想观念自其形成伊始,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与时俱进地注入新的内涵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那么周人对于“德”的观念当然也不能例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直到制作于西周穆王时期的《尚书·吕刑》篇中①,才首次出现了更具神圣义与抽象义的“天德”概念,其文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后来注家多用“天的道德性”或“上天立下的道德标准”来解释“天德”的内涵,如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曰:“天德,谓五常之德。”即是用后世伦理道德范畴上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来比附“天”所具有的道德性。虽然西周时期的“德”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伦理道德意蕴,但若结合文献中“德”字出现的上下文语境,以及从“德”的思想观念发展史上来看,它还不能等同于后世那种为人们所熟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心性道德。故用后世道德范畴上的“五常”来理解“天德”,不仅证据明显不足,而且与《吕刑》全篇主旨不符。孔颖达疏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为德,当谓天德平均。”[1]249说“天德平均”较为符合《吕刑》中穆王所倡导的“明于刑之中”的刑罚原则,而说“言能效天为德”则暗示了“天德”这一概念有着更为深邃的思想内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天德”作为西周中期出现的新词语,应该是以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依托,体现了对周初之“德”的继承和发展。
一、西周中期“天德”概念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笔者认为,周人把“天”与“德”二字耦合起来而形成“天德”的概念,是以周王为首的统治者随着政权的日趋巩固而进一步神化王权的必然结果。如何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和谋求政权的持久性,是历朝历代的执政者所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永恒政治话题,但在一个新兴政权的建立初期,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较之持久性问题,则具有相对的优先性地位。周革殷命以后,面对管叔、蔡叔、霍叔联合武庚的叛乱,如何使周人的新兴政权在严峻动荡的社会形势中站稳脚跟,确定自身统治权的合法性依据,从而为广大民众尤其是殷商遗民所认可,成为摄政时期的周公需要率先解决的第一执政要务,因此,“德”在周初首先是为论证周人政权的合法性而提出来的。周公在总结夏商两代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主张。他在《召诰》中说:“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上天不会无条件地永久护佑统治者已有的政权,天命是可以发生移易的,有“德”者膺受天命,无“德”者坠失天命,这就为以周代殷的合法合理性找到了神学依据。究竟何为配天之“德”?由于周人获得上天的眷顾而拥有天命是自文王始,文王为“小邦周”受命开基立下不朽功勋,故文王之“德”理所当然地成为“配天”的典范之“德”,这体现在周公等人对“文王之德”的大力颂扬中,如:
我道惟宁(文)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君奭》)
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君奭》)
(武王)不敢替厥(文王)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 (《立政》)在周公看来,周代嗣王唯有继承、保持、效仿和发扬“文王之德”,才能真正做到持德固命,“文王之德”成了“受天命”的重要象征。文王之“德”究竟包含哪些政治内涵呢?从《尚书》的周初文献记载来看,主要是指文王“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2]、“无彝酒”[3]、“和恒四方民”[4]、“不敢盘于游田”[5]等等美善的政治行为。也就是说,周公所言之“德”主要是以“文王之德”为范本并有着具体内容实指的政治概念,刘泽华先生将之归纳为十项内容:敬天,敬祖,继承祖业,尊王命,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怜小民,慎行政,无逸,行教化,慎刑罚。[6]38周文王所具有的“德”在解决了周人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也为周代嗣王提供了确保政权长治久安的施政策略——敬德,而敬德以保民为核心,保民又以“明德慎罚”为落脚点,文王“克明德慎罚”,最终“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这样,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就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较为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
迨至穆王时期,西周政权经历了成、康、昭三代的平稳运行而日趋巩固,国力的强盛和社会的繁荣使政权的合法性问题逐渐退居其次,而维护王权的神圣和永恒则成为政治上的头等大事,那么,“天德”正是为迎合此种政治需求应运而生的。周公的“以德配天”较好地解决了政权合法性问题,在周初“以德配天”的论调下,“天”能够赏善罚恶,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7],“天”只是“德”的监督者而不是拥有者,周代嗣王需持恭敬谨慎的心态兢兢业业地以“文王之德”为榜样,真心实意地保民惠民获得民意的支持而使自身有“德”,进而获得上天的眷顾和青睐。君权虽然神授但君王还居于“天”的位格之下而受其监督,故周公在政权建立之初从不称文王、武王为“天子”,只是宣扬文武是“受命于天”。 周公极力推崇的“文王之德”只是为周王提供了一整套具体的施政策略以确保天命在身,但还没有把王权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政权的日趋稳固使周人昔日的忧患意识和敬畏心态逐渐消散,周代嗣王自成王开始便俨然以天的代理人自居,被直呼为“天子”。于是,周人便把现实尘世的“德”弥漫到至上神“天”上,创生出比“文王之德”更为神圣的“天德”概念,使“天”成为“德”的完美拥有者和最高象征者。这样,从思想逻辑的角度来说,具有抽象性的神圣“天德”实质上是人间的“王德”在神灵世界的折射,“天德”已为“王德”所形塑,“天德”体现的是现实世界君王的意志,“天德”与“王德”合为一体,王成为了“天”的化身,从而取得了与至上神平起平坐的位置。《吕刑》篇中穆王对诸执法官员的训诫之辞:“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体现的正是周穆王那种唯我独尊的心态,因为“奉我一人”即是“敬逆天命”,天下万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仰仗于周天子一人。
二、“天德”概念的哲学内涵及历史影响
从《吕刑》所体现的法律思想来看,西周中期的统治者虽然仍继承秉持着文王“明德慎罚”的刑法传统与理念,但与周初那种强调保民惠民以维护民本的思想主旨已大相径庭,因为王权的进一步神化必然会伴随着对民众政治地位上升的抑制,如何用适当的刑罚治民理民使之安于等级秩序以维护君本、确保王权的至上性,才是“折民惟刑”的终极目标。因此,穆王在《吕刑》通篇中对以保民为核心的“文王之德”都只字未提,而是通过总结远古时代蚩尤用酷刑和颛顼用中刑治理民众的正反两方面教训,借助于更具抽象和神圣的“天德”概念,来论证“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的合理性,以此来告诫四方诸侯将之贯彻到底而须臾不可动摇。“惟克天德”的背后乃是穆王要求诸侯对王命的绝对服从,忠心耿耿地做好王的牧民工具“以奉我一人”。这样,“天德”就具备了天理的意蕴并成为人间之理的预设,人世间的宗法等级秩序及维护此种秩序的各项政策法规,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充分体现了穆王用“天德”来贯通天人、以天道论人道的思想观念,这是神化王权的政治期望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故《吕刑》中的“天德”不是在说明天的道德性,也不是指上天立下的道德标准,“天德”之“德”具有了抽象的哲学内涵,“天德”相当于“天理”或“天道”。《国语·越语下》载范蠡语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此处哲学层面上的“天道”与“天德”只是词异而义同,它们有着相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的完整意思是说:四方诸侯惟有恭敬谨慎地用中正之刑治民才能上合天道,从而为自己积下延期长久之寿,在人间配天命而享天禄。故孔疏“能效天为德”的解说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就《吕刑》篇的前后文义来说,穆王是将“明于刑之中”视为“天德”(天道)在人世的体现,告诫诸执法官员由政治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天德”是不可怀疑的,必须身体力行去效法、顺合“天德”。但如果将此理论内涵和运思理路再做进一步拓展延伸,那么凡是有助于维护和加强现存等级秩序的各种政治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均可以纳入“天德”的视域之内。制作于宣王时期的诗《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说的就是众民连同人间的各种法则都是天之所降,众民如果能够秉持顺应降自于天的人之常道,并乐于为之才算是具备了美好的德行。我们认为,“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即是对“惟克天德”思想的推衍和发挥,充分体现了“天德”概念内涵的广延性。
兼具政治内涵和伦理内涵的周初之“德”在西周中期通过“天德”词语的表述,又被抽象上升至哲学的层面,这在“德”观念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天德”所内蕴的哲学内涵,使周人“德”的思想成为了贯通天人、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有学者指出:“‘天德’既体现着自然法则,也体现着社会法则;既彰显着宇宙之理,也呈现着人生之理。这样的‘德’,不仅具有了明确的哲学内涵,而且还具有了统摄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本体的义蕴。”[8]尽管“天德”在整部《尚书》中仅此一见,并且是专门为神化王权而被提出来的,沾染着浓郁的政治功利色彩,但由于“天德”是首次出现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新概念且具备了“天道”的雏形,表明周人已经开启了用抽象的“天德”概念来阐释自然规律和社会秩序的思辨历程,它直接引发了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规律、社会伦常以及人道性命的深刻思考。“天德”一词屡屡闪现于先秦诸子讨论自然、社会、人生之理的经典话语中。如墨子在《天志下》中曰:“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即是用“天德”来阐明“天道”(自然规律)的例证。荀子讲“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9],是把运动流行、新陈代谢概括为天地运行之理(天德)。庄子讲“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10],是用隐喻的方式将水性喻指为天道(天德),并认为只有契合于水性或天道的虚无的人生才是最理想的,所谓“虚无恬淡,乃合天德。”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惟克天德”所构建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为后来的思想家们对天人之际的思索积蓄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周易·乾·文言》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的“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管子·版法解》中的 “法天合德”等思想,都是在用天道论证人道并强调人道应当顺合效法天道,以期达到内在“人德”与外在“天德”的统一,进而实现将“天德”内化为“人德”,此种思维和论证方式与“惟克天德”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注释:
① 对于《吕刑》的制作年代,学者们向来多认为成书于西周穆王时期,但郭沫若和张西堂两位先生对此提出异议,蒋善国在《尚书综述》中对两家观点和论据进行了考证,认为《吕刑》为穆王时期作品仍是可以信据的,笔者赞同蒋说并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详见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3页。)
[1]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
[2]尚书·康诰[M].
[3]尚书·酒诰[M].
[4]尚书·洛诰[M].
[5]尚书·无逸[M].
[6]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7]尚书·蔡仲之命[M].
[8]孙熙国,肖雁.论《尚书》“德”范畴的形上义蕴[J].哲学研究,2006(12).
[9]荀子·不苟[M].
[10]庄子·刻意[M].
(责任编辑:徐星华)
K225.04
A
1008—7974(2014)06—0106—03
2014-09-06
李德龙(1978-)吉林松原人,史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及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吉林省教育厅项目“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研究”。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3]第5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