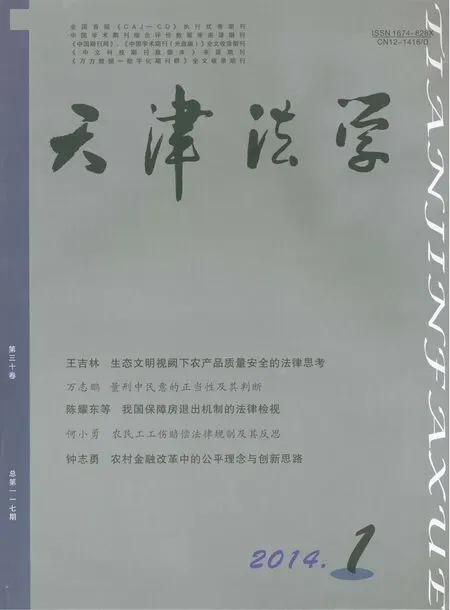农民工工伤赔偿法律规制及其反思
2014-02-12何小勇
何小勇
(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江苏南京210012)
·学术热点·
农民工工伤赔偿法律规制及其反思
何小勇
(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江苏南京210012)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劳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仍难以被完全纳入《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者”范围。农民工工伤索赔时除面临“劳动者”身份界定、劳动关系认定障碍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的冲突与分歧也使其在索赔时面临适用法律选择的困境,而工伤赔偿程序中劳动仲裁、行政、民事诉讼交叉问题更加剧了农民工工伤索赔的难度。因此,立法应明确把农民工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摈弃非法用工单位概念,同时改革现行工伤索偿模式,赋予法院直接认定工伤的权力,以解决农民工工伤索赔难题。
农民工;非法用工单位;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法律适用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和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用5年时间,全程跟踪统计了北京地区约50个工地的73起工伤案例后,发布了《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遭遇职业灾害的建筑业农民工群体中,没有一例有正规的劳动合同与工伤保险,89.1%的建筑工人是既无劳动合同,又无工伤保险。由于劳动关系认定难和赔付执行难,在遭受职业灾害时,15.1%的农民工选择按照工伤维权程序维权,70%选择以法定程序之外的方式维权,12.4%的农民工则选择放弃维权。调查发现,建筑业总包施工单位中,47.9%为私人挂靠,劳务分包公司中94.5%为私人挂靠。在73起工伤案例中,农民工没有一例获得总包公司的赔偿,仅11%获得了分包公司的赔偿[1]。另据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与安全帽大学生志愿者流动服务队发布的《京、渝、沪、深四城市建筑工人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建筑领域从业的劳动者中,92.6%的人员是农业户口。
建筑业农民工工伤赔偿难不过是农民工群体工伤索赔现状的一个缩影。参与《社会保险法》起草的郑功成教授曾对北京、深圳、苏州、成都四地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保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四地平均70.9%的受访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伤保险[2],而学者周慧文的调查统计结果也显示,约有69%的被调查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伤保险[3]。人社部工伤保险司司长陈刚指出:打到法院的工伤认定官司中80%是用人单位没有参保的,对工伤认定发生争议的案件中,有70%-80%是农民工的案件[4]。因此,妥善解决农民工工伤赔偿问题已迫在眉睫。
农民工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类劳动力群体,其称谓与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相关,通常指户籍在农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2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18993万人中,农民工人数为7173万。即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保率为27.31%,约有73%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伤保险,与上述学者的调查数据大致相符。大批的农民工游离在工伤保险的保障之外,其原因是农民工群体法律维权意识淡薄?还是因为现行的劳动法与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在顶层设计上存在着重大缺陷?
一、农民工“劳动者”身份认定及工伤保险权利享有历程回顾
德国法学家罗伯特·霍恩认为:“一个国家的劳动法与其合同法或侵权行为法相比,总是更深刻地打着本民族历史和社会的烙印”[5]。在我国的劳动法理论研究及相关立法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两大基本概念的内涵定位不仅决定了在劳动过程中,劳资双方发生争议时应适用劳动法抑或是适用民法规范来调整,更决定了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能否享受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劳动法律制度的保护与保障。
雇用他人为其劳动,国外一般称之为雇主,《劳动法》使用的称谓为“用人单位”。学者认为:“用人单位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单位,而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用人单位的提法,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劳动法学中的反映”[6]。但是,“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关系主体一方的重要概念,在解读上容易产生歧义。曾任职于劳动部政策法规司并参与起草制定《劳动法》的黎建飞认为:起草《劳动法》之初,对使用“用人单位”的概念曾有过反复斟酌与推敲,因为这关系到劳动法调整范围的划定、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的确立,同时也清楚地预知了使用“用人单位”一词表述的缺陷,知道使用“雇主”与“雇员”比使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更为贴切。但是,在宪法规定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立法中,要在劳动者之上规定“雇主”是需要慎重考虑的[7]。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用人单位”的范围呈不断扩展之势。2010年《工伤保险条例》修订时,“用人单位”已从《劳动法》规定的境内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扩大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主体。“非法用工单位”的提法,源自于2002年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4条的相关规定。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订《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时,参考了该法的界定标准,把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规定为“非法用工单位”,以区别于《劳动法》中的“用人单位”。然而,能否将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规定的经营组织直接嫁接成为劳动法中的“非法用工单位”,但对其职工在劳动过程中遭受事故伤害时,参照适用工伤赔偿规定而不是参照适用民事侵权赔偿规定来处理,其法理依据何在?成为在司法实践中引发适用法律争议的根源。
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以获取工资,国外称之为雇员或劳工,《劳动法》使用“劳动者”提法,但没有明确其内涵及范围。司法实践中,往往是以界定“用人单位”范围的方法来明确或反证提供劳动力者是否具备“劳动者”的身份。农民工是否符合《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身份,一直存在争议。学者认为,1994年《劳动法》颁布时,正值国企改革攻坚之际,因而在立法上选择把国有企业的职工作为“劳动者”的原型,并以此确立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该机制建立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而农民工由于户籍问题,无法进入到这种体制化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中,因而不是《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范畴[8]。这种分析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至今,《劳动法》如果仍然坚持将调整范围限定在含义模糊的“用人单位”及“劳动者”上,罔顾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实际情况,便显得不合时宜了。
农民工一词历经“外来工”、“打工仔”等称谓,其变化揭示了我国的社会变迁,使来自农村的城镇务工人员更加接近其本应有的身份——劳动者。2003年国务院首次发布《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其显示1990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500万人,2003年为9800万人。2012年末,农民工总量已达26261万人。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年数平均为7.01年,28.6%的农民工达10年以上;另新生代的农民工(指80后出生)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成为现行农民工主体[9]。其表明了农民工在人数不断增长的同时,就业的稳定性也得到显著提升,就业趋于长期化。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和我国城镇化的推进,更多的农民工开始谋求市民身份,谋求平等享受城市提供的就业、入学、医疗等公共服务。农民工的就业变化及权利诉求变迁,就劳动法而言,就是在谋求“劳动者”身份的确认,谋求劳动法所规定的各项劳动者权利的平等享有。
尽管如此,农民工被视为属《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并因此而享受各项劳动权利保障,仍历经曲折。1994年劳动部《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农民工跨省及在本省范围内的大中城市内流动就业问题首次作出规定。该法对农民工就业在职业介绍、从事的行业、工种、劳动合同订立、续延等方面予以了种种限制,并规定农民工须持有外出就业登记卡,并领取就业当地劳动部门颁发的外来人员就业证,证、卡合一后才能有效就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对实现就业的农民工能否因此而获得社会保险保障,未作任何规定。与此相应,1995年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明确规定:农村劳动者不适用劳动法。因此,可认为仅部分符合规定条件的农民工才被视为属于《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2003年国务院《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使农民工逐渐得以部分享受各级政府为劳动者提供的公共就业服务权利;同年,全国总工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农民工加入企业工会的问题被首次写入大会报告中。但是,2003年《工伤保险条例》颁布时,对农民工是否享有工伤保险保障问题,规定含糊不清。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从制度层面上承认农民工可以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其前提条件为雇主必须是《劳动法》所规定的“用人单位”。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重申要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但直到2010年《社会保险法》颁布,其第95条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才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保障的权利。但是,不管是《劳动法》还是配套的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均缺乏将该权利具体落实的明确规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末,全国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为4543万人、4996万人、2702万人、7173万人,可知,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实际上并未真正享受到各种社会保险权利的保障。
二、农民工工伤索赔时适用法律选择及其原因探讨
农民工享受工伤保险保障除受其身份属性的困扰外,对用工单位性质的认定也影响了其权利的享有。实践中,使用农民工的单位既包括《劳动法》所规定的用人单位,还包括了非法用工单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6条规定,非法用工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该单位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待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根据该法授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以下简称一次性赔偿办法)。但是,如将《一次性赔偿办法》与《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各项赔偿项目与赔偿标准相比较,两者仍存在一定的差别。并且,前者的赔偿责任承担主体是非法用工单位,而后者的赔偿责任承担主体则包括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用人单位,两者在赔付能力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农民工在遭遇事故伤害时,不可避免会出现适用法律方面的选择。
另非法用工单位的提法,不仅强调用工单位主体资格的非法性,而且还蕴含着其与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如果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那么,能否认为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民法上的雇佣关系,按雇佣关系的相关规则来予以处理?2003年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区别于《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规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同时,为区别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对“从事雇佣活动”规定为:“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根据该司法解释,非法用工单位似乎应当理解为属于民法上的“雇主”,而农民工应理解为属于民法上的“雇员”,农民工在生产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其性质应认定为属于一种民事侵权损害。《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在第17-32条条文中详尽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涉及的各项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与《一次性赔偿办法》、《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相比,三者在适用法律、索赔程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于是,农民工的事故伤害赔偿问题便被置于工伤赔偿、比照工伤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的夹缝之中,三者似乎都能给农民工提供赔偿法律依据,农民工可根据有利原则进行选择,但又都存在着种种障碍和不确定性。
《社会保险法》第41条首次规定了先行支付制度,即用人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发生工伤事故时,劳动者可要求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根据该规定,如果能够认定农民工与具有合法用人资格的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便可以适用《社会保险法》规定,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向其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显然,这种法律适用的效果会远优于选择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和《一次性赔偿办法》,尤其是在雇主或者非法用工单位不具备赔付能力时。于是,在提起工伤赔偿劳动仲裁或者诉讼时,请求裁判机关认定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寻求适用《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成为大多农民工的诉讼选择。
三、农民工工伤索赔时对相关法律规定的解读与适用
农民工工作时遭受事故伤害,获得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是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须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因此,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主要依据为双方是否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实践中,普遍存在用人单位无书面劳动合同使用农民工的做法。据统计,2005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人数仅占农民工总数的28.7%[10]。即使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调查结果仍显示,大量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仍然偏低。如浙江省总工会督查组2010年上半年在对温州1299家用人单位、共计3.8万劳动者的专项督查中,责令用人单位补签书面劳动合同达2.1万份,占劳动者总数55.2%[11]。无书面劳动合同情形下如何认定用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时,如果具备: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条件的,可认定双方劳动关系成立。但是,该规定最大不足之处在于,仅能用于判定农民工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用工而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时,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实践中,企业的用工形式呈多元化态势,如劳务外包,或建筑行业对工程建设实行层层分包,转包,农民工在包工头的带领下提供劳务活动,以至于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在非法用工单位的指挥监督下提供劳务活动。但这类农民工的工作场所在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场所区域内,其从事的劳动也属于用人单位业务活动的组成部分,并间接受用人单位的监督指挥。劳动过程中发生事故伤害时,由于与用人单位无书面劳动合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只能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或《一次性赔偿办法》规定,由雇主或非法用工单位予以赔偿,与用人单位无关。
为纠正此类规避劳动法法定义务的用工行为,《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但“用工主体责任”为何种性质的责任?其责任承担是否包含工伤赔偿内容?能否据此认定农民工与发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如果承包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但其将工程分包、转包,承接业务的是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主体时,如何处理?规定不详。2013年4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即只要接受转包、分包的主体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承包人就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该规定对承包人工伤责任的承担清晰明确,但是却并未涉及发包人的工伤责任承担问题。两规定的性质为行政部门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法律层次较低,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国务院部门对于具体应用法律、法规或规章作出的解释,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的约束力。因此,其对帮助农民工向用人单位工伤索偿的作用极其有限。《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研报告》中反映的农民工工伤赔偿中,没有一例获得总(承)包公司的赔偿,仅11%获得劳务分包公司赔偿的事实,也印证了这种分析。
与上述两文件的规定相似,《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该规定,发包人、分包人应否对遭受安全生产事故损害的雇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取决于其是否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有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那么,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界定标准应如何把握?上述调研报告中反映我国建筑业广泛实行资质挂靠、层层分包,但农民工在发生事故伤害索赔时鲜有获得总包公司或者分包公司赔偿的事实,表明该司法解释规定在实践中也未能成为农民工工伤维权可依赖的法律武器。
《劳动合同法》第94条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规定曾被学者寄予厚望。例如曾参与起草《劳动合同法》的学者王全兴认为:由发包人作为用人单位对承包人所雇劳动者承担劳动法责任,比由发包人负连带赔偿责任对劳动者更为有利[12]。但是,“个人承包经营”的立法本意是指“企业与个人承包经营者通过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将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权在一定期限内交给个人承包经营者,由个人承包经营者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13]。其实质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权有偿和有期限的让渡经营,目的是为了防止在企业承包经营期间,承包人与发包人相互推诿对劳动者的责任。这与在建筑业中发包人将建设工程违法发包、转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主体完成大相径庭。并且,个人对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的,其因取得合法经营权,也就当然享有用工权,故不存在违法招用劳动者的情形。因此,对在非法用工单位中提供劳务遭受事故损害的农民工,显然难以适用该规定追究发包组织的赔偿责任。
对上述涉及承包用工时劳工事故伤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我国台湾地区的《劳动基准法》第62、63条规定:“事业单位以其事业招人承揽,如有再承揽时,承揽人或中间承揽人,就各该承揽部份所使用之劳工,均应与最后承揽人,连带负本章所定雇主应负职业灾害补偿之责任。”“承揽人或再承揽人工作场所,在原事业单位工作场所范围内,或为原事业单位提供者,原事业单位应督促承揽人或再承揽人,对其所雇用劳工之劳动条件应符合有关法令之规定。事业单位违背劳工安全卫生法有关对于承揽人、再承揽人应负责任之规定,致承揽人或再承揽人所雇用之劳工发生职业灾害时,应与该承揽人、再承揽人负连带补偿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应采用“共同雇主”理论,即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虽然实际上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他们在雇用问题上共同参与决定,如果存在用工企业与劳务输出机构对劳动者的双重管理,则应认为两者存在对劳动者的共同责任,用工企业要么接受法定的责任,要么对劳务输出机构的赔偿能力作出担保[14]。因此,对共同雇佣情形下的劳动者在完成发包事务过程中遭受事故伤害的,发包人、承包人或分包人与劳动者的直接雇主,应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不以相关主体是否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或者是发包人是否存在过错为考量。
四、地方法院、劳动仲裁机构对工伤赔偿适用法律的司法能动
农民工与非法用工单位之间能否建立劳动关系,进而适用工伤赔偿规定,各地法院与最高院的认识视乎并不完全一致。2010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4条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最高院解释为:非法用工主体由于违反工商登记规定,理应受到行政处罚,但行政违法行为不应影响到其民事行为的效力,即便存在非法用工,也应当承认其劳动关系的存在,当纠纷发生时,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用人单位不存在或者无力承担责任时,出资人应当依法予以承担责任[15]。把部分非法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建立的关系认定属于劳动关系,无疑是在劳动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但是,对此类劳动者发生职业灾害时,能否直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该司法解释规定不明。
2011年江苏省高院、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二)》第10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劳动者起诉请求确认与发包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不予支持;但劳动者依据劳动部门作出的工伤结论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请求赔偿工伤保险待遇,并要求发包方与承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予以支持。这是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具体应用的地方操作性规定,即发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以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雇主有无相应的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为判断依据,而以劳动部门是否已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依据。对于不存在承包用工形态的非法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受到事故伤害索赔时,该指导意见规定,由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依据劳动部门作出的工伤结论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按照《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2012年广东省高院、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13条规定,发包单位将建设工程非法发包或者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分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其与发包单位或者承包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不予支持,但社保部门已认定工伤的除外;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94条与《一次性赔偿办法》直接主张由发包单位或者承包单位与实际施工人连带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予以支持。其从宽解读《劳动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也是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第2款关于如何确定发包人、承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具体尺度把握规定。但劳动部门的工伤认定结论是否能作为反证非法用工单位的劳动者与发包单位或承包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有待商榷。在赔偿适用法律上,与江苏类似,不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或《工伤保险条例》。
2006年上海高院《关于通过劳动争议处理途径解决非法用工单位发生事故伤害赔偿纠纷的意见》规定,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赔偿不纳入工伤认定范围,以非法用工单位的出资人作为赔偿责任主体,依据《一次性赔偿办法》及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予以判决。
从上述规定可知,《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所规定的雇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处理方式已被地方法院、劳动仲裁机构所抛弃。
五、农民工工伤维权面临的程序障碍分析
农民工工伤维权难的另一原因是工伤赔偿程序繁琐,耗时长。大多农民工因经济压力和时间成本等原因,要么妥协于用工单位提出的赔偿数额,要么是无奈放弃追偿。
农民工发生事故伤害将面临何种索赔程序?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6条规定,如劳动者就赔偿数额与非法用工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如何理解该规定?是否为:在诉讼程序上应遵循普通劳动争议处理“一裁二审”的程序性规定?还是在事故伤害性质的认定上,应遵循《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认定的程序性规定?或者两程序均为农民工工伤索赔的必经程序?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23条规定:“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工伤认定决定和职工工伤医疗的有关资料。”《一次性赔偿办法》第3条规定劳动能力鉴定按照属地原则办理。因此,工伤索偿的前提条件是须经过劳动能力鉴定程序,而劳动能力鉴定的前提条件则是农民工已获得了劳动部门出具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于是,不论是在用人单位还是非法用工单位,农民工工伤索赔首先必经的程序是申请工伤认定。有学者认为,对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的一次性赔偿,工伤认定程序不是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程序的前置程序和必要条件,伤残人员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后,根据鉴定结果即可向非法用工单位索赔[16]。但实践中,包括江苏在内的大多地方法院、劳动仲裁机构均规定,劳动者申请工伤赔偿的必须持有劳动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仅上海高院规定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赔偿不纳入工伤认定范围,由法院对劳动者伤害性质是否属于工伤予以确认。并且,如果是在用人单位内发生工伤事故的,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两道程序便成为农民工工伤索赔必经的法定程序。
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6条规定,工伤认定,申请人应提交劳动、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农民工无法提交书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往往矢口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虽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条明确把“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纳入劳动仲裁的范围,但同时也使得农民工在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前,不得不首先进行“劳动关系确认”的“一裁两审”程序。有学者认为,工伤认定程序中对劳动关系的确认,只是该程序中的一个环节,不应作为一个独立程序[17]。但是,由于劳动关系的确认涉及伤害赔偿的性质及适用法律的选择,且其确认权归属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因此,难以被工伤认定程序所覆盖。
经过对劳动关系的确认程序后,将开始正式的工伤认定程序。根据《工伤认定办法》规定,此阶段将面临:社保部门15日的资料审核期和15日的受理决定期间;60日的工伤认定期间;20日的工伤认定结论文书送达期间。如果对社保部门的认定工伤结论不服的,当事人可提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虽然工伤认定行政复议已不再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但是,提起工伤认定行政诉讼的,申请人将面临行政诉讼一审、二审两道程序及由诉讼引发的相应法定期间。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对社保部门作出的认定工伤结论,可以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判决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20条规定,工伤认定的职权属于社保机关享有,因此,法院无权通过行使审判权作出有关工伤认定最终结论的判决。由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5条、第16条对“认定工伤”、“视同工伤”、“不属于工伤”的情形已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法院对工伤认定结论存异议时,判决撤销或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依据只能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这时,对工伤认定相关法律的正确解读和对法院司法审查权界限的考量,便成为在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与社保部门互持己见,难以妥协的症结所在,并由此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18]。
工伤认定问题解决后,将进入劳动能力鉴定程序。该程序包括初次鉴定、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等程序。鉴定结果的性质属专家鉴定,根据《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7条规定,劳动者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有异议的,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即不可诉。该程序终结后,劳动者依据伤残等级鉴定结论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用人单位主张主张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如发生拒付,劳动者只能通过诉讼或者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来解决。
尽管对劳动能力鉴定是否必须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特别是对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的劳动能力鉴定是否必须启动劳动关系确认的仲裁、诉讼程序,或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存在较大争议。但是,面对无赔付能力的雇主时,大多农民工往往还是选择将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作为被告提出索赔,于是,劳动关系确认与工伤认定两程序便成为了农民工工伤索赔的必经程序。如需走完工伤索赔全部的程序,耗时将可能会超过1000天,甚至出现了劳动者历经10年维权仍然无法获得工伤赔偿的例子。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恶意利用繁琐的程序来消磨劳动者的维权意志,以逃避工伤赔偿责任,不如说是现行的工伤赔偿制度顶层设计出现了问题,其不仅使劳动者无法及时获得工伤赔偿,同时还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六、农民工工伤赔偿法律规制完善之探讨
综上所述,农民工工伤索赔难主要基于两大问题,一是因“劳动者”身份认定引发的法律选择问题,二是工伤索赔程序中涉及的劳动仲裁、行政、民事诉讼程序交叉问题。为此,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一、劳动法应打破身份、户籍限制,明确将农民工纳入“劳动者”范畴,摈弃以“用人单位”或者以户籍为考量来界定的“劳动者”身份的做法,使农民工群体真正获得工伤保险保障。摈弃“非法用工单位”的提法,以“雇主”来替代现行劳动法使用的用人单位概念,以求最大限度地把各类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保障的范围之内。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所保护的劳动者,是以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取工资为界定标准,而不以与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依据。其《劳工保险条例》围绕劳动者为核心进行立法,依据劳动者所从事的单位、行业以及劳动者的特殊情形进行立法,即使对于无一定雇主或自营作业的劳动者,也通过规定由职业工会代为参保的方式,最大限度覆盖应参与工伤保险的劳动者。
二是改革工伤索赔程序中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劳动仲裁、劳动能力鉴定等诸程序繁琐和交叉问题。例如,可考虑赋予法院享有工伤认定权力。美国《联邦雇员赔偿法》规定,劳工部雇用标准署工伤赔偿项目办公室负责工伤赔偿处理。其对于工伤认定问题作出的决定,性质属于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的,有权上诉至雇员赔偿委员会;对雇员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仍然不服的,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具有重新审查并针对案情直接作出认定判决的权力。美国法律曾赋予行政机关对工伤认定具有最终裁决权,但是法院认为,国会立法不能用行政机关代替法院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实问题作出最终决定,司法权属于宪法规定的法院,法院必须能够审查所有法律与事实问题。工伤认定由于涉及公民基本权益的保护,因此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可以用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对基本事实的认定[19]。与此类似,香港《雇员补偿条例》规定,负责工伤补偿事务的行政机关是劳工处,其作出的工伤认定意见是工伤补偿的前置性程序,但并不形成行政决定,主要从医学角度就案件属于工伤的可能性向雇用双方提供意见,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有异议的,雇用双方可通过法院司法裁判最终解决。
我国理论研究中普遍认为,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仅享有有限司法权,因此,一般不能在判决中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对当事人实体权利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认定[20]。基于此认识,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的法院在地方性的审判指导意见中均规定工伤认定属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不能直接作出工伤认定,未经工伤认定而要求享受工伤待遇的,不予受理。但是,三地法院却选择了把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赔偿案件,及用人单位未办理工伤保险但对劳动者构成工伤无异议案件,规定不纳入工伤认定范围,由法院对事故伤害性质是否属工伤予以确认。由此可见,地方法院对其能否享有工伤最终认定的司法职权,正在进行小心翼翼的探索。但是,如果劳动者要求确认其与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并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保护的话,上述法院的探索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我们认为,劳动法除应扩大工伤保险保障覆盖的“劳动者”范围外,还应实行工伤赔偿案件的司法裁判与工伤待遇的行政给付职能合理分工。即在工伤索赔中,改革劳动争议处理“一裁两审”程序制度,赋予法院享有直接的工伤认定司法裁判权,并规定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根据法院的工伤认定判决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社保部门根据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向劳动者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唯有从实体权利赋予与索赔程序精简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者工伤赔偿难的问题。
[1]王梦婕.公益机构发布建筑民工职业保护调研报告——近九成受伤工人遭遇“工伤拒赔”[N].中国青年报,2012-12-15,(3).
[2]郑功成.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21.
[3]周慧文.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 2007,(6).
[4]黄洁,朱雨晨.工伤维权何时不再难?社会各界冀望《社会保险法》出台破解难题[N].法制日报, 2009-3-19,(4).
[5]曼弗雷德·魏斯,马琳·施米特著,倪斐译.德国劳动法与劳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
[6]常凯.劳动权论[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138-139.
[7]黎建飞.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4.
[8]周长征.劳动法中的人——兼论“劳动者”原型的选择对劳动立法实施的影响[J].现代法学.2012.(1).
[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趋势与战略取向[J].改革.2011,(5).
[10]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情况的研究报告之一—当前农民工流动数量、结构与特点[N].中国劳动保障报,2005-7-28,(7).
[11]姚先国.权利的边界——反思《劳动合同法》[J].经济学动态.2011,(5).
[12]王全兴,黄昆.外包用工的规避倾向与劳动立法的反规避对策[J].中州学刊.2008,(2).
[1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解读与适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73-276.
[14]何小勇.劳务派遣用工的法律规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6).
[15]罗书臻.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杜万华就《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答记者问[N].人民法院报,2010-09-15,(2).
[16]唐慧.在处理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争议中不需要进行工伤认定[J].中国劳动.2006,(1).
[17]陈荣鑫.工伤认定中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权[J].中国劳动.2005,(6).
[18]江苏泰州一起工伤认定陷入循环诉讼怪圈[N].工人日报,2006-09-18,(5).
[19]汤洪源.美国工伤赔偿处理程序—与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工伤赔偿处理程序比较[J].中国劳动.2009,(9).
[20]章志远.工伤认定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J].清华法学.2011,(5).
Legal Regul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on Migrant Workers'Work-related Injury Compensation
HE Xiao-yong
(Law school,Jiangsu Police Institute,Nanjing Jiangsu,210012,China)
Themigrant worker grou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na,but in labor legislationandjudicial practicethisgroupisstill difficulttobefully includedinthescopeof"laborers"inLabor Law.Except for the obstacles of identity definition and labor relations,conflicts and differences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lsoblock migrant workers'work-related injury claims.Labor arbitration,administrative,andcivil litigationofthecompensationprogramexacerbatetheoverlappingproblemof the difficulty of migrant workers'work-related injury claims.Therefore,legislation should clarify the migrant workersintotheregulationrangeof Labor Law,abandonillegal employment unit concept andreformthemode of work-relatedinjury claimfor payment method,givethepower withthecourt tocognizework-related injury directlyandsolvetheproblemsofmigrantworkers'work-relatedinjuryclaims.
migrantworkers;illegal employmentunit;laborrelations;work-relatedinjury;applicationof law
D922.5
A
1674-828X(2014)01-0039-08
(责任编辑:郭鹏)
2013-07-14
何小勇,男,江苏警官学院法律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民商法、经济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