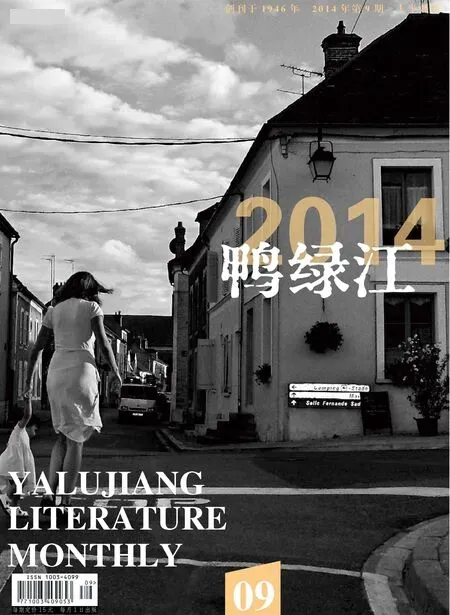“北2830”海湾在涨潮
2014-02-12孙春平
孙春平
理论
“北2830”海湾在涨潮
"BEI2830"HAIWANZAIZHANGCHAO
孙春平

孙春平,满族,195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现居沈阳。著有长、中、短及小小说作品多篇部,作品曾获骏马奖、东北文学奖、辽宁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奖、金麻雀奖等奖项。另有影视剧编剧作品《爱情二十年》《金色农家》等多部集。
“小说北2830”文学社成立已经七年多,快接近八年抗战的时间了。作为“顾问”,在这七年多时间里,我曾多次“顾”过这些朋友的稿件,当然,读后也“问”过。坦率地讲,以前读“北2830”的稿件,有期待,也有遗憾,欣喜也有过,但不多。今年,《鸭绿江》杂志6期和9期分别为“北2830”开了专栏,再读这些朋友的稿件,感觉大不一样了。“北2830”海湾已在涨潮,而且涨势明显,这确是令人欣喜的事情。要知道,涨潮和水面上陡然掀起的一两朵浪花不同。浪花随风而来,虽漂亮,但转瞬即逝,不会留给人太深的印象。潮水涨起来就不同了,虽不动声色,但水势却带着能量,可以载起舟楫,并使船舶扬起风帆远航。
总体上看,“北2830”朋友们的创作风格还是比较相近统一的,都很关注现实,贴近现实,当属现实主义流派。时下,波涌在这个流派中的作家和作品很多,要想有所突破与超越,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中给出与他人不同的东西。创作嘛,那个“创”字,就是强调前人(包括自己)未曾有过的,或题材,或结构,或语言,或角度,哪怕只有一点点创新,就应该为之击掌叫好。而一些写作多年的作者,比如老朽我辈,拿出一篇新作品,编辑看过,说到底是老手,写得很圆熟,留下待发吧。一声“圆熟”,不要以为是表扬,而是批评。一个老手,很会编、很会写了,挑不出什么毛病,但也看不出什么新意,却之不恭,留用算给了面子;就像一头磨道的老驴,戴着眼蒙顺着那个圆圈不紧不慢地走下去,多一圈少一圈的,又能怎么样呢。
这些作品中,我比较看好的是张驰的《过年》。爆竹声声中,“那人”奔波在回家乡的路上。在列车上,他遇到了于哲,主动上前搭讪,人家却不想理睬;在站前广场上,他看到于哲坐进前来接站的史鸣的小轿车,自己则钻进出租车司机肖海军的汽车;在足疗店里,面对按摩女白玲玲,还主动捧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一路上遇到的这几个人,都是昔日的老同学,即使他认得人家,人家也认不出他了。通篇,“那人”连个名字都没有,可他却是作品的主角。读过这篇似乎并没有什么故事与情节的作品,让人感觉到的是一言难述的苦涩。作者是在描述过年返乡人的情感吗?还是为曾经的失足人抒发内心的悔恨与惆怅?或者,他在描述着虽是老同学却各为不同阶层人的当下生活状态?都是,或者都不是。好作品就应该是一言难尽的,在看似并无传统的起承传合的叙述中,我们读到了作者别一番的匠心。
写惯了市井人物的少梅今番也要另辟蹊径了。《饥饿的女儿》当然还应属现实主义流派,但作者却为她蒙上了一层荒诞的或曰象征的色彩。男友黄为的突然离去(作品没说他是辞世还是离家出走)是象征,女主人公宁夏吃包括苍蝇在内的昆虫,吃纸屑,吃玻璃碎片,那肯定也是一种象征,因为人类是不可能以那些东西果腹生存的。宁夏经营着一家时装店,衣食不虞,这应该不是象征。于是问题便来了,当象征着精神依靠(黄为)的某个人物或某种信仰丧失之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它将怎样充填突然出现的巨大精神空虚,可以随随便便抓来什么就往空荡荡的身体里充塞吗?作者写给我们的故事似乎很荒诞也很可笑,但提出的问题却严肃而深刻。
潘洗一直把他的小说背景放在玉城,那是个亦真亦假的小城,他的很多作品也多是书写当下那种急切的欲望和快餐式情感。但这一次,潘洗一改套路,把故事的时间放在二十多年前。在《亲爱的给我写信吧》中,“我”是一个刚走出校园参加工作的青年。那个年月,生活条件工作环境都很艰苦,但在苦涩中“我”却有着对甜蜜爱情的深切期待与憧憬。他每天最惦记的事便是女友的来信,他把自己大部分业余时间也多用于给女友斯漪写信上。“从秋天到冬天,一共持续到春节后,我给她总共写了三十七封信……总字数在十三万字左右。”这就是那个年月年轻人的爱情,有点像《庄子》中“尾生抱柱”的典故,“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在这篇作品中,潘洗还揉进了发生在当地的另两起关于爱情的故事。这些故事讲给当下的只顾荷尔蒙冲动的人们,引来的可能是嘲笑。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时下的男女可能只需按动几下电脑或手机键号码,就可把性爱对手带到宾馆的床上,甚至连对方姓甚名谁都不需知道。但恰恰是这种快餐式爱情,麻醉了人类主导爱情的神经。反思生命与爱情,对于潘洗的创作,这篇小说或许也有着另辟蹊径的意义。

在两期专栏的七篇作品中,万胜的《铁马桥》可谓独树一帜,他在写六七十年前的抗战。一个刚四十出头的人,书写近百年前的故事,况且那段往事与作者当下的生活有着不言自明的巨大距离。应该说,是有着相当大难度的。万胜一改以前写现实生活的语言风格,笔触从容老到,让人感觉历史的沧桑感迎面扑来。作品中的故事悬念丛生,步步紧扣,意到则止,给人想象的留白也恰到好处。其中的人物无论是民间抗战义士(或曰土匪头子)陆文呈,还是他的管家随从侯三,还有那个表面上是茶店东家实则为日本间谍的庞老板,都写得栩栩如生。
我下面要说的可能对万胜这篇小说就是离题之语了。《铁马桥》结尾处有这样一笔:“走吧,别让抗联的杨司令等急了。”这个杨司令,估计许多人都会想到抗日英雄杨靖宇。但没有这一笔行不行呢?写杨靖宇当然没错,但抗战驱虏的好汉是否只有杨靖宇?时代发展到今天,历史唯物主义早已不被人们仅仅挂在嘴上,而是深入内心。中国人民深信,只有尊重历史的民族才是真正自信、强大的民族。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民心与力量的凝聚,张灵甫、戴安澜、孙作人等抗日将领虽非共产党人,但他们为民族为国家做出的功绩与牺牲理应受到后人的尊敬与纪念。数年前,我去黑龙江林区采访,当地朋友给我看过几盘新录制电视剧的带子,说未得批准公开播放,只能私下里看看了。那个剧的主人公是座山雕,讲述的是他抗战初期如何变卖家产购买武器蓦集民众打鬼子的故事。据朋友们说,这个座山雕是真实的,当年打鬼子绝对够狠,至于后来投靠国民党跟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军前身)作对,那则是另一回事了。这让我又想起前两年央视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中国地》,剧中的主人公王老凿也是有原型的,就在我的老家辽西。解放初土改时王老凿因是地主被镇压,数十年后,他的形象却在荧屏上重新站立起来。因为他在民族危亡时刻,曾有过与日寇拼死抗争的英雄壮举。让历史回归到真实的本来面目,不仅仅是写作者,我们整个社会都应有这个清醒的理性。有了理性的认识,我们下笔时才不会有戴着脚镣踏进舞池的滞涩。

言归正传。说到对民间生活的熟悉和对人物、细节刻画的准确生动,“北2830”的这些作品中,可能当属毕雪飞的《倔强的槐花》了。毕雪飞长期生活工作在县乡,对笔下的人物可谓熟悉到骨子里。但也许正是这种熟悉,影响了她对生活的发现。在创作上,我有一个观点,要与熟悉的生活拉开一些距离,才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遗憾。我的这个观点有些朋友不赞成,但我仍要坚持。毕雪飞的这篇小说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人物、情节、细节、语言都真实得纤毫毕现,那种娶了媳妇不管娘的故事在中国乡间,可能数百年前就有。但作为写作者,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社会转型期,又发现了一些什么呢?须知,发现、求新,才是我们写作者最应孜孜追求的目标。如果只求真实,时下人人手里可能都有照相机(手机),尽管按下快门好了。但那种真实绝大部分并不是摄影艺术作品。我记得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一种文学如果只满足于‘描写事物’,满足于由事物的轮廓和表面现象所提供的低劣梗概,那么尽管它妄称现实主义,其实离现实最远。这样一种文学最使人感到思想贫乏,感到伤心……”我把这样一段话复述出来,不仅是说给毕雪飞,也说给更多的文学朋友,当然,也说给我自己。
其实,毕雪飞的《倔强的槐花》也并非完全没有发现。作品的结尾处,雪飞写到了七婶和老八叔的夕阳恋。在传统观念仍很顽固的乡间,这种同宗之间的叔嫂恋,要想冲破传统礼数的牢篱肯定很难很难。很可惜,作品中老八叔出现得太晚了,关于两人间的感情用笔也很是吝啬,结尾那一笔更写得过于匆忙。如果正面书写两人的夕阳恋,把家里的那些揪心事只作为两人故事的背景,也许作品就别有一番滋味了。
潮汐来兮,积蓄着水势,也积蓄着能量。我们有理由期盼,终有一天,潮水会托载起2830号文学之舟(最好是巨轮),出海远航!
责任编辑 李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