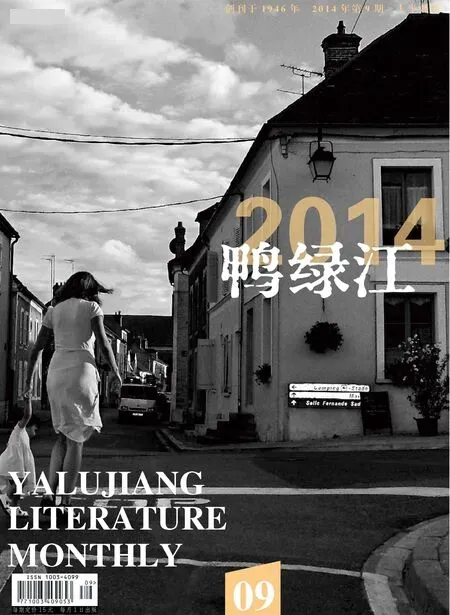在暴雨中(组诗)
2014-02-12陈先发
陈先发
诗歌
在暴雨中(组诗)
ZAIBAOYUZHONG
陈先发

陈先发,1967年生,安徽桐城人。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著有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前世》,长篇小说《拉魂腔》诗集《写碑之心》等。曾获十月诗歌奖、十月文学奖、1986 年-2006年中国十大新锐诗人、2008年中国年度诗人、1998年至2008年中国十大影响力诗人、首届中国海南诗歌双年奖”、复旦诗歌特殊贡献奖、首届袁可嘉诗歌奖等数十种奖项。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腊文等多种文字,亦被选入多所大学的教材与辅助读物。代表作品有短诗《丹青见》《前世》,长诗《口腔医院》《白头与过往》等,长篇哲学随笔《黑池坝笔记》等。诗歌主张:“本土性在当代”与“诗哲学”。
忆顾准
让他酷刑中的眼光投向我们。
穿过病房、围墙、铁丝网和
真理被过度消耗的稀薄空气中
仍开得璀璨的白色夹竹桃花。
他不会想到,
有人将以诗歌来残忍地谈论这一切。
我们相隔三十九年。
他死去,只为了剩下我们。
这是一个以充分蹂躏换取
充分怀疑的时代。
就像此刻,我读着“文革”时期史料
脖子上总有剃刀掠过的沁凉。
屋内一切都如此可疑:
旧台灯里藏着密信?
地上绳子,仿佛随时直立起来
拧成绞索,
将我吊死。
如果我呼救,圆月将从窗口扑进来堵我的嘴。
逃到公园
每一角落都有隐形人
冲出来向我问好。
要么像老舍那样投身湖下
头顶几片枯荷下下棋、听听琴?
可刽子手
也喜欢到水下踱步。
制度从不饶恕任何一个激进的地址。
1974年,这个火热的人死于国家对他的拒绝
或者,正相反——
用细节复述一具肉身的离去已毫无意义。
1975年,当河南板桥水库垮坝
瞬间到来的二十四万冤魂
愿意举着灯为他的话作出注释。
我常想
最纯粹的镜像仅能在污秽中生成,而
当世只配享有杰克逊那样的病态天才。
忆顾准
是否意味着我一样沉疴在身?
但我已学会了从遮蔽中捕获微妙的营养。
说起来这也不算啥稀奇的事儿
我所求不多
只愿一碗稀粥伴我至晚年
粥中漂着的三两个孤魂也伴我至晚年
养鹤问题
在山中,我见过柱状的鹤。
液态的,或气体的鹤。
在肃穆的杜鹃花根部蜷成一团春泥的鹤。
都缓缓地敛起翅膀。
我见过这唯一为虚构而生的飞禽
因她的白色饱含了拒绝,而在
这末世,长出了更合理的形体
养鹤是垂死者才能玩下去的游戏。
同为少数人的宗教,写诗
却是另一码事:
这结句里的“鹤”完全可以被代替。
永不要问,代它到这世上一哭的是些什么事物。
当它哭着东,也哭着西。
哭着密室政治,也哭着街头政治。
就像今夜,在浴室排风机的轰鸣里
我久久地坐着
仿佛永不会离开这里一步。
我是个不曾养鹤也不曾杀鹤的俗人。
我知道时代赋予我的痛苦已结束了。
我披着纯白的浴衣,
从一个批判者正大踏步地赶至旁观者的位置上。
夜间的一切
我时常觉得自己枯竭了。正如此刻
一家人围着桌子分食的菠萝——
菠萝转眼就消失了。
而我们的嘴唇仍在半空中,吮吸着。
母亲就坐在桌子那边。父亲死后她几近失明
在夜里,点燃灰白的头撞着墙壁。
我们从不同的世界伸出舌头。但我永不知道
菠萝在她牙齿上裂出什么样的味道。
就像幼时的游戏中我们永不知她藏身何处。
在柜子里找她
在钟摆上找她
在淅淅沥沥滴着雨的葵叶的背面找她
事实上,她藏在一支旧钢笔中等着我们前去拧开。没
人知道,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但夜间的一切尽可删除
包括白炽灯下这场对饮。
我们像菠萝一样被切开,离去
像杯子一样深深地碰上
嗅着对方,又被走廊尽头什么东西撞着墙壁的
“咚、咚、咚”的声音永恒地隔开。
京郊崂山记
连猛虎也迷恋着社交网络
更遑论这些山里的孩子
爱幻想让他们鼻涕清亮
整个下午,夺我们手机去玩僵尸游戏
滂沱的鼻涕能搭起好几座天堂。
而老人们嘲笑我们这支寻虎的团队。
他们从青檀中榨出染料
令我们画虎
画溪上的鸟儿,揣了满口袋的卵石而飞得缓慢。
画村头的孕妇,邋遢又无忧。
画那些柿子树。当
复杂的脑部运动创造出这群山、小院和颜色。
面赤、无须的柿子像老道士前来问候
“你好吗”——
山里太冷了。我无以作答。废玉米刮痛我们的神经。
我能忍受,早年收获的那些
有少数的一部分仍在绽放
一口大锅中,浮出衰老的羊头。
孩子们可等不及了。
而“我们吃掉的每一口中,都焊接着虚无”
在臆想的语法中姑且称这里为崂山。
饭后的月亮越来越大
我们四肢着地,看鼻涕的群山沸腾。
孩子们一直嘲笑直至
暮色剥去我们的人形。
入殓师
我的朋友:乐队大提琴手
其实只想做个入殓师。
蛰伏于金碧辉煌的舞台中央
在众多乐手间
他土黄、常见的脸算是个障眼法:
从中苦练着入殓的技艺。
D 弦是缓缓涂抹于死者面部的彩绘?
而G 弦
又像是隔世的交谈:
(当代浮躁的葬仪省略了这个环节)
A 弦上的错觉,正努力
撬开台下已紧闭的耳朵。
他记得小时候练琴
穿过杂乱的小巷
桐花满地
从低矮木檐下涌来那些模糊的哭声。
瓦砾之上
是流云磨砺的虚空
也是我们终被烧成灰烬的虚空。
他看见自己蹲在那里
用油漆描绘一具具快速冷却的身体
绘他的耳廓
绘他C 弦上曾经柔韧的脚踝
绘他曾情欲蓬勃的阴茎。
“我能在另一个上醒来?”
为了两种技艺的转换
他站在紧紧拉起的猩红色天鹅绒大幕之后。
旋转的灯光熄掉
像从不承认,也绝不依赖一个真正的旁观者仍能独活下去一样……
在暴雨中
我喜欢注视被暴雨击溃的
四处奔逃的人群
头顶公文包、缺少权谋的
底层官吏。双手紧扣着鱼腮的小贩子
一手攥着红领巾、一手捂着胸的
女学生和她病虎一样的妈妈
我死去多年的老父亲
也突然现身在暴雨中
被铸成泥俑的秦汉士卒,塑成
蝴蝶的那些女人也愤怒地恢复原形
在银白又急遽的雨点中,广播播放各种警告
广播中住着将咖啡一饮而尽的闲人
我从窗帘后看去。也从镌刻为书页被摞入
柜子的旧版中看去——
当穹顶慢慢地合拢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四分五裂的脸
失去的四两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火中莲、山头浪?”
褒禅山寺的老殿快塌了,而小和尚唇上毫毛尚浅。
“今天我买的青菜重一斤二
洗了洗,还剩下八两。”
我们谈时局的危机、佛门的不幸和俗世的婚姻
总觉得有令人窒息的东西在头顶悬着。
“其实,那失去的四两,也可以炒着吃。”
哦,我们无辜的绝望的语言耽于游戏——
“卖菜人两手空空下山去”。
似乎双方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
当然,炒菜的铲子也可重建大殿。我们浑身都是缺口。
浑身都是伏虎的伤痕
责任编辑 王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