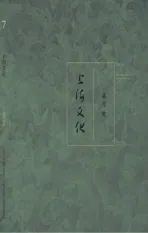在缅甸阅读奥威尔*
2014-02-12艾玛拉金王晓渔
艾玛·拉金 王晓渔 译
在缅甸阅读奥威尔
艾玛·拉金 王晓渔 译
在缅甸有人开玩笑说,奥威尔不是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小说,而是写了三部:由《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组成的三部曲
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以他在远东的经历为基础,但使他跻身20世纪最受尊敬和最有预见作家行列的是他后来的小说,如《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
命运特别神秘之处在于,这三部小说实际上讲述了缅甸的近期历史。这种联系开始于《缅甸岁月》,小说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1948年缅甸从英国独立不久,军事独裁者就将国家隔绝于世,启动“具有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缅甸建设成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奥威尔的《动物农庄》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在这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如何失败的寓言小说里,一群猪推翻了人类农场主,又毁灭了农庄。最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描述了一个恐怖并且缺乏灵魂的反面乌托邦,精确地描绘出今日缅甸的图景,这个国家由世界上最野蛮和最顽固的独裁者之一统治。
在缅甸有人开玩笑说,奥威尔不是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小说,而是写了三部:由《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组成的三部曲。
我的朋友们把我介绍给同样对奥威尔有兴趣的缅甸作家和历史学者。没过多久,我开始组织起一个非正式的奥威尔读书会。
那是很小的群体——这是必要的,以免招致当局的注意。未经当局允许的民众集会严格地说是非法的,包括外国人在内的集会会招致更多的注意。我们的第一次聚会选在一个有着亮蓝色雨篷的喧闹茶馆。我们选择了位于角落的桌子,旁边是吵闹的电视机,肥皂剧的哭哭闹闹掩盖了我们的声音,以免被不速之客听到。我们总共是四个人。扎扎雯,这名二十岁出头的女大学毕业生想提升她的英语,阅读任何可能获得的英语读物,特别偏爱《读者文摘》杂志(“因为里面的故事经常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她说)。小组里的两名男性是年轻的作家、诗人貌果和退休教师屯林,后者的最大爱好是开玩笑和阅读乔治·奥威尔。
我们的第一次聚会准备讨论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在政府眼中这是一个无害的话题,虽然《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被禁,但是你只需要大概一美元就能买到盗版的英文《缅甸岁月》。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必须点杯茶。
茶是缅甸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曼德勒以有全国最好的茶馆而著称。它们大都是露天的,撑出高高的雨篷或者遮阳伞,小木桌和小凳子一直摆到人行道上。每家茶馆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每个人都垂涎明蒂哈连锁茶馆的咖哩羊肉泡芙。我喜欢旅馆附近转角的茶馆,那里随叫随烤的印度烤饼和豌豆汁是我的早餐主食。在曼德勒茶馆的生活有着让人愉快的节奏,可以整天沉浸其中。早晨,周围是成排的自行车和摩托车,顾客在上班之前喝下一天里的第一杯茶。午饭时间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茶馆有些慵懒和安静,年轻的服务生趴在桌子上打瞌睡,就连他们头顶的苍蝇也在闷热中放慢了盘旋的速度。傍晚和黄昏,当服务生忙于茶和点心的订单时,节奏开始快起来,茶馆再次恢复聊天的喧闹。
但是,缅甸茶馆并不像第一印象那样简单。聊天的话题,会从当年凤梨的昂贵价格到茶馆茶叶的质量到爱情、文学,当然还有政治。引发1988年起义的导火索是茶馆里的一次争吵,茶馆被军事当局视为反政府行动的潜在温床。政府暗探通过窃听对话或者桌边的流言蜚语搜集情报,那些流言蜚语被称为“茶馆里的蒸汽”。因此,你必须小心翼翼地选择座位。当一个缅甸人进入茶馆时,他或者她总是立即若无其事地扫视一下顾客。
奥威尔理解茶的神奇力量。他写道,一杯好茶可以让你明察、勇敢和乐观。他宣称唯一的茶道是浓茶并且不放糖,最好是蒂夫茶包。缅甸人同样对茶非常讲究,一个茶馆的名声建立在满足每个人的个性要求上。配上炼乳的茶仿佛浓厚的蜂蜜,可以再搭配乌龙茶。在每张桌子的中央都有一瓶这种清茶,《缅甸岁月》里的反传统女主角伊丽莎白,抱怨它的味道像土一样。为了给《缅甸岁月》讨论助兴,屯林和我点了微甜的浓茶,貌果点了加奶和加糖的茶,扎扎雯点了加奶和不要太甜的茶。
奥威尔理解茶的神奇力量。他写道,一杯好茶可以让你明察、勇敢和乐观
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这个临时的奥威尔读书会对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有何看法。在我看来,《缅甸岁月》是一本让人绝望却又精彩至极的书。它讲述了约翰·弗洛里的故事,这名英国木材商人在1920年代居住于上缅甸的偏远山区。弗洛里挣扎于两种身份,既要坚持正人君子式的绅士风范,这是他所在的英国管理阶层的社会要求,同时又被身边缅甸人的异域风情深深吸引。他观看皮乌,这是由流动剧团表演的丰富多彩的缅甸街头话剧。他游荡于带有刺鼻的“大蒜、鱼干、汗水、灰尘、茴香、丁香、姜黄”气息的集市。他在酒吧畅饮不冷不热的金汤力打发夜晚,因为冰块还没有从曼德勒的冰工厂运来。他通过沙沙的留声机听那些老唱片,打桥牌,抱怨无法忍受的炎热和同样无法忍受的当地人的无礼。
作家貌果若有所思地搅拌着他的茶,声称发现了《缅甸岁月》的无礼。“奥威尔蔑视缅甸人民,他不喜欢我们”,他一边说一边将桌子中央瓶子里的清茶倒入四个小陶瓷杯,每人一杯。确实,书中的缅甸人物有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弗洛里的缅甸情人放荡不羁并且铤而走险。他的仆人溜须拍马,一个腐败的缅甸地方法官试图以敲诈勒索的方式进入只有英国人才能加入的俱乐部。貌果向我们展示了一篇最近由缅甸学者撰写的奥威尔评论。这篇文章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出发点,提出一个理论:西方人无法按照东方和东方人自身的方式观看他们的文化和人民,只是把他们看成西方的创造物。如果东方只能通过西方的观念棱镜被观看和被解释,就注定了它会被描述成未开化的、不近情理的,缺乏法律和秩序的。貌果说奥威尔的《缅甸岁月》跌入了这个陷阱,他选择到东方,是为了在一群没有教养的土著中成为被尊敬和有教养的那一个。他认为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只有两种人:主人和奴仆——白人总是主人。
奥威尔曾经写过,他成为作家的一个潜质是,能够面对不快的事实:他认为他能够说出他所看到的真相,不管那些真相是如何残忍和让人尴尬
刚刚毕业的扎扎雯,同意这个观点。小说以主人公弗洛里的自杀而告终,弗洛里是一名同情缅甸人的英国人,他的自杀说明那些不识时务者无法生存。她总结:“奥威尔坚持英国道路是唯一的道路。”
开放式的厨房区域一阵手忙脚乱,炭火上的水壶沸腾了。两个年轻的服务生用湿抹布拿起水壶,把茶倒进大锡桶。泡茶师傅是一名上了年纪的男人,他的将军肚把柠檬黄色的背心撑得满满的。他逐份地把茶和炼乳调配在一起,娴熟地操作着两只瘪瘪的锡罐,倒着奶油调味品。茶馆服务生大声地把顾客的偏好告诉他(“两杯加奶加糖!”或“一杯微甜!”),师傅将调好的茶倒入等候的杯子中,它们立即被分送至店内各处的顾客。当上茶的服务生们从我身边飞奔而过,我能够闻到新鲜泡出的沁人心脾的奶茶味道。
我请求为奥威尔做个辩护。奥威尔曾经写过,他成为作家的一个潜质是,能够面对不快的事实:他认为他能够说出他所看到的真相,不管那些真相是如何残忍和让人尴尬。在《缅甸岁月》里,奥威尔只是描绘了一幅他在缅甸所见所闻的风情画。并不是奥威尔不喜欢缅甸或缅甸人,我说:他不喜欢的是体制。他在谴责一种使好人——包括缅甸人和英国人——作恶的政治结构。
然而,退休教师、自认奥威尔铁杆粉丝的屯林,听不进任何一句反对英国的话。六十四岁的他出生于英属缅甸时期,在曼德勒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依然记得每一位教师的姓名。他曾经向我展示过一张泛黄的女教师照片——穿着平底鞋的朴素的女士们,头发在后面扎成紧紧的圆发髻。他甚至记得在学校写过的散文标题(以“在榕树下”为题写一篇五百字的文章)。在他眼中,英国不太可能,也不会做过什么错事。“在英国统治下我们生活得很安宁。”他曾经告诉我:“一名十六岁的女孩可以独自从铁路线最南端的毛淡棉旅游至最北端的密支那,没有什么危险。英国照顾民众。我们有一个安稳的生活。每个晚上我们都能安心入睡,不用担心看不到明天。”
有那么一些不自在的瞬间,我们都盯着自己的茶杯,因为互相之间无法说服而感到不快。街上的一些事情吸引了我,传来一阵刺耳的嘎嘎声。我向茶馆的入口看去,在炫目的阳光下一名路过的小贩吹着玩具喇叭。他的肩上挂着一个网兜,装着粉红色足球,在热浪中轻轻地摇晃着。
茶过三巡,我们的交谈意外地转向狗。在《缅甸岁月》的结尾,弗洛里在自杀前,将惊恐的黑色可卡犬弗洛拖进卧室,用手枪打爆她的头。屯林深情地回忆英国人如何爱狗。二战期间,他说,很多英国人在日军占领之前射杀了自己的狗,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把它们留给敌人。他描述一部从朋友的卫星电视上看到的关于英国犬的纪录片,“在探索频道我看到许许多多狗,他们吃着美味,皮毛经过洗梳”。他说着,因为其中的荒谬忍不住地笑起来:“在英国你过着狗的生活,也会胜过在缅甸你过着人的生活。”
在1988年的风波之中,一个神奇的传说在缅甸四处传播。它讲述了一个时时处在恶龙威胁之下的小村庄。每年,这条龙都会要求村庄献祭一名童女。每年村子里都会有一名勇敢的少年英雄翻山越岭,去与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当又有一名英雄出发,开始他九死一生的征程时,有人悄悄尾随,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龙穴铺满金银财宝,男子来到这里,用剑刺死龙。当他坐在尸身之上,艳羡地看着闪烁的珠宝,开始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直到他自己成为村民惧怕的龙。这个传说的寓意,与奥威尔的《动物农庄》相似。
《动物农庄》是唯一一本被翻译成缅甸语的奥威尔著作——那是在1950年代,军方控制政权之前。译者是已故的德钦巴当,他是在缅甸历史和文学中深孚众望的人物。缅甸语中的“德钦”是主人的意思,被缅甸人用来称呼英国人。巴当是德钦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这场运动反对殖民政府,寻求独立,运动成员敢于把“德钦”冠于名前。毫无疑问,如果奥威尔知道他的著作由一名领衔反对英国统治的异议者翻译,会乐观其成。这名异议者因为在寄信时将乔治五世的邮票挑衅地倒贴在信封上,一度被英国人关进监狱。
如果奥威尔知道他的著作由一名领衔反对英国统治的异议者翻译,会乐观其成
德钦巴当翻译《动物农庄》的时候,将故事改编成缅甸背景,并且取了一个更有诗意的标题《四条腿的革命》。在《动物农庄》里,一群农场里的动物决定推翻人类主人,自己管理农场(在德钦巴当的书里,庄园农场的琼斯夫妇被改编成因马宾农场的吴达高和杜欧莎)。领导革命的猪群,有着平等主义乌托邦幻想,试图摆脱暴虐的人类。但是,当权力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他们的理念慢慢被遗弃,他们变得残忍而且贪婪。他们颁布命令宣称只有猪才能吃果园里的苹果(他们声称这是猪脑必须的营养),他们豢养了一群恐怖的狗看管农场里的鸡群、羊群、牛群、马群。猪群继续了他们推翻的人类的奢侈生活——睡在农场房屋里,畅饮威士忌——其他动物死于过度劳动和饥饿。奥威尔《动物农庄》的原型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斯大林对苏联农场恐怖的强制集体化,这导致数百万农民死于非命。我把这部作品看做奥威尔关于缅甸历史无心插柳的三部曲的第二部。
那就是我们在缅甸的《动物农庄》里不得不做的事。整个国家都像那些驴子一样,被迫戴上绿色眼镜
缅甸社会主义实验的悲剧开始于1962年,军方领导奈温夺去了英国撤离之后的民选政府的权力,建立了他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在军事政变期间,国家陷入混乱。二战期间,缅甸是盟军和日军的主要战场,国家的基础设施基本被摧毁。一支共产党军队发起战争试图推翻政府,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试图武装寻求独立。许多和我交谈过的老人记得,当军队重新获得对政权的控制,他们如释重负。但是,如同《动物农庄》里的猪群,局势慢慢变得明朗,奈温并非仁慈的领袖。他启动了所谓“具有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种让人亢奋同时又具有毁灭性的马克思主义和佛教的混合。所有其他的政党被宣布为非法,奈温的反对者被捕入狱。所有的民营商业被宣布为国家财产。许多居住在缅甸的外国人——大都是印度和中国商人——被查抄资产,当这个国家开始闭关自守时,他们纷纷主动逃离或者被迫流亡。没有商业经验的军人,开始控制缅甸的工业和农业。不久,他们就耗尽了国家的外汇储备,无法进口必需品——从机器的备用零件到牙刷。商店的货架迅速被扫荡一空,人们不得不为了限量供给的食用油和大米排成长队。奈温和他的军队将缅甸——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变成不毛之地。经过奈温二十五年的统治,1988年起义前的一年,联合国宣布缅甸是世界上最欠发达的国家之一,并列的十个其他国家大都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在曼德勒,当我同奥威尔读书会讨论《动物农庄》时,开朗的退休教师屯林占据了发言的大部分时间。正如他所说,他亲历真实版的《动物农庄》。屯林把奈温统治时期称为“戴着绿色眼镜的时期”。透过绿色眼镜看事物,他解释说,就是看到一件不好的事情,却被迫把它想为好事。这个说法来自一段神奇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和炮弹摧毁了缅甸的稻田和种植园,日军最终占领这个国家,农民发现很难种出可以食用的作物。甚至农场的牲畜和运货的马匹也拒绝食用干枯的谷物,因为它们呈现出反常的白色。日军担心在上缅甸崇山峻岭中运输军火的驴子会忍饥挨饿,想出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法。他们制作了绿色玻璃的眼镜,把眼镜架缠绕在驴子的耳朵上。“驴子看到谷物是绿色的,高兴地进食”,屯林解释:“那就是我们在缅甸的《动物农庄》里不得不做的事。整个国家都像那些驴子一样,被迫戴上绿色眼镜。”
知道屯林喜欢笑话,我讲了一个从缅甸语老师那里听到的关于奈温昏庸统治的笑话。一名士兵住在仰光茵雅湖畔的临时营房里,与奈温的宫殿式官邸相隔不远。一次午饭时间,他来到湖边看看能够抓到什么可以当做午餐。他钓到一条又大又肥的鱼,高兴地把它扔到水桶里,带回驻地。他决定切些番茄和洋葱,做份咖喱鱼。但是,他在柜橱里寻觅,发现没有番茄,也没有洋葱:柜橱空空荡荡。“没关系”,他想,“我可以用油炸鱼——或许那样味道会更好”。但是,当他寻找食用油的时候,看到瓶子是空的。“我有个主意”,他想了想,“我可以在炉子上烤鱼,虽简单却美味”。但是,他去炭箱取木炭,看到炭箱同样空空荡荡,没有木炭。最后他意识到最好把鱼放生,继续忍饥挨饿。他回到湖边,将依然活着的鱼扔回水里。鱼儿高兴地摆着尾巴跳起来,欢呼:“奈温万岁!”
屯林以前听过这个笑话,他再次捧腹大笑,提醒我奥威尔曾经写到过政治幽默:“每个笑话都是一次小型的革命。”
讨论小组中的扎扎雯,大学刚刚毕业,太过年轻以至对奈温时代或1988年起义没有记忆。但是《动物农庄》里的一句话对她有特别意义:“革命之后会有糖吗?”她记得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的父亲这样喃喃自语地反问,直到上周读到《动物农庄》,她才意识到那句话出自奥威尔书中时髦的白色母马莫丽。“我以为它们已经清醒”,她谈到《动物农庄》里的动物,“当母马莫丽询问革命之后有没有糖,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
1950年代《动物农庄》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在缅甸并不受欢迎。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领袖具有左翼倾向,认为这本书是对他们向往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美国大使馆印刷部分章节作为反共宣传,这本书的命运似乎由此确定。资助翻译的社会团体必须免费赠送以消化压仓库存。但是多年以后,人们开始重读这本书,他们发现与自己历史的相似性。我遇到一位大学讲师,她告诉我她试图将《动物农庄》列入英国文学专业的课程大纲,但是当局告诫她删除:这本书与缅甸正在发生的一切过于类似。几年前,英国广播公司缅甸语节目播放《动物农庄》的连载,此后的几个星期,屯林告诉我,曼德勒的茶馆都在议论,缅甸自己的领袖如何与那些动物性格一一对应。能把民主领袖昂山素季,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夫人”比作流亡的猪类革命者雪球吗?奈温将军是哪头猪?他是那头专横同时预见到自己暴死的老猪“少校”吗?(但愿如此)或者他是越来越强大同时也越来越神经错乱的古怪统治者拿破仑?(可能是)
他再次捧腹大笑,提醒我奥威尔曾经写到过政治幽默:“每个笑话都是一次小型的革命。”
奈温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他是以离群索居而著名的统治者,有着一张出言不逊的嘴,有许多次婚姻和迷信强迫症。他对命理学一知半解,缅甸为此承担了很多戏剧性后果。1987年,奈温废除部分货币,代之以面额四十五缅元和九十缅元的新币——每个面额都可以被九(一个占星术中的幸运数字,是将军的最爱)除尽。人民少得可怜的积蓄一夜之间被清扫一空,几无剩余,一年之后他们在1988年起义中走上街头。
2002年12月,奈温死于仰光湖边公馆,时年九十一岁。那是一个在缅甸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当时我在仰光。奈温自从1988年从政府辞职,很少在公共场合出现,许多分析人士推测他在去世时已经失去了所有政治权力。一场高度公开的审判显著说明了这一点,他的女婿和几个外孙因为涉嫌密谋推翻丹瑞大将被判处死刑。在国营媒体中,唯一提及奈温死讯的是《缅甸新光报》末版一则短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讣告。整个事件被精心控制,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奈温的遗体在他去世的当天下午就被秘密火化。我注意到他去世的那个晚上,仰光的军人多了一些,一些茶馆比往常提前歇业。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迹象能够看出缅甸铁腕统治者的离去。我问扎扎雯如何看待奈温之死的象征性意义。“没有什么”,她说,“什么也不会因为他的死亡而改变。他的死亡无足轻重。不会改变什么”。她或许是正确的:我注意到即使是在奈温死后,人们在茶馆依然不习惯把他的名字大声说出来。
两名男子坐到隔壁的桌边,我们关于《动物农庄》和缅甸奈温时代的讨论告一段落。我的一名同伴以让人无法察觉的方式轻轻推了推我,屯林趴近桌子中央。我可以从他的表情中看出——眉毛扬成问号,仿佛在微笑——到了笑话时间。“你们听说过牙医的故事吗?”他问。“曾经有一个缅甸人,一路跋涉去邻国看牙医”,他开始讲笑话。“当他抵达牙医的诊所,牙医对他不畏漫漫长路专程赶来感到惊讶。‘在你的国家没有牙医吗?’他关心地问这名男子。‘有啊,有啊,我们有牙医’,这名男子回答。‘问题是,我们不能张口。’”
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缅甸长期以来都在各种预言的重负之下,奥威尔的三部曲仅是你解读缅甸未来和过去的众多作品之一
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个夜晚,印度北部古老的憍萨罗王国的统治者波斯匿王,做了十六个噩梦。梦中的世界栩栩如生又让人不安,比如双头马,漂浮的岩石,在金碗撒尿的野狼,还有母牛跪在泥泞里从自己刚生下的小牛那里吸吮奶汁。波斯匿王向宫廷里的婆罗门占卜者描述这些场景,询问这些梦意味着什么。婆罗门们断定这意味着王国的厄运和无望,提议大规模屠杀王国里的动物以满足邪恶的力量。然而,国王的妻子不认为牺牲动物是必要的,她劝说国王征求佛陀的意见。佛陀能够让国王的心灵平静下来。他聆听了每一个梦境,告诉国王不必担忧:这些梦境是预言,但在国王统治时期不会成为现实。佛陀说,他们讲述的是未来,当统治者变得邪恶,开始沉迷于贪婪和权力,预言就会成为现实。许多缅甸人认为国王的十六个梦境预言了今天的缅甸。
1962年,奈温和他的军队开始统治之后,在缅甸各地佛塔的墙壁上都有地方人士以波斯匿王的梦境为原型绘出的图画。佛陀对波斯匿王梦境的解读,读起来有点像关于缅甸困境的因果报应。比如在国王的第八个梦境里,人们向一个巨大的水缸倒水。水缸已经倒满,并且溢出,但是人们依然向里面倒水。旁边有很多需要注水的小水缸,人们却视而不见。大水缸里的水溢到地面上,然而小水缸却空空如也。佛陀解释,未来有一位统治者将会强迫他的人民不惜自己的营生为他劳作。人民将会被迫为统治者收种粮食,把他的粮仓填满大米,自己的储物仓却空空荡荡(波斯匿王的梦境也经常用来批评英国统治:我曾经看到一幅描绘这个梦境的绘画,讲述英国殖民地官员如何欺凌一名身穿笼基的农民,让他交出自己的收成)。
在国王的第十五个梦境里,一只丑陋笨拙的乌鸦领着一队高贵的鸭子,每一只都纯洁优雅,有着金色,栗色和宝蓝色羽毛。在佛陀看来,这个梦境预言了一个粗鄙将会控制高贵的时代。当无知开始当家作主,真正有价值的人将会被迫向他们的命令弯腰,以苟全性命。
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缅甸长期以来都在各种预言的重负之下,奥威尔的三部曲仅是你解读缅甸未来和过去的众多作品之一。缅甸最有诗意和神秘性的预言艺术是民谣。从王朝时代开始,民谣就提供诗歌和韵律形式的预言。它们不是出自智者或占卜者之口,而是由儿童和疯子传唱,有时是以戏剧性的表演来展现。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民谣来自何处:它们只是出现在街头玩耍的孩子哼唱的小调里,或者出现在荒诞不经的疯子喃喃自语的韵文里。在古老的过去,国王想知道王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派遣占卜者到市场里搜集民谣,民谣通常会在大变动之前出现。一首民谣警告国王不要向邻国暹罗调兵遣将,国王无动于衷,以战败而告终。另一首民谣预测缅甸锡袍王的王朝将会成为缅甸的末代王朝。英国人控制缅甸之后,锡袍王朝不光彩地走向终结。1901年,缅甸作家觉拉对他在缅甸各地见到的各种小调和符号进行解读,预言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他迅速被英国当局抓捕,理由是煽动颠覆英国的统治。就在几年前,有一首民谣获得应验:
两座寺庙,两颗牙齿;
人民乞讨,军队争吵。
这首民谣讲的是两座佛塔分别在曼德勒和仰光动土,以供奉复制的佛牙。民谣警告,两座佛塔落成之时,就是缅甸人民穷困、军队分裂之际。1997年,佛塔落成前后,军方内部出现严重的权力洗牌,执政的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成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我常有一种感觉,那种波及缅甸全国的奇怪传闻,承接了民谣的传统。有时,传闻建立在集体期待的元素之上。一名男性喝过两杯威士忌苏打后,告诉我,克伦尼军队即将控制仰光。但我在曼谷的报纸上读到,克伦尼军队遭到政府军的打击,最近签署了停火协议。“他们有新型炸弹,”男人一边说,一边摇着饮料里的冰块:“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炸弹,会向水平方向炸开,摧毁周边地区的一切事物。还有枪,他们有枪。很多很多枪,美国军队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给他们枪。克伦尼军队解放整个缅甸,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情。”
四处弥漫的各种传闻和预言,使得缅甸弥漫着魔幻和不祥的气氛:经常有某些事情一触即发的不安感觉。我在曼德勒有一位学者朋友,每次我遇到他,他都声称很快会有起义或会有将军死亡。他永远处于一种期待的状态。“我随时准备着,”他告诉我:“我准备帮助同胞,为同胞做出牺牲。”有一次,我碰到他,他刚刚乘过从曼德勒到仰光的夜车。他的眼睛下面有黑黑的眼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疲倦,是不是旅途很糟糕。
“不,一点也不是,”他回答:“但我必须做好准备,在整个旅程中我把包放在腿上,等待着。”
“等待什么?”
“任何事情,”他说:“在缅甸,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周边有一起火灾,一次轻微的地震,一颗可以观测到的彗星,或者其他超出平常的轻微事件,我的这位朋友都会预言政府的垮台。在缅甸语中,这种幻觉被称为预兆。在你面前有壁虎从天花板落下,或者你在离开房间时有一只狗向你吠叫,这都是不好的预兆。我的朋友解释说,他不知道自己看到的预兆意味着好事情还是坏事情。他所知道的,是有些事会发生,在不远的将来。“如果你想看到精彩的事情,留在这里。”他一边慢条斯理地说着,一边成竹在胸地点着头。
我常有一种感觉,那种波及缅甸全国的奇怪传闻,承接了民谣的传统。有时,传闻建立在集体期待的元素之上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至少没有达到我这位朋友预测的程度。但是,即使没有全国范围内的事件,我也有一种感觉,各种涉及具体个人的事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没有人能够预测和控制这些个人事件,这些内心的不满。在《一九八四》里,奥威尔努力控制住自己的不满:“他忍不住想拉开嗓门,大声呼喊,口出脏言,或者用脑袋撞墙,把桌子踢翻,把墨水瓶向玻璃窗扔过去……”我认识一名在仰光工作的导游。他喜欢缅甸,他告诉我,五年前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人住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他说。我们过去经常坐在茶馆里,就人权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他是亚伯拉罕·林肯的崇拜者,钦佩这位美国总统废除奴隶制和献身“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行动。然而,这几年,我注意到导游开始出现神经紧张的症状——他的右眼下面经常出现轻微的痉挛,仿佛他经常对我眨眼。每次我们碰面,痉挛都会越来越严重,直到我们最近一次碰面,痉挛已经扩散到他的半边脸。仿佛他不管戴上什么面具,面具都会破裂。关于这个现象,《一九八四》里有一个词“脸罪”。在我们最近一次碰面中,导游开始请求我帮他离开缅甸。“我无法在这里生存,”他说,“如果我继续呆在这里,最后一定会入狱”。
在波斯匿王的最后一个梦境里,国王看到山羊在追逐豹子,吞下他们
在波斯匿王的最后一个梦境里,国王看到山羊在追逐豹子,吞下他们。豹子恐惧地奔逃,浑身颤抖地藏在灌木丛中。佛陀解释说,这个梦境预言了一个时代,不义的人将会掌控权力,从人民那里窃取了本应属于人民的东西。当人民请求执政者归还他们的权利时,执政者会折磨人们,威胁砍去他们的手和脚。恐惧的人们将会被迫接受这些新的执政者,只能畏畏缩缩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或者逃走。
❶缅甸地名,位于曼德勒以西100千米。
编辑/张定浩
*艾玛·拉金(Emma Larkin)系一位美国记者的笔名,她在亚洲出生和成长,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缅甸语。她以曼谷为基地,对亚洲进行广泛报道,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访问缅甸。本文节译自Emma Larkin: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Penguin Books,2006;Granta Book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