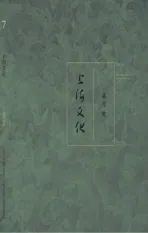《阿玛柯德》:再现永无法重现的乡愁
2014-02-12沈仲旻
沈仲旻
《阿玛柯德》:再现永无法重现的乡愁
沈仲旻
我在纸上反复演练里米尼(Rimini)和费里尼(Fellini)这两个词。里米尼的确如费里尼所言,是一个“一笔成形的字,一排小士兵”,它在笔下变成了一个天然自洽的、带有卷边的小港湾。费里尼那个词与里米尼有着部分类似的连绵结构,只是除了开头那个字母,那个巨大伫立在首位的F,像是一堵里面住着树妖、浑身是劲的墙。我将笔扔下,费里尼和里米尼的幽灵在桌上那堆废报纸、旧哈哈的文稿纸、餐巾纸里爬来爬去。这一个月里,我一个字也写不出,天天两只手揣在口袋里,在雾霾里到处晃荡,后来染上了什么流感病毒,像一个五十岁的男人一样咳嗽,我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贪婪地吃药,贪婪地跑去黑漆漆的电影院。每场费里尼影展片放映结束后,我都面赤气躁、心不在焉,你可以理解成因摄入含碘盐过量而导致的内分泌毛病,或者只是简单的司汤达综合症。有一次《罗马》映闭,朋友们各抒己见,说着说着走进了饭店,点了一盆葱姜花蛤,他们企图从食物的某种形式上去呼应银幕上罗马海鲜大排档的氛围,傻乎乎地羡妒那个彼岸,愤斥彭浦夜市的销毁。费里尼与里米尼,可怜的朋友和葱姜花蛤,我和《阿玛柯德》。我害怕谈论这部电影,就像害怕机械性地表述出我的感情。
我从餐巾纸堆里找出香烟,边咳边呼吸,在这一蓬蓬美妙的尘雾中,那些手写体又变了样,现在那个F,就完全像一个带着帽子的费里尼本人了。
因为这海洋未能被他所征服,他相信里面藏着他害怕又依恋的妖魔与幽灵之母
“昨天晚上我梦见里米尼港湾,澎湃、苍绿、骇人的大海,如大草原般滚动,海面上厚重的云块往陆地奔腾而去。巨大的我从小小的、狭窄的港湾出发,想游到大海去。我告诉我自己:我如此巨大,但大海终究是大海,要是游不到呢?……”乡愁在冬天的大海里,在白色的浪花里,在狂飙的风里,清晰地被认(呈现)出来。在里米尼完成了童年和青春期的费里尼,将这十七年一直小心翼翼地藏在这片断瓦残垣的海边。费里尼从小和他的伙伴蒂塔、奶酪头、大噶巴一起玩,小时候费里尼用沙铲敲蒂塔的头,长大后蒂塔为了见他和医院的修女干架,但在精神上,费里尼一直是一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人,他孤僻成性,对政治没有兴趣,不喜欢体育课,不好意思穿泳衣。然而我们的天性总是让自己陷入一种对缺陷的迷恋状态中,所以里米尼的大海反而对费里尼产生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因为这海洋未能被他所征服,他相信里面藏着他害怕又依恋的妖魔与幽灵之母。《阿玛柯德》是费里尼最后一部依旧可以随心所欲拍的电影,1973年的时候,《访谈录》里所说的体制宣战还未上演,这是一个绝好的时候,费里尼似乎觉得可以将有关青春的障碍一吐为快了。在《阿玛柯德》未诞生前,里米尼的乡亲们对费里尼在外的名声十分漠然,费里尼当然也不屑于回到里米尼,有几次,他都是在晚上回到里米尼,商店都关门了,路上没有人,只有几排列队经过的海风能见证他的到来,他有时甚至不过夜就又走了。里米尼是费里尼生命中的一个障碍,也是触发他所有特质的摇篮,《阿玛柯德》的真实性若即若离,它的碎片像幽灵一样穿梭在任何一部费里尼其他的作品中。直到《阿玛柯德》在里米尼上映,乡亲们态度开始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人们开始络绎地进入电影院,慢慢接受了费里尼描绘的那个里米尼,他们开始在这部影片里寻找现实原型,经常放到一半时,一个人指着某个银幕说“这是我!”“噢!那是隔壁老王他爹!”“放屁,那是我!”“烟店老板娘奶子没有那么大。”蒂塔有一次开车带着费里尼回到里米尼,有些街坊认出了他,他们居然在大街上伸手向他打招呼:“嘿,费里尼,你好吗?”费里尼感到欣慰,但和里米尼依旧保持距离。我很不想用“残酷青春”这样的词语去给青春强加一种情感色彩,青春是这样一个东西,它为你留守着一些关乎生活和自我永不会过期的秘密,但作为其副作用的伤痛则也相应地藏匿在漫长的潜伏期中。少年不识愁滋味,往日的自己不觉时光荏苒,只有时过境迁在此处回望青春时,才第一次与自己见面。孕育青春的真实处所并无新意,它的生命在“我”认为如此浅薄的、不开化的、与自我异质的方式中自顾自地延续着,而现在的自己与那个地方俨然已成了两个对立的世界,对它的情感早已幻化成梦中的一丝魅影,它真实的肉身却使我感到倦怠、厌恶。它就在那里,它没有变,变的是我,只是我将它曾穿越过我青春的那一部分视为了永不可重现的乡愁,它浓缩成了大海,将正在老去的我吞噬。《阿玛柯德》所取得的共鸣,包含着失落、慰藉和一种极为柔软的沧桑。它同时也展现了艺术家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最核心的精神问题,即我相对于这个世界的边缘性。尽管里米尼的政府后来意外地送给费里尼一栋海边别墅,希望他“想回来时可以随时回来”,但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费里尼而言,他那个里米尼是永远过去了,他既不在那个意识中的里米尼,也不在现在这个充满荣耀的小城,这也是他为什么一辈子都在想象中重塑一种隐喻中的现实。《阿玛柯德》释放了费里尼的完整性,他从里向外全盘托出自己,我们诚实地站在边缘上,不断回溯自己,并认识到世界的虚幻,以及虚幻的真实。费里尼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里米尼人,当然也只有这样,才能造就出《阿玛柯德》。
费里尼后来曾去找过真正的格拉迪斯卡,他开着捷豹汽车去到可马斯科牧场,这是一个泥泞的三角洲,路很不好走。他看见一个老妇人正在菜园里晾衣服,他跑过去问她:“请问格拉迪斯卡住这儿吗?”老妇人说:“你找她?”“嗯,我是她以前的一个老朋友。”老妇人看着他:“我就是格拉迪斯卡”。费里尼这才意识到,格拉迪斯卡原来已经六十多岁了。
再现1:真实性,塑料纸的海
我们在《浪荡儿》、《八部半》、《甜蜜的生活》、《卡萨诺瓦》里都能看到一片海,海的气息是费里尼有关回忆的重要象征,有时候我们的确在影片里看到了真的海——罗马的奥斯提亚海,但对我来说,费里尼塑造的最具力量的海,是《阿玛柯德》中等待雷克斯号时,那片用塑料纸做成的海洋(这片塑料纸海后来也被沿用在《卡萨诺瓦》中)。
费里尼在雷克斯号的模型上装了一百盏小灯泡,在摇晃的船身前方设置了一束水花,就像卫生间里忘了关的喷淋花洒。海洋是一大片半透明塑料纸组成的,晃动感经人为拉扯产生,淡淡的冷光灯是梦里才有的一轮月亮。费里尼并不是没钱做一个泰塔尼克号式的模型船,或在真的大海上拍摄一场滤镜夜景,相反的,逼真与代入感恰恰是费里尼极力避免的。他希望能在想象中重塑隐喻的现实,以达到一种他认为的真实,尤其在《阿玛柯德》这样一部对自己完全诚实的影片上。类似的手法还出现在《甜蜜的生活》尾声中的怪鱼、《朱丽叶与精灵》中的精灵身上。我忽然想到马尔克斯的一段话,他曾一度非常反感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说法,并否认自己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身份,他说:“我们的世界是浩淼无垠的,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也宽广无边,所以有时我们能理解的‘真正的’现实,对于其他人来说则不成立,他们并想方设法要加以解释,于是就有了那些结论,认为这是鬼怪的现实主义或者魔幻的现实主义。而对我来说,这仅仅就是现实主义。”
精通“鬼怪”和“梦”的费里尼,其实是个真正对现实忠诚的人。
逼真与代入感恰恰是费里尼极力避免的
再现2:角色,脸爱好
当年《阿玛柯德》在意大利上映时观众的反应,也在世界上任何一处都发生了,包括这次在上海,有观众喊出来:“那个卖烘山芋(其实他卖的是烤瓜子)的阿诈狸(说大话的/骗子)老像阿拉弄堂里的阿倪头哦!”你在里面还看到谁了?看到了爷爷、姆妈、隔壁酱油店洋葱头的囡、戳轮胎的同桌小黑皮、秃顶的物理老师、风韵犹存的前弄堂垃三……费里尼是如何做到的?卡尔维诺评价他:“费里尼脑中始终有一个像起跑点那样精准的表现法。”如果仅从《阿玛柯德》的角色设定、选角的表现上来说,费里尼已将这点做到了极致。那些人物呼之欲出,他们一个个出场,如同一道道早已设定好来击中观众内心标靶的烟火,轻易跨越了语感、人种,以及文化差异,这些面孔,仿佛是已被提炼过的人性图景。上次采访库斯图里卡,我们也谈过这个话题,库认为有着典型面相的演员有时根本不需要表演,只需要将镜头对准那张脸,打开机器,人性的秘密就能展露无遗,他运用某些特定长相的动物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有着典型面相的演员有时根本不需要表演,只需要将镜头对准那张脸,打开机器,人性的秘密就能展露无遗
现在我们见到老法师了。
在角色塑造上,费里尼的画家身份功不可没,他笔下的人物丰乳肥臀、神态夸张,几根快速思维下产生的线条一把就捏准了人物的神韵,这一切也缘于费里尼的识脸爱好——我们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已经不经意涉及了艺术家“如何”精准表达抽象概念的一些本质问题。这位识脸爱好者有一个私人的演员工作室,那里聚集了几个同样眼尖手快、对面相颇有研究的演员副导演,费里尼团队对每一个人物的重视,没有主配之分,其准确性无一漏网。这次在大银幕上观看《阿玛柯德》,可以让我们再度清晰轻易捕捉到藏在画面一隅的某个小配角的风采,在蒂欧叔叔那场上树下乡的戏里,嘲笑发狂的爸爸的农民,确由当地真实的农民扮演,我们也多次看到神采飞扬的侏儒演员们参与费里尼的电影中,甚至哪怕是一个酒鬼、一个糟老头、一个流浪汉,都会引起费里尼的巨大兴趣。格拉迪斯卡的扮演者玛加丽·诺尔(Magali Noël)对一件事情印象深刻:在拍摄母亲葬礼的那场戏时,NG了许多次,奔丧队伍和马车的配合总有衔接问题,许多看热闹的人和费里尼的影迷都聚集在摄影机后面观看这场戏的拍摄。最后一条,费里尼终于喊过了,忽然从人群中传出一个声音:“不行,完全不行,重来!”片场顿时鸦雀无声,费里尼有些生气地回头问“是谁啊?”那个被费里尼在路上搭来的扮演流浪汉的流浪汉正捧着瓶老酒,靠在石柱边发表着这句让剧组人员瞠目结舌的意见。费里尼一看是他,语气立马缓和下来:“哦你这么觉得吗?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玛加丽对费里尼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到玛加丽·诺尔,她其实并不是格拉迪斯卡的原配人选,费里尼一直认为桑德拉·米罗(Sandra Milo)才是格拉迪斯卡的最佳演绎者,但快开拍前,桑德拉的老公醋意大发,一出意大利式的闹剧让女主角的人选一夜间落空。当天晚上,《甜蜜的生活》的舞女扮演者玛加丽·诺尔在法国的床上睡得正香,一个深夜夺命call把她惊醒:“马加丽塔(费里尼自己对马加丽的昵称),明天上午十点准时来五号棚找我,有一个角色给你。”马加丽惊魂未定:“……明天上午十点?就算我现在不睡也不一定赶得上飞机啊。”“你一定赶得上,亲爱的马加丽塔。”第二天上午十点,马加丽蓬头垢面地出现在了罗马Cinecitta电影城五号棚,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赶上飞机的。费里尼叫服装师给她换上一身红衣,把她一边的刘海强迫症一样地弯出那个独特的波浪,再加个毛领子(为的是看起来更胖一些),最后戴上帽子,几番折腾后,费里尼退后两步,两眼发光:“啊,一个格拉迪斯卡!”
如果费里尼手稿的朋友一定对阿玛柯德的人物角色画难以忘怀,除了女主角格拉迪斯卡,最让人震惊于漫画与演员匹配度的就是“蒂塔爸爸”一角了。最开始,费里尼想邀他的好朋友蒂塔来演这个角色,他说“没有人会比你更懂你的父亲。”但是蒂塔的老婆不答应,费里尼气坏了。这几乎又是一个塞翁失马的故事,后来他遇见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那不勒斯演员Armando Brancia,他完全就是那个头上那两撮会生气的秃发、喜欢打自己耳光和咬帽子的蒂塔爸爸啊。与之呼应的是妈妈,我想说的是,费里尼太懂女人了,与片中其他身上带有各种魔鬼性的女性形象相比,妈妈干净消瘦的脸庞,散发着港湾般的温暖、羞涩与善良。叔叔的大只身板、机会主义的混子生活、但自己姐姐去世却哭得要昏倒的样子,就像每一个80年代的“叔叔”和“舅舅”一样,带有一种独特的时代烙印。而“我”,蒂塔,虽然依照的是好友蒂塔的原型,但剧中的蒂塔混有了一半费里尼的魂魄,因为在电影院里摸格拉迪斯卡大腿那件事的确是费里尼所为。我们试图将《阿玛柯德》的剧中人物平铺开,就像那张横开画卷式的手绘海报一样。患有强迫症的神父、为法西斯而狂热的斯芬克斯般的数学女老师、忠于透视法的馋痨胚艺术老师、舌头功大神希腊语老师、矮敦敦的花心爷爷……每一个脸部的特写都是一把打开记忆的密钥,而那些雾、风、雨,就像是巫师铺洒的灵汁神粉,将坐在黑暗中的我们席卷进私人的回忆中,那一场大雾戏,你难道没有和熊孩子们一起在大饭店门口翩翩起舞么?影片结束许久,所有角色的脸却依旧历历在目,男女老少、胖高矮瘦,一切如此具体,他们亲切、温暖,也叫人伤感,然而,这场呈现这些脸庞秘密的魔术本身,却让我感到另一种屏息凝神的震慑。因为我知道,除梦境与虚构,我们曾拥有过的珍宝,永无法被重现。
除梦境与虚构,我们曾拥有过的珍宝,永无法被重现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