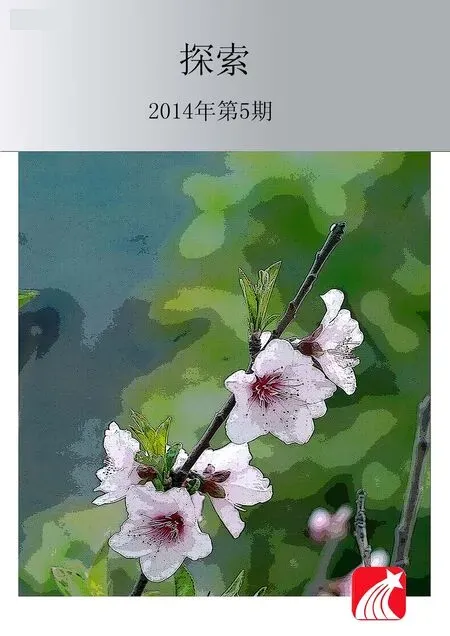“实事求是”命题的当代所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念
2014-02-11张定鑫
张定鑫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实事求是”命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其当代“所指”已超越其往日的“能指”。然而,这个范畴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被常识化现象。深究这一哲学范畴就成为进一步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者说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念一道“绕”不过的学术“工序”。
一、“实事求是”命题含义演绎
“实事求是”一语作为中国人的发明始于东汉《汉书·河间献王传》[1](p1839)。唐朝训诂学家注之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2](p1105)也就是对所获得的古代典籍、文物或文献一一客观地予以辨别真假、对错、是非,即一种严谨、求真的考据(学)态度。这是“实事求是”古语的原初含义。
两宋理学提出“即物穷理”而突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境界。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物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3](p4)。曾国藩则进一步把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融合起来:“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4](p166)“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阙一不可。”[5](p17963)从而把“实事求是”进一步归类为认识论命题。
“实事求是”命题在晚清被注入近代科学精神即注重实验。郭嵩焘说:“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知洋情之为然,而不知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殆犹知彼而不能知己者也。其言蒙养书院章程,大致以西法佐中法,而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6](p904、857)这样,在事实上,“实事求是”所蕴含的由考据(学)传统到“格致”之学的精华在近代被融入世界近代科学思想系统之中。我国学者后来直接用“实事求是”古语去解读黑格尔的现象学即“由现象去寻求本质”,说“‘实事求是’也是这个道理”[7](p9-10),有的甚至明确肯定“求是”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一脉相承的思想”[8](p42)。
“实事求是”命题在延安时期被毛泽东赋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阐释”,“实事求是态度”被判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9](p801)。然而,哲学思维上的进步总是付代价的。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多次挫折表明,躺在老祖宗的“本本”上简单承继“经典”只能是形式上“实事求是”实际上脱离“实事求是”甚至背离“实事求是”,正如中国哲学家所概括的,“多年以来,我们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总难做到从实际出发”[10](p70),应该在尊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典的基础上以新理念取代既往定论,开显“实事求是”新的时代内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在成功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就是坚执这样的哲学理念:一方面“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11](p165),另一方面推出“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1](p141、149),把“解放思想”置于实现“实事求是”的突破口,使“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联袂“出场”,把“实事求是”定位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这样,“实事求是”这个词汇就被提升为代表整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凝结中共治国智慧的“符号”,而不再止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或“作风”范畴。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20、21世纪之交以来,中国人没有简单重申“实事求是”概念而是推出“实事求是的目的”命题[12](p130),拓展、丰满其当代涵义。正如我国哲学家所指出的,“要实事求是,当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正确处理主客观关系,等等。这是属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可要做到实事求是,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群众和群众路线,是很难做到实事求是的”,“只有关心群众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才可能实事求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是共产党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牢固站稳这个出发点,才可能实事求是,才愿意实事求是,才能够实事求是。”[13]这样的新“诠释”显然使当代语境中的“实事求是”所指超越了其往日的能指即限于认识论或科学方法论范畴,从而在认识论、价值论上覆盖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整体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性或人民性,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哲学上的新理念。这个让中国人民深深受益的哲学理念值得人们“饮水思源”。
二、“实事求是”结构解析
从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逻辑即认识论看,当代意义的实事求是内存着主体怎样“实事求是”的问题。实事求是当代所指这一侧面包括两个层次:
——存“真”,就是充分尊重“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科学精神或老实态度。实事求是的“主体”对客观存在的既有理论或普遍真理(“矢”)、实践或实际问题(“的”)都抱着虚心的态度或“敬畏”的心态——“心诚”,全面地、系统地掌握这些“客观存在着”的“矢”与“的”两端的完整内容。就对待“矢”或“普遍真理”的存“真”心态而言,当代中国人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即“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就对待“的”的存“真”心态而言,当代中国人始终立足中国国情,从“工作重心转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了在中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老老实实”地始于“部分先富起来”,为了在中国展现社会主义的“名副其实”而“老老实实”地长期立足于“初级阶段”,为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老老实实”地在国际舞台上坚执“发展中国家”角色,中共十八大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4](J)这种对“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之存“真”的科学态度或老实态度,用卡莱尔的话说就是那种作为“伟人和他的一切言行的根基”、“伟人的首要定义”之“真诚”[15](p50、51)。这正是实事求是当代所指的第一个层次。
——求“是”,就是认识规律、尊重规律的“形而上”境界。这种“形而上”境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呈现为:崇尚法治和科学,冲破经验和传统的束缚;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世界文明发展的普遍性成果。由于我国习惯势力、常识思维根深蒂固而影响了人们这种“形而上”境界的修炼,“实事求是”在当代的侧重点或突破口定于“解放思想”,主攻因长期以来的“习惯”、“经验”、“常识”所酿成的“僵化或半僵化”现象。这种探求并尊重规律或科学(规律的“可知”形态)的“形而上”境界可以说是实事求是当代所指的第二个层次或在“认识世界”领域的最高层次。
求“是”层次标明:实事求是当代所指并非“事实整理”或“史料整理”,并非“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没有是非标准或优劣标准,而是比存“真”更高的层次、更高的要求——求“是”≠求“实”。人们有时把这一层次误认为求“实”。要知道,历史上那些所谓“教条主义”错误,与其说是理性或“形而上”这只手伸得过“长”——“读多了书”或“书呆子”,不如说是“形而上”境界没有真正到位,理论思维不开阔,对某个问题知识不系统、参悟不透彻,致使“有效”理论或“系统”的知识、智慧“供给”不足或滞后。所谓“深化”对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认识,就体现了求“是”的意境。
“实事求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念实际上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即“改善世界”的统一而不是“两张皮”。凡哲学的认识,其实都以人的某种道德立场为条件,用马克思的话说即“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16](p236)。否则,在一定条件下,“‘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7](p103)实事求是当代所指作为哲学范畴也不例外,内存着主体为什么而“实事求是”、为谁而“实事求是”的动力源问题,也就是价值论问题。这是实事求是当代所指另一侧面。
——务“实”,就是重现实效果、向前看的实践精神。邓小平释之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11](p118、279),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式纳入实事求是范畴而使“实事求是”中的“求”在具体形式上拾得一个新的“规定性”即“实践”或“实验”。这个“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所谓“社会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是穷社会主义总不能说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18](p687-688),即形象地“挑明”了“实事求是”之务“实”的彻底性。
这种将存“真”、求“是”与务“实”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服务于后者,不囿于既往原则、成见的“唯实”精神,是实事求是当代所指在“改造世界”领域第一层次或根本要求。以哲学术语来表达,也就是“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达到统一。马克思曾经比较过人类劳动活动与动物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9](p97)。人类生产劳动优越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依据客体尺度(实情)和主体尺度(需求)并把它们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黑格尔以哲学语言把人类实践活动这一特性或优越性表述为“扬弃了理念的片面的主观性”、“扬弃了客观世界的片面性”、“实现善的冲力”[20](p410-411)。实事求是之务“实”就充分彰显了人类实践活动中这一最呈人类本质的特性。
——至“善”①这里是对《大学》、《四书集注》中“至善”一词的借用。《礼记·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之为“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页),就是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境界。在当代中国,“至‘善’”意指锲而不舍地追问中国人民朝思暮想的是什么,遵循世界文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去实现中国人民所思所想,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和平和谐。所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一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简约地宣示了实事求是之至“善”境界。从价值论角度看,这种至“善”境界是实事求是当代所指之务“实”层次的进一步延伸或升华,是“实事求是”在“改造世界”领域的至高境界。
至“善”境界表明实事求是这一哲学范畴不限于个人的生存“智慧”,不等于个人的“生意经”,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凝结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全人类”意识。邓小平当年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时就表露了这种至“善”情结:我们太穷,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18](p381、380)所谓“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12](p279),便体现了实事求是范畴的至“善”境界。
三、整体把握实事求是当代所指
实事求是当代所指不仅包含两个侧面及其四个层次,并且这些侧面及其层次之间存在着“合则全,离则伤”的关系。
存“真”是求“是”乃至“实事求是”全过程的“始基”,属于“实事求是”这一中华古语的原初本义。“实事求是”之“首”就是立足于“事实”,仅仅在“事实”中“求是”而不离开“实事”去“求是”,更不违背“事实”独撰“是”,也不为了某个先入为主的“是”而对马列文本断章取义或剪裁历史实事,即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21](p34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存“真”——尊重“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科学态度或老实态度被当下某些“时尚”视为“傻冒”、“过时”,结果背离了黑格尔秉持的“着重在‘真’的研究”这一哲学本义[22](p83),致使一些人的心理世界或世界观系统埋下“心不诚”的“隐患”。任其“放任”下去,将近乎于一种“不可活”式的“自作孽”[23](p46)或“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24](p103)。
另一方面,“实事求是”中的“是”≠“实”即不等于“事实”或“意见”,不是在“事实”里“照葫芦画瓢”或“跟着感觉走”,而高于“事实”,存“真”以求“是”为其“形而上”境界。就此而言,“实事求是”过程与其说是理论“联系”实际、“反映”实际的过程,不如说是让科学理论“矫正”实际(现实)、引领实际(现实)的过程。
实事求是当代所指中的务“实”与至“善”也是相互依存、前后递进的。务“实”是至“善”的途径,舍此,至“善”会“乌托邦”化;至“善”又是“实事求是”全过程的“终极”目标,舍此,务“实”会降为市侩,存“真”、求“是”会沦为繁琐哲学。换一个角度说,务“实”层次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体现了事物矛盾普遍性寓于矛盾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区分对待经典的态度(学风)是否科学的“标杆”;至“善”层次体现了“是”与“应该”或“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反映了人们改造世界的终极境界,显现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之间的分野,显现了实事求是当代所指的崇高性。显然,务“实”若离开了至“善”,实事求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将被“打折”。
并且,存“真”、求“是”与务“实”、至“善”这两个侧面是合二而一的整体。实事求是当代所指若只有务“实”、至“善”一面,那么,她或者就有可能被演变为一个违背规律、排斥理性、对抗科学的情感性东西,其结果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乌托邦化,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科学性;如果当代意义的实事求是只有存“真”、求“是”一面,那么,她就无关乎人民痛痒,不过是“对事不对人”的“学问法”或生存“智巧”,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其实,正如雅斯贝斯所说的,即使是“不涉及价值的科学……在选择其问题和对象的时候,整个说来仍然不能不受它自己所能够加以直观的那些评价的左右。”[25](p357)遗憾的是,在常识或舆论界乃至学术界,一些人在论说“实事求是”时大都驻足于“实事求是”之认识论、方法论范畴,比如在说到那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精髓”时,就将“实事求是”驻足于“方法论”或学风层面。
实事求是当代所指这些层次之间的彼此依存又层层递进,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整体性所注定的。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是贯通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不限于某种纯粹“认识”,而是与实践论联为一体,是“实践认识“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19](p127)。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样明确肯定:当认识与实践结成一个统一体时,实践活动则是整体,认识活动是部分,认识是实践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以一个认识过程作为考察对象,我们也可以说其中的实践是认识这个整体的部分,但就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践总和而言,实践是整体,认识只是部分[26](p382)。并“挑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首要功能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否则,等于“自杀”。[27](p313)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来就不是止步于书斋内的“学科形态”,不满足于“概念世界”驰骋,而指向“改变世界”。不难看出,实事求是当代所指所包含的存“真”、求“是”与务“实”、至“善”这两个侧面之间的统一或融合,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之间的这种融合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价值论之间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固然强调“实践”或“生产实践”对于一般人类社会形成发展的始源性意义,说“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28](p67注①),“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8](p68),但他们始终关注的是特定社会形态里特定的“人”——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工人阶级的生产实践和政治斗争实践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对于实现包括产业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人类解放、自由的意义,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28](p75),无产者在“共产主义革命”中“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8](p307)。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就是这样同时内含着无产阶级的“价值取向”,二者是具体手段与终极目的之间的关系。当然那种与无产阶级实践过程脱节的“价值论”只能重蹈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覆辙。
四、几点结论
既然实事求是当代所指存在着一个彼此连贯、依次递进的思想系统,就不能忽视或割裂认识论与价值论之间的有机联系,不能片面凸显其中某一个侧面或层次而使其他处于“短板”状态。否则,将伤害实事求是当代所指。不是有哲学家针对本学术领域存在的“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现象而发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29](N)的呼吁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把“实事求是”两个“侧面”及其四个“层次”联通成一体,就大大有助于整体地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念,我们可以通过“实事求是当代所指”等具体形式来进行这一“构建”工作。
尽管“实事求是”久已约定为中国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对待世界文明成果的基本态度或基本逻辑,但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与关注点落在务“实”层次以致于存在“实事求实”现象。至于其中的存“真”、至“善”层次也显“稀薄”,把那个“熟悉”的毛泽东断语——“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习惯地归之于“的”一端,而把本来包含其中的“矢”之另一端则有意无意地“悬搁”在“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之外,似乎不属于“客观存在”范畴。
“实事求是是动态的。“实事求是”所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历史环境实际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或历史内涵,所存之“真”、所求之“是”、所务之“实”、所至之“善”的具体内涵总是历史的,它们会随着客观环境或时代的巨变而演绎不止,因而在“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念上不能持“一劳永逸”态度。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颜师古.汉书补注[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
[3]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5]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一辑《曾文正公(国藩)全集·求阙斋日记》:二卷上[M].刘传莹集录,台北:文海出版社.
[6]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
[7]贺麟.译者导言: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引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高清海.哲学在走向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陈先达.心中有群众才能实事求是[N].光明日报,2000-9-5.
[1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J].求是,2012(22):9.
[15][英]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M].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0]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9.
[23]孟子[M].王常则,译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24]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5]黄颂杰.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6]黄枬森.学的科学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李景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N].光明日报,2004-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