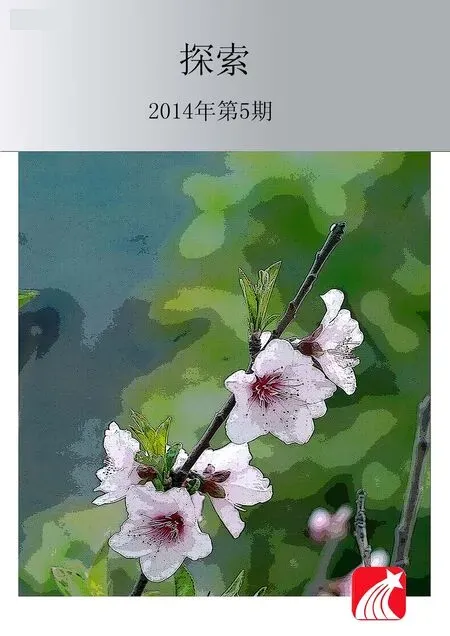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问题
2014-02-11汤苍松
汤苍松,林 盛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
作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城镇化中总体展现出较好的精神风貌和道德风尚。但是也必须看到,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对未来城镇主人翁的道德要求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还存在一些较为明显又相对严重的问题,影响其道德发展乃至新型城镇化建设本身。
(一)边缘化生存状态导致负能量累积和道德发展“内卷化”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生活中处于边缘化状态,生活满意程度不高。这种边缘化感受与满意度认知主要源自“与身边城镇同龄人生活差距的横向比较”[1]。就业方面,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缺乏向上流动渠道,难以摆脱低收入粘性,收入只够维持最低生活,很难体面生活。社保方面,据2011年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显示,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21.3%、34.8%和8.5%。居住条件方面,城镇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仅为城镇户籍居民的1/5,超过六成的广东90后农民工居住在员工集体宿舍。此外,受户籍限制和社会排斥,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机会较少,很难享受同等文化权益。
现实的不平等易导致心理失衡,诱发失德失范行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报酬、生活环境、社会支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劣势,使他们较早且深刻地感受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不同程度地产生对城镇的疏远甚至抗争。心理的失衡容易产生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危机,导致负面情绪累积和群体戾气蔓延。加上年纪轻、不成熟,心理脆弱而自卑,更是容易受到生存困境、外部诱唆以及亚文化驱动的影响,突破道德约束,加大失德失范风险。
相对封闭的圈内交往易导致对城镇道德的自我隔离。“具有相同嗜好的和性情的人,就会把人口分成种种道德区域”[2]。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居住在员工集体宿舍和以同事、老乡、亲友等为伴为邻的合租房,其交往对象集中在同事、同学、老乡和亲友等同质群体中。他们这种自发重构的游离于城镇主流文化外的道德空间和道德世界,构成了一种严重的自我道德隔离和城镇道德排斥现象,形成了道德发展的内卷化态势,使得其城镇融入和社会认同进展缓慢,阻碍其道德观和现代性的生长发展。
(二)流动性生活方式导致道德约束较差和失德成本较低
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正在实现从钟摆型向稳定型的转变,但由于工作性质、住房情况和个人选择等因素,相较于其他群体依然流动性较大。这种流动性既有城镇间的流动,更多体现为同一城镇不同工作单位和居住场所的变动,继而不断变换活动场域和接触人群。“(城市生活中的)流动会模糊人的理念,破坏人的道德”,“民风民德以及个人道德中首要的因素是连贯性”[3]。考虑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发展,必须考虑生活方式的这种流动性。
这种流动性往往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自律性不够。“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4]。新生代农民工不少是曾经的留守儿童或者是随亲进城儿童,传统家庭管教相对欠缺,基本学校教育不够扎实,加上阅历单薄和修养不足,面对社会环境影响和生活压力催化,在外界刺激下容易出现失控现象和失德言行,甚至是违法犯罪。而且,他律的缺失更是弱化了自律作用,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城乡之间,其思想道德教育引导严重缺失。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中对其管理基本上是“只管手脚不管头脑”[5],只干预其“动手动脚”及违法犯罪,对思想观念、情操培养、精神文化和价值取向等“头脑”问题关注不够,对合法权益维护不够。教育引导和管理服务严重不到位,往往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放松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同时,这种流动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经常处于新环境、置身新场域、接触新群体,对于外界评价的顾忌和禁忌大为减少,行为规范的参照相对淡化,自我约束因之松弛,失德的精神成本和物质成本随之降低,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失德行为,甚至既有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也有丧失风险。
(三)城镇化生活环境催生轻职业道德、重消费文化等消极道德现象
一是吃苦耐劳精神缺失,职业精神有待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较多缺乏务农经历,工作忍耐性与吃苦精神与父辈有明显差距。在技能学习上,往往偏爱看似轻松时髦但普及泛化的本领,而不愿接受相对苦累但市场急需的专业培训。在职业选择上,职业期望较高,方向不明确,出现短工化、高流动性趋势,甚至部分被称为工漂族。这导致不少人长期对现有工作“不满意”,业务停留在学徒期的浅表水平,“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6],既导致职业枯竭,又影响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构建。
二是勤俭节约意识相对淡化,消费行为比较超前。既有城镇青年的刺激影响,也有过分追求时尚生活的意愿,在消费主义流行的时代和追求时尚时髦的年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过度追逐新潮的生活休闲方式,甚至出现“娇子农民工”、“月光族”等现象。一味追求享乐消费,很可能误入歧途,将自身置于道德和法律的边缘。
三是心理压力明显较大,挫折承受能力不强。一方面,工作压力较大,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的等级性和经济条件的制约,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认同的差异不断冲击其自尊心,使得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形成焦虑或恐慌。长期处于这样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状态,导致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精神式微,情感丰富却脆弱,抗压抗挫能力不强,遇到重大挫折容易一蹶不振甚至消极遁世。
(四)网络化精神生活使其更易受到多样价值观念的影响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干扰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化精神生活相对普遍。一方面,众生平等、不问出身的网络空间更容易获得认同感,另一方面,失落感觉和不满情绪更容易在虚拟世界寻求慰藉、得到释放。据调查,九成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会上网,周均上网时间在5~10个小时之间[7]。在丰富精神生活、舒缓生活节奏的同时,网络上充斥的不少低俗垃圾信息和错误舆论导向,也容易对其身心健康、价值取向和道德发展形成不良影响、构成错误引导。
虚拟世界负面情绪加剧对社会的不满,容易引发失德行为。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关注负面信息和娱乐新闻。由于其生存发展的现实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与践行程度不高。而虚拟世界的引导规制相对不够,负面情绪和夸张渲染相对较多。通过网络,新生代农民工首先成为这种负面情绪的被动接受者,然后又往往通过与自身经历的比照共振、宣泄吐槽,通过习得技术转变为这种负面情绪的再传播者和放大者,从而导致这种网络负能量的多次扩散蔓延。这样,一方面个体容易受负面情绪影响,在网络世界和虚拟交往中获取负能量,挑战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另一方面,这种负面情绪的网络弥漫容易导致涉世未深的新生代农民工被组织起来形成共鸣,增强社会怨恨、激化社会矛盾。
二、加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从本质上讲,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社会成员道德建设的物质依托和根本保证,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关键是积极稳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但考虑到这一过程的长期复杂性,当前应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加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以培养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为切入点,以塑造道德自信与正确价值为根本,以促进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和强化虚拟世界教育与引导为手段,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综合构建制度保障,帮助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道德人格成熟、道德习惯养成,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升华、由道德义务向道德良心的转化,从而为新型城镇化“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9]。
(一)在职业教育中更加重视敬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培养
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认可、赢得尊重的核心道德内容,也是加强其道德建设的重要切入点。经验表明,强化职业培训是提高农民工素质、实现农民工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但是一方面,超过50%的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既有的农民工教育培训更加侧重职业技能训练,对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培养重视不够。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农民工培训基本补贴制度和政府购买培训成果机制。当前,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突出特点,更加注重职业教育中以务实肯干、爱岗敬业为核心的职业道德培养,重点培养职业选择中的务实态度,重点增强日常工作中的吃苦精神,重点提高职业发展中的敬业意识,让“劳动·创造·奋斗”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追求,让良好职业精神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素质建设的核心亮点。同时要看到,农民工正成为未来城镇私营业主的重要来源,正成为参与国家事务的重要力量,城镇私营企业主中原职业为进城农民的约占1/5[10]而且有明显上升趋势,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代表的数量也从十一届实现零的突破增加到十二届的31名。要宣传好这些典型,善于以身边榜样激发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创新创造创业精神,使其在职业跃迁、财富积累、地位调整中永葆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二)在教育引导中更加重视道德自信与价值取向的塑造
社会群体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塑造道德自信、形成与主流社会共通的价值取向。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与道德规范的教育引导,增强道德自信、培养健康心理、提高道德自律、引导道德行为,是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一是从政策、人员、经费多方面支持开展新生代农民工道德教育专项活动。二是注重培育、发现和选树道德模范。使其葆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律。三是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积极推动与城镇居民的道德融合。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心态、积极力量和良好品质。
(三)在社会管理中更加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个体道德的培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对社会的认同和融入上。有研究表明,相较上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社会距离值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11]。如果选择放任,而不采取有效的社会管理措施,则可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对其中任何一种文化群体的价值标准忠贞不渝,又不能为他所认同的任何一种文化群体所充分接受”[12],从而加剧其道德游离和管理无序状态。第一,强化相关部门思想道德教育与管理的社会责任。特别是要强化输入地政府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责任,强化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在维护合法权益和思想引导方面职责,强化用人单位用管教结合的多层职责。第二,加强社会支持网络建设。社会支持网络对承受压力的个人具有预防、舒缓和治疗的功能。要支持新生代农民工突破乡土社会、工友圈子等同质交往群体,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第三,加强重点聚集区域的道德建设。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重要的社区成员纳入规范的社区环境,加强社区载体建设,支持发展社区的监护、管理、服务作用,支持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法律服务、人文关怀,以 “个体—社区—城镇”形成其对所在城镇的情感纽带和融入渠道,帮助消除社会孤独感和个体孤立感,从而更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德、维护文明形象。
(四)在网络治理中更加重视精神熏陶与思想引导
第一,增加网络精神生活的内容供给。新生代农民工是相对弱势的,以其为主要对象的内容供给明显不足。要支持建设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融就业服务、婚恋交友、社会生活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并鼓励群团组织、青年自愿组织、志愿团队遵循市场规律和社会机理,加强线上线下活动,促进网络交流与社会参与,同时对不良内容充斥的网络平台重拳出击,应对网络众声喧哗,应对网络受众争夺,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在互动、融入、思辨、选择中增进社会认同、提高自律意识、增强辨别能力。第二,有效改善网络精神生活的环境条件。重点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聚集区域如厂区附近、社区周边上网场所的清查治理,确保网吧及周边休闲娱乐场所安全、绿色、合法、健康。
(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道德建设制度保障
制度保障是道德建设长效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托。加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离不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综合配套改革,离不开不断完善的社会制度环境。要逐步实现在劳动就业、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平共惠。积极推进中小城市(镇)廉租房等保障住房制度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探索宅基地退出和城镇保障房配置挂钩,鼓励新生代农民工退掉宅基地到城镇购房。
参考文献:
[1]李丹,李玉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7):151-155.
[2][3][12][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4,59,273,5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515,15.
[5]张承安.城市农民工道德问题及其化解[J].特区经济,2008(4):141-142.
[6]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课题组,张昭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6):5-22.
[7]管雷.网络时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的换代与转型[J].中国青年研究,2011(1):31-35.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32.
[9]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N].人民日报,2013-09-27(1).
[10]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2年-2004年6月)[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
[11]史斌.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J].南方人口,2010(1):4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