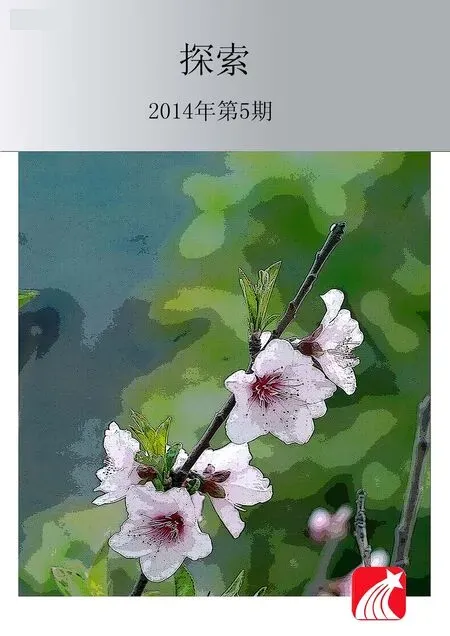人群知识分布与经济增长分析
2014-02-11张尚毅
张尚毅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0047)
一、由信息获取量所构建的知识的价值指向
人的经济活动成为自觉的活动始于人类的进化以及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只是到了最近的几百年才有了所谓的发展(即人均收入增长超过每年2%)。在漫长的社会史上,人均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几乎总保持为零”[1]。如果没有这几百年的经济增长,对于经济研究的所有对象都是难以展开的,因此,研究经济增长相关问题就必须能够解释清楚这些问题。在经济研究史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即将越来越多的要素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中,从土地、资本到管理再到教育、管制、制度等等,但这也只是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进行解释。然而,不管将要素扩展到何种程度,有一个最为基本的事情必须明白,那就是如果这个星球上没有了人类,而这些土地等自然因素大体上存在,自然力掌控世界,那就无所谓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必须把人的因素纳入其中,“我们确有必要研究生产过程中的‘非物质’投入对‘物质’投入的替代关系”,“我们所在的世界恒处于变动之中,另一方面,我们的感受也恒处于变动之中。为应付并适应变动的世界,我们需要知识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并且需要信息以调整我们对世界的预期”[2]。正如西方经济学所表明的那样,在经济增长分析中把人的劳动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纳入了经济增长分析,然而,这里我们并非仅仅把人的劳动作为经济变量,我们所考虑的视角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性特征,就是人的生物性结构使人能够运用其所掌握的知识。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另一类是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通过积累两种经验——那些从物理环境和那些从社会文化语言环境中学得的经验。”[3]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意在指出的是正因为人所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知识,这种知识使人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了自主性地推进经济增长。
但是,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的个体所掌握的知识状况是不同的,而经济增长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人群知识进行耦合,使之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这就涉及一个人群知识分布的问题,人群知识分布程度的不同,使人群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而且“当个体作为群体一员时,个体的行为会表现出他所在群体的社会角色,如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地区或国家的人群状况,其知识分布状况所体现出来的对问题的看法以及对经济发展的观点都十分不同,而这种差异不仅在于关于自然知识上的差异上,更重要地表现在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的差异上,博伊索特等人以默会知识作为表达,即“关于这些东西的知识年深月久已经被有意或无意地内在化了”[4],正是这种内在化的知识成为决定其行为的因素。然而,还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各类关于知识分析的研究中并没有把知识划分为自然知识和人类自身两个不同的方面,事实上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十分不同的作用。正如我们在大多数经济分析中所看到的情况,即使把知识纳入分析也只是把知识不加区别地作为总量和标量进行着分析,而没有进行相应的区分。事实上,关于自然的知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知识,主要体现为对自然的认知度,而不存对自然认知的方向性方面的差异性,因此,这类知识只是一种数量性的积累,因而可以视作为标量。而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则是一种主观性的知识即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是具有方向性的,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以及朝哪个方面发展,因而这类的知识不仅有数量上的差异,同时又具有方向性的差异,如对经济制度的选择就有计划、市场等若干种选择方向,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类的知识认为是一个矢量,而这个矢量在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意义是约束人群的行为方向,或者更一般地说就是使经济增长朝着哪个方向推进,而这决定了经济增长制度优化水平,“我们认为制度的演进将影响我们能否产生和适应未来知识”[5],正因为受到知识所决定的制度的约束,因而影响了一个制度能否使新知识得到运用。
我们可以把获取的这类知识用一个矢量和的方式来表达,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人的智力的空洞描述上。“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6]。可以假设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是由所获取的信息构成的,获取的每一个信息都是具有一定量值和一定方向的矢量,设定一个个体在获取这类信息时具有一个Z0矢量的知识存量集,获取的任意一个新的信息可设定为Zi,那么,当具有Z0知识存量的个体得到任意一个新的信息时,其知识将演进为(Z0+Zi),而对获得若干个信息的个体而言,其获得的信息所构成的知识量为Z0+∑Zi,作了这样的分析后,我们将不难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当Z0是一个具有较大量值的矢量时,如果Zi的量值较小,即∣Z∣远远大于∣Zi∣时,个体知识在获得新的Zi信息时,新的知识存量Z0与Zi相加的结果近似于Z0的结果,但是,随着获取信息量的不断增加,最终将使具有知识存量Z0的个体将改变其原来的状态,即当且仅当∑Zi量值很大时,Z0+∑Zi的结果是近似朝向∑Zi方向,而且,原来的知识存量将纳入新的知识存量集,如果我们令Z=Z0+∑Zi,那么就将出现一个新的具有知识存量Z的个体。
这个结果可以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看到,如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区域的个体,当其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区域时,一般持相对保守状态,并且,当个体知识存量Z0越大时,就越不容易与新的区域形成共性的知识,这点可以通过对老年人难以融入新的社会经济区域得到解释。这里,我们借用奥地利学派的知识传统概念来说明问题,也即该个体不容易与新的经济区域形成知识传统,因而也就是一个与新的社会经济区域不具有相同知识传统的个体,意味着这个个体不容易参与到新的社会经济区域制度的演进中来。但是,一种新的情况是当具有这一类知识存量的个体数量足够大并进入新的社会经济区域时,其关于自身知识的状况将影响到新的社会经济区域的状况,进而形成新的均衡即新的知识传统,正如哈耶克所指明的那样:“均衡仅以人们在试图执行其可能达到均衡的初始计划的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为基础”[7],对此,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对新的社会经济区域制度产生影响,进而演进为新的制度安排。关于这点,我们认为当且仅当有J个个体进入新的社会区域时,每个具有知识传统∑Zi存量的个体,其对新的社会经济区域制度安排的影响将取决于J个个体以及原来在新的社会经济区域中个体的知识分布状况。
当然,正如前面我们分析的一样,决定知识分布状况并不取决于某一个个体的知识存量,而是取决于人群的知识状况,当人群的知识分布状况越具有相类似的共性知识时,也就越容易构建起知识传统,从而建立起适应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与制度安排。
二、人均知识分布的决定作用
人群中个体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人群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个体所具有的知识状况,而必须从人群知识的总体分布状况来进行解释,这里群体可以表征为集团。这正如奥尔森所指明的那样:“集团利益是经济和政治行为的绝对基本决定因素”[8],这里奥尔森所想指明的是群体状况(集团)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分析经济增长应该建立在人群的知识分布状况上,而不仅由个体的知识状况来决定。事实上,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点在于人的知识性,即使马歇尔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这点,他明确指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结构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9],而大多数经济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这点,即使在一些分析中引入了人的因素也只是将人的知识性特点简化为劳动的付出,不论是古典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乃至李嘉图传统都大体如此,即使如罗默等人的研究把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进而推导出一个递增的经济增长,而没有指明为什么在同一时代有些区域经济增长而有些区域经济没有实现增长。如果我们从知识的溢出效益来分析,更对此有疑问。但是,正如前面我们所指明的那样,通过把知识分为关于自然与人类自身的知识,以及进一步把知识分解为关于自然的知识是标量性的知识,而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是矢量性知识,最终将给出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方向性的价值指向,进而构建起具有选择性的制度进化以决定经济增长。
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人群知识分布状况,进而分析出人群的制度选择优化水平,从而构建起这样一个图景:即人均知识分布状况决定经济制度优化水平,而制度优化水平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通过相关文献及数量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较好地解释一个地区发展与落后的根本性原因,进而揭示出推动经济增长的人群知识分布状况。我们可以通过人群受教育水平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人群知识分布状况对发展的重要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舒尔茨曾经非常重视知识的作用,也做过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分析,并且非常强调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且强调:“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能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10]。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的一点,即使在舒尔茨的分析中也没有比较好地对知识进行划分,从而得出受教育本身对制度进化的作用,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同时,要分析人群知识分布状况还必须建立在人群足够的数量水平上。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群数量状况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分析经济变迁的历史时必须充分考虑人群的数量状况。之所以作这样的阐明,其目的是表明只有当人群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形成经济增长,而我们通常所研究的市场的扩大也在于将更多的人群数量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忽视这点就既没有生产也没有需求,更谈不上市场的扩展。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人群虽然都是由个体组成的,当人群数量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近似地看作连续的函数系列。因此,我们可以用经济理论常见的连续函数模型进行研究。之所以说明这些,就是如前面我们所提出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建立在更加符合现实的基础上,从现实情况来看人群总体状况符合连续性的要求。
但是,要研究一个区域中的人群状况可以将之看作为一个相对数量非常大的随机结构,而对于任意总体只要样本数量充分大,样本均值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在研究知识在人群中的分布状况时,我们也可以用正态分布进行研究。考虑到一个社会区域人群数量的足够大,这种极大数的平均分布状况可以近似于正态分布,而每个个体的知识状况都可以视作为一个样本,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而言,假设其所具有的人数N即为样本数,因此,这个经济体系第i个人所体现出来的决定其行为的知识量就为Xi,那么,这个经济体系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均衡水平也即样本均值就应该为,这个样本均值的经济意义体现为经济体系所能达到的平均知识存量水平,这种平均知识存量水平体现为一个社会区域中所有经济主体对一些经济问题所能具有的预见性,而我们所需要得到的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区域中人群知识状况的平均状态所能体现的社会知识化水平,从而得到由人均知识分布状况所决定的制度优化水平,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存量的累积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迁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1],随着人群中个体知识的进展,社会经济区域中所有经济主体所体现出来的人均知识存量的提高,即前面分析的Z=Z0+∑Zi的提高,可能发展出新制度安排,进而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环境。
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人群知识分布的数量模型。我们把人群设定为具有N个个体的群体,其中N足够大。每个个体所具有的知识不完全相同,我们将每个个体具有的知识设定为Xi,这些个体所具有的知识来源于所获得的信息Z,而Z=Z0+∑Zi,同时,可运用前面所提出的人均知识分布状况决定于制度优化水平的论断,从而得出一个相对应的制度安排,而出现这个制度安排的概率取决于人均知识分布水平。由于,在现实中一个社会经济区域的个体数N是一个非常大数量,因此,在设定其期望值EX=μ,DX=σ2的情况下,来自一个社会区域的个体的知识存量的样本X1,X2,X3,﹍﹍,Xn,当且仅当N足够大时,人群知识分布平均水平近似服从正态分布N(μ,σ2/2),由此可以得出人群中人均知识分布密度为其中f(X)具有的经济意义是,当人均知识分布状况服从正态分布时,可能出现的人均知识状况所决定的制度安排。根据经验我们可以知道,个体的知识存量理论上可以取值区间(0≤X≦∞),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可以把获得正规教育状况作为一个区间进行说明,考虑到学生学习从小学一直到研究生这20来年的学习过程对于个体的知识积累起着主要作用,因此,可以设定个体知识存量的下限为a1,个体知识存量的上限为a22,取区间(a1≤X≤a22),作了这样的设定后,可以将问题的视野从(0≤X≤∞)缩小到(a1≤X≤a22)。这样,就可以用获得正规教育的情况来检测人群知识分布状况,进而得到一个人均知识分布密度情况,从而确定由此决定的经济制度优化水平,并得出这样一个。事实上,还可仅考虑接受过大学教育及其以上个体在人群中的分布状况对制度优化的重要作用,设定区间为(a16≤X≤a22),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个群体在整个人群中的分布状况,
还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均知识分布状况如何与制度优化状况相对应,其中相关联的是具有相同知识结构的个体在制度中的作用不同,可以作这样的设定,即对于任意具有知识存量的个体Xi,给予一个权数ai,这个ai表征了具有知识存量Xi的个体在社会经济区域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的重要程度,从而也就是可能影响制度优化水平的权数。作了这样的设定后,我们得出新的人均分布状况。显然,∑aixi是线性结构,因此,也服从正态分布,这足以说明制度优化状况仅与人均知识分布状况相关,而与每个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状况即权数ai无关,因此一个社会经济区域所能出现的制度优化状况并不取决于个体的位置状况的推动,而取决于社会经济区域人均知识分布状况。
三、由知识分布决定的制度优化水平
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假设命题,即制度的优化水平与人类的知识结构是相适应的,越与人类知识进展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其制度优化水平就相对越高。因此,可以假设由不同知识水平的人构成一个完备的事件X1,X2,X3,……,Xn,构成一个社会经济区域完备的可能出现的知识结构状态,同时,假设这些知识分布状况对于于相适应的一个制度优化状态B,那么,对于任意一个由一定知识构成的小的人群而言,如由高中毕业生构成一个人群,设定为Xi,那么,在制度优化状态为B的状态下,一个社会经济区域可能出现具有知识构成为Xi的人群的可能性概率为P(Xi)。对于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可以认为具有知识存量Xi的人群出现的状况,对可能出现的制度优化的作用。由此,可以构建起一个由社会经济区域人群知识分布状况所决定的制度优化水平出现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即出现的概率水平。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均知识分布状况决定于制度优化水平,但是并不必然等于一定的人群知识分布状况就确切地出现相适应的制度优化水平,这里还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取决于社会经济区域人均知识分布状况,而且还取决于在社会经济区域中人群知识结构状况,也即是前面我们所分析的那样,整个社会经济区域中各个层次知识结构出现的可能性,即知识结构出现的概率水平。在做了这样的分析后,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明白人均知识分布状况与制度优化水平的相互关系。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点:对于任意的人群知识状况Xi,存在一个可能出现的概率P(Xi),而当制度优化水平为B时,Xi在整个社会经济区域中出现的可能性即P(Xi∣B),这个可能性即当制度优化水平达到B时,Xi在人群知识分布中出现的可能性。同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当整个社会经济区域中存在人群知识结构为Xi时,可能出现的制度优化水平为B时的可能性P(B∣Xi),同时假设Ai为整个社会区域经济区第i个个体的知识存量状况,按照贝叶斯公式,我们可以有,从这个等式我们可能看到,当出现制度优化水平状况B时,在整个社会经济区域中知识结构具有Xi人群的出现的可能性水平不仅取决于整个社会经济区域中具有知识结构Xi出现的可能性,而且取决于具有知识结构人群存在可能出现的制度优化水平,同时,也与整个社会经济区域知识分布状况出现的可能性相关,以及由整个社会经济区域中人群知识分布状况可能出现的制度优化状况相关联。
由此,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人均知识分布状况如何影响制度优化水平。这里,我们可以把上面的等式适当处理成这样,即,从这个等式我们可以看到,当整个社会经济区域存在知识结构为Xi的人群结构时,由此对应的制度优化水平出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与整个社会经济区域知识分布水平相关,又与整个社会经济区域中知识分布状况可能决定的制度优化水平相关,同时也与这种制度优化水平时可能出现的人群知识结构相关。通过这样的分析,事实上可以看到一个演进的知识分布与制度优化的关系,不仅可以推论出人均知识分布状况服从正态分布从而构建起一个与此相对应的制度优化水平,同时,又可以演进出具有不同知识分布状况的人群对制度优化水平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以出现的概率水平来表示,从而构建起一个由人群知识分布状况所对映或称之为决定的制度水平。作了这样的设定后,就可以通过制度的作用得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水平,正如赫尔普曼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制度结构不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可能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12]。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增长的最终依赖因素在于人群的知识分布,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和地区也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这时,可以回到前面所论述的那样,正因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所特有的知识性特征,从而使人类能够运用他的知识来推进经济增长,进而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引致增长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对世界和人类组织自身知识的匮乏。
从人群知识分布状况中可以推出人均知识分布状况,以及人群知识分布对制度演进所起的作用结构性相关的结论,对此,可以知道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区域制度演进的根本在于人均知识分布状况,这点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13]。制度的演进取决于社会发展规律,但又与个体具有关联性。通过对人群知识分布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群的整个知识状况发生变化时,对制度演进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由此决定的制度演进状况又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正如诺思所指明的那样:“当经济为从事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活动提供制度激励的时候,就会产生经济增长。”[3]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罗默所研究的知识的递增效应中虽然没有区别出关于自然的知识与关于人自组织的知识,但是,经济发展的确取决于人的知识的进展应该是无疑的了。
总之,通过对个体知识来源以及人群知识分布状况的分析,使我们明白这样一点:即一个社会经济区域的制度状况并不必然地取决于人在整个社会区域各个知识层次人群的知识状况,但却必然地取决于人均知识分布状况,由此,影响了社会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如果在一定社会经济区域内提高人均知识分布水平,就完全有可能提高这个区域的经济制度水平,进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同时,由于知识存在溢出效应,也使增长极理论在知识层面可以得到解释。
参考文献:
[1]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J].社会学研究,1998(2).
[2]汪丁丁.生产函数的知识理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1).
[3](美)道格拉斯.C.诺思.理解经济增长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美)马克斯.H.博伊索特.知识资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美)ThomXs sowell.Knowledge Xnd Decision.Published by BXsicBooks,X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1996.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瑞典)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8](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为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式1993.
[9](英)阿费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0]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11](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2](美)E.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