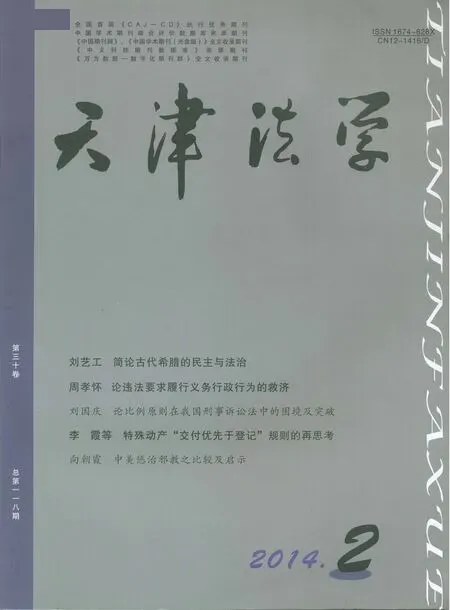李大钊38篇轶文的历史考辨
2014-02-11冯铁金
冯铁金
(中共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河北唐山063300)
·李大钊研究·
李大钊38篇轶文的历史考辨
冯铁金
(中共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河北唐山063300)
李大钊曾在《甲寅》日刊发表70篇文章,几乎是将近每两天就发表1文;在《新生活》周刊发表68篇文章,平均每期发表1.2篇。可是,他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竟然在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存续的近5年时间里,没有用本名或常用笔名发表过一篇文章。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实际上,他在该报以列武、子棠、其颖、罗敬、田诚5个笔名发表了36篇文章。另外,在《政治生活》以罗敬署名的两文亦为他所作。
李大钊;笔名;38篇轶文
李大钊是一位将写作视为生命重要组成部分的伟大革命者,是一位能迅速撰写时政评论的大家。如《甲寅》日刊从1917年1月28日创刊至6月25日止,他共在该日刊发表文章70篇,几乎是将近每两天就发表1篇。再如,《新生活》周刊于1919年8月17日创刊后,他就从第2期(8月24日出版)起至第46期(1921年3月5日出版)在该刊发表文章68篇,平均每期发表文章1.2篇(该刊共出55期)强。可是,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竟然在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存续的近5年时间里,没有用本名或常用笔名发表过一篇文章,不为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鼓与呼。事情的真相会是这样吗?笔者认为:不是。实际上,李大钊在该报创刊后不久的1922年11月8日,就在第9期以笔名“田诚”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直到1927年4月6日被张作霖的军警逮捕那天,还以“列武”的笔名在该报第193期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总共发表了36文。
下面,采用倒叙的方法,加以论证。
之所以采用倒叙的方法,因为以最后两个笔名“列武”、“子棠”发表的文章,是一个突破口,无论是哪位读者,只要看了以下第一个大问题的论述,都会毫无疑义信服地认为:列武、子棠就是李大钊。如果先从李大钊以田诚(1922年11月8日至1923年6月7日期间用的笔名)、罗敬(1924年9月3日至1926年6月9日期间用的笔名)、“其颖”(1925年4月12日至5月30日期间用的笔名)开始论证,可能不会使所有的读者都认为田诚、罗敬、其颖就是李大钊。而如果用倒叙法考证出子棠、列武就是李大钊,那么,作为撰写时效性极强的时政评论大家,李大钊绝不会从1926年1月至1927年4月才在《向导周报》上发表这些时政评论,应该是向前推到1925直至1922年《向导周报》创刊后不久就在该报上发表文章,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不可能设想,《向导周报》创刊后,在3年多(到1925年底)的时间里,李大钊不在该报发表文章,突然从1926年1月起开始在该报发表文章,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分别以“列武”、“子棠”署名的8文、2文为李大钊所作
说列武的文章就是李大钊所作,有何根据呢?根据是:《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五卷收有《奉系最近军事计划——白和报告》(一九二七年一月)[1]一文,而1927年1月17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83期同样刊登了一篇同名的文章(内有少量修改),只要将这两文放在一起阅读,无论是谁,都会信服地认为这两文同为李大钊所作。为节省文字,这里就不转录这两文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看看笔者说的对不对。
《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五卷,还在附录中收入以列武署名的3篇文章,同样都发表在《向导周报》上:《靳云鹗免职前后北方军事概况——六月十一日北京通信》(第160期,1926年6月30日)[2]、《天津会议与时局的将来——六月十九日北京通信》(第161期,1926年7月7日)[3]、《北方政治情形与天津会议——北京通信》(第180期,1926年11月)[4],此期出版日期为1926年12月5日。以上3文中“日”期,是笔者加的,原书无有。将这3文作为附录,就说明编者还不能肯定列武就是李大钊。通过笔者的考证,可以证明列武就是李大钊。这样,也可以说,李大钊以列武署名的文章共有8篇,是一个“通信”系列,其先后发表的次序、题目(笔者发现在《向导周报》发表的文章用楷体字标明)为:
1、《郭松龄失败后北方政治军事之概观(北京通信一月十一日)》,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2、《靳云鹗免职前后北方军事概况(六月十一日北京通信)》,第160期,1926年6月30日。
3、《天津会议与时局的将来(六月十九日北京通信)》,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4、《张吴会面后北方的政局(七月十六日北京通信)》,第165期,1926年7月28日。
5、《北方最近政情及安福派之时局推测(八月一日北京通信)》,第167期,1926年8月15日。
6、《北方政治情形与天津会议(十一月二十日北京通信)》,第180期,1926年12月5日。
7、《奉系最近军事计划(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通信)》,第183期,1927年1月17日。
8、《北京政局近情(三月十八日北京通讯[信])》,第193期,1927年4月6日。
同时,《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5卷收有《〈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四)——关于杨宇霆的报告》(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5],这就是说,该文为李大钊所作。1926年11月4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77期上,将此文标题改为《奉张总统梦的过程》(二月八日北京通讯)予以刊登(内中同样有少量修改)。这说明,子棠的这篇文章亦是李大钊所作。
另外,1927年2月16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88期还刊登了署名“子棠”的《北京之政闻种种》(十月十八日北京通讯),迄今未发现他人用此名公开发表过文章,所以,在考证了署名“子棠”的《奉张总统梦的过程》为李大钊所作后,也可以认定该文为李大钊所作。
二、以其颖署名的3文为李大钊所作
1925年4月12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10期,发表了署名“其颖”的《上海的童工问题》(以下简称《童工》一)。对此,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该文是贺昌所作,根据是贺昌又名“其颖”[6]。并且,在李大钊著作各种版本的《选集》、《文集》、《全集》中,均没有收录此文。笔者则认为,《童工》一与李大钊的《上海的童工问题》(以下简称《童工》二)是同一篇文章,因而,不是贺昌而是李大钊所作,考证如下:
(一)《童工》一的前4个自然段(全文共6个自然段)与《童工》二基本相同,因此,《童工》一是《童工》二的一个缩写。增加的内容,是针对1925年4月15日将召开的“纳税外人会”要讨论“工部局这个改良童工的建议案”,而提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与童工切实有利的条件”。
《童工》一的第一个自然段:“于是以前在家庭内的儿童劳动,都跑到工厂里做工,一变而成为中外资本家最贱价的小奴隶了。[7]”此为来自《童工》二的这句话:“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均极惨苦,而不得一钱。作了工厂主和包工者的小奴隶”[8]。
《童工》一的第二个自然段:“去年上海工部局童工调查委员会,将上海租界内分为十区调查,雇佣童工的大小工厂共二百七十五个。童工总数共有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其中十二岁以上的男工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女工十万零五千九百二十一人,十二岁以下的男工四千四百七十五人,女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9]”这是来自《童工》二的此话:“上海的外人自治会,曾为调查和研究上海的童工组织一委员会。委员会费了一年的工夫,研究这个问题。据其调查的结果,系把上海市分为十区,共得雇佣童工的大小工厂二百七十五个。童工总数有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就中含有十二岁以上的男工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女工十万零五千九百二十一人;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四千四百七十五人,女童(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10]”《童工》二在叙述这个问题时,将上面的这些数字是分区(哈尔滨Harbin Road区、提篮桥区、杨树浦区、小沙渡区、西虹口区、新闸区、虹口区、中央CentraI区、闸北区、浦东区)作了详细记载[11],而《童工》一则将这些内容都省略了。
《童工》一的第三个自然段“:这许多童工,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学徒的年龄,以工作的性质各有不同,学徒的期限依照惯例都为五年。在这学徒期内,普遍均不给工钱,就是间或有给工钱的,数量亦极少。很多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做工。他们多半都是站着,每天做十二小时的苦工。一天的工钱,最多不过两角。工厂里的设备太坏,毫不讲究卫生。这些童工大半是由包工头从乡里雇来,一个月只给他们的父兄银二元,而包工头可在工厂老板处领到四元。[12]”应该说,此话与《童工》二中的这句话没有什么区别:“徒弟的年龄,以工作的性质而有不同,其期限则依惯例为五年。在此期间,普通多不给报酬,即偶有给与报酬者,其数亦极少。很多的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作工,十二小时内,仅给他们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他们大都是站立着作工。分日夜两班换班,直到一星期终了的时候,才停一班。工钱只按工日给与。一天的工钱,至多不过二角。工作场所的卫生设备极坏。那些儿童,多由包工者Contractor由乡间招来,一个月只给他们的父母银二元,而包工者则一个月由工厂主得到银四元。[13]”
《童工》一的第四个自然段:“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公布这个调查而后,提出一个名归而实不至的改良童工建议案!如凡十岁以下的童工,禁止在租界内作工,四年以内,可将童工的最低年龄增加至十二岁,童工仍照惯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其中应有一小时为进食休息时间;对于日内准许工作的童工,轮作夜工时,不全禁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每两周须有继续二十四小时的休息……(此删节号是原有的——引者注)。[14]”这句话,无疑是来自《童工》二如下的记载:“该委员会(指上海的外人自治会,也就是工部局,为调查上海的童工而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引者注)调查既毕,随着亦有所建议,其要点如下:1.禁用十岁以下的童工。……3.此条例施行后四年以内,须将年龄的限制提高到十二岁。4.禁止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在任何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超过十二点钟以上的工作。每一个十二点钟内,必须休息一点钟。每一个十四天的作工时间内,至少要拿二十四点钟来休息。[15]”原文还有“2、5、6、7”点,此处略。
为了使读者看清该文不是贺昌所作,恕笔者大段引用了《童工》一与《童工》二的文字。
《童工》一(公开发表于1925年4月12日)最后说:“四月十五日上海的‘外国国会’——纳税外人会,又要开会了,工部局这个改良童工的建议案,必将提出讨论”[16]。针对这个情况,《童工》一呼吁“希望上海租界的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个小奴隶联合起来,提出与童工切实有利的条件(如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的童工,由工部局或厂主设立平民学校,供给童工的教育费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八小时,绝对禁止使用童工做夜工及其他有害健康的工作;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星期须有继续二十四小时以上的休息,不得克扣工钱;童工工钱,须与成年工人相等,不得克扣;改良工厂中童工的条件……。)反抗帝国主义的这个名归而实不至的骗局!全国的工人阶级和真正民族革命运动者,都应予童工以实际的援助。[17]”这段文字,实际上是李大钊对《童工》二最后说的“设法一改进”童工悲惨、痛苦状况的进一步呼应,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名归实至的办法,使我们再次看到了李大钊对上海及全国童工的无限关爱。
(二)《童工》二于1924年9月写出、在1925年4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4期发表,李大钊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作为时任团中央委员的贺昌在看了《童工》二之后,不可能再写同名同内容的文章。
前面谈到,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于在6月14日前赶到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李大钊留在苏联进行考察,并对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的学员和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进行指导,一直到1924年10月30日,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作了《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的报告后,他即启程回国,于11月15日前回到北京(据李大钊自己说:“自满洲里来莫斯科,约经七昼夜可达。”从北京到满洲里,约需与此相同的时间)。在苏联期间的9月28日,他根据在日本大阪《编军英字日报》和上海《密勒式评论周报》第二十九卷第八号(1924年7月26日出版,李大钊在该文中未写该报出版日期,这个日期是笔者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张玉菡同志查阅得到的,在此向她表示深深的谢意)刊登的文章,以“守常”署名写出《童工》二,后在1925年4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4期发表。
虽然《中国工人》杂志没署出版“日”期,但通过以下叙述,可断定是《童工》二发表在先,《童工》一发表在后,时间当在1925年4月5日左右。《童工》一与《童工》二内容大体相同,而《童工》二早已于1924年9月28日写完,故不可能是李大钊在看了《童工》一之后才动笔写《童工》二,只能是《童工》二发表在先、《童工》一发表在后。读过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两文内容基本相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童工》二发表后,李大钊为了使全党同志都重视上海的童工问题,便将《童工》二(全文约4500字)缩写成《童工》一(全文约1060字),投给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因为童工问题属于工人的范畴,所以李大钊先把《童工》二投给了《中国工人》)。二是,《童工》二发表后,《向导周报》认为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应该引起全党的重视,便请李大钊将该文加以缩写,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加些新的内容,李大钊表示赞同,于是便出现了《童工》二与《童工》一先后发表这种情况。况且,李大钊当时在党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如果“其颖”是贺昌,作为团中央委员的他绝不可能在看了《童工》二之后,再写同名同内容的文章。
(三)从写作起因来讲,《童工》一不会是贺昌而是李大钊所作。
李大钊为什么会写《童工》二,这是因为,他一直对劳苦大众特别是工人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对他们无限同情、关爱。早在1919年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2号上,就用“明明”的笔名发表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述说了工人们的悲惨遭遇:“他们终日在炭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情。[18]”当他在苏联通过考察得知了苏俄儿童的生活无比幸福,通过阅读报刊了解到上海童工的悲惨的生活后,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他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于是奋笔疾书,写下了《童工》二这篇战斗的檄文,寄望于全社会共同努力,把万千童工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正如他自己在《童工》二中所说:“吾侪身在苏俄,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娱乐,教育,不禁想起这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因特函述其要,愿贵报(指《中国工人》——引者注)记者及留心社会的青年同志们,看一看你们的小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而设法一改进之。幸甚幸甚!”[19]读着以上这些写于80多年前的文字,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李大钊就在我们眼前,依然能感知到他那无限关爱儿童火热的心的跳动。李大钊写作《童工》二的起因,他自己写得清清楚楚,而《童工》一如果是贺昌所作,他为什么不写写作起因呢?这只能说明《童工》一是李大钊所写,因为李大钊已经写过相同的文章了,不须在后面的这篇文章中再提写作起因了。
(四)“一文两用”是李大钊原已形成的一个特有做法,将《童工》二的内容,缩写为《童工》一,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延续,这为《童工》一是李大钊所写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
“一文两用”是李大钊此前已形成的一个习惯,仅举4例:
一是,1917年3月20日左右,他写了《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一文,先发表1917年3月24日的《甲寅》日刊上。后来他又将此文作为第二部分,写进《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发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1册上,小标题为“(二)德[法]国”[20]。
二是,1917年3月下旬时,李大钊接着写了《最近奥国政变之颠末》,投给《言治》季刊第1册,成为上说《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中的第四部分,小标题为“(四)奥国”[21]。同时,他还将《最近奥国政变之颠末》投给《甲寅》日刊,发表在1917年4月1日、2日出版的该刊上。
三是,约在1918年1月,李大钊写了《俄国革命与文学家》一文(约540字,分为2个自然段),发表在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3册上。差不多与写作上文同时,李大钊还写了《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约5200字,分为22个自然段)。此文在李大钊生前没有发表,初刊于1979年5月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对比两文,可知《俄国革命与文学家》的第一段(主要内容是“十九世纪间,社会的动机,政治的动机,盛行于俄国诗歌之中”[22],并提到了普希金等几位俄国诗人的代表作)第二段(主要内容是提到几位俄国诗人受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就是《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的第6、7和第18段,这3段与上文所说的内容基本相同。可以推测的两种可能,一为《俄国革命与文学家》写作在先,然后将其充实到《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中。二为,《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写作在先,然后将其中的第6、7和第18自然段抽出,节缩成《俄国革命与文学家》。
四是,1921年12月15日至17日,李大钊在北京中国大学作了题为《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演讲。1922年7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发表了《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这两文题目仅有一个小的差别,即前文比后文多一“由”字。文中内容基本一样,文字略有差别。但后文比前文要少520字[23]。通过上述“一文两用”的事例,我们可以得知,《童工》一与《童工》二内容基本一样,正是李大钊以往“一文两用”做法的延续,可证《童工》一为李大钊所写。
(五)如果《童工》一是贺昌所作,有一个极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就是文中引用资料没有注明出处。而对李大钊来讲,因在《童工》二中已说到引用资料的出处,故在《童工》一中无须再这样做了。
《童工》一中只提到“去年上海工部局童工调查委员会”,将上海租界内分为十区调查”,却没有提到这个调查发表在什么报刊上,而如果《童工》一是贺昌所作,他是不可能知道上海工部局调查委员会这份调查内容的。《童工》一的第二、三、四段所记,均来自这份调查。这份调查没有公开发表前,肯定是上海工部局的一份绝密文件,贺昌是不会得到的,也就无从知道其内容。而他得到的实际上是在报刊上已公开发表的内容,他却又不指出其出处,这岂不是很不应该吗?再说,贺昌1924年2月至1925年1月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团的三大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工农部长。三大闭幕后留在上海工作。即便他在1925年4月写作《童工》一时能找到8个月前出版的《密勒氏评论周报》第29卷第8号(其实能找到的概率也是很低的),但当时是否能找到刊登上海童工悲惨生活的另一份资料——连李大钊也未注明出版日期的日本大阪《编军英字日报》,则是颇为值得怀疑的。还值得怀疑的有,他为什么要在《密勒氏评论周报》第29卷第8号出版8个月后才写《童工》一,这岂不是太没有时效性了吗?李大钊1924年9月28日写《童工》二,几乎是在看了《密勒氏评论周报》第29卷第8号的同时就动笔了(该报1924年7月26日在上海出版后,邮到莫斯科约需一个半月时间),其时效性是很强的,时政评论就是要讲究时效性。在这种情况下,说贺昌写了《童工》一,恐怕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对李大钊来讲,由于他在《童工》二中已讲了引用材料的来源,因而,无须再在《童工》二上这样做了。
(六)两人同用一个笔名(又名、化名)的大有人在,“其颖”之名并非是贺昌的专用又名,李大钊也可以用。
我们知道,贺昌的又名是“其颖”,但不可以反过来说,称为“其颖”的人就一定是贺昌。两人同用一个笔名(又名、化名)的大有人在。如周恩来、谢觉哉用过“飞飞”[24],刘少奇、陈独秀用过“实”[25],向警予、杨度用过“九九”[26],瞿秋白、郭沫若用过“同人”[27],邓中夏、李立三用过“李成”[28],陈独秀、彭述之用过“张次南”[29],高君宇、杨靖宇用过“尚德”[30],恽代英、赵世炎用过“英”[31],等等。因这种现象较为普遍,恕不一一例举。
(七)“其颖”这个笔名,只在20余天内用过3次,此后至李大钊于1927年4月6日被捕就再未出现过,也为该名是李大钊的笔名提供了旁证。
“其颖”除发表过《童工》一外,还在紧接1925年4月19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11期发表了《萍矿工人的奋斗》,在1925年5月3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13期发表了《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奋斗》。笔者认为,这后两篇文章也是李大钊所作。上述3篇文章几乎是连续发表的,而在此后直到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的军队逮捕,“其颖”之名就再未出现过。这也为该名是李大钊的笔名提供了旁证。如果李大钊能多活几年、十几年或更长的时间,他也有可能继续使用这个笔名。
三、以罗敬署名的12文为李大钊所作
罗敬在《向导周报》发表的12文是:
1924年12月3日第93期:《段祺瑞来京以前》(十一月十九日北京通信)。
1924年12月10日第94期:《段祺瑞来京以后》(十二月四日北京通信)。
1925年1月9日第98期:《北方最近之政情》(一月二日北京通信)。
1925年3月7日第105期:《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二月三十日北京通信)(这里的“二月三十日”为原文)。
1925年3月28日第108期:《中山去世之前后》(北京通信三月日)。
1925年4月12日第110期:《革命与反革命》(北京通信四月四日)。
1925年5月3日第113期:《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四月二十五日北京通信)。
1925年5月24日第116期:《奉军入京以前》(五月十四日北京通信)、《北京五七怒潮的经过》(五月十三日北京通信)(这两文的顺序,是按《向导周报》登载先后排列的)。
1925年12月30日第140期:《北京民众反段运动与国民党右派破坏阴谋》(北京通信十二月十日)。
1926年5月8日第152期:《白色恐怖下的北方反动政局》(四月二十五日北京通信)。
1926年6月9日第157期:《北方政局新变化之征兆》(五月二十八日北京通信)。
有的读者可能会说,你说罗敬是李大钊的笔名,可我看到的一些资料,都说罗敬是赵世炎的笔名。确实,现在的一些党史文著,都说罗敬是赵世炎的笔名[32]。但是,按照学术界公认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该用事实证明罗敬是赵世炎的笔名才对。可是,据笔者所知,并无一人对此说进行考证,只有结论。而没有经过考证的结论,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现在的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33]。
下面,对罗敬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加以考证。
(一)最重要的一点是,赵世炎没有分身术,他不可能在1926年5月26日以乐生署名写“广州通信”,又在5月28日以罗敬署名写“北京通信”。仅此一点,就可证,罗敬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1926年6月9日,赵世炎以“乐生”署名在《向导周报》第157期发表了《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五月二十六日广州通信)一文,文中开头说:“国民党中央最高干部,自本月十五日起,举行第二次会议,至今已将结束了。[34]”为什么此时赵世炎能写出“广州通信”呢?是因为他在开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没有马上离穗。他于5月30日在《向导周报》第155期发表了以“乐生”署名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五月十三日广州通信),文中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自‘五一’节起至十二日止,开会于广州。[35]”
如果罗敬是赵世炎,他不可能于5月26日在广州以乐生署名写“广州通信”,又于5月28日在北京以罗敬署名写“北京通信”,与《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同时发表在《向导周报》第157期上。赵世炎没有分身术,他不可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一为5月26日,一为5月28日),既在广州写“广州通信”,又在北京写“北京通信”。仅此一点,就可以肯定,罗敬绝不会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的笔名。
(二)赵世炎在1926年5月12日开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并没有返回北京,而是在广州一直逗留到5月26日[此日他撰写了《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广州通信)]。于27日赶赴上海,30日与汪寿华指挥了六万余人在南京路上举行的“五卅”周年游行示威。因此,写出并发表《北方政局变化之征兆》(五月二十八日北京通信)的罗敬,肯定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赵世炎在开完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后,他并没有回到北京,而是直接去了上海。因此,写出并发表《北京政局变化之征兆》(五月二十八日北京通信)的罗敬,肯定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赵世炎为什么在开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不回北京,而去了上海。这是因为,“世炎同志由广州到上海,中共为加强江、浙地区的工作,委为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其后,有任军委书记”[36]。
(三)罗敬在两文中称《向导周报》为“本报”,以当时的身份,赵世炎无权而李大钊有权代表该报发表文章,故罗敬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1925年5月24日,罗敬在《向导周报》第116期,发表《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一文,文中说:“本报代表民众利益,并曾屡次勉勖会之成功。……特作此篇以告本报读者,并盼本报读者特别注意于该会议之各种议案与宣言”[37]。在这句话中,连用3个“本报”。他在此文中又说:“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有两种政治的遗嘱:一为国内的;一为国际的(即致苏俄之遗书),笔记而出,为全国民众所普知。在这两种遗嘱传授之时,中山先生警告其同志说:‘你们不怕敌人之软化吗?’记者曾于本报通信中述过”[38]。罗敬在这里所说“记者曾于本报通信中述过”指的是罗敬发表于1925年3月28日《向导周报》第108期的《中山去世之前后》,该文说:“中山说:‘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39]。同在这期《向导周报》,还发表了罗敬《奉军入京之前》的文章,文中说:“奉军与国民军之战本不可免,本报于数月前已言之,记者并曾说,张作霖出京之日,即这个战争局面之开始”[40]。我们知道,此文发表时及以前,赵世炎从未在《向导周报》工作,因此,他无法将该报称之为“本报”。但李大钊就不同了,一本辞典说:《向导周报》,“初由陈独秀、蔡和森主编,编委会还有高君宇、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等”[41]。同时,李大钊还在中共四大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以他的这双重身份,是完全可以代表《向导周报》的。
(四)赵世炎在兼任《政治生活》主编时,常以“士炎”、“乐生”的笔名发表文章,并称该报为“本报”;在提到《向导周报》时,则不称为“本报”,而是特意标出其名,可证罗敬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1924年12月21日,赵士炎以笔名“士炎”在《政治生活》第26期发表了《国民会议之理论与其实际》,文中说:“中国共产党屡次向全国被压迫民众提出政治奋斗之方法与出路,而这次复响应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号召,并提出了十三条具体方案(见《响导》第九十二期及本报第二十四期)来”[42]。1925年5月1日,赵世炎以笔名“乐生”在《政治生活》第38期发表了《驳斥对于苏俄的谤言》,文中说:“本报记者虽以为为应读者之要求,这是应有的工作”[43]。1925年12月30日,赵世炎以“乐生”的笔名在《政治生活》第62期发表了《京津战争与农民》,文中说:“陈炯明解散农会时,曾对人说:‘群众我是很怕的,尤其是农民,我从前在广西时几乎被赶出来,兵力虽足以战胜桂军,而没法镇压农民,他们出没神秘莫测’。(见《响导周报》第七十期海丰通信)”[44]又说:“当我们到时,有好几村的农民都树起‘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旗子来欢迎的。偏僻乡村的农民,欢迎丘八如此热烈诚恳,怕是在中国从未看见过的了!”(见《响导周报》第百十期)[45]发表这3文时,赵世炎正分别担任中共北京区地执委书记、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的主编。因此,他有资格和权力称该刊为“本报”。但他在提到《向导周报》时,则不称为“本报”,而是特意标出其名,可证罗敬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五)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3月28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08期头版头条,发表了罗敬的悼念文章,以下两点可证,罗敬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罗敬在这天发表的悼念文章为《中山去世之前后》(北京通信三月廿日)。从以下两点来看,此处的罗敬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一点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头版头条发表的文章的人,可以肯定,是中共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中的一人,而不会是时任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赵世炎。在1922年8月28日-30日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决定由中央领导人首先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中旬,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议决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因此,孙中山逝世后,中共中央应作出反映,发表中共领导人悼念孙的文章。当时,赵世炎为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故他无权代表中共中央发表悼念文章。而李大钊是在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召开的“四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的,他可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悼念文章,故罗敬不可能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另一点是,从个人友谊程度上,亦应当由李大钊而不是由赵世炎发表悼念文章。“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受党的委托,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深入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亘数时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会谈极为融洽、成功,孙亲自主盟“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加入国民党”[46]。自此,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3年10月19日,孙为改组国民党事宜,正式任命李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8日,李大钊在国民党特别会议上,被孙中山指派为临时中央侯补执行委员,会后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除了指定李为大会主席五名成员之一,让李与自己共同主持大会外,还让李分别在预算委员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担任委员。由于孙的工作,李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李还担任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大力发展国民党员,致北京地区的该党党员迅速增加,孙与李的情谊更加深厚。从与孙的个人情谊讲,中共四大选出的另外8名中央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无一人能与李大钊相比,李是发表悼念孙的文章的不二人选。即使陈独秀,论与孙中山的私人情谊,也不如李大钊。起码,他未参加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再说赵世炎,他1922年留法,1923年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秋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与孙的交往也很少,故他不可能是罗敬。
(六)李大钊以“列武”、“子棠”署名的10篇“北京通信”,与“罗敬”署名的12篇“北京通信”,是一个系列。可证罗敬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本文第一个大问题已考证出分别以“列武”、“子棠”署名发表在《向导周报》的10篇“北京通信”为李大钊所作。这10文实际上是罗敬所写12篇“北京通信”的延续。换句话说,李大钊所写“北京通信”,并非是从“列武”、“子棠”而是从“罗敬”开始。
(七)赵世炎并未以本名或常用笔名写过一篇“北京通信”,他曾以常用笔名写过除北京以外的3地通信各1篇,可证罗敬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迄今为止,还无人考证出赵世炎以本名或笔名(罗敬除外,但通过上述,可以否定他不是赵世炎)撰写的“北京通信”。不过,笔者却发现,赵世炎曾在1925年2月28日,以他的常用笔名“乐生”在《向导周报》第104期,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经过与结果》(二月十二日郑州通信);在1926年4月16日,又以“知因”的常用笔名,在《政治生活》第73、74期合刊上,发表了《天津民众的不幸与教训》(四月十日天津通信);在1926年5月30日,以“乐生”的笔名,在《向导周报》第155期发表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五月十三日广州通信)。赵世炎撰写的各地“通信”,仅仅这3篇,没有再写过其他各地“通信”。上面叙述证明,李大钊与赵世炎有过约定,“北京通信”由李大钊来写,其他各地“通信”由赵世炎来写,这亦可证罗敬不是赵世炎而是李大钊。
另外,罗敬还分别在《政治生活》(1924年4月27日至1925年夏为中共北京地执委机关报、1925年秋以后为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第27期(1925年1月11日出版)发表《小资阶级对共产主义恐怖》、在第62期(1925年12月30日出版)发表《日本帝国主义之狂暴》之文,这与上说罗敬发表的前10文是在同一时间,在考证了那12文是李大钊所作后,这两文亦可以认定是李大钊所作。
四、以“田诚”署名的11文为李大钊所作
(一)李大钊在1922年8月28至30日召开的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排序第二(陈独秀排序第一)的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众所周知,在“二大”上选出的五名中央委员中没有李大钊。故许多党史著作特别是一些权威著作都认为李大钊不是二届中央委员。笔者认为,如果不承认李大钊是二届中央委员,解释不了下列四个问题:一是他既然不是中央委员,何以在西湖会议解决张国焘的小组织问题时,中央不让他退席。二是西湖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何以能第一个加入国民党(该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中央领导人以个人名义率先加入国民党)。三是他何以能在1922年10月3日代表中共中央,为陈独秀签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任命书。四是陈独秀何以在“三大”上批评“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实际上是在批评李大钊,因为与吴佩孚的往来都是由李大钊进行的)。据此,笔者从8个方面撰写了《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以下简称《拙文》二),发表在《北京党史》2010年第2期,其内容不再复述。需要在这里补充的是,李不但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而且是排在第二位。其根据就是《拙文》二提到的4条理由。一是1929年底,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讲到在西湖会议上,参加人有“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47]。二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即高君宇——引者注)和我共七人”[48]。陈独秀是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排序第一,他把李大钊排在第一,实际上李是排序第二,张国焘亦把李排在了第二。三是1986年,李维汉会议说:“1923年初抵京,我向中央汇报了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情况和要求,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座”[49]。四是1922年10月3日,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签发对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任命书。如果李大钊不在二届中央委员中排序第二,他是没有权力为陈独秀的任命书签字的。
(二)田诚于1922年11月至年底在《向导周报》发表的文章,多次排在几位二届中央委员之前,这说明是排序第二的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可证田诚即李大钊。
这11篇发表在《向导周报》上的文章是:
1922年11月8日第9期:《资本主义世界的休战纪念》、《国家主要者要注意罢工运动》、《真不愧好人奋斗》。
1922年11月15日第10期:《外国资本家的宣传员真聪明》。
1922年12月13日第13期:《曹锟做寿与宣统结婚》、《国民党那里去了?》。
1922年12月20日第14期:《看看日本侵略家的话》、《中国人与外国人》。
1922年12月27日第15期:《“今日”派之所谓马克思主义》。
1923年1月18日第16期:《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汉口之逞凶》。
1923年6月7日第28期:《狼狈为奸之中外资本家》。
既然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排序第二的二届中央委员,那就有一个十分值得奇怪的事情,就是以勤于写作著称的他,在西湖会议后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前这段时间内,竟然未在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过1篇以“李大钊”或其他常用笔名署名的文章。此时李真的未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吗?笔者认为,上说以田诚署名在该报上发表的11篇文章,就是李大钊所作。如果能找到田诚此后也在二届中央委员中排序第二,我们便可以有理由地说:田诚就是李大钊。
田诚在《向导周报》第9期(1922年11月8日)发表的《真不愧好人奋斗》,排在国涛(即张国焘)《庆祝海参威工人》之前;在第10期(1922年11月15日)发表的《外国资本家的宣传员真聪明》,排在蔡和森《国人对于苏俄的同情》、《赵恒惕与湖南自治》两文之前;在第13期(1922年12月13日)发表的《国民党那里去了?》,排在致中(即邓中夏)《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特立(即张国焘)《劳工司与劳工局》之前;第16期(1923年1月18日)发表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汉口之逞凶》,排在陈独秀《革命与反革命》之前。我们知道,“二大”选出的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并没有叫田诚的人。而且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5人中,也无人起过“田诚”的笔名。笔者认为,在考证了李大钊是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排序第二的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和这里田诚排在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也即是田诚在西湖会议后排在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第二位)之前,可证田诚就是李大钊。
上说“致中”是邓中夏,证据有四:
一是在1922年9月13日出版的《向导周报》创刊号,“致中”发表了《宪法与自治学院》、《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两篇文章。应该说,在创刊号的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上能发两文,应该是中央执行委员级人物。况且,《向导周报》是在1922年8月底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决定创办的,到出版创刊号仅仅不足半个月的时间,即便该报向党内一般同志约稿,也有可能不按时交上来。从这点来说,致中也应该不是一般人物。
二是致中在《向导周报》第13期发表的《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排在特立(即张国焘)《劳工司与劳工局》之前,证明了他是排在张国焘之前的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三是马林1922年8月12日至9月7日的“工作记录”载:“张太雷与陈独秀和邓[中夏]会谈后决定,邀请北京参加会议。增加李大钊”[50]。如果邓中夏不是在“二大”上被选为第二号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决不会让邓参与此事。否则,就会影响各中央执行委员之间的团结。
四是马林在《关于罢工问题的讨论记录》(1923年3月30日,李大钊的住所)中说:邓——蔡——张太雷讨论湖北代表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51]。这里邓又排在了蔡和森之前。上述“四是”都证明了邓是在“二大”被选为排序第二的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也就证明了“致中”就是邓中夏的笔名。
(三)在田诚发表于《向导周报》的11篇文章中,如果考证出《“今日”派之所谓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今日”派》)(不必篇篇都考证)是李大钊所作,那就可以证明田诚即李大钊。
之所以选择《“今日”派》,是因为,在这11篇文章中,此文字数最多、分量最重、最具代表性,最容易认定田诚即李大钊。
《今日》杂志第2卷第4期既泄露了中共中央核心机密,又迫使中共中央必须表明态度。
《今日》杂志1922年2月15日创办于北京,社址位于慈惠殿5号,由当时的新共和党党员胡鄂公、熊得山、邝摩汉等人联合创办。初定为月刊,实际并未按月出版。目前我们所能见到只有从第1卷第1期到第3卷第2期(此期1923年8月6日出版)共10期的内容,如果按月,到7月15日应出18期。
《今日》杂志第2卷第4期出版于1922年12月8日。此期发表了3篇文章,即熊得山的《“名”“实的讨论”》、初民的《我对于陈仲甫派变更态度的批评》、《汝为的社会主义与民治主义——并质陈独秀先生》。这3文的共同点是:强烈反对中共中央1922年8月28日—30日西湖会议[52]作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称陈独秀加入国民党是“变节”[53];称中共是“从根本上自己取消自己的资格”[54],作者此文的题目就是“我对于陈仲甫派变更态度的批评”;称“马克斯主义啊!你在中国多么倒霉!”[55]等等。作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今日派”,不知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西湖会议精神,并公开发表在他们办的杂志上,这是将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公开泄露出来,迫使中共中央必须表明态度:如果不公开发表文章,对他们予以反驳,就等于他们默认中共中央在西湖会议上确有这个决定;如果公开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同样证明中共中央在西湖会议上确有这个决定。无论中共中央怎么做,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中共中央经过权衡,决定对“今日”派予以反驳。这个任务落到了田诚身上。
田诚是谁呢?
肯定不是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和普通的共产党员。因为西湖会议决定中共领导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件事和他们没有关系,因而,西湖会议精神无须向他们传达。
肯定不是中央“一把手”陈独秀。因为《今日“派”》一文说:“在他们那几篇文章里面把陈独秀同志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认为是他变节了。这个多么可笑呢?谁也知道陈独秀同志是多年的老革命家;老早就是共产主义旗下最勇敢的战斗员,历年不断的用全部精力为共产主义作战。那些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马克思派,也有这种资格来说共产党员变节,这不是太可笑了么?”[56]这段话,完全可证田诚不是陈独秀。
可以肯定,田诚是除陈独秀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员。这里我们用排除法来考证,谁不是田诚。据笔者统计,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的另外4名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发表3篇,用的是“致中”笔名;张国焘发表12篇,用的是“国焘”、“国涛”笔名;蔡和森发表52篇,用的是“和森”笔名;高君宇发表文章21篇,用的是“高君宇”、“君宇”的笔名,他们4人从未用过田诚之名,因此,田诚绝不会是他们4人中的1人。排除了以上5名中央执行委员(包括陈独秀),剩下的就是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了。实际上,李大钊在这里亦是排在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第二位。反驳“今日”派的任务,在不由陈独秀承担后,最适宜的人选,就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中排序第二的李大钊。以上(一)(二)(三)中,分别是李大钊、田诚、李大钊排在中央执行委员的第二位,这足以说明田诚就是李大钊。
本文考证出李大钊分别以列武、子棠、其颖、罗敬、田诚为笔名发表在《向导周报》的36篇和以罗敬署名发表在《政治生活》的2篇佚文,如果能得到李大钊研究界的认同,建议《李大钊全集》(修订本)再版时,将这38篇佚文予以收录。
[1][2][3][4][5][8][10][11][13][15][19][4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27-234.584-587.588-594.606-615.273-281.32.28. 28-31.31-32.33.34.298-299.
[6]陈玉堂.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6.
[7][9][12][14][16][17]向导周报(110).均见1924-04-12.
[18][20][21][2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35.106.113.270
[23]这两文分别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7.102-107.
[24][25][26][27][28][29][30][31]陈玉棠.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92.209.192.201.203.206.211.211.
[32]陈玉棠.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1.周家珍.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16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84.
[33]于光远.忆国务院政研室[J].百年潮,2000,(7).
[34][35][36]赵世炎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426.425.584.
[37][38]向导周报(116).1925-05-24.
[39][40]向导周报(108).1925-03-28.
[41]萧超然等主编.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956.
[42]政治生活(26).1924-12-21.
[43]政治生活(38).1925-05-01.
[44][45]政治生活(62).1925-12-30.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二大”和“三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21.
[48]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25.
[4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32.
[50][51]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82.143.
[52]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989.83.
[53][54][55]今日(2卷4期).1922-12-18.
[56]向导周报(15).1922-12-27.
(责任编辑:张颖)
D231
A
1674-828X(2014)02-0102-11
2014-03-10
冯铁金,男,中共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主要从事李大钊轶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