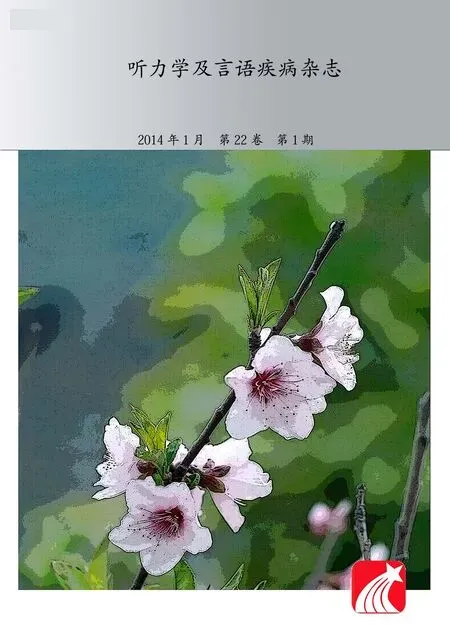新生儿听力筛查、诊断、早期干预的影响因素*
2014-02-10杨影综述孙喜斌审校
杨影 综述 孙喜斌 审校
随着新生儿听力普遍筛查(universal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UNHS)项目的发展,不同程度听力损失的婴幼儿在6个月内即可得到诊断和干预。在UNHS项目实施之前,永久性听力损失的儿童约3岁后明确诊断,听力损失程度与发现年龄呈反比,配戴助听器和/或人工耳蜗植入的年龄更大,严重影响了听障儿童听觉、言语、语言、认知以及社会交往等能力发展;在UNHS开展后,永久性听力损失儿童可得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尤其为听力损失婴幼儿的治疗和听觉言语康复训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然而,从新生儿听力筛查到听障儿童的早期干预过程受很多因素影响,本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为新生儿听力筛查、诊断和早期干预等一体化工作模式和康复技术的研究提供参考。
1 影响新生儿听力筛查和诊断的因素
目前,国内外多采用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POAE)和自动听性脑干反应(AABR)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越来越多的听障婴幼儿在出生后3个月即可得到诊断[2],而新生儿及婴幼儿听力筛查和诊断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缺乏筛查设备 开展UNHS项目的医院要有合格的筛查设备、标准的测试环境和专业培训的筛查人员等条件才能申请UNHS项目,经考察合格获得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许可证后才能进行大规模的UNHS。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域发展不平衡,截止2010年,我国内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程度开展了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3]。但有部分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偏远地区医疗机构并未开展UNHS项目;另外,新生儿从筛查到诊断要几次去筛查和诊断机构,而有些基层单位缺乏筛查设备或筛查设备不可靠导致家长必须带小儿去更大的医院或诊断中心,导致筛查率和转诊率降低,进一步影响诊断、干预和随访[4]。
1.2记录结果多样化 新生儿的听力筛查设备多种多样,各个地方记录结果的方法和格式差异很大,没有统一的记录标准或者是记录结果不规范,导致转诊到上级医院时要重新做听力学测试,患儿档案管理的信息缺失,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给听障儿童的家庭造成一定的损失和负担[5]。卫生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统一记录标准和规范记录方法,为筛查、诊断、干预过程的工作人员、听障儿童及家庭提供更好的专业服务和信息。
1.3缺乏专业的早期干预人员 听障儿童早期干预人员包括听力学家、儿科医生、言语病理师、聋儿教师、学前儿童的特殊教育者、双语教育者、社会工作人员以及心理学家等,多领域人员之间要相互交流与协作,早期干预人员要接受专业培训,内容包括早期干预的咨询、听觉发展、言语发展、符号语言发展、语言发展、认知发展和社会情感发展等方面的康复训练内容及评估方法[6,7],强化听觉言语康复训练的同时也更关注听障儿童的全面发展。
经开展UNHS的接产医院、儿童医院和妇幼保健院统计显示,未通过筛查的听障婴幼儿约为2‰~3‰,新生儿重症监护中心(newborn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的比例更高,约为20‰~40‰。在国外,通过筛查发现的听力损失婴幼儿常先就诊于儿科,而能完成诊断性测试的专业儿童听力学家非常缺乏,尤其是农村地区,听障婴幼儿要到很远的地方进行完整的诊断性测试和寻找好的治疗方法[6]。大部分儿科医生在未通过UNHS的儿童随访计划中有首要责任,很多原因导致他们没有得到筛查结果或者诊断性听觉评估的结果,从而影响了干预和随访工作[8]。而且,很多儿科医生缺乏对听力损失相关知识的认识,导致其没有参与到新生儿听力随访工作中来。文献报道在UNHS计划中约33.33%的儿童学家不看筛查结果,导致医生和家长对听力损失不重视,进一步影响听障儿童的早期诊断和干预[7]。目前,我国新生儿听力筛查多集中在妇幼保健院、产科和耳鼻咽喉科,未通过筛查的新生儿和婴幼儿要转诊到听力障碍诊断中心进行综合听力学评估,缺乏儿童听力学家,缺少系统的小儿听力学专业教育,没有“儿童听力学家”、“听力师”、“听力医师”、“言语病理师”和“言语康复师”等职业。因此,针对以上问题要加强听力学、言语病理学、康复教育等专业的建设,解决职业资格和相关法规问题[9]。
1.4早期干预的支持体系尚未健全 听障儿童早期诊断和干预过程需要听力学工作者、儿科医生、妇产科医生、耳鼻咽喉科医生、特殊教育学工作者、家长以及其他社会工作领域等多学科、多领域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只有多部门、多领域人员的沟通与协作才能把筛查、诊断、早期干预一体化服务落到实处。自2004年我国发布《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规范》[10]开始,全国各省(市)陆续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2009年提出《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11]和《新生儿及婴幼儿早期听力检测及干预指南》[12],明确了新生儿听力筛查是全国新生儿三大疾病筛查之一。目前,我国的“筛查中心”和“诊断中心”的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筛查率可达90%以上,其他地区的筛查中心多着重于筛,缺少整体管理、随访和数据库建设,诊断中心没有将诊断结果上报“筛查中心”与其建立联系,导致部分听障儿失访,并不能得到早期干预[9]。2010年卫生部颁布新版《新生儿听力筛查技术规范》,修改方案中明确指出复筛未通过新生儿应在3个月内转诊至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听力障碍诊治机构进一步诊断,并增加了随访和康复的环节[13]。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筛查、诊断和随访系统,而多学科多部门间的交流协作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需建立医疗部门、康复机构、社区等多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另外,我国的质量保障和监督系统尚不完善,应组织制定考核评估方案,定期对筛查机构和听力障碍诊治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改进措施[7]。
1.5缺乏早期干预服务知识体系 在听障儿童康复的过程中,早期干预服务知识体系发挥重要作用。1970年,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建立了家庭干预计划(home intervention program,HIP),并建立了“共同的听觉协作系统”作为初始的交流平台,为家长提供初始阶段的咨询、指导、教育需要,在发现听障儿童的早期,让父母针对孩子的情况选择更好的早期家庭干预服务[7]。最近,Wood等[14]对有特殊健康需求家庭的医疗服务满意度进行调查,在特殊儿童健康服务中对治疗工作人员不满意度约为13%~14%、与儿科医生交流不满意度达10%、参与治疗决定的不满意度达15%~16%,值得注意的是有58%的家庭对儿科医生的能力和提供的家庭服务资源不满意,这表明听力学工作者、儿科医生和相关工作人员应提高社区资源相关知识体系,提供更好的知识和服务,减轻家庭的压力。然而,早期干预服务知识体系的建立需要社会支持、经济支持、工作人员支持、听障儿童父母的支持以及早期干预资源有关的信息支持,才能为听力损失儿童提供更好的指导和获得可靠信息的途径[15]。
目前,国内听障新生儿和婴幼儿早期干预服务知识体系尚不完善,尽管各专业人员之间的协作是家庭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多专业人员缺乏相关知识和当地服务信息,也不能指导家长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和干预模式[9, 16]。应加强与先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为听力学工作者、儿科医生、耳鼻咽喉科医生、康复人员和保健人员提供和更新相关的专业知识,熟悉和了解听障儿童早期干预服务的相关内容和方法。
1.6社会医疗保障不健全 随着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的不断进展,越来越多的新生儿和婴幼儿需要听力服务和教育服务,服务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听力学的诊断、评估和治疗;②听力学功能测试;③助听器服务;④人工耳蜗植入服务;⑤辅听装置服务;⑥听觉言语发展等康复训练服务[17]。Jimenez等[18]从听障婴幼儿父母和早期干预人员的角度对早期干预服务进行评估,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①家长与儿科医生交流有问题,包括医疗保险的误解和不能理解儿科医生推荐的转诊程序;②许多父母认为他们自己是孩子发育方面的专家,应该由他们决定是否让孩子接受早期干预服务;③一些家庭在早期干预之前更倾向于解决孩子发育中的问题,而不是听力障碍引起其他方面能力发展障碍和长期听力障碍引起的严重后果;④摇摆不定的家长遇到困难就很难完成早期干预评估,部分积极性高的家长可以克服困难完成评估过程;⑤早期干预人员认为家庭不选择评估的原因是他们误解了早期干预,其实早期干预是对孩子的保护性服务。
听障儿童早期干预服务来源于社会资源的支持,医疗补助是早期干预服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美国大约有33.33%的儿童参加了医疗补助,这种补助的服务就是让儿童进入早期筛查、诊断和治疗的过程,重视孩子健康问题的早期预防和早期治疗[17]。随着UNHS的发展,我国也提出将UNHS列为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经费由政府负担,同时将干预项目列入医保和基本医疗服务,目前北京、上海和江浙部分经济发达省市已经开展和实施[9],北京地区在2012年3月率先开展新生儿耳聋基因免费筛查。但我国超过9亿人为农村人口,地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大部分地区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尤其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还有待于进一步推广和实施。
2 影响早期干预的因素
2.1早期干预时间 在UNHS项目中,要求被诊断为永久性听力损失的听障婴幼儿争取6个月内进行干预,在配戴助听器前明确病因和进行病原学询问,根据结果采取合适的治疗手段和干预措施[6]。目前,国外主张对小于10月龄听障儿童行助听器验配,10月龄以上的听障儿童根据听力损失程度进一步行助听器验配和/或人工耳蜗植入,同时进行早期康复训练[7]。我国现阶段首先推进UNHS,不具备条件的单位采用目标人群筛查的策略,将有听力损失高危因素的新生儿转诊到有条件的筛查单位,偏远地区的所有婴幼儿都应在6个月内接受听觉发育观察表的调查,所有确定为永久性听力损失的婴幼儿都应在6月龄内实施早期干预[12]。目前,我国北京、上海、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听障儿童可在早期进行干预和康复,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尚未能实施UNHS和早期干预计划,需要政府部门和各领域人员的进一步支撑。
2.2早期干预模式 听障儿童早期干预康复训练模式一方面包括专职人员访问特殊家庭和集中到社区、残联的干预模式以及专门机构进行培训以父母为主的干预模式,前者可以提高家庭信心、帮助父母制定计划并演示康复过程,后者包括家长心理辅导、康复知识、辅导孩子发展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包括深入家庭的早期干预模式和中心式的早期干预模式,前者不脱离孩子熟悉的环境并在家长协助下对孩子进行康复治疗;后者由家长陪护到早期干预中心,老师对儿童进行正规的集体教学,安排儿童参加小组活动,教家长一些训练方法[7]。UNHS实施后,听障婴幼儿的发现年龄越来越小,家庭早期干预模式也越来越受关注,以尽早为听障儿童进行听觉言语康复训练[15]。目前,我国听障儿童早期干预以听障儿童集中到康复机构的模式为主,婴幼儿的家庭康复模式及以社区为中心的康复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2.3早期干预评估 早期干预评估包括从医疗系统到教育系统的过渡,很多家庭此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6],评估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方面包括言语能力、语言能力、交流能力、听觉处理能力和听觉言语康复水平的评估;另一方面包括对以上能力进行康复教育的效果评估[17]。早期干预的评估工具一方面包括问卷、量表、活动视频、听觉测试、言语测试等各方面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估方法,另一方面包括教学康复记录评估和家庭康复记录评估等方法。言语和语言发展是衡量听觉康复效果很重要的指标,由于我国的地区、民族和语言差异,还需要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寻找适合自己国家和地区的评估方法。
3 影响随访系统的因素
3.1随访时间 在国外,对有致聋危险因素但筛查或诊断听力正常的婴幼儿,建议随访到3岁,随访的内容包括听力学检查、言语、语言、认知、运动和社会情感评估等方面[5,6];我国《新生儿听力筛查技术规范》增加了随访环节,指出诊治机构负责可疑患儿的追踪随访,对确诊为听力障碍的患儿每半年至少复诊1次,筛查未通过的NICU患儿应当直接转诊到听力障碍诊治机构进行确诊和随访,并且特别强调对NICU患儿需进行听力监测,即使通过筛查仍应结合听性行为观察法,3岁以内每6个月随访一次[12]。
3.2失访率高 法国学者对1 461例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结果分析,约4.55%的婴幼儿诊断为听力障碍,60例婴幼儿最终进入早期干预阶段,而在早期干预过程中约10%的婴幼儿失访[19],高失访率进一步影响了听障儿童的早期诊断和干预。美国国家数据显示接近50%初筛未通过婴幼儿没有听力诊断记录,大部分是归因于失访或失去记录,而近33.33%永久性听力损失婴幼儿没有接受早期干预的记录[6]。最近,Chen等[4]对我国5个县的11 568例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其中135例新生儿复筛未通过,仅有90例进入诊断性评估,复筛后的失访率高达33.33%。说明政府应该采取紧急措施和相关政策促进农村地区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诊断工作。同时,在UNHS工作中由于缺乏相关专业指导,许多实施UNHS的医院缺乏标准的筛查原则,不能呈现标准的筛查结果,而且仅部分筛查人员知道如何向家长解释筛查结果,这也影响了未通过筛查的婴幼儿家庭决定是否进一步随访[7]。
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UNHS必须由政府来组织和发动才有可能实现[6],在早期诊断和干预的过程中,听障儿童的高失访率提示应将听力损失对儿童产生影响的相关知识提供给进行UNHS的工作人员、儿童家长和医护人员[19],这样才能引起更多人关注听障儿童,使其进入早期干预的过程。
4 展望
新生儿筛查、诊断、早期干预到随访等过程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听障儿童早期干预一体化的服务模式和技术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以便帮助更多的听障儿童从早期干预中受益。
5 参考文献
1 Yoshinaga-Itano C, Sedey AL, Coulter DK, et al. Language of early- and later-identified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J]. Pediatrics. Nov,1998,102:1 161.
2 Kennedy CR, Kimm L, Dees DC, et al. Otoacoustic emissions and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s in the newborn[J]. Arch Dis Child,1991,66:1 124.
3 韩东一, 王秋菊. 新生儿听力筛查的发展与未来[J].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11,46:177.
4 Chen G, Yi X, Chen P, et al. A large-scale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in rural areas in China[J]. Int J Pediatr Otorhinolaryngol,2012,76:1 771.
5 White KR, Forsman I, Eichwald J, et al. The evolution of early hearing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J]. Semin Perinatol,2010,34:170.
6 Russ SA, Hanna D, DesGeorges J, et al. Improving follow-up to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a learning-collaborative experience[J]. Pediatrics,2010,126(Suppl):S59.
7 Yoshinaga-Itano C. From screening to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discovering predictors to successful outcomes for children with significant hearing loss[J]. J Deaf Stud Deaf Educ,2003,8:11.
8 Committee AAoPNSA.Newborn screening expands: recommendations for pediatricians and medical homes--implications for the system[J]. Pediatrics,2008,121:192.
9 卜行宽. 我国新生儿听力筛查新里程中的思考[J]. 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2010,10:273.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规范.2004-12-15.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64号).2009-02-16.
12 黄丽辉, 倪道凤, 李兴启,等. 我国婴幼儿 “早期听力检测及干预指南” 编写思考[J].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2009,17:93.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规范(2010版).2010-11-27.
14 Wood DL, McCaskill QE, Winterbauer N, et al. A multi-method assessment of satisfaction with services in the medical home by parents of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special health care needs (CYSHCN) [J]. Matern Child Health J,2009,13:5.
15 Fitzpatrick E, Angus D, Durieux-Smith A, et al. Parents' needs following identification of childhood hearing loss[J]. Am J Audiol,2008,17:38.
16 Dorros C, Kurtzer-White E, Ahlgren M, et al. Medical home for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 physician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J]. Pediatrics,2007,120:288.
17 McManus MA, Levtov R, White KR, et al. Medicaid reimbursement of hearing service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J]. Pediatrics,2010,126(Suppl):S34.
18 Jimenez ME, Barg FK, Guevara JP, et al. Barriers to evaluation for early intervention services: parent and early intervention employee perspectives[J]. Acad Pediatr,2012,12:551.
19 Ohl C, Dornier L, Czajka C, et al.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on infants at risk[J]. Int J Pediatr Otorhinolaryngol,2009,73:1 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