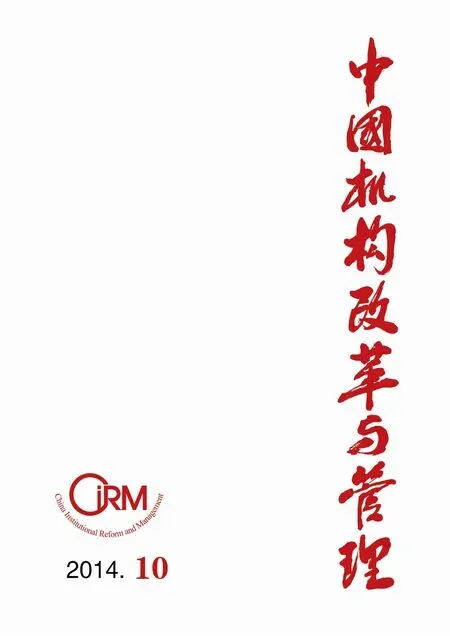论点摘编
2014-02-03
论点摘编
“中国模式”的成功缘于一整套制度安排
张维为在2014年9月22日《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解释“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一整套制度安排上。可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协商民主”,这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是“选贤任能”,即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在经济制度方面,是“混合经济”,力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
反垄断的核心是反行政垄断
2014年9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访问上海司法研究所所长杨寅的文章,他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比较充分的国家,反垄断主要是针对企业集中等问题,排除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然而在市场和政府的职能区分并不十分清晰的情况下,行政职能被滥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中国出现行政垄断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权和市场权的配置及分工仍存在不合理。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掌握资源配置,决定产业发展,甚至直接参与某些产业投资,这种“非市场化”或者“半市场化”的现象成为制约市场活力的重要因素。地方保护主义的长期存在,可能加剧了某些行政垄断行为。破除行政垄断,需尽快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专业的、统一的、有权威性的国家反垄断执行机构,有效强化反垄断力量。反垄断机构作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执法者,无论是面对国内有上级监管的国有企业、金融企业,还是有国外政府组织支持的外资企业,抑或是地方行政机关,都应“一视同仁,同罪同罚”。
县乡行政管理层级改革不宜“一刀切”
杨嵘均在《公共行政》2014年第8期撰文对县乡行政管理层级的结构调整与改革路径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县乡行政管理层级结构改革和创新的出发点在于把该下放的权力下放,减少管理层级,降低成本,提高地方基层治理的效率与效能,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国行政管理层级结构的改革方向,是将现行的五级层级结构模式改为“中央、省、县”三级层级结构模式,由省直接管县。但乡镇一级政府是否要改为农村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尚需商榷。改革决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迥异、人口众多、资源禀赋差异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基本事实,即使在同一省内,各县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一刀切”地将乡镇改为农村基层社区自治组织,不仅达不到制度设计的初衷,还可能会造成民族分裂、政治分割、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等隐患。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的现实条件和实际困难,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族性、差异性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进行有针对性地调适与改革。
重新审视事业单位的社保制度改革
2014年9月23日人民网刊登了丁元竹对事业单位及其社保制度改革的分析文章。他认为,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涉及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要把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与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一道考虑,某种程度上,它们的性质相同,在国际上都可以划归到实现公共利益的机构中去,因为它们承担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标、代替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只是它们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模式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采用相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似乎无可厚非。值得争议的是,我们对公共利益、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认识,以及如何从传统的思维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中解脱出来。人们之所以对事业单位社会保障问题关注,还因为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碎片化”严重,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养老保险均不同。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半积累制的,还有其他形式,积累制与个人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每个人的收入又不尽相同,就自然造成养老金交费和待遇上的差异。一个时期以来,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施多年后,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险制度改革依然按兵不动,这难免给社会造成一种印象,即机关事业单位特殊,甚至会有人认为,个别官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延误改革,或为自己谋利。
办好小事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潘维在《人民论坛》2014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办好小事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人民是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人人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当家作主,各种小事就能迅速得到解决,人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正。对日常生活的公正和伦理道德有信心,人们心情愉快,就会支持国家,支持政府办大事。政府支持并尊重社区自治的集体权力,便能免除“小事”之扰,保持人员精干,集中财力和精力“办大事”。他还认为,“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首先,“小事”中的每一件都跨法规、跨部门,而科层系统分门别类,依法办事。哪个公务员去管,责任和风险自负。若相关的公务员头脑清楚,必定“踢皮球”,这是执法机构依法治国的理性本能。而且,公正处理小事靠的是“天理人情”而非“法治”。小事都发生在没有法律和法律模糊的地带。到处发生轻微违法的小事就只能法不责众。其次,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付得起管“小事”的高昂成本。办好小事,解决社区生活中缺乏公正的问题,不是靠严格法治、推行选举、逼官员下沉、实行彻底市场化,而是靠组织人民,靠自然社区的扁平组织,靠人民的自组织。以人民的“参与”取代政府的“覆盖”,方为正道。
发展中国家更要重视支持小微企业的成长
《南风窗》2014年第9期刊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丹尼·罗德里克的文章,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领先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与低生产率部门没有衰落反而扩张有直接联系。工业化使年轻人从农村不断涌向城市,但他们的最终归宿往往不是工厂,而是非正式的低生产率服务岗位。缩小经济中领先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的差距,要让小微企业成长并提高生产率,而这需要消除诸多壁垒,包括政府服务和基础设施、全球市场的进入、融资、工人和管理者的技能等。支持小微企业通常有助于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即维持经济中最贫困和最难就业群体的收入水平,但这无助于刺激产出和提高生产率,关键在于经济环境,以及取消政府管制和限制。政府也需要采取更具前瞻性的策略,如税收激励、投资特区或有竞争力的货币,以提高这类投资的盈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