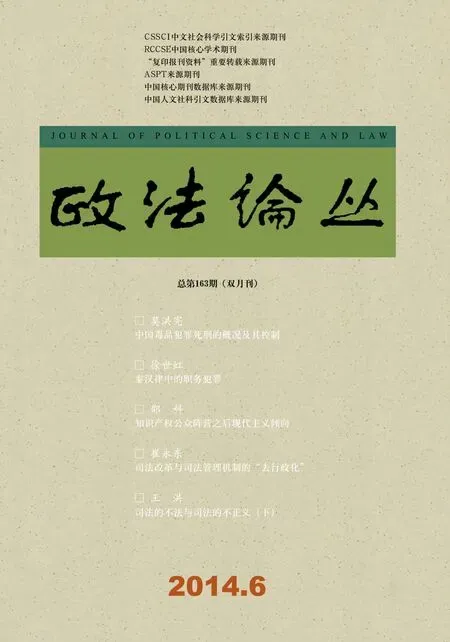知识产权公众阵营之后现代主义倾向
2014-02-03邵科
[澳]邵 科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法学院)
过去数十年中,知识产权这一全球议题在政治、商务、法律及公共视野中引发了长期、激烈、规模浩大的争论。这尤以“私权阵营”与“公众阵营”的对峙为其最大看点。这一分类法可能有些过于简单化,但却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争论的群体性特征——在争论的一端是主张利益攫取主义的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政府,而另一端则是诸如公民运动、科学家团体、自由软件运动、知识产权批判研究,或是代表发展中国家权益的非政府组织等更为广泛、多元的群体。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以维护全球化主导者商业利益及相应的高保护标准为特征的知识产权法律模式,究竟是否具有“合法性”。①众所周知,现行的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是在自由贸易框架下展开的,这就是由世界贸易组织(WTO)管辖的、高度协同化并由强国主导的法律体系。如果依照公共阵营的说法,则私权阵营使用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却似是而非的说辞、理论、公关手段以及法律与商业的策略,以纹饰其追求利益攫取主义的用意,和对永续创新、教育、人权、环境保护、粮食安全、技术转让、医疗及公共健康等全球重大议题的漠视。
公众阵营参与上述激烈争论的方式是高度发散性的,牵涉到法律、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等许多领域。在这些广泛的、多元的参与方式中,可以看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公众阵营有一种不约而同的认知倾向,即将私权阵营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及其历史轨迹,诠释为权力话语作用的结果。权力话语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词汇。对于法学、政治学或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而言,这并不是新鲜事物。在知识产权法领域,虽然国外研究者极少使用后现代主义来定义自己,但他们大多对后现代主义的宗师、大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之“作者是现代性的发明”这一著名论断耳熟能详或表示赞同。福柯认为,作者观念的现代性,是以作品的私人财产权化为其特质的。②虽然如此,国际知识产权法学的批判研究似乎并未接受福柯后现代主义的直系衣钵,而是倾向于关注著名英国文学史家马克·诺斯(Mark Rose) 等学者对欧美知识产权的历史考察。诺斯撰于1993年的名著《作者及财产权人:版权的发明》(Authors and Owners: The Invention of Copyright)对知识产权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该书中,诺斯指出,现代作者、版权,以及其支撑的西方知识产权商业模式之出现,与17世纪拥有绝对垄断权力的英国出版行业,存在着内在的、深刻的联系。③
本文拟依据后现代主义的原理来解读西方知识产权公众阵营的论争现象。笔者将使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公式来匹配公众阵营的主要研究成果,以考察后现代主义对这一阵营的影响。在此,本文要进一步指出,后现代主义在诠解全球知识产权的权力主导现象方面极有裨益,但如若引入被西方权力话语排除的中国知识产权历史经验,则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便可能需要作出一定的补充或调整。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知识产权的产生不必然是权力话语的结果。因此,批判地对待知识产权的全球不合理扩张,不必然要否定知识产权制度本身。
一、后现代主义及解构
后现代主义是后二战时代的产物,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式回应。从20世纪末开始,它日渐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流行起来。④要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精确的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它包含了一系列极为不同的概念、方法及流派,涉及到批判理论、哲学、建筑学、艺术、文学、文化研究、法学等不同领域。但是,所有学派几乎都同意后现代主义思潮及解构主义的领军人物、法国学者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一句名言:如果将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极度简单化,那么,我认为它是指对于大叙事(metanarratives)的怀疑。⑤
大叙事是指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叙事方式,旨在通过一定的逻辑组合将某种知识或经验描述为真理。⑥福柯对叙事方式的过程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权力-知识”的连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科学不是中立的,而是由权力影响或宰制的某种特定话语结构左右。福柯相信,在权力之外没有真理,始终只是权力在创造知识被构建、被叙述或被驱逐的过程。⑦在此,权力的定义可以是宽泛的,不限于统治者用来压制不同意见的政治或宗教话语权。正如下文将要分析的,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跨国公司强大的政治、立法及全球化影响力,是福柯式的“权力-知识”架构中的主角。如果将福柯的主张推展开来,则似乎没有任何事件是完整的真理,而只是不同角度对现象的叙事。
当代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擅长通过解构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任何一组叙事的结构。这种方法论被认为是用以怀疑、驳倒或推翻传统定义上的理性或确定性的强大理论武器。德里达的研究表明,任何语言叙事的结构都不是中立的,而是用来创建、维护等级制度。在一组概念中,总是存在着优先顺序。⑧比如,善为正、恶为反;国家主权总是包含褒义,而无政府主义总是名声不佳。就知识产权领域而言,私权阵营将一切反对他们利益的行为,都认定为是邪恶的、不重要的或是已经得到合理保障的。因此,“保护知识产权”这一内涵不明确、外延可以无限扩大的措辞,就变成了不容质疑的六字真言,而盗版、侵权之类的含糊用语,便可以在不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任意使用在各类场合。
知识产权研究者有时会引述福柯的观点,或是受到福柯式分析方法的影响。比如,在批判知识产权强权理论时,他们经常会使用诸如独创性、作者观念(authorship)等具有福柯气息的词汇。福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作者是一个新近的发明,并且单一地指向私人所有权和对知识创新成果的财产权化的过程。这一福柯式的论证对现代知识产权研究影响颇深。英国文学史家马克·诺斯(Mark Rose)或是欧洲历史学家戴维·颂德斯(David Saunders)等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⑨虽然他们不是法学研究者,但却对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在知识产权批判研究的领域,公众阵营对知识产权的批判大多是围绕知识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和作为财产权的知识产权之对立来展开的。
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绝非无懈可击,但对于许多发生于西方社会的现象而言,却又能无奈而真实地作出精彩的诠解——它显然可以很好地描述知识产权领域发生的许多不合理现象,它当然也深刻地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普遍存在于西方现代生活之中,表现为只关心自我利益维护的“自说自话”的对话模式。在知识产权领域,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政府拥有强大的国际游说与政策影响力,他们发布了大量旨在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报告、立法、言论及演说,明确地反映出权力-话语这个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二元现象。比如,他们在推进不利于他国综合发展的知识产权法律时,只是反复强调知识产权对本国经济的好处,或是在现行国际贸易等级制度前提下对穷国脱贫的好处,却从来不提其他诸如公共医疗、穷国教育及创新前景等更为重要的议题,仿佛这些议题根本不存在。当然,这些议题自有对立的组织提出,因此形成一种对立、抗辩的阵营文化,这就是“自说自话”的对话模式。
相反地,在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固然是尊重一多相融、求同存异的对话模式,但不同意见持有者共同遵守的是“真理本身”,所谓道理最大,关注的是谅己谅人的利益兼顾,而不是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发表有利于自己的观点。这当然仅是从文化特征上讲,而非是从历史上讲的。显然,这种明道致理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获致完全的实现。就本文而言,中国文化中一多相融的文化特征,可以视为对作为哲学的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根本否定。
二、西方知识产权的大叙事
在私权阵营看来,知识产权是不容置疑的、神圣的财产权利,甚至将之称为人权。美国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办公室的官方表述具有代表性。依据其官方网站的声明,该办公室的使命是在“全世界推动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以“增加美国商业及私营经济的增长与投入,并为美国产品与服务开拓市场”。⑩在这一叙事中,我们只看到美国企业“皇威远届”的强大权力或自由,而看不到其他群体(包括美国国内的公众群体)的利益。这令人不禁想起将知识产权描述为“人类自然的需要”、普世价值或是“永恒的观念”的一些诗化语言。这些绝对的、权力主导的大叙事不是凭空降生的,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哈佛大学法学家安守廉教授(William Alford)在试图论证古代中国没有知识产权时就曾说:一言以蔽之,自从17、18世纪以来,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展出了一种观念,即认为作者、发明人应当在他们的创造力成果中享有可以不受政府权力干扰的财产权。
在此,安守廉采用的也是大叙事的方式。先不论知识产权是否是不受政府干扰的权利——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立法中,可因紧急情事或中央政府之需,在不经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专利充公,单就安守廉的叙事方式来看,他和美国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办公室的理解视角并无不同,也是先验地将西方的知识产权模式视为正当而不容质疑的。同理,在对现代作者观念的经典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史教授伊恩·瓦特(Ian Watt)天真地认为,现代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在资本主义、新教运动和个人主义等背景下诞现的。这种“浪漫主义”十分滑稽,且只能推导出一个结论:既然知识产权是17-18世纪先进的欧洲社会“个人觉醒”的结果,那么,知识产权(当然仅是指欧美模式里的知识产权)岂能不是普世价值?如果是这样,那么大量象美国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办公室这样的机构,当然只需要在全球维护这一永恒的普世价值就足够了。
安守廉和瓦特所艳羡与称道的在17-18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发展出的“神圣”的知识产权财产权观念,指向的是17-18世纪开始形成的知识产权的洛克自然权利论,这一理论简洁而强大。在其不朽名著《政府论》中,伟大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庄严地写道:尽管土地及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我们可以说,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是正当地属于他个人。…… 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或导致的原始状态,他就已经掺入了他的劳动,并已在此物上增加了他个人的东西,从而使之成为他的财产。…… 既然相应的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的其他任何人便不得对之享有权利。
如果说人们拥有自己的身体是不容质疑的,那么拥有身体劳动产生的成果(包括脑力劳动成果),便当然是不容质疑的。洛克也为其强大的财产权设立了某些限制,比如不能妨害其他人的劳动权益,但这些限制都是消极主义的,其唯一目的乃在于论证强大财产权的正当性。正如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言,洛克试图在充沛的公有资源和强势的私人财产权之间寻找妥协点,但他的财产权却事实上吞噬着公有资源。更严重的是,在洛克理论中,找不到促进永续创新或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可能性。著名知识产权学者麦克尔·卡瑞(Michael A. Carrier)曾说,西方法院、评论者和企业大多将知识产权描述为不应受到任何限制的绝对化的财产权。观诸洛克理论的特性,出现这种局面实是必然的。
洛克财产观之所以会出现此种倾向,根本上是因为他主要地从个人本位来解读财产权。洛克为个人财产权所设定的所有崇高目标及道德限制,其根本目的在于防止他那个时代君主权力的滥用而对个人权利的妨害,而不是为了关注公益。因此,洛克式的自然财产权本质上具有绝对的、神圣的、不断向外延展的意涵,而不是可妥协的或愿意接受较多的限制。这种个人本位的结果是一种消极的反证——只要洛克为财产权设定的限制原则获得满足,便没有任何理由不赋予财产权。显然,很难说这种个人本位的财产权观念的特性,其每个细节都是深植于自然法则的正义。比如,完全有理由论证社群本位的财产权观念才更符合自然法则中的公平与正义。
三、解构知识产权话语权
公众阵营对上述安守廉、瓦特或洛克式的叙事方式不以为然。他们拒绝“浪漫主义”,而是依靠历史微观细节来审视欧美知识产权历史上权力话语之嬗变过程。他们认为,现代西方语境中的知识产权概念及实践,绝非是普世价值,而是由权力支配者依照他们的利益需求炮制的。正如颂德斯指出的,浪漫主义的知识产权史观将(西方定义上的)作者认定为历史的必然结果,这是忽视了它产生的偶然性。据此,关键的问题乃在于,既然西方模式下的知识产权不是“人类自然的需要”这种必然结果,那又是何物催生了西方式的作者观念以及它背后强大的洛克自然权利论等有力捍卫商业利益的模式呢?如果从历源头来看,则马克·诺斯及出版研究史专家约翰·费瑟(John Feather)等对欧洲知识产权的详细考察表明,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群体——英国伦敦的出版垄断行会,主导了洛克自然权利论在智力成果领域的嫁接,并从此在欧美及全球的知识产权立法中产生了持续至今的、关涉根本的影响。
在所谓人类第一部现代版权法《安娜法案》(1710年)颁布之前,英、法等国的出版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极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是政治、宗教权力对书籍出版进行过十分严厉的出版前审查。作为一种对价交换,王权赋予了出版行会垄断市场的绝对权力。这种垄断被限定在伦敦和巴黎地区的印刷行会内部。1557年,英国国王敕令建立伦敦出版公会(London Stationers’ Company)。王室颁予出版公会的章程上,明确规定道:在英国领土之内,除伦敦公会成员之外的任何人,均不得从事印刷出版一业。这一章程因此授予伦敦公会以绝对垄断的印刷权利,而禁止伦敦以外的所有印刷出版;并且,理应属于可以自由翻印之列的古籍,其出版权亦完全为公会成员所独占。这一制度所导致的垄断是惊人的,它实行后仅仅二三十年,相当数量的极珍贵书籍之出版权,便被极少数公会成员高度垄断了。法国国王采取的措施更为严苛。从1686年开始,路易十四将巴黎印刷公会的成员,恒定限制在36名。如若要想成为这36名成员的一分子,除需要在印刷行会内忍受长期的学徒生涯、接受行会首领及巴黎大学校长的考核,以及支付高昂的行会费之外,更需要在漫长的时间内等待36名成员之一的过世。
对于本文的视角而言,这种绝对的垄断培养了一个可以影响政治权力话语的团体——垄断出版商。在1694年左右,作为王权言论垄断核心组成部分的伦敦垄断出版商,开始面临反王权的国会的巨大压力。但是,这些出版商并非小人物,而是具有一定的政治与产业影响力。他们积极游说,以期获取国会的支持。经过数番尝试,出版商们发现,风靡当时英国社会的洛克自然权利论,不但对出版商有利,而且也是国会可能认同的解释知识产权正当性的“合理”理论。英国的模式很快被处境相同的法国仿效。1726年,巴黎出版行会委任了一位所谓的法学家来鼓吹洛克自然财产权论,主张作者的财产权以及作者通过契约而转让给出版商的财产权,均应受到法律保护;即使作者离世,只要此一财产权仍在出版商手中,便仍然有效。根据此种洛克论,1777年的一项法令规定道,作者对其作品拥有特权(privilèges d’auteur),除出售给第三人外,此一权利永久地为作者及其后嗣享有。在此之前,出版权则被认为是法国国王的恩惠。
上述17-18世纪知识产权嬗变过程中的权力介入现象,在西方知识产权的发展史上并非是唯一的。剑桥大学教授莱昂内尔·本特利(Lionel Bently)等学者曾对英国19世纪狂热的知识产权立法进程进行过详细的考察。这一立法进程涉及到专利、版权、商标等所有知识产权的门类,可视为相关法律的标准化过程。换言之,17-18世纪以来在英国出现的有关知识产权的一系列理解与实践,最终在19世纪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扩张,并且在立法、司法上“固化”为西方知识产权的特定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标准化、固化的背后,是商业利益的主导。正如权威知识产权学者格雷默·杜特菲尔德(Graham Dutfield)的研究所表明的,20世纪西方的专利法,是根据一些主要行业的利益书写的。
这种权力积极介入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且仍在不断延续。众所周知,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知识产权的游说行为急速增长,并弥漫到全球各种公共机构、学术团体和商业运作之中。对此,知识产权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军人物彼得·达沃豪斯(Peter Drahos)和苏珊·赛尔(Susan Sell)进行了充分的实证研究。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WTO框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是一小部分意欲经由国际知识产权框架来维持其全球市场的跨国公司积极游说的结果。这些公司的总部大多设在美国,掌握着全球经济的命脉。公众利益或是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议题。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过程中被边缘化或妖魔化,极少能够捍卫其自身权益。在后TRIPS时代,发达国家又通过双边协议、区域协议等方式,和一些国家签订比TRIPS协议要求更苛刻的知识产权条款,以期在国际贸易中占有更多的利益。这种商业利益的主导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因此进展并不十分顺利。但是,仍然有一些国家出于无奈,接受了这样的协议。
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话语权十分强大。而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情,也并不是一句口号。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兴起了公民运动和非政府组织,以支持自下而上的反对知识产权霸权的运动。达沃豪斯在其名著《知识的全球化管理》(2010年,剑桥大学出版)中,曾提到他访谈时的一段详细亲身经历,对于我们理解何为不合理的知识产权话语权而言,最为发人深省。他写道:菲律宾一位卫生部门的官员,也许是觉得我应该和一些真正受影响的人们见个面,乃安排我与一个妇女群体会晤,她们负责一项名为“削低价格减轻苦”的获取药品运动。这些妇女知道专利制度的问题,但我却无法帮助她们。她们告诉我,在菲律宾,肺结核治疗的每日开销是50披索,而一家六口人一天的收入仅约250披索。……但菲律宾食品与药品局的对策是什么呢?……通过对该国食品与药品局的拜访,我看到了寻常不过的赌徒行为:“每天,这些[外国]公司都会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他们的专利权”。……如果菲律宾专利局的审查员被要求进行检索,他们会拿出欧洲专利局批准的权利要求书,告诉食品与药品局某种专利是存在的。食品与药品局由此便不会授予非专利药品公司经销许可证,直至与大型医药公司的争议解决为止。……加拿大的非专利药品行业认为,只有通过强势的诉讼途径,才能破除这些专利障碍。可是,在菲律宾,诉讼可能吗?
上述的回顾表明,西方知识产权学者对欧美知识产权立法过程的考察、参与或反抗,多是从权力话语的角度展开的。这种反抗现象,在权力二元对立的情况下,是必然会发生的,更是不断在发生的真实现象。换言之,从17世纪开始,西方知识产权的嬗变就遵循了一条强权主导的线路。强大的出版垄断行业运用其政治、经济资源来建立符合他们意愿的理论,并最终通过立法的模式,来确立或“固化”他们的利益。这种模式一直被广泛继承,并延续到今天的全球社会。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制度设计以及文化教育方面,以上的背景应该作为核心内容出现,以使我们对相关问题的前提及其国际大势,有明确的认知。
四、被权力驱逐的话语
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既然有权力支撑的叙事,当然也有被权力驱逐的“他者”的叙事。这导致了这些被驱逐的叙事渐渐淹没或变得无关紧要。比如,我们有多少人知道,在法国曾经存在两种完全对立却同样举足轻重的知识产权理论——财产权理论和自由无限制的知识接触理论。就后者而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许多作家都认为,对智力成果不应授予任何私有产权。在美国,19世纪杰出的法学家莱桑德·斯波纳(Lysander Spooner)坚决支持强知识产权,而同时期的美国著名作家威廉·里格特(William Leggett)则认为不应当对思想流通施加限制。虽然这两个人的观点完全相左,但却都确信自己代表了自由、私人产权和自由贸易的价值观。正如本特利所指出的,这些反对的观点,在19世纪狂热的知识产权立法进程中,被排斥或边缘化,只有支持知识产权“正史”的观点才得以保留。
与权力相左的话语固然会被人遗忘,但不应忘记的是,美国这一当代最坚定的知识产权捍卫者,在19世纪却根本不承认外国人版权。正如梅雷迪思·麦克格尔(Meredith McGill)和詹姆士·马恩斯(James J. Barnes)等人的研究指出的,19世纪的美国在法理上、政治上、舆论上都拒绝承认外国人的版权。为此,麦克格尔只好用“重印”而不是“盗版”来定义美国这一时期的版权文化。显然,在当时美国的词汇表中,没有“盗版”一词,因为“重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需要。在美国版权史上的经典案例Wheaton v. Peters(1834)中,美国法院拒绝承认洛克理论的正当性。今天的美国则完全不同。正如著名法学家詹姆士·波义耳(James Boyle)生动地指出的,在捍卫西方作家和发明家这些“创造性天才”利益的全球反盗版运动中,美国是“道德高尚”的维权先锋。美国故事的前后差别,真实地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西方社会中的权力话语架构。在西方现代性中,二元对立本来就是其文化特质。
被权力驱逐的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西方社会中的替代理论,更包括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经验。在国际知识产权语境中,中国是一个热门词汇。私权阵营娴熟地运用安守廉塑造的“中国人就是窃书不算偷”的文化形象,将中国定义为全球最大的盗版贼,并通过政治施压、立法优势和贸易制裁等方式,群起而攻之。他们完全赞同安守廉的看法,即认为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加大知识产权的干预是正当的,只是需要仔细衡量干预的合理性。在此,权力话语既未论证其西方知识产权模式之是否正当,又根本不屑于耐心了解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便径直要将代表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法律体系,强加到中国头上。总之,中国的国情、发展诉求以及历史与文化经验,统统被拒之门外。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过程,可以较好地反映这一点。
如果我们走出安守廉基于极少史料而草率得出的结论框架,则中国历史可以为当代全球知识产权论争提供丰富的经验启示。在笔者过去的一系列研究中,至少发现了两个有意义的现象:一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前现代中国的确发展出了知识产权的实践模式,尤以版权和商标最为明显;二是这些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模式,没有变现出英、法等国的垄断出版模式及基于洛克哲学的知识产权强权理论。正如前述,英、法等国的模式主导了19世纪以来以西方模式为唯一版本的全球知识产权游戏规则的“固化”,而这种固化的模式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无法在英、法等国18世纪特定的历史经验之外,找到普世的依据。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经验更象15-16世纪早期法国的模式,其知识产权的自由发展极少受到权力(特别是巨大的垄断权力)的影响或支撑,而是主要受到经济、技术变革的影响。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后现代主义关注“权力”对人类社会的话语、思想、制度的宰制现象,的确给人启发,且能够解释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在全球扩展的几百年里对他者利益的漠视。然而,如果考察中国的历史经验,则后现代主义的进路便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中国的知识产权历史固然比较原生态,没有象19世纪以来后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欧那样,发展出详细的成文立法。但正如前述,这种“固化”的成文立法有利有弊,并且体现了明确的权力-话语二元对立现象。对中国历史而言,权力没有明确地介入到知识产权这种私权的嬗变过程之中,而是作为了一种民事行为的自然、自发现象存在。
对于西方知识产权争论以及影响着公众阵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考察具有另一种价值。在公众阵营中存在着某种倾向,即认为既然西方的知识产权历史并不光彩,那么就应当弃绝这种没有历史与现实“合法性”的模式。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本·莫各林(Eben Moglen)就认为知识产权是“在道德上令人不悦的”,复提出了软件保护的“无政府主义”。这种因为反对强权而主张废除强权的作法,同样是二元对立的,无法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找到支撑。对欧洲历史而言,权力支撑的知识产权嬗变史足以导致人们质疑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中国的历史则表明,没有权力的明显参与,照样可以发展出知识产权实践。因此,对于公众利益的维护,并不必然需要否定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本身。就此而言,达沃豪斯教授提出的知识产权的工具主义,是更为理性、成熟的说法。
结论
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扩张并非是单纯的法律书斋活动,而是受到跨国公司商业利益、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区域竞争的左右。在此等复杂的冲突中,代表公众利益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公众阵营,在西方社会日益壮大。虽然这一阵营的定义十分宽泛,但总体上却认同某种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即通过对西方知识产权“人造光环”的不断解构,来发现权力对知识产权理论及法律的介入与左右,从而否定跨国公司及其推动的不顾其他群体利益的知识产权全球扩张。这种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二元视角极具震撼力,也确多宏效,但却可能导致某种盲目否定知识产权正面价值的思潮。
如果考察中国知识产权的历史经验,则不论是公众阵营某些全盘否定知识产权的思潮,或是私权阵营向中国灌输的知识产权霸权理论,在中国文化看来,都主要适用于西方二元文化的范围之内,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经验,也不充分具备对中国当下及未来发展的建设性。换言之,我们不必拘泥于英美国家及其悠久的案例法传统所确立的、不断支持知识产权扩张的一整套庞大体系,也不必简单地基于西方知识产权并不光彩的历史,来否定知识产权本身的价值。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如何在西方主导下建立的国际知识产权霸权体系中,创造性地发展自我。
今天,中国正在努力创建国家创新体系,并争取在2020年左右初步建成创新型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知识产权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环节,但又不是唯一环节。西方国家在华企业对这一战略体系十分忧虑。但最好的办法应当是摈弃二元视角,谋求如何真正尊重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合作模式,在创新、知识产权、共同发展,以及有关环保、医疗、教育等公益议题上,探索双赢机制。显然,安守廉在20年前倡导的加大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干预,不论当时是否正确,现在显已经不合时宜了。但要让各国人士真正明白这一点,以及其背后更为广泛的文明对话议题,却自不应由知识产权研究者来解决,而实是中国文化复兴无法回避的使命。
注释:
① 这一表述引自Richard A. Spinello & Maria Bottis, A Defen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9), 第1页。
②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uthor?’ in Textual Strategies, Josue V. Harari 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141-60页。
③ Mark Rose, Authors and Owners: The Invention of Copyright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④ John Baylis & Steve Smith (ed.),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285页。
⑤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第xxiv页。
⑥ John Stephens, Retelling Stories, Framing Culture: Traditional Story and Metanarrativ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London: Garland Pub, 1998), 第3-5页。
⑦ Baylis & Sm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第285页。
⑧ Scott Burchill & other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第168页。
⑨ Mark Rose, Authors and Owners: The Invention of Copyright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David Saunders, Authorship and Copyright (London: Routledge, 1992).
⑩ http://www.state.gov/e/eb/tpp/i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