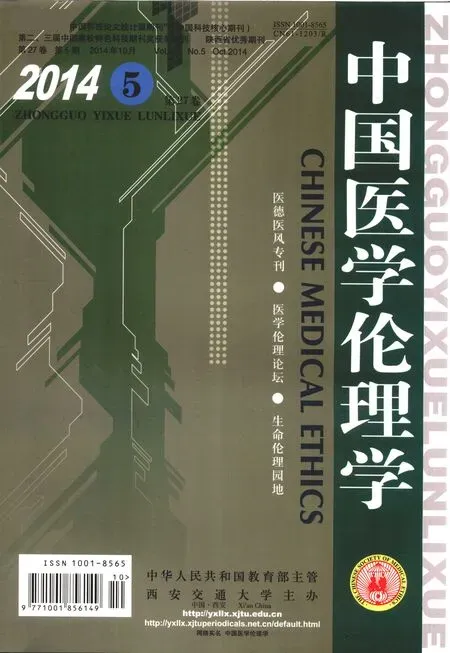从医护伦理看近代中国医院与家庭的多重变奏*
2014-01-30张婷婷李久辉
张婷婷,李久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社科部,上海 201203,ttzhangsh@163.com)
从医护伦理看近代中国医院与家庭的多重变奏*
张婷婷,李久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社科部,上海 201203,ttzhangsh@163.com)
通过分析西医对中国家庭在医学护理中的作用经历了拒斥质疑-认同移植-主动利用的发展过程,指出了医疗空间的转变客观上促使了医护伦理转换。认识到西医制度与中国家庭、地方伦理模式的相互妥协与契合是西方医疗系统进入并内化于中国人生活状态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近代医院;医学伦理;医疗社会史;社会服务;转变
西医传入中国,打破了中医一统的局面,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也引发了从家居到医院的医疗体验变化。医疗空间的转换不仅表征了中西医医理的区别,更隐含了医护伦理的差异。
1 近代中西医不同的医疗空间和医护伦理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医院与近代西方医院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在古代中国,医事制度完全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虽有太医院设立,但以皇室和贵族为服务对象。民间社会的医疗空间主要由私人运作。医生以个体化形式独立而分散执业,不管是中医郎中被请至家中的上门施诊,还是医生坐堂开店或悬牌应诊的家居式行医,医疗空间多与家居环境连为一体。病人在家庭氛围的亲切感中接受诊治,医疗单位以“医家”而非“医院”的形式出现。因此中国传统医疗特征是病体的医治虽依靠外请的医生,但护理程序的进行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家庭是最基本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
中国以家为主导的医疗格局出现,是与传统“家本位”的伦理思想紧密相连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形象地解释了中国人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来确立,即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离中心越近关系越亲,越远关系越疏。[1]因而家庭或家族的人被认为最值得信赖和托付,病人由最亲近的家属来看护有着毋庸置疑的伦理正当性。
近代西方医院作为一种医疗体制,发端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盛行年代。医疗空间最初脱胎于宗教空间。早期的医院是教堂或修道院的外延机构。17世纪以前,医院主要收留穷人、流浪者、残疾人、孤儿、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其对病人的宗教关怀(care)远远大于对其救治(cure),医疗救助的目的为了让病人皈依基督。
中国传统家庭治疗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家庭控制诊断和决定治疗方案,病家在治疗过程中居于主动地位。医生在病人亲属的目光注视下完成诊治,并且病家可以自由选择医生。为了获得最佳治疗效果,病家常常多次试医、择医,并参与治疗方案磋商。家属(一般来说是家长)握有最终决定权。湘雅医院创办者,美国传教士医生胡美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有篇名为“家属控制着医疗”的记述,描述了家属拥有判断病情、决定治疗方案的生动案例,“他们(家属)是陪审委员会,我只是被安排在台上的证人”,其职责就是做出家人认可的诊断结果。[2]与此相对应的,以个体化方式行医的医家为自身声誉和生计考虑则选择自认为有把握的病人进行医治。因此“择医而治”与“择病而医”反映了以家庭为主导的医疗模式中的医患伦理。
而在西医委托理念下,医生被赋予值得信赖的身份,病人需对医生有绝对信任。在西医看来,唯有医生和病家有相互委托的默契,医生握有治病主体的权力,而且病家对医生有“信仰”,病家才能要求医生对病人负责任,责任、权力与信仰,三者相互支持、密不可分。[3]在教会医院发展过程中,即使后来宗教的委托理念越来越淡,但医生的主导地位却进一步强化,一个重要原因是福柯所谓的“规训”权力的出现。医院作为重要的规训场所,通过空间分配、活动编码、时间安排等微观技术,以及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手段来规范、训练、控制病人身体。因此,在医院的医疗空间中,负责任的医生和有信仰的病人成为西医致力追求目标,也成为现代医患伦理导向。
不同医疗空间实践促成了中西医各自医护伦理,二者的伦理逻辑迥然相异。而近代医院空间能否植入中国社会,不仅取决于医学本身疗效,医院医护伦理能否被认同和接收也是十分关键之影响因素。对中国家庭在医护方面的作用,西医传教士最初持拒斥、质疑态度,但随着医疗实践的展开,情况发生了变化。
2 中国语境下医院对家庭医护伦理的妥协
随着西医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文化权威,他们有意识地教中国人如何扮演“现代病人”角色。而做一个“现代病人”的重要前提乃是接受医院作为医疗主要场地。而委托理念与中国差序格局伦理的差异,使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将病人委托给陌生人予以照顾这种他们认为既无情又不妥的方式。中国人习惯的是在亲情氛围的协调下,疾病在自然的状态下得到消除,后来被视为“迷信”的传统习惯和草根伦理不仅不是医术的敌人,反而可能是医疗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且一旦现代医疗技术无法与乡民的日常伦理保持一致,无数挖眼剖心的恐怖故事就由此想象出来。[4]中国近代史上层出不穷的教案冲突即是这一矛盾体现。
针对于此,西医传教士有意识在医院中创造出病人疗养的家庭式环境,设法保留或者模仿病人原有家庭环境及人际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病人的疏离感。当时有传教士专门写文章探讨如何让中国病人感觉更适应和舒服些,“我们经常看到妇女入院时忘了带洗脸盆、梳子、洗脸毛巾、枕头、衣物等等,这并非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刚到医院感到陌生而激动,以至于把这些事置诸脑后。如果为她们准备好这些必需品,我想病人将很快感到医院与家庭是一样的,也许思想上会因舒适而有所触动。”思想上的触动有利于消除病人对医院的恐惧感与陌生感。上文提及的胡美医生在接受第一位住院病人时,在缺乏专业医护人员的情况下,就让病人的母亲充任了护士角色。英国传教士德贞在北京建立教会医院时,有意将病床设计成中国北方家庭常见的炕的形式,“由砖泥砌成的平台,盖着席子,病人就睡在上面。冬天,由泥和煤制成的煤球将炕烧得火热,炕下面埋有烟道以保持炕的温暖,……根据不同的尺寸,每一个炕可睡上12到14人”。[5]一张病床容纳十多位病人,虽从医护科学来看极其不合理,但病人可能更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医院中不仅病人家属被允许陪护,甚至病人的一些迷信活动也得到默许,如在病床下烧纸钱驱魔逐妖,摆放贡品讨好鬼邪等。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医护具有毫无疑问的伦理优先性。但医院作为陌生空间逐步嵌入中国社会后,为了获得中国民众认同与接受,不得不对中国家庭人际伦理关系作一定妥协、移植。如果说西医传教士最初是在医院设施置备和日常管理方面,承认和迎合中国人的伦理观念,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则是主动利用中国“家本位”伦理,将家庭及社区转化为可利用的医疗资源。
3 医院与家庭、社区的契合:以医院社会服务部为例
中国传统个体化行医的中医深入家庭,能较好地了解病人的生活环境和情感氛围。但现代医院中的标准化、统一化管理,使得医生面对穿着统一病服的病人。病人的姓名被单调的就诊号、病床号所代替,医生无法获得与患者病情有关的生活、精神、情感方面信息。20世纪初流行于西医界的“社会服务”运动的兴起是医院主动寻求与家庭及社区地方伦理契合的表现。“社会服务”运动要旨是使医院治疗与家庭社区的资源相互配置发生作用。
“社会服务”运动与医院社会工作在欧美兴起有关。中国最早将专业社会工作引入医疗实践领域,当推北京协和医院。该院专门为困难患者提供了医疗救助服务机构——社会服务部。1921年,从小生活在中国、对中国人生活情感较为熟悉的美国人蒲爱德女士被洛克菲勒基金会选聘来筹建社会服务部。
蒲爱德最初担心社工活动很难在中国推广。她曾在一份报告中担忧地写道:“中国的家庭是否欢迎家访,是否有足够的社会福利机构以便可能对病人进行社会治疗。”在工作中她发现,“尽管中国正式的福利机构比西方国家社区少得多,但也有一定的数量可以利用,而且非正式的或者说自发组织起来的福利机构比较多。从家庭到远房的亲戚都在分担着大大小小的责任”。[6]她根据中国社会和文化实际情况加以本土化的工作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社会服务部主要接受医院门诊医生介绍来的病人。这些病患通常被认为是除生理疾病以外,还需了解社会背景予以辅助治疗。社会工作者随后到患者家中探访,与患者家庭成员进行谈话,了解患者家庭环境、衣食与精神生活状况、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等,最后研究患病的原因是否与家庭或社会背景有关,并制定治疗意见交给主治医生。医生据此及时重新评估最初治疗方案,对不妥之处做出调整。对于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社会工作者会定期进行回访,不断了解患者最新病情与社会生活状况,并及时反馈给医生。当时医院社会服务工作者认识到,对中国病人来说,患者家属的合作、家庭因素对于疾病治疗有重要影响。除北京协和医院外,上海、南京、山东等各地教会医院也相继建立社会服务部。
从以上分析可知,早期医院被引入中国时,医院制度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只是进行了相对被动的妥协。而20世纪初医院社会工作兴起后,医院开始积极主动地适应并利用中国家庭、社区伦理秩序,将之转化为可资利用的医疗资源,以拓展医院工作。这为医院获得更多底层民众的认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 总结
近代来华西医认识到医疗事业不能悬置空中,必须与本土文化相联系,而依托中国人最信赖的地缘与亲缘关系则是进入本土社会较为有效之路径。西医对中国家庭在医护伦理中的作用经历了拒斥质疑-认同移植-主动利用的发展过程。从近代中国医院与家庭的多重变奏,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医疗系统能进入并逐步内化于中国人生活状态之中,西医制度与中国家庭、地方伦理的相互妥协与契合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医院的兴起,促使了中国传统的个体行医模式开始向集团行医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也对医生的行为规范提出了新的伦理道德要求。在新体制下,医生的责任心,不仅在于对个体病人的责任心,也包括对社会、对受聘医院、对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涉及同行之间的合作监督、技术公开等,这直接促进了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27.
[2][美]爱德华·胡美.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M].杜丽红,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134.
[3]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和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A]//李建民.生命与医疗[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477.
[4]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23~1985)[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6.
[5]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12.
[6][美]蒲爱德.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J].唐佳其,译.医药世界,2007,(7):12-17.
〔修回日期2014-06-10〕
〔编 辑 李恩昌〕
The M ultiple Variations Between Chinese Hospital and Fam 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 edical Ethics in M odern History
ZHANG Tingting,LI Jiuhui
(Department of Society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201203,China,E-mail:ttzhangsh@163.com)
About the effect of western medicine in medical care,Chinese family had experienced developing process of from rejection to question identity and then to transplantation active using.From multiple variations between modern hospital and family,we can find that the compromise and accord ofwesternmedical system and local ethics is a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western medical system gradually internalizing into Chinese living.
Modern Hospital;Medical Ethics;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Social Service;Transition
R-052
A
1001-8565(2014)05-0706-03
2014-03-13〕
*项目资助:2012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2ZS110);2011年上海市教委预算内课题(2011JW72)
**通讯作者,E-mail:lijiuhuiethique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