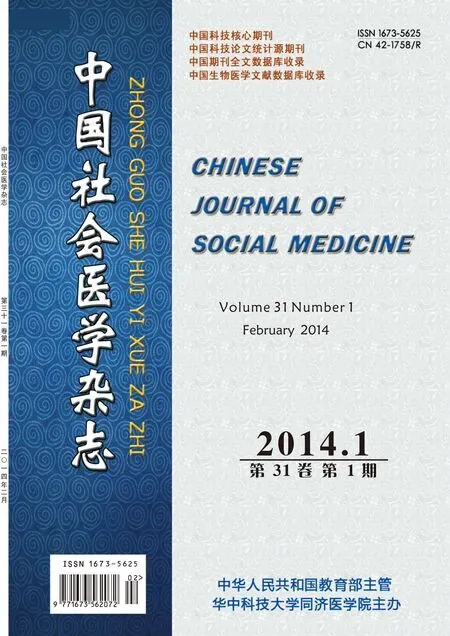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及其干预研究进展
2014-01-24吴贤华吴汉荣
吴贤华, 吴汉荣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报告,截至于2011年12月,我国网络使用用户规模已达到5.13亿,其中30岁以下网民占56.5%[1]。青少年已成为我国网络用户的主要群体。目前,网络已是人们工作与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门工具,但随着网络不断发展,网络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也逐渐突显出来,其中“网络成瘾”作为一种心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Block[2]提到网络成瘾将会以冲动控制障碍为主的疾病谱出现在DSM-Ⅴ中。对于网络成瘾概念、诊断与干预,国内外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对其系统研究,为进一步研究网络成瘾提供参考。
1 网络成瘾的概念与诊断
回顾网络成瘾概念,研究者主要从症状学角度对网络成瘾进行界定,认为网络成瘾行为是一种强迫冲动下的行为表现。网络成瘾诊断工具有很多,可以分为3簇,即以Young为主的测量工具簇、以Davis为主的测量工具簇及其他研究者的测量工具簇。
1.1 Young簇诊断标准
以Young[3]为主的测量工具簇,是借鉴DSM-Ⅳ病理性赌博成瘾标准而提出的诊断标准,即满足一定数量条目就可诊断为网络成瘾者;它是把网络使用看成分类变量,即成瘾与不成瘾的分型状态。Young最早正式介绍了网络成瘾,把网络成瘾界定为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冲动控制障碍[4],并陆续提出了4个诊断标准:第一个为8条诊断标准,取自于DSM-Ⅳ病理性赌博成瘾的题目,删除2条不适用于网络条目后,5条及以上选“是”即诊断为网络成瘾,不足5条则为正常上网。Beard等[5]修订了Young的8条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提出了“5+1”标准。Young等[6-7]借鉴于物质成瘾提出了7条诊断标准;同时她的10题诊断标准,4道及以上选“是”就诊断为网络成瘾,不足4条为网络使用正常者;Young[8]于1998年又提出了20道诊断网络成瘾的标准,39分及以下为正常使用者,40~69分为网络成瘾倾向者,70分及以上为网络成瘾者。有研究者以法国文化为背景,改编了Young的20道网络成瘾问卷,以49分及以下为正常使用者,50分及以上为网络成瘾者[9]。
1.2 Davis簇诊断标准
以Davis为主的测量工具簇,则从认知行为及相关行为问题方面编制条目,形成问卷。把网络成瘾看成是一个连续体,不对网络成瘾分型,没有提出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Davis[10]提出了病理性网络使用术语,从内容上对网络成瘾下了定义,即强迫性上网思维、耐受性和冲动控制能力降低、无法停止上网、出现戒断反应等症状内容,分一般互联网成瘾与特定内容的互联网成瘾。其在线认知量表,按7级记分,总分表示病理性网络使用程度[11]。Caplan[12]编制了一般性病理性网络使用问卷,还有研究者提出病理性网络使用指数问卷[13]。
1.3 其他诊断标准
其他研究者所编制的测量工具簇中,包含大量个性化网络成瘾问卷,其使用不够普遍,只在特定地区或个别研究者中使用。Morahan-Martin等[14]从内容症状上定义了病理性网络使用成瘾,即情绪改变、未能承担主要角色义务、有罪感与渴求上网等。他编制了13题的病理性网络使用,其中有4题及以上回答“是”,则可以诊断为病理性网络使用成瘾。陈淑惠等[15]在DSM-Ⅳ各成瘾标准与临床个案访谈基础上,编制了24题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即为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雷雳等[16]编制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以按维度平均分高低判定网络使用者分型状态。昝玲玲等[17]以项目反应理论编制了中学生网络成瘾诊断量表。
2 干预研究
网络成瘾表现出的一类心理问题,临床学家与研究者纷纷地提出了不少治疗理念与思路。网络成瘾心理干预分个体心理辅导与团体心理辅导两个范式。个体心理辅导主要存在于心理咨询机构等;而团体心理辅导主要存在于学校及网瘾干预的专业机构。
2.1 网络成瘾的个体心理辅导
在个体辅导理论上,主要有认知行为治疗、动机访谈程序、家庭治疗等[18]。如针对成年人的生活风格培训计划,有认知行为治疗与动机访谈程序两个部分,该计划有诱导与加强改变的动机、选择治疗目标、赢得自我控制、预防复发和培训应对技巧等项目。
2.2 网络成瘾的团体心理辅导
在团体辅导理论上,与个体心理辅导理论相似,有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疗、现实疗法[19]、系统补偿综合心理治疗[20]、体育锻炼[21]等方法。在认知行为治疗理论指导下建立互助团体,其构建步骤为团体组建(设计团体名称、确定团体达成目标)和实施团体辅导。家庭、学校等环境对孩子的行为有重要影响,有研究者从多主体干预网络成瘾[7]。杜亚松[22]对网络成瘾者、成瘾者父母以及成瘾者教师进行了网络成瘾干预,针对网络成瘾者干预措施有:情绪识别与控制;亲子关系健康交流的原则;掌握如何处理通过网络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技术;掌握如何处理通过互联网所带来的内容体验技术;控制冲动的技术;识别成瘾行为何时出现的技术;如何停止成瘾行为;回顾干预效果。针对网络成瘾者父母的干预措施有:在孩子接受干预同时,孩子的父母也接受干预;重新认识自己孩子情绪状态的技术与原则;家庭成员间高质量沟通的技术与原则;问题解决的技术与原则;控制父母自身情绪与行为的技术与原则;管理孩子上网的技术与原则。针对网络成瘾者教师的干预措施,包含了针对网络成瘾者与父母的措施,干预过程以工作坊形式进行。
2.3 综合心理辅导
有些研究者则综合了个体心理辅导与团体心理辅导的范式。陶然等[23]采用“五位一体”的综合干预模式与“八阶段三分之三”策略治疗网瘾患者。Davis[10]提出了网络成瘾认知行为治疗框架,把非适应性认知公开化,允许个体灾难化非适应性认知,最后重构认知体系。Young[24]根据其他成瘾行为的治疗经验,提出了网络成瘾心理干预措施:①改变上网时间,其旨在打破已有的上网模式,建立新的上网模式;②使用外部计时器;③设定目标;④限制特别的应用程序;⑤利用提醒卡;⑥制定个人清单;⑦加入支持小组;⑧家庭治疗。Young[25]认为,认知行为治疗(CBT)是治疗网络成瘾的理想框架,提出将CBT-IA框架分成3个阶段,即行为矫正、认知重建与伤害减少治疗阶段。
3 讨论
回顾以往网络成瘾干预文献,研究者主要从理论层面上结合家庭、社会与学校提出综合干预框架[26]。具体干预实践,从形式上看,团体心理辅导较多,个体心理辅导为次,再次为二者结合形式;从干预环境看,分为学校环境、医院及其他机构环境两大类;从采用理论看,主要涉及到认知行为理论、药物与身体治疗;从干预群体看,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其中中学生为甚;从干预设计看,以单组自身对照设计为主,以干预组与控制组设计为辅,辅导时长或频率通常为3个月或12周次;从干预效果看,均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针对青少年群体,未来研究应该重视家庭治疗与团体心理辅导的作用。家庭治疗是网络成瘾干预的一个重要手段[27],青少年主要面临的是发展性与适应性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家庭环境有关,因此对网络成瘾者干预措施中,应该有家庭治疗的一部分。家庭治疗主要目的就是改善家庭环境与家庭功能,它立足于患者的整个家庭,把家庭看成是一个整体,通过改变家庭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才能改善个体症状。家庭治疗试图通过调整家庭关系、构建新的互动模式、改善家庭功能来解决网络成瘾者的心理问题及其消除不良家庭因素,从而促进个体与家庭的成长。从网络成瘾的生理、社会与心理的模型来看,家庭是孩子成长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因此,应该系统地改变网络成瘾者的外在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但面临的挑战则是调动家庭成员参与干预活动积极性。
团体心理辅导是受网络成瘾研究者与临床学家欢迎的一种干预形式。团体心理辅导是将网络成瘾者组织成一个小团体,团体内成员间有共同的网络情感体验与上网认知,容易对这些问题产生共鸣,当干预者为其提供一种平等无压力的成长环境时,他们易在团体里得到情感支持,易建立共同戒断网瘾的目标和措施,通过强化积极行为巩固治疗效果。团体心理辅导在各网络成瘾治疗专门机构中使用广泛,适合网络成瘾患者集中的地方,如在学校、社区、班级等环境。青少年的发展性问题与适应性问题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把这些同质的网络成瘾者集中在一起,接受有组织的系统干预,是一种高效的干预措施。
[1] CNNIC.The statistic re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ternet network,No.29th[R].Beijing CNNIC,2012.
[2] Block JJ.Issues for DSM-Ⅴ:Internet addiction[J].Am J Psychiatry,2008,165(3):306-307.
[3] Young KS.Internet addiction: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onsiderations[J].J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2009,39(4):241-246.
[4] 张梦菡,赵笑颜,孙易蔓,等.大学生网络成瘾现状及其对交往焦虑的影响[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3,30(1):39-41.
[5] Beard KW,Wolf EM.Modification in the proposed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internet addiction[J].Cyberpsychol Behav,2001,4(3):377-383.
[6] Young KS.Psychology of computer use:XL.Addictive use of the Internet:a case that breaks the stereotype[J].Psychological Reports,1996,79(3):899-902.
[7] Shek DTL,Tang VMY,Lo C.Evaluation of an Internet addiction treatment program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kong[J].Adolescence,2009,44(174):359-373.
[8] Young KS.Caught in the Net:how to recognize the signs of internet addiction-and a winning strategy for recovery[J].Database,1998,21(5):89-89.
[9] Khazaal Y,Billieux J,Thorens G,et al.French validation of the internet addiction test[J].Cyberpsychol Behav,2008,11(6):703-706.
[10] Davis RA.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J].Comput Human Behav,2001,17(2):187-195.
[11] Davis RA,Flett GL,Besser A.Validation of a new scale for measuring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Implications for pre-employment screening.[J].Cyberpsychol Behav,2002,5(4):331-345.
[12] Caplan SE.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nd psychosocial well-being:development of a theory-based cognitivebehavioral measurement instrument[J].Comput Human Behav,2002,18(5):553-575.
[13] Mitchell KJ,Sabina C,Finkelhor D,et al.Index of problematic online experiences:item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elation with negative symptomatology[J].Cyberpsychol Behav,2009,12(6):707-711.
[14] Morahan-Martin J,Schumacher P.Incidence and correlates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J].Comput Human Behav,2000,16(1):13-29.
[15] 陈淑惠,翁俪祯,苏逸人.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之编制与心理计量特性研究[J].中华心理学刊,2003,45(3):279-294.
[16] 雷雳,杨洋.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的编制与验证[J].心理学报,2007,39(4):688-696.
[17] 昝玲玲,刘炳伦,刘兆玺.中学生网络成瘾诊断量表的初步编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16(2):123-125.
[18] Van Rooij AJ,Zinn MF,Schoenmakers TM,et al.Treating internet addiction with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a thematic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rapists[J].Int J Mental Health Addiction 2012,10(1):69-82.
[19] Kim J.A reality therapy group counseling program as an Internet addiction recovery method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Korea[J].Int J Reality Therapy,2007,26(2):3.
[20] 高文斌,陈祉妍.网络成瘾病理心理机制及综合心理干预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4):596-603.
[21] 李立,陈玉娟,李敏,等.篮球运动处方对网络成瘾中学生干预效果评价[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5):551-552.
[22] Du YS,Jiang W,Vance A.Longer term effect of randomized,controlled group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for Internet addiction in adolescent students in Shanghai[J].Aus N Z J Psychiatry,2010,44(2):129-134.
[23] 陶然,应力,岳晓东,等.网络成瘾探析与干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4] Young KS.Internet addiction:symptoms,evaluation and treatment[J].Inn Clin Practice,1999,1(7):19-31.
[25] Young KS.CBT-IA:the first treatment model for internet addiction[J].J Cognitive Psychotherapy,2011,25(4):304-312.
[26] 卢官庐,郭继志,庄立辉.青少年网络成瘾防治研究进展[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06,23(2):102-106.
[27] 宫本宏,王晓敏,叶建群,等.青少年网络成瘾家庭治疗效果评价[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3):3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