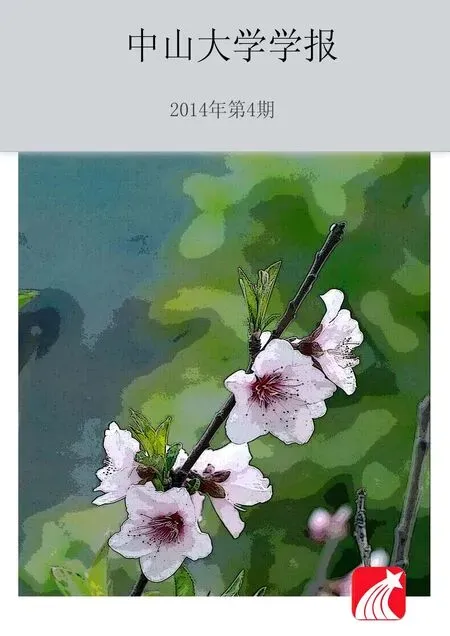宋明儒家责任观中的人己关系论*
2014-01-23雷静
雷 静
以道德关怀为宗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承担意识,是宋明儒家的政治理想①余英时详细论述过宋代儒者"以天下为己任"以及明儒"觉民行道"的责任承担意识。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74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10页;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37页。有学者亦批评余著将责任意识等政治动机作为道德哲学建构的原因。参见丁为祥:《余英时"政治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再读〈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哲学分析》2012年第3期,第189—196页。本文认为:一方面,责任意识的挺立,是儒家群体努力的成果;另一方面,儒学责任思想等政治观念从属于其道德哲学。。职是之故,责任就不仅仅是外在的规范,更具有内在德性的内涵。基于宋明儒家责任思想的内在德性特点,在如何给出其伦理学定义的问题上,有过“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争②黄进兴认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不相容,儒家伦理不属于责任伦理(氏著:《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21页)。相反,李明辉认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相容,儒家伦理中二者兼具,并详细论述了韦伯责任伦理学中界定不清晰的地方,批评了以黄进兴为代表的观点(氏著:《存心伦理学、责任论理学与儒家思想》,《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第6—17页)。。尽管研究者们已经做了不少相关讨论,但是对于宋明儒责任思想本身并没有充分的专门研究,其人己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研究更付阙如。从责任问题的范畴而言,“人己关系”的视角不仅是宋明儒者的共识,也是现代社会学人己关系理论的核心。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utz)认为:人己关系理论(或曰主体间性哲学)可以深入揭示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提出的“责任”这一伦理学范畴的哲学理路*许茨借鉴现象学为韦伯社会学作出哲学论证(参见[奥地利]阿尔弗雷德·许茨著、霍桂桓译:《社会实在问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卢崴诩:《从解释社会学到修身社会学——舒兹与孟子思想中的人己关系及其社会学意涵》,《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55页)。。本文试图通过回到人己关系这一重要视角,细绎宋明儒家对责任问题相关经验的论述。
一、德性之“己”
宋明儒家责任思想中的代表性观点当属“以天下为己任”。朱熹曾评论北宋名相范仲淹:“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129)*[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088页。“己任”之己,主要指士大夫阶层*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74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10页。。延续“己任”的担当,顾炎武的《日知录》卷13“正始”条有云:“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7页。天下兴亡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而不仅限于士大夫阶层。顾炎武此说固然与明代社会环境、士风嬗变有关,若从儒家道德哲学而论,同在“己任”范围中的士大夫与普通民众,构成了道德共同体*余英时的《“致良知”与觉民行道》指出:明代政治文化与宋代不同的地方,即用“觉民行道”代替“得君行道”(氏著:《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49—51页)。明代儒家的责任意识主要是道德共识,这方面的典型是阳明学泰州学派之学风的庶民化,以及形成的“社会性的精神运动”(参见[日]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64页)。。
“己任”之己,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共通性,甚至优先于政治认同,这与人们对天下责任的日常认识有关。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若非亲身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责任事项,人们很难切身体会到“天下”究竟与自身有多深的关联,自身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现实地承担了对“天下”的责任。这种日常理解也进入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视野,即可以根据各人的政治身份来划分其责任:普通的平民,要承担对自己、亲人、家庭的责任;为官的士大夫,还须担当对国家的责任。或如明儒何瑭的《儒学管见》所言:“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则又有国与天下之责焉。修齐治平,莫不有道,此则道之实体也。”*转引自[清]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8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73—474页。
平民和士大夫的责任分野,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可以解释为士大夫不同于一般百姓的职责。程颐认为,天下即是君、臣的分内职责:
今言当世之务者……臣以为所尤先者有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今虽纳嘉谋,陈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听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责任宰辅,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协心,非贤者任职,其能施于天下乎?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1页。
这种责任分野,还可以用“大人”“小人”的志向、才识、气度的区别来做解释。明儒杨爵说:“大人当治安之时为危乱,小人以危乱之时为治安,皆此小(阙文)也。有大人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识度,有小人之识度;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天地生物之不齐,教化之施固有要,而以宇宙间事为己责者,不可不慎也。”*[明]杨爵:《杨忠介集》第6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65—66页。“天地生物之不齐”,从而有立志承担天下责任的大人,亦有满足自身家庭与社会生活的小人,存在道德禀赋与后天教化导致的分别,这种分别最终由一己之道德觉悟能力所决定。因此,己任之己,实乃德性之己。
德性之己,为什么要承担起对天下、对他人的责任?我与他人处于何种关系,故而我应当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从张载到顾炎武,答案都是我与他者是“同胞”关系。张载有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顾炎武的《日知录》卷19“直言”条认为我对他者的责任在于:“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册,第1084页。将血缘同胞关系扩展到天下,那么,天下人都是自己的同胞,我自然得对天下人尽责。具体而言,“在上位者”与我分别承担“救民以事”和“救民以言”,这是与个人社会身份相应的具体责任。总的来说,天下人与家庭成员一样,是与我血脉相通的“一体”,天下责任对于我而言,是自然的、不可割裂的,正如陆九渊所道“宇宙内事便是己分内事”*[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83页。。
自我与他人乃至与天下万物之间,显然并不具备必然的血缘关系。“民吾同胞”的一体,与其说是事实存在的关系,毋宁说是儒家信仰共同体所认肯的关系。在认同一体关系的前提下,自我的德性挺立,“己任”之“任”,才是毫不勉强的自觉承担的“分内事”。为了强调“己任”的重心落在德性内在的、认肯自我与他人、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己”,明儒赵贞吉的《答胡庐山督学书》指出“己任”不能被视为外物,也是不可以“取”的:
来谕云:“道通天地万物,无古今人我。”诚然,诚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己立处未充,不能了天地万物也。”斯言似有未莹彻处耳……如公云:“责任之重,有不容己,欲为己任,又立处未充。”则不免于揽厌之病矣。何则?天地万物古今与我一体也,而欲取为己任,则二之矣,是揽之累也。谓迎之也,我与天地万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己立未充,则二之矣,是厌之累也。谓将之也,均之非谓随顺觉性也。*[明]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77—578页。
二、人己同情
宋明儒者讨论的主要责任行为是责人、责己。关于儒家责任思想的现有讨论,也是围绕责人责己观念,给出责人在于责己的描述性说明*余治平:《儒家责己与责人的道德要求》,《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5—66页。。然而,为什么责人在于责己?在责任经验中,人己之间是何种关系、故而责人在于责己?这就有必要深入到宋明儒者对责人、责己两种经验的具体讨论。
在宋明儒者看来,责己并不是简单地将所有责任归于自己,因为一味揽责容易积压心理负担,反而败坏了修养工夫。《近思录》卷5有云:“罪己责躬不可无,然亦不当长留在心胸为悔。”*[宋]朱熹、吕祖谦同编,叶采集解,[清]江永注:《近思录集注》,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99页。此语是朱子之师李侗所传,源自《二程集》所载伊川语录。李侗强调,一味揽责不仅不是修养,更且是修养工夫要克服的“私意”:“某窃以谓有失处。罪己责躬,固不可无,然过此以往,又将奈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积下一团私意也。”*[宋]朱熹编、严佐之校点:《延平答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这种“私意”的根源,是因为“克己”的工夫不纯,尚未涵养好本源:
到此境界,须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为何而来。若来谕所谓,似是于平日事亲事长处,不曾存得恭顺谨畏之心,即随处发见之时,即于此处就本源处推究涵养之,令渐明,即此等固滞私意当渐化矣。又昔闻之罗先生云:“横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过者化。私吝尽无,即浑是道理,即所过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说,于静默时及日用处下工夫看,如何?*[宋]朱熹编、严佐之校点:《延平答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第340页。
李侗提倡“存神过化”,存神是反己涵养,过化是应事应物皆成善。责己的实质就是反己,即复归和涵养自己内在的善(存神),从而在应事应物皆成善的过程中(过化),自然实现对他人、家国天下的具体责任。
从责己之“反己”的实质出发,于主体自身而言,即是改过;于他人而言,若我通过反己来促成他人改正过错,则为何我之“反己”可以导向他人改过,这就需要解释。对此,王阳明提出“工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奸’,本注说象已进于义,不至大为奸恶。舜征庸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乂,以乂薰烝,不去正地奸恶。凡文过掩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工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处。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廷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3—124,111页。
这个提法是根据舜如何对待象的过错而分析出来的。象的做法固然大奸大恶,但舜并不是正面“奸恶”,而是通过“自进于义”的反己工夫,“以乂熏烝”来感化象。恶人的常态是隐匿其恶,所以正面指摘是非,就会激化其恶性。舜也曾“要象好的心太急”,正面“奸恶”太过,激得象屡屡杀他。阳明认为,舜是实实在在经历过,才悟到“工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如此方“克谐”。从反己导向他人改过,是舜经历了种种努力与失败、千死百难中悟到的。经由反己来导向他人改过,不是直线的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他人(尤其是恶人)的心理情感反应的策略。阳明所谓“曲当人情”,事实上是要使人发自内心、自觉主动地向善,即感化他人向善*事实上,在现代心理治疗中,仍然可以看到,劝人改过,本质上而且首先需要劝人者自我完善:“对别人提出批评,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仅凭直觉就坚定自己是正确的;另一种是经过反省,确认自己有可能正确。前一种方式,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而父母、配偶或者教师,常常以这种方式教育他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招致不满和怨恨,而没有给对方的成长带来帮助,甚至只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第二种方式,给人谦逊而谨慎的印象,它需要批评者首先自我完善,由此让很多人知难而退。但与第一种方式相比,这种方式更有可能带来成功,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它通常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美]M·斯科特·派克著、于海生译:《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08—109页)这可视为阳明观点的一个例证。。
促成他人主动改过、承担责任之“责人”,与主体“我”自身的“责己”是统一的,这是一种人情的同感同情过程。在这种同感同情中,责己的反省不是单纯地反思自己,而是有方向的。这一方向就是阳明所说的“凡当责辩人时,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④[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廷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3—124,111页。,即我把他人的过错当成自己的过错来反思和对治。经过这种责己之后,一方面,我检查了自己是否也有此过;另一方面,正因为我设身处地地反省了他人的过错,我与他之间的同感同情加强了*陈立胜对于儒家论述的同感同情经验有细致的论述,详见氏著:《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哲学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9—27页。,从而最终有可能不断贴近他人内心,对之进行熏陶和感化。同情、感化,促成了他人的改过,也将他人的责任内在化为我自己的责任。
人己之间的同情,是他人责任被纳入到我自身的现实渠道。在同感同情中,主体没有了主观性的“私意”,而是置身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中,如实体会另一个主体(他人)的感受,从而获得两个主体间同情和感化的方式。其中,已经消融了主客之间的绝对分野:相对于主体“我”而言,他人是客观的;同时,主体“我”亦把“他”作为主体。正因这种互为主体的观照,他人现实地获得了“我”的尊重,以及相对于“我”的客观性。
主体“我”经由同情这一现实途径,如实地接续他人的责任事项、并纳入到自己的责任当中,现实地将主体“我”拓展为生活世界的具体责任事项。这样,主体“我”就不再是单纯主观的、甚至“私意”“私欲”的我,而是不断地实现生活世界的具体责任事项的“我”。“我”不再囿于一身,而是扩展到家国天下,与万物为一体。正如张载说的:“天下一人而已,惟责己一身当然尔。”*[宋]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29页。
三、父子君臣“责善”中的人己关系
责人从根本上是通过“责己”来实现的,需要经由人己间的同情,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人己关系。宋明儒最为重视父子君臣伦理,其中体现了人己关系的具体样态。为了进一步考察此问题,可以先从“责人”的直接情况入手——即我使他人必对其过负责,亦即宋明儒说的“责善”。责善需要指出他人的过错,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适当地给出指正。陈献章《与罗一峰》有言:
君子未尝不欲人入于善。苟有求于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强而语之,必不能入,则弃吾言于无用,又安取之?且众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别生支节以相矛盾。吾犹不舍而责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不可不戒。*[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8页。
陈献章特别反对“强而语之”的责善,以为是“取怨之道”;而“苟有求于我者”,则我可以予以指正,这是基于主体“他”的自觉自愿,可以达到责善的现实效果。因此,“适当”标准乃在于是否能达到使他人自觉改过的效果。
以自觉自愿的效果来衡量,不告其过是“非忠”,但指正他人的过失必须首先要有“诚意”的交流。二程指出:
门人有曰:“吾与人居,视其有过而不告,则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则奈何?”曰:“与之处而不告其过,非忠也。要使诚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则言出而人信矣。”*[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74,75,393页。
二程径直以“诚”为责善之道:“责善之道,要使诚有余而言不足,则于人有益,而在我者无自辱矣。”④[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74,75,393页。“要使诚有余而言不足”,是诚作为责善之道的具体表现。二程还进一步说明为:“圣人之责人也常缓,便见只欲事正,无显人过恶之意。”⑤[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74,75,393页。
“责人常缓,不显过恶”是二程提出的责善原则。既要指正其过失,又不能凸显其过失,这似乎很难理解。并且,众所周知,惩恶扬善,这两者是统一的。若不凸显恶,怎能充分扬善?二程却认为责善不应当有揭示他人过恶的意思,那么惩恶从何做起?儒者“不显过恶”的责善原则,该当何解?
按照二程的解说,“无显人过恶之意”表明显人过恶并非责人或者责善的目的,责善的目的是“只欲事正”。既然如此,我们诚恳地帮助他人改正过错,就应该表达出“只欲事正”的意图,而不是使人误解我们,以为我们有“显人过恶”之意。所以,“言不足”“责人缓”,都是要求经由交流过程最大限度地凸显诚意。
“诚意交通”的语言、行为等交流方式是责善之道的表现。责善,其实质不在于主体我问责他人的过错(责人),而正是经由“我”的恰到好处的交流艺术,使他人主动责己、改正过失。宋代的余允文举了一个例子:
疑曰:“经云:‘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传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不责善是不谏不教也。可乎?”余氏辩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谓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间不责善。’父为不义则争之,非责善之谓也。传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岂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观之:鲤趋而过庭,孔子告之‘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诗》与礼,非孔子自以《诗》、礼训之也。陈亢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孟子之言,正与孔子不约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宋]余允文:《尊孟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523页。
孔鲤趋而过庭,孔子正在庭上,孔鲤失礼了。孔子的教子艺术不是直接责备儿子有失礼数,而是启发儿子学《诗》和礼,并点出“《诗》以言,礼以立”的要点。孔鲤既愧且疚,回去发愤,学习《诗》与礼。《诗》与礼是学习、培养德性的范本,但在本例中,先有“趋而过庭”的特殊情景,再经由孔子“言”与“立”的指点,变成了父子之间有着道德告诫、指导与期待等指向的媒介物。其意义不仅仅是平面的学习材料,更是立体的生命指引——孔鲤由此反省自身,激发出自觉自愿的学习热情。
孔子的责善艺术是二程所说“诚意交通”的典范,既委婉、又旗帜鲜明地突出了改正的要点。除了作为交流艺术的“诚”,还有作为父子伦理关系的“诚”。周敦颐《通书·诚下》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15页。诚是伦常之本,是行为的源头。责善之道,包括诚意的交流方式与亲情伦常(父子、兄弟)以及血亲外的一体化伦理(君臣、师生、朋友)。责善之道落实到父子关系中,有“父子之间不责善”之说。这个说法是孟子提出的,亦是所谓“易子而教”。历来对孟子这一说法褒贬不一,争议很多。余允文是为孟子辩护的:“辩曰”之前是司马光《温公疑孟》的内容,之后就是余氏的反驳*宋代孟学史有两股对立的思潮:疑孟派与尊孟派。疑孟派的作品有司马光的《温公疑孟》;尊孟派的作品有余允文的《尊孟辨》,以及朱熹在余氏基础之上加以评述的《读余隐之尊孟辨》。关于疑孟派与尊孟派的辩论往来,参见杨海文:《李泰伯疑孟公案的客观审视》,《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第81—89页;又刊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第4辑《荷尔德林的新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80—311页。本文无意于是否尊孟,而是选取能够体现“诚”这一责善之道的论述,认为余允文的论说提供了较丰富的资源。。余氏的辩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孟子这一说法中的责善之道。
余氏开宗明义地辩护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并非反对父子之间有教有谏。所谓“易子而教”,也是“教”的一种方式。《孝经》的“父为不义则争之”,“争”并不是责善。并且,《左传》的“爱子,教之以义方”,以及孔子教子,这些虽未责善,但确是教子的方式。父子不责善,有谏有教,却不以直接问责对方的形式,这是为什么?余允文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朱熹也认为不能够直接问责。不过根据《论语》等经典,儿子可以“微谏”父亲,这就更加充分证明父子之间有“谏”。因此父子之间不责善,并不意味着丧失了对正义的维护(有谏),而是通过“微谏”这样的形式体现出来。朱熹认为,他的证明可以作为余允文的补充:“子虽不可以不争于父,观《内则》、《论语》之言,则其谏也以微。隐之说已尽,更发此意尤佳。”([宋]朱熹撰,戴扬本、曾抗美校点:《读余隐之尊孟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15页),同为宋代学者的吕祖谦点出了个中奥妙:“父子之间不责善,非置之不问也,盖自常有滋长涵养良心底气象。”*[宋]吕祖谦著、吕乔年编:《丽泽论说集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第403页。
涵养良心,亦是涵养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等四心,是同感同情的先天基础*陈立胜:《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前揭刊,第23页。。维护良心,正是为了维护父子生命一体的同感同情,或曰父子感通*陈立胜认为:感通是人我之间同感同情、生命一体贯通的同感共振(氏著:《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前揭刊,第21—23页)。本文采用感通来表述父子血缘生命一体相通的同感同情经验。。父子感通的生命一体特性,又被晚明大儒黄宗羲表述为“父子一气相通”*参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5—6页。。父子一气、父子一体,这是“诚”的伦常表现,是父子感通的生命基础。孝子日日晨定昏省,强化了父子一体的相感相通;而不孝子与父亲疏远,造成父子一体关系的断裂,也消解了父子一气的感通。
父子不责善、父子一气感通是“诚”之亲情伦常。若没有血缘关系,责善之道该当何种“诚”?若非血亲关系,“诚”就是某种一体化关系。按照儒家的理解,血缘亲情之外还有师生、朋友、君臣等一体关系,师生与朋友之间的责善之道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诚意交通”中做到,而君臣关系就较为特殊。仍然回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对比父子一气来解释君臣如何才能一体:
或曰: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后,日远日疏,久之而气不相似矣。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夫父子固不可变者也。*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5—6页。
与人们熟知的用父子来比喻君臣不同,黄氏区分了两种一体关系的不同本质:父子一体是因为父子一气的血缘关系;君臣一体不是基于亲子血缘,而是基于“天下”的责任。正因共担天下责任,二者才能成为命运攸关的责任共同体。黄氏特别指出:共担天下责任的君臣,是师友关系。然而,假如君臣之间对共担天下责任的一体关系没有共识,要么虽为君之臣、却是君之仆妾,与师友关系相去霄壤;要么根本就没有承担天下之责、无法与君成为一体,形同陌路。并且,父子君臣,在各自的一体关系中,展现了孝与忠的内涵。孝子是因为与父亲保持一体,由此推及,忠臣亦是在君臣一体关系中才得以成立;孝子源于先天固不可变的血缘关系,忠臣则本乎后天的责任共同体。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惟有共担天下责任,才有君臣一体,君臣责善之道也正是建立在这种一体关系的基础之上。如果这种一体关系不存在,君臣责善的渠道也就消失了。或者说,对于君臣关系而言,共担天下责任的一体关系与相互责善,本来是一体之两面。从这个角度看,臣子对君主尽忠,就不仅仅是臣子单方面效忠,而需要君臣双方面的责任共识。这是因为,若臣子不去承担天下责任,或者君主去掉了臣子承担责任的资格,君臣二者责善的渠道也就不存在了,臣子要么沦为仆妾,要么离作路人。君臣并非一体,臣子的忠又谈何而来呢?
总体而言,在父子君臣伦理中,人己关系的具体样态是父子亲情与君臣一体,其责善之道的“诚”即为父子一气的感通,与君臣共担天下责任的一体化。基于君臣一体关系往往处于血缘之外、发生于社会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忠”不仅仅在形式上比照孝的亲子一体关系,更在内涵上凸显了君臣一体乃在于责任承担的社会性、后天性。君臣责善渠道不可或缺,是自朱熹到黄宗羲的宋明儒家的共识。
余论:宋明儒责任思想研究方法问题
讨论宋明儒的责任思想,是连接现代社会与古代经典之间的努力。责任思想本身,包含了人类社会跨越古今的经验和知识。“责任”的伦理学—社会学专门研究,主要由社会学家韦伯提供了范式,“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是其核心。这一范式对于划分责任行为的信念动机与行为后果是有效的,但在思想史研究中,衡量某个责任思想的价值,则容易发生混淆。已有西方和汉语学界的研究者着力阐述了这个理论缺陷*参见[瑞士]G·恩德利著,王浩、乔亨利译,白锡校:《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一种假对立(上)》,《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13—17页;[瑞士]G·恩德利著,王浩、乔亨利译,白锡校:《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一种假对立(下)》,《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16—19页。。事实上,现有研究已经指出,儒家思想中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是联系在一起的*如,张春香指出:《周易》的责任伦理与韦伯的事后责任不同,侧重于事前预测指导和价值引领(氏著:《〈周易〉责任伦理思想浅析》,《周易研究》2005年第2期,第65页);邓凌认为:责任伦理思想是传统儒家心性学说道德理论的核心(氏著:《中国传统儒家责任伦理思想浅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37页)。。
宋明儒的责任思想问题,从属于儒者的道德实践。无论“以天下为己任”,还是责人在于责己、以及父子君臣责善,都是在德性之“己”与他人关联的基础上展开。就像杜维明所说:“儒家的修身是通过日益扩展的人际关系圈的交流和参与而展开的。”*杜维明:《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44页。儒者的道德实践,是在人己之间展开的主体间的实践。责任行为的种种经验,要在人己关系的脉络中呈现。
人己关系是宋明儒道德实践开展的基础,但许茨的人己关系图式并不适用于儒者的世界观*卢崴诩指出:许茨(舒兹)人己关系理论“单层的、平面的”世界观无法解释孟子“多层的、立体的”世界观(氏著:《从解释社会学到修身社会学——舒兹与孟子思想中的人己关系及其社会学意涵》,前揭刊,第58页)。。宋明儒描述的世界是道德实践开展的过程与存在。在道德教化中,人己之间具备不同的秉性和境界。因此,世界不是许茨眼中的主体关于存在的共同知识,而是在道德境界崇高的君子对周围人的教化过程中,信仰共同体所先后感应到的境界(教化是君子变化了人们的气质,使之能够感受到世界的超验本体)。
宋明儒有关责人责己责善的经验表明:人己之间关系的关键点落在同情,儒者尤其重视父子君臣这一特定伦理关系中的同感同情的一体形式。就此而言,宋明儒的责任思想具备儒家伦理的本质特点,即人们的伦理行为都具有伦理身份的根据,父子君臣均有其伦理角色所决定的行为方式。若从宏观结构上把握,宋明儒的道德责任问题乃是存在于“差序格局”中的。责任行为的种种——责人、责己、责善是否能够达成实效,即“己”的德性是否能感化他人,需要立足于“己”的德性的人己之间的同情。这一同情过程以“己”为价值的中心,人己之间的同感同情一体化的具体形式则取决于双方的宗法伦理关系。这种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伦理特点,以及教化、同情本身的因材施教的特殊性,使得宋明儒家责任问题的研究,无法直接套用西方社会学家通常采用的理论模型建构方法,而是要真正进入到“己”的德性价值开展的人己关系的现实具体的场景来进行。
这一现实的具体场景,通常在日常生活的道德风尚和习俗中展开。“里仁为美”,美风俗以广教化是孔子以来的儒家传统。各类史书方志都会记录道德风尚与习俗,风俗论更是历代儒家著述不可或缺的内容。选取宋明儒的风俗论作为诠释文本,并进入他们身处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对其道德责任实践进行深入考察。有感于目前鲜有从风俗论视角探讨道德责任实践的专门研究,本文认为:面对宋明儒风俗论这一日常生活论域,未来的研究可以聚焦于认识论基础、道德情感来源、信仰根据等要素,亦即围绕宋明儒对道德风气、习俗及其如何改善风俗的论述,进而深入探讨道德责任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如何成为人们的共识,道德责任意识源自怎样的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责任行为的终极信仰根据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