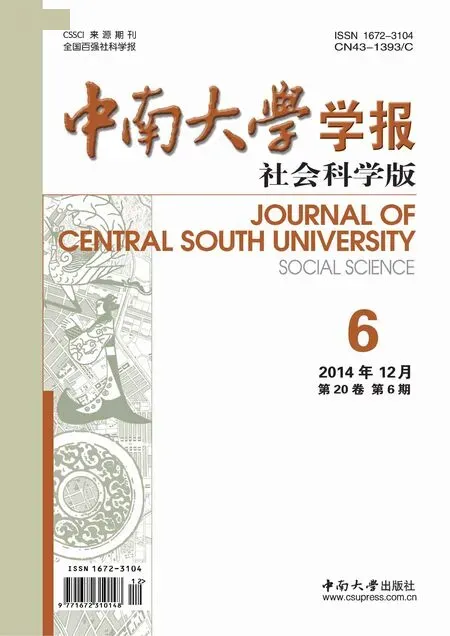从实践本体论哲学到个体生存论美学:王国维“感悟诗学”的构建
2014-01-22黄菲蒂杨经建
黄菲蒂,杨经建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从实践本体论哲学到个体生存论美学:王国维“感悟诗学”的构建
黄菲蒂,杨经建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王国维对旷世命题——“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求索,借助的是一种存在论哲学(美学)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立足于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直观说,并吸纳了感悟体验等本土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和再造,重构了一种具有潜哲学和超美学形态的“感悟诗学”,以参悟生命的诗性哲思解答了存在的意义。王氏对“可信”“可爱”的探求,是从实践本体论哲学走向个体生存论美学的必然结果。
王国维;存在论思维;感悟诗学
王国维无疑是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标志性文化象征。如果把王国维放归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陈寅恪谓之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中[1](13),那么,王国维代表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命体验的痛苦与文化选择的困惑。
学界对王国维的诠释一般是从其旷世命题——“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开始[2],这缘于王氏在“可信”和“可爱”之间的左右探询和上下求索,其中蕴含的是深重的时代忧患意识和寻找灵魂归宿的价值诉求。笔者认为,破解这一命题首先应从王氏所追询的“第一义”入手[3]。由此而开启的则是一种参悟生命的哲思方式,一种存在论哲学(美学)视野的呈现。
众所周知,王国维将人类的知识分为“直观的知识”和“概念的知识”。所谓“直观的知识,自吾人之感性、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识,则理性之作用也”[3](253)。问题在于,后者——理性、科学知识只能分析、认识世界,却难以全面地把握、理解世界。因此,尚有不能凭借科学、理性思维所认识的另一“直观的知识”。更何况,“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宜疑”(《六月二十七日宿陕石》)。科学、理性知识有时只能“增疑”,不一定能“解惑”。这意味着, 在缺乏宗教传统、却有着深厚的审美文化传统的中国,“他虽然已经感受到传统文化日趋沉滞的大势,但并没有失去那种已渗入他全部生命的文化感”[4](28)。也即,当“可信”的问题难以使他信服后,“可爱”这一问题被提到生存层面乃至生命存在的维度。
事实上,王国维曾清晰地辨析了诸如“性”“理”“命”等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在传统哲学思想中由“性”“理”“命”构成了完备的哲学宇宙论知识。所以王国维说:“我国哲学上之议论, 集于‘性’与‘理’二字, 次之者‘命’也!”[5]以知识论立场对这些核心概念进行审视,可以看到一方面王国维以“性”“理”“命”这三个哲学范畴为线索去反思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另一方面,又以现代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康德的哲学对这些核心话语概念进行阐释,诚如此言,“王国维从思维方式上对传统学术的批评无疑几乎达到了全盘否定的程度”[7]。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知识的“真理性”(义理)让他感到无法安身立命,知行合一的要求又使他并不满足于哲学思辨。究其实质,这是中国传统宇宙观崩溃后王氏面临的思想困境和意义危机——“可信者不可爱”的痛苦和困惑。
而且,与同时代的学人相比,王氏更具有注重情感和希望得到慰藉的精神气质,“以承担人生之苦为代价的忧郁, 是王国维知行合一的终极显现。……这种承担很大程度上是王国维将中国抒情传统内化后的行动”[7]。这里所说的“抒情传统”,是20世纪后半期海外汉学界在“抒情美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一种理论概括。正如海外华裔学者高友工、陈世骧等指出的那样,“抒情性”几乎涵括了中国的古典文艺形式,“抒情美学”也成为中国文学艺术所拥有的审美意识,“认为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结合了形式和生命直觉之反思的‘美感经验’,从而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视经验的传统找到一种现代依据和一个西方知音”[8]。
很明显,这种“现代依据”最先体现在王氏的学术研究中。比如,《〈红楼梦〉评论》就一反当时的研究只注重或索隐本事或才子佳人话题的格局,将研究思路引向《红楼梦》之于人生永恒困境的表现,从而延伸了中国文学艺术中感时伤逝的抒情传统脉络;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往讨论抒情问题多偏重诗文,王国维却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变迁,“抒情传统”必然会在文类中出现转移;他之所以发掘作为叙事文学的《红楼梦》的抒情性质,意在揭示《红楼梦》中人们对无法回避的“情”的关切以及情本体——以情为本体的艺术世界的悲剧美学价值。至于1906年发表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也体现出对于“抒情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他断定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其实就是超乎政教的“怨”与“刺”,更能呈现出私人与公共、“可爱”与“可信”之间的思维张力。而不管是陈述《红楼梦》还是褒扬屈原的文学精神,抒情的解脱与升华才是文学能给人以精神慰藉的原因所在。
同样,为“抒情传统”寻觅到“一个西方知音”的这个先知先觉者还是王国维。不但他本人公开表明,学界也公认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对他的影响至深。当王国维在《汗德像赞》《叔本华像赞》《叔本华与尼采》等著述中表达了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人的敬仰时,透露的正是他所倾心的那种非理性主义思维特质。换言之,王氏之钟情叔本华,很大程度上缘于后者哲学中的主观气质。“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10](406)正是在重气质而轻知识的接受视野中, 虽然叔本华和尼采在否定还是张扬生命意志上观点迥异, 但在王氏心目中他们的学说差别不大,“古今哲学家性行之相似,亦无若彼二人者”,他们作为“旷世之天才”而让王氏深感敬佩[10](72)。这种重视心性气质超过具体知识的倾向,其实便是他对“抒情传统”命题的现代性阐释。
如果从哲学思维范式上考量,“抒情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与杨义所指称的“在中国具有原创性的诗学专利权”的“感悟思维”相通[11]。客观地说,作为哲学(美学)思维范式的感悟思维,着眼的不是西方式逻各斯,而是从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出发,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的本真性的心灵通融和精神契合。王氏就认为,人类不能充分认知世界缘于两点:受功利的束缚和过分地依赖理性认识;而艺术、哲学、文学其实具有相似的功能:通过培养人类的诗性之思,使人沉浸在“物我两忘” 的艺术境界中才有可能摆脱功利的束缚、培养感性直觉的心灵,这样“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之问题”[3](68)。
惟其如此,王国维对外来哲学(美学)资源的吸纳就执迷于以叔本华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叔氏之出发点在直观(即知觉)而不在概念是也。……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唯直接间接与此相联络者,斯得为真理”[3](326)。宇宙是一个无情而冷漠的场所,叔本华们却许诺把人从宇宙式生存中拯救出来,这当然不是通过理性逻辑分析出来的,而只能是“直观”或“感悟”到的。借助于叔本华,王国维以一种参悟生命的诗性哲思去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解答生命存在的意义。
要言之,王国维对“可爱”与“可信”的探求,是从实践本体论哲学出发走向个体生存论美学的必然结果。
二
无疑,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美学)资源的采纳主要倾心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具体说,在王氏的视野中,尼采学说形成的渊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康德对“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区分;也是借助于这样的区分,并通过叔本华的生存哲学的过渡,此岸的、感性的、当下的成为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审美存在[12]。
简略而言,在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现象和本体、自然(必然)和自由的分立,是以认识和实践(道德)的分立——由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至于怎样把分立或对立结合起来,康德设想出一种人不能具有而又与自然同一的“知性的直观”,这样一来自然的多样性无须任何思维(概念)的中介,本身即是现象和本体、必然和自由的统一;它可以被作为理性借以制定从现象反思本体、从必然反思自由的主观原理的根据。这种作为“多样性的直接统一”的“知性直观”,不但为理性主义的辩证思维说、更为非理性主义的直观说奠定了发展的契机[13]。
接着康德说的是存在主义先驱谢林。“谢林的‘理智直观’可谓是非理性主义的最初表现形式,……谢林思想中所流露出的非理性主义为所有后来的非理性主义提供了方法论的样本。”[17]《先验唯心论体系》是谢林的主要代表作,他在该书中提出关于知识的来源、形成、对象、体系及其相关问题,其中“直观说”构成其哲学内涵的核心话语。
首先是与知性反思相对的“理智直观”。如果说,知性反思从对立面中反观自身,并在主、客对立中把握对象的性质特征;那么,“理智直观”以既不是主观也不是客观的绝对同一性为对象,对象不是独立于直观活动的外在的东西,而是与活动、直观与被直观的东西——创造者和被创造者是同一的,是绝对自由的;谢林甚至认为“理智直观”是一切哲学的官能。相对而言,艺术哲学才是谢林哲学体系的拱顶,其思路如下:“理智直观”本身是内在的直观,哲学的创造活动直接向着内部以便在“理智直观”中认识绝对的同一体;当“理智直观”诉诸直接经验、变得客观时就是艺术哲学中的“美感直观”。只有艺术才能反映其他任何事物都反映不出来的东西,艺术能够以普遍有效性的方式不断地重新确证哲学无法从外部表示的东西;艺术哲学是理论哲学、实践哲学的最高完成,也只有发展到“美感直观”这个层次,绝对同一体作为主观与客观的原始和谐的根据才最终显示和敞亮。王国维在译介桑木《哲学概论》中就提到了谢林的“直观”:“‘直觉’或‘直观’法者……与寻常之智力异而得直知事物之真相……则欲观之(需)要感性理性以外一种之心性,希哀林(谢林)名之曰‘知的直观’。”[15](25)犹如《人间词话》中所言说的“无我之境”,无我的超验境界作为独特的创作追求, 强调的是直觉的灵光未被遮蔽的自然本真状态,它基于心的印证和齐物——以物观物,如庄生梦蝶,与天地共存,与宇宙同在。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美学也主张直观体验,讲究静观、玄览、妙悟……等审美范畴。庄子的“心斋”“坐忘”更如同存在论现象学的“现象学还原”之“悬搁”——将现象界中的外物与知识加以“悬搁”,通过凝神守气而去体悟宇宙万物,最后达到心之“无待”的逍遥游。完全可以说,王国维是第一个自觉地接受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并以之重新来审度、化解传统美学的直观体验,进而熔炼成一种现代哲思方式,通过培养感性直觉的心灵来追询“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对这样的感性直觉王国维称为“天眼”[3](275),佛雏先生对此的阐述颇为精辟:“王国维此处‘天眼’即指脱离普通感觉之域,且与一般理性(概念、推理)无涉,它凭直觉而直契‘现象之奥’或人生真谛之所在。”[15](275)故而,王氏大量吸收非理性主义哲学(美学),并将之融解到有关“直观”思维上来,为解决艺术思维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纯粹直观早在1904 年已经成为王国维美学的基本理念, 境界则是它的中国称谓。”[16]所谓“纯粹的直观”就是王国维将中国传统的直观体验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维相结合的产物。
与叔本华相似,尼采同样拒斥西方传统的理性本体论而瞩目于审美静观,其审美静观是以诗性话语通过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在《悲剧的诞生》中审美静观则展现为“日神”艺术;“日神”艺术的状态特征是对美的内心观照,对规范、节制、和谐的冥思,与中国的“抒情传统”有着内在的契合;“梦幻”则是“日神”艺术的表征,创作者“沉浸在对对象的纯粹静观之中”和“日神”冲动下个体的“无意志静观”[17](173)。之所以如此,皆因尼采在赋予“生命意志”(诗化创造力)以本体地位的同时,将对生命的感性把握和诗意直观视为一种真理性透视。
海德格尔探询的是一条由“存在”到“道说”的哲思之路;海德格尔首先认定,世界的亮敞和存在的澄明呈示为语言给万物和人自身命名;而第一次命名的活动——使人的世界敞开的就是诗。“一切凝神之思就是诗(Dichten),而一切诗就是思。两者从那种道说(Sagen)而来相互归属。”“道说意味:显示、让显现、既澄明着又遮蔽着把世界呈示出来。”[18](270, 211)唯有诗人才真正珍爱语言,“倾听”语言并听从它的召唤。“倾听”是有限的生命把握自己人生意义的一种特殊的认识功能,是人以本己的心性去体味、去感悟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按照海德格尔的思想,只有用诗的语言才可以表达一个人的世界或境界。……境界可以通过诗意或审美意识一次性地体验到、把握到。”[19](254)这使人联想起《人间词话》第77 条中的“隔”与“不隔”说,冯友兰将之列为王国维美学的两大贡献之一。实际上,“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在原稿中则是“语语可以直观”,可见“不隔”在王氏的本意中实为如在“目前”的“直观”;“王国维赞许的‘不隔’‘语语都在目前’,……皆是境我一如、天人合一,澄怀纳象、目击道存的景象, 皆为一切现成的现量境和不著思议的本来境, 皆系诗人用‘清净心’直感所感之,用‘平常眼’直观所观之。”[20]更如《人间词话》中标举的三重“境界”,王氏对此并没有演示出通常的逻辑推论过程,仅仅是借用了前人的三句诗词予以描绘,却自然完美地表达了从得悟→渐悟→顿悟的审美感知(感悟)过程,类似于谢林的“美感直观”,以一种参悟生命的诗性哲思解答了存在的意义。应该说,王氏立足于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美学)立场,注意到直观感悟在诗学表达上既是思维本原又是体验方式,其中包孕着从哲学(美学)探究到生命关怀的多层面的内涵,体现了他建构一种“感悟诗学”的现代性努力[21]。
总之,王国维以其深厚的中西文化学养和学无中西的博大胸襟,将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准确地说是存在主义与中国文化、艺术传统通融一体,营造了一种具有潜哲学和超美学意味的、姑且称为“感悟诗学”的参悟生命的哲思方式,一种中国道统(抒情传统)和西方学统(非理性主义)的东方化重构。也可以说,在生命存在的困惑中,王国维从以人类学为基础的实践论——哲学(“可信”)走向以个体生存为目标的存在论——艺术(“可爱”),从而完成了他对存在论思维范式的思考。
[1] 陈寅恪. 陈寅恪集·诗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2] 徐洪兴. 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 中国哲学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3]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4] 温儒敏.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5]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M].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6] 王攸欣. 王国维朱光潜接受西方美学方式比较研究[J]. 中国文学研究, 1999(2): 74-79.
[7] 张春田. 王国维的学术转变与抒情传统的现代危机[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9-37.
[8] 沈一帆. “抒情美学”: 现代形态与中国经验[J]. 人文杂志. 2010(4): 110-115.
[9] 傅杰编. 王国维论学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0] 周锡山.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7.
[11] 杨义. “感悟”的现代性转型[J]. 学术月刊, 2005(11): 114-121.
[12] 张辉. 尼采审美主义与现代中国[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2): 169-184.
[13] 杨祖陶. 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J].哲学研究, 1998(3): 7-17.
[14] 陈海燕. 谢林与非理性主义[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51-55.
[15] 佛雏. 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6] 张节末. 纯粹直观与境界—意境[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4): 96-101.
[17] 周国平.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8]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9] 张世英. 天人之际: 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20] 詹志和. 王国维“境界说”的佛学阐释[J]. 中国文学研究, 2008(4): 64-69.
[21] 欧阳文风. 如何建构中国原创诗学——从杨义“感悟通论”谈起[J]. 中国文学研究, 2009(2): 25-28.
From practice subject philosophy to individual survival theory: construction of Wang Guowei’s “empathic poetics”
HUANG Feidi, YANG Jingji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Wang Guowei interpretated “Trusted not lovely, lovely untrustworthy” by using an ontologe philosophy (aesthetics)thiking paradigm, which was based on non-rationalism intuitive theory. It absorbed feeling experience theory and constructed the “empathic poetics”. The thinking paradigm was the corollary originated from the practice of ontological philosophy to the individual survival theory of aesthetics.
Wang Guowei; ontologe thinking; Empathic poetics
I0-02
A
1672-3104(2014)06-0248-04
[编辑: 胡兴华]
2014-07-21;
2014-10-15
黄菲蒂(1982-),女,湖南汨罗人,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杨经建(1955-),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