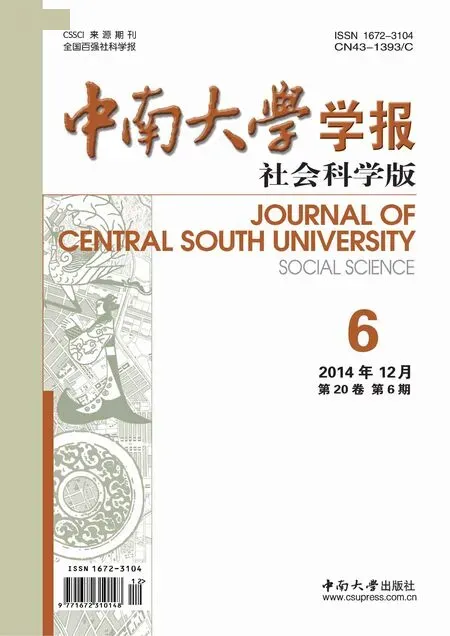ICSID公约第72条之“同意”释义
2014-01-22银红武
银红武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ICSID公约第72条之“同意”释义
银红武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伴随着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三个拉美国家相继通知退出ICSID公约,国际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在理解与适用ICSID公约的退出条款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究其原因,对公约第72条中的“同意”一词理解不同乃关键所在。ICSID公约第72条中的“同意”应被解释为“同意要约”或“单方同意”。东道国受ICSID管辖的“同意”一旦做出,即成为其一项强制性的国际义务,该“同意要约”具有不可撤销性。退出国在通知退出前所作的受ICSID管辖的“同意要约”非但在退出前有效,而且在通知退出与退出生效之间的“缓冲期”内仍能保持效力,即便退出ICSID公约生效后,依然有效。但有权“接受”退出国“同意要约”的投资必须为东道国退出ICSID公约生效前已进行的投资。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同意”;解释;不可撤销性;有效期
截至目前,全球共有159个国家签署了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ICSID公约),其中150个缔约国已交存了公约批准书、接受书或认可书①。毋庸置疑,ICSID公约和“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下文均简称ICSID)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解决国际直接投资争端国际性机制。但是近年来,这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却受到了三个拉美国家的挑战②。面对拉美三国咄咄逼人的退出ICSID公约的行为,西方国际法学者围绕ICSID公约的退出条款(即第71条③与第72条④)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学理探讨,但分歧较大。究其原因,学界与实务界对公约第72条中的“同意”一词理解不同乃关键所在。
一、ICSID公约第72条中“同意”的两种不同解释
一派国际法学者认为,应对ICSID公约中第72条的“同意”一词作严格解释,即应将“同意”理解为在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已形成的一个“同意仲裁的合意”[1]。如果将公约第72条的“同意”理解为“仲裁合意”的话,那么退出国在退出通知做出前,其于双边投资条约抑或保护外资国内立法中所表示的受ICSID管辖的要约——由于未被外国投资者所“接受”,也即“仲裁合意”尚未实现(perfected)——将归于无效。而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若其在东道国向ICSID做出退出通知前,仍未能与东道国达成“同意受ICSID管辖的仲裁合意”,那么投资者也就丧失了向ICSID递交仲裁申请的权利。
而另一派学者(如Sébastien Manciaux[2]、Emmanuel Gaillard[3]、Michael D. Nolan & Frederic G. Sourgens等[4])则主张,ICSID公约第72条约文中的“同意”用语应解释为“单方同意”或“同意要约”,不应理解为狭义的“同意仲裁的合意”。在这种解释下,东道国于退出ICSID公约的通知做出前在双边投资条约或保护外资国内立法中所表示的受ICSID管辖的“单边同意”或“同意要约”,就能为外国投资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接受”,从而在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同意受ICSID管辖的仲裁合意”。根据这一“仲裁合意”,ICSID就获得了两者间所引发的投资争端案件的管辖权。
二、“同意”一词的正确理解
众所周知,关于条约约文或用语解释的一般规则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文均简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中得到了阐释。但需注意的是,该解释规则似乎并不适用ICSID公约。原因有二:一是,并非所有的ICSID公约缔约国都已签署与批准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二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4条规定,公约只适用于公约生效日(即1980年1月27日)后所签署的条约。ICSID公约显然不在其可适用的时间范围内。然而,考虑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一些单独条款通常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国际习惯法的一种编纂,并且在实践中,许多投资争端仲裁庭也承认这点[3]。因此,考虑到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规定在条约解释问题上所处的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地位,国际投资法学界一般也适用其来指导解释ICSID公约第72条中的“同意”一词。
具体而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根据这一总体解释原则,若要对条约用语进行正确释义,首先应根据其所处的上下文仔细求证。具体考虑到ICSID公约第72条约文中“表示”“同意”的主体为“他们其中之一”,而“他们”并不包括“外国投资者”的情况,那么可以推论,“由他们其中之一所表示的同意受中心的管辖”的措辞暗示了“同意”不应被严格解释为“受ICSID管辖的仲裁合意”,而应被解读为需要外国投资者事后做出“接受”的“同意要约”。关于这点,有学者曾强调指出,“(ICSID公约)第72条没有对‘同意’进行限定的事实就是对该词涵义的一个清楚阐释:假设ICSID公约起草者意指‘合意同意(agreement to consent)’,而不是‘同意’的话,那他们就应已经那样规定了。”[3]据后来的研究表明,当初在起草ICSID公约时,公约拟定者们就已经注意到了“同意”的单边性问题了⑤。而且,仔细参读ICSID公约第25条“……当双方表示同意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撤销其同意”的条文,不难推断出公约其他条文中所使用的“同意”措辞同样具有单边性质。
其次,“同意”一词的解释,还应参照ICSID公约之“目的及宗旨”。公约的宗旨在第1条得到了明确阐述,即“中心的宗旨是依照本公约的规定为各缔约国和其他缔约国的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提供调解和仲裁的便利”。外国投资者寄希望于ICSID法律框架能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争端解决国际法机制,从而弥补投资者在与东道国政府引发争端的情势下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若将“同意”解释为东道国政府的“同意要约”的话,更能促成争端双方的“同意受ICSID管辖的仲裁合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与优化国际投资环境的作用,最终ICSID公约之“目的及宗旨”能更好实现。
其实,将“同意”作如此释义,除了出于“根据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考虑之外,也还基于自公约生效以来,国际投资法所发生的种种结构变化这样一个事实。众所周知,由于外国私人投资者在投资争端产生后常会反感将争端诉诸东道国内国法院,而若依赖投资者母国行使外交保护的话,也会带来种种不利。故自20世纪30年代起,外国投资者就已倾向于将其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提交至各种国际仲裁庭进行解决。最初,这些投资争端的仲裁都是通过在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签订的国家契约(如自然资源特许合同)中规定专门的仲裁条款来实现的。[5]然而在实践中,东道国往往无视国家契约中专门仲裁条款的存在而拒绝遵守仲裁程序,他们甚至通过单边行动终止包含有仲裁条款的协议⑥,并且投资争端基本上是通过一些临时仲裁庭来裁决的。正是在如此较为混乱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背景下,ICSID公约应运而生[6]。
此后,ICSID仲裁管辖权的获得方式变得日益丰富——受ICSID管辖的仲裁合意既可体现在同一个文件中(in a single instrument),也可通过投资者接受东道国在其他文件中所做的“普遍同意”或“同意要约”来实现。在前一种方式中,要么由东道国与投资者对国家契约中的仲裁条款进行约定,要么俟投资争端发生后再由双方协商达成。该种仲裁合意达成方式的特点体现为:“仲裁合意”由几乎同时做出的“要约”与“接受”相结合而成。而在后一种“仲裁合意”的达成方式中,东道国的“普遍同意”主要体现在国内立法⑦或双边投资条约(以下简称BIT)中。
最后,将ICSID公约第72条中的“同意”解释为“单边同意”还基于“动态—演进式”条约解释原则的考虑。在解释多边条约(尤其是《联合国宪章》)以及旨在保护人权的各项公约)时,该解释方法的重要性经常被强调[7]。“动态式”条约解释原则的精髓已在Tyrer v. United Kingdom案中得到了生动的阐述:欧洲人权法院主张,《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欧洲公约》“是一个活的法律文件……应根据现今的情况予以解释”[4]。虽然ICSID公约之于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无法与《联合国宪章》之于一般国际法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但ICSID公约曾经为、现在仍是以“保护个人为导向的”。也正是基于这点理由,在谈论人权保护领域的新近发展时,ICSID公约常被提及[8]。考虑到这样的背景,有必要利用“动态—演进式”条约解释原则将ICSID公约视为一部“活的条约”,并据此对ICSID公约的“同意”作符合当前国际投资现状的解释,这非但完全恰当,而且无论是与ICSID公约最初的,还是现今的“目的及宗旨”均保持相当一致。
三、“同意要约”的不可撤销性
Christoph H. Schreuer在其著名的关于ICSID公约的评论中解释道,与其他任一以合同为基础的仲裁一样,申请方(即投资者)与被申请方(即东道国)之间必须存在一个同意仲裁的书面合意,尽管双方的同意可体现于两个相独立的文件中。但是,在未被“接受”前,“仲裁要约”本身不能约束东道国将投资争端递交ICSID仲裁,原因是该项“要约”通常可被撤销。比如,自玻利维亚退出ICSID公约后,退出行为立即就会对投资者接受该国先前所作的“将投资争端递交ICSID仲裁的同意要约”的能力产生否定作用[1]。因而,Christoph H. Schreuer的“要约—接受”理论会导致投资者在东道国退出ICSID公约后,出现无法诉诸ICSID的风险。
对以上观点,许多学者明确表示反对。其中,Emmanuel Gaillard教授坚持说,若东道国已做仲裁“同意要约”的表示,则陷自身于需承担更多责任的境地——如果东道国试图撤销其受ICSID管辖的“实盘”,其结果将引发外国投资者更大的仲裁成本或遭受更大的损害[3]。众所周知,在私合同成立的法律制度中,“实盘”即“一旦满足其条件则不可撤销的一个要约”。实盘“只须在双方签署的书面文件中确定将保持其效力。其在约定的期间内或在合理期间内(若没有规定有效期)为不可撤销的”。实盘一旦做出,要约人的日后行为若与之不相一致(根本不可能撤销该要约)的话,那么对受要约人所遭致的任何损害,要约人均需负赔偿责任。
基于合同法中的“实盘”理论再加之东道国政府在国际法中的特殊身份,东道国在BIT或保护外资国内立法中所承诺的、将与外国投资者间的投资争端诉诸ICSID的仲裁同意就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个“仲裁的同意要约”,而应当被看成为一项独立的国际义务。从而,东道国退出ICSID公约并不能必然导致投资者援引ICSID仲裁管辖权的能力的即时丧失[4]。
事实上,将东道国的“受ICSID管辖的同意”视为一项独立的国际义务才可更全面地保护投资者基于自身所做的投资的种种合理期待。外国投资者寄希望于东道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来防范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有可能遭遇的各种常规风险以及东道国对他们的投资有可能采取不正当干涉的风险,从而更好地保障自身的投资预期利益。确实,如果投资者的期望不是如此的话,那他们的投资就不可能做出了。因此,东道国的“仲裁同意”最好上升至吸引外国投资者前来进行国际投资的一个前提条件,并且该“同意”一旦做出,就必须一直保持效力——与投资者是否接受该“同意”无关(投资者的接受行为并不能改变东道国的同意行为,接受行为仅能改变投资者自身方面的同意)。毕竟,东道国受ICSID管辖的“同意”一旦做出,即成为一项强制性的国际义务,而并非一项任意性的义务。换言之,该“同意要约”具有不可撤销性。
四、“同意要约”的有效期
既然ICSID公约条文中的“同意”应被解释为需得到私人投资者“接受”的“同意要约”或“普遍同意”,那么东道国一旦做出,即会产生公约下的法律义务。而根据ICSID公约第25条第1款的规定,东道国当然也不能通过退出ICSID公约从而单方面、间接地撤销其在通知退出前所作的受中心管辖的同意。[9]也就是说,退出国在通知退出前所作的受ICSID管辖的“同意要约”非但在退出前有效,而且在ICSID公约第71条所规定的“六个月”期间(即通知退出与退出生效之间的“缓冲期”)内仍能保持效力,即便退出ICSID公约生效后,依然有效,而外国投资者也均能在此有效期内接受退出国此前所作的“同意要约”或“普遍要约”。
比如,假若ICSID公约退出国在通知退出前已与外国投资者母国签署了约定投资争端受ICSID管辖的BIT,那么退出国在该BIT中所表达的受ICSID管辖的“单方同意”在条约的整个有效期内都对退出国有约束力,而投资者也可在该期限内任何时候接受该“普遍同意”[10, 11]。无疑,BIT的有效期通常会延续至东道国退出ICSID公约生效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但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见解⑧,主要是因为这些学者要么将ICSID公约中的“同意”作狭义解释,即理解为“仲裁协议”或“仲裁合意”;要么将东道国“同意要约”的有效期限定为ICSID公约退出生效前的时间内。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理解偏差,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若对ICSID公约的第25条与第72条作过于宽泛解释的话,可能过于偏袒投资者的利益。事实上,正是这种过于偏袒投资者的“嫌疑”刺激了几个拉美国家相继退出ICSID公约。
基于此种考虑,于是在实践中,国际投资争端案的仲裁庭便一贯主张,条约的解释不能先入为主地太过严格或太过宽松,既不能偏袒投资者,也不能损害其正当利益,而应实现一种公正与实效的解决——遵循诚信基本原则,采取“均衡”的解释方法[4]。虽然退出国在BIT或国内立法中所作的受ICSID管辖的“同意要约”的有效期可以延续至退出生效后,但是基于平衡退出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考虑,有必要对有权提交ICSID仲裁的外国投资进行时间上的限定:仲裁所涉的投资必须是东道国退出ICSID公约生效前已进行的。而这主要是基于四点考虑:第一点,假若不对所涉的外国投资进行一个时间限定的话,那么退出国的退出利益无从谈起,从而退出ICSID公约显得毫无现实价值。第二点,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70条第2款之规定,“自废止或退出生效之日起,在该国与条约每一其他当事国之关系上”,“解除当事国继续履行条约之义务”。ICSID公约退出国在其退出行为生效后,无须承担新产生的公约下义务。假设所涉投资是在东道国退出生效后所进行的,那么该项投资则应被视为是对退出国产生了新义务的投资。第三点,通过领悟BIT中的“存续条款”的立法精神,也应对所涉的外国投资予以时间上的类推限定,即将BIT中“本条约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规定类推为“ICSID公约退出生效之日前进行的投资”的解释。第四点,东道国在其内国的外资立法或 BITs中所作的受ICSID管辖的“单边同意”一旦做出,即上升为该国的一项不可撤销的“同意要约”。那么按照合同法的一般理论,“要约”之所以不能随意撤销通常是基于保护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考虑⑨。几个拉美国家退出ICSID公约生效后,基于维护当前投资者的信赖利益考虑(因为当前投资者正是基于对“同意要约”的信赖而进行了投资),退出国在国内投资立法与BIT中所作的受ICSID管辖的“同意要约”不能撤销。但对于东道国退出ICSID公约生效后才进行的投资,投资者应无信赖利益可主张,因为东道国的退出已为公众所知晓,其中当然包括相关外国投资者。
五、ICSID公约退出条款的正确适用
建立在上文的研究基础上——应将ICSID公约第72条中的“同意”解释为“同意要约”或“单方同意”,须认识到“同意要约”具有不可撤销性,且应正确对待“同意要约”的有效期——那么,如何正确适用ICSID公约退出条款的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对于ICSID公约退出前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所签订的含有ICSID管辖条款的国家契约、或俟争端发生后双方同意ICSID管辖的仲裁协议,东道国退出ICSID公约的行为对此类具体的国际法律文件影响不大。
其次,针对东道国退出前所签署或所制定的同意ICSID管辖的BITs或保护外资的国内立法,既然ICSID公约条文中的“同意”应被解释为需得到私人投资者“接受”的受ICSID 管辖的“同意要约”或“普遍同意”,那么一旦其经东道国在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中做出,即会产生东道国无论是在ICSID公约下的、还是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下的国际法律义务。其原因在于,非但ICSID公约使得东道国承诺的将投资争端递交ICSID仲裁的“同意要约”成为了东道国必须信守的一项条约义务与国际义务[12],而且含有此类“同意”的内国投资法以及BITs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已使这种“同意”承诺上升至东道国的国际法律义务的高度,并且完全独立于ICSID公约[4]。
事实上,这一结论——东道国在BITs或国内投资立法中承诺将其与外国投资者间的投资争端诉诸ICSID的管辖“同意”不受东道国通知退出ICSID公约的影响,即便是在ICSID公约第71条规定的六个月内(即通知退出与退出生效之间的“缓冲期”)也不受影响——的做出除了基于上述原因外,还因为该种解读符合ICSID公约之所以设计这一“缓冲期”的初衷。当初,设计这一段时间是为了处理缔约国对ICSID公约的修改提出反对的情形。缔约国可在与公约修改生效“等待期”相等的六个月时间内退出ICSID公约,从而有机会规避其他缔约方已对公约所做出的、己方不赞成的修改。鉴于此,对于在该“缓冲期”内缔约国所引发的任何义务,仍应受先前未变动的ICSID公约管束,即便是该义务产生出超过通知期的ICSID公约下的影响。具体地说,如果缔约国在退出生效(或公约修改生效)后仍遭起诉,那么该义务可被视为是在退出生效前引发的,因此也应受修改前公约的约束。
在这一点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假若ICSID公约退出国在通知退出前已与外国投资者母国签署了约定投资争端受ICSID管辖的BIT,那么退出国在该BIT中所表达的受ICSID管辖的“单方同意”在条约的整个有效期内都对退出国有约束力,而投资者也可在该期限内任何时候接受该“普遍同意”[13]。无疑,在此种解释下,BITs的有效期通常会延续至东道国退出ICSID公约生效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最后,还有一个关于ICSID公约退出条款的适用问题需解决:即ICSID公约的退出对外国投资者的法律影响问题。
2007年11月15日,荷兰籍投资者E.T.I. Telecom International N. V.向ICSID递交了其与玻利维亚政府的投资争端仲裁申请。该公司对ICSID仲裁程序的启动正是基于玻利维亚政府在《荷兰王国与玻利维亚共和国关于促进与相互保护投资协议》第9条第6款所作的受ICSID管辖的“普遍同意”。该BIT的仲裁条款约定,缔约国受ICSID管辖的唯一条件就是双方“已经加入(have acceded)”ICSID公约。这一要求即便是在任一缔约国退出ICSID公约的情形下也已成就——因为在退出前,缔约国已先“加入”了该公约。满足了该条件后,荷兰投资者当然可在该BIT的整个有效期内接受玻国所作的“同意要约”,即便是玻利维亚退出ICSID公约的行为已于2007年11月3日生效。
事实上,玻利维亚与德国《关于促进与共同保护投资条约》的仲裁条款也作了与荷兰—玻利维亚BIT相类似的仲裁规定。根据玻利维亚与德国的BIT第11条第3款,如果两国“已经成为(have become)”ICSID公约的缔约国,那么缔约方与另一缔约国国民间的投资争端均要递交ICSID管辖。事实上,只要两缔约国成为ICSID公约的缔约国后,那么受ICSID仲裁管辖就变得无条件可言。这也就意味着,从玻利维亚与德国均已批准ICSID公约之日起,其与另一缔约国投资者间的投资争端均须提交ICSID仲裁。同理,玻利维亚政府在该BIT中所作的“普遍同意”即便是玻政府已退出ICSID公约后仍为有效[13]。
六、结论
自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与委内瑞拉相继退出ICSID公约以来,围绕ICSID公约退出条款的适用问题的讨论相当激烈,分歧较大。而分歧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公约第72条中的“同意”一词理解不同。由于在ICSID的仲裁实践中,尚未产生与ICSID公约的退出问题直接相关的裁决,因此关于ICSID公约退出条款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也许,这些问题的最后澄清要等到ICSID仲裁庭对E.T.I. Telecom International N. V. v. Republic of Bolivia案⑩以及更近些时候的Pan American EnergyLLC v.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案⑪做出裁决之后了。但从ICSID应对这两个投资争端案所表现出的种种积极行动(如对案件予以登记以及主动组织仲裁庭等),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ICSID在ICSID公约退出条款的解释与适用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与倾向。
注释:
① https://icsid.worldbank.org/ICSID/FrontServlet?requestType=Cas esRH&actionVal=ShowHome&pageName=MemberStates_Home. 2014-09- 6.
② 玻利维亚于2007年5月2日递交了退出ICSID公约的书面通知。2009年7月6日,ICSID公约的保管机构收到了厄瓜多尔退出ICSID公约的书面通知。2012年1月24日,委内瑞拉向世界银行递交了退出ICSID公约的书面通知。
③ 任何缔约国可以书面通知公约的保管人退出本公约。该项退出自收到该通知六个月后开始生效。
④ 缔约国依照第70条或第71条发出的通知,不得影响该国或其任何组成部分或机构或该国的任何国民在保管人接到上述通知以前由他们其中之一所表示的同意受中心的管辖而产生的由本公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⑤ Gutierrez Cano考虑到了在东道国与投资者间并无仲裁合意,只有东道国倾向于将争端提交ICSID的一个“一般宣示(general declaration)”的情形。Aron Broches也假设了东道国通过退出ICSID公约撤回其“单边声明(unilateral statement)”的情况。ICSID Conventio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Vol. Ⅱ, Part 2, para. 61, 62, 1968, p. 1010.
⑥ 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前Anglo Iranian Oil Company与伊朗政府之间。1933年该石油公司与伊朗政府签订了一个包含有仲裁条款的特许协议。1951年伊朗政府单方废止该协议。⑦ 举例说,《委内瑞拉外国投资促进和保护法》(1999年10月2日第356号令)规定,外国投资争端可受ICSID仲裁管辖。并且,东道国的这样一些类似国内法规定已构成国家同意受ICSID管辖的观点已得到ICSID仲裁庭的判决确认。如在Southern Pacific Properties (Middle East)Ltd. v. Egypt案中,ICSID仲裁庭认为,埃及的国内投资法的相关规定足以构成该国同意将投资争端诉诸国际仲裁的一个书面承诺。Southern Pacific Properties (Middle East)Ltd. v. Egypt, ICSID Case No. ARB/84/3, Second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pril 14, 1988, at ¶ 121, 3 ICSID REP. 131, 163.
⑧ 如Christoph Schreuer认为, 只有在缔约国通知退出前,投资者已与东道国达成“双方已成就的仲裁同意(perfected consent)”的情形下,ICSID的管辖权才不受退出的影响。Christoph Schreuer. Denunciation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and Consent to Arbitration[C]// Michael Waibel & Asha Kaushal (eds.). The Backlash against Investment Arbitration: Perceptions and Reality. Kluwer: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0: 353-368. 而Aron Broches则认为,缔约国所作的同意ICSID 管辖的“普遍声明”除非已为投资者所接受,否则不能约束该国。如果该国在投资者接受前通过退出公约撤回其“单方声明”的话,任何投资者均不能向ICSID递交仲裁申请。然而,如果东道国所作的“单方同意要约”在该国退出ICSID公约前已被投资者接受,那么东道国与投资者间产生的争端,甚至在东道国退出生效后,ICSID仍拥有管辖权。ICSID Conventio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Vol. Ⅱ, Part 2, 1968, p. 1010.
⑨ 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6条第2款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发价不得撤销:(a)发价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发价是不可撤销的;或(b)被发价人有理由信赖该项发价是不可撤销的,而且被发价人已本着对该项发价的信赖行事。
⑩ 遗憾的是,应申请人要求,该案仲裁程序已于2009年10月21日停止。
⑪Pan American Energy LLC v.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10/8。该案于2010年4月12日在ICSID登记,并于2012年8月24日由ICSID组成了仲裁庭。争端双方于2014年8月25日达成一致意见,仲裁程序中止至2014年10月20日。https://icsid.worldbank.org/ICSID/FrontServlet. 2014-09-18.
[1] Christoph Schreuer.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86.
[2] Sébastien Manciaux. Bolivia’s withdrawal from ICSID [J].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2007(5): 4-10.
[3] Emmanuel Gaillard. The denunciation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J]. New York Law Journal, 2007(122): 6-12.
[4] Michael D. Nolan, Frederic G. Sourgens. State-controlled entities as claiman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 early assessment [J].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2007(9): 15-37.
[5] August Reinisch, Christina Knah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context [M]. The Netherlands: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08: 7.
[6] Aron Broches.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J]. Hague Recueil, 1972(136): 340-341.
[7] Ceorg Res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ter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1.
[8] Lauterpacht 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ivate foreign investment [J]. Indian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1997(274): 259-265.
[9] Julien Fouret. Enforcement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wards: a global gui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08(25): 71-75.
[10] Garibaldi O M. On the denunciation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consent to ICSID Jurisdiction, and the limits of the contract analogy [C]// C. Bi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for the 21st Century: essays in honour of Christoph Schreuer. Oxford: OUP, 2009: 262-278.
[11] Michael D. Nolan, Frederic G. Sourgens. The interplay between state consent to ICSID arbitration and denunciation of the convention: the (possible)venezuela case study [J].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2007 (9): 15-45.
[12] Andrew Newcombe, Lluís Paradell. Law and practice of Investment Treaties: Standards of treatment [M].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9: 28.
[13] Tietje C. Once and forever? The legal effects of a denunciation of ICSID [J].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2009(1): 8-53.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ent” in Article 72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YIN Hongwu
(Law School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The thre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namely Bolivia, Ecuador and Venezuela, successively denounced the ICSID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law theorists as well as the practitioners diverge a lot on the issue of comprehending and applying the denunciation clauses in the ICSID Convention. The critical reason is that they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 “consent” in Article 72 of the Convention. “Consent” in Article 72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shall be interpreted as “offer of consent” or “unilateral consent”. Once the “consent” to subject to ICSID jurisdiction has been given by the host state, it amounts to a compulsory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and the “offer of consent” becomes irrevocable. The “offer of consent” to subject to ICSID jurisdiction given before the denunciation notice by the denunciation country is acceptable not only before the denunciation, but also during the “waiting period” (between the denunciation noti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denunciation), and it remains valid even after the denunciation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takes effect. But the foreign investments able to “accept” the “offer of consent” made by the denunciation country shall be confined to the ones made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host country’s denunciation.
ICSID Convention; consent; interpretation; irrevocability; validity period
D996
A
1672-3104(2014)06-0166-06
[编辑: 苏慧]
2014-05-04;
2014-09-18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湘教发[2011]42号);2014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国际投资法学双语教学实践研究”(20148559);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条约退出权研究”(2013BQ08)
银红武(1973- ),男,湖南武冈人,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投资法,条约法与国际贸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