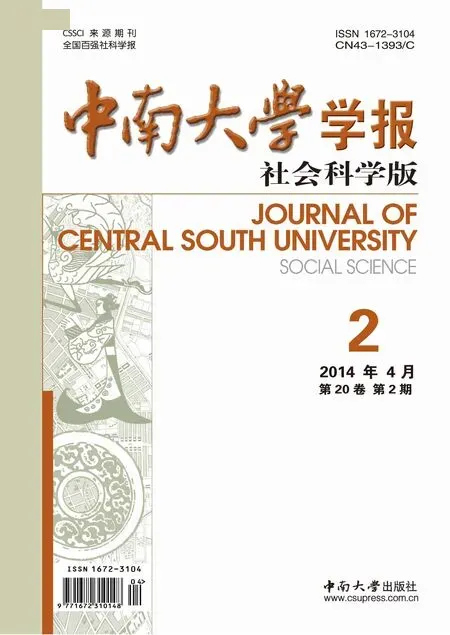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观念考辨
2014-01-21王进
王进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欧美后现代语境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它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勃兴却是伴随着国内文坛逐渐兴起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热潮[1](142)。 当代文艺研究的历史、文化和诗学转向,不断激发中外学界对文艺经典与历史意识的研究兴趣。与此呼应,非物质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的高调兴起,理论方面是回应从文艺形式到文化活动的研究转向,实践方面却是源自从城市空间到民间经验的趣味嬗变。如果说“今天的历史,是身体处在消费主义中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2](21−22), 那么非物质文化研究,就是要将身陷城市空间的主体视界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现代性思想梦呓当中解脱出来,以历史意识和文化传统积极应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异化城市”,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幻象的“自我迷失”。诚然,非物质文化研究能够改善和提升不同城市空间话语的历史形象、文化品质和认同意识。因此,从文化诗学视角来看,有必要在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对象、理论范式和社会价值三个层面,总结和反思其对文艺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利弊,从文艺形式、历史情境和民间经验等方面深入探讨非物质形态的学术空间。
一、作为研究对象的非物质文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话语经过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推波助澜,业已成为当下使用频率最高、最负有争议的理论话语。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本身也发展成为形式上无所不包、实质上内容宽滥的混沌概念。如果说物质化的文化概念已经漫无边际、无法界定,那么当下学界何必又多此一举? 再次推出“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对象,意欲何为?又有何作为?
与侧重大众文化和意义生产的文化研究思潮有所不同,非物质文化概念首先源自于对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的保护责任和生态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在巴黎签订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官方定义如下:“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3](1)相对于文化研究的文化观念,非物质文化概念更加关注群体性的文化遗产观念和集体性的社会建构活动,具体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创新意识,即基于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文化认同经验和历史传统意识,以及尊重文化差异和社会阶段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在非物质文化的文化观念当中,“这些集体创造的社会产物,其美学价值存在于特定的再现方式,同时却又联系到由机制、实践和信仰组成的整个文化网络”[4](6)。因此,非物质文化研究具有文艺形式和文化经验的两个方面内容,它在社会建构层面上与文学艺术的文化形态具有相似的文化生产实践,在文化遗产层面上则呈现出与其迥异的历史传播结构。对于非物质文化的理论研究应该首先关注和探讨它本身的二元属性,即群体性的文化遗产观念和集体性的社会建构活动。
从文化诗学的理论视角来看,非物质文化和文艺作品一样,在文化生产的社会活动当中实质上“都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5](6−7)。有所区别的是,文艺创作的价值视角可以时常呈现为不同作家个体对各自时代的主流文化的叛离和颠覆意识,非物质文化的价值观念则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社会群体对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的继承、恢复、改良和传播过程。对当下语境的研究者来说,首先要关注这些文化生产活动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境。如果说各种历史主体的时空对话是文艺作品作为文化遗产的历史属性和社会潜能,那么对文化诗学批评来说,“这种交流,正是现代审美实践的核心,为了对这种实践做出回答,当代理论必须重新定位:不是在阐释之外,而是在谈判和交易的隐秘之处”[6](14−15)。因此,它最终指向的乃是非物质文化作为历史经典的塑型经验和传播过程。
实际上,能够在历史传播过程当中最终成为经典的文艺作品,它们内部要素必定包括以下内容:“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以及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7](86)文艺经典的这六个要素基本上围绕特定历史情境的文化生产实践,在作者创作、社会传播、读者阅读和文化消费之间,形成一种基于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历史传播结构。以文艺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批评观念,它的弊端主要在于回避文艺作品本身的社会属性和传播方式,因此在重视形式价值的同时反而忽视作品之外的诗外功夫,在强调形式结构的同时反而消解文学艺术的传播结构,专注形式批评的同时反而遮蔽文化生产的生态空间。有鉴于此,文化诗学视域中的文艺批评也好,非物质文化研究也罢,就是要重新回到文艺传播的社会空间,充分关注文化生产的民间经验。
二、作为理论范式的非物质文化
针对非物质文化的理论范式,高小康先生主张以“非文本诗学”作为文艺研究活动的“文化生态视野”。具体来说,就是要转向以文艺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还原“文学文本发生和传播的活态过程”;以民间文化的生态意识作为研究视野,考察“经典的文学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以文化生产和社会传播作为理论范式,致力发现“活态的多样性特征”;以田野实践作为研究方法,“以参与、同情、体验和对话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异”[8](13)。作为文化生产和历史传播的两种不同批评视角,文学艺术的文化概念与非物质文化的历史意识之间相互影响并且彼此渗透:文学的文化批评对非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影响主要在于社会建构层面的文化生产实践,非物质文化对文学批评的理论价值则在于文化遗产层面的历史传播结构。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视角来看,非物质文化与文艺研究的泛文化观念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它们的理论重心或许有物质和非物质,或者是文本和非文本之间的形式差异,但是最终指向的都是文艺作品的文化生产实践以及文化活动的历史传播结构。
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对象是各种集体性的社会建构物和群体性的文化遗产,它关注的是文艺形式的文化生产过程和文化形态的历史传播结构。从文化诗学的理论角度来看,文本诗学与非文本诗学或许只是作为非物质文化的两种批评范式,并非是其转向社会、回避文本的理论借口。实际上,从后现代文化的学术语境来看,文本和非文本之间的文类区别,或者说是诗学距离,确实有可能扭转当代学界自语言转向以来日益走向极端的文本化和平面化倾向,也有利于促进文艺研究积极转向历史情境、传播过程和文化生态的理论范式。然而,从符号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非文本概念并没有真正解决非物质文化的批评范式问题,它突出和放大社会语境的文化活动和生态价值,反而被视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文本”或“口传文本”。对此,康奈尔大学拉卡普勒教授认为,“这种语境主义范式鼓励的通常是片面和狭隘的档案阅读”,在此之中“语境只不过是时间符号或现象表述,不加分析的阅读阐释方法常常成为绕过文本自身的途径,最终成为忽视文本阅读的某种借口”[9](147)。
卡普勒描述和批判“语境修辞”和“情境阅读”的话语虽然有些极端,但是从侧面却强调了文本阅读的理论范式:语境阅读同样离不开文本层面的文化符号,文本结构已经蕴含时间符号的历史语境。蒙特洛斯用“历史的文本性”概念进一步阐明文本性对历史语境的两种批评范式:① 从社会文本到历史语境的阐发范式,文本形式的文化遗产是“一种不依靠社会现存文本踪迹的中介作用而存在的活态物质形态”,“它们至少部分是源自那种保存和抹杀的那些复杂而细致的社会过程”;② 从历史语境到社会文本的传播范式,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传播过程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对于社会文本的重新搜集和整理工作,“这些文本自身一方面是作为历史学家阐释历史文化的‘文献’平台,同样也是作为后续、甚至后世学者阐释和研究历史文化的传播媒介”[10](15)。无论是历史文化的阐发范式,还是社会文本的传播范式,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工作在理论视角上采用的是非文本诗学的生态批评观念,然而在研究范式上却仍然延续着人类学和符号学意义上的社会文本模式。
非物质文化的研究重点就在于“考察艺术话语与社会环境话语之间关系”:在群体性的社会建构层面,它必须关注历史情境和社会机制的阐释和生产过程,“将多种社会、机制和政治实践,连同其它比如文学或非文学文本这样显著的话语现象一样,被放置于同样的阐释过程”;在集体性的历史传播层面,它又必须重视社会文本和文化活动的传播和消费方式,“将社会重写成‘社会文本’,将历史、机制和社会实践视为‘文化脚本’”[11](257)。从文化诗学的理论视角出发,高小康先生指出这种“作品链和活动史”理论范式表明当代文艺研究的非物质文化导向,他认为文艺研究话语应该关注文艺作品之后的“叙述——接受”活动演变历史,并且延伸到“作品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演变的活动过程及其文化环境中去”,从而“从作品价值与关系的研究扩展到作品背后的活动方式与形态研究”[12](63)。 由此可见,当代文艺研究逐渐重视文艺作品和文化文本的社会属性和传播结构,更加突出非物质文化在社会建构和历史传播两个层面的理论观念,文化诗学的理论视角为非物质文化研究则提供出从文化符号的历史传统转向社会活动的文化传播的研究范式。
三、作为价值体系的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的理论对象表现为文化符号或叙事文本,它的研究路线大致是首先从文本和符号来解读出符号制品和文化仪式的历史情境,其次从文化符号的历史情境来探讨和重现相关文化生产过程的社会活动,最后从群体性的社会活动来考察各种文化符号的历史传播结构。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视角来说,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工作同样要“研究各种独特文化实践的集体性建构过程,以及探讨这些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它首先要针对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播结构,“探讨这些集体信仰和经验如何得以成型,如何在媒介之间实现传播,如何专注那些可以被操控的美学形式,以及如何被提供给消费活动”;其次要针对文化符号的社会建构过程,“考察如何标识在各种文化实践艺术(通常被理解为形式和相近表述方式)之间的各种边界,也可以厘定这些特别划界的区域如何被给予权力去赋予愉悦、激发兴趣或是产生焦虑”[13](5)。从文本和符号的社会建构过程来考察历史情境的文化活动,从它们的历史传播过程来考察当代社会的群体文化意识,文化诗学的批评观念在社会建构和文化传播两个层面丰富和提升了非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非物质文化的深入研究促进文化诗学批评对文化符号与群体意识的不断关注。这两种批评话语的理论对话和渗透过程,不仅融合文本和非文本形态的诗学空间,而且呈现出活态历史与生态文化的价值体系。
从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体系来看,它必须厘定至少三种理论关系,即文学文本与文学活动的关系、经典文本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学形式与文化空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研究对象从文学文本转向文化活动表明它更加关注非文本形态的文化经验和非典型特征的艺术价值,理论范式从经典文本转向民间文化体现它更多采用去精英化的批评视角和社会介入式的研究方法,理论旨趣从文学形式转到文化空间突出它更加重视历史性的文化生产过程和结构性的历史传播体制。然而,从文化诗学的批评观念来看,非物质文化的活态历史观念首先应该确立三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即关注对知识与意义的研究立场,穿梭在文本与历史之间的研究方法,审视中西文化对话的研究视角[14](46)。
实际上,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体系不仅呈现为客观知识形态的史学考据和文化考古,而且还表现为主观意识形式的历史阐释和审美经验。它的理论范式不但包括对文本结构层面上的文化符号的厚度阐释,而且蕴含在历史情境层面上的文化生态的活态阐释;它的理论旨趣不但在于反思西方理论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研究、文化诗学视角下的本土文化形态分析,而且在于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在理论空间和诗学层面的交相呼应和彼此融通。文化诗学视域中非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虽然呈现出“厚度描写”历史和“深度阐释”文化的不同形态,但是两者在本质上强调的都是文艺活动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符号的传播属性,彼此关注的也都是社会文本的整个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最终呈现的也都是历史情境的集体生产过程,以及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播结构。就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体系来说,文化意义的传播结构实际上是同时存在于文化符号的社会生产、 历史情境的文化再现,以及当下群体的认同意识,它所承担的研究任务不仅是对历史文化语境的逆向研究,而且也包括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
针对文化诗学的价值体系问题,童庆炳先生曾经强调:“文化诗学有三个维度:语言之维度、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度;有三种品格:现实品格、跨学科品格和诗意品格;有一种追求:人性的完善和复归。”[15](9)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研究来说,它的价值体系同样可以拥有文化符号、传播结构和群体意识的三个分析维度,具有社会文本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跨学科意识,以及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这三种批评观念,而其最终目的就是在民间经验层面上建构自愿的群体意识和自觉的文化认同。具体而言,它在文化符号维度上考察文艺活动作为文化生产的活态历史,在传播结构维度呈现社会文本维系文化传承的审美空间,在群体意识维度探讨文化遗产作为认同方式的民间经验。然而,非物质文化研究对文化诗学的理论借鉴,不是要以后者的诗学体系规化收编前者的非物质形态,更不是要以原本作为理论视角的诗学话语越俎取代理应作为研究内容的文艺经验,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补充强化文艺活动的活态历史意识和民间经验的群体传播结构。由此,非物质文化研究致力呈现的不仅是活态历史和生态文化相互交织的理论阐释视角,而且是文艺形式、历史情境和民间经验彼此对话的文化诗学空间。
[1]李圣传.“文化诗学”流变考论[J].《天府新论》2012(5):142−149.
[2]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http://www.unesco.org/new/zh/unesco/resources/publications/unesdoc-database/, 2003年, 巴黎.
[4]Stephen Greenblatt,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 1982.
[5]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M].Oxford:Clarendon, 1990.
[6]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7]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 86−88.
[8]高小康.非文本诗学: 文学的文化生态视野[J].《文学评论》,2008(6): 13−17.
[9]Dominick LaCapra.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10]Harold Abram Veeser (ed.).The New Historicism[C].New York:Routledge, 1989.
[11]Murray Krieger (ed.).The Aims of Representation[C].N .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高小康.作品链与活动史-对文学史观的重新审视[J].《文学评论》, 2005(6): 57−63.
[13]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李春青.文化诗学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1(6): 46−50.
[15]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