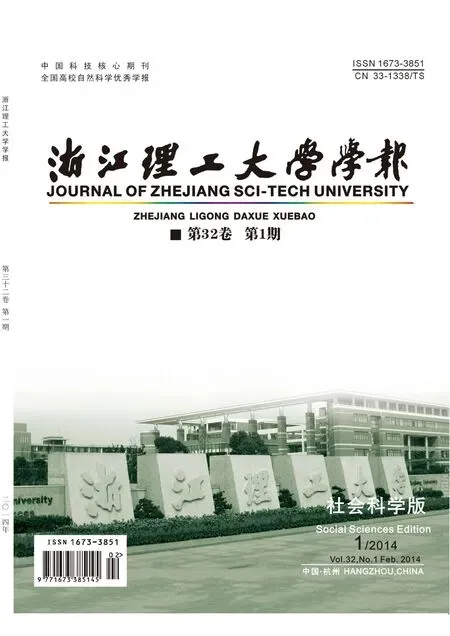排污权交易监管的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研究
2014-01-21魏静
魏 静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杭州 310018)
排污权交易监管的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研究
魏 静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杭州 310018)
由于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的局限性及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内在要求,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在排污权交易的监管中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文章对比分析了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和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在排污权交易监管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认为非强制性环境执法方式(包括环境行政指导、环境行政合同和环境行政奖励等),在弥补法律空白,提高执法效率、节约执法成本,平衡各方利益,最终实现环境管理目标方面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环境行政指导;环境行政合同;环境行政奖励
排污权交易监管的非强制性执法是指,排污权交易环境主管机关采用指导、奖励、合同等非强制性执法方式,诱导、促使排污权交易主体主动履行排污权交易义务的一种执法方式。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注重与行政相对人的充分协商和沟通,注重信息的准确及时发布,注重相对人积极性的发挥,让相对人主动作出有益于环境管理目标实现的相关行为,从而有利于减少环境行政执法的成本、提高环境执法效率。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实现污染控制的制度安排,市场机制能否发挥作用,有赖于排污权主体的积极、主动参与,否则这一制度的功能难以实现。这种制度要求与非强制性环境执法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在排污权交易监管中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但遗憾的是,在排污权交易监管的实践中,仍然倚重于传统的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方式。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监管方式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尽管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方式在环境执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方式执法成本高、效率低的缺陷也是不容否认的。在我国,由于受资源、法律等多方限制,环境监管能力不足的局面相当普遍并将长期存在[1]。因此,积极探寻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方式在实践中的运用有着重要意义。在环境执法理论研究上,近些年来,学者们逐渐将视野转向“柔性”的非强制性环境执法方式上,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就排污权交易监管领域的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探讨适合排污权交易监管领域的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监管方式,以期抛砖引玉。
一、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在排污权交易监管中遭遇“瓶颈”
(一)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依据缺失
规范、严格、完备的立法是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的前提。目前,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相关立法尚处于探索阶段,国家层面的立法缺失,地方立法不完善,且存在效力危机。
首先,排污权交易的前提条件缺乏明确法律规定。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立以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建立为前提,实施排污权交易必须具备完善的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但目前我国的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没有统一的立法,相关规定散见于各单行法中,且这些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此外,由于缺乏排污许可证管理国家层面的立法,使得地方发放的排污许可证法律效力存在问题,这使得缺乏前提的排污权交易显得底气不足。
排污权交易环境行政执法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将排污权交易法律规范中抽象的权利义务变成排污权交易主体的具体权利义务的过程,但目前排污权交易规范缺失、不完善,排污权交易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定不明确,更遑论排污权交易的行政执法监管了。
(二)排污权交易监管中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成本高、效率低
在排污权交易中,准确掌握污染源排污情况既是排污权交易的先决条件,亦是排污权交易后监管的重点。无论是排污总量的核定、排污指标的合理分配还是交易后的排污监管都以排污单位的实际排污情况为依据。所以,建立高效、经济的污染源执法监管机制以监控排污权的使用情况是排污权交易执法监管的基础和关键。目前,从现行的污染源执法监管机制的运行情况看,一些行业、区域的污染源执法监管情况不容乐观,呈现出高投入、低效率,环境监管成本高昂,污染源长效管理效果差的态势。
首先,环境执法监管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执法监管力量分散、环境监测能力不足、技术力量薄弱、技术方法不完善,执法监管基础设施不完备、技术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尤其是污染物排污总量监测监控能力不足。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推行总量控制,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污染源监测监控能力建设,虽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仍存在明显不足: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尚未通过计量认证,尚不能成为执法依据。环境监测人员、实验条件、仪器装备缺乏,难以满足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和在线监控设施监测比对工作的要求等。
其次,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监管机制僵硬,成本高、效率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监管手段无法应付数量庞大、情况复杂的污染源执法监管任务。一些行业、区域的排污单位偷漏排、隐瞒真实排污状况等逃避环境责任的行为时有发生,难以禁绝;长效监管效果差,一旦环境监管力度稍有放松,污染反弹严重;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的环境监管工作、负担重,容易成为矛盾的集中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本应由排污单位自行承担的污染源执法监测责任,高额的行政开支由社会大众承担,造成社会不公平,同时缺少权力的监督制约反而易引起权力寻租行为。一旦排污权交易制度开始实行,受巨额经济利益的驱使,排污单位逃避环境责任的动力更大,污染源执法监管的难度和压力将更大。
二、非强制环境执法在排污权交易监管中的优势
(一)弥补法律空白,进行法律试错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有关排污权交易的相关立法存在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立法;地方立法层级低且存在“合法性”危机的现状。依照行政法“法无明文规定则禁止行政”的原则,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在法律规定不完善或没有规定时常显得束手无策。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通过指导、奖励、合同等“柔性”执法方式诱导、促使环境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目标,并且可避免执法不能的尴尬。此外,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往往还具有法律试错的功能。制定法的非全真性和非周延性,是制定法无法完全克服的一个“硬伤”。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个缺陷。环境行政执法主体通过环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方式,对环境行政相对人进行规制和引导,以实现环境管理目标,可以根据实施的效果对指导等规定进行相应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之后再上升为相应的法律规定,从而减少立法的盲目性。
(二)提高执法效率、节约执法成本
传统的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方式以其强制性,可能某一时段能以少量成本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长远看,这种执法方式是高成本、低效率的。因为这种强制性执法机制的运行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庞大的人员和日常开支来支撑,而更为重要的是,强制性执法的“刚性”执法方式,忽略了相对人的诉求和利益,容易引起环境行政执法相对人或显性或隐性的反抗,这种“抵抗”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而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以其协商性、引导性、非强制性和交流性等“柔性”特征引导,促使环境行政相对人能自愿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从而减少环境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减少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特别是在排污权交易这一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实现污染控制的制度安排中,市场机制能否发挥作用,有赖于排污权主体的积极、主动参与,否则这一制度的功能难以实现,将会出现“有平台无交易”的局面。目前在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相关法律不完善,排污者还在“等待观望”的情形下,更需要环境行政主管机关通过示范、鼓励、建议、劝告、提倡等非强制性方式,加强政策引导,让排污者明确政策的效益,充分调动企业购买排污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使排污权交易制度得以顺利实施。
通过观察图6图7中响应面的变化情况和等高线的稀疏程度可直观地反映山羊发酵乳菌种添加量/%(X 1)、后熟时间(X 2)、发酵时间(X 3)交互作用对水解度的影响,当等高线呈圆形时表示两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而呈椭圆形或马鞍形时则表示两因素交互作用显著。
(三)平衡各方利益,实现环境管理目标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运作原理在于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通过利益的引诱促使排污者主动减排,从而实现污染控制的环境管理目标。在排污权交易过程中有多方主体参与,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排污者能够获得经济利益,而环境主管部门则能实现环境管理目标,从而使得公众的环境利益得以实现。这与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的理念不谋而合。在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中,环境行政执法主体不再以自己单方的意志进行执法,而是充分考虑环境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诉求,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方法,激发环境行政相对人将个体逐利的能量转换为环境保护的动力,从而使得环境行政相对人能主动地、自愿地作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最终使得环境保护目标得以实现。换言之,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因兼顾了相对人的个体利益,而最终实现了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
三、排污权交易监管中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的具体形式
学者们一般认为,环境行政执法行为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环境行政指导、环境行政合同、环境行政奖励。
(一)环境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作为一个行政法概念首先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而在欧美等国家,行政指导被归类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或非正式行政行为、非正式的协商性程序裁决和简便式行政活动等[3]。将行政指导这一非强制性行政方式运用于环境法执法中,产生了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指导。具体而言,环境行政指导是指环境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环境行政目的,在其职权内,通过制定诱导性法规、政策、纲要、计划等规范性文件以及采用具体的示范、鼓励、提倡、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式并辅之以诱导,促使相对人自愿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目标的一类权力性行政行为[4]。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法规确立了环境行政指导这一非强制性环境行政制度。如《环境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高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6条规定,“国家采取有利于煤炭清洁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使用低硫份、低灰份的优质煤炭,鼓励和支持洁净煤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水法》第10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先进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等。但这些规定大多数是鼓励性和宣示性的,而对相关的环境行政指导的法律效力、法律程序、法律后果等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使得环境行政指导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运用。
环境行政指导根据其作用可以划分为调整型环境行政指导、限制型环境行政指导和助成型环境行政指导。调整型环境行政指导是指通过利益调整等方式,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纷争而实施的环境行政指导行为。限制型环境行政指导是通过警告、规劝等方式对环境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进行预防或阻止的环境行政指导行为。助成型环境行政指导是指环境行政主体帮助行政相对方实现其价值和利益的环境行政指导行为[5]。在排污权交易中,可综合运用这三种环境行政指导方式,而其中尤其应注意运用助成型环境行政指导。因为在助成型环境行政指导中,环境行政相对人只要接受环境行政主体的环境行政指导,就能获得环境行政指导所明确的利益,在利益的趋使下,在理性“经济人”的指引下,环境行政相对人将愿意选择接受指导,从而顺利地实现环境行政指导的目标。目前,排污权交易还处于试点阶段,许多排污企业对排污权制度的认识不够,参与排污权交易的积极性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应当充分运用助成型环境行政指导,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政策引导,推行优惠政策,让排污企业明确政策的效益,充分调动企业购买排污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可喜的是,一些地方立法中这一环境行政指导方式已得到体现。如《杭州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实施细则》(试行)关于指标分配的规定“为鼓励对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因处理生活污水新增的化学需氧量(COD)部分由环保部门无偿划拨。处理工业污水新增的化学需氧量(COD)部分可从现有纳管工业企业的化学需氧量(COD)配额中优先通过排放权交易获得。”“热电联产机组因增大供热量而增加的二氧化硫(SO2)排放量,其所需配额从被替代的现有小锅炉腾出的二氧化硫(SO2)排污配额中优先通过排放权交易获得”。这些规定虽还不细致、完善,但相信对刺激排污者的积极性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前所述,我国关于环境行政指导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善。在排污权交易监管中设立环境行政指导制度,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环境行政指导的设立应关注行政相对人一方的利益诉求。环境行政指导是通过示范、建议、提倡等方式诱导环境行政相对人自愿接受指导的内容,环境行政相对人能否自愿接受指导的关键在于指导的内容是否符合其利益诉求。因此,环境行政指导的设立应充分考虑相对人一方的利益诉求。这要求环境行政主体在作出一项具体的环境行政指导行为前,应充分听取、考虑环境行政相对人的意见,环境行政主体不能仅凭单方的意愿作出指导行为,否则指导行为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引起行政相对人的抵触和对抗。当然,环境行政指导不能只考虑相对人的利益,毕竟环境行政指导实施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环境管理目标,在于维护社会公众的环境利益。因此,在环境行政指导出台前,还应充分听取相关公众和相关专家的意见,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以可行性论证的结论作为是否实施具体环境行政指导的依据。其次,环境行政指导应当程序化。正当、完善的程序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力武器。环境行政主体在实施环境行政指导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性,如果不加以规范,就难以避免环境行政主体滥用环境行政指导权。因此,应当明确规定环境行政指导的程序,用完善的程序来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最后,完善环境行政指导救济。和所有的行政行为一样,环境行政指导可能因为权力者滥用权力、行政程序不完善等原因给环境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根据“有损害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应当设立和完善环境行政指导救济措施,对违法的、不当的环境行政指导行为进行救济。救济方式应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
(二)环境行政合同
环境行政合同是环境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环境管理目标、行使环境行政职权,而与环境行政相对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与环境管理直接相关的权利、义务的协议[6]。与一般民事合同和普通行政管理行为相比,环境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环境性和合同性,是公法精神与契约自由的完美结合。既能维持行政效率所要求的“行政权优先”,又能体现对环境行政相对人的尊重与关怀。环境行政合同的应用,可以弥补环境立法的不足,有利于法律法规的灵活执行;有利于调动环境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从而更利于实现环境管理目标;有利于保护环境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更好地实现环境管理中的利益平衡。
在欧美等国家的环境管理领域,环境行政合同早已得到了广泛运用,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环境管理中运用环境行政合同,已有的环境行政合同类型包括污染费使用合同、“三同时”承包合同、污染源限期治理合同等。在排污权交易的监管方面,环境行政合同大有可为。首先,在排污指标的分配、回购、交易上,可运用环境行政合同。环境行政机关根据区域环境容量,确定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并分成若干排污指标,然后以招标、拍卖等方式分配给排污者,环境行政机关与排污者签订排污权许可合同。排污许可合同一经签订,排污者根据合同规定的排污指标排放污染物,并能将通过技术改造获得的富余排污指标进行交易。在排污许可证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未全面施行的现况下,运用环境行政合同进行排污指标的分配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如山西太原市结合企业承包租赁,以合同形式将污染物排放指标和浓度指标一起承包。其次,就排污企业的污染源限期治理、削减污染物排放量以及排污权交易后的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等方面,也可以运用环境行政合同来实现。例如,对超标排污的排污者,环境行政主体可与环境行政相对人就有关限期治理目标、期限和违约责任等问题达成环境协议,要求排污者按照协议内容完成治理任务。如果排污者逾期不履行治理义务或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环境行政主体可以与第三人签订限期治理代履行合同,由第三人代替排污者履行治理义务,而治理所需费用由排污者支付,以保证限期治理的任务能够切实完成,实现环境管理的目标。
为保证环境行政合同能真正发挥作用,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合同订立阶段,应凸显环境行政合同的“合同性”,充分尊重环境行政相对人的意愿,激发环境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虽然,环境行政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环境行政相对人不享有是否就某一事项订立环境行政合同的决定权、不享有要约权、也不享有选择合同相对方的权利;但环境行政合同也不同于一般的环境行政行为,它不是环境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的体现,而应当是环境行政主体和环境行政相对人合意的结果,因此,环境行政相对人应享有是否接受要约的权利,否则环境行政合同就不能称之为合同,就和一般的环境行政行为无异。既然环境行政合同应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那么,在环境合同内容的拟定上,环境行政主体应考虑环境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充分听取环境行政相对人的意见,以协商的方式确定合同的权利义务。只有这样,环境行政合同才能因符合环境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而得到其自觉履行。其次,在环境行政合同履行阶段,应加强环境行政权力的控制,凸显环境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如前所述,环境行政合同要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才能激发环境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自觉履行合同。但就其本质而言,环境行政合同是为实现环境管理目标、实现环境公共利益而缔结的。环境行政合同中有关环境公共利益的特定义务能否实现,直接决定了是否会产生环境损害。换言之,为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有关环境公共利益的特定义务必须获得实现。因此在环境行政合同履行阶段必须加强行政权力的控制,确保合同能够得到全面履行,从而实现环境管理目标。最后,由于环境行政合同“环境性”的要求,环境行政合同的内容不可能一层不变,为顺应环境保护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环境行政主体可以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环境管理目标的调整而及时变更合同内容,以确保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但为保障环境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环境行政主体在变更环境行政合同时一般应与环境行政相对人协商,征求其意见,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单方变更合同内容。
(三)环境行政奖励
环境行政奖励是指环境行政主体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或精神鼓励的具体行政行为[7]。环境行政奖励通过对受奖人环境行为的肯定与褒扬,激发环境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其主动实施一定的环境行为,以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环境行政奖励在充分考虑环境行政相对人的价值偏好、精神需求等利益因素的基础上,将环境行政行相对人个体逐利的需求转化为环境保护的动力,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相较于环境行政指导和环境行政合同,环境行政奖励更符合非强制性环境行政执法的理念,更有利于消除环境行政相对人的对抗情绪、激发环境行政相对人的环保意识,降低环境执法成本。依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把环境行政奖励进行不同类型的划分。依奖励形式的不同,可分为荣誉性奖励、职位性奖励、信息奖励、权能性奖励和财物性奖励等。
目前各国环境法大都建立了奖励优秀环境行为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的环境保护实践中,设立了诸如环境保护百佳工程奖、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环保科技奖等环境行政奖励,肯定和鼓励环境行政相对人实施某些行为,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环境奖励制度作为一种环境保护的行政法律形式,在我国历史上由来已久[8]。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的颁布,标志着环境行政奖励作为一项基本环境法律制度得以正式确定。在一些环境单行法中,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法》《森林法》等均有关于环境奖励的规定。虽然我国环境立法中普遍规定了环境奖励制度,但现有规定不够完善,如环境行政奖励授奖主体不明确;环境行政奖励种类、等级不明确;环境行政奖励条件过于笼统;缺乏程序性规定、缺乏责任规定、缺乏救济渠道等,致使环境奖励制度的实际操作存在困难。
环境行政奖励既能满足环境行政相对人对个体私利的追求,从结果上看,又能实现环境管理目标。在排污权交易领域,也可广泛运用环境行政奖励,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关于环境行政奖励的规定只是针对有“显著成绩”和“显著贡献”的主体进行,范围过于狭窄。如《环境保护法》第8条规定,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对水污染防治有显著贡献的单位或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事实上,环境行政奖励是通过满足环境行政相对人的逐利需求,诱导其主动实施环境保护义务,从而实现环境管理目标。就其本质而言,环境行政奖励是和环境行政处罚一样,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环境保护目标的一种执法方式。在强制性执法方式占主导的现状下,为提高执法效率、降低执法成本,应充分利用环境行政奖励这种正面引导和激励的执法方式,扩大奖励范围,只要排污者的排污行为符合环境管理目标,并取得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特定实效就应当纳入到环境行政奖励体系中。如在排污权交易监管中,可以建立定期排污绩效考核机制:对于排污企业所购买的不同类别污染源的排污权许可证额度,在一定期限内与污染监测体系所监控的实际排污数据和年度环境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同时参考环保局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对企业排污权配额的实际运作绩效进行考核。对考核合格的企业,在今后年度排污许可拍卖以及新建扩建项目排污权配额时予以优先申购权利,以促进排污权的优化配置。环境行政奖励在具体运行方面,还需对奖励的具体标准、奖励的内容、奖励的程序、奖励的监督以及环境行政相对人的救济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1]齐 晔.中国环境监管机制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6.
[2]沈满洪,钱水苗,冯元群,等.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52-54.
[3]莫于川.法治视野中的行政指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
[4]周玉华.环境行政法学[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2:192-193.
[5]崔 冬.论环境行政指导在水资源保护中的运用[C]//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水资源、水环境与水法制建设问题研究:2003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2003:282-284.
[6]钱水苗,巩 固.论环境行政合同[J].法学评论,2004(5):95-102.
[7]张梓太,吴卫星.环境保护法概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131-132.
[8]胡宝林,湛中乐.环境行政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16-19.
(责任编辑:张祖尧)
Study on Law Enforcement of Non-mandatory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in Emission Trading Supervision
WEI Jing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law enforcement of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intrinsic requirements of emission trading system,the law enforcement of non-mandatory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has wide application space in emission trading supervision.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roles of law enforcement of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of non-mandatory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in emission trading supervision and thinks that the method of law enforcement of non-mandatory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including guidance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contract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reward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etc.)will play a vital role in making up for legal blanks,improving law enforcement efficiency,saving law enforcement cost,balancing interests of various parties and finally achieving the go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of non-mandatory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guidance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contract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reward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1673-3851(2014)02-0007-06
D922.69
A
2013-07-02
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委托项目(12090162-J)
魏 静(1975-),女,贵州开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法、商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