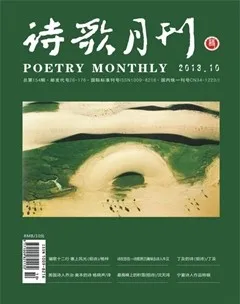西湖柳丝纤如发(外二篇)
2013-12-31林馥娜
暴雪来临的前一天,我们来到了杭州西湖,严寒中的柳丝虽无叶叶如眉的娇媚,却有着发丝如云的柔美。杭州西湖因为有断桥、雷锋塔等蕴藏着凄美故事的古迹和临水而栽的垂柳而带着柔软的韵味。一条情人堤跨湖而过,据说有情人如果携着手在这堤上走过一遍就能终成眷属。而我更喜欢它的另一个名——苏堤,它让人想起豪放的苏东坡和娇柔如水、至情至美的苏小小。
苏东坡对于杭州的重要性自不必提,从杭州人尊称他为老市长就可知一斑。而苏小小却以其情义和才貌而存活在人们心中。未到西湖时,己提起要到小小墓一看,最后却还是顺众意而错过。只有李贺的诗《苏小小》,犹在心里絮絮丝丝,缠绵不已——“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泠下,风吹雨。”一个我见犹怜、痴情空付而又倔强仗义的女子,宛如这西湖边纤若游丝的垂柳,影影绰绰地立于这水色湖光中。
白娘子与许仙的断桥、雷锋塔也都是在船上远远的瞭望一番,这样匆忙的游历,不无遗憾,但也有意外之喜,只见一个铁质镂空女人像闲花照水地立在西湖旁,确切地说是一块纪念碑,原来是著名诗人、建筑学家林徽因碑像。碑上的记述文字与人像采用镂空的方式,依稀可见斯文逸秀的伊人轮廓。林徽因出生在杭州的一条小巷——蔡官巷,并在杭州生活了5年,如今她又回到了故里,湖水悠悠流过她的身后,流过旧日时空,而那蓊郁的湖中树,犹如她作为诗人、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的动人往事,在水中、在襟怀中,温润如新。林徽因之所以成为佳话,不但在于她的才情与柔美,也在于她的柔中所葆有的刚,她既有诗人的浪漫与柔情,也有学者的坚韧与冷静。正因为冷静,她才会让自己成为徐志摩的终生眷恋,成为金岳霖那枝可望不可采的“白玫瑰”,成为粱思成志同道合的伴侣。
与朋友谢说起西湖之行的匆忙,他说:“本该找个时间,在那里住下来慢慢走、慢慢看,才不负这份柔软心事。”正如杭州的西湖是骚人墨客心中的柔软地带,各地的西湖也必是当地人心中的温存之境。故乡揭阳的西湖也是一个浸润人心的去处,榕江水幽缓地在湖畔流淌而过,湖中间是跨湖而起的九曲栏桥,宛若有情人的罗带心结缱绻地绕在湖面上,雕栏亭台处常出没着成取成对或一家老少的温馨剪影。右侧是树木掩映着的工夫茶园,正宜三两知己相约园中,品荼谈心,赏湖光、花影、曲径。昔日,我与友曾在临江的椿树下谈心,几个调皮的小孩攀附在绿叶婆娑的树丛中嬉戏着,不时探出头来偷窥一眼,仿佛在静候我们上演什么新奇的戏码,而我们也欣然地分享着他们的无忧与天真。每当忆起旧景,竟是一片水洇般的湿润。
此趟行旅,发觉杭州的香樟树和榉树特别多,原来这也是有由来的,这里的旧习俗是以树为标,夹藏着每户人家儿女的性别和寄意。家中生女就会在屋前种香樟树,生男则种榉树,榉树取其中举之意,香樟则表示家中有女儿,是给说媒人的一种标示。女儿出嫁时,香樟树也会随之砍伐,因为香樟树是一种能散发香气又不生虫蛀的好木料,用来做装嫁妆的箱子最是适宜。这种含蓄的示意与家常的实在,也如贤女子般款曲可人。而前人与自然万物这种生息相倚的状态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可贵的智慧!
喀什风物
据说“没到过喀什,等于没到过新疆”,所以我们去南疆的第一个地点,就是喀什市。到了喀什市也就顺理成章地去了说是“没有买不到的货,没有吃不到的新疆小吃”的喀什大巴扎(市集),巴扎里沿街摆卖着各色新疆特产,有雕刻、乐器、洗壶等独具民族特色的货件,有当街摆卖的新鲜羊肉,现场烤制的大如蒲团的馕饼。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不知能作何用选的小物件。比如一个商铺的门口挂着一大摞烟斗状的小木器,大家站在那里七嘴八舌地猜那是什么东西,铺主看我们猜的起劲,就说谁猜中了就奖给谁一个,这下大家更来劲了,有说是烟斗的;也有说是吹泡泡用的;还有说是喝酒的工具,硬是没有一个能猜中,最后还是铺主揭开了谜底,原来那是给小女婴把尿用的,于是大家嘻嘻哈哈地玩笑着把奖品奖给刚才说用于喝酒的同伴,说是物尽其用、饮之不竭。像这样可有可无的小物件,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属于本地区的民间智慧,让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殖与日常生活更为便利。
这七月底太阳热辣辣直射的季节,南方正是短裤背心美女大行其道的时候,喀什的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却是把身体和头脸遮盖得严严实实的女人。按照清真教旧俗,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不能被外面的人看到,有的女人干脆就裹一身长袍,头上用一条大盖头一罩了之,只不过她们用的不是新娘的那种红盖头,而5wXvf7zAZKtgteqNB8z3SQ==是或黑或灰的更大布块,布的密度比较疏松,让她们能够透过布帘看世界,这样既挡住了别人的眼光,也挡住了阳光和灰尘,窃想,她们倒是省了南方女人出街打阳伞的麻烦呵。据陪同的当地朋友吐尔洪江说,很多女人(比如他那当医生的妻子)早已不再这样着装了,露胳膊露腿的连衣裙早已是常装。其实现在新疆的开放程度已经很高,怎样的装束都没问题,只要自己心里觉得妥当就行了。当然,如果到了一些宗教场所,还是遵例为好,互相尊重是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
巴什旁边就是世界四大清真寺之一的艾提尕尔大寺。以明黄色为主色,白线勾边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坐落于喀什市的艾提尕尔广场西侧,占地25.22亩,是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由寺门塔楼、庭园、经堂和礼拜殿四大部分组成。进礼拜殿的路口有一个小屋,专门提供统一的披巾(说是披巾,其实就是一块很粗糙的青褐色长方形布块),给女人们用于遮盖裸露的手臂,虽然我和同伴们都很不喜欢这灰头土脸的披巾,但述是尊重宗教习俗,一一披上。出来时把围巾归还时有个小插曲,一位朋友顾着和同伴说话,忘了把围巾归还,管理的大叔满脸愠色地斥责起她来,同伴赶忙把披巾归还,并向他致歉。后来大家说起这事时都觉得挺好玩的,这位大叔也未免太紧张了,也许在他眼里披巾也是圣物,是大寺的一部分,只因为过于执真了,故显得有点不近人情。
在未到新疆之前,对这个遥远的地方就已心向往之,并写过关于香妃的一组诗,传说香妃“玉容未近,芳香袭人,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别有一种奇芳异馥,沁人心脾”。于是我把香妃与新疆知名的薰衣草结合在一起,让美丽的传说与景象通过想象联结在一起。香妃墓坐落在喀什市东郊5千米的浩罕村,据说墓内葬有她同一家族的五代72人。第一代是伊斯兰著名传教士玉索甫霍加。主墓室外墙和层顶用彩色琉璃砖(也即我们俗称的马赛克)贴面,并夹杂一些绘有各色图案和花纹的黄色或蓝色瓷砖,但因为现在己没有制这种砖的工艺,所以一些因年久而剥落的部分,只能由它裸露着。陵墓厅堂高大宽敞,项上不见有横梁,是一个巧妙的借力结构建筑,平台上排列着坟丘,丘上覆盖着彩色绸缎。其实史上“香妃”确有其人,与发动“大小霍加之乱”的波罗尼都兄弟是堂兄妹,是玉素甫霍加的长子阿帕克霍加的重侄孙女,不过据考证,这里只是香妃的衣冠冢,而她是否真的通体生香便无从考证了。但对于美丽的事物,人们总是愿意附加上美好的传说,使之更为动人。主墓室外有成片的花田,玫瑰花正在其中盛开,仿佛香妃的香气依然在此间缭绕不绝。
在喀什老城区,我们穿梭在窄小的巷道里,不时拐进一家家既是住户又是商户的居民家里,淘一些古旧的小物件和各种美丽的纱巾。一路上,我发觉维族的小女孩都长得特别水灵可爱,其中有一个路遇的小女孩,在我们的围观,赞叹声和她妈妈的指引下摆着各种舞姿和天真的表情,惹得大家的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心想,在这个地方出现香妃这样的美人也不足为奇了。
生活阅历的心灵档案
人们往往在做了某些错事之后,悔恨地说:“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不会做了。”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早知道”呢?电影《恐怖游轮》里的杰西就因为独自抚养有孤独症的孩子,生活压力太大,总是为一些小事打骂儿子,乃至于在焦躁中造成车祸,与儿子双双丧命。杰西的灵魂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一心想恢复失去的爱,弥补自己曾经带给儿子的伤害。因而一再选择进入三维时空的残酷循环中,一次次地陷入同样的轮回中,唯一支撑着她走下去的是她对儿子那绝望的爱。虽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艺术的力量就在于它能给我们以各种各样的启迪,在生活中,我们也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像杰西一样产生焦虑,也不乏无意之中伤害亲人的的实例。我们不能拥有先知的预感能力,但我们还是可以尽量避免的,我甚至认为,如果杰西有写日记的习惯,她将会在记录的过程中反思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给心程立下路标”,生活的辛酸便不至于会蒙蔽她的心灵。
之所以会联想起这部电影和里面的杰西,皆因读了杜朗朗的日记体诗歌集《倾听花开的祝福》,诗集的独特之处是作者在每一首诗的后面都做了自注,把触发诗意的来由和生活线索贯穿于其中,有家史的性质也有为心灵立档的意味。他的诗歌有比较分明的两条线,一是情义:从乡村到城市;从乡情到亲情;从分离到聚合:无不记录着他与故乡、父母、姊妹、妻儿的浓浓深情。比如《等车时的一场竞赛》对母亲熨贴的怀想:《写给贝贝》系列则真切地洋溢着为父的欢愉与爱怜;还有写给妻子的《当你在心程立下路标》等对爱人的疼惜之情。二是励志:从立志改变命运到奋斗拼搏;从遭遇磨难到坚定志向。“坚持使命在上命运在下/坚持青春在左奋斗在右”(《我并不拒绝生活的困苦》)他在诗写中反思,在反思中领悟,从而在生活中更坚定地前进。从杜朗朗的心灵档案和他的生活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诗写能使我们在感知事物中柔软,在追溯过去中汲取生存的力量,在观照世事中解除自身的极限,并从而超越困难。思想上的活跃往往有助于生活上的淡定,“给心程立下路标”,是为了留下心灵颤动的痕迹,也是为了更稳妥地前行,所以,我固执地一再想到杰西的悲哀,如果她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哪怕只是记录一下自己和孩子的日常事务,也许生活的乐趣就来到了她的面前。同时,杜朗朗的诗也让我们看到——珍惜现有的一切,生活的路会走得更加踏实。
杜朗朗诗写的指导思想,也即审美理性是:“以记日记的思路写诗,写下生活、情感、处世的点点滴滴,记录真实的情形,抒发真实的情感。”故即便在他结集后陆续抒写的其他诗歌中,也都具有相同的品性。这种注重真实记录的方式使他的诗歌呈现了“真诚”的高贵品质,但同时也难免因为侧重“建档”这种求实的写作意图而轻慢了“技艺”的元素,忽略了诗是语言的艺术。诗歌不同于报告文学,如果过于注重真实过程的描画,而不注重凝练与留白,则会使本来可以浓郁饱满的诗意被过多的文字罗列所稀释。在我们将心中的诗意付诸文本的时候,不妨想一想,是否还存在另一种或另几种的表达方式,可以在准确表达了主题的情况下,使文本更趋于“诗”这种体裁所应有的简洁和饱满,而不致于读到最后倒是涉了诗气,可惜了一个好题材和心中的诗意。我认为,艺术评论的最佳状态是能通过作品的桥粱使作者与评者之间达成一种创作交流,起到互为触发、促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