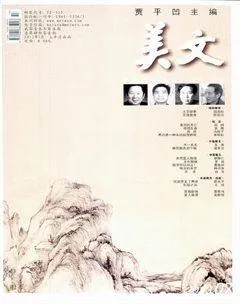炕是诱人老死的饵
2013-12-29葛水平
炕是诱人老死的饵
窑洞,最美好的地儿是炕。多少年之后,我居然在单元楼里盘了炕,青砖勾缝,榆木炕沿,炕心里铺了羊毛毡,炕桌上放了我收藏的油灯。傍晚,天光暗了,我说不出此时到底藏着什么打湿心灵的东西,它们冒出来,诱使我把灯树上的蜡烛点燃,心旌神摇那一瞬,我盘腿坐在炕上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万事万物诸多情谊都有怀恋,只要懂得,都是贵重。
我落地在炕上。
生我的那一年,妈妈在碾跟前簸谷子,突然的肚子疼,她的婆婆说,快,上炕。
我的出生没有异象。
十月份,青草繁茂。正午的日头照亮了接生婆的小脚,进进出出,紧束的围裙如同克制的欲望,没有多余的背景,炕,一张席片,妈妈扎着马步,我的出生,妈妈用了一个很可恶的词:红蛐蛐地跌下来了(大约指那种鼠科、猫科动物的初生)。妈妈说,百日后,你脱出来,白了,我才知道疼你。
一年后父母离异,万事过去皆与我无关。
三岁上,继父来相亲。妈妈坐在姥姥家的门墩上,抱着我,我坐在她的一条腿上,另一条腿则搭在门槛上不让他进门。继父无聊,站着端详了妈妈半天,妈妈手里掰着一只秋桃子,一点一点送进我的小嘴里,我像小驴一样惊异地看着继父错愕着嘴片,有口水流下来,继父扔过来一卷很糙的卫生纸。那时候乡下人没见过这么薄透的纸,妈妈抬眼看了他一眼,搭在门槛上的腿缩回来,继父进门。
我随妈妈嫁人时三岁。
山神凹,那时候,院子里有两颗枣树,秋天枣儿红了。驴拴在枣树下,我和妈妈下驴,进窑,上炕。炕桌上放着一碗红糖水,窑洞里的小奶奶四颗镂空金牙露出来,好奇地看着妈妈和窝在怀里的我,大概我与妈妈都很生动引人。山神凹的女人们从窑门上挤进来,空气如水流动。有人说:“小闺女好看。”窑洞里的小奶奶说:“是我成土的闺女。”(我父亲的名字叫成土)
都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翻过一座山头我成了葛家闺女。
因为小爷没有儿子,小奶奶又大小爷十几岁错过了生育年龄,我祖父又被扩军南下生死不明,这样我继父就等于过继在我小爷名下。小爷的窑洞里有两盘炕,互相对应着。两领羊毛黑毡,白天时铺盖是卷着的,夜晚,卷着的铺盖展开来。窑墙上还挖了洞,洞很小,像一眼小窑洞。放了细粮,比如麦子、豆,都用一斗缸装。那年月,因为是集体,农民改叫社员。秋后分粮,人均口粮,麦子也就只能分十几斤,都不舍得吃留着过年。粮食是有味道的,不单单是一个香字。一个冬天里,窑洞里最活跃的是老鼠。闻香而来。小爷不叫它老鼠,叫它老君爷。窑内中堂前的方桌腿上敬奉有老君爷的牌位。黑是老鼠最喜欢的颜色,四只爪子细脚伶仃,夜里走路收收缩缩,不显山水。窑炕盘在进门处,临门有窗,窗户最下一格有猫出入,常常不糊窗户纸,用钉子钉一帘花布由猫出入。
有一段时间老鼠成灾,小爷下了许多鼠药,猫吃了药死的老鼠大都死了。灾难降临的时候,真是平分秋色啊。这下,老鼠的孙子们欢喜死了。窑梁上挂了玉米,五更天,老鼠开始夜生活。它们叽嘛乱叫着,有从梁上掉下来的,放肆的大笑声扰得炕上人无来由要学几声猫叫吓唬老鼠。小有停顿,老鼠想:人呐,也仅仅扮演了一个岁月喑哑的歌者。
六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炕上午睡,看见一只老鼠从地锅前爬上炕,小眼睛贼溜溜儿顺着炕沿越过我走到我的脚头,我抬起头轻声叫了一声:“哎!”它停顿了一下,身躯稍向后仰了仰,似在微微着力,想回头,那神态,慵懒到不慌不忙。时间慢下来,我指望它能回头,接下来它还是稍息一下走了。它爬上窗台钻出猫洞,我很伤感。屋外的蝉,浑圆而饱满地叫着,我坐在炕上,一副伤身伤世的样子。小奶奶在对面炕上剪鞋样,看着我失落的小样从花肚兜里摸出一块糖递给我,迢递的安宁,窑外,蝉声一声接一声落下来,我跳下炕走出窑,等那细脚伶仃的“它”回来。

有一种纹理,它沿着成长的肌肤深深嵌进来,我对家的概念,是一进门不由分说地陷进炕上。任何一种光影的闪现都不能去除我对炕的怀恋。炕和祖先一样功德无量。祖先的功德是繁衍子孙,没有祖先也就没有后人。炕上生育,炕下生活。什么样的时代,便有什么样的艺术,只有睡过炕的人才知道炕的好处。乡间窑洞里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沙发,炕是人们生活的舞台,进窑的人说话吃饭都坐在炕上,一铺炕有时候能放下七八个人。记忆中炕上铺羊毛毡,每到冬天,小爷都要剪羊毛擀毡。擀毡的主要工具是弹杖和一床木帘。弹杖用来反复均匀羊毛,如弹棉花的棉花客,弹杖被拉扯得“嗡嗡嗡”响,好听极了。擀毡需要豆面,豆面有黏性,羊毛和豆面掺和在一起,怕虫蛀常要熬一些花椒水搅拌在一起。木帘用来铺平羊毛,而主要的工序全是脚踩手揉。擀一领毡要用去两个汉子三天时间,擀毡的日子里,窑洞里的气氛显得温情脉脉,很多很多的细节都极其可爱,比如,小奶奶会因小爷一手一脚羊毛喂小爷饭吃,一口饭一口菜地夹在小爷嘴边,小爷那细嚼慢咽的样子极是滑稽。
铺了毡的炕,夏天隔潮,冬天保暖。因小爷是放羊的羊倌,近水楼台,窑炕上常铺两领毡,厚一些毛质不好的贴着席片铺,上面的毡是绵羊毛,坐上去要柔软许多。炕都是火炕,与脚地上的地灶相连接,烧火做饭时烟就从炕下面的炕洞子通过,饭熟时炕就热了。有时候冬天里仅靠烧火做饭把炕烧热还不行,还要在炕洞子里烧柴。夜晚的炕头下因是炕洞热度要高一些,炕梢不及炕头热。晚上睡觉时我早早躺在炕头,不愿意睡炕梢。
窑炕靠墙的一面画炕腰围子,沁水人叫“炕腰围子”,也有叫“炕墙画”。会画炕腰围子的油匠在乡间很吃香,谁家没有两铺炕呢。炕腰围子的造型艺术形式,是壁画、建筑彩绘、年画的复合体。躺在炕上脸朝炕墙,看那月光下的美好,常常会觉得自己要融化进去了,整个夜晚的世界会在入睡前忘记贫穷。光说炕腰围子画的边道就很有讲究,常用的有:退色边、玉带边、竹节边、边棠边、冰竹梅边、卷书边、万字边、狮子滚绣球边、富贵不断头边、暗八仙边(八仙手持的道具)、鹤寿边(白鹤与各种寿字)、福寿边(佛手与桃或蝙蝠与寿字)、金玉满堂边(金鱼加水草水纹)等等,可谓是百色百样、美不胜收。每套炕围画边道的繁简多寡不尽相同。同边道相配的还有几种适合形图案纹样,画在画空两旁的为“卡头”;设在第二组边道下面角隅处的称作“角云子”,这些图案都是“细炕围”的附加装饰,乡间有钱人才要如此讲究。小爷家的炕墙上只简简单单地画边道,内里几朵富贵牡丹。
小时候出山到外村常去看大户人家的炕腰围子,常见的有历史典故“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太公垂钓”“苏武牧羊”等。也有戏曲故事“莺莺听琴”、“貂蝉拜月”等。各种“选段”的集锦式“会串”在炕墙上,一路看过来,比较历史典故我更喜欢戏剧故事,“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幽幽怨怨似乎更适合生殖的热炕。“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炕上的岁月是一个家族的红火,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故事,早已因为千万遍的重复变为我们自己的故事。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炕,看似一副落魄遗老的架势,可对于它的欢喜,永远都有旺盛的生命精力。
炕上除了蒲扇、苍蝇拍、烟袋、捻线陀以及凌乱的糖纸,也只剩下了我的小爷、小奶奶的从前。而今,扑簌簌往下跌土的墙上,曾经的炕腰围子画和贴着的挂历画,因了窑顶的塌落已经斑驳得模糊不清,所有的岁月为什么都是一闪而过呢?隐隐没没的日子过后,我再也睡不回欢喜的从前。
家里的乡下男人
一直感觉在某一个黄昏或上午,父亲会背着一个帆布行囊远足而来,会用他憨厚的影子堵住我正门的光线,那时有一个很不能概括的念想:“我们家的乡下男人进城来了。”
我忍不住遥想当时形貌,居然有那么几分近而远的缘由,但我明白,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是永远住在乡下了。
每年的清明这一天,无论刮风下雨,我都要回乡上坟。说是坟,其实只是一眼废弃的窑洞,在山神凹后山的黄土崖下,十年了,父亲很安分地在等活着的我妈,而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多么捣蛋的人。老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夫妻一场先走的人一定要放在一个地方等在世的、留在红尘中的那个人百年后一起入土为安。
春天的植被像世界地图一般,散淡地铺设在崖的周围,崖下的土窑内是父亲的家,阳光直截了当地照进洞内,那一口玫瑰红的棺木横放着,我们家里的乡下男人被装殓在里面平躺着,成为一个戛然而止、无法再继续坐起来或站起来的存在。无往而不胜的岁月呀,好端端把一个人一生的里程,减缩在了这个大匣子里。我跪卧在地上,点燃一堆亿万元冥票,有风丝绒般吹来,那灰烬很是舞蹈一番。这种无告的陌生竟伴着我那么多绝望和酸辛,但我却无意怨恨它,反想到有一双厚实的黑手在抖擞着收取女儿送他的这一份殷实的家资。
人生真是一个过程。我是一九六九年认识父亲的,在这之前父亲的绰号叫:“跑毛蛋”(沁水县十里镇方言,意指对生活不负责的人)。在这之后,我三岁,随母亲改嫁而来。母亲嫁时骑小黑驴款款地从田畦的小路蜿蜒而来,给满世界秋阳注一剂斑驳。父亲的兴致随驴屁股的一声疼痛而“得得”高昂,母亲的笑便暧昧得意味深长了。而一路的累乏,让我懒得兴致,也就是说,三岁的我还记不得多少当年的往事。父亲的家是一眼土窑,墙上的许多洞和地上的许多洞是老鼠的家。父亲后来用许多玉米芯塞住了那些洞,那些老鼠很是无奈地和人一样光明地在窑洞里生活了几年。这期间,父亲到太原的西山煤矿,为了像个男人一样活着养家,决定下坑。人称下窑汉。我妈嫁过来不久,因井下塌方,俗世的父亲脑袋冒出泥地的一刹那间,决定逃生,黑炭一样逃回老家,前后走了不到一个月,我妈开始和父亲生气。
这气,一生就是一辈子。我记得我生孩子时回老家坐月子,妈和爸吵,吵得我大声喊:“离婚吧。”片刻后父亲嬉皮笑脸说:“还不到离婚那步。”我说:“爸,你怎么在这家里熬的?”父亲想了想说:“你知道啥,我在你妈跟前还没有小学毕业,还得熬。”
这里我不得不说我的爷爷,爷爷是被远一些年扩军扩走的土八路,后来得益战争的最后胜利,身份转成了南下干部。正遇荒年,失去音信的奶奶无法养活父亲,作为对丈夫的报复心里,想把父亲丢在山里让狼吃。是小爷从山里找回父亲的。父亲的一生便是依靠几位叔伯爷爷的呵护成长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父亲因山性而长成“三不管”式的人物,即:小队管不住,大队管不了,公社够不上管。
父亲的家就是我后来的家。我的老家叫山神凹。这个名字需让我反复记起,它不仅是我父辈生存的地方,而且在抗战年代,是八路军的一个地下印刷厂。我的家族本不姓“葛”,从祖坟的墓碑上刻的姓氏看是姓“盖”。姓氏的过程也得怨我爷爷。当时大字不识一斗的爷爷被扩军扩走时,有军人问,你们家姓甚?爷爷很光荣地喊姓“盖”(盖姓念葛)。那军人说,知道,姓“葛”。用毛笔工整写下。一个“知道”断了盖姓家族的香火,从此“葛”姓在山西十里镇山神凹广延。这大体可信,族人淳厚,还不大懂得“冒”姓。
老家没什么风景,有山。有人住的和羊住的窑。羊住的窑比人住的窑大,因羊多而人少。羊多,族人便穿生羊毛裤,生羊毛衣。父亲因此而会织毛衣。逢年过节家穷买不起鞭炮,父亲领人到山和山的对顶上甩鞭,用牛皮辫的长鞭,长鞭一甩,因山大人少,回声也大,脆生生漫过村庄直铺天边。天边并不能看真,生生地,凝成千百年一气,鞭声滚滚滔滔跌宕过来,山里人激动得出窑,听父亲隐隐然鞭笞天宇的响彻,能把人的心吞得干干净净。这种甩鞭和赛鞭过程,要延续过正月十五,十五过后老家的山上没什么内容,赤条条地与荒漠的群山对峙。荒山沟里,父亲开始了他生长期的旺盛。
父亲是一个高智商的人(用现代的话说)。他不太懂音乐,夏天打一条蛇,从马尾上剪一缕马尾,再从大队的仓库里偷一段竹节,三鼓捣,二鼓捣,一把二胡从他手上就流出了音乐。父亲不懂宫、商、角、徵、羽,更别说现在1、2、3了。窑中一盏豆油灯,父亲擦一把脸,憨厚地笑一下,挽起袖管,从窑墙上拿下二胡,里外弦一“扯”,就这过程已有人对父亲手头这把民族乐器投来歆羡的目光。而真正的艺术,在父亲的手上,还没有扯开弓拉出声响。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不是那种龙飞凤舞的,一溜儿正楷。父亲的出名好像不仅是这些,从小掏鸟蛋,大一点抓蛇,再大一点摸鳖。他一上午能摸一木桶鳖,用铁锅煮了让光棍汉们一起吃。他说,现在人吃鳖,大补,狗屁!我吃一辈子鳖,把十里河的鳖快吃完了,也没补出名堂。十里河的鳖从父亲开始吃后,渐少,与父亲摸鳖关系重大。父亲玩蛇能把蛇玩出神话,让它走它才敢走。玩过的蛇,父亲从不打死。我至今不清楚这种吐纳百毒的长虫,为什么在父亲手里如此服帖?那个年代,父亲的故事频繁。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强悍与苦难汇合让父亲野出了风格。我妈常说:“早知道你这样,我嫁给好人家也不来你这沟里。”父亲总是看着我和我妈说:“你带着驮油瓶上哪儿嫁好人家?来沟里就算你享福了。”
其实,父亲身上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他的诚恳和逼真和来自大自然野性的浪漫。父亲多半不会在痛苦面前洒泪悲叹,寻死觅活。他的思想散漫得很阔,人生道路也铺展得很广。他像《水浒》里的一百单“九”将,该出手时比谁都出手快。路见不平,拳脚相助。在他五十五岁时,三十岁的我还陪他到几十里之外的沁水县柿庄乡派出所交打架罚款。父亲在中年以后把兴趣逐步改向狩猎和打鱼。记得有一年夏天黄昏,父亲不知从哪里偷来“夜壶”,趁天黑装了炸药。五更天叫我快起床,领着我骑嘉陵摩托车翻山到另一个县。一路风驰电掣后,摩托停在山脚下。我和父亲潜入就近村庄的鱼塘。见他点了雷管使了老劲抡圆了把夜壶扔进鱼池,接着冲天一声响,我看到“哗啦”一声,鱼塘掀翻了。等水花落下,鱼翻着肚皮漂满了水面。我吓坏了,父亲却高兴得喊:“发财了。”忙活着张开渔网准备要打捞了,村里的叫喊声朝着这边鱼塘来了。父亲来不及打捞拉着我的手抬脚就跑。我不敢往后看,大口喘着气,跑到摩托车跟前说不上话来,喘气声把喉咙都拉伤了。
父亲于1996年得病,那年的正月初九,父亲从乡下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怕是病来了,来得不轻。一贯孩子似的作风,让我忽视了他非常时期的实际。我又以非常含糊的感觉很自然等到正月十一。那天回乡后,我看到父亲在麻将桌子上鏖战,胸口上冲着桌沿顶着一根木头,止胃疼。我想哭。我要父亲走。他坚决不走。说要把四圈打完。从父亲的态度上,我知道他输钱了。在乡人劝说下,父亲很是不情愿地离开了麻将桌。
回到城里,一连串的检查,证明父亲是胃癌,晚期。
我说不出一句话,一句话也说不出;父亲吃不下一口饭,一口饭也吃不下,我知道,父亲气数尽了。我告诉他是胃癌,晚期。父亲难过了一下便笑了,说:“我说嘛,不吃一口饭,雷锋还讲,人不吃饭不行,就不吃饭不行,一辈子就算完了。”我说:“以后怎么打算?”父亲说:“打算什么?父死之后见人磕头。”我说:“就女儿一人,怕忙不过来,想将来火化了。”父亲不语。三天后父亲说:“水,千好万好烧了爸爸就不好。你想想,我走了,活人的嘴脸要骂你,骂你把爸烧了,你愿意不落好名声?”父亲讲此话时一脸坏笑。
我是三月初三开车送父亲回老家的。沿途我买好了木板,回老家后叫了木匠赶做了棺材。我在做好的棺材里躺下试了试身长。我站在父亲身边不语,父亲说:“有话要说?”我告父亲:“大小正好。”父亲说:“躺下试了?”我说:“试了。”父亲说:“把它漆成红色。”我在寿棺大头写了“寿”字。因我字写得不好,远看近看都像个草书“春”。我和父亲说:“坏事了,把“寿”字写成‘春’了。”父亲说:“还寿什么?你爸的寿已尽了。春就春,春天生,春天终。”因父亲生于1937年四月十五。
父亲说:“死后把我放置在一个干燥的窑内,等你妈百年后一起下葬。死后多烧点冥钱,才学着打麻将,老输,那边的钱在这边可便宜买到。你写文章的人,爸爸知道你辛苦,对我这件事你千万别太寒酸,寒酸了叫那边的人笑话你写文章供不起你爸打麻将。那可就不是笑话我啊。”我哭着说:“爸,怎么两边都是笑话我呀?”
爸说:“闺女呀,我死了呀。”
1996年三月初十晚,父亲拉着我的手说:“闺女,我来世做牛做马报你对我的恩情。”
我说:“爸,来生我们做亲父女。”
父亲哭不出来,从鼻孔流出一丝清鼻涕,眼睛死死盯着我:“近跟前来,跟你说句悄悄话儿。”我近到他嘴跟前,他小声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存款都贡献出来,给爸找点不死的药?”
我闪开了哭着说:“爸,钱买不来命,毛主席都死了。”
父亲半天后说:“瞅你那哭相,难看死了。我是试探你对我有多好。我能不知道,和毛主席比我不敌人家小拇指盖大。”
我不语。泪像河一样。三月十一早8时10分,我看到父亲长出了一口气,又长出了一口,没回气,父亲的眼睛就闭上了。
农历三月十三日,我把父亲放置在山神凹后的羊窑内。我告慰父亲,窑内放得下十桌麻将。我给父亲烧了四麻袋张张是亿元的纸钱。活着时,我曾和父亲说,无论那边怎样情形,都要托梦给我,我好给你打点打点。
至今梦中出现的还没有父亲的影子。
父亲,你会在午后的暖阳下斜靠在我门扉前欣悦地凝视我吗?你这如此野性的城里上班的乡下男人,你现在躲在老家哪座山褶子里贪玩?
驴是兄弟
从什么时候开始,故乡的驴对于我来说,就已演变成为我童年的兄弟姐妹,一些难以忘怀的季节的冷暖景致,一些远离文明的诗意的原始,而不再是一般的劳动工具的浅表印象?真是这样,庄稼人知道,人与牲畜的缠绊比提起的话题更牢更长更雨露阳光时,人才会接近人模样。乡间的土窑,小石门洞的暖炕和窑掌深处的驴,没有人能够明白,人与驴同住一窑的风景。祖父说,驴是兄弟,它不会背人的视线而走向不归,蹄脚老了就凭借风力。印象中的风景,都被驴走尽了,遥远而又凝固,仿佛暖阳下的苍山,只在自己的故园,只在窑洞。
这是一个充满遗憾的世界,用什么来抵御岁月的风霜?牲畜成为庄稼人一种安详的皈依。童年时随祖父骑驴出山放羊。寂静的午后,胯下的驴踏起阳光下的尘土,羊群在温暖睡意中被镀上了簿金,空气中山林的气味浓得像是液态。松树的针叶从脸上抚过,会看见腐殖的泥土透出的松菇,朗晴的,满目皆是圆润的黄。这时的羊群如果无知或故意分群,山下的驴会仰起后腿,颐指气使,蹄声归处。分群的羊会在这“嗒嗒”声中安然复群,这是动物间一种奇怪的默契。祖父回头笑骂:“狗日的驴!”然后勒细嗓子唱:“皇天后土人儿黄尘小,苍山绿水牲儿浮萍大……”那声音荡起天地一片瑞祥。
庄稼人知道,生命耗尽本能才会存活。存活的幸福和好天气一样,有,但不会很多。天地之间,风霜雨雪,人类彼此生存及农业耕种的开始,就意味着一切的到来。人养了牲畜作为农耕劳力,是人类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功利主义,也是出于那些生命的善良和驯服。牛羊追水草,人子逐牛羊,迤逦一途。生命同等于四季,是牲畜使人类浪游的脚步停下来,并根植出了乐土息壤。
还记得冬日里和祖父一起出山驮煤。天近黄昏,雪片飞扬。雪天里直程的背阴路因寒风吹滞,滑溜狭窄,驴鞍头挂辔,笼嘴系缰,走,打滑,一人牵,一人打,生命延续彼此交困。驴处险,将后蹄牢牢把住雪地,前蹄实质上已经因滑弋而虚拟。祖父身体抽抖,注力于双脚,贴附于路边山坎,只用眼睛看驴。祖父说:“水,快脱去我的鞋袜。”天寒地冻,祖父赤脚着地,趾肚脚掌似乎有牙,冒出丝丝白气。祖父屏气不敢大声呼吸,使出“驴”劲,生凉的地气能把人的骨缝扎透。那真个是一幅人类艰辛的生存之图,先是蕴含着无尽的力,之后就是心头的一线明悟——是人类存活的永远经典。
踩过的雪地留下一汪清水。生命的庞大与卑微,是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呢?走上山顶,看见村庄的窑洞,满世界苍凉的白。雪中炭,人与驴如水墨画上甩出的斑点墨迹,祖母在窑顶上眺望山头,晃着一根桃木棍子,我在雪天的驴背上疯喊着祖母,那声音显得那么渺小和孤独,且透射着俗世的暖意。
祖父说,老驴灵性,工于识途、警路、避险。在没有路延伸的崖壁前,人若强行,驴也会气恼人的愚昧,歪着脖子,两腿夹尾,回避崖塌泥陷。驴作乘骑不欺生,一根桑条握手,通过骑乘重量的分流变化即会右行或左转。记得一年春上祖父牵驴出山跳马。腊月里驴生驴骡。叫驴跳马,牡马所生为马骡,儿马跳驴,牡驴所生为驴骡。老驴体弱无乳,祖父让我去和叔伯婶婶说,要她给小驹一口奶吃。月子里丧子的婶婶羞红了脸走进窑洞,祖父避羞走出窑洞,婶婶解了衣扣,托乳相赠,小驹受惊惧退缩。无奈叫了叔叔来,叔叔气盛,从老驴身上揪下一把驴毛,缠在婶婶乳头上。时是黄昏,可以清晰地听到小驹吸乳之声,那是生命繁衍的本源之声。年轻的婶婶,肌肤透亮,在黄昏的天青下流溢出丝绸般的光泽。婶婶有泪流下,那是失子的疼痛中艰难赎回的幸福。多少日子,她就这样在悲伤的边缘上喂养了小驹。生命的等级超越了,那苍苍深山中血脉里流淌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款款情深啊,很亲切,很亲切。
庄稼人给予牲畜的爱,也许可以用无私的母亲来比喻,但我认为它远远超出了母亲的狭义。大自然所具的那种永恒、自在、单纯、朴素的性格,培植出了庄稼人的良善。山高水长,由于自然的素朴,庄稼人的爱,就如山中日月,明澈而高洁。
眼下,驴突然少了,我沿着沁河走,温情如故,友情如故,再孤寂的心也会为两岸的村庄动容,为什么河沟里没有驴?门前的树上没有拴着驴?驴不是朝三暮四的动物,它本色,涵纳很深的教养,以及对人的依赖和安全感,只要一根缰绳在手,它永不会厚此薄彼。一路走来,我真的没有看到驴。乡间有两种动物,一种是人,一种是驴:家畜。人占据了大地和天空的两个世界,人是能牵制和使用家畜的高级动物,人放弃什么都不能放弃家畜。放弃便意味着将要背井离乡。
从前的正月,我还记得胸前糊着驴头的小媳妇在公社的广场上闹十五,广场是一块并不太宽敞的坪地,前来闹正月的人们席地而坐。那几头人扮的驴蹦跳着穿越人群,来自这“几头”驴的热烈的民间声音让坐着的人跳起来,笑声烂漫如即将到来的春天,鲜活得叫人想着世界会永远繁花似锦。驴让我对往昔那些个真实的日子怀想和凭吊,我的目光在追寻它的同时,我看到丰收的田野上缺少了驴的身影,怎么都觉得少了幸福的指向。
有一天,我心情郁悒,从书架上乱翻一通,抽出一本杂书,看到有人写汉时,驴曾是贵族宠物,人人皆学驴鸣,驴叫声成为一天里最好的将息。写魏帝别出心裁,给臣下王仲宣送葬时,令官员一人各作一声驴鸣,送王西行。山野旷地驴鸣声此起彼伏,实为空前壮观。驴生活在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是多么的旷达和动人。
风霜雨雪在时间中潜隐地流过,驴走到现在“上下山谷”已成为“野人所用耳”。人类的苦难早已浸涉了爱的双臂,驴的体力已被岁月咬噬得骨瘦嶙峋。假如以最早出现生命的形式来想,人与驴也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自然选择进化出来的东西。每每想到故乡的驴,就会想到驴的眼睛,直戳戳的,一切悲怆意味全在温柔里。岸边风景,怡悦心性,或引颈长鸣,人与畜,畜与人,是否有悖于生命后来的事实?
驴在远离人类喧嚣的田野里耕作,随缘放达。有农人在地垄上用火镰敲出一缕烟尘,春山鸟鸣,我在追忆极苦极甜的缠络中,想神闲气定的乡村,想生活羁绊中愚冥孤独的驴,心,就会滋生出一腔生生的痛,上帝有意设置了这样一种未来,我们只能告别和放弃所有意义上诗意的原始了。
黄昏的内窑
黄昏的风景是斑驳的。黄土地上的人生,是亲情的乳汁酿造的。尤其是在这内窑8/Tn7MVOx7FG8eAf2ID8SAvC2IaqXTscc5kG+XoiV/w=。
祖母是王月娥。尽管王月娥已在这个世界上走得很远,但是在我生命中,岁月如此辗转盘桓,光阴如此流逝嬗变,都无法更改王月娥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可是这么多年来,曾经在那一方土地生长的人却没有人不知道祖母。老辈人叫“老葛家里的”,晚辈人叫“内窑婶”,次晚辈人叫“奶”。这叫法的统一点就是指王月娥。
二十六岁上,二十岁的祖父葛启顺被扩军南下,王月娥就守了一眼土窑,眼睁睁活了七十,四十四年间,苦守寒窑。曾经有人力劝王月娥改嫁他乡,但终是苦心枉费。那种形势上的安抚又岂能均衡王月娥内心的失落……
开头儿,夜静的时候睡不着,王月娥坐起来想走时王必土的样子,自个儿傻笑,那都是光阴下的苦守寒窑啊!到后来,夜静的时候俯身像咬豆腐似的,咬自个的肉,疼得窒息了,夜却不动声色。再到后来,人上了年纪了,早早烧了炕团在炕上,听梁上的动静,一只老鼠倒挂在梁上,一窝老鼠在地上跑着耍闹,听着响儿反倒能睡个好觉。祖父一走再无音讯,天是到黑的时候黑了,到白的时候白了,黑白之间王月娥心里有个活物。
山神凹走出去回不来的人都有“光荣军属”的牌牌送回来,祖父没有。这就让祖母的眼神看上去像土窑窟窿里的老鼠一样,明亮而惊慌,令人陡生怜爱,却又怕人于一定距离之外。仲夏傍晚,王月娥穿了月白短袖布衫,双耳吊着滴水绿玉耳环,坐在内窑院的石板上走神。缕缕阳光透过枣树荫蓬的隙缝漏射下来,远远看去,神情恍惚的她就像一个无法企及的诱惑,甜蜜而又伤痛。男人的视觉在这时大体是相同的,二十岁与六十岁没有多大区别。葛姓本家族人暗恋上了侄子媳妇,终于在一个黄昏时分走进了内窑院,祖母发狠地喊了一声:“你坏良心呀,你欺负弱小,小走得没音讯,大做下这种下作事,一把秃锄头你锄地锄到自家人身上,你今儿等不得明儿你就要死呀!”事情到底因辈分的节制没有弄出大的举措。可时令已入三伏,满山的山丹丹在风中闪闪地耀出了大片嫣红。
难得王月娥年华如梦却能心静如水。她因传统而忠心于祖父,她因本分而体恤关心族人,从未滋生杂芜之念。内窑院的枣树蓬勃着朝气和骚动。青石铺就的石板地却浑然冷冷。这冷冷中就有了那么一丝微妙的季节性悸动。那恰是“文化大革命”的脚步踏踏来临之前。在接踵而来的大革命潮流中,大风席卷了中央之国的角角落落,红颜薄命之虞的王月娥竟也不能绕过。于是,在这场偶然与独特并存的浩劫中,历史执拗地切入主题。
曾经的王月娥是地主的小妾。荒山沟里的小地主既无万顷良田,也不敢为非作歹,最多娶一半房小妾。葛启顺当时是地主家里的短工,进进出出在不同季节里和王月娥有了仔细的照面。最长的一次照面是土改前夕。那一年熬豆腐,葛启顺来帮工。熬浆熬到了一定火候,葛启顺进房端浆水,问题就出在了葛启顺看见了冬日暖炕上王月娥雪白一片。屋外喊塌天了,屋内的倒骇异地看得出神入化了。那一年的豆腐据说因祖父的憨胆点老了,但也仅用二斗玉茭从地主家换回了王月娥。这就让王月娥在最为动荡的日子里受了一些委屈。
1966年,国家最权威的报纸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的目标是改造人的灵魂。山神凹虽处贫穷僻远的深山,而革命热潮则是“四海翻腾云水怒”。因为一些无法猜测的原因,一些乡村的红卫兵,把王月娥叫到请示台前定罪。红卫兵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抓挖社会主义墙根的典型。内窑院的,因历史问题,你就算一个。”王月娥说:“社会主义是甚,山高皇帝远,借了胆,我也不敢。”红卫兵说:“你仇视社会主义,你是反革命大破鞋!”王月娥抬起头神经质地断然否认:“不敢!”“哪敢!”红烈的阳光把王月娥晒得如妖儿一般,楚楚动人。王月娥想:我一生从没得罪过人,咋好端儿被人黑杀了,这世道真是要坏规矩了。
这世道本就没有一定之规,一定之形的,水把山开成石,把石揉成沙,云成风生意,水随地赋形,规矩是甚?野花绣地。王月娥在请示台前早晚汇报了半年有余,红卫兵开始了内乱弃她而去,与往日的岁月不同处是她接下来的日子活得生硬而苦涩。
岁月辗转中老了王月娥,不老的是她的记忆。鬓染银丝的王月娥翻出日伪时葛启顺一张泛黄的良民证,手微微颤抖了几下,然后又轻轻折起压在了箱底。尽管那照片已经退色又有许多深深折痕,但王月娥对他倾注的感情,却如石下清泉。
有一个春天,终于从公社乡邮员的手里接到了南方的信函,落款是:“内窑院启。”王月娥的名字都省略了。字里行间仅是对他年已半百的儿子的问候,只字未提王月娥。王月娥想:不管吧,儿是连心肉,只要葛启顺还活着,就有我王月娥的一天。
是等那归无定期的一天吗?
内窑院的枣树高大而繁茂,盘曲错纠的枝节伸向青冥的天空。王月娥拉着长长的麻绳把三寸长的鞋底纳得细密、匀实。灰蓝色的外罩把一头白发衬得如一幅水墨写意,看上去有一种与世隔绝的雅致。有晚辈惊异地说,内窑婶怕要成精了,七十岁还纳鞋底。王月娥抬头笑笑,用豁了牙的嘴捋捋绳子,一针一针纳得瓷实。
王月娥在等那被遗忘了的那一刻的到来。1980年,葛启顺老大归乡领着后娶夫人,走回了他离别了近半个世纪的故乡。美人迟暮与王月娥比起来就少了一些韵味。南方的小女人体态盈盈,一回北方就吵着要走,离心离肺的。择了吉日祖父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在走进内窑时,王月娥正靠着炕沿捻羊毛,就只刹那,王月娥抬起头时已是泪满双襟了。祖父说:“解放战争打完,我就在南方成家了。”王月娥含泪点头。祖父对那女人说:“该叫姐姐。”那女人说:“姐姐,用开脸帕把脸开开。”祖父说:“她要你用毛巾擦净眼泪。”祖母王月娥一脸悲啼。几十年了,擦不擦吧,擦来擦去都一样的痛。王月娥含着泪说:“成家了好,一个男人不成家,道理就说不过去。”祖父说:“你一个人能把日子活过来,要我怎么说好。”王月娥说:“没啥,眨眼就到现在了,到底是我守在山神凹,你在外,出门在外你不是闲人,你是为国家当兵打仗啊。”

王月娥在祖父远走他乡半月之后,终于倒在了内窑院的土炕上。王月娥说:“四十四年了,我找到了活水源头。”祖父临走时的话还在她耳内萦绕:“我死后把骨灰送来与你合葬。”一个活物,一句活话,是对内心深处埋藏的人生悲苦的生命祝福之念吗?还是姻缘变幻的不悔不忧!祖母等老死他乡的祖父再次回乡,她做了许多准备,有时候甚至嫌日子走得慢,日子把人的一辈子过完了,到死,总算要拼凑成人家了。她用祖父留给她的钱打了坟地,坟在隔河的山嘴上,朝阳。她要打坟的人留个口子,夜静的时候她把一些庄稼人用的物件放进去,锅啊、盆啊、缸啊的,大件的搬不动,她就像滚球似的滚着它走。有一天夜里,她滚着一口缸过河的时候,摔了一跤,骨折了,山神凹人才知道她在忙活地下的窑洞。下不了地,心急,人瘦得和相片似的,望着进来看她的人就说以前的祖父,人们也都跟着她的话头说以前的祖父。想来,祖父在她的记忆里被扩大了,稍动一点心思,面容就浮现不已。
春日和风使枣树抽枝开花,秋日萧飒使枣儿泛红透甜,一样的时空流变中,美丽的景致就这样保持了一生预约的守候。
王月娥,我的祖母。当我以一种过早到来的苍老的目光悲哀地看进了三十年时,三十年前活着的你——可知日月与你几近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