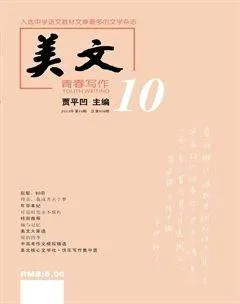路上的冬天
2013-12-29怀杉
2013年的冬天,背起行囊,一辆单车,在家乡周围享受着时光。
——题记
五年前的暖冬,通往燕窠硐的路上,曾找到一处不为游人所知的古镇,因为偏远,所以安宁。我竟不舍得去问这座小镇的名字,能躲开这世间飞短流长的搅扰,来到这青绿河畔,做上一段致意情暖的美梦,这背后必然孕育着一种孑然于世的心态。
记得小时候曾在课堂上学过一篇文章:《小镇的早晨》,童年的纯真与遐想总会将许多好奇久久隐藏,过些年再翻阅,不得不感叹这境遇的奇妙。
古镇走过了很多,似这样拥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恬淡的令人如饮一盏清茶的小镇,却还是头一次,它勾起了我对童年美好的回忆,多年前那个懵懂中有着猎奇心理的孩童终得以接近“课本”中的真实。
早晨人们行走在青石铺成的小路上,笑容在朝霞的陪衬下显得格外晴朗,吆喝声伴随着妇女们洗衣时的敲打声,柳絮下狗正贪婪地享受晨光的沐浴,河面一层层涟漪,氤氲的水雾揭开了一天的面纱。人说,当一个人品过了所有的茶,尝过了所有生活的味,就明白了茶的本身本没有好坏之分,如同生活的质地没有好坏之分一样,品者的心态决定着一切留在心底的感怀。我想,这里的人们便是如此,清茶相伴,乡情浓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从来只有金丝雀羡慕飞鸟的自由安然,却没有飞鸟羡慕金丝雀的锦衣玉食。我想,我既不是飞鸟,说是金丝雀倒也牵强了些,宁做这河畔的一株水草,与这小镇天长地久相依相伴。
几年后,再回到这座小镇,却发现,原来走在消逝中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宿命。
我悄然接受着命运的安排,终于明白,曾经小镇的幸福,来自于满足,他们不求永恒,只争朝夕……
很多人选择活在回忆里,却发现渐渐地忘却了自己。我选择在回忆里活在当下,那里的我没有风尘,没有面纱,那里的我足够真实,足够自由,这让当下的我多了一丝选择的可能。这样的“回忆里”是每走一个地方,就在心里留下一亩三分地,累了倦了往内求得栖息。
一
告别小镇,来到儿时曾走过的地方,一切似曾相识燕归来。
该有怎样的坚忍将一座海中岛屿守望成一道富丽而不失细腻的风景,又是怎样的力量吸引着五只本是远走天涯的白燕来此衔泥做窝?也许它们本就是希望飞到海角天涯,却发现这里有着足以停息的一切,它们不再奢求遥远,只因心安便是真正的世外桃源。从此它们望着这片别有洞天的众妙之门,乡自归故里,是停留的最后一站。
燕窠硐,熬煮着世态的安然。
很喜欢山中的这一诗句“神燕古巢真洞天,色颜垒卵却高眠。一山之水清无曲,赊尽风花不用钱”,这该是这样一位潇洒自然的红尘墨客所留下的?
千年前,吴越节度使林倪在吴越归宋后,辞官归隐,访遍名山,最终回乡在燕窠硐旁结庐学道,历史上很少有关于他的记载,当地村民却对此津津乐道。
在中国历史之中,但凡高洁之士,有多少是能够坦然接受亡国之恨,继续走着自己的仕途呢?也许这位节度使本就不喜官场种种,他的心,不在宦海,而在自然。
当北宋的军队兵临城下之时他无可奈何地落泪,兴衰更替本就是历史常态,他改变不了,也无从改变。无尽的落寞中不禁煮了一壶世上最苦的茶,他像饮酒一般畅饮而下,为这烽火不止的天下,也为这终得一时太平年间的黎民。宋太祖欣赏他的才能,让他续任吴侯,他婉言拒绝,他的一生被政治绑定太久了,疲了,累了,是时候离开了。
宋太祖没有留他,宋朝没有留他,他就像一只飞鸟,看尽一路风景回到家乡。
从此春花酿酒,岁月煮茶,时常拂琴于山林之间,放下后的心凝形释与身旁的湖水心心相犀,湖水千年岿然于此,似乎只有他懂得这真意。
别了庙堂,韶华白首,他没有消极避世,只是选择入得这村舍之间做一位恬淡的老翁。天气好时,或垂钓于山顶之湖,或漫步满山洞府之间;雨打芭蕉,则屋舍之内煮一壶清茶,悠然读书。一月之内,定时教当地村民练武强身,开了江南乡民习武的先河。
翻开当地相关资料,这一地的武状元在历史上写下了几笔辉煌,也许在哪一代,会有一位武状元,放下了庙堂,回乡成为另一位林倪。
自然山水留不下名利之心,名利之心亦无法在这淡妆素雅的境地安眠。林倪一生没有爱上过谁,也许所有的个人情愫都随着五代的结束而消散,若说无情,却又是那样牵强。我更愿意说,林倪把那份儿女私情化成了对恬淡生活的爱,化成了与孤独相伴,当爱有了依托,情也就有了归宿。
就这样,林倪的故事镶嵌在这山水之中,踏足其间,风划舒竹,水过石间,似又听得了那一阵畅意悠远的古琴声。
这段天然合奏,也必然在这世外之地,予游人以慰藉,千年又千年。
二
一座城,面朝大海,守着边防,远处菖蒲、芦苇丛生,那是四季对蒲壮所城的安慰。
站在城头,望滩涂泛着岁月的厚重,有多少城能够带着哀怨经历长久的凄苦别离?我很难想象,那段眼看着自己的故土却无法踏足的岁月,那段由“插竹为界”而萌生的恒久悲凉。可他们却又没有怨恨,他们明白,蒲壮所城为边防而生,他们的生命,早以纳入了这一片滩涂之中。
那日,城隍庙香炉的灰积的厚重,如同这被世间遗忘的城,覆上了厚重的尘。走在“田”字形的街舍中,觉得分外畅意,街街相贯,巷巷相通,牌坊林立,卵石铺面。多年前,每逢战事,当地军队必是由这宽敞相连的街道迅速集结,守着城,守着永恒的宁静。
很喜欢这样,走在没有商业元素的古城中,似乎回到了某一年,穿着长褂白衣,坐在楼阁之上,看着风与柳絮的缠绵,听着雨落青石的轻灵。或许会即兴赋诗一首,或许会被远处的锣鼓吸引,寻声前去,品着一盏清茶,听上一段戏曲。可以是《白娘子》,一生追求只为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为了这个看似轻易却无限遥远幻梦,宁愿等到雷锋塔倒西湖水干。也可以是《梁祝》,他们的故事让世间无数痴男怨女明白相遇,懂得缘分。离别时的十八相送,是放不下的情缘,是割舍不断的留恋。冷漠的俗世没有给他们一个安宁的世界,因而化蝶。
恍然问看着古戏台上时光留下的纹络,是为了让后人缅怀曾经那段莫问来去的岁月。
翻看当地资料,有这么一句话令人顿生追寻之意,“秋色晚来赊,断雨残霞,萧疏芦荻满丛花。流水小桥红树外,几点归鸦。”写的是蒲壮所城的村居之景,却清新婉转,令人回味。
道光年间,当地有一位才女谢香塘,从小沉溺古籍,醉心诗词,为当地百姓所称道。有一天,城内往来诗人在楼阁中约谈赛诗,那场面必然是杯酒助兴,纸扇染风。诗人们没有想到,会有一女子令他们心服口服,她所作的骈文甚为婉约,诗词更是收放自如。从此,香塘进入了当地的文化领域,为诸多府门所青睐。
有时候我不禁会想,在那个由男子扛起一片天的年代,女子的才究竟是幸还是悲?只因读了太多这类的故事,多以悲欢结尾,了解这段故事时,也逃不过这哀怨之感。
香塘在二十岁时选择嫁与蒲门金洛先,金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本应是一段良缘,却终逃不过这年代之乱。金洛先吸鸦片成瘾,挥霍无度,昔日繁华终变成明日黄花,三十岁时便病逝了,那一年香塘不过二十五岁。
她本育有一子,不到周岁便夭折了。面对着这人生中的低谷,香塘也曾几度以泪洗面,却终没有因此而倒下。她的坚韧代替了对平淡生活的渴望,曾经拿笔的手操持着井臼,她没有因孤独而狭义,而是从这清苦的生活中提炼出了刚毅与自尊。
三十岁时,从族内过继了一子,将自己对于古籍文学的梦延续到了孩子身上,她延师授客,学会了种月耕云。
很多年后,写成了《红余诗稿》,满意地离去。
正是这样一位柳絮才高品性坚韧的女子,为这古城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
古城的故事有很多,一路青石铺排,似乎每一块都有着属于它的故事,每一块牌坊之下,也必然见证过一曲人世赞歌。
走时,忽然觉得古戏台唱了一曲小调,人生也好,红尘也罢,都不过一场折子戏,留得下命运的痕,忘得了内心的伤,要学着潇洒忘记。
三
当一个人在路上时,时光的脚步就再也无法留下印记。
清晨,下着些许小雨,淋湿了路人来时的路,看着细雨中的蒲壮所城安然依旧,我满意地离开。沿着海岸线,任柔和的细雨打在脸上,行了很远,还是可以看见那城头,总觉得它在等着故人的归去。
世上的风景不胜枚举,多得也许一生都看不完,但并非每一处风景都需要我们去抵达,很多时候,阳光会将同一种色彩带到许多地方,我们只需随缘,走过的地方,也就有了留在记忆中的价值。正因如此,我没有刻意去选择那些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胜景,也许年少时总以为历史人文构成的景观才足够恢弘,足够细腻,直到有一天,来到了这片海天一方,才明白,真正的风景,在于路人的心情。当然不会像古人那般留下千古绝句,或因贬谪或由升迁,只是做着一个大时代下的过客,看着每一处自然风光,让它留在眼中,让它留在心上。
对这南国的海鱼来说,鱼寮便是魂牵梦萦的故乡,无论游走何方,终会有一天回到这里。
沙滩柔软却承载着旅行者自由的抒怀,我曾试着对一块贝壳说上一句话,将它留在时刻能够看到海浪的地方,几年后再去寻找那块贝壳,我告诉自己,当时的心愿已经随着海水漂泊天涯。一样是站在音乐石上看着海面,一如年少时那追风的模样。
我与这片海有个约定,每隔三年来一次,对贝壳许下一个心愿,放在同一个地方。贝壳在海上流浪,也许某一夜,会悄然进入我的梦乡。许多人都会这样,面对辽远的风光,纵有千言,也再不需要一一陈述,只因站在海边,海的深邃早已明白一切。
还记得童年时的一个秋天,和家人来到海滩,油菜花迎风摇摆以最舒适的姿态迎接着秋的归来,那时节的景一片金黄,一片蔚蓝,虽不记得当时模样,必然也是快乐酣畅。
童年之趣,情若霞光,也许我会在礁石上对着远方的船只朝手,然后一路奔跑直到父母牵着手在夕阳的告别中回家。
在回忆中醒来,未几,夕阳满意地落下,如同游人离去的脚步那样缓慢,我尽量爬得高些,踩在音乐石上,看得更久些。
这片石块的确是趣味盎然,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或铿锵有力,或低沉悠扬,自然的音对上了世间的乐,一切指向了一路走来的时光,将忧愁分解,融入了轻快的旋律中。
夕阳将一切抚摸得非常柔顺,海浪的诉说一如在陈诉一段青春年华,把心事告诉贝壳,让它带到更远的地方,年长的礁石拂着青苔看着这一切,回忆成长如在沙滩上写上冗长繁杂的故事,仅是一阵风,故事被遗忘,却留下了简单与纯真。
我想,年岁便是如此,我们所需铭记的,并不是这一路走来的眼之所见,而是那经历之后的幡然醒悟。
寻着晚霞,我放手驰骋,远处的五彩礁石将夕阳的余晖折射到路人的脸上,像儿时那样,对着远处的船只招手,转身去往下一站。
四
如果没有来过,我又如何能知道,在家乡附近,有一个古村落,静卧山中,任光阴荏苒世事变迁。它就像一位老者,看过了锦绣繁华,走过了绿水人家,最后来到这里,拥抱安宁祥和的时光。
也许有一天它会被世人忘记,时光走得太仓促,没有留下太多可以追思的物件,但只要那一方古窑还在,总会有人想起,这片村舍曾经的花样年华。
走在碗窑村中,如同活生生的历史风貌展现在眼前,这座山城与玉龙湖相依相伴,虽未许诺,却已深情。
若是能做上一场梦,必然会选择坐在古舍旁的木椅上,似乎回到了某一年,竹杖芒鞋随着明净澈底的玉龙湖,走到这南国瓷器之乡。贯通村舍的,不仅是青石相连的山路,路旁还流淌着晶莹山泉,尚有山花顺水而下,水光潋滟,默然相间。我会取上一瓢山泉,洗去旅途的风尘,再煮上一壶浊茶与村民弈上一局。也许眼前,便有技艺娴熟的乡民在烧制陶瓷,因了这系列工序,本已离开了山中的土才有了新的生命,得以进入万色红尘随光阴流转。
待风起时,折入山间小道,清幽怡然,无声美眷。正当这样安逸地走着,猛地被惊醒,原是三折飞瀑从天而降,苍劲灵秀傲视世间,玉倾珠帘银花四溅,世事妖娆却抵不上自然一景,光阴菲薄却带不走苍绿流年,这胜景伴着简朴的古村,淡妆浓抹总相宜。
听得当地村民讲述着古村的历史,我难以将情绪从这故事中抽离出来。
那时节,又是一次历史常态中的改朝换代,又是一次烽火缔造的纷乱年间,福建连城县的巫氏无声地隐忍着,看着兵戈下的乡土不断经受着战时的摧残,看着一批又一批时值壮年的族人马革裹尸,他们再也无法安土重迁。于是在族长的带领下,一路内迁,来到玉苍山南麓南坡,若说是什么让他们留下来,我想必然是这漫山胜景与凄清冷艳的湖水。
从此,他们重新开始了安定的生活,并利用当地自然资源重操旧业,烧制陶瓷器皿。有一天,村长巫仕人将青花瓷带到县城市集上,当地客商见陶瓷纹理有秩、温婉灵秀,不禁感叹,在买下所有瓷器后,更是带着一大批客商前来碗窑选购。从此,一个小小的村落客商不绝,成为了江南地区最为繁华的乡镇。之后,许多文人慕名而来,为这村落添上了笔墨熏香,有的甚至留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宁做自然情趣之下的读书郎。村内因此旅舍林立,戏台演着脍炙人口的故事,锣鼓声中似乎在讲述一段乡间的动人传奇。
转眼又是寒冬,素雪褪祛了山花的姹紫嫣红,老戏台不再喧闹,甚至找不到一丝烟火,只能在残碎的剪影中静待风霜满鬓。时光走得太匆忙,虽不至世态炎凉,倒也是人迹消散,碗窑的梦,就像破碎的青花瓷,曾经那样熠熠生辉,终躲不过最终的颓败。
与老人的一局弈棋早已结束,我闲敲着棋子,看着旧客店,望着古窑,再多的繁华也会是一场清古素颜收场,曾经的华美成为了如今长满苔藓的方丘,或喜或悲,在于回味。
老人问道要不要花上十元钱用泥坯做一回碗,我笑着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