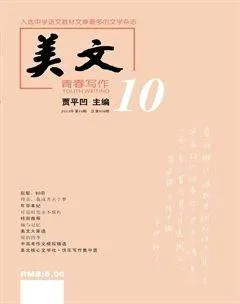非关命运
2013-12-29朱之丛
这部小说融合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空间,形象地展示了哥伦比亚和整个拉美地区一百多年的殖民史和社会生活史。
——人教版《历史》必修三
教科书上对《百年孤独》的评价仅此一句。
我已不太记得什么时候买回的这本书,以及一向看书飞快的我为何选择购买而不是就地解决。买书的当时,依稀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便理所当然地猜测这个陌生名字又是某年的冷门新锐。读了书才知道,实在有够老。
这也是《百年孤独》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厚重历史感给我的暗示。很奇怪,并没有怀古文字一贯的萧索与苍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一种看遍沉浮荣辱世态炎凉、完全预知命运走向的“洞悉者”那般的平静。这总让我想起烟大(烟雨江南),尽管马尔克斯选择了孤高的魔幻现实主义,烟大写的却是最为媚俗的网络小说。
但是那种客观到接近冷酷的叙述方式,奇诡的结构,上帝的视角,这两个同样踏上虚幻一途的男人别无二致。
《百年孤独》并没有花很大笔墨在“孤独”上,因为极目所尽,皆是孤独。
书中布恩迪亚家族每个角色的命运都充满至大的孤独。无论是发动三十二场内战的布恩迪亚上校也好,抵死渴求爱情最终装聋作哑客死异乡的梅梅也罢,当他们回顾自身命运时,感受到的,只是铭心刻骨的孤独。
我到现在也不是很能理解:他们都有那样波澜壮阔,或则至少平稳安宁的人生,都曾爱过、痛过、哭过、笑过,谈何孤独?难道他们真的“爱过、痛过、哭过、笑过”吗?
——布恩迪亚家族那些传奇的人们,真的有认真活过吗?
《死神》虚圈十刃之首是代表“孤独”的柯雅泰·史塔克,虽然实力上略显废柴,但他排名第一的理由是“孤独是人类死亡的永恒诱因”。很好笑,我总是拿流俗的大众作品去跟高雅的经典著作相比较,但有时候,它们之间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相通。
“在一道清醒的电光中,他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承载不起这么多往事的重负。他被自己和他人回忆纠缠,如同致命的长矛刺穿心房,不禁羡慕凋零玫瑰间横斜的蛛网如此沉着,杂草毒麦如此坚忍,二月清晨的明亮空气如此从容。”
奥雷里亚诺·巴比伦作为布恩迪亚氏的末裔,注定要承载整个家族的悲欢记忆,但他绝不可能因此而死,因为他同时也接手了整个家族百年来所积蓄的孤独。他打破这份孤独唯一的悲壮举动,是和一个自己真心相爱的女人结合,尽管他的妻子最终被证实是他的姨妈。各种巧合最终促成了他们在血脉迷宫中的邂逅,也注定了他们要产下“终结整个家族的神话般的人物”。梅尔基亚德斯羊皮卷上的预言得以完美应验。
而他们孕育出带着猪尾巴的孩子,并使孩子的母亲失血过多而死的唯一理由,只是“他们真心相爱”。
我骤然意识到整部小说中真心相爱的人究竟有多少?整部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里,因真心相爱而结合的夫妇真的存在吗?聊聊少数,全都不得善终。偏瘫半世的马乌里肖·巴比伦,用弹奏钢琴的双手割破脉管的皮埃特罗·克雷斯皮,都成为享祭孤独的牺牲。
正如老乌尔苏拉所认为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只不过是一个不会爱的男人,反倒是敢爱敢恨的丽贝卡,拥有着布恩迪亚家族一贯缺失的基因。
因为对布恩迪亚家族来说,相爱即是罪孽。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无疑是《百年孤独》的重要人物,尽管他只是表面上的“贯穿全文”,最终也逃不脱死亡。但不得不承认,他的命运是家族中最可歌可泣的。
他发动过三十二场武装起义。他逃脱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伏击和一次枪决。他缔造着无处不在的神话。他曾经是令政府无比头疼的自由军首领。他用手枪瞄准自己心脏开枪却得免一死。他的名字被用来为马孔多的道路命名。但他最终只能不知疲倦地制作着小金鱼,作为一个怪癖的老人了此残生。正如乌尔苏拉所说,他不会爱。
所以即便是马孔多的居民们,也仅仅把他当做一个虚幻的神话而已。
奥雷里亚诺为祖先被人遗忘而愤怒得浑身颤抖。但正如三千工人被枪杀后弃尸大海的惨剧也被轻描淡写地遗忘一样,对于马孔多这座“蜃景之城”来说,人们本不晓何为真实。无法得到承认的辉煌功绩,也便风化成了孤独。
上校同十七个女人有过十七个儿子,然后在一夜之内被追杀殆尽,没有一人逃脱宿命的钳制。他们受洗后额间永抹不去的灰烬十字,正是继承家族宿命的绝望证明。所以我相信他们在死亡之前一直是孤独的,尤其是倒在奥雷里亚诺跟前的最后一个流亡者,眼神一定孤独至极。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人生确实充满传奇色彩,但对于一个不会爱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活得越壮美,越是孤独!
真正贯穿全文的人物不是他,而是一个游离于布恩迪亚家族之外,却通晓这个家族所有法则的算命师——庇拉尔·特尔内拉。她与布恩迪亚家族的伦理关系早已错乱,接连几代的男人都与她有牵连。在同这个古老家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同时,她又参与了无数人的命运,最终活过一个多世纪的她,根本不需要纸牌就能毫不费力地预测布恩迪亚族人的过去与未来。
庇拉尔·特尔内拉是全书最充满魔幻色彩的人物。越苍老,她就越能自信地预言并插手他人的命运,将布恩迪亚家年轻小辈的未来导入新的方向。无法从道德和法律上判断这种插手的对错,甚至就宏观历史来看也不行。她和梅尔基亚德斯一样,都是洞察命运轮轨的神祗。前者凭借人类灵魂中的清晰预感和丰富经验预测命运,代表了人类的自省;后者则是绝对的先知,有着宗教意味。仿佛梅尔基亚德斯推演了布恩迪亚家族的一切,然后在重要关节由特尔内拉去实施。
乌尔苏拉和特尔内拉形成鲜明对比。两人都已活过百岁接近无限久远,她们看问题的角度早已不同于常人,而更接近神。不同的是,乌尔苏拉观察的是家族中的个体,特尔内拉却着眼于整个家族的命运走向。前者陷于局中,后者站在局外。所以乌尔苏拉只能察觉当下的琐碎事实和已经逝去的真相,特尔内拉却能提取历史的精粹,大胆预言未来。
因此说,乌尔苏拉只能是有限时空内的智者,特尔内拉却是掌握命运符咒的巫师。
逃离孤独的人并不是没有,只是方式未免怪诞到略显悲情。
蕾梅黛丝,人称“美人儿蕾梅黛丝”,只有学龄前儿童智力水平却貌若天仙。她的存在不可不说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异数。在此之前和之后,再没有一个人能如她这样弃绝孤独,全然幸福地沉醉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
如果说布恩迪亚家族的人全是沾染了神秘色彩的宿主的话,那么蕾梅黛丝就是唯一免于孤独之厄的人,尽管这种“赦免”是以先天弱智为代价。这之后,即便是破译了整个家族历史的奥雷里亚诺·巴比伦,也无法自拔地深深陷入孤独的泥潭中。
最终的结局是“飓风”,在网络小说中,这种结局一般称之为烂尾。
但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显然不同。《百年孤独》的末句是:“……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马尔克斯的一种哀痛,同时,也是一种慈悲。
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并非通常意义上“无人陪伴”的孤独,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孤绝感,即便有人认同、有人理解,他们的灵魂依旧作为独立个体存在,在一种看似平常、实则无法沟通的高度上各自往来。他们与世界并非完全没有交集,但这样的交集完全没有意义。若如芥川龙之介所说“天国之民首先应不具有生殖器和胃袋”,那么天神首先应具有的,应是这种烙入灵魂的孤独。
东西方两位文学怪杰在此形成共鸣——此处便是人神之间的永恒的鸿沟。
所以脆弱的芥川服毒而死,而马尔克斯制造了一场飓风,将不属于人间的布恩迪亚家族和整个马孔多小镇抹除。纯正的人类是无法在天堂生存的,反之亦然。正是本着人性中不可交融的巨大矛盾,马尔克斯还给了我们一个充满喜怒哀乐、白永远至永远都污浊滔滔的人间。
不复孤独当是一种巨大的幸运,亦是一种刻骨的悲哀。
教科书上对《百年孤独》的评价显然太过浅薄。小说中不可胜数的细节和叙述技巧,是唯有亲身阅读才能体会的。
这便是为何马尔克斯能摘下诺贝尔奖,烟雨江南却只好一个人撑起17K:前者是从容不迫的深度思考,后者只是陷身于充满烟火气的快餐文学。
庇拉尔·特尔内拉说:这个家族的历史不过是一系列无可改变和重复,若不是车轴在进程中不可免地磨损,这旋转的车轮将永远滚动下去。
我想这才是“百年孤独”真正的寓意:不可改写的绝望。
与其孤独,不如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