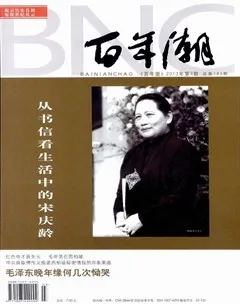将军风采岂止在战场
2013-12-29李永戈
2012年初,在杜义德将军诞辰100周年临近的日子,我接到杜义德将军的夫人齐敬轩的长途电话,她在整理纪念杜老的文章时,急于核实杜老晚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时的情况。幸好我保存着一本我任杜老秘书时记录的《承办文电》册,在完成杜义德夫人交办的核对杜老在中顾委工作的有关情况后,我开始细细翻阅这本26年前的《承办文电》册。看着当年一页页文电登记的内容,透过一段段的文字记录,我眼前又浮现出在杜老身边工作时的件件往事。
年过古稀,犹如还在前线
1985年5月,我被选调到杜义德将军身边任专职秘书。对身经百战的杜老将军,我早就有所了解。他青少年时代到武汉做工时就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27年回乡参加农民协会,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前,他已担任师政委、师长,抗日战争后期任冀南军区指挥部副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兵团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归国后,他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政委,海军副政委、第二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1977年当选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我到杜老身边时,他已经退居二线。1982年,邓小平从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考虑党的建设问题,为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年轻化,解决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问题,同时让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退出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作用,提议中共中央成立顾问委员会,并在时间上提出少则五年、多则三届的时限设想。中顾委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是过渡性的组织,由邓小平担任第一任主任。杜义德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深知这是邓小平深谋远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解决党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重大抉择。对此,他积极响应老首长的号召,主动要求从兰州军区司令员位置上退下来,到中顾委工作。
中顾委的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中顾委的委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担任过地方正部(省)级以上、军队大军区正职以上重要职务的高层领导干部,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中顾委委员列席党中央全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平时在正常情况下每周开两次会议。刚调到杜老身边做秘书时,我是个营职干部,过去虽也接触过一些高层领导,但经常在如此众多的中国政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身边工作,深感荣耀和自豪,也深感责任重大。
杜老20世纪80年代初做过胆囊切除手术,在兰州战区工作期间深入一线边防部队,由于高原反应身体也受到些影响。虽然他已在中顾委工作,却犹如还在前线,以饱满的热情和对党的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积极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活动,按照中顾委委员的职责经常深入到部队、革命老区、企业、农村、学校搞调研,参加军史、战史的修订编撰领导工作。不了解内情的人很难想象古稀之年的老将军把工作日程安排得有多满……
1986年三四月间,《承办文电》册上有这样几条记载:
1.《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来函:请杜司令员对《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稿第七章、第八章及说明进行审定(当时,杜老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委员、《第二野战军战史》顾问)。
2.中共四川省泸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史编撰办公室向杜司令员了解1949年12月—1952年8月,中共川南区党委和泸州地委、市委常委任职等情况(1949年12月第二野战军南下驻该地时,杜老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10军军长,并兼川南军区司令员)。
3.海军政治部干部部任免处来函,需要了解一批干部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请杜司令员对名单上所列干部提出意见(杜老在海军任副政委、政委20多年,是很有发言权的)。
4.中央档案馆来函,希望杜老说明,毛泽东主席与杜老合影照片的有关情况。
以上来函涉及的内容很多,而杜老在审阅和回复时从不拖延,许多事项还是统筹兼顾进行的。譬如在3月份的文电中,有邀请杜老到外地参加会议的函件。我记录了杜老要求随行工作人员把《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稿带上,以便在外地参加会议期间审阅修改稿。
《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在1986年3月19日的来函中,请杜司令员审阅《战史》修改稿第七章、第八章及说明,提出意见并于4月15日前函告修改委员会办公室。按来函要求,修改时间不到一个月,而杜老在此期间又应邀到外地参加7天会议。当时警卫员小刘曾建议:首长外出开会只有一周时间,就别带那么多资料了,《红四方面军战史》的修改稿回京后再看也来得及。但杜老严肃地说:这项工作是军委的任务,很重要,时间紧,要求高,修改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们工作很辛苦,邓主席、徐帅和先念等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对这项工作都非常重视,需要我们做的事只能往前赶,不可往后拖,不能影响编辑人员的工作进程。两周后,杜老在审阅修改稿后致修改委员会办公室的回复中写道:“您们送来的《战史》修改稿第七章、第八章及说明均已看完,我完全同意您们对《战史》修改稿第七章、第八章及说明的意见,其中有些情况你们比我了解得还清楚……我的几处修改意见是,第七章:356页倒5 行,李聚奎后面应加上杨梅生,李卓然后面应加上黄火青;385页正3行,军长前应加上‘代’字;第八章:448页正8行的‘此’字错了……”
从上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一位70多岁的高龄老人,仍以饱满的热情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工作着。他不仅对《红四方面军战史》中大的事件和原则问题认真把关,而且对文字也逐字逐句阅读和修改。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历史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军队负责的精神。杜老为《红四方面军战史》和《第二野战军战史》编纂修改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成员和《第二野战军战史》修订人员,包括宋任穷、陈再道、陈锡联、秦基伟、杜义德等老同志。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见结束后,杜老说:小平同志的讲话很重要,“我们要把军队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写好,这是党和军队的重要财富”。
实事求是,坚持对历史负责,
客观表述上甘岭功绩
我多次听杜老说过:“对待历史问题,我们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杜老不仅经常这样说,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念。我在《承办文电》册上记载的一件事,体现了杜老对历史问题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
1985年10月末,我跟随杜老陪同中顾委王震副主任乘专机到南京,参加一代名将许世友的追悼会。杜老在南京军区的战友很多,连日来,两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向守志等都来看望他。
向守志司令员多次到南京饭店看望杜老,谈了许多许世友晚年的事情以及治疗、生活、安葬预案等有关情况。他们对战史方面的问题谈得也很多,尤其是交换了对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之战记述问题的看法。8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快10年了,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都提了出来,杜老遇到了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的功绩应如何表述的问题。
1952年秋,抗美援朝战争中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此役“联合国军”先后投入6万余人兵力,出动3000架次飞机和170余辆坦克,进攻不到4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在43天的激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敌2.5万余人,在中美两国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志愿军第三兵团的司令员、政委由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陈赓兼任,杜老任第三兵团副政委,王近山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上甘岭战役打响前,陈赓已奉命归国筹建军事工程学院,杜老与老搭档王近山受命联手指挥了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战役胜利后,杜义德还曾应召回国,向毛泽东、中央军委汇报上甘岭战役始末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
一些老同志给杜老来信反映,过去宣传上甘岭战役的功绩只讲15军坚守gKicnAOlo5FvZpfj+aimDEnEoBsT0uNAKFz4OpibV6I=作战,这是不全面的,其他部队支援15军坚守上甘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比如12军,就对上甘岭之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许多指战员的鲜血洒在了上甘岭的战场上。但有许多年,12军的作用、12军指战员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雄事迹,却没有被提及。
抗美援朝战争中期,第三兵团下辖12军、15军、60军,向守志任15军44师师长。杜老在南京期间,与向守志一起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共同分析了整个战役的情况、主要任务、兄弟部队之间的相互支援,详尽探讨了上甘岭战役的作战方案,取得胜利后的总结和评价以及回国参加国庆观礼事迹报告等情况。最后,两位老将军谈道:上甘岭战役打得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志愿军总部作出的决策正确,是各级指挥正确果断,是志愿军将士们英勇顽强,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机动灵活地创造性地完成作战任务。上甘岭的作战任务主要是下给15军的,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其他部队给予了大力配合和支援,为取得上甘岭作战的胜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位老将军边散步边谈论,最后,我听到两位老将军讲:上甘岭的作战任务是下达给15军的,主要功绩应该是15军的,多年来以宣传15军为主是正确的。由于战斗打得异常残酷,部队伤亡极重,面对美军强大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单靠15军已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所以需要12军加入战斗。12军部队参战后作出了重大牺牲,功不可没。另外,还有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的炮火支援,志愿军工兵的密切配合等等,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都应该实事求是地记载。
严于律己,坚决按中央政策和规定办事
在《承办文电》册上,还记载了一些关于杜老严格执行中央和中顾委的规定,严格要求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事。
要按规定交伙食费
1985年10月,杜老到南京参加许世友的追悼会。杜老与许世友都是在鄂豫皖参加革命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抗美援朝战争后期,许世友接替陈赓担任第三兵团司令员,杜义德任第三兵团政委。他们是老战友、老搭档,也是老朋友。到南京后,我们下榻在南京饭店。
20世纪80年代,杜老出差都住军队招待所或省委接待处,没住过地方宾馆,由于参加许世友后事活动的人员较多,我们被安排住地方宾馆。地方宾馆房间内有小酒吧,冰箱里还有多种饮料。军区接待办的同志告诉我们:房间内的水果、冰箱里的饮料等都可以用。但杜老要求随行人员要特别注意军人形象,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说:虽然南京军区接待办的同志允许我们在宾馆消费,但我们要自觉,要体谅接待单位,为接待单位节省开销。房间小酒吧和冰箱里的东西都不要动,以免给南京军区增加负担。
参加完许世友同志的治丧活动,离开宾馆时,杜老要求我们一定要交伙食费,还特别强调,他的伙食费也要交。他对我说:虽然接待的规格高,但必须按部队的伙食标准把该交的基本伙食费留给南京军区接待办。要按部队的出差规定办,这是人民军队的老传统,我的伙食费你们先替我垫上,回北京后由齐静轩(杜义德夫人)给你们还上。
严格遵守政策规定,中顾委委员的子女不允许经商
杜老爱孩子,但在原则问题上从不通融。一次结束中顾委会议后,他召开家庭会议,非常严肃地传达了中顾委的会议精神——中顾委委员的子女严禁经商。他郑重地对孩子们说:中顾委委员的子女是不可以经商的,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定,这可是原则。“我们家任何孩子决不允许违反中央的这个规定。”
杜老最疼爱小女儿杜红,在她的记忆里从没有见过父亲如此严肃。当时杜红负责海军某研究所的开发经营工作,也是家里唯一涉及商务工作的孩子。于是杜红就去找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提出不干这个工作了,后来党委书记开具了证明函:“杜红同志担任研究所的生产经营工作是组织决定的,是按照党的原则工作,按照组织的指示办事……在工作期间没有任何违反党和政府规定的行为。”杜老一遍遍仔细看了证明函的每一句话后,才认真地把盖着研究所党委红章的证明函慢慢收好,没有再追究下去。多年以后,杜红提起当年往事依然心有余悸地说:“当时真捏着一把汗,庆幸父亲没有把我逐出家门。”
对身边工作人员管理严格,关心备至
杜老不仅对子女要求严格,对自己及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同样也很严格。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0年代至90年代,中顾委委员参加中央全会都住在空军大雅宝招待所。由于在京委员的司机不安排住处,司机们中午习惯在车上休息。杜老时间观念很强,通常总要比规定时间提前10分钟下楼坐车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有一次,杜老下楼后等了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车,也找不到司机,直到各位委员的车陆陆续续驶往大会堂时司机才急忙驾车赶来,原来司机开车到后面找阴凉地方睡午觉
去了。
当时杜老非常生气,他批评说:“你们都是军人,军人最讲遵守时间,无论干部战士都要严格遵守纪律、强化时间观念。军人迟到可不是一件小事,会养成纪律松懈的坏习惯,这对军人危害极大。”他还说,农民是看太阳下地干活和收工,时间差一点没关系,但军人必须守时,不论在一线战斗还是在二线工作,都要严格遵守时间。事后,他还要求我专门召集工作人员开会强调守时守纪律的重要性。会上,杜老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战争年代,有一支部队由于没掌握好时间,结果造成该部队人员本来可以避免的无谓牺牲。
杜老在大事情、原则问题上很严肃,不讲情面,但对工作人员的生活非常关心。每当工作人员休假探家,他和老伴齐静轩都要给战士带上些吃的用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加班写材料,有时来不及到食堂用餐,杜老就让我在他家里吃饭,吃饭时他对我说:“你经常加班工作劳累,要加强营养。”边说边把炊事员给他做的菜拨给我一半。
每逢过年过节,杜老还会把秘书、司机、警卫工作人员召集到家里,吃顿节日餐,同大家一起聊天。这时候,他常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和笑话,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工作人员也会把外出有趣的见闻和家乡的新鲜事讲给他听,老首长往往像年轻人一样同工作人员在一起有说有笑。
情系老区人民
1986年,杜老和中顾委常委段君毅同志、全国政协常委刘子厚同志一起,到湖北参加大别山党史会议。战争年代,段君毅和刘子厚都曾长期在大别山区工作,段君毅担任过鄂豫军区政委,刘子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湖北省省长。他们二位与杜老一样,都对大别山老区怀有深厚的感情。会议结束后,杜老、段老、刘老一起深入红安、麻城等地搞调研,了解老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和经济发展情况。
杜老感慨地说:红安、麻城是大别山革命老区,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发源地,为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里曾诞生过多支红色武装——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等。大别山是革命摇篮,在共和国的第一代将军中有200多位是大别山人。大别山也是国民党反动武装的重点“清剿”地区,当地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曾遭到疯狂的报复。据不完全统计,仅红安县,惨遭杀害的群众就达14万多人,麻城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群众有13﹒7万多人。黄冈地区惨遭杀害的群众更是多达44万人。
杜老对大别山革命老区一往情深,他深切地眷恋着那里的父老乡亲,牵挂着老区人民的生活。他在一线岗位工作时抽不出时间,退居二线后虽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还是坚持多走一些地方,多了解一些老区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革命老区的贫困现象尚普遍存在,生产生活条件很差,有些地方连温饱问题也未解决。杜老、段老、刘老一起深入到大别山老区农村,一家一户地了解真实情况后,心情都很沉重。
进村后见到村民住着破旧的房屋,用水、淘米、洗菜、喂牛、涮马桶都在一个水塘中。有一户村民家,里屋一张旧床上只有军队扶贫救济的一条绿军被和一件军大衣,外屋的一张方桌上只有一个搪瓷水缸,上面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一看便知也是军队扶贫给的。这家一贫如洗的家境实在令人心酸。村干部介绍说,这种现象在各村很普遍,旧社会这里的青年一批批地参加革命,留下的又遭到国民党的屠杀。村里的军烈属很多,贫困面太大,但单靠年年救济解决不了几十年战争造成的创伤。老区人民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所做的牺牲太大了,战争留下的后遗症太重了,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已吹向祖国的大江南北,但解决老区贫困和经济发展问题要有特殊政策。
杜老和两位老战友认为,对老区生活贫困的群众在经济上给予救济是必要的,但只靠救济不行,应该从如何解决根本问题方面多考虑,要扶持他们尽快加速经济的发展,要扶持这些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条件好的市、县和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都要对口支援老区,国家在安排建设项目时,在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给老区安排一些小项目,以增加老区的造血功能,这才能使革命老区从根本上靠自力更生脱贫致富。
为此,杜老写了调研报告,报送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这篇调研报告同时在中顾委内部刊物《通讯》上发表,而中顾委《通讯》每期都报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以及有关的国家机关,有关省的省委、省政府。刊登杜老调研报告这一期中顾委《通讯》,据我所知报送给了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以及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教育部、卫生部、湖北省委、湖北省政府等部门。据说,引起了有关领导同志和相关部门对老区脱贫致富问题的重视。
我翻阅着当年的《承办文电》册,回想着杜义德将军在中顾委工作时的往事,缅怀之情涌上我的心头:这是多么受人崇敬钦佩的首长啊!在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仍然需要杜老以及杜老那一代人的宝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