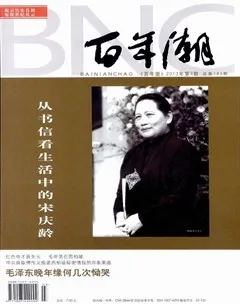解密邓小平莫斯科留学档案
2013-12-29汪东亚王超群
1926年初,22岁的邓小平(当时叫做邓希贤)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从法国抵达莫斯科,在苏联居住和学习了一年。留学莫斯科期间,邓小平和蒋经国是同窗好友,并且结识了首任妻子张锡瑗。
这是他第一次在共产主义国家生活。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保存有一批记述邓小平这一时期生活和思想轨迹的档案,表明他愿意接受“铁的纪律训练”和“共产主义
洗礼”。
这段经历显然影响了他的一生,特别是若干年后他在中国大陆推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稀可见当年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痕迹。
站队时与蒋经国肩挨着肩
1926年1月17日,星期天,莫斯科比拉罗斯火车站,邓小平和17名同行者受到了中共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代表的热情欢迎,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位于市中心普希金广场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这所大学是当时苏联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共有学生1664人,大多数来自欧洲,中国学生约有100名。
中共旅莫支部的总部不在东方大学,而在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成立于邓小平抵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前,仅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学生中不仅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成员,也有中国国民党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些负责人认为,把有前途的中国共产主义者送到苏联重点“中文”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更加合适,所以邓小平到达莫斯科12天之后就转到了中山大学。
1月29日,邓小平收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学号233,化名“多佐洛夫”。学生一共分13个组,每组25—40人,邓小平被分到共青团第七小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班组。班上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以及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谷正鼎、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政工局局长的邓文仪等蒋介石心腹亲信。
蒋经国和邓小平个儿都不高,站队时老站在一起,肩挨着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蒋经国“学得不错”。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他这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常常责问蒋经国,“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
邓小平是第七小组的组长,他爱上一个俄文名叫多加多娃的漂亮女组员。她的中文名叫张锡瑗,1907年10月28日出生于顺天府房山县良山乡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小邓小平三岁,比他早两个月来到莫斯科。
张锡瑗性格开朗、活泼,这一点跟邓小平一样。体型纤瘦的张锡瑗有着淡黑的眉毛,常常梳着短发,长相很漂亮。当时,中山大学几百个男生中只有二三十个女生,相对于那些整日纠缠女生的男同学,邓小平要保守得多,他并没有把对张锡瑗的爱意过早地表达出来,两人的恋情在回国后才明朗化。
1927年初,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张锡瑗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第二年初两人结婚。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父亲和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1926年10月9日,在邓小平担任组长的第七小组会议上,他因“积极尽责的工作表现”而转为正式党员。
中山大学的学制为两年,学生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在教室里学习。课程安排比较紧凑,除俄语以外,还有社会形态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党史、经济地理学、政治经济学(以德国社会学家卡尔.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主),以及党建、军事事务和新闻学。
邓小平来莫斯科是为了学习“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在中山大学注册前夕,他在自传里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不足,经常发生错误,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未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了,更感觉到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所以,我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
他在自传里表示,将“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留苏期间,中山大学党委会在定期的《党员批评计划案》中,也给予了邓小平非常积极的评价。1926年6月16日的一则评语写道,邓小平“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倾向;对党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而且有相当的认识;从无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能切实执行党指定的工作……”
还有一条1926年11月5日的评语,也强调“多佐罗夫同志非常有纪律性、自控能力强、能力卓越,对同志们友善,是最成功的学生之一,很适合组织工作”,称赞他是“中国共青团在中山大学支部最好的组织者之一”。
1927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进入决定性阶段,中国国内政治瞬息万变,共产国际准备从中山大学挑选出训练有素而且可以信赖的中国学生派给冯玉祥,他们一共选出了20名中国学生,其中就包括尚未完成两年学业的邓小平。1927年1月12日,邓小平从中山大学退学,取道南西伯利亚和蒙古返回中国,至此结束了在莫斯科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他此前从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决议也同时
撤销。
中山大学党委会给邓小平的最后一次评语写道:“他态度积极且精力充沛,是最优秀的组织者之一。守纪律,自制性强,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追随能够消灭贫困的政策”
1926年,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宗旨的新经济政策在莫斯科和整个苏联燎原般发展,国家经济全面开花,市场上商品丰富,品类繁多,商店、饭馆、咖啡馆随处可见。
作为入学新生,邓小平被安排住在一个招待所里,他转入中山大学第一天,就收到了一大堆日用品:西装、外套、皮鞋、鞋刷、衬衫、毛巾、浴衣、香皂、手帕、梳子、牙刷和牙膏。
中山大学一日三餐非常丰富,早餐有鸡蛋、面包、黄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有鱼子酱。为了让中国学生吃得习惯,学校特意雇来了中国厨师,学生可以随意挑选俄式饭菜或中餐。学生们的休息和娱乐也组织得很好,除了参观博物馆、看展览、去剧院,邓小平还在1926年暑假游览了一趟列宁格勒。
这与邓小平留法时期的拮据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法国时,他们为了微不足道的小钱整日工作,靠微薄的失业救济金勉强支撑,竭力维持卑微的生存。相比之下,苏联新经济政策所显示出来的优势,很快就触动了他的
神经。
留苏期间,邓小平阅读和摘抄了苏联领导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很多论述,其中包括布哈林的一段话: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我们利用了农民、小生产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元素的经济主动权,允许私人积累,同时还让他们在客观上服务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经济……我们可以向所有的农民说:“富起来吧,积累财富、发展你们的经济!只有蠢人才会说穷人是应该一直存在的。我们应该去追随能够消灭贫困的
政策。”
这些思想毫无疑问影响了邓小平一生。他后来说过,不管是来苏联之前还是离开苏联之后,从未如此严格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而从其晚年在大陆开辟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看,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有异曲同工
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