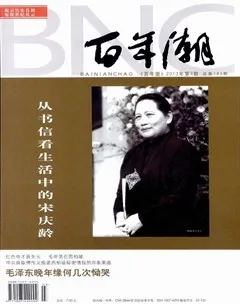文安洼垦荒记
2013-12-29张颂甲
从《文汇报》上看到钱江同志撰写的《屋顶上的毛驴》一文,佐以图片,记叙的是1960年全国粮食紧张,人民日报社食堂已经紧张到每一粒粮食都要珍惜的地步,眼看报社员工体质日衰,再也难以忍受饥饿了。于是,总编辑吴冷西提出想办法种粮食;于是,千方百计办了人民日报农场;于是,毛驴踏上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办公楼楼顶,拉碌碡压麦子……
读了这篇文章,不禁使我联想起当年北京大公报社(《经济日报》前身)派我去文安洼垦荒种粮的那段经历。
领队开进文安洼
在那非常时期,作为首都三大中央级报纸之一的北京大公报社自然也陷入粮食危机之中,也要想方设法搞粮食。当时的大公报社坐落在宣武区永安路上,楼内还有中国财经出版社,两块牌子,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一个党组、一个党委),两社职工约有500多人。大公报社党组书记、总编辑常芝青曾多次开会研究讨论在保证每天出报和正常出版图书的条件下,如何度过荒年,使员工的身体健康得到保障。这时,机关后勤同志用土法制造了一些“小球藻”和“人造肉”,用以增加员工的营养,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解决员工半饥饿问题,需要粮食。
种粮食需要土地,报社深居大城市中心区,何来土地?报社党组成员、出版社副社长林形如有一次在大街上巧遇当年在解放区军政大学的同事杨震,得知杨现是建工部给排水设计院农副业办公室主任。当谈到自办农场生产粮食时,杨震告以他们已在河北省文安县的文安洼租了洼地1000亩,即将开赴那里,开荒种地。当时的文安洼,地域广阔,十年九涝,有“涝了文安洼,三年不还家”之谓。1960年初,大水刚刚退去,灾民大多逃身在外,荒地遍野,无人耕种,一些中央机关如人大常委会和煤炭部等单位便前去开荒办农场。大公报社通过杨震,也租了1000亩地,人们翘首企望在洼地里能生产出金灿灿的宝贵粮食来。当地又有谚语:“收了文安洼,粮食没人抓。”大公报人憧憬通过自己的汗水,到金秋季节能有丰富的收获。
要派出一支队伍去开荒种地,谁去?报社、出版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知农、懂农、务过农的同志实在是凤毛麟角。无论如何,只有去边干边学了。大家踊跃报名。时任编辑部记者组长的我是一个“三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干部,还未曾下放锻炼过,这次积极报名,多次表示决心,愿意下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
抽调员工下乡,对报社和出版社来说,是件难事。因为人员编制本来很紧张,报纸天天出版,图书不断编排,没有富余劳力。这次情况特殊,必须下决心抽人。经过几上几下,最后抽出30人,编辑、记者居多,工人较少。报社领导宣布:由我领队,出任大公报社农场场长,农场由报社经理王柱国领导,有事也可直接向社党组报告。
我受此重托,毫无思想准备,可以说是“赶着鸭子上架”。能否完成全社交付的任务?既无把握,也没信心。我想起胡适先生的两句诗:“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1960年初春,天气异常寒冷,30名抽调人员除留下一人做联络员外,全部人马携带着行李,开赴荒原。
当我们到达距离文安县苏桥镇十华里的一个荒村时,满眼残垣断壁,有屋无门窗,有路无人行,没有烟火,村里找不到一点木料,我们只好用纸板遮住窗户,找来破雨布做门帘,幸好有土炕,可以作为宿舍;在另一处较大的房屋里,埋锅造饭,就是伙房,副领队杜友良等三人掌管炊事,其余人员下地劳动。大公报社农场就这样草草在文安洼安营扎寨了。
洼地变良田
批给我们的荒地在村头南面五华里以外。我们原以为在这大平原上,有一台拖拉机,便可以畅行无阻地驰骋开垦了。报社答应随后送一台大马力拖拉机来。谁知,当我们一行冒着早春的冷风细雨,来到地头时,又是一惊:这哪里是可耕地?竟是大坑连着大坑,小丘连着小丘,坑坑洼洼,有的坑里还有积水,难以下脚。原来,灾民无以为食,便在大水刚退去时,纷纷来此挖掘一种叫“地梨”(即“荸荠”)的植物充饥,挖出了难以计数的坑,堆起了难以计数的土丘。
这样的地形地貌拖拉机如何耕作?一项急迫的任务是平整土地。从下地劳动第一天起,我们便操起铁锨和耙子,连片修整这块坑洼不平的土地。面积这样大,20多人撒在洼地里显得那么渺小;任务这样重,委实使我们有些力不从心。大家不断遥相鼓劲,一定要在春播前“把这块难啃的地拿下来!”
村里既无人烟,更无任何娱乐设施,没有电灯、电话,连个收音机也没有。我们每天除了三餐粗茶淡饭,下地干活,便是倒头睡觉。一天下来,累得贼死,连“摆龙门阵”的兴致也没有了。生活枯燥,索然乏味。看到这个情况,我有些着急,便发动大家每人每天讲一个笑话,或破一个谜语,以活跃气氛;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动员大家写稿,由美术编辑策划,以《春泥》为报名,出版了一期图文并茂的壁报。还搞过一次歌咏比赛,有人唱歌五音不全,大家听了哈哈大笑。通过组织这些活动,沉闷的情况稍有改观。
荒村附近的苏桥镇,在大清河畔,是个水陆码头,还相当繁华。周日允许人们去苏桥赶集,购物或打个“牙祭”。每月可以回京一次,休息四天,交通工具自行解决,大抵是起大早,步行20华里,到霸县(今霸州市)汽车站乘车。平时不准请假。
从报社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拖拉机开来了。经与给排水设计院农场友好商定,由他们出司机和犁铧等机尾附属设备,先为大公报社农场耕地、播种,然后给他们农场耕地、播种。又经多方求教和征求意见,决定播种玉米和黄豆,三垄玉米和三垄黄豆间作,有利于通风和光合作用的发挥。当看到铁牛在用我们双手平整过的土地上奔驰往返时,大家个个心里乐开了花,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
随着拖拉机耕作的头几天,我特派报社印刷厂的刻字工人杨广才跟车学习开拖拉机,他年轻、聪明、灵巧,很快就学会了。后期的拖拉机就由他驾驶了。
荒原上渐渐有了人气、生气,逃荒在外一年多的灾民陆续从内蒙古和邻县返回,荒村开始热闹起来了。特别是小孩子看到过去少见的大拖拉机,又新奇又欣喜,都围着机身玩耍。6月末或7月初的一天,突然传来了噩耗:一个五岁多的男孩在杨广才驾驶拖拉机倒车时被压
死了!
“大公报的拖拉机压死人了!”乡亲们愤怒地呐喊着,遇难孩子的父母嚎啕大哭,抱着鲜血淋漓的尸体往自家奔跑,村里群情激愤。消息传来,对我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事起突然,我简直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不知如何
是好。
我和副领队杜友良等赶赴遇难孩子家中请罪,吃了闭门羹。一家人扬言不活了,要自尽。我们心情更加紧张,赶紧请村里大队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加以调解。由于事出意外,为了避免再出乱子,杨广才躲避回家了。
当地村民也善良厚道,遇难孩子父母经多方劝解,终于与农场达成了谅解:由农场购置棺木,并负责葬埋,赔偿了三万元。这次事故,让我们多日未曾消停,不知费了多少口舌,陪了多少笑脸,请了多少次罪,伤透了
脑筋。
使出浑身解数克难关
玉米、黄豆播种后,不久就出苗了。机播的苗较密,需要间苗,间苗需要劳力,我们人手不够,20来个人就是昼夜不合眼奋战,也是无法完成的,便多次向王柱国经理请求援手,报社抽不出人来,他也为难。勉强派来了7个人,干了10天,算是暂时缓解了人手之缺。后来,连下几场雨,草苗齐长,需要除草,需要劳力,报社这回真派不来人,我们干着急,没办法。接着,大片庄稼快成熟时,每天丢失粮食,迫切需要来人护秋,还是派不出人来。面临无人可以支使的情况,作为一场之长的我,简直是五内俱焚。
对中央机关来文安办农场,文安县政府很重视,当时作为一个贫困县,他们衷心希望各农场能给县里以帮助。县政府召开过两次农场场长会议,第一次是让各单位汇报对县里能支援点什么,轮到我发言时,我诚恳地说,报社只能支援点报纸,再无其他。各单位农场场长同样也都诉苦。这次会县里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可以说是不欢而散。第二次县里要兴修一条水渠,给各农场分配任务,限期完成。大公报农场被分配了一段挖渠任务。虽然农场人手有限,终究不敢有违县里命令,比那财物支援容易许多,我们派人员出工完成了修渠任务。
荒村复员,百废待兴,困难不少。一日,村里大队长约我和杜友良到大队部谈话。几句寒暄之后,队长开门见山说:“你们在这里半年多,村里的苦难你们是亲眼所见的。村里连电灯都没有,现在县里给了电杆,已在栽插,可是电线尚无着落,你们农场能否支援我们电线?”听后,我和友良面面相觑。农场哪有这笔经费?我俩只能说农场穷苦,开支有限,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实无此能力,请求谅解。最后,我们只有推托向报社领导请求支援。报社最后并未答复。这就给后来秋收时庄稼大量丢失埋下了伏笔。
中秋节快到了,我和杜友良商量,农场使用了村里的土地,需要得到村里多方的照顾,这次村里提出的请求,我们没有兑现,现在过节了,需要对村里略加“表示”。于是到苏桥镇买了两斤月饼和两瓶白酒,送到队长家中。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礼尚往来”了,可是,以后在历次运动中,都把这事上纲上线说成我“腐蚀农村干部,梦想复辟资本主义”,任你有嘴百口,都无法洗清自己的“罪名”。这也是后话了。
夏天,我们赤身露体日夜穿梭在千亩青纱帐里干活,被玉米叶子刺得伤痕累累;入秋后,夜风冷嗖螋,让人感到透骨寒。庄稼成长一度呈现旱情时,我们翘首云天,多么希望有一块云彩能带来甘霖啊!当秋雨连绵时,我们又提心吊胆,唯恐再来洪水,冲毁我们好不容易种出来的庄稼。
最让我们心痛的是,四周逃难返乡的乡亲,看到庄稼快成熟,便三三两两前来“偷秋”。我们的护秋队人员太少,防不胜防,即使见到,也只能劝说离去,没有其他办法。如此损失的粮食,当不在少数。穷苦的乡亲们看见自家土地上长成的庄稼即将被外人掠走,更是眼红,于是他们暗中串连,集体劫粮,成片的庄稼被洗劫一空。当时护粮与“偷秋”的矛盾一度十分尖锐、紧张。由于我们忍让,幸好未发生大的冲突和事件。
不辱使命获丰收
历经八个多月的艰苦奋斗,金秋收获季节终于来到了。那年,属于中等年景,眼看着金黄色的玉米和黄澄澄的豆荚俱已成熟,消息传到北京,报社人员极大兴奋,国庆节前,搞了一次秋收“大会战”。
这次报社借调了十多部大卡车,组织了50多人的收秋队,报社党组成员、经济部主任胡邦定、记者部主任姚仲文、出版社副社长阎达寅和王柱国经理等率队,浩浩荡荡来到农场。他们目标明确,下车就收秋,只要粮食,不收秸秆,有的掰玉米,有的收豆子,有的运粮,有的装车,人虽多,嘴虽杂,但忙中有序,忙而不乱。天黑,十多辆车俱已满载,为避免有人中途劫粮,直到午夜才陆续发车。
大部队走后,我发现尚有81亩黄豆没来得及收获,便决定次日由农场常住人员收获。谁知次晨起床发现,大批村里人已把这一大片黄豆抢收走了。我气急不过,连忙给县政府写了报告。事后有同志笑我十足的“书
生气”。
1961年元旦前,经过脱粒晾晒,实打实收实测,农场共收获纯粮十余万斤。报社有了这批粮食,员工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我卸任回报社,算是交了差,立即投入采写活动之中。事后,王柱国经理告诉我,农场账目已经财会人员审计检查,结论是“账目清楚,勤俭办场”。我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报社交给我的任务。掐指算来,事情已过去50多年,但这一经历,点点滴滴印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