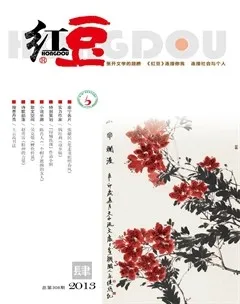在洱海的时光
2013-12-29林虹
在鲁迅文学院西南青年作家班学习,幸福得奢侈,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美丽的洱海、苍山。黄昏沿着洱海边散步,垂柳,微风,晚霞,暮色,岁月静好得有点不真实。寂静的夜里,听得到马车的铃铛叮当叮当地响,似乎是从唐宋诗词里走出来般。因了这种慢时光的影响,我也是慢悠悠的,因此被周同学称为林慢慢。呵呵,这不是我的小说《清澈》里的主人公吗?徐慢慢,一个推崇无痕生活的聪慧女子。姑且照单全收,遂又被韦同学等称为小慢。
在鲁西南班,我似乎是隐形的,为此,西藏的同学琼吉说我很淡。我对她一语中的评价很惊讶,因为我们并无太多的交流。也许本性如此,我对谁都是淡淡的,不过分热情也不淡漠,一种本真的生活状态。这和白描副院长在开班典礼上说的,要我们同学之间相处要快热,不要慢热是背道而驰的。不过,我仍愿意遵循我的内心生活。
那段时间,除上课,我就伏在房间里写小说,时间于我,总是太少。我觉得有点苛刻自己。但我知道,这段清静的时间很难得,我将远离我的生活、工作,进入一种禅道的境界。班上四十一个同学,来自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广西,都是在文坛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因此,有点彼此相轻的感觉。我倒没有,我喜欢隐和无痕,这种张和徐慢慢的生活哲学,除在我的小说里体现之外,我也将它们延伸至我的生活。更或者,它们的呈现其实就是我的内心呈现。由此,我也推崇仓央嘉措的诗:不要在人群中,说出咱俩的秘密,你内心如果有深情,请用眉目传递。爱和尊重,才是真爱。由此,尽管张的隐是伪道德的隐,我也依旧认为他是真实的。
第一节课是白描副院长的《优秀作家素质解析》,觉得这样的题目想着会枯燥,但听起来却津津有味。我坐在第一排,全神贯注,听入迷了。白描副院长是陕西人,很有陕西汉子的味道,就是那种朴实的、敦厚的,又像风一样辽阔、通透的。白院长选了陕西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三位著名作家来解析优秀作家的素质,从他们的生活背景到写作背景再到文本,脉络清晰,极具文学魅力。
比如贾平凹从商州的山地出发,路遥从陕西的高原出发,陈忠实从关中的平原出发,这些不但是他们的创作出发点,也是他们一直坚守的艺术领地。这些土地是连接他们生命的脐带,也是他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通过三位优秀作家,我们了解到了优秀作家具备的素质,除必须勤奋地创作外,要有诚实的劳动态度,也要有丰厚的美学修养和强烈的超越意识。他说文学作品就是从作家人格之树上生长出来的叶子和花朵。他谈到文学的终极较量,是和自己较量。我很喜欢他的这种说法,真切领悟了“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这句话。
在学习期间,印象最深的是毕飞宇老师,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推拿》获得这届的茅盾文学奖,又因为他长得帅和高大,因此,人气很旺。记得那天清早,我们在餐厅吃早餐,透过透明的玻璃落地大窗,看见毕飞宇老师从车上下来,藏青的牛仔裤,格子蓝的T恤,近乎光头的小平头,五官很江南和东北,既硬朗又温和,且有阳光的笑容,就听到有女同学说,哇,真帅!呵呵,当然当然,也包括我啦。又听到一女同学说,毕老师把才气和帅气都占尽了,还让人活不?这话自然是转载别人的。由此,毕飞宇老师是偶像派和实力派的。不过这样的男人,其实是个深情的男人,在课堂上,他多次提及他的妻子和儿子,在写作的状态上还引用了妻子为其整理行李这一细节,可见其感情的纯粹。
毕老师谈及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说要以小见大,比如一块羊肉,要让人注意这块羊肉,最简单的是用火慢慢烤,味道就出来了。真喜欢他这个比喻,慢慢散发的味道,小说要的就是这种调子。他说到,真正的好作家是有趣味的,可玩的,可爱的。比如他写小说,用的是玩字,真是大师的语言。毕老师说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就和它玩,一些可爱的有趣的地方都是和小说玩的过程中发现的。毕老师说的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玩,就是端详、发现、修改,仿佛雕玉一般。我愿意是这样理解的。
徐坤老师是我期待的,还因为她是唯一的一位以女作家的身份来讲课的。我对徐坤老师的印象,最先来自她的小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学者派的写作自是不同一般的,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叙事风格,抑或是情节安排。印象最深的是结尾,男同学终于得到了高中时代追求的女同学,亦不过如此。真是让人悲凉和丧气。为什么要这么狠嘛?把生活撕开,把人性里的本性撕开,还让人憧憬什么呢?可现实不是这样吗?我就这样记住了徐坤老师。暗地里猜想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女子,大气、豪爽,有江湖的味道。
后来,看徐老师获鲁迅文学奖的《厨房》,女性文本的小说,相当有代表性,结尾也是悲凉和心酸的。那袋从男友家里带出的垃圾,寓意很多。由此推及,女人对爱,要矜持,不能太主动,当然,这要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才能凯旋而归,否则就是相反。小说讲叙的就是这种相反。一个被男人拒绝的优秀女人,在深夜拎着一袋从男友家里带出的垃圾,那种落寞的背影,真是让人回味。正如徐坤老师说的,女人过了四十,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越来越少,女人有点迫切。我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遂又在猜想徐老师是个长相妩媚,美丽温情的女子。
那天见到徐坤老师,皮肤白皙红润,高贵优雅,美丽大方,眼睛清澈有神,笑起来无邪和干净。真是奇了?和我后来的想象还是很接近的。徐老师说话就像春风拂过,很有亲和力和感染力。徐老师是鲁一班的学员,所以,她让我们叫她师姐。呵呵,一点距离也没有。徐老师讲的是《刀锋上的写作》,单看题目,就很期待了,终于听到徐老师讲叙她怎么写《狗日的足球》和《厨房》了。《厨房》的结尾,女人提着的那袋垃圾有了新的诠释:女人都是带着情感的垃圾上路的。这也包括她自己。徐老师说十年前写《厨房》时压根就没想到十年后的事,十年后,她最终也成了那个带着情感垃圾上路的女人了。单身了。但看不出她有半点这种婚姻失落的阴影,一个聪慧的女人,是有能力让自己过得好的。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一段话,她说,女人到了四十多岁,可选的东西越来越少,那就把自己选择的路走好、走通、走顺。还有她给我们的话:把文章写好,来认同自己的命运,打点好自己的生活,再来写作。
“短篇王”刘庆邦老师也拥有众多粉丝,他的讲课也是很受用的,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写短篇的人来说。刘老师讲叙的是《小说的虚和实》,用了他的中篇小说《神木》来解构。由《神木》改篇的电影《盲井》在中国禁映,在国外却获得了很多奖项,影响很大。小说由现实的题材改编而成,如此赤裸裸的现实,让人触目惊心,感叹世态的炎凉和人性的缺失。大师的写作,选取的写作角度都是很有吸引力和张力的。印象最深的是刘老师在讲到他小说的某个情节时,露出害羞的神情,可爱得很。年近六十的刘老师,还是如此本真,真是难得。
对施战军副院长的印象,是他的歌声。这个高个子的北方男子,长得刚毅和帅气,如白杨般挺拔。刚开始讲课时,我觉得是那种领导式的,可是循序渐进,施院长越讲越生动,期间还唱了一首蒙古的歌,歌声高亢和清冽,让我们耳目一新。原来这位年轻的副院长,这位著名的评论家身怀绝技呢。真正长见识的还在中秋晚会上,他的歌声让学员的脚步无法移动。当时我坐在他后面,看见他也和我们一样狂热,用手拍着桌子打节奏。郭艳老师上去唱黄梅戏《女驸马》选段时,施院长也敲着桌子跟着大声唱,全然没有领导的风范。晚会结束了,还有西藏的同学要唱歌献给他,可见施院长的魅力和亲和力。我们私下感叹,上帝怎么可以这么偏心?给其如此多的才华?离开的那天清晨,我们在洱海边送老师们去机场坐飞机。洱海一别,不知何日再聚?离别的愁绪如洱海的水轻涌而来。施院长和同学们一一握手告别,经过我时,我上去拥抱了施院长,轻轻的,以一个朝圣者的圣洁之心。想起施院长曾说的,鲁院在任何一处。是的,是这样,鲁院对于一个文学的朝圣者来说,它在任何一处。
李蔚超老师是后一阶段的带课老师,年轻美丽,五官精致。她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总结、梳理授课老师的讲课内容很到位,很精辟,显示了她北大博士生的深厚的文学功力。这样一位才女,有着江南女子的温情,在结业晚会上,她说起在鲁迅文学院带课的感受,说到动情处,哽咽着,泪流而下,让我们也眼角潮湿。她唱了一首英文歌,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我们知道,那是她心底流畅的情绪,寄予我们将别的时光。前一阶段带课的陈涛老师回去了,他年轻、阳光,笑容清澈干净,像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他在鲁院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有次闲聊,我以为他不知道我是谁,同学那么多,他不可能一下记住的。他说,我记得你,在课上自我介绍时,很特别。我才想起,我用客家话介绍,后又引用了小柯的歌《多好啊》来总结。我说,我想用小柯的歌《多好啊》,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多好啊,我们在洱海边相遇!
胡性能老师,是我们班主任,也是云南作协的副秘书长,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在温暖中入眠》、《有人回故乡》,是鲁十四班的学员,说来也是我们师兄了。他长得俊朗儒雅,性格温和宽厚,淡淡的,喜欢穿牛仔裤和格子衬衣,很年轻,但近看,居然也有了白发,想来也是被时光染白的。他的小说《下野石手记》发在《十月》,后被《小说选刊》选载,我们在报刊亭看到他的名字,觉得很亲切,杂志买回来,争着要拜读。胡老师为人很好,为了这期培训班,他很辛苦,要管理班级,又要接送授课的老师。
对胡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歌声。在去洱海县梨园村采风的路上,同学们一路玩击碟传瓶的游戏,结果,我第二个就中招了,上去用客家话读了一首《月光光》的儿歌。后来,轮到胡老师,他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唱的是云南的民歌《小河淌水》,声音浑厚宽越,旋律优美动情,同学们都跟着唱。又后来,是在晚会上,他唱了一首韩国的童谣《三只熊》。他说,他以前不善唱歌,后来去鲁迅文学院学习后,才学会唱的这首歌,接着开始唱,有点害羞的样子,模样可爱有趣。我也一直记得一幅像油画一样的情景。某天晚上,我们在餐厅吃饭。那时,暮色降临,透明玻璃大窗外的洱海是深蓝的,暮色也是深蓝的,海边的垂柳也是深蓝的,我从没看见这样的情景,胡老师和李老师站在窗前,他们在聊着什么,我觉得有点像电影的画面。
还有丹增老师,张清华老师,李建军老师,叶梅老师……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文坛的大腕,能听到他们的讲课,不能用受益匪浅这个词来简单概括的,我将珍惜这段生命中特别的时光。
关于同学,印象最深的是阿黛,喜欢穿民族风格的棉布衣裤,而且是花色很鲜艳的,戴着个民族风格的帽子,很远就能看见她。阿黛毕业于某大学的音乐系,却爱上了写作,辞职前是某杂志的记者,后辞职深入泸沽湖的摩梭族,写下《摩梭密码》的长篇。她说学习结束后,继续回泸沽湖,开始写第二部长篇。一个文静柔美的女子,放弃城里优越的生活条件,就为写作,我为她的勇气所感动。
窦红宇是我们的班长,说来好笑,开班几天了我都不知道他是班长。有次他跟我打招呼,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旁边的一位同学说,不会吧,林同学,你连班长是谁都不知道啊?窦班长刚在《十月》杂志发了个长篇《青铜》,就被改为电视连续剧了。他戴着眼镜,好像有胡子,呵呵,没注意看。总之很艺术的样子。
顾野生是我的同桌,她来自西藏,80末的,很年轻,长得很漂亮。但她不是西藏人,是广东的。她没上大学就带着把吉他,行走墨脱支教了,最后在西藏电视台工作。她写下《朝圣》一书,有个性,既婉约又时尚,写作的时候抽烟,喝酒。中秋晚会她是导演,弹唱了自己填词的《生命中的二十一天》,一个如花盛开的女孩,和我一样是客家人,她说西藏是安放她身体和灵魂的地方。
樊忠慰,一个用生命写作的诗人,被誉为中国当代诗坛的传奇人物,“中国诗坛的梵高”。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患了“思想鸣响”这种诗意的精神病,但他勇敢地面对生活,用诗歌去拯救自己。他的诗歌是会飞的,因而他是唯一的。我记得在和大理文学院互动时,班主任胡性能老师谈及他的诗歌,还朗诵了他的代表作《悬棺》:“我没去过这地方/我不想去,去了,也看不见/看不见时间打败的英雄/流水带走的美人/大风吹散的文字”。回来后,收到樊忠慰的诗集《家园》。想起在学习时,他就住我隔壁房,只是见面时打招呼,并未交谈。记得那天,我写完一段文字,就到屋后的山去散步,看见他从山上下来,告诉我,山顶有只狗,叫我不要上去。我记得他穿红色的开襟布衫,像他的诗。
还有西藏的琼吉,云南香格里拉的央金、怒江的马瑞玲,贵州的巴文燕、邓君……
四十一个同学,有四十一个印象,他们都在我的记忆里。
学习回来后十多天,我去南宁开会,接到鲁十二班严师兄的电话,说鲁院的郭艳老师在南宁,让我开完会过去一起吃饭。原以为见鲁院老师的机会很少了呢,没想到一个月能见两次。见到郭老师,她依旧高贵优雅,温暖亲切,谈及她唱的黄梅戏《女驸马》,谈及鲁西南作家班,那些时光仿佛从未消逝。是的,是这样。我们在彼此的祝福中一致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