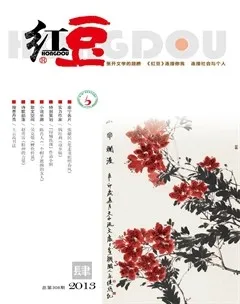土家二题
2013-12-29谢德才
土家人
土家族人爱喝酒。包谷烧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到山里伐木料,腰杆上常常吊着一酒壶,什么时候想喝,就拖出来品上一口。在田间插秧,累了,就抱着酒壶饮。他们喝酒,不在乎人的多寡。有朋友在一起,喝的时候,相互敬;没有朋友到面前,就左手碰右手、右手碰左手,一个人自由地品。他们喝酒,从不在意菜的多少,一个辣椒也可成为下酒的菜,给辣椒尾巴沾上一点盐,就可以喝半天。他们真正在乎的是酒的分量,如果杯子小了,就端着碗喝,用碗不过瘾,就拖出土钵来喝。他们喝的往往不是酒,是感情,是热情,是激情,一举杯,一饮而尽。一杯完了,二杯再来,二杯完了,又来三杯。宁愿伤身体,不愿伤感情。说来还真有趣,一个土家汉子与朋友就着呼呼的火炉在一起喝酒。别人刚喝一口,他却主动喝上几口。这个土家汉子微醉,伸筷拈菜,却把筷子伸到自己面前的烟灰缸里,肉没拈上,而拈上烟蒂。嚼啊嚼,他觉得不对头,立即喊来老板:“你这肉怎么这么硬?”老板心想,这是自己刚从冰柜中取出做成,怎能?当酒醉者从嘴巴中吐出一团东西后,一桌人才露出哈哈的笑声。笑得眼泪鼻涕一把把地往外甩。
土家族人爱唱歌。桑植不大不小也有三十多个乡镇。乡乡有山,镇镇有水。山与水的融合,亲如热恋中的一对,哪里有山,那里就有水。这里的山水,点缀乡村的一片美丽,造就山里人唱歌的背景。他们从不吝啬自己的嘴唇,对着大山唱,山那边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迅速给予久久不息的扣人心弦的回音。烧火土粪时唱,歌声像村庄炊烟一样冉冉升起,好像要触摸海水一样美丽的蓝天FoSK86/BnhDnbr6isQuonw==和没有穿裤子的白云。对着水唱,水马上睁开自己的眼睛,暗送秋波,从内心发出“哗哗”的笑声。生活在澧水河边的土家族人,歌像他们的生命,一天不吃饭行,但一天不唱歌,会感到力不从心。不知他们从哪来的那么多的歌声,家家都能喊出调子,个个创造原声。山里人的爱情,不少由歌声编织而成,什么“鸳鸯枕,荷花被,被子盖哥,哥盖妹;龙凤席,红木床,席子垫妹,妹垫郎”等,情意绵绵,还有“山是万宝山,地是刮金板;树是摇钱树,人是活神仙……”这就是土家人自编自导自唱的响彻神州大地的歌声。当你走进如画的桑植,歌声马上涌入,如Q75TRNeVx6vZm3bFzpI3JQ==同山中的绿一样,热情地把你围紧,让你久久欣赏,令你如痴如醉,醉得你半天回不过神来。
土家族人爱跳舞。“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可见,土家歌舞之恢宏场面。跳舞,也是一种享受,如美丽诗歌一样心旷神怡。四十多万人的桑植,会跳舞的,占绝大多数。土家族人,舞瘾十足。他们跳舞,不需要专门的舞厅,露天舞台也行,哪怕只有放脚的地方,舞蹈也会马上诞生。土家人在山里干活,采下一片树叶,抓在手中,一扬,舞蹈如机器一样转起;点上一支香烟,衔在嘴里,屁股一扭,舞蹈如雨水点在河面跳起;邀上一些同伴,走在一起,手一牵,脚一提,舞蹈如爆米花般蹦起。在桑植一条绿得不能再绿的河水边,躺着一个不大不小的民歌广场。这个广场,生下来,就没有被寂寞占领,最喜欢热闹,一点也不爱安静,一天到晚人不断,吹拉弹唱的,应有尽有。住在乡里的土家人,只要手头的农活一完,扔掉锄头,跳进城里,其他地方都不愿去,唯独这民歌广场像一块磁铁而强烈吸引他们。尤其是在晚上,民歌广场就成了舞蹈的海洋。一屋屋的土家人,吃罢晚饭,出门,少数乐悠悠地登登梅家山,其他的都主动来到这里。无数个黑点把整个广场挤满。他们跳着摆手舞,一会儿单摆,一会儿双摆,一会儿回旋,动作相当逼真,刚柔相济,粗犷雄浑,舞姿极其优美,展现出了民族迁徙、狩猎征战、农桑绩织等一幅幅富有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的艺术画卷,震撼人的灵魂。
土家族人,爱酒、爱歌又爱舞,爱得是如此真诚又深沉。
覃老先生
我写的“覃老先生”,大名叫覃永辉,笔名叫“覃葛”。这个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家老汉,活跃在大湘西的“土记者”,乃贺龙元帅故乡桑植人。称他为“覃老先生”,其实他也不是特别老,因为退了休,一些人出于尊重,便有这样亲切而顺耳的称呼。说实在的,他没留一根胡须,腰不弓,背不驼,也不像我们年轻人早在鼻梁上卡上一副眼镜。他走路少有碎步,牙齿没缺,吃起硬点的东西,也可嚼个稀烂。
覃老先生,我认识他时,他写点土家人的小稿子,相当投入。后来,我调进了县城,与老覃见面的机会自然多起来。在街上遇到他,他隔老远就招手:“小谢!”我离老远也喊他:“老覃!”一见面,他说这里声音嘈杂,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讲话,那一坐一讲,就是老半天。
老覃穿的常常不是解放鞋就是草鞋。一看到他那双草鞋,立马想起祝勇《草鞋下的故乡》中的许多片段,老覃的草鞋上也渗有浓浓的泥土气息。在桑植大街上,如果你见到戴着一顶蓝色布帽,背个背篓,臂上挂个“为人民服务”字样黄布包的人,你不用去猜测,这个人绝对不是别人,一定是老覃。
老覃进城来,背篓里常装的是熟透的橘子或者梨子,或者自家产的还冒热气的包谷粑粑。他把背篓往文友办公室一搁,好吃的东西亮了出来,大家吃得香喷喷的。吃完香的甜的,还有回味的,他马上又从包里扯出折叠好的报纸或者杂志,说:“秀才人情纸一张,这是我近期发表的作品,大家看一看啊。”大家品啊品,尝啊尝,品尝出老覃这个土家人不简单,真是“文武双全”!
老覃能文能武,说他能“武”,并不是指老覃有武功,嘴巴能咬断钢筋,手可推垮墙壁,腰能撑上千斤,而是他在耕种庄稼这方面,确有几下子。
在老覃家里,有几亩薄田、几亩山地,全由他一人耕耘。他喜欢“刨岩壳”,不像农村有的人蜻蜓点水。他如写文章一样精雕细刻,把大块大块的坡地变成平地,不让一根杂草在庄稼地里作怪。犁田的时候,老覃几乎是让耕牛自己行走,即使用鞭子抽,也是象征性的,没有一句吆喝声出现。耕牛也顺从他,行走在他的面前总是规规矩矩,速度不慢不快,也不带一点眼色。老覃什么时候放下犁辕,这牛就任劳任怨地犁到什么时候。凡经过他的手长起来的庄稼,过路的人都会多注视几眼,说:“这庄稼,长得太好了!”
在他家吊脚楼的阶沿下、阳沟坎上,都有他亲手栽种的果树。那些果树好像懂得知恩图报,该开花的时候,努力地把大片大片的花开出来;轮到挂果的时候,果实把树枝都压得弯弯的。老覃也有趣,我常给他拨打手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哈哈,我正在摘玉米啊、踩田草呢……”我怕打扰他,想少说几句,他却说,你只管说。他一手热情地接手机,一手不停地干农活。摘啊摘,踩啊踩,从他生命的内部跳出一句又一句极有想象力的诗!
覃老先生,不仅爱作诗,也爱写点散文。他写的散文,数游记最多。人说“生命在于运动”,他做到了。名胜风景,只要一天能赶回的地方,就是凌晨一点出发,他也得去找找那里深藏着的美的感觉。他去观看过气势雄伟的矮寨大桥,游览过文学大师沈从文笔下的茶峒,品尝过刘晓庆在王村吃的米豆腐……一溜,一看,一尝,感觉如泉水一般猛地涌入老覃的脑际。一回家,他就趴在八仙桌子上沙沙地写成文章。他写东西,跟著名作家贾平凹一样,不用电脑,好几屉子的稿子诞生,都得感谢自己的拇指与食指和中指的耐力。他写的《吊脚楼里的戏台》曾在《人民日报》国庆40周年“民族、团结、进步”征文大赛中获三等奖。他那些朴素而真实的文字,记录的都是土家山寨里野山笋一样的新鲜事,或者是县城里各单位里民族团结和谐的好人好事,或者是贺龙元帅的传奇故事。这形成一种记忆,种在朋友的心田里,也种在如潮水一般涨落的时间里。
老覃的父亲今年95岁高龄,脸上爬满贮有诗意的皱纹。老人家过着“种豆南山下”的田园笔耕生活。他父亲的诗,也是从生活中流出来,从感情中流出来,从哲理中流出来,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的步沈鹏先生《腕底》原韵,就是一气呵成:“笔扫千军那得停,经纶满腹一文星。四诗群怨兴观颂,几度纵横捭阖情。江浙斯时悬素日,梦魂此夕锦添萍。佳章读罢欣然喜,愿与先生骥尾行。”老覃的大儿子覃代伦研究员,游走全国美术界和文博界,书写得好,美术评论写得酷,散文也写得棒!他在《走玩大湘西》中写道:“湘西在哪里?”“湘西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湘西在宋祖英的歌里,湘西在黄永玉的画里,湘西在贺龙的枪杆子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先生为老覃家题词“耕读人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古建筑大师罗哲文先生也为老覃家题词“茹古涵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先生录其父老舍先生名句“有朋相亲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题赠老覃家;中国少先队队徽设计者刘恪山先生为老覃家治印“天子山下人家”,还刻赠堂号“浴德草堂”闲章。这是大师们对他们祖孙三代为诗、为文、为人的激扬。
老覃爱交朋结友,与他交流,感觉如溪水一般的纯与洁。一些同性、异性的文友,无论老少,都喜欢与他亲近。他每年自费征订大量报刊,《张家界日报》从创刊到现在一直没有中断过订阅,还征订《清明》等十余种文学刊物,常向文学朋友赠送和借阅。文友的文章上了报,登了杂志,只要他看到,他都会打去电话,送上诚心的祝贺。他的祝贺,不是单纯的“哎呀,文章发表了,挺好啊”之类的话语,而是像一个评论家走进作者创作的思维空间,表扬的话固然存在,不足的语言也不是只字不提。在老覃家一个老得掉牙的木柜中,珍藏着许许多多报纸和杂志,文友寻找自己发表的作品,到档案室寻觅不着,可往他家一跑,一翻,竟翻了出来。一翻出来,覃老先生先笑了,找文章的朋友也哈哈大笑。
接近过年的时候,按土家族农村的风俗习惯,平常喂得肥壮的猪到这个时候就该宰杀。他家杀年猪的那天,天一亮,他就跳下山坡,租辆面的车哒哒哒地开到县城。然后,拨通一个个先前约好的文友。人一等齐,车里唱着歌,哐啷哐啷地进了他家村寨。文友在他家吃“杀猪饭”,围在一起品酒,老覃敬文友酒,文友也敬老覃酒。一切情谊尽在白酒中。文友们返城,老覃连扔下手头的活儿,跑出来相送。他站在山坡上,双手围成喇叭状:“慢慢走啊,朋友们!文学是心灵的回声,是通向高尚情操的桥梁,愿大家多架这样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