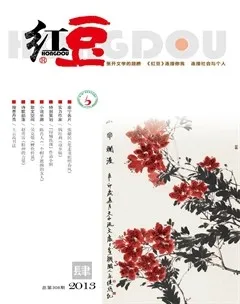鲤鱼传说
2013-12-29吴克敬
传说是有条件的,浦源鲤鱼具备传说的所有条件。
寻龙先生(风水先生)在纯池村松杨溪找到一穴鲤鱼朝天的风水宝地,他自己不敢享用,却推荐给纯池村的大财东、大善人徐翁。徐翁人是不坏,可他娶了个刁钻的婆娘,屡次玷污鲤鱼朝天的美穴地,使此地风水大坏。美好的鲤鱼不堪忍受玷污,在徐翁婆娘破穴之日,羽化飞天……乙丑年秋染周宁,我随《福建文学》编辑部组织的采风团来到这时,听得最多的,都是关于鲤鱼的故事。我听他们说,听不明白时自然是要问的,问不出所以然来,就只有传说了。我不知他们传说“羽化飞天”的鲤鱼去了哪里?但在他们的引导下,去了青山掩不住的浦源村,见到鲤鱼溪里悠然潜翔的众多鲤鱼时,我相信“羽化飞天”的鲤鱼,肯定是到这里来了。
鲤鱼来了,这条原名浦源的溪流便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鲤鱼溪。
不只我喜欢鲤鱼溪这个名字,八百年前辗转迁徙到这里的郑尚公就一定也被这个美好的名字所迷惑,而歇下他移动的脚步,在这里开始了他们郑氏一脉的生息衍进。
这位郑尚公可是不简单哩。南宋嘉定一朝,他官拜开封朝奉大夫,很体面地娶了一位皇家公主,但他生性淡泊,且又遭逢战乱,就从他祖居地河南荥阳举家南下,蹉跎寻觅到了鲤鱼溪,看见溪水里悠然游动的鲤鱼,他笑了。我相信,郑尚公带着他的公主夫人,还有他的血亲子女,人困马乏的那一笑,该是怎样的会心呢!
会心的人把鲤鱼神化了,以为鲤鱼就是“三仙姑”的化身,来拯救落荒逃难而来的郑氏血脉了。
郑尚公落脚在鲤鱼溪畔,他为自己和家人立了一条规矩,宁肯饿死,绝不食鱼。他所以订立这样一条规矩,有他心头一个不能抹去的阴影,他是驸马爷,他没法逃避大内的眼睛,大内之中有太多的尔虞我诈,有太多的阴谋诡计……郑尚公和他的公主夫人,逃离了大内的繁华和富贵,却还担心大内之中的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他定下规矩不准家人捕食溪水里的鲤鱼,是要仙气悠然的鲤鱼护佑他们郑氏血脉。
鲤鱼的护佑是具体的,优游在溪水里的鲤鱼,天然地可以起到澄清溪水的功效,有鲤鱼在,溪水便是纯净的,放心的……鲤鱼和郑氏血脉,就这么坚定而和谐地衍生下来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溪水里的鲤鱼生生不息,溪水畔的郑氏血脉亦然生生不息,从最初的郑尚公一门,呼啦啦传了八代。此一时期,郑氏族生晋十公者,他感激鲤鱼功劳,带领郑氏族人,拓宽溪道,沿溪建房。晋十公设计拓宽的溪道为“丁”字型,他的用心是明确的,“丁”字溪道既寓意了他们郑氏血脉人丁兴旺的一种诉求,同时又使溪水里的鲤鱼遭遇山洪冲击时,有个藏身遮体的港湾。
晋十公护鱼、敬鱼的措施还不只拓展溪道一役,他把传说“羽化飞天”的鲤鱼,也确立为神鱼“三仙姑”。晋十公给族人宣传,敬鱼者随时能够逢凶化吉,偷捕鱼者会降灾得疾。
后来发生的故事,也很神奇地印证了晋十公的宣传。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大总统黎元洪经由浦源郑氏十九世孙郑慕荼、郑敏斋等人呈讫,敬赐了“孝阙流芳”四字匾额,刻石立起一座碑坊,旌表他们祖叔大雅公。这位大雅公为浦源郑氏始祖朝奉公的第十五世孙,他生平急公好义,孝敬父母,曾割股煎药为母疗疾,舍身顶罪代父服刑。相传,明末清兵南侵,南方豪杰多有举旗抗清复明者,福安进士刘中藻(明末兵部尚书,抗清将领。清兵入闽东,刘统兵据守福安三月,城破,吞金殉节。),从北京南下入闽,集结明军数万人,与郑成功联手抗清。刘中藻驻军浦源、周墩。大雅公的父亲方三公深明大义,尽力资助粮晌,支持刘中藻抗清。清顺治六年(公元1849年),清将白进宝从建瓯掩杀过来,在浦源查知方三公倾家资助刘中藻,遂将方三公逮捕送宁德县治罪。时在萌源村岳父家的大雅公,闻迅追了八十里,在七步梨追上白进宝,向他苦求无果时,自愿替父顶罪受刑。白进宝倒也畅快,把方三公身上的镣铐解下来,枷锁在大雅公身上。大雅公是浦源村护鱼、敬鱼的一个模范,鱼仙要显灵救他了,使他天黑路过穆阳溪时,脚下一滑,把人滑落水中。穆阳溪水深数丈,大雅公身受镣铐重枷,想活命是难了。他的身子往水下急速坠落,不偏不倚,落在了一只千年龟背上,驼着大雅公,浮出水面,送他到了人不知、鬼不觉的对岸,躲进一孔天然的山洞里。大雅公知道清兵不会善罢甘休,暂避山洞,眼看着几只白腹黑背的蜘蛛,在洞口紧张地织着蛛网,不大一会儿功夫,就把洞口密密细细地封起来了。清兵搜山而来,看了蛛网密结的洞口,一点怀疑没有地转身而去。
大雅公的这次历险,使浦源郑氏后裔,不仅禁食鲤鱼,以后又加上龟鳖,也是不能食用了。自然,神性的蜘蛛亦成了他们的保护对象。
敬鱼可以逢凶化吉,伤鱼又必遭报应,在浦源关于鲤鱼的传说中是屡闻不鲜的。最近的一次发生在解放后的1976年,是关于一位将军的,因为有所忌讳,不好明说。但闻明朝时,倭人聚众来犯,其中一标浪人从福建海边登陆,烧杀抢掠,到了浦源鲤鱼溪,哇哇乱叫的倭寇看着溪水里的鲤鱼,觉得新鲜好玩,但他们一路作恶,到这里时全都饿了,进到溪畔人家找吃的。他们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人,就把溪水里的鲤鱼捉来吃了。倭寇们捉鱼的方法是残酷的,他们站在水流中,挥舞着手里的弯刀,乱砍乱劈,砍劈而死的鲤鱼浮在浮水上,把水流都阻断了,涌流而出的鲜血,染得鲤鱼溪都红成一片……浦源郑氏民众,躲避倭寇没有躲远,就在附近的山林里,眼看倭寇滥杀鲤鱼,一个个心如刀绞,也不知是谁先冲出山林的,举着锄头向倭寇头上抡去。有人带头,四周避祸的郑氏人家,不分男女老幼,手头有板荡的拿板荡,手头有木杖的拿木杖,全都冲出山林,向施暴于鲤鱼的倭寇冲了去,一鼓作气,把倭寇追撵到鲤鱼溪的下游九龙漈。慌不择路的倭寇跑到这里,还想往前跑时,却有一团乌云飞来,笼住了逃跑的倭寇,笼了不长时间,也就是眼睛一闭一睁的功夫,乌云不见了,同时乌云笼罩下的倭寇也不见了。
善与恶,让鲤鱼的传说更加多了一份传奇。
我不想再传说了。因为我在浦源听到的传说还有一大把,说是说不完了。我漫步在溪水潺潺,古村错落的小街上,像浦源的郑氏民众一样,和这里的鲤鱼来一次亲密的接触。
花红的鲤鱼,青黛的鲤鱼,五颜六色,自由地来,自由地去,“闻人声气往返,见人形影相聚”,彩鳞翻转,翅尾闪光……是一位淘洗鸭肠的阿婆哩,她端着一只瓦陶的盆子,刚在溪水边坐定,才把细柔的鸭肠浸进水里,就有寻着来的一尾锦鲤,叨住了鸭肠的一头,却不吞咽,拽着鸭肠向溪水的一边去了。我看在眼里,以为阿婆是要气恼的,最起码,阿婆该与锦鲤争夺鸭肠的,可是阿婆没有气恼,也没有与锦鲤争夺鸭肠,任由顽皮的锦鲤口叨着鸭肠在溪水里戏嬉……离着阿婆不是很远的溪水边,是位淘菜的小媳妇,她端在筐里的青菜,太南方了,我这个北方佬认不出来,只觉那菜青碧碧的,特别嫩、特别鲜。她端着青菜筐子,下到溪水边,把菜筐往溪水里一推,菜筐便离了溪岸,向小溪深处旋去,我以为那菜筐将溺水不存,却不知在水深处旋了几旋,又往小媳妇的手边旋了来。我疑惑小媳妇有什么特异法力,可以在溪水里自由地收放青菜筐子。我是惊讶了,正惊讶着,即已看见青菜筐子下面,鬼鬼祟祟滑出两条鲤鱼来,在小媳妇的面前且歌且舞。我恍然大悟,小媳妇放进深水里的青菜筐子,是可爱的鲤鱼给她推到手里来的。
多么有灵性的鲤鱼呀,它们都是通着人性的。
我从溪畔人家买了两块“光饼”。这“光饼”与北方的烧饼没有什么差异,所以有个“光饼”的名讳,是沾了戚继光的名头了。他在明朝时候,在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抗击倭寇,浦源的老百姓为了犒劳他,烙了饼食慰问,他食了饼后打倭寇,打得更加有功劳。事后,浦源的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就把他们平常也吃的饼食改叫成了“光饼”。
“光饼”喂食鲤鱼是最合适不过了。鲤鱼溪里的一众鲤鱼,不知可晓得抗击倭寇的大英雄戚继光。如果晓得,话就好说了,它们把自己全都想象成了戚继光,天生地都特别好食“光饼”。我从溪畔人家买来“光饼”后,就小心地掰成碎块,往鲤鱼畅游的溪水里扔。每扔一块,都会吸引无数的鲤鱼,从水下往水面上冲,冲着争食水面的“光饼”。这个图景太迷人了,群鲤惺闪,唼喋之声激烈,喂食的我,脸上禁不住是要笑成一朵花的。
我买的“光饼”太少了,小小的两个圆团,不一会儿就都喂给了可爱的鲤鱼。于是我还想要再买几块的,但溪畔人家不给我卖了。他们说,有个意思就够了。这是什么话呢?我很想与人争辩,嘴张开来,却争辩不出声。因为其时,正值浦源人中午吃饭的时候,溪畔人家的小孩儿,你端着米饭碗出来了,他端着米饭碗出来了,他们星散在鲤鱼溪畔,把他们碗里的米饭,先都毫不吝啬地分出一半来,拨进溪水里喂食鲤鱼,剥下一半,才一颗一颗数着,把米粒吃进他们的肚子里。
《周易·彖传》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享。”浦源郑氏,用他们八百年的毅力,诠释着至为难得的一个大道理:天人合一。
请到浦源去吧,那里人鱼同乐,咱们可别后悔来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