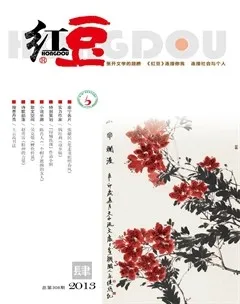迷上奚啸伯(外一篇)
2013-12-29尧山壁
高中时代是我的京剧狂热期,节衣缩食买戏票。邢台是剧团流动的一个重要码头,几乎所有的名角都要占领。1956年,北京京剧四团来了,在人民剧场演出,头场戏是奚啸伯和吴素秋的《乌龙院》,演绎一个宋江包二奶,逼上梁山的故事。
我花了五角钱买的后排座。奚先生上场,貌不惊人,但儒雅的台风一下子征服了观众,台下鸦雀无声。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不是一般地走程式,做戏,而是着力地表现人物,写意传神,自然而又有法度,举手投足都是精心设计,带着锣鼓点。上楼下楼,第一次上楼与第二次上楼,手眼身法步各不相同。宋江的情态,从心平气和、油腔滑调到因忌而恨、精神恍惚、失去控制、恶向胆边生,性格变化层次分明,刻画逼真。第二天剧场经理张高生召开座谈会,一片赞扬。就是有个愣头青说,唱得好,就是声音小,后边听不清。那时还没有扩音器,全凭真嗓子。我也忍不住站出来表现一下,说这出戏通篇四平调,本来就低沉,只要静下心来,就听得真真切切,韵味无穷。奚先生善意地向我点了点头,转过来笑着说:“多高才算高,再高八度就是驴叫了。”一阵哄堂大笑。
在天津上大学期间,我一度住在劝业场等地,四楼有个天华景戏院。混熟了,天天晚上泡在院子里看看戏。渐渐地由看戏发展到听戏,懂得了角要看熟,戏要听旧,京剧流派主要表现在唱腔上。须生一行,谭(鑫培)醇厚,余(叔岩)清新,言(菊朋)空灵,马(连良)潇洒,而奚派的特点是委婉细腻,雅致清新,有书卷气,中国四大须生当之无愧。
奚先生出身正白旗,曾祖官拜中堂。到他这代家道没落,迷上了京戏。幼拜言菊朋为师,后又学余叔岩。19岁在天津中和戏院下海,与坤伶陶默厂(读安)唱《武家坡》,一炮打响,先后搭尚小云、梅兰芳戏班,演二牌老生。27岁排班,红遍全国,时有须生一行,“马跃谭溪”一说。天津是他的福地,一度定居于此,天津有他的知音、挚友,如夏山楼主、杨宝森兄弟,所以一到天津就兴致大发。
以奚啸伯的派头,是不在天华景演出的,通常是中国大戏院、新华礼堂。到天津又必演《杨家将》,一赶三,前令公,中寇准,后六部。导板上场,凛冽北风中弹髯,抱肩,哈手,捂耳,一系列动作洗练生动。与其他名角不同,尽管满脸愁云,步履蹒跚,却不是着意渲染老态,而是表现英雄末路的无奈,一种悲怆美。
毋庸讳言,奚先生音域确有先天不足,音窄而量小。可贵的是他能绝处逢生,勤学苦练,扬长避短,在音律、发声、吐字、喷口、尖团音诸方面刻苦钻研,琢磨入微,创造出一种独异的嗓音,泽厚柔婉,清彻圆润,人称“有如洞箫之美”。《叹杨家》一段,慢板、快三眼、原板、散板,如泣如诉,声声绕情,句句入戏,听起来像一首叙事诗,在创造意境、刻画人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菊坛盛传先生擅长“一七”辙。因为它难唱,剧本已很少见。我给天华景的老经理说了,他常带我外出看戏。莫非他传言过去,几天后先上唱了一出《焚棉山》,“春草青青隐翠溪,老田叮咛结草衣……”,二十二句一韵到底,果然名不虚传。鼻腔共鸣,膛音充沛,低回凝重,美如旦行的程派,让我听过了瘾。这出本来是马派的戏,比较起来,马先生的美声在空中飘荡,而奚先生是脚踏实地行吟,更符合此情此景。
京剧现代戏绝不是江青抓出来的,从李少春《白毛女》之后不断出现,一些名角也都参与,我还看过马连良先生在《南方来信》中扮演的一个角色。但是热衷京剧现代戏,演出既多又好的名角,应当首推奚啸伯先生。我在天津和石家庄、邢台,先后看过他的《白毛女》、《霓虹灯下的哨兵》、《血泪仇》、《节振国》、《桥头镇》、《红云崖》。因为年岁原因,不带髯口,他一般不演主角,充当配角,据说编导唱腔设计出了很大力。因为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白了“应当唱哪些戏,做怎样一个演员,塑造怎样的人物”。对时代和人物的理解,使他创造了范进、杨白劳这样的典型人物。他演的杨白劳,从扮相到声腔更接近人物性格,被称作舞台上的“活杨白劳”。
1968年,我进入石家庄省直文艺学习班,身边的“三名三高”被一网打尽,残酷迫害。我想起身在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的奚啸伯,因为他是京剧界有名的“右派分子”。当年北京成立京剧联谊会,梅兰芳、马连良任正副会长,他被推举为秘书长,因为名角中属他文化高。传说是大学生,实际上过中学,给张学良当过录事。大鸣大放时一言未发,做记录,也被扣上帽子,流落石家庄。“文革”来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恐怕没人能保他了。我抽空从省直学习班来到地区京剧团,空无一人,也到下边搞运动去了。
1972年,我到省文艺组,《河北文艺》复刊后,当诗歌编辑兼管戏曲,认识了石家庄市一名诗歌作者,名叫孙纪才,求他带我去见奚先生一面,尽管他并不认识我。
离八一礼堂不远,西拐棒胡同,一间矮小的平房,除一张床,一张桌子,别无长物。时值隆冬,寒风从破门帘钻入,小小蜂窝煤炉哪里抵挡得住。只见一个老人蜷缩在被窝里,须发皆白,满脸褶皱,两颊深陷,显然牙齿脱落。哪里还是昔日叱咤风云的四大须生,哪里还是舞台上羽扇纶巾的诸葛亮,风流倜傥的宋公明,比那《碰碑》的杨继业、《白帝城》的刘备、《七星灯》的孔明更加凄惨十分,他是水深火热中穷困潦倒、奄奄一息的一个老演员。
提起这些年的遭遇,先生潸然泪下,用了一句常见的戏词:“一言难尽了。”“文革”突如其来,“右派”问题倒还罢了,造反派又抓住他的“现行反革命”不放。1964年,剧团在束鹿县搞“四清”,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多年养成的习惯,午夜前难以入睡,听半导体收音机,转动旋钮找台,忽然听到“昔日有个三大贤”,《珠帘寨》那段西皮导板转原板,嗓音好耳熟,唱到快板“耳边厢又听人呐喊”,是自己当年在“百代”灌的唱片,末了报的是台湾电台。不料隔墙有耳,抓了他“反攻倒算”,外加“偷听敌电”。“文革”开始后每月只给15元生活费,只能抽一角钱一包的“太阳”烟。解放初,他戒了大烟,烟卷因此比别人抽得多,有时买火柴的钱都没有。
后来两派武斗,被子也被人抢了。眼看冬天到了,剧团的老陈给出一个包行头的大包袱皮,儿媳给他做了一条被子。此事让造反派发现,上纲上线,胆小怕事的老陈上吊自杀了。可怜老陈师傅给他当“跟包的”(管理行头),跟了二十年,情同手足,遭此不幸,奚先生悲痛欲绝,当场晕倒在地,突发脑溢血,经过一位戏迷医生的抢救,才保住一条性命,落下了半身不遂。
说到伤心处,老人哽咽不止。考虑到先生的病情,赶快改变话题,可是我自己的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了。扭转头来,看四壁空空,如此清冷,脑子里又冒出了一句常用的戏词:“打入冷宫。”倒是“冷宫”里的奚啸伯先生没有绝望,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他念念不忘两件事,一是给孙子中路谈戏,二是练习书法,说以后不能登台了,给剧团写字幕。
不便久待,告别出门,我想起了先生演过的《七星灯》,二黄慢板:“四百载东西汉六元七甲,传至在献帝朝群寇如麻。十常侍乱宫闱董卓强霸,许田射猎曹孟德把主欺压。曹丕贼篡汉位万民叫骂,我主爷扶汉室年不天加,哭一声先帝爷九泉之下,保佑臣增寿算扶保汉家。”气息奄奄,奚啸伯心中的汉家,就是中国京剧事业!
想起“王宝钏”
这是一件真人真事,曾经轰动一时,家喻户晓。然而时过境迁,回味起来未免让人辛酸,是那个时代酿出的一出悲剧。更不忍再说出她的名字,以免饱受摧残的灵魂再受到一次伤害。权且就叫何辛吧。
1971年腊月,冀南平原三省交界处,传来一件奇闻,一名女大学生决定嫁给一个贫下中农饲养员。好事者闻风而来,那时尚无众多媒体,都是各级革委会报道组和文艺宣传队的人。县招待处人满为患,挤不上公用的大卡车,我骑了一辆自行车赶去。白花花的盐碱地上,黄土房组成的小村,黑压压的人群在看热闹。新房门上的对联格外醒目:扎根树上结硕果,连理枝头话丰年。门垛是新的,泥缝未干。木门是旧的,腐朽处用报纸糊上,再刷一层墨汁。
众人张罗喜事,婚礼如期举行。新娘白白净净,大大方方,有几分男人气慨。新郎又黑又瘦,扭扭捏捏,倒似女儿态。第一印象是不大般配。天公也不作美,空中飘着点点雪花。可是随着鞭炮锣鼓声起,高音喇叭震耳欲聋,隆冬寒气已被驱散。这些响动也让我惊醒,不能以陈腐眼光看待新生事物,带着亮晶露珠的新事新办。如此,眼前便一片亮色,扎根树上的纸花,也像真的一样红火欲燃。扎根树是新娘从集上买来的,几株桃树苗子,在众目睽睽下栽到院里,扶正,浇水。
访问了几名知青,他们没去贺喜,躲在家里议论,也并不反感。认为这种结果并不出人意料,甚至是大势所趋。知识青年下乡,转出城市户口,断了后路,只能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厮守一片土地,当一辈子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别无选择。有的人出身“不好”,希望渺茫,万念俱灰,只想找一户贫下中农人家,改换门庭,不再低人一等,当黑崽子了。
几位本地婆婆说了实话,这些城里妮子刚下来,她们不欢迎,是给咱们庄稼人争工分来了。后来转忧为喜,是福不是祸,给咱们送媳妇来了。咱这里人穷地薄,越穷越兴要彩礼,大闺女论斤卖,正上愁小子们打光棍。女知青不要彩礼,天上掉下来的便宜货。身旁又没三亲六故,没人撑腰,不偷嘴光拉磨。
问何辛的事谁保的媒?邻居大嫂们说,是大伙将军将来的。那天在场里干活,这个引:“小辛到俺队,吃糠咽菜不在乎,脏活累活抢着干,真不孬哩。”何辛说:“响应毛主席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与贫下中农结合呗。”那个逗:“光耍嘴,口头革命派。”小辛认真了:“不是不是。”这个又说:“忠不忠看行动,寻个贫下中农结婚,那才叫真结合呢?”何辛没当回事,笑笑说:“中啊。”嫂子们紧追,“你看石头中吗?”何辛随口说:“中,中。”何辛打哈哈,众人起哄,紧锣密鼓,竟然弄假成真了。
何辛虽说是大学生,正赶上那几年运动多读书少,灌了一脑袋政治。头脑简单,又好面子,下不来台了。从提亲到进洞房,连哄带骗,又推又拉,总共十天工夫。直到坐在人家炕上,面前一个大活人,梦才半醒,哭着说:“你说这世界上谁最丑,谁最俊?”新郎是个没嘴葫芦,光顾着笑,答不上来。何辛还得自问自答:“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丑的,没有比我傻的。”
生米做成熟饭,何辛也就认了,当一名农妇,烧火做饭,喂猪起圈,侍奉公婆,生儿育女,扑下心来过日子。可是指望相依为命的丈夫,让她越来越看不懂了。得了便宜卖乖,不知心疼人。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夫权观念,稍不如意,张口就骂,举拳就打,一向敬重的贫下中农怎么会是这样?忍无可忍时,想到离婚,可是看他老实巴交,磕头求饶,可怜兮兮,心就软了。1973年何辛被安排在乡中当教师,与人发生口角,被那人恶语“丑闻”,一怒之下,无处诉说,向报社写信:“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看不起庄稼人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把自己并不称心的婚姻,说成是扎根农村的自觉劳动。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何辛的苦果,正好被江青一伙拿来当作“反潮流”炮弹用。197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敢于同旧传统彻底决裂》的文章,并全文配发了何辛的“事迹”,夸耀“是一幅生动的批林批孔教育的好教材。”“希望涌现出更多敢于同地主资产阶级旧思想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何辛一夜成名,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地区知青办副主任,按着上级的调子到处做报告:“爱上农村,爱上农民,是毛主席思想哺育了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贫下中农教育了我。”为此累坏了身体。这一阶段,下乡知青嫁给农民成为时尚,据保定地区统计,占知青总人数的75%。
其实对何辛的遭遇,至今我并无厌恶,更多的是同情。因为人们的智慧中,对婚姻的知识是懂得最晚的。何辛的悲剧并非是与贫下中农结合。相反,贫贱之中人才多,嫌贫爱富倒是为传统道德所不齿的。京剧中的《王宝钏》、《西厢记》,外国文艺中也有不少公主与乞丐的恋爱故事。公子王孙看不上,“绣球专打平贵男”,明明是薛平贵,大家都读作薛贫贵,其中含有深刻的哲理。选贫还是选富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选择自己的所爱。为财产而选择是出卖自己,为眼前的势力选择是赌博。“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理的。”这是恩格斯说的。何辛的婚姻悲剧在于,选择的对象不是具体的人,是一个政治概念,而这些往往是最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