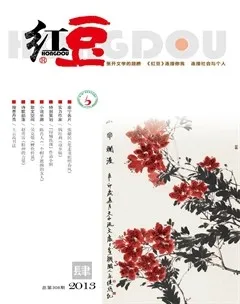倩何人,持得倪田扇?
2013-12-29初国卿
杜甫《纳凉晚际遇雨》诗中有“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两句,深得后人喜欢,每每称引。我曾在2005年中贸圣佳春拍会上见到一把清末民初著名海派画家倪田的折扇,上面即题此诗句,画意也好,竹林和人物绘得生动传神。春末夏初时节,见此扇顿觉凉意幽幽,是一件难得的老派男人书斋把玩之物。机缘难求,最终不知那把扇子落入谁家。然而,正当我为此感叹“惆怅彩云容易散,疏香阁外雨如丝”的时候,不意却得到了倪田的另一把扇子。巧的是此扇与中贸圣佳那把折扇上的画意相似,题款一致。最吸引人的是它的精致——无以复加的精致。它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折扇或团扇,而是一种芭蕉扇,是用竹、宣纸、白绫和象牙制作的芭蕉扇。
此扇为椭圆形,扇面长约35厘米,宽约25厘米,中间约略回收,上半部微弯,形似传统的芭蕉扇。说它精致,是它的主体只是一根无名指粗的竹节,在一厘米处劈开极为匀称的针一般细的64根竹丝。又在竹节处横穿一根细竹签,弯成半圆,成为扇子下半部分的外缘,饰以大漆。扇内64根竹丝按芭蕉扇的形状,随弯就形均匀地分撑在一个平面上。64根竹丝的稍等距排成扇子上半部分的圆弧形,用一根丝线从每根细竹丝的梢上穿过,绷紧,两端系在下半部分的竹签上。扇的裱糊材料也分外讲究,正面为上等玉版宣纸,背面为薄如蝉翼的白绫。裱糊后,透出的竹丝如同芭蕉叶的纹理脉络,巧夺天工。扇上半圆弧处饰以黑色蜡笺纸,同时扇面根部也以黑蜡笺纸云纹装饰。扇柄为活动的上好象牙,自然纹理清晰,通体包浆,乳白中泛着岁月的浅黄。扇柄上坠以米色丝绦编成的缨络,工巧而富情致。略显不足的是此扇上端多有破损,但画面完整,情趣不减。
画面为一幅完整的“竹林纳凉图”,给人以幽幽的情致和出尘的空灵。近景是翠竹林下,流水潺潺,板桥上一童子提壶汲水而行。循着童子的行走路线进入中景,只见竹林深处,茅亭掩映,亭的一角于竹梢中露出。透过栏杆,可见亭中对坐的两高士,一红衣,一蓝衣。红衣者侧面亭外,望着竹林外若有所思。亭边,一泓湖水,清波荡漾,荷叶田田。扇的上方行楷小字题款:“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光绪乙未仲夏,二江仁兄大人雅属即正之,墨畊倪田。”款后钤阳文鸡形生肖印。图中景物与诗意相合相契,构图简洁,设色雅淡,笔墨工细而灵动。人物动态悠闲自在,栩栩如生,衣褶用浓墨勾勒,略似折芦描法,笔势流畅自然。尤其是大片的竹林最具神韵,蓝彩与淡墨相间,深深浅浅,层次既分明又交融,枝枝清秀,摇曳生姿,既生动地表现出了“竹深”之意,又滟潋着宋词元曲般的幽婉之韵。
题款中所用杜甫两句诗的原诗为五律,其诗题有的版本作《携妓纳凉晚际遇雨》,还作《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但多数还是《纳凉晚际遇雨》,去掉“携妓”二字,大约也是为“诗圣讳”一类。其实杜甫“携妓”自己都不避讳,后人倒替他担心起来,以至于一般唐诗或是杜诗选本都不选这一首。这个诗题下共两首诗,其一为:“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客观说这是一首写得很好的闲适诗,明白晓畅,情景怡人。尤其是中间两联,对得工稳且诗情画意。诗人说:水边竹林的深处,静谧幽雅,正是留客的好地方;池塘里荷叶碧绿如洗,正是歇凉的最佳时机。贵公子耐心地用冰调制着冷饮冰水,温婉的美人则剥去嫩藕上的白丝,共同制作冰镇嫩藕小吃。多么美丽的一番情致,说是朋友聚会或是携妓纳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所创造的这种诗情画意和闲适情境。
倪田在扇上的题款只用了此诗的“竹深”一联,留下“公子”一联让持扇人去想象和体味,也足见出画家的含蓄用意。因为持此扇的公子和佳人不会不知此诗的出处,更不会不知诗还有这样的下两句,或许整个夏日都生活在冰水藕丝的情境中也未可量。但画家不说出来,持扇者也不说出来,心领意会,留下的则是妙不可言的想象和意味。
在江南,夏天吃一碗冰镇雪藕是很惬意的一件事。古人在这方面自有一套办法,他们常在冬天凿冰藏于地窖,到了夏天,开窖取冰,将去掉藕丝的嫩藕和冰糖放在冰中镇上,等冰化成了水时,那嫩藕正好冷而不冰,清甜脆爽,可谓人间消暑之极品滋味。试想,公子佳人在炎炎夏日里寻一处荷风习习的竹林深处调冰品藕,谈情说爱,当是怎样的一种温馨和着醉意?如果一边吃着冰藕,再手持一把倪田画的竹制芭蕉纸扇,想象着“藕”“偶”相谐,“丝”“思”同音,当是怎样的一番雅趣幽怀。
这样的生活或是情境,作为画家的倪田是不会陌生的,否则他也不会多次创作这种题材的扇面,这方面也可从他的性情和经历中见出。倪田字墨耕,江苏扬州人。晚清之时,在扬州画坛上,他与王小梅同为翘楚。据郑逸梅《任伯年延誉倪墨耕》一文讲,倪田善画马,他画的马瘦骨锋棱,骄嘶顾影,间着一二胡奴,韦韝红樱,作控制状,令人兴凉秋九月,塞外草衰之感。对此,深得王小梅赞赏。有一天,王偶过某斋,见壁上悬有一幅《豆棚闲话图》,署着自己的款识,但笔墨风格却不是自己的。询其来历,云从书画铺购得。小梅知是墨耕所为,回去后责备他不应当私作赝品以欺世。墨耕大为惭愧,于当天即渡江出走上海,在豫园萃秀堂前席地卖画。恰逢任伯年路过见到他,于是招其到家中,对其画大加赞誉与鼓励,遂得结交朱梦庐、吴昌硕、胡公寿、王一亭等画坛诸公,所用印章亦多为缶庐所冶。其画风也深受任伯年影响,水墨竹石,设色花卉,腴润遒劲,擅胜于时。并工山水,鬻画于沪上三十余年,所订润格比王小梅的还要高。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称其“名重一时,流传最盛”。
郑逸梅的这段记述,至少说明倪田品性中是不太约束自己的。这从他以后的所作所为中也可印证,比如有的文章记载说,倪田刚从扬州到上海时寄寓客栈中,一日晚餐店主叫伙计把热腾腾的大蟹送其品尝,谁知倪画师竟吹灯上床,蒙在被中大吃大嚼,自得其乐。翌晨伙计为他整铺,枕边尽是蟹壳与零星脚爪,衿褥沾满油污。如此而为,你说他是乡巴佬也行,说他是名士也可以。还有记载说他天性渔色,老于花丛。郑逸梅先生还讲过这样一件倪田好色而受骗的故事:墨耕性好渔色,所获十九耗于其中。他曾见过一位裱画人家的女儿,豆蔻梢头,丰姿娟美,于是以裱画为由,灵犀一点与之相通。不久将该女弄到自己家中做为随身侍女,相处了很长时间。一日,该女忽然对他说:“我哪天哪天要赴某家喜宴,你须为我置办一套新装,且送一份厚礼。”墨耕一一应允。到了这天早晨,该女盛妆艳服而去,临行还对墨耕说:“我先去了,你待一会也要去道贺。”并告诉他详细地址。快到中午,墨耕按地址访得,见客人都很陌生,殊感落寞。不一会儿,弦管声喧,合卺礼行,待红巾牵挽,新娘亭亭玉立于堂前时,墨耕一看才傻了眼,那女子正是自己所养的侍女。这故事骗术奇诡,完全可入光绪年间雷君曜编著的《绘图骗术奇谈》或稍后的《女子骗术奇谈》。
不管倪画师的性情怎样,他的作品在今天越来越为人喜欢则是毫无疑问,尤其是他的小幅精致的作品,如扇面、册页一类。记得早在2003年上海朵云轩秋拍时,他的《摹任熊大梅诗意120开册页》曾拍到了880万元,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很震动的价格了。
得到倪田的这把独特的竹制芭蕉纸扇后,我将破损处略加修理,象牙柄也用牙膏仔细擦过。我曾在夏日炎炎的夜晚把玩这把扇子,抚弄它纹路发黄的象牙扇柄,看着扇上拂水的竹影,牵情的荷叶,以及破损的扇子边上刻染着的沧桑如梦的岁月痕迹,仿佛百年前的公子佳人簪花约鬓,携手闲行的跫然足音就近在咫尺。只要轻轻喊一声,他们就会提着一壶龙井,捧着一杯冰藕,移出茅亭栏杆,闲步进来细数半世的风尘。把玩之余,我竟然想象不出当年何人能使用这样精致的扇子?想来想去,最终认定执过此扇的人一定是飘着撩人的妩媚,打扮精致,气定神闲,有着幽幽书香,类似李秋君或是张爱玲、周练霞一类。
如今,这样的风月已成遥远的绝响。当年海上文人的清雅与幽香,半个多世纪前残留的旧时月色,我们只能通过这类扇子的精致而领略一二。我不忍再去随意把玩这把扇子,于是请人压装在一张洒金宣纸上,并请书家南朝明兄在空白处题上了杜甫的原诗,体体贴贴地镶在花梨木镜框中,挂在书房一角,闲来欣赏,满心企慕的也就是那一点半窗绿荫衬托下的纸上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