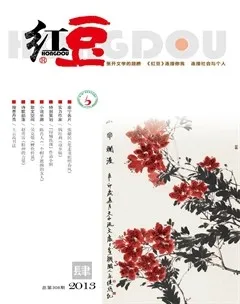低眉信手续续弹(评论)
2013-12-29江少宾
与小说和诗歌相比,近年来的散文写作似乎是最寂寞的。虽然其间也不乏“新散文”、“大散文”、“原生态”、“在场主义”以及“非虚构”之类的倡导与运动,但众声喧哗的表象繁荣,却无法掩盖本质上的虚浮与困境。因此,在这个精神物欲化的现代语境中,也只有那些甘于寂寞的写作者,才能持守自己的底线,用看似单薄的努力,为散文写作正名。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安徽女作家钱红莉,应是其中坚定的持守者之一。
钱红莉成名久矣。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钱红莉的文字就像天女散花,占领了大江南北的诸多平面媒体,成为炙手可热的专栏女作家。二十年下来,笔耕不辍的钱红莉既优质又高产,先后推出了《华丽一杯凉》、《低眉》、《风吹浮世》、《诗经别意》、《当我老了》、《读画记》、《万物美好,我在其中》等多本散文随笔集。单看这些书名,就不难发现钱红莉的广博,她写浮世,也写《诗经》,还写草木和张爱玲。难得的是她一以贯之的苍凉,其标签式的笔触清瘦而凛冽。她惯于不经意间笔走偏锋,让俗世和人生露出苍凉的底色。她的文字看似冷而瘦,但匍匐于冷瘦之间的,却是饱满的气场和丰腴的物象。我尤其喜爱她的《诗经别意》和那些描摹故乡物事的篇章,她将《诗经》里的那些小哀愁,写出了现世的体温和草木的暗香。这是一条幽微的通道,我以为,自《诗经别意》始,钱红莉走上了另外一条迥异于专栏作家的散文写作之路。她文笔华丽,极富才情和书卷气,流淌着一种寒凉的气质和古典的情怀。对于故乡的回望式书写,钱红莉从琐碎的日常生活出发,自觉摒弃高蹈的抒情,行文如话家常,而又恰到好处地承载着她的个体生命和精神历程。这使得她的故乡写作有别于时下习见的那些乡土散文,源于现实而又有所超脱。这种超脱不是技术性的,钱红莉的散文没有“技术”,有的只是情怀和气场。
我无意于剖析钱红莉的散文艺术和写作伦理。我猜,钱红莉也不屑于那些空泛的理论,正如不屑于网络上对她的诸多热捧。钱红莉的散文既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底层书写,诸多篇章反倒显出一种“小”来——小人物,小命运,小生活。然而正是这种种“小”,凸显出钱红莉在散文写作上的孤愤与持守。在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钱红莉从来不跟风,她所要的不是那种标签式的写作与文本,而是精神上的自由与妥帖——钱红莉的自由是信手拈来的自由,钱红莉的妥帖是真正意义上的“我手写我心”。她写枞阳乡下钱家祖的腊月,写腊月里熬糖稀,做炒米糖,细致入微几近白描,让我这个同乡感念不已。在腊月里写着写着,钱红莉就写出了下面的闲笔——
“在乡下,大人们一致认为,一个女孩子是万万不能好吃懒做的,以至于名声不好听,嫁不掉人,更坏的结果是被人唾弃。反正我妈就是这样灌输下来的。这种理念像蛇蝎子一样毒辣,一直隐秘地埋伏在将来的道路上,时不时伸出来咬一口,让我的心痛上加痛。直到成年,再来反省过去种种,不得不佩服,一个大人是怎样将自己的节制观念,钉子一样牢牢地镶嵌给了一名少年,即便成年以后自己拔出来,还是带着铁锈与血肉,非常痛,一直影响到老。”
——《故乡帖——腊月讲述》)
这样的神来之笔令我这个散文写作者异常妒忌,它只能发生于作者的自由与自信。而这样的闲笔在钱红莉的散文里俯拾皆是,它们从钱红莉笔下的“小”中冲决而出,简洁而冷硬,折射出钱红莉骨子里的心性:疏离、决绝而孤愤。而她的情怀和气场,也正生发于这样的疏离、决绝和孤愤,看似漫不经心,却渗透出生命的体温与质地。
写作是让笔下的人事发出光来,进而温暖现实生存,照亮内心世界。生活中的钱红莉朴实而内敛,也不喜表达,她所有的表达都交付给了书写——“低眉信手续续弹,诉尽心中无限事”。虽是低眉,却是高看,心性极高的钱红莉让笔下的文字披上了一袭华丽的外衣,而打底的,却是一阕枯瘦的宋词。身居省会城市合肥,供职于一家颇有影响的主流平面媒体,钱红莉浑然不觉其中的好,倒时常念起故乡,写起故乡,笔下多惆怅。令她怅然的,其实不仅仅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还有那种深居闹市的悬浮感。对钱红莉,写作是持守,也是慰藉,更是个体生命与自然万物之间的隐秘联系。她的文字几乎都是“后退”的,她有意识地与立身的时代保持着距离,形式上趋于现代,意蕴上归于古典。在我看来,钱红莉是一个很难标签的散文写作者,她在后退的文字里,享受着内心的大安宁与小悲喜。
或许,这正是钱红莉的人生追求与文学信念——人生自守,枯荣勿念。万物美好,我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