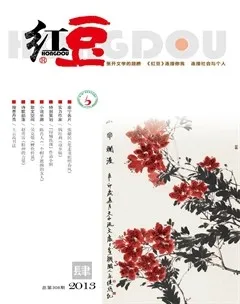故乡帖(散文)
2013-12-29钱红莉
向农业致敬
每年都会空出来一两只花盆,一直空到秋深。忽然有一天,阳光很好,我想起来了,就爬到露台上,把花盆里板结的土松松翻翻。可以种点什么了。那么,撒点小白菜籽吧,或者再秧点蒜瓣。
先把白菜籽撒下去,再秧几圈蒜瓣。对,是叫“秧”,在我们老家都兴这么说,名词活用于动词,形象传神。仔仔细细把这些搞好,快晌午了,拍拍两手黑泥,直起腰来,正值秋风徐来,把此刻的心情衬托得分外愉快,比雪夜读书还要愉悦。
愉悦何来?具体也说不出所以然,就觉得一颗心比秋天的长空还要辽阔,虽空无一物,却应有尽有。
今年,是跟孩子一起做这件事的。我对他说:过几天,我们就能看见白菜籽出芽了。孩子将信将疑:真的呀,妈妈?
当然是真的,妈妈从来不诳讹孩子。
跟泥土打交道,人就会愉悦。这是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弄明白。
比如,有时情绪陷入低落,坏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时,你什么都不要做,径直去郊区,看看大爷大娘们在地里劳作……慢慢地,你的情绪就缓过来了,会非常平静,然后默默回到城里继续生活。
我居家附近荒着几十公顷的田地,是一家开发商买来屯着的。附近郊区一些老大爷老大娘们闲不住,纷纷垦起了荒,种什么的都有,一年四季有得看。我常去看他们挖地,那种熟悉的土腥味非常好闻。一闻着这个味,就想起自己的来处,有山河旷野晚霞的来处。前一阵,碰见他们割芝麻,黄叶簌簌落了一地,踩在上面就跟踩在绚烂的黄绸缎上一样软绵,梦一样的奢蘼美好。这么美的黄叶,被秋雨一淋,慢慢沤烂,不是奢蘼是什么?现在正值农历九月,九月是挖山芋的季节。山芋一垄垄一畦畦地铺在那里,拿锄头把山芋藤拂开,再拦根斩断,然后一点点往土里刨,虎头虎脑的芋头纷纷露头,被秋阳一把接住,格外殷实,再被一双手捡到稻箩挑回家,这一年的正果就修成了,非常圆满。
所谓春叶夏花秋实冬藏,年年轮回。还有比土地更守信的吗?憨厚、实诚,一直站在原地等,等漫天大雪,等春风夏雨,等秋漓淋淋。而今这年月,什么都不保准了,就剩下土地把道德的底线给紧紧守住了。
当霜降来临,所有的晚稻都要动镰。在色彩上,晚稻比早稻更要绚烂,或许是被秋风吹秋雨浸的吧。这个季节,露水特别深重。那年月,正值琼瑶小说流行,电视剧也跟着拍出来。当我们弯腰割晚稻的时候,田埂上不知谁带出来的收音机里,正传出缠绵悱恻的片尾曲,其中,“更深露重,落花成冢”的字眼被凄凉的女声唱出来,有举世滔滔的虚无感。我直起腰,站在晚稻田里四处张望,不禁有“众鸟高飞尽”的孤单。
一晃也20多年了,这么回忆的时候,心仿佛被荡了一下——无非想,回到乡下割一次晚稻。谷穗饱满,遍野金黄,众鸟高飞,孤云独闲。秋天的主旋律自古以来都是金黄色系的,梦境一样沉甸甸。
寒露与霜降之间,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所有的谷物都陆续进了家门。紧接着就是立冬,立冬意味着储藏,意味着休养生息。冬天的风也寒,冬天的夜会更长,一村老老小小缩在厚棉被里做梦,而窗外大雪降临,山河皆白——乡下至此走的是沉静的笔调。
挖藕人
如果3岁是一个人开始记事的年龄,那么,就是3岁了吧。从出生到上小学一年级这段光阴,我一直跟着外婆生活在稻圩村。那个阶段,舅舅在横埠高中上学,小姨每天放牛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架在她的脖子上。
稻圩村正如它的名字一样位于圩区,地势低凹,每年夏天发大水,十有九淹。河流纵横密布,产野菱和藕。遇到没菜可食时,大人会去河边抓一把野菱角回来炒,搁几只红辣椒,挺下饭。大多时候,我的菜很特殊,外婆拿菜籽油炒粗盐粒给我拌稀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乡下还没有完全摆脱贫穷,那个时候的菜籽油少而精贵。到如今我都记得,当外婆炒菜时,把菜籽油从玻璃瓶里倒入大铁锅里,一回回坚持用大拇指把瓶口塞起,以免油流得太多。就是大拇指上沾的那一点油,外婆也舍不得似的,全揩在她乌黑的发上。嗯,那个时候她正值壮年,还没有挽髻。村里人都敬称她“大妈妈”,我作为她的第一个外孙女,少不了得益于村里人的优待。他们总是“小红子啊,小红子”的喊着,脸上堆着喜悦的笑,温暖又信赖。
跟外婆家隔壁而居的是“大汉子”家,村里人都称这家的女人为“大汉子”,虽然年龄跟外婆相当,但辈份小,我都可以直接喊她“大汉子”。所谓“大汉子”,即个高之意。她有一张宽阔的脸庞,皮肤白皙,笑的时候总习惯把嘴巴抿起来,说话温和。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在3岁孩子眼里算得上美人的女子,嫁的却是一个哑巴。他比她矮些,皮肤黑亮,看上去要比“大汉子”老十几岁的样子,额上皱纹深而乱。生气的时候,一个劲地在嘴里咕咕噜噜,眼神亮而有光,凶煞煞,简直要把人生吞下去。我一见他就怕,可是,越怕越想要研究他,每次都是站在外婆家门槛上远远地打量他。
冬天的早晨,他端着一个硕大的蓝边碗,蹲在门前柳树底下喝粥。粥是白粥,漾漾地一圈一圈流出蓝边碗外,千篇一律的腌菜,先飘在粥上,一会儿又沉下去。我看着他一碗接一碗地喝。喝粥的声音那么好听,粥像是在傻呵呵地笑着,笑得冒起白雾,陆续进到他的嘴巴。他在我眼里,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气鼓鼓的,见谁都拿眼风刮,恨不得吃了你;倘若平静下来,总是不停歇地干活,挑水、犁田、打耙……仿佛将不能说话的遗恨全寄托在体力活上。后来,我大点,才理解些他——不停地劳作原本就是对于身体的一种安慰,劳动可以使人投入,人一投入,就忘我。忧伤,愁烦,暂歇下来。
如今,我们家冬天的餐桌上每天都不缺一样菜——素炒藕片。我每天早晨喜欢就着它吃稀饭,也喜欢去菜市挑那种塘藕买回来炒,个大,肉白,口感脆而糯,偶尔也放在小排里炖汤。每当挑藕的时候,就会想起一个人来。
想问一问,寒冬腊月的乡下,什么人最辛苦?
当然是挖藕人。
每到寒冬腊月,乡下基本上没什么农活可干,人们一律猫在火桶里煨冬,要么,手上拎只火球满村四处转悠。对于哑巴来说,他不能加入到谈话的一群,若一味猫在家里可能会更难受,于是他不闲着,出门找事干。冬天能有啥子事呢?只能是挖藕了吧。塘藕一般都是人家放养的,只有河藕是野生的,也少,经不住挖,一年两年三年的光景,差不多挖尽了。没有了,别人就会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赶紧放养一些家藕,再一年的时间,满河皆是了。冬天是起藕的最佳时节,起出来洗干净挑到周边的镇上卖,换回一些收入。种藕卖,好像是那个时期人们暂时想得起来的唯一的经济模式。并非全村人有资格种藕,一般是有势力的人或者村干部。
渐渐地,哑巴靠他的吃苦执着,挖藕挖出了名。每年冬天,他默默出去帮别人起藕。有了一点积蓄,他为自己置办了一个挖藕行头,背带橡胶裤,那种把脚直接插进去穿的挖藕衣服,做工粗糙,橡胶品质极差,穿起来,给人又胖又丑的印象,穿着它走在平地上,哐啷啷的闷响——这踩在淤泥里,该要用多大的力,才能一脚脚跋涉出来啊。
黄昏,远远地,小路上,有他拎几节藕回来的矮小身影,最是他开心快乐之际。接近村里,他的眼神满含讽刺,无非轻蔑村里那些青壮年怕冷怕累缩在家里当乌龟,独他一人风雪无阻出外劳作——这个时候,他是骄傲的,骨头缝里散发的骄傲,洪水一样倾泻,流着流着不禁热血沸腾,整个身体都暖起来了。
常常,我们需要独自一人给自己取暖。
偶尔我在村口玩耍,恰巧一抬头,跟他眼神四接,我也不慌,定定看住他,他的眼里开始有了笑意,嘴里还咕噜一通,我听不懂,一阵大风灌进脖子里,我赶紧把颈子一缩头一低,继续玩耍,不再理他。他收起笑意,悻悻走掉。有时我们晚饭都吃过了,他仍然没回来,“大汉子”会焦急地站在村口张望。
如今的冬天,常常温习一些古诗,当读到“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一首,觉得刻划得太像我经过的稻圩村的日子。
那些“天寒白屋贫”的日月,值得铭记。那么苦,那么冷,他一个人在淤泥里劳作,默默无言。回家时顶着一头白雪,走在泥路上,也没有个伴,多寒冷孤独啊——他到底有没有过大放悲声的时候?我想,偶尔会的吧,当脚趾头陷在淤泥里冻僵,哭一哭,反而会暖和一点。
所有的藕都喜欢藏身于淤泥深处。由于长期没有挖泥净河,有些地方的淤泥会堆积成一人高的厚度。在寒风冷雨里,他一锹一锹掀开泥巴,把肥美的藕节一根一根找出。一找就是一天,锅巴裹腹,不知可有热水喝?
一个终生不言语的人,该有多寂寞?我想象着,他挖藕时,会不会跟藕对话?咕噜一句:狗日的,藏得真深呐!
后来,我离开稻圩村,回到了钱家祖。渐渐地,童年的事情差不多都自动引退了。直到上了初中,某一年冬天,钱家祖有户养藕人家非常缺人手,到处请人,当被我妈得知,她自告奋勇牵线搭桥,帮那户人家请来了哑巴。
那天,我见他带来了好几个人,一律穿的工装皮裤。七八年未见,他更显苍老,眼神未变,还是那么亮堂,仿佛有一种光在里面闪耀。他们一共干了三四天,就走了。那家的藕根本没起完,还有一大片呢。我一直纳闷,是工钱没谈妥,还是别的?
再后来,我终于从村里心直口快的人那里得知,是那家嫌他们挖藕挖得不专业,许多藕被挖破。藕一旦破了,灌了泥进去,就卖不上好价钱。于是,把他们辞了。
为这事,我失落了好几天。我妈一番好意到底付了流水,临了还要遭埋怨。他到底老了,没力气了,找藕不再精准,一锹下去,难免偏差。
最难过的,还是他自己吧。人老了,不中用了,终归力不从心,落得个被人辞退的局面。回到稻圩村,他该有多怨责自己?另外,这份活还是大姐介绍的,更多了一层愧疚。我妈在稻圩村,与我外婆一样受人尊敬,每次回娘家,老老小小碰见了,都热情地招呼:“大姐回来了,多居几天!”
后来,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许多年,我都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仿佛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人。谁知,今年,每当我去菜市挑藕,他又一次次复活过来。
人真是——年岁越大,越留恋童年经过的事,过电影一样没个完的时候。连我外婆都去了好多年,何况他呢。小时候,我没能跟他有过交流,但在我的成年,却牢牢记住了他,是因为他的残缺,还是因为他的忍辱负重?
一直跟气场比较弱的人亲,觉得那是同类——他们的苦,就是我曾经现在将来要受的苦。
今年清明,想带孩子回去看望我外婆——孩子跟外婆竟然同一天生日——我相信人是有灵魂的。曾经以往,是她照顾我,如今,她投胎做了我的孩子,由我来偿还她了。我回去的时候,也顺便看看稻圩村还在不在。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限量版,在我的童年生活里出现过的人,都那么珍贵、难忘。
腊月讲述
在钱家祖(位于安徽省枞阳县横埠镇某村),一到腊月,全村老小像是受到了一种感召,责无旁贷地投入到忙年的生活里去。在乡下,过年就是一种仪式。这个仪式相当繁琐,可达一个月之久。
记忆里,腊月总以晴天为主,日头一天照到晚,把什么东西都晒得焦干,甚至好久不穿扔在屋角的一双旧棉鞋,也要拎到小河里涮涮。迎接新年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要把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的。月初,我妈把垫的以及盖的被褥一床一床拆下来清洗。老布的粗里子越洗越白,在河边大青石上被棒槌捶得翻滚,如一尾刚起网的鱼。我们家垫的毯子上印有两只凤凰,展翅欲飞的逼真感惹人一看再看。老布的被里子洗干净后,要放到米汤里浆一浆,晒干以后特别挺刮,夜里盖在身上,米的芳香与日头的芬芳齐袭梦境,一个又一个美梦“接天莲叶无穷碧”。
糯米已经浸了几天了,用拇指与食指轻轻一捻,便碎了,拿去有石磨的人家碾磨,一勺一勺往磨眼里填,雪白的米浆倾巢而出,流进下面的木盆。当所有的糯米都化作了米浆,在木盆里荡漾,经过一夜的沉淀,糯米粉逐渐沉到水下,把上面汪着的一泓清水舀去,再用青灰裹进白纱布扎紧,放在米粉上吸水过滤,抓一把在手,轻轻捏捏,基本上可以成团,就可舀到簸箕里晾晒,十个白天九个日头的,时不时去簸箕里捻一捻,筛一筛,细如银丝的糯米粉被抓起一把,扬一扬,若恰好碰见一阵寒风经过,会吹得很远很远……这些糯米粉,是要等到正月十五做元宵来吃的。
除糯米粉之外,还要准备米披子,就是炒米糖的原材料,籼米或梗米均可。把米蒸熟,暴晒,晒成透明色,越干越好,炒起来蓬松。晒好的米披子暂且寄存在瓦罐里,接下来是熬糖稀。对于孩子来说,熬糖稀是最甜蜜的一件事。麦芽是出糖稀的一个引子,无它不可。大人把麦子放在淘米箩里,上面覆盖着一层稻草,早晚各过一遍温水。谁知没过几天,神奇的事情出现了,麦子真的在寒冬里发了芽,金黄里杂有嫩白,锲而不舍地穿过稻草,直到长成一尺来长,拔一根对着阳光晃,水晶一样透明。麦芽好了,该熬糖稀了——山芋烀熟,皮驱除,揣成泥,加水和麦芽,在大铁锅里熬,先是烈火鼎沸,然后改中火,再改小火,慢慢熬,用锅铲不停地搅动,慢慢地,又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所有的水被蒸发,最后剩在锅里的,是黄汪汪的糖。捞一筷子上来放在嘴里,满坑满谷的甜,那种甜可以直达漫山遍野,甚至上了云霄。那种甜,是令人恍惚的甜,不知所终的甜,物以稀为贵的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糖,对于一个乡村孩子,依然是一种奢靡的向往,轻易触不到的期盼,但唯一在腊月里,是可以重逢的梦。
糖稀被大人装进大瓷缸,藏在碗橱深处。有一次,我妈没在家,我动念了。即便偷吃成功,也是心怀歉疚与不安的,简直是——吃了,比不吃还令人痛苦。在乡下,大人们一致认为,一个女孩子是万万不能好吃懒做的,以至于名声不好听,嫁不掉人,更坏的结果是被人唾弃。反正我妈就是这样灌输下来的。这种理念像蛇蝎子一样毒辣,一直隐秘地埋伏在将来的道路上,时不时伸出来咬一口,让我的心痛上加痛。直到成年,再来反省过去种种,不得不佩服,一个大人是怎样将自己的节制观念,钉子一样牢牢地镶嵌给了一名少年,即便成年以后自己拔出来,还是带着铁锈与血肉,非常痛,一直影响到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则是父母是孩子的终生老师。从小到大,我妈潜移默化灌输给我的种种做人理念,太过根深蒂固,像一棵树一样,越长大,越枝繁叶茂,永远倒不了,嵌进了骨头里,长成了钙,死了以后火化成一捧灰,依然在灰里。
这些不表,接着说过年——我们要做炒米糖了。选一个日子,把所有的米披子都炒掉。大铁锅里黑砂翻滚,米披子一投进去,立马膨胀,嘶嘶作响,赶快铲出来筛一筛,再把黑砂倒入锅中,重新舀米进锅。如果不累,是可以炒出一稻箩米的,关键就看熬的糖稀够不够用。将糖稀适量倒入锅中加热,迅速倒炒米进去搅拌,再盛入洗刷干净的抽屉里,铺平、压实,如此三五分钟,糖稀与炒米已相互渗透得差不多了,不软也不硬,趁势倒到饭桌上,切成条,再切成块,等彻底冷了,装进瓦罐里密封,可以从过年吃到春三月插秧之际。
炒米糖嚼在嘴里,崩脆崩脆,最关键是它的香甜,鼻腔受用,口腔更是至乐。除炒米糖,还有炒蚕豆,偶尔也有炒花生,碌骨炮子更脆,是万念俱灰的脆,上牙下牙一碰,它就粉身碎骨。所谓碌骨炮子,就是玉米粒,是到镇上花钱买回的。皖南地处丘陵,地少,大多种了稻麦棉芋,哪有闲地点花生、玉米呢。
然而,这些都不是钱家祖过年的主打,说白了,以上都是哄孩子的玩意儿。在钱家祖,过年最隆重的仪式,应该是请祖宗。
腊月二十三那天。黄表纸买回来,在地上铺一层青灰,放一刀黄表纸上去,用铁模子在上面印铜钱。这种事一般需要家庭里的男孩子来完成,我弟那时年幼,由我代劳。铁模子放在黄表纸上,用锒头敲打,手都震麻了,密密实实,全是铜钱的意象,干这事,得跪着,以示虔诚。等我把所有的黄表纸都印上铜钱,我妈再把这些黄表纸拿在手里团一团,顺一顺,一顺就顺成了一把把纸扇子,交叠在那里,非常好看——黄灿灿的,不是铜钱,分明是黄金。
大公鸡早已杀了,它身上漂亮的尾翎已被我收藏起来留待日后做毽子用。烧滚一锅水,把整只鸡放进沸水里泖一泖,原本软塌塌的鸡在沸水里刹时精神抖擞起来,简直快要站起来奔跑了,我妈拿一根小竹签插在它的头脖间,搞了一个神似昂首打鸣的造型,非常完美地盛进大碗——这是接祖宗回来的一道主打菜。其次,一盘生腐烧肉,还有一道菜“磐”——也不知可是这样写法,音似。所谓“磐”,就是整块带皮大肥肉,同样放沸水里泖一泖就捞起装盘。我妈把这三盘菜分别装进腰篮,另外盛上三碗米饭,一头一只篮子挑着,装一包火柴,拿几刀黄表纸和一挂小炮竹。我就知道,她跟村里的大人无出一辙,这就是要到野外请祖宗去了。通常是门前的田埂,或者圩埂背风处,是太阳将落欲落的黄昏——黄表纸的灰烬随风飘荡,粘在大人的眉毛上,发上,拂一拂,仍不肯离开,舍不得的样子。
夜黑下来,头顶的星星很小很亮,把这些食物挑回家来,逐一摆上饭桌,给老祖宗再吃一次,再烧几刀纸,炸一挂小炮竹,叩几个头以后,菜被悉数收回碗橱里入定。我们再接着吃饭,无非一碗青菜,或者再添一盘腌雪里蕻。
从腊月二十四这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每天早饭前,必须盛三碗粥供在桌前给列祖列宗。然后,我们自己才能享用早餐。要说过年最烦心的事情,这个也算是一件吧。祖宗,我总是看不见,更不见他们出来喝粥。那么,这种盛粥的事情做起来,毫无意义可言。但,烦在心里,有敬畏在,到底不敢拂逆。
也许,所有祖先的灵魂在年关的时候,都愿意回来。在外飘荡了一年,也该回来歇歇了,我们做晚辈的,每天早晨盛三碗朴素的白粥给他们,也算是一种微薄的孝道吧——血缘的延续都在这三碗白粥里。
要说仪式感,这就是,虔诚、庄重。我们家的中堂画每每都是松鹤延年图,两副红底黑字的烫金对联左右并立,画下是枣红色茶几,紧邻茶几的是枣红饭桌,饭桌旁站立两把大木椅,同样是枣红色。过年的时候,堂屋里许多摆设都变得庄重起来,仿佛沾染了仙气,仔细想,跟往日也没什么不同,怎么到了过年,就有了异样?还是说不清。那几年,别人家开始流行张贴港台明星画像,塑膜的,被煤油灯微弱的光一照,恍惚地大放异彩,她们是汤兰花、林青霞、吕秀苓,一律琼瑶剧里的主角,无论戏里戏外,她们都那么美。七十年代末的少年生活,分外寒瘦寡淡,只能有她们给我们美的启蒙,不比如今的孩子,尚处黄口小儿阶段,就有巴赫和怀特来启蒙了——时代是往前进了几大步,革命性的,颠覆性的。
少年在腊月,被一种未知的情绪激荡着,连步伐都迈得轻快,哪里顾得了酷冷?一趟一趟往河边跑,卷起袖子,小手冻得彤红,协助大人把家里的什物洗了又洗,顺便抓点炒货放荷包里,抽空捻一点放嘴里,心下仿佛有大慰藉。那时,忙得连望天的事情都忘了,记忆里,总是阳光普照,天蓝云白。到了黄昏,坐下歇歇喘口气,又一个激灵,还没给牛喝水呢。于是,又急急望牛栏去了,把老水牛牵出,往村口池塘去。少年蹲在池塘边,看牛饮水,十多分钟之久,然后,老水牛抬起头,撒一泡尿,再次沉默地跟在少年身后,回它的家。
乡村的夜,是在这时候黑下来的。那种黑,像网一样罩在大地上,密不透风,四周群山不见了,对面的村庄不见了,偶尔几声狗吠,算是为黑夜划着了一根火柴,接着又暗下去。
第二天,太阳升起,钱家祖的大人小孩接着忙。忙年忙年,无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