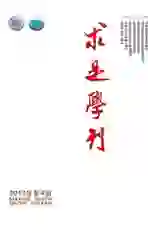中国私法法典形式的历史与现实
2013-12-29严城董惠江
摘 要:我国私法体系虽已基本完备,但因其在形式上体系化程度不高,有必要借助法典编纂的方式对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材料进行系统而科学的整理和完善,实现私法的体系化。从私法的分化和融合的历史变迁看,民商法间的关系在当今很难用“民商合一是立法趋势”这一论断来概括,影响立法更多的是既成的法律传统、立法者采取的立法政策以及统一国法的政治经济需求等因素。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并兼顾民商法的私法共性以及商法的诸多个性,通过制定民法典统率整个私法,并另定商事通则和完善商事单行法对其补充,实为我国当下法律体系和立法政策下的最现实合理的选择。
关键词:私法体系;民商法关系;法典编纂;民法典;商事通则
作者简介:严城,男,法学博士,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学院私法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民商法研究;董惠江,男,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民商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民商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090-09
一、中国大陆私法法典化的意义
一国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是其法律制度已完备,突出表现为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已经制定。中国大陆已相继颁布《民法通则》、《票据法》、《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物权法》、《保险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商事法律制度,虽然各项法律之间基本保持了一致,意味着我国民商事立法已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但在形式上却因为没有民法典而体系化程度不高……与私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严重不符”[1]。因此,我们需要借助法典这一工具将民商事法律予以体系化,其不仅是基于立法形式上的考量,更在于它是实现私法体系化的一个完美方案。[2](S.39)
法典作为一种立法形式,代表某一法律领域的完整规范,但究竟是否为最好的选择,自20世纪中期起就已在盛产法典的欧洲大陆引起越来越多的怀疑。意大利学者那塔利诺·伊尔蒂为此提出了“去法典化”的主张,其认为“特别法本来是作为对法典法的原则的例外或纯粹的展开而出现的,现在却控制了法律关系的整个类型的调整,并且施加上新的、具有不同逻辑的规范体制,表现出一般性、自主性的标准”[3](P98-99)。事实确实表明,继法国、德国、瑞士等声誉载满的民法典之后,鲜有新的高峰,而行政法、劳动法、社会法等新的领域,尽管法律常常多如牛毛,案例更是汗牛充栋,却始终无法产生一部和上述民法典并驾齐驱的法典,各色单行法成了唯一选择。这些单行法虽然增加法律适用上的烦琐,但并未偏离以法典为中心构筑的一国私法制度的内在逻辑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私法法典化的立法经验早已充分证明法典所具有的统一国法、揭示价值、体系效率、集中资讯、规范指引等重要功能。[4]中国大陆地区现行制度下从无私法法典,民商法法律均以单行法发布。即使从容忍各单行法之间的冲突和立法上的疏漏的代价以及缺少体系化思考的代价与“去法典化”的代价相比,仍然是前者更可取。此外,私法法典化也有利于法教义学思想在我国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得以深入贯彻,促进司法裁判的高效、公正和合理,纯化法律人的法律思维,借以进一步促进内在体系的不断完善。问题是,是民商法各自法典化,还是合一式地制定民法典或者商法典,抑或其他?[1]
二、私法分化与统一的历史流变
(一)私法分化实践与民商法典的分立
近代西方国家的私法来源主要有三:罗马法、教会法和中世纪商法。就商法史而言,商法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皆晚于民法。公元5世纪前的西方世界在罗马统治下,即使陆上和地中海沿岸存在一些商业交易,此间已高度发达的罗马法足以应付这些商事交易的需要。[5](P4)公元5世纪到11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国家间海上及陆上交易近乎停滞,商人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巡回兜售的小贩,并且从事贸易的也只是一些被派出推销商品的非专业人士。[6](P328-329)罗马法文献包含有适用于达成各种类型契约的一整套高度复杂的规则,这些契约包括金钱借贷、抵押、买卖、租赁、合伙和委任。然而,关于这些契约的规则并没有被自觉地概念化;虽然人们对它们加以分类,但却没有按照一般原则使它们明确地相互联系并对它们进行分析。而且在商业契约和非商业契约之间没有做出任何自觉的区分,所有的契约都被当作是民事契约。[6](P333)此时的民法概念和私法基本等同,并无商法的产生基础。
直到11 世纪晚期和12 世纪,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1“无论是重新发现的罗马市民法还是仅仅残存的罗马习惯法,包括万民法,不足以应付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各种商业问题”[6](P333),但“至少在个人主义的法律时代,商法总不断扮演一般私法的开拓者和急先锋的角色”[7](P73)。引领商法兴起的动力并非法学研究的结果,而是靠商人自己完成。11—12世纪农业的发展,产生大量可用于交换的剩余农产品,由此推动了商业城市的建立和海上交易的繁荣。面对纷繁复杂的商业交易,古老的罗马法已不足以规范这些新生的商业问题,私法一元化的格局由此被打破,其结果便是在民法之外产生独立的商法。“商法的制定在历史上是为了消除在民法形式主义束缚下商业交易的障碍,从根本上根植于加速经济交易的需要以及加强债权(更多和更准确地保护商业债权人)的需要。”[8](P67)
为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自发组成自治团体(Innungen,商业行会),按照已经发展起来的商业习惯(如汇票规则、海上保险契约、商业契约等)来解决商人内部的商事纠纷,并争取到独立的管辖权。他们组织国际集市和国际市场,组建商事法院,并在整个西欧的新城市社区中建立商业事务所。所有商事法院的程序都具有迅速和非正式的特性,起诉与答辩采不要式主义,抗辩及防御的范围不得超过一定的限度,并且案件主要适用商事习惯,依照良心和衡平原则来处理,而非世俗法院的形式主义程序或者是教会法院的成文程序。[6](P340-341)欧洲的统治者通过编纂商事习惯和整理保存商事法院的案件判决促进商业发展,为此大大推动了商法体系的自觉发展。商事习惯经由商事法院反复适用,逐渐形成具有国家强制力保证的习惯法,于是独立的商法由此真正产生。所以,从历史上看,商法一开始就是在民法之外独立产生并形成的。
时至近代,伴随着新兴国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经济上的高度繁荣,法、德等欧洲主要国家开始整理汇编普遍适于规范各国商人间具体行为的各种商事习惯法,由国家制定的成文商法取而代之。法国1673年的《商事条例》和1681年的《海事条例》便是最早的两部商事法规。1807年制定的法国商法典,则撷取二者之精髓,被公认为真正名副其实的商法典。[5](P8)德国在1861年亦师从法国,制定德国商法典,但其内容仅为私法规定,为纯私法立法的先驱。[5](P9)这一时期,欧陆各国继踵效法,分别于民法典之外制定商法典,一直影响到远在东方的日本和拉美国家。因此,近现代商法是以法典与民法分立的形式独立于民法存在的。
(二)私法统一思潮与民商法典的合一
自罗马法起,古代商法主要为罗马私法所包容,即使一些海事交易契约不是由市民法支配,而是由包括市民法在内的习惯法(如《罗德岛海洋法》和其他海上贸易习惯)所支配,并无独立商法的存在。唯因近代商法直接从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且只适用于商人阶层,因此商法并行于罗马法和教会法之外。尽管此后新兴资产阶级国家成立,陆续制定了商法典,但商法典的出现并非和19世纪前一样,仍带着浓重的身份等级,并且原则上和民法不相交叉。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首先不再把商人视为特殊的等级。这反映在《法国商法典》上,此一立法影响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但是1897年《德国商法典》则采取了主体标准,从商人角度界定商法。不过Canaris认为,商法的内涵与民法并无重大差异,唯一形式上的差异,是商法为商人的特别法,但由此仍然无法导出商法相对于民法的独立性。[9](S.8)正如《德国商法施行法》第2条规定的一样,民法规定仅于商法典无特别规定方有其适用。由此导出的问题是,商法究竟应融于民法之中还是并立于民法之外。
荷兰法学家Molengraaf、意大利商法学家Motanelli和Vivante等教授是私法统一论的主要代表者。Motanelli首倡民商二法统一论,为Vivante所支持而得势,其论据为:在一般社会生活进步的今天,商法规定的大部分事实上得适用于所有的生活关系,商法所提供的交易简易迅速、信用强化的便宜,并无保留于商法的正当性,此类规定仍置于商法,乃沿革的产物。商法典为保护大企业者利益的阶级法,编纂之际,仅征询大企业利益的代表者,牺牲一般市民的利益。再者,在民商二法适用上,区别的标准并不明确,二者并立易引起混乱,阻碍交易的安全,且因就同一事实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典,如适用不同的消灭时效期间,产生法律处理不公平的结果。且因妨碍私法全体的圆满及调和理论的形成,不利于私法学的发达。[5](P44-45)Vivante也认为,民商分立违背了社会生活的统一本质,“从而也自然违背了正义……民商分立会带来司法管辖权归属方面的许多不必要问题”[10]。
此外,和中世纪商人之间的纠纷主要依靠商人习惯法处理不同,尽管近代欧陆诸国多实行民商分立,但不免要承认商法的法律适用与民法仍有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商事交易是否有效成立、是否有意思表示瑕疵等问题,纵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亦甚少明文规定于商法典,而须回归民法的一般原则。此外,商法典的规定,纵然是民法所未规范契约类型,如交互计算、行纪、运送、承揽运送等,但其法律适用,无论是在学说发展还是实务上,大多数情形,均须与民法的规定并用,商法的规定绝少有独立适用的机会。[9](S.4-5)
私法统一浪潮的兴起推动了民商法法典的统一化运动。加拿大魁北克省于1865年放弃民商分立,改采于民法典中一并规范一些重要的商事规则。民商法合一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瑞士民法民商合一的立法例,但其并未制定如德国、法国一样的民法典,而是制定由民事规范和商事规范共同整合而成的瑞士债法典。1926年土耳其照单全收瑞士的立法例,几乎将包括债法在内的民法规定直接翻译为其民法典。[11](S.176f)1929—1931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亦采民商合一体例。原本采取法国体例的意大利,在1942年也改采民商合一。比较法上备受瞩目的1992年荷兰新民法,亦扬弃民商分立。[11](S.100)
以上是私法完全统一的思潮并表现为部分国家在法典上抛弃商法典而统一于民法典中。在同样有着民商法典分立传统的一些国家中,还有一种被学者称为“有限度的私法统一”的法典化运动。一些拉美国家因深受殖民统治的影响过去曾单独制定商法典,但自21世纪起,“以巴西为首的拉美国家‘让美洲发现自己’的声音日益高涨,掀起了努力摆脱葡萄牙、西班牙民商分立的立法传统,向意大利私法统一立法模式靠拢的修法运动”[12](P248)。如巴西新民法典专设第二编借以规范其企业法,而其商法典中的票据、破产等以及有关商人、商业公司和商行为的法律仍得以保留。
最近,日本民法修订研讨委员会在着手日本债权法修订时提出:“包含有关消费者交易、经营者交易之私法上之特别规定中的基本规范。”关于经营者交易,将商法典中“商行为”编中与营业的关联度较低的规定纳入民法典。[13](P23)可见,日本修法的设想,是谨慎地将部分商行为的规范吸纳到民法典中。
(三)民商法典分立的另一股风潮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多将商法的概念包括法典予以摈弃而只起草和颁布民法典。1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到21世纪初, 捷克、波兰、匈牙利等近十个国家为适应各自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需求纷纷重新开始审视商法的地位,兴起了一拨商法法典化的运动。2
与此情形相类似的亚洲的越南,早在1997年5月10日就颁布了商法典。此外,西非的加纳于2006年颁布了“商法守则”,由此也加入了商法改革的行列。
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在“脱亚入欧”进程中提出了“新商法改革”方案,也即单独制定商法典。据最新消息,新《土耳其商法典》已于2012年年初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并于当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替代此前已实施了半个世纪的旧版本。土耳其新商法典主要由企业、公司、证券、保险、海商和运输法六部分构成,其立法主旨在于“向瑞士法和欧盟法看齐,目标是建立公平竞争、信用至上的市场秩序,奠定以透明度和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法制基础,提供公司治理的原则,确立一般公认的会计和审计标准以及实现股东民主”[14]。新法首次将国际会计准则纳入土耳其国内法,旨在增加企业透明度,与欧盟立法接轨。评论认为,新法的实施将进一步改善土耳其商业环境,帮助吸引更多外来投资。
三、民商法典分立与合一的理性分析
以上民商法典发展变化的历史实践,至少说明民商法的关系很难用“民商合一是立法趋势”3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如果说20世纪初开始的民商合一思潮及以民法统一私法的立法实践,相对于之前的主要国家民商法典各自独立的状况已经呈现出一种趋势性的态势,但随后一直不断的理论争议和近二十年欧亚非诸多国家另立商法典的事实,已经足以构成对这种所谓“趋势”的否定性怀疑。
从上文可知,现代商法起源于商人自己所形成的商事习惯,是为适应地中海商事贸易的发展而在商人间独立发展起来的,其一开始就独立于民法之外。中世纪西方国家的私法学者也只是关注罗马法研究,商法不受欧洲传统民法主流学说的关注,但基于商事交易的实际需要,商事实务独立自主地形成其自由的习惯与法则。正是因中世纪固有法无法满足商人阶层的特殊需求,商人因此自己主导商法的形成,建立起适用于商人阶层的特别法。其一经产生,便自治自立,与罗马法平行发展。其后,随着国家中央集团制的出现,商事习惯经由主权者的采用,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成为一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法官不能根据经济要求的改变而相应调整法律,只能以谦逊的克制去适用传统的法律,致使一个特别的商法必须产生”[7](P72)。15世纪后,资本主义商业市场日益繁荣,原先割据的经济和分散的立法严重妨碍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和国家统一市场的建立,贸易的发达迫切需要在一国之内实现商业交往规则的统一。基于此项经济立法上的迫切需求,亦有力地推动了商事成文法的制定。因此,19世纪商法典的诞生,更多是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为解决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而生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
至于民法商法的融合,最根本的基础当然是二者私法的共同属性。因二者同属私法,商法和民法从来就没有深刻的不同。当商法发展到了现代,所谓商人这个特殊的阶层早已不复存在,甚至特殊的商行为也失去其纯粹性。像票据制度、保险制度已普及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全社会的人所利用与参与。因此,仅为只规范社会生活中某一特殊方面,或规范社会中某一特殊阶层的商法已失去存在的依据。[15]当商事活动日益扩张,社会生活并不会因为民商法各自规则的独立存在而不相往来地运行。比如,因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解决商事纠纷不再简便,甚至出现归民事法庭或商事法庭来管辖的纷争时,自然会产生民商合一的诉求,民商合一的价值理性也才会被重视起来。商法从中世纪的商人法经近代民族国家的商事立法而发展到今天,由于商事活动的扩张和商人概念的泛化使得民商法之间本就不甚清楚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16],从而出现所谓的“民法商法化”(如我国《合同法》中诸如融资租赁、行纪等商事合同的规定)和“商法民法化”(如司法适用上商法对民法的依赖)现象。正如当今社会,即使存在公法私法的划分,也出现了“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现象。不同法律部门正打破壁垒,互相借鉴、互相配合,综合调整社会关系,这应该可以作为江平先生“民商融合是趋势”的真正解读。
但是,商法原本就是法律体系中最具发展性[17](P14)和进步倾向[18](P8)的部分,否定商法独立性绝不可以拿早期的商法及其社会背景做靶子。商法产生的初始固然是为规范商人这一特殊阶层的法律,包括其特许主义的特权,但现代商法早已不再将商人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予以保护,商人群体也扩展到具有营业能力的一切个人和组织。例如,德国商法典中的“商人”不仅包括营利性法人、合伙,也包括自然人商人,其范围远大于传统商法中的商人概念。事实上,尽管瑞士等国家改采民商合一,但是其学术界仍肯认商法在实质层面上的独立性,毕竟商法旨在规范商人(尤其是企业)所从事的营业活动,和一般民众的法律行为差别甚大。“尽管商法和民法(尤其是债篇)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的法律,有其共同的原理,但论其性质,两者颇有不同。盖商事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19](P123)基于彼此规范目的较大的差异,民商事法律在各自具体规范领域内所持有的价值取向、立法目的、信赖保护程度以及对规范主体的注意义务程度、法律行为的评价、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承担方式等也自然有着差别。陈自强教授就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之关系以及商事契约和民事契约之关系在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下的境遇做了详细考察,其通过研究指出,无视商行为的特殊性,一味依照民法规则处理案件,反而在实践中造成不公平的结果。1
当两种理论难分轩轾,影响立法更多的是立法政策或政治上的因素。时至近代,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商品交易的繁荣和以宗教为核心的封建割据势力的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开始逐步形成。原先分散于自治城邦和商业团体的立法权逐渐归结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主权者汇集商人的商事习惯和汇编而成的商事法院的判例制定成国家法律统一适用于全国,其意义与其说是满足商业交易的规范需要,毋宁为借此宣示和稳定其统一的、无上的主权。[20](P28)对于民族国家的建立,法律,特别是法典以民族语言象征统一而唤起认同,加上其内容散发的共同价值,可以不带强制地轻易深入民间角落,视为极佳的统合工具。[4]因此,从政治层面看,不论是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都是主权者统一国法,宣示主权的一项工具。
简言之,19世纪欧陆国家民商分立法典化的历程,并不在于主张民商合一的理论欠缺说服力,而在于政治和历史的特殊背景。而瑞士采民商合一,亦并非落实民商合一论的主张,而纯然系政治上时间的因素有以致之。[21](P353,357)其后,形式上或实质上政治统一大业完成后才进行民法法典化的国家,先前既然无商法典的存在,眼前又有法国、德国等民商分立法典为现成的范例,自可优哉游哉决定是否采取民商分立或民商合一,此为立法者法律政策的决定,如何建构私法体系,立法者有相当大的决定空间。一旦采行民商分立体例,学者再对民商合一的观点予以辩驳,不外正当化立法者的决定。1比如越南商法典基本承袭了法国商行为主义立法模式,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则干脆复活社会主义前的旧商法。[22](P186-300)
如前述分析,本文并不赞成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是立法趋势”这一论断,但也无意更深介入合一论、分立论何者为优的讨论,并且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主张民商法典合一的一些学者,也并不否定商法实质上的独立性。在这个前提下,民法与商法的法典形式如何选择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四、中国大陆民商法立法的形式选择
坚持商法的实质独立,是不是一定要选择商法典独立的立法形式呢?我们知道,法典质量的高低以及成功与否,需要看它在社会关系变化之后能否完成其规范预设的功能,而不需要制定新的法律。“由于体系化编纂涉及大量的法律材料和事实材料,因此就面临一个危险,即法典获得成功后不能认识或不能充分认识新时代的要求。对于《民法典》和《商法典》必须承认,它根据的是关于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方式及需求的过时的观点。”[23]但是,德国的经验至少已经告诉我们,回顾德国民法典百年史,它总是为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的私法关系提供根本性和规范性的标准。Manfred Wolf教授分别从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一般条款、基本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宪法的影响和欧盟法律的影响等五个方面论证了民法典能适应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变化的原因。[23]
但是商法毕竟不等同于商法典,如果说人类的经验肯定了商法的不可替代性,商法典的制定与否始终还只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它的内容和形式,当然也应在回应时代新变化之时予以详细考量。商法从一开始便带有商人习惯法的局限性,是商人利益的典型体现,更是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的产物,其制法过程缺乏类似于民事立法那样的理论准备。在缺乏理论准备下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商法体系,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其内容被不断修改和补充。法国商法学者克洛德·商波指出:“《法国商法典》起草仓促,杂乱无章,人为地把商事活动圈定在一个‘法律隔离区’内;然而事与愿违的是,19世纪、20世纪是在商人‘法区’之外发展工商业及创建相应法制的世纪。”[24](P10-11)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法典被多次修订和补充,许多内容已从法典中删除,仅有30余条原始条文尚存规范效力,几乎为因新经济形势所需应急而生的各部单行法所架空,这些重要的法律有1867年《公司法》、1909年《营业财产买卖设质法》、1919年《商事登记法》以及后来制定和修订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证券交易所法》、《保险契约法》等。法国于1958年最终放弃《法国商法典》的全面改革计划,继续在法典之外以另立单行法的方式修补商法典。此外,法国商法典不论是在措辞上还是在规范质量上, 都远远不及民法典。造成这些法典低质量的原因,是这些法典的起草者没有或者很少有模式可以遵循。[25](P165-170)德国商法典则采主观主义立法例,商人是商法典的中心,因此很多商行为法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被排除在法律之外,如票据法。商事组织法原则上也不属于商法典的内容。德国商法典尽管私法性纯粹,但仍免不了被大量修改的命运。1937年《股份法》被从法典中取出,成为独立的法律。1953年和1989年两次修改了代理商法。1998年商人概念和商号被重新构建,并且同年运输和仓储法亦被彻底修订。此外,在法典之外存在着诸多因时因势而制定的单行法,如1892年《有限责任公司法》、1908年《保险契约法》、190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证券交易所条例》、《合作社法》等。日本商法典坚守的相对更为持久,但也在21世纪初完成了公司法等商事部门法的出逃。此即所谓“商法的改革不是来自商法典的完善,而是来自法典以外的单行法”[26]。
由此可见,尽管在私法体系内商法仍是形式上重要的部门法,但是它在法典意义上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民法因其调整私人间的关系,在和公共利益的考量中原则上有优先的地位,反而使得民法不必随着公共政策的变化而变动不居,民法典越能维持私法的纯净,就越有持久性。[4]而商法与民法相比,含有更多的公法因素,这使得商法常因涉及市场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尤其是消费者利益、社区等利益,受新的公共政策、新的立法或者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做出频繁的变化。然而一国的法典具有固有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征,能给其国民以指引、评价、预测和惩戒等规范作用。而商法一旦制定成法典,频繁地修改无疑会给法典的权威和稳定性涂上暗淡的色彩。
从以上主要国家商事单行法纷纷独立于商法典之外,及其背后原因合理性的描述,传统商法典渐渐收缩于商主体、商行为等一般规定的变化,倒可以用“趋势”一词来形容。这个时候,这些国家的商法典已不再是包括商事部门法的商法典,或不再是包括主要商事部门法的商法典了,此时我们再去搞商法典恐怕就是走回头路和不合时宜的了。1那么,不再追求独立的商法典,是不是就必然选择或者契合了民商合一的思路了呢?即或者像瑞士、意大利那样,将商法的大部分内容都纳入民法典,或者像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那样,将商法一部分内容纳入民法典,而公司、票据、保险、海商等商法的主要内容则采用单行立法。这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民商事立法的现实。
中国大陆地区在对待民法和商法上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但总体方向是在民法之外并不制定单独的商法典。就民法而言,在民法典一直缺位的情况下,通过分批陆续制定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作为民法典组成的各项单行法的方式,渐次为民法典的最终制定打下基础。同时,这种分步走的立法模式又可以把民法的法典化作为修正现行法律的一次机会。2同时,立法当局也试图把当今世界私法发展趋势下原本属于商事法而今上升为民法的一些规则予以吸收,扩大民法的包容性。而商法的立法形式,除了陆续制定重要的商事单行法,如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和破产法等,还在地方具体实践商事通则条例的运行效果。如此的设想和实践,中国大陆无疑是在走民商合一的道路,并且形式上更接近中国台湾地区的民商合一形式。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大陆司法裁判机关审判庭的设置经历了自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取消经济审判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至2009年又提出设立专业商事审判庭的设想的变化。3现在,全国各级法院已纷纷设立商事审判庭,独立审理商事案件。这也说明私法关系,一概交由民法解决,恐怕是不切实际的臆想。接下来的问题是:独立的商事审判面临立法资源的空位,即现行商事法律缺少关于“商人”制度和“商行为”制度的规定,而这些制度由民法来规定,至少是缺乏对商事关系特点的尊重。自江平先生主张“在民法典之外另立一部商事通则”[27],该主张现已成处理民法和商法关系在立法形式选择上的通说。由此可见,通过考虑民商法的私法共性制定民法典,并考虑到商法的个性另行制定商事通则,从而形成以民法典、商事通则、商事单行法并行的私法体系,应该是我国当下立法政策的现实主义选择。
结 论
我国私法体系虽已基本完备,但因其在形式上体系化程度不高,有必要借助法典编纂的方式对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材料进行系统而科学的整理和完善,实现私法的体系化。为实现此项目标,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法典编纂才是当下中国最现实的选择呢?从人类私法的分化和融合的纵向历史变迁来看,民商法之间的关系在当今很难用“民商合一是立法趋势”这一论断来概括。如果说19世纪欧陆国家民商法典分立化的历程,根源于政治和经济的特殊历史背景,那么当这些背景不再成为法典编纂的主要考量因素时,20世纪初开始的民商合一思潮及以民法统一私法的立法实践同样也并未成为此后一贯的立法趋势,至少近30年来欧亚非诸多国家另立商法典的事实,已经足以构成对这种所谓“趋势”的否定性怀疑。无论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法律实践,都表明民商法律只是在理论甚至规范上的融合,而非法典意义上的融合。当两种理论难分轩轾,影响立法更多的是该国既成的法律传统、立法者所采取的立法政策以及统一国内市场交易领域的基本法律的政治经济上的因素。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并兼顾考虑到民商法的私法共性以及商法的诸多个性,通过制定民法典统率整个私法,并另行制定商事通则和完善商事单行法对其补充,实为基于我国当下法律体系和立法政策下的最现实合理的选择。
参 考 文 献
[1] 王利明. 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民法典制定[J]. 广东社会科学,2012,(1).
[2] Karsten Schmidt. Die Zukunft der Kodificationsidee: Rechtsrechung[M]. Wissenschaft und Gestzgebung vor den Gesetzswerken des geltenden Rechts,1985.
[3] 那塔利诺·伊尔蒂. 解法典的时代,薛军译[A]. 徐国栋.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4卷[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苏永钦. 民法典的时代意义——对中国大陆民法典草案的大方向提几点看法[J]. 月旦民商法研究,2004,(3).
[5] 大隅健一郎. 商法总则[M]. 东京:有斐阁出版社,1994.
[6] 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7] 拉德布鲁赫. 法学导论,米健译[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8] 马沙度. 法律及正当论题导论,黄清薇,杜慧芳译[M]. 澳门:澳门大学法学院,2007.
[9] Claus Wilhelm Canaris. Handelsrecht[M].23 Aufl.,Müchen: C.H.Beck,2000.
[10] 米健. 现今中国民法典编纂借鉴德国民法典的几点思考[J]. 政法论坛,2000,(5).
[11] Zweigert/Kötz.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M].3 Aufl., Tübingen:Mohr Siebeck,1996.
[12] 阿尔多·贝特鲁奇. 在传承与革新之间的巴西新民法典,薛军译[A]. 徐国栋.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5卷[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3] 大村敦志. 日本民法修改的现状(2)——以民法(债权法)修改研讨委员会草案为中心,解亘译[A]. 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九卷)[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4] 官欣荣. 破解“商事通则”立法迷局的开放式新进路[J]. 法学,2010,(8).
[15] 谢怀栻. 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三)[EB/OL].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761.
[16] 尹彦久. 论民法商事化与商法民事化[J]. 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1).
[17] 叶林,黎建飞主编. 商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8] 末永敏和. 商法総則·商行為法基礎と展開(第2版)[M]. 东京:中央経済社,2006.
[19] 张国健. 商事法论[M]. 台北:三民书局,1980.
[20] John Henry Merrymann. The Civil Law Tradition,2ed[M]. California:Stanford Unibersity Press,1985.
[21] Eugen Bucher.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Schuldrechts im 19. Hahrhundert und die Schweiz[J].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2003,(2).
[22] 徐国栋. 东欧剧变后前苏联集团国家的民商法典和民商立法[A]. 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14卷)[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3] Manfred Wolf. 民法的法典化,丁晓春译[J]. 现代法学,2002,(3).
[24] 克洛德·商波. 商法,刘庆余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5] 艾伦·沃森. 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6] 郭峰.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评析[J]. 中国法学,1996,(5).
[27] 江平. 关于制定民法典的几点意见[J]. 法律科学,1998,(3).
[责任编辑 李宏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