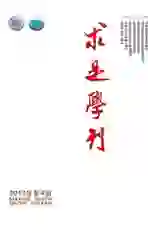休谟法则和拯救实践
2013-12-29马万东
摘 要:休谟法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疑难问题,它不仅抽空了价值判断的理性基础,而且质疑理性对行动的指导作用,从而对人类的理性行动或实践构成严峻挑战。从述谓或判断的分类入手,可以揭示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传统二分的基础上不足以对理性行动进行有效辩护,并提出比较性述谓和归属性述谓的区分来替代传统二分。以“好”为谓词的价值判断固然不能还原为事实判断,但是可以还原为比较性述谓,比较性述谓所蕴含的“知好选好”结构则表明了价值判断的理性特征以及理性和选择的内在统一,由此理性行动得到了更为有效的辩护。从比较性述谓到归属性述谓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不是从“是”推出“应该”,而是从“应该”推出“是”。
关键词:休谟法则;实践;比较性述谓;归属性述谓
作者简介:马万东,男,哲学博士,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研究成员,从事实践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方德性伦理学视域中的功能论证研究”,项目编号:13YJC720028;中山大学“985工程”三期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B561.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031-08
休谟在哲学史中常常作为怀疑论者出现,20世纪40年代,学者们开始试图扭转休谟的传统形象,转而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解读休谟,但不可否认的是,休谟提出的很多见解和问题不仅惊醒了康德这样的大人物,也激发出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样的哲学工作方式,直到今天依旧构成难以回避的理论挑战。
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第一节最后一段话中如是说道:“对于这些推理我必须要加上一条附论,这条附论或许会被发现为相当重要的。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需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1](P509-510)上述休谟所主张的不可能由一些“是”命题推出一个“应该”命题,被20世纪英国元伦理学家黑尔(R. M. Hare)称为“休谟法则”1。休谟法则不仅对当时传统的伦理学体系构成挑战,对当代的伦理学也同样构成挑战,究其根本在于,休谟法则明确指认行动的根源在于激情而非理性,从而瓦解了人类行动或实践的理性基础。因此,对休谟法则的挑战提供一种回应或解答,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理性行动的拯救,而这其实正是休谟之后许多思想家所致力的工作。本文也试图直面休谟法则的挑战,加入到为人类理性行动辩护的行列中去。
正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就现当代哲学家对休谟法则的两次回应做一简要考察和梳理,使休谟法则所提出的问题意识能够更加明确;其次阐明比较性述谓是比价值判断更加根本的述谓形式,也能够为人类行动提供一种理性基础;最后借助比较性述谓向归属性述谓的转化,揭示出人类行动的发生机制其实不是从“是”推出“应该”,而是从“应该”推出“是”。
学者们对休谟法则的回应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自20世纪以来,通过对休谟法则的回应而积累起大量学术文献,形成研究规模、蔚为风潮的则有两次:一次是元伦理学研究;另一次则是道德心理学研究。这里按顺序择要评述如下。
摩尔于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开创了元伦理学的研究进路,并与亚里士多德专家罗斯的《正当与好》(1930)一道作为元伦理学早期代表著作致力于“好”的问题研究。摩尔认为,形容词之“好”(good)不同于名词之“好”(the good),形容词之“好”如同“黄色的”一样,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此是不可定义的,也不能被还原为类似“快乐的”、“希望得到”等经验语词,否则就犯了所谓“自然主义谬误”。摩尔显然继承了休谟关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分2,领会到诸如“黄色的”和“好”这样的谓词之间存在质的差异,而“好”的不可还原性,无非就是“从是不能推出应该”的另一种表达。正因为“好”这种特殊性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摩尔只好诉诸直觉,成为所谓“直觉主义”3的代表人物。
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则将元伦理学研究推向尖锐化。按照逻辑实证主义所秉持的可证实性原则,命题或判断被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描述事实,因而可以被经验证实的命题,这是有意义的命题,称之为“综合的”判断;还有一类命题不以经验为转移,而是按照命题本身的用语或者说基于逻辑规则就能决定其真假的命题,这也是有意义的命题,称之为“分析的”判断;还有一类命题,包括形而上学的、伦理的和审美的命题,因为不具有真假值,只能归为“认知上无意义的”判断。[2](P11)这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把包括道德命题在内的价值判断一并否定了,价值判断的合法性危机至此大白天下,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艾耶尔作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即试图解决上述问题,他也同样认为伦理语词或价值语词不能还原为事实或经验语词,但是直觉主义的取向却不符合可证实性原则,因此,他转而寻求其他出路。
艾耶尔将伦理命题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表达伦理学的词的定义的命题,或者关于某些定义的正当性或可能性的判断;第二类是描写道德经验现象和这些现象的原因的命题;第三类是要求人们在道德上行善的劝告;第四类是实际的伦理判断。[3](P83)艾耶尔进而认为第一类命题才构成伦理哲学,而第二类命题应该归属心理学和社会学,至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命题则是对某种特定态度的表达,因此伦理语言其实是为了表达或激发情感。这就是艾耶尔就价值判断给出的“情感主义”出路。
如果说在艾耶尔那里伦理判断只是可证实性原则“切割”世界留下的“剩余”,查尔斯·L. 斯蒂文森则将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视为这个世界的常态,因此对价值判断的语言分析就成为其《伦理学与语言》的全部主题。在他看来,我们关于事物的诸多争论和分歧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信念分歧;一种是态度分歧。就我们的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而言,其实往往既包括信念问题,也包括态度问题,因此“如果说传统理论经常只见信念不见态度,那么我们一定不能犯相反的错误,只注意态度而看不见信念”[4](P29)。斯蒂文森还进一步认为,信念问题往往与陈述句相对应,表达的是一种语言的描述功能;而态度问题往往与祈使句相对应,表达的是一种语言的情感功能。以“这是好的”为例,按照摩尔的观点固然是不可还原、不可定义的,但是不容否认该价值判断所发挥的实实在在的心理作用,上述命题的实际意思是说:我赞成它,你也赞成吧!斯蒂文森将第一部分“我赞成它”视为描述性陈述,描述的是说话者的态度;第二部分“你也赞成吧”则是祈使性的表达,致力于改变或加强听话者的态度。因此,价值判断绝不是只有情感功能(这并不是否认具有独立情感意义的价值判断),往往同时具备描述功能,语词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就是明证,因此,元伦理学的研究就不能人为割裂信念与态度,而应该将二者的关联视为分析重点。
黑尔从祈使句的分析入手,认为道德语言的首要特征是一种规定性语言,而不是一种描述性语言,因此不能混淆陈述句和祈使句之间的区别;道德语言的规定性特征乃是促使一个人去行动,是一种命令,而不是如斯蒂文森所说的一种“态度”,因此也不允许混淆“告诉某人某事和使他信或做别人所告之事的区别”[5](P14)。由此,黑尔明确提出一条实践推理规则:“如果一组前提中不包含至少一个祈使句,则我们就不能从这组前提中有效地引出任何祈使式结论。”[5](P28)黑尔在《道德语言》一书的第二、三部分就通过对“好”和“应当”等价值词的分析表明了道德语言和道德行动相关联的推理机制,从而完成了元伦理学研究中最为成熟的理论建构。
透过对元伦理学发展线索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摩尔到黑尔的元伦理学研究的根本用意在于通过对道德语言的分析和论证来解释并拯救道德行动,这一点特别是经由黑尔的工作才得以明确的。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上述学者们的基本观点与休谟法则的关系十分密切,或者是休谟法则的延伸,或者是休谟法则的回应,或者就是休谟法则的语言哲学版本,充分显示了休谟法则的思想生命力。黑尔通过对休谟法则的创造性使用,区分出价值判断的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并认为价值词的使用是与我们的行动和选择直接相关的,但是价值词如何与行动相关,描述与评价两种意义如何关联以及理性在其中有何位置等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这是英美学界对休谟法则的第一次现代回应留下的问题。
英美学界对休谟法则的第二次现代回应则主要体现在道德心理学的研究。1由于该领域问题众多、论证复杂,本文只择其一点予以简要评述,以窥其一斑。在英美学者关于实践理性的争论中,对行动理由的解释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般来说,如果存在着某个东西,一个人有欲望获得这个东西,并相信采纳某种行动即可以获得,那么,这样一种引发行动的理由就可以称之为“动机性理由”,这是休谟主义的观点;康德主义者则认为,不管一个人有没有欲望做某事,他都应该做这件事情,与此相关的理由可以称之为“规范性理由”。[6](编者导言P5)在康德那里,规范性理由是由实践理性给出的,也就是说人的行动受实践理性的激发和指导,而实践理性的存在是无须证明的,或者说已经通过纯粹理性的证明完成了。上述观点激起了休谟主义者的强烈反弹,他们对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指导行动疑虑重重,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对实践理性的怀疑论。按照科斯嘉的看法,这种怀疑论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认为理性无法为选择和行动提供任何实质性引导,理性也无法确定我们的目的,而只是限于确定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称之为“内容怀疑论”;还有一种则认为理性不能激发行动的动机,所有具有动机性影响的推理都必定始于激情,这是动机的唯一来源,称之为“动机怀疑论”。[7](P294)[8](P314)
康德之所以强调“规范性理由”,本意是要和动机、运气等因素撇清关系,对一个行动的发出只问是否“应该”,不及其余。但威廉姆斯在《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一文中发展了一个休谟主义的论证:一个行动的发出必有理由,理由若想激发行动必须是动机性的或者与“主观动机集合”相关联,所以行动的理由只能是内在的。[9](P144-161)威廉姆斯的论证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因为他的论证会引发对康德主义者而言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我们假设有一位教师(这样的假定比较没风险),在其“主观动机集合”中只有酒色财气,而且依此而行,但是没有教书育人这样的“应该”,那么,按照内在理由,岂非是合理的?从根源来看,威廉姆斯其实是从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出发,即一个行动已经发生之后再来反问其理由,那么,任何一个行动必有动机性理由或由此得到说明;而康德主义者对行动的观察视角则是在一个行动发生之前来追问如何选择,那么,“应该”岂因其他动机的生灭而不复存在呢?所以有康德主义者批评威廉姆斯的内在理由并没有提供选择或行动的规则。因此,概略说来,威廉姆斯强调的是动机的复杂性和选择的真诚性,而康德主义者强调的是选择的多样性和“应该”的绝对性,二者并不构成针锋相对的对立和反驳。1但是,有了上述挑战之后,康德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就必须承担“理性如何引导行动”、“理性如何与动机相关联”等问题的解释任务。
综上所述,休谟主义者在道德心理学研究中其实又一次重申了休谟法则,只不过把原来的“是”与“应该”转换为理性与激情的关系问题:行动的发生不能诉诸理性,而只能诉诸激情,按照休谟自己的说法就是“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2;理性不是别的,而只是对能够达成目的之手段的慎思。这样,休谟法则就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人类的理性行动,使我们徘徊于非理性主义者和工具主义者之间,而若想拯救实践,拯救人类的理性行动者的身份,就不得不直面上述两次回应留下的两个问题:第一价值判断到底是不是理性的;第二理性如何引导行动。
无论是休谟关于“从是不能推出应该”的论断,还是摩尔对“好”不可定义、不可还原的强调,抑或是黑尔对价值判断既有描述性意义,又有评价性意义的表述,其实就是在以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表达同一种洞见: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异质性。但是对上述二分法的习惯性依赖,使当代元伦理学家们断然拒绝了价值判断之“可还原性”的思路,因此转而诉诸直觉、情感等非认知因素,以此表明价值判断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其实,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的异质性和价值判断的可还原性之间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价值判断并不见得非得还原成事实判断,倒是可以进一步还原为比较性述谓。
在现代英语中,形容词(某种意义上就是价值词)有一种所谓比较级的形式,表示“比……更……一些”这种比较的关系和结果,因此,只要谓语是以比较级的形式出现,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比较性述谓,最常见的如“It is better”。1至于我们所说的价值判断,其谓语虽然是以原级形式出现,如“It is good”2,但究其实质也是一种比较性述谓,只不过隐藏了比较的语境和标准。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以“is”的形式出现,因此更具普遍性和客观性,但同时也更具迷惑性。姑且不探讨“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样复杂的问题,就“德系车好”还是“日系车好”而言也已经足够令人困扰了。
以购车为例,如何确定是“德系车好”还是“日系车好”,显然是比较出来的。我们可以列出各种一般性的比较标准,如安全性、舒适性、环保性、经济性、耐用性、美观性等等,同时还要区分出不同等级,因为显然不能将豪车级别与入门级别等量齐观,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同一等级(如同一价位)中就安全性、舒适性、环保性、美观性等标准进行一一比对,让较好的一方胜出,然后在这些不同组合和不同等级之间进行再比较,直到最后选定一款车型。通过上述购车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性的价值判断已经淡化或遮蔽了比较性的特征和语境,因此如果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价值判断层面进行争论,就会变成无谓的语词之争,只有将其转化或还原为具体性的比较性述谓,我们才能触及问题的根本。
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还可以揭示出比较性述谓的层级结构:
A.德系车好;
B.德系车好在安全;
C.就同级车的安全性相比,德系车比日系车好。
在A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好”的使用是非常一般性的,几乎看不到其比较性的意涵,其表达也是最为简略的;而在B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的具体标准已经呈现出来;在C中,不仅比较的参照系、标准和范围,而且比较的具体语境都完整地呈现出来了,其可检验性也是最强的。由此,我们可以将A称为“种词之好”(genus good),B称为“属词之好”(species good),C称为“比较之好”(better than)。3无论是哪种层次的“好”,只要充当谓词,我们就称该述谓为比较性述谓,只不过有的表现得明显一些,有的隐蔽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在威廉姆斯那里,他把“种词之好”称之为“稀薄的”概念,而把“属词之好”称为“厚实的”概念,却未能进一步揭示出“比较之好”,也就不能完整地看到比较性述谓的层级结构,由此做出“厚实的”、“稀薄的”这样的概念区分就显得似是而非了。
价值判断的“可还原性”问题一旦解决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价值判断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休谟主义者因为固执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两分,又把理性和事实判断严格对应起来,因此不得不将价值判断归为非理性,难免让人心生明珠暗投之恨。休谟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其理论预设过强,只看到了理性与信念之间的关系,却没有看到理性与比较之间的关系。上文我们已经揭示了价值判断可以还原为比较性述谓,那么,比较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呢?如果说像大小、高低、明暗、冷热这样的比较还可以诉诸感官知觉,那么,像好坏、美丑、勇怯、智愚、正邪这样的比较就不能诉诸知觉,也不能诉诸欲望或情感,而只能诉诸理性。想想我们对西瓜、玉石、钢琴等物品的好坏评判和挑选,挑西瓜我们还可以应付,而对玉石、钢琴的挑选和评判却只能有待于专家为之,这里面增加的显然不是知觉的强度,也不是欲望的大小,而只能是理性(化)的含量。理性不仅仅体现在具体性的优劣比较中,而且也体现在一般性的价值判断,因为从具体的比较性述谓上升到一般性的价值判断之过程也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因此,借助比较性述谓这一视角来看,价值判断就不能被归为非理性的,而恰恰是理性的。1
如果上面的论证成立,那我们就解决了元伦理学家们留下的问题之一,即价值判断是不是理性的(仅就“好”而言),但是还有一种价值判断的形式是“应该”,又该当如何呢?日常生活中我们人人都有体会,明知生命在于运动,可是偏偏不能付诸行动。休谟主义的道德心理学家们为了解决上述“是”与“应该”之间的鸿沟,提出动机概念,认为一种行动必须有一种动机或欲望的激发,仅凭信念则不足以引发行动。这实际上提出了理性如何与行动相关联的问题。当代英美学者在探讨上述问题时的一个通病在于其所使用的“行动”、“好”等概念在概念层级上太高,含义过于复杂,因此无法看出二者的关联。2就“行动”而言,英美学者在安斯康姆的影响下往往强调其“意向性”,可是“意向性”概念并不能帮助我们对行动进行有效的分殊。相比之下,德国学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将行动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韦伯和哈贝马斯把行动划分为四种类型,就更具思想力度。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对“行动”和“好”采用一种紧缩策略,将它们从较高的概念层级回溯至较低的概念层级。当我们将“行动”紧缩或具体理解为选择(因为再复杂的人类行动也能从中辨识出选择因素,选择其实是人类行动的原初形态和基本特征,比如采集活动),而把“好”从“种词之好”下降到“比较之好”(所谓比较之好,就是两两比对的优劣判断,例如两种茶叶、两个苹果、两间办公室之间的比较),则行动和理性之间的关联已经昭然若揭。就挑选活动而言,人们总是“知好选好”(know better,choose better),想想我们买苹果时对苹果的挑选,孩子入学时家长对入读学校的挑选,写作论文时对材料的挑选,乃至对于记忆的挑选,无不遵循“知好选好”的原则。“知好选好”其实也是苏格拉底“无人自愿作恶”这一命题所试图揭示的道理所在,因此,只有在这里,“知道一事物是好的”和“应该如此行动(选择)”,也就是“是”与“应该”是合二为一,了无罅隙的。比较和选择其实是内在统一的,人类的整个生活世界都是在不断比较和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至于苏格拉底式的对“好”无知以及“知好不选好”的意志薄弱问题,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这样,我们就通过将价值判断还原为比较性述谓,一方面揭示了“好”这种类型的价值判断是理性的,另一方面则揭示了人类行动的基本结构乃是“知好选好”,在选择活动中,“是”与“应该”是合二为一的。本文对休谟法则的回应和对理性行动的辩护就基本完成了。
休谟法则所做出“是”与“应该”的传统二分,其实是一种教条,已经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理论困难,而按照普特南的说法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本文不准备就此展开论述,而仅就休谟法则自身做进一步分析和澄清。休谟法则带有一种先在的理论预设,即认为事实判断比价值判断更基本,因此才否定价值判断还原为事实判断的可能性。但真是如此吗?本节笔者试图反驳这一成见。休谟法则还有一个缺陷在于对价值判断的界定含混不清,元伦理学家们认为价值判断不仅包括“好”(good)和“应该”(ought),还包括“正当”(right),并在三者的关系上大费笔墨却难有公断,价值判断问题俨然成了混乱之源。重新考量一下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二分,其划分的依据源于谓词的差异,“黄色的”与“好的”被用作谓语时显然是不同的,这一区分后来又被学者们从述谓功能的角度表达为描述性判断和评价性判断。但是即便如此,上面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事实判断,如“这是一面国旗”、“国旗是红色的”,往往被认为是最根本的语言功能,但是,这一点遭到了维特根斯坦的有力驳斥,“似乎只有一件事情叫做‘谈论事物’。其实我们用句子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只须想一想各种呼叫。它们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10](P16-17)。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只是一种工具(这其实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观点,因为亚里士多德把相关考察称为“工具论”),有多种多样的用法,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奥斯汀也认为,事实判断其实是将语言的功能限定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中,而语言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才更基本,并认为语言即行为,由此开创了言语行为理论,进而区分了“话语行为”(locutionary act)、“话语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话语施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1姑且不论上述两位哲学家的具体观点如何,将语言和行为或者说语言和实践相勾连的这样一种致思取向是极富洞见的。我们可以循此思路进一步追问,事实判断除了描述之外还有什么作为?在事实判断中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即除了专名之外,所有的谓词都是普遍性的。通过对普遍性谓词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普遍性的谓词除了进行描述之外(如“这是红色的”),还可以用来分类(如“这是波斯猫”),也就是将一事物置于种属关系中(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问题),而一旦种属关系成立则推理活动就出现了。2因此,事实判断并不仅仅是用于描述或命名事物,更为重大的意义是用于分类和推理,由此将其界定为归属性述谓才更为准确。这样,结合上一节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重新界定为归属性述谓和比较性述谓。那么,归属性述谓和比较性述谓相比,哪一种述谓更为根本呢?答案是比较性述谓,因为归属性述谓源于比较性述谓。
具体性的比较虽然可靠,但是效率低下,因为必须两两比对,但是随着比较和选择活动的日益成熟,“好”的标准也逐渐成熟了。以砍削活动为例,在石器时代,人们是通过比较才逐渐意识到扁平的形状要好于圆钝的形状,一旦扁平形状作为好的标准确立起来,人们就不再笨拙地两两比对,而只需进行识别和归类就可以了,斧头的形态也随之逐渐定型;青铜时代,人们又发现青铜斧头比石斧更加有利于砍削,也就是更好,这时材料的质地又作为分类的标准确定下来;而随着制造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不同的制作工艺(比如冶炼和锻造方式)对于砍削活动又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制作工艺也可以作为分类标准确定下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前认为是客观的事实判断,其实是在人类的比较和选择活动中才被逐渐筛选和确定下来的,带着深深的价值印记。当这些原本作为分类标准或尺度的“事实”一旦成熟出来,“好”也就从原来的“比较之好”转化为“属词之好”,因为相应的实践活动已经从原来的比较活动转变为分类活动。“种词之好”则是加总后的总体权衡,用于协调和权衡“属词之好”之间可能具有的冲突和否定。至于选择,却作为本质性特征贯穿于从比较到分类的活动始终,因此构成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
当人类的活动从比较活动转化为分类活动,也就意味着从原来两两比较之“好”(better)转变为按照分类标准进行取舍归类,因为分类标准已经明确,因此分类活动之好坏就在于能否遵照标准的问题,也就是“正当”(right)问题。显而易见,“正当”乃是由“好”转化而来。3在规范伦理学中,后果论者主张,正当奠基于好——某种行为之正当的最终理由是它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是好的;义务论者则认为正当奠基于内在的道德价值,而非工具性的好,好坏问题恰恰要诉诸正当问题。1上述两种主张虽然都有正确的成分,但是在关键性的支撑论点上却有失足之处,即未能充分意识到“正当”与“好”乃是由不同的行动方式支撑起来的。“正当”问题在元伦理学家那里被归为价值判断,并困惑于“好”、“正当”和“应该”这三种价值判断形式之间的关系,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当”其实属于归属性述谓,“好”则是比较性述谓,“应该”则是对未达到标准的期待、督促和责备。从语言即行动的观点来看,“好”是比较;“正当”乃是分类;“应该”则是教导。
参 考 文 献
[1] 休谟. 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 希拉里·普特南.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
[3] A. J.艾耶尔. 语言、真理与逻辑,尹大贻译[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 查尔斯·L.斯蒂文森. 伦理学与语言,姚新中,秦志华等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 R. M. Hare. The Language of Moral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6] 徐向东编. 实践理性,李曦译[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 克里斯廷·M.科斯格尔. 对实践理性的怀疑论[A]. 实践理性,徐向东编,李曦译[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 保罗·拉塞尔. 实践理性与动机怀疑论[A]. 实践理性,徐向东编,李曦译[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9] 伯纳德·威廉斯. 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A]. 道德运气,徐向东译[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10]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陈嘉映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