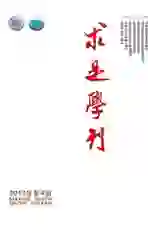“个体”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2013-12-29张守奎
摘 要:经由指谓分析法可以揭示一个具有丰满规定性的个体如何展示出来或出场的逻辑机制。从指谓分析来看,个体要真正出场必须既保证主词指称对象的“现实”,又保证展开的谓词能够在主词指称对象身上得以被“例示”。换言之,一方面要保证主词-主体指代一个现实的、专名指称意义上的个体;另一方面,又必须使得主词-主体(行为主体)自身运行扩展开来,其谓词得以展示,从而使得作为主词-主体的个体意义丰满起来,并保证在现实的这一个体身上能够找到谓词谓述的“意义对应物”。
关键词:个体;指谓分析;异质性
作者简介:张守奎,男,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马克思哲学、西方实践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发展趋势”,项目编号:12&ZD1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实践语言、实践思维与实践智慧”,项目编号:11JJD710010
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023-08
在现实生活中,凡存在的皆是个别者,所谓的“普遍”,只不过是人的思维之抽象的产物而已。这似乎早已被人们作为一种毋庸置疑的既定存在论事实接受下来。以人为例,如果说生活中存在的只是张三、李四或王五等这样的“唯一者”或“个体”(the individual),“人”只是对上述诸个体的“抽象”1,恐怕不会遭致太多人的怀疑。然而,事情往往是,“怀疑与否”跟“是否自觉承认和接受”并不能直接对应。比如,为强化自己言辞的可靠性和说理的能力,张三在写作过程中经常会说“我们认为”,而不说“我认为”,但事实上,该文章明明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这种知识论上的修辞性强化,一定意义上遮蔽了个体在存在论上在场的事实。1结果,在“我”向“我们”滑动的不知不觉间,普通专名指称对象意义上的“个体”,要么沦落为匿名性的“能指”,要么被转化为复数意义上的“集合”2。由此,个体似乎在不知不觉间“不见了”。这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可进一步延伸为:个体如何才能真正出场?3本文将从指谓分析法重点考察这一延伸性问题。
诱发笔者思考“个体如何才能真正出场”这个问题的触发点是马克思,或者扩展开来说,是马克思早期所属的青年黑格尔派针对黑格尔哲学和基督教而明确提出的“主谓颠倒”问题。4尽管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这一“主谓颠倒”的问题主要是把主词指称对象由抽象的“普遍”落实为经验的“个别”,以及由观念论转变为唯物论的问题,但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却是仍然停留在抽象的“普遍”层面,根本没有真正触及经验的“个别”。这充分体现在,针对黑格尔兼容主词和谓词于一身的“Being”或“绝对精神”,鲍威尔要把它落实为“自我意识”,费尔巴哈则把它看作基督教中“上帝”的化身,并主张主谓颠倒就是把这样的“绝对精神”或“上帝”实现为“人”。施蒂纳从绝对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之视角一眼就看穿了他们思想背后的“玄机”:他们仅仅还停留在把主词指称对象落实为抽象的“类”(属,species),而非真正的个体——“我”上。施蒂纳相信,“自我意识”和“人”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并无实质性区别,它们均是“普遍物”,只不过抽象程度不同而已。并且,在其面前,个体性的“我”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因此,要改变个体之“我”受“普遍物”宰制的状况,就必须彻底废除“我”之外的任何先在性的“普遍物”(谓词),从而独显主词之“我”的唯一性。
施蒂纳这种排除任何先在性谓词的绝对主词“唯一者”或“我”,在马克思看来必然是非“现实的”5,因为主词的意义必须靠谓词来赋予,“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1](P255)。因此,主谓词颠倒的实质,既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落实和停留于谓词性的“类”上,也不能像施蒂纳那样完全抛弃谓词而独显主词的地位。主词当然要下降和落实为经验中的个体(个人),但这样的个体必须由谓词来包围,从而给其填补和建构意义。马克思提出的“现实的个人”实际上就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一方面,他要求“现实的个人”要落实为经验中“从事实践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2](P71);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样的个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个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当然,马克思由于直接针对施蒂纳抛弃谓词的状况而发动攻击,结果导致他对“现实的个人”的“谓词”的方面过分突出,而忽视了对其作为主词之“指”的方面的深入考察。尽管他强调要把其落实为经验中的个人,但这样的个人如果不能落实为有名有姓的专名指称对象,那么显然仍是普遍物。由此可见,马克思基于对主谓词颠倒问题的考察和理解,企图把具有丰富意义的“现实的个人”实现出来的诉求,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他并没有真正解决主词与谓词、个别与普遍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倘若把视野放开,费尔巴哈、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所谓的“主谓颠倒”问题并非没有哲学史的渊源和根据,哲学史上关于普遍与个别(或共相与殊相)、唯物与唯心、经验与唯理等问题的争论,均直接或间接地牵涉这个问题。因此,呈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哲学史依据也就成为笔者进行学理分析的“基底”。
概而言之,哲学史上曾发生过两次主要的哲学主题不断“下沉”的情况,并且均是从主谓词关系的角度出发和实施的。第一次由苏格拉底肇始,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成”;第二次则由黑格尔把问题推向极致,由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施蒂纳、马克思等实践和“完成”1。
学者们认为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主题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人,他把哲学关注的目光从早期希腊神话和哲学的“神”(“gods”,是一种“多神论”,并不等同于后来基督教的“一神论”的“上帝”,即“God”)与“自然”,转向生活中的人的生存处境。苏格拉底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主要致力于为生活世界中的个人提供行为的凭据和道德判准。因此,他在对话中旨在追问“虔敬是什么”、“美是什么”、“善是什么”、“勇敢是什么”如此等等的本质问题。并且,苏格拉底强调,他问的不是虔敬、美、善和勇敢的个例是什么,而是问“虔敬本身”、“美本身”、“善本身”和“勇敢本身”诸如此类的“类名”是什么,苏格拉底的追问就是要给出它们的“定义”。
柏拉图的“型相论”无疑直接继承了苏格拉底对话的上述旨趣,并把它推到了极致,从而使得“型相”2(eidos,idea,Form)成为一个个脱离感性个别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说在苏格拉底那里,形式与个体并没有分离,而柏拉图则把它们分离了。[3](P291-292)柏拉图“型相论”的主旨是为了“拯救现象”,即以超越的“型相世界”来为流动多变的“感性世界”奠基。柏拉图是从解决“普遍”(“universal”,“共相”,在柏拉图那里指“型相”)问题即谓词问题出发的。他认为,解决了谓词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主词问题,解决了“普遍”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一切“个别”(“particular”,“殊相”,在柏拉图那里指“感性经验世界”中的事物)问题。因而,他把重点放在解决普遍性的“型相”问题上,并认为,感性的“个别”仅仅是“模仿”或“分有”(“participate”,又译为“参与”)“型相”才得以“实存”(exist)的。由于他把目光放在了谓词和普遍上,忽视了对主词的深入思考,因而,作为主词位置上的个体之在不在的问题,在他那里根本就没有成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或者说没有被主题化。柏拉图解决谓词问题的初衷是为了“拯救现象个别”,而且随着对谓词问题研究的深入,他发现如果过分抬高谓词或普遍,把它与现象彻底分离,就会造成“经验世界”与“型相世界”之间的巨大分裂。因此,他认为,必须思考经验个体与谓词意义上的“型相”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分有说”和“模仿说”上。然而,如同后来亚里士多德批评的那样,不论是“分有”还是“模仿”,在说明经验性现象个别与超越性“型相”的关系上都存在诸多困难。况且,柏拉图追求作为属种谓词意义上的“型相”的理论实质,决定了他理论关注的重心是属种意义上的“普遍”,从而无视经验个别。因此,在柏拉图的思想中,“个体”或“个别”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本体地位。柏拉图晚期的“通种论”实质上仍然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但并不成功。可见,主词与谓词、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在他那里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个体”作为一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
柏拉图“型相论”的盲区成就了亚里士多德的“个体论”。前面说过,柏拉图把关注点放在了谓词上,放在了作为普遍或共相的“eidos”上,然而,“普遍”的东西是存在争议的。这样的争议只有回到经验的“个别”所指才能够得以解决,因此,亚里士多德由柏拉图对“普遍”和“谓词”的强调退回到对“个别”和“主词”的凸显。亚里士多德不满柏拉图把“型相”看作是超拔于经验个别的看法,他认为“型相”只能存在于经验个别之中,而不能脱离开经验个别而独立存在。柏拉图晚年的《智者篇》(251a-b)曾从语言分析的角度重新探讨一事物为何可以有多种命名,这一做法启发亚里士多德主要从谓述类型和句子结构去考察哲学问题。从谓述类型和句子结构出发,必然离不开“是”,何况亚里士多德本来就认同先哲们所谓的思想的对象必然是“是”而不是“非是”的观点。不过,亚里士多德发现,这个“是”并不固定,因为可以在多种意义上说一物“是”,退一步说,即使它相对固定,也可以多种方式言说“是”。[3](P128)但不论如何,这多种意义上的“是”有着一个中心点(central point)或核心意义(focal meaning)[3](P58),即“实体”(substance)。他明确区分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范畴篇》),并把“第一实体”的一条标准规定为只作主词不作谓词、只可被其他东西谓述而不能去谓述其他任何东西,认为只有“第一实体”才是最真实、最确切的存在。[4](P12)但是,当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实体”进行言说和谓述时,他又必须借助于“普遍词”。一旦借助于普遍词来谓述,个体就又变成了普遍性的东西。正因如此,他最终不得不把个体看成是“形式”与“质料”的组合,并且强调,在型塑个体的“形式”和“质料”中,“形式”才是个体化的原则(principle of individual)[5](P64)[6](P98),即是说,与“质料”相比,“形式”才是更基本的,才是“首要实体”或“第一实体”1。但如此一来,就与他开始主张的只有具体的“个别事物”才是“第一实体”相矛盾。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普遍与个别、主词与谓词的关系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十分明确主词对个体的“指”和谓词对个体的“谓”之间的真正区别,他也没能真正把个体主义的路子坚持到底。
亚里士多德之后,上述问题在哲学史演进中总是反复出现,如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或殊相与共相之争,近代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之辩等,均是上述普遍与个别、主词与谓词之关系问题的直接体现。不过,真正把这个问题发挥到顶峰和极致的无疑是黑格尔。
黑格尔化解主词与谓词、普遍与个别关系问题的方法比较特别,他完全把其纳入一套严格的辩证逻辑系统中来处理。在黑格尔看来,这个世界无疑是生成的,但它总有一个逻辑上的“起点”,即“Being”。黑格尔实际上是把作为“起点”的“Being”看作统纳主词和谓词于一身的东西。就“起点”而言,它是绝对的主词-主体2,而就其对象化展开过程和“终点”而言,它又是谓词。但这样作为主词对象化结果的谓词实际上并非“别的”什么,仍然是主词Being自身,即主词自身的展开。黑格尔凭靠这一绝对的起点、这一绝对的终极主词-主体Being,把世界中的一切几乎都给化解了,依据他的逻辑,大千世界、万物生灵均是Being自身“是”出来的结果。黑格尔自己也承认,这个作为逻辑起点的、无任何规定性的纯粹的Being,事实上只是思维本身。1因而,说到底他只不过是在思维中“解决”了一切。黑格尔实质上混淆了范畴词和实在词2,尽管他也涉及个体问题,但他把三阶的哲学谓述理解为可以直接用来展示个体的实在性和现实性。他不理解个体展现其实在性、现实性的场域只能是一阶的句子。3
物极必反,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再次遇到当年亚里士多德面临柏拉图型相论的局面,哲学家们纷纷要求哲学主题发生重大转变:从天上降到地上,由“上帝”落实到“人身”。上文的论述已经表明,黑格尔所代表的那套路数无疑是柏拉图式的,不过,他比柏拉图走得更远。在柏拉图那里,型相还都是一个一个的,是“多”而不是“一”。尽管柏拉图一直在努力解决诸型相之间的关系,在《理想国》中他认为在诸型相之上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善”之型相,但总体上而言,他并没有把型相看成是唯一的。黑格尔则把柏拉图的这一思想推向了极致,他把“绝对精神”自身看作是兼容主词和谓词于一身的绝对唯一者,把它理解成一个最普遍的、离感性个别最远的东西。然而,这样一个最普遍的东西,是最不现实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能直接落实为经验中的感性个别。4它实际上是个范畴词而非实在词,根本不能提供任何实在意义。
总体上,就青年黑格尔派内部而言,这种针对黑格尔的“废黜普遍精神,回归感性生活”5的趋势主要有三条进路最为典型。第一条进路表现为,费尔巴哈针对基督教中的“神”提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状态”,要求把哲学关注的主题从“神”、“上帝”、“绝对精神”下降到“自然”和“人”,即下降到“普遍”(universal)、谓词性的“类”(人)或“属”(species)。第二条进路表现为,施蒂纳针对全部观念论传统而进一步要求下降到个体、绝对主词的“我”或“唯一者”。6第三条进路表现为,马克思企图在费尔巴哈与施蒂纳之间调停,他要求从主词和谓词两个方面出发,要求回到“现实的个人”。费尔巴哈仅仅把人落实到“类”,施蒂纳则把“人”下降到绝对主词的“我”,前者因为没有进一步把“人”下降到一阶句子中主词指称对象而“不现实”,后者因为排除一切谓词(社会关系)独显主词之“我”而“不真实”。
由于前文已经对费尔巴哈与施蒂纳的相关理论进行过论述,此处就不再重复。笔者把重点放在马克思身上。
在批判黑格尔观念论的普遍物“绝对精神”上,马克思扮演着终结者的角色。这主要体现为他通过对主谓颠倒问题的处理,要求把“绝对精神”落实为“现实的个人”。那么,马克思所要求的落实到“现实的个人”的目标是否真的实现了呢?
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有过诸多的论述,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说:“这里所说的个人(individuals)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并说:“人们(Men)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
在提到其方法与思辨哲学方法的区别时,马克思说:“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men),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the real individuals),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their activity and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ir life),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P66-67)因此,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the real living individuals themselves)”2。
可见,针对费尔巴哈“类”的不实以及施蒂纳“唯一者”的虚假,马克思要求“人”进一步下降到“现实的个人”,提出要“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就主观意愿而言,此种要求显然是要把立足点放置到现实经验世界中的、普通专名指称对象意义上的个体。但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进行论说和谓述必然要借助普遍性的谓词,一旦如此,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就又变成了普遍性的东西。马克思当时针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的“类”、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和施蒂纳的“唯一者”而提出来的“现实的个人”,恰恰是要从纯粹抽象的“超验世界”回到“经验世界”,从“精神”回到“人”,回到“诸个体”(individuals)。但当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仅仅成为人们谈论的“理论对象”,成为谈论者在现实中非专名指称意义上的抽象物、普遍物时,它就成了一个纯粹的教条,一个纯粹的“能指”。这样的一个“东西”与马克思的初衷显然相距甚远,这样的“现实的个人”当然也不可能是现实生活中实存的真实的个人。这是其一。
其二,仅就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的个人”来说,尽管他给予了“现实的个人”诸多的规定性,使得“现实的个人”概念越来越丰富,其意义也越来越丰满,一个富含诸多异质特性(主要是偶性谓词)的个体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然而,不论对谓词说一千道一万,如果主词-主体本身并没有真正落实为普通专名指称意义上的“第一实体”,那么,谓词再多也给不出一个真实的个体。这背后的学理依据在于:主体-主词的“在不在”不能靠谓词保证,只能直观认定;主词只“指”不“谓”,而谓词只“谓”不“指”;“指”的部分只能靠直观认定,“谓”的部分有些靠逻辑推定,有些则不能(异谓不比)3。因此,“指”与“谓”各自扮演着不同的功能,再多的谓词也兑换不了一个主词-主体,再多的主词-主体自身也不会具有意义。依据上述理论,马克思所谓的“现实的个人”在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他的全部文本中,似乎恰恰没有被落实为专名指称意义上的“第一实体”。换言之,马克思尽管反复谈论“现实的个人”,谈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但他从来没有明确要求这样的个人一定要落实到绝对主词-主体,即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马克思本人等这样的活生生的真实个体身上,而是要求落实为某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或某些团体中的成员上,但不论是阶级还是团体中的成员在此均是“匿名”的,是没有具体到专名指称对象的。4就此而言,马克思实现的从黑格尔“以头立地的哲学”到“以脚立地的哲学”的转变,也是十分有限的:他在二阶指谓中颠倒了属种,但没有把属种和个体再加以颠倒。换言之,由于他未能为“现实的个人”指明落实为第一实体意义的、活生生的个人这一方向,即便给主词-主体(现实的个人)谓述再多,他的整体理解也是有问题的。
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尽管谓述了很多,从而使得其意义得到了填补和建构,他谓述出来的观点也的确都颇有创见,但问题在于他以为通过这样的谓述之后,个人之为个人的现实性就得到了最到位的规定。马克思没有从根本上说明,作为属种的类型和个体之间存在着鸿沟,三阶的哲学谓述并不能提供个体的实在性,个体实在性的展现只能在一阶句子中。不过,相对于黑格尔观念论的“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抽象的“类”来说,马克思已经实现向“真实个体”的尽可能的理论接近(已经达到了最靠近现实个体的属),在此意义上他是“以脚立地的”,但这是“以单脚立地”,另一只脚则由于上述所谓的他对“主词-主体”理解的“不现实”(仍是落实到“属”,即“较靠近个别事物的属”上,而不是“现实个体”本身)还悬在空中。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诸多规定相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一方面旨在揭示“类”相对于“个体”(个人)的虚假性,另一方面亦旨在揭示“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性规定(此点似乎继承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历史性之维)。不过,尽管马克思反复强调“现实的个人”,但他并没有真正触及现实个人本身,即张三、李四等普通专名指称意义上的“第一实体”之个体。就此而言,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一样把个人给“平面化”了(海德格尔的“此在”与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均沦落为无个性的“平面化个人”)。1马克思旨在强调人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这是针对黑格尔的观念论传统而言的。而前文提到的施蒂纳则是强调个体“唯一者”的内在独特性以及自我之创生性,尽管他也直接针对观念论传统,但就回到主词-主体个体本身来说,他比马克思更触及了个体的本己性。
由此可见,直到马克思,“个体如何才能真正出场”依然是一个尚待进一步分析和处理的问题。从指谓分析法来看,我认为,“真实的个人”要出场,或者说以语言逻辑的形式把一个现实的、真实的、具有丰满规定性的个体给谓述出来,就必须从主谓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保证主词指称对象落实到专名指称对象上,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丰富地对主词进行谓述。并且,谓词之“谓”必须在这一个现实个体身上能够得到“例示”,或者说在现实的这一个体身上必须能够找到这一谓词谓述的“意义对应物”。2谓词之“谓”必须以主词之“指”的真实存在为前提,主谓之间就功能来说存在着异质性关系,再多的谓词以及谓词联合也不能兑换一个主词-主体。主词仅起“指”的作用,谓词只起“谓”的作用。从符号指谓三个阶次的划分来看,由于二阶句子的主词是普遍词,三阶句子的主词尽管也可是个别词,但它有待填补和建构的只是范畴意义而非实在意义,因此具有专名指称对象意义上的“个体”只能在一阶句子中展开其实在性,并表现为得到众多实在词的谓述,而高阶句子则不是个体展开其实在性的场域。因此,我在行文的过程中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马克思相关思想的考察,主要看他们是否照顾到了主谓词两个方面,以及他们是否把在高阶句子中所谈论的“人”的问题落实到了一阶句子中的主词指称对象上。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 亚里士多德. 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 B.A.G. Fuller.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Aristotle[M].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31.
[6] Jonathan Barnes. Metaphysics[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istotle, Edited by Jonathan Barnes[M]. 北京:三联书店,2006.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