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山纪事
2013-12-29梁国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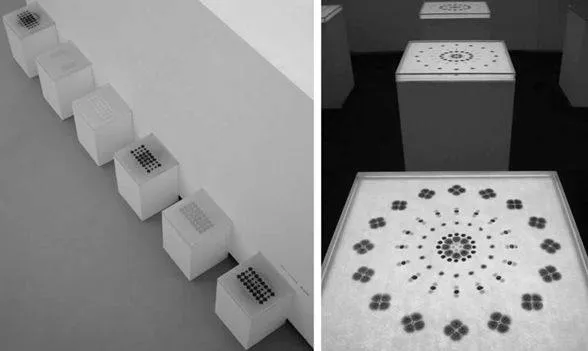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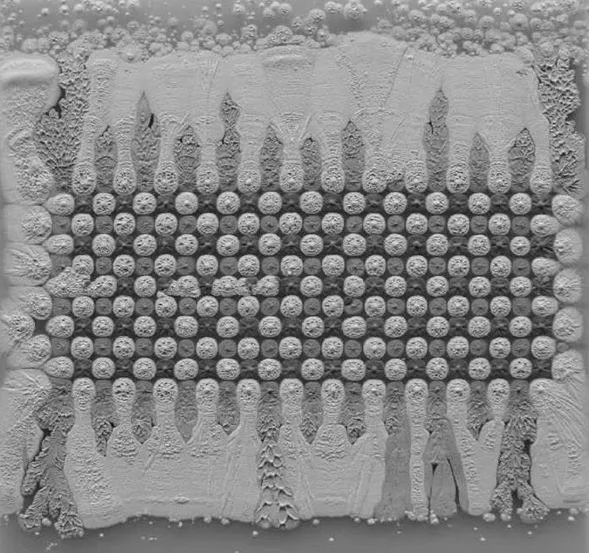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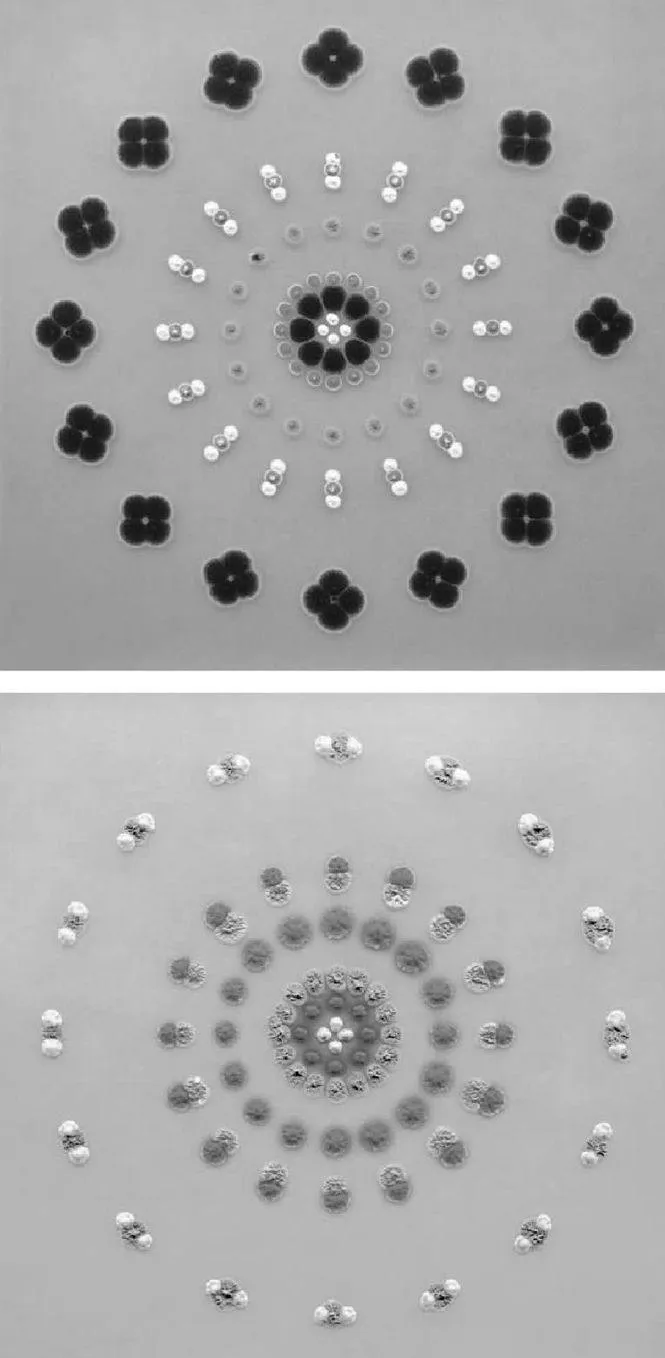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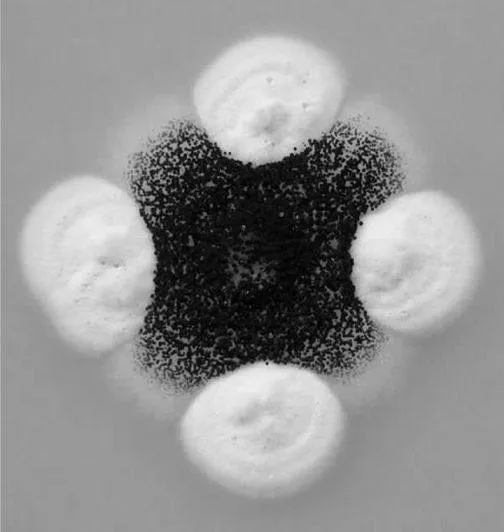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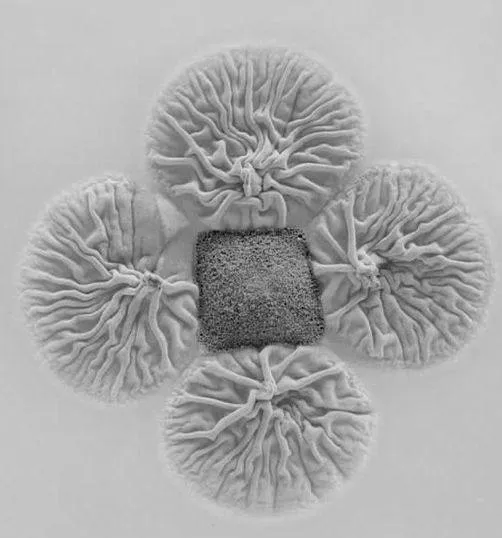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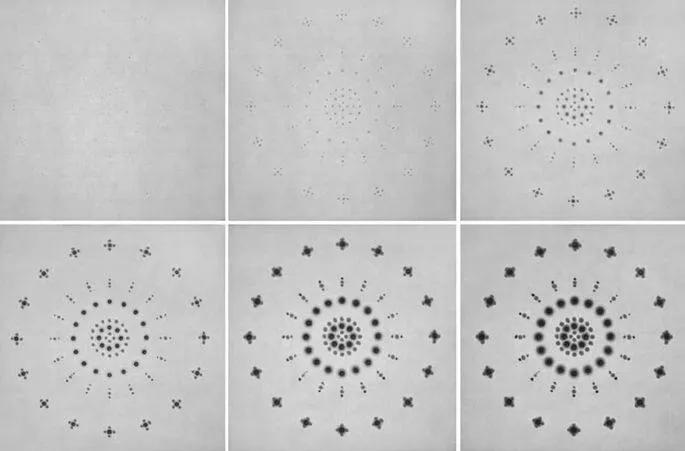

追 山
雪米子是夜饭时开始下的。之前有风。风很硬,直往袖筒和裤裆里钻。大公穿得单薄,冻得瑟瑟的,还是站直了身子,拉了一泡热尿,之后看了看天,说,天要变脸。
其他几个放牛娃子当没听见,趴在地上认真下着五子棋。大公走近看了一眼,没出声,就主动弄了些柴草,打燃火镰子,柴草就哔哔剥剥燃了起来。这样,放牛娃子们就热和一点。
事实上,放牛娃子并不领情。也只有大公穿得单薄一点。其他人,该穿上的都穿上了。没得穿的,都披了蓑衣。蓑衣是个好东西,春天可以挡雨,冬天可以遮风。每家都有新旧大小好几件,出门时,就见蓑衣一大片,或走路,大小高矮错落,或干活,曲动着身子,也是黑鸦鸦一片。
大公好手艺,编得好蓑衣,从年轻编到九十岁,每家都有他编的蓑衣。有的大,有的小,大的大人披了干活,小的由娃崽披了挡风挡雨。大公还编草席草被,编菜墩。需要的人家就拿了去,也不要别人一分钱。至多是材料不够时,主动把材料给大公送过去。送过去材料时,大公还管人夜饭。
雪米子的确是夜饭时开始下的。瓦片上有沙沙的声音,且越来越密,不仔细还听不见。那时,夜饭做得晚一些的人家,屋脊上还有浓重的炊烟。火塘里柴火当然是很旺了。山寨里的晚饭一向做得晚,所以叫作夜饭。之前,自然有好多事要干:刨地,或下种,锄草,或施肥。猪牛羊鸡鹅鸭的饲料都得弄好。柴草也得弄一些回去,天毕竟是越发的冷了。吃了夜饭,就彻底累了。烤一阵火,也就胡乱睡去。
因此,下不下雪,下多大的雪,抑或雪后是不是有多长时间的凝冻,大体和大多数人并不相干。入冬后,取暖的柴火已备足。
只有大公很在乎这一年是不是有雪。
雪后好追山。
雪当然是有大有小。
也分泡雪和雪米子。雪米子是一粒一粒的,撒在屋脊和地上有声响,沙沙的。泡雪,通常叫着雪花,飘在地上没有声——只有风大风小的区别。风大时,漫天飞舞,风小时,飘落在地,静静的。如气温低,积得也厚,四处皆白。也是追山好时节。雪米子,积淀的时间就要长一些。如遇冻雨,面上就要积好厚一层冰壳子,脚踩在上面,溜滑溜滑的。这段时间,村人大多窝在火塘边或被窝里,是很难出门去的。山里的大小动物们也是这样,蜷缩着身子,梦寐着草水肥美和花开的春天。
只是这样冰天雪地的时间,有时会很长。
说不上是一月或半月。
大公都能看准一个最好的时机。
走兽或飞禽跟人一样,有时都耐不住饥饿和寂寞。大公更多的不是因为饥饿,是寂寞。
之前,马的草料是备足了的。有粗有细,细的有米糠,有包谷粒。三条狗和自己吃的,烤的有红薯,煑的有米饭,也备足的。如果不出门,就只能窝在崖腔里编蓑衣或草席,按时伺候那匹马和三条狗。马吃饱喝足以后,在那里刨蹄,三条狗也是吠得有些不耐烦——都是因为寂寞。
雪下的时间长,先是雪米子,落在地上沙沙的,积得很厚,后来飞雪花,树上也全挂满了的。崖壁上的水滴不再跌落下来,倒挂了冰柱或冰笋,路上不见行人,也不见鸟飞。崖腔前面那条河,也有了冰面,只有中间那浅浅一线绿。原先半壁间的那一溜清流,流经之处,都泛起了很厚的冰花。
正应了那句话: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天地冻得嘎嘣嘎嘣响。
要是往常,大公会去蹓狗蹓马,或停下来,看放牛娃子们下五子棋。之前的三十年间,就是这样过过来的。大公并不高大,八十岁前身子似乎还显墩实。四时里都穿得很简单,一双自己编的草鞋,只有到冬天时才套上一双布作的厚袜子,出门时在背上披一蓑衣,大热天里也是这样,下雨时才戴上随身带的斗笠。出门时骑马。大公骑马时不用马鞍,只在马背搭一马挞子。马挞子用棕丝编的,两面有肚兜,装有常吃的椒盐,修理马蹄用的刀和刷马背的刷。骑在马上出门时,三条狗就跟在后边,不声不响的,嗅觉是非常的灵验,能发现哪里有野兔有野鸡,或者其它动物。烧了柴火,烤了野鸡和野兔,蘸了点椒盐,与放牛娃子们一道分享,吃得尽兴。不过,大公很少吃肉,只啃骨头。人虽然九十多岁,牙还好,把烧焦的骨头嚼得嘎嘣脆。因此,大公在哪里,放牛娃子就喜欢跟在哪里。当然,更多时候,是放牛娃们在哪里,大公会主fa64c181877bc0b9fee6be36334ca0939779300ee014157d60a070a868394f10动跟在哪里。没啥嘛子吃的,大公也会捉一些蚂蚱或烤一些红薯给娃娃们吃,之后,就很有兴致地看娃们斗五子棋。三十年间,大公就是这样看着放牛娃子们一天一天长大的,长大也后都要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尽管这样,放牛娃子和岁月一样还是延绵不绝,只不过是一茬去了,一茬又来了,只是认不清是哪家的。新来的很快就学会了斗五子棋,也习惯了跟在大公身边吃烤蚂蚱烤红薯,有时也能分享烤野鸡烤野兔。同样,大公很少吃肉,只吃烤焦黄的骨头,牙口同样好,把焦黄焦黄的骨头嚼的嘎嘣脆。
有时,大公也会给放牛娃子们提一点建议,哪里草水好一点,哪里地块宽展一些。有时,也帮放牛娃子把不怎样听话的牛羊赶回家里去,这样说起来,是放牛娃子们看着大公一年一年把年岁变大的。
其实,大公并不显老,只是身子不如之前墩实。倒让人觉得还精神了一些。
大公独自一个人和一匹马三条狗住大崖腔里,之前还养有一群鸡。鸡是自由交配,生了蛋又孵成小鸡,最多时有三十多只,大公不杀鸡,也不吃鸡。鸡和狗不和睦,整日追得鸡飞狗跳。大公嫌吵,就请人把鸡全捉了去,只留下一只公鸡叫更。公鸡把更啼得很好,狗们出门时,公鸡把日子过得也很简单,夜里和白日里休息时,就飞到木梁上站着,狗们也奈何不了它。
大公住得简单吃的也简单。
大崖腔原先是一处营盘。之前打过几回恶仗。前面有大料石砌的石墙,左右两端有石门,头顶是一溜石壁。抬头只能看见半片天。崖壁上有树,或直立或倒挂。之前树上有猴,有鹰,有水滴从石壁间滴落下来,在墙内形成三处不小的水塘,人畜都可以喝。当然,左面石缝间流出的泉水就更显清冽一些,天热时,可用葫芦舀了直接喝。人站在石墙上,就可以看见前面那条河。河叫绿池——前面那段是石板滩。有渡船。七十多岁的船娘也是孤身一人,四时都是光脚片。夜里不渡船时,就光着脚走到崖腔里来和大公说说话。有时,大公就留她在床上过夜。村里的当家人贵林就不止一次说过,两人都是单身,去乡里领个结婚证,正大光明住在一起,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
大公说,船娘还年轻,才七十多岁,他自己已过了九十多岁的年纪,是下了坡的太阳,怕等不及她。事实上,大公是嫌船娘吃的荤,人前人后放的全是哑屁,臭味捂在裤裆里,要好长的时间才散去。后来又说船娘,她一个单身女人,四时两片光脚板,让人看了太不雅观。贵林把话传到船娘耳朵里,船娘很是生气,说,他个老狗日的,还说我闲话,他不弄个镜子自己看看,一辈子没干过几件正经事,除了能编几件蓑衣草席草墩以外,他还有啥嘛子本事?
贵林说,人都到了这把年纪,就宽容一点,将就一点过。如果都同意,就办一台酒,人多人少,也算喝个热闹,地点选在崖腔里或渡口边,你们两个自己商量定。
船娘说,要是少吃点荤,她倒也同意,但不让她光脚板,这事她到死也做不到。不光脚板,全身里里外外像火烧一样。之前她试过,每日里要光脚板早晨夜晚的蹬踏一段时间,身上和心里的火才泄掉。
尽管这样,大公要是在山里在林间弄到了野物,还是不时送到渡口船娘的茅屋里去。
比较而言,大公住的简单,吃的也简单,没用床板,九棵大小相同的树条相拼成木架支楞起来就是床架和床板。为了避风,在四周搭了草帘子,支架也比较坚固牢实。垫的也是自己亲手编的草垫子,厚实,耐磨,也透气。看起来精致大气,其实,要是两个人睡,还是嫌窄了一点。船娘就跟贵林说过,他老狗日的根本就没有两个人一起过的心。要是有这份心,之前就应该弄宽大一点。
贵林想想也对。
就是到了现在,也没谁晓得大公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只是听老辈人说过,他很可能是逃兵逃到这地方来的。之前也不住大崖腔,住在大山梁子上的。有一年也是大雪,四面封山,白茫茫一片。冰凌一个月。村人出门追山,发现山梁子上有炊烟,寻去一看,有茅屋。茅屋里柴火烧得旺,屋顶没有积雪,只有少许柴烟。当然,茅屋的四周都挂着冰挂。那时,男人还很年轻,不过三十多岁,屋里还有一盲女,盲女年轻,不过二十多岁。一听口音,男人就是远方人。领头的宝山问,瞎子姑娘是哪里来的。男人说,是揹上来的。
看得出来,男人和盲女在山梁子上已经住了不少时间。有羊有鸡,还有一片菜园子。
宝山那时也年轻,是贵林他祖父。同去的几个人还在山梁子的茅屋里一道喝了茶,吃了烤红薯,到了快夜晚时才下的山。
到了第三天,村寨里二十多个青壮年全都往山梁子上去。人分三路,前后两拨。一拨进茅屋抓人,一拨接应。带了用麻绳和棕绳编的两张大网。如果不听安排,就用网子把俩狗男女装进网里拖下山。
四面的山峰全是雪白一——雪上还有一层厚厚的冰壳子。有不少树,被冰雪压折压断。二十多个青壮男人都分别披着蓑衣。一御寒,二壮声威,就一步一挪往山梁子上蠕动。
男人似乎早有觉察,把茅屋里的柴火烧的很旺。火塘里烤着几个红薯。皮已烤的焦黄,滋滋地冒着油星。盲女子当然不晓得有二十多个男人正向山上靠近,夜里睡足了,起床后吃饱了,正用身子撩拨着男人。男人不像先前那样顺从,几次走出茅屋,后来就在雪地上狠狠拉了一泡热尿。热尿拉了有一阵时间,尿液很浊,化出的雪水也是黄黄的。进屋后,对火塘边的女人说:
野牛已经出山,两条大牛后面跟着一头小牛。
之后就在草垫子床铺边抓了枪。
二十几个男人,前一拨要靠近茅屋时,男人立在茅屋前面摆动枪栓,都不敢靠近,且都把头埋在雪地上用蓑衣把身子盖住。之后宝山说,见了那条不曾见过的枪,大气都不敢出。男人说,天冷,进屋烤火,喝茶。宝山才敢抬起头来。水旺说,第一次见真枪,吓得还尿了裤裆。
很是僵持了一段时间,才敢抬起头。男人说:
大小三条野牛已经现面。打下领头的那一条招待大家吃夜饭。
说了这话以后就不见了男人的踪影。不过,把头埋在雪地上的男人前后都站直了身子。后来听见一声枪的脆响,就见领头的公牛往前蹿了一蹿,就重重的倒下,母牛和那条小牛瞬时就不见了踪影。
大老远的,都能看见雪地上鲜血一汪滩。
那餐饭,大家吃得欢。
吃的全是肝肠肚肺和里脊肉。锅太小,全炖不管饱,在雪地上架了柴火,烧烤了蘸盐吃的。可惜没酒,有酒就更好。
夜半才下山。
都看得见,白晃晃的有如白天。
带去的两张大网也不冤枉,一条牛分两半,用网装了拖下山。男人说,进山打猎,见人有份,他只留牛头。
过了一月宝山到山梁子看见,茅屋里只剩头骨和两只牛角,肉则吃得干净。天还很冷,屋里则暖和。这次去,带了自己酿的一葫芦烧酒。三个人都喝得很尽兴。只是过去不久,有人把话有意或无意传到乡里区里,说大山梁子里有土匪,手里有枪,能连发,一梭子能打死一条野牛。
因此,区乡两级要组织剿灭。
动作很大。当然,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之后,就不见了持枪男人的踪影。有人说,是中了枪,死了。有人说,是听到风声,连夜跑了。反正,那人那事,人们就渐渐地忘记了。
只是有一件事,大家都明白,那时还很年轻的盲女,后来作了宝山的婆娘,也就成了贵林终生难忘的祖母。至于贵林他爹是不是宝山的种,那就说不一定。不过,贵林他爹朱发子到二十岁才从山梁子上搬到山下来的也是事实,只是那个瞎女人一直不肯下山来住,她说,她要等那个出门去的男人回来。
后来,瞎女人和宝山在山梁子上又生下一男一女。
男人是三十多年后才回来的。大多数人已经记不起他,也识不了他,他也没直接往山梁子去,先走到山下宝山的家里,说,要和宝山兄弟先喝点酒喝点茶。其实,酒也喝得不多,当天夜里宝山兄弟就脑溢血,过三天,他坟前就树起一杆白幡。办完了丧事,男人才上到山梁子去。瞎女人眼里突然有光,似乎也很清冽。其实,是从来没见过的泪光。瞎女人说,你回来了,恐怕我就要走了。
相处了十天。男人也没留住女人还有些暖热的身子,独自把她埋在茅屋右边菜园子里。
三十余年间,男人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树少了,山变光了,似乎四处都有人家,宽大的木屋或低矮的茅屋。天黑时,四面有炊烟。
独自在山上的茅屋住了一年多时间。
人们有个直觉,这男人是个祸害。进了寨子,宝山没有了。去到山上,瞎女人就死了。都不敢接近他。
只有差不多年纪的老人,仿佛还记得他。相见时,还能简单地说上一两句话。事实上,男人记不起有这个人。他说,他只记得有一个宝山。那会打下一条野牛,后来,宝山到他山上的茅屋喝过酒喝过茶。其他的,就记不得了。比较而言,他比寨子里同年纪的人年轻,耳不聋,眼不花。下了山以后,从不进哪户人家里吃饭喝茶。最大的爱好,是喜欢跟在放牛娃子们身后放牛,也不怎么说话,不声不响地看他们下五子棋。
后来住进离寨子有五里多地的大崖腔。
养了马,养了狗,后来还养了鸡。
有人也到崖腔里和他说上几句话。不出门时,就坐在草墩上编织蓑衣。之后,就分别送给寨子里每户人家。人家不需要蓑衣时,他就编草墩,编草席和草垫,同样分别送给寨子里人家。
不过,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编织的蓑衣或草席草墩,都非常的精致也结实。事实上,大部分人家都需要,也喜欢。
日子久了以后,大家都认为,这个突然出现又一直不走的男人,一定与这里的某件事情有关,只是不想也不敢多问。
问多了,也怕出祸害。
他自己啥嘛子也不肯多讲。只是说,过去的事,都记不得了。
贵林晓得,守寡的船娘对这老头有好感,就托了她,夜里去他枕边掏个底细。后来,船娘跟贵林说:
冤枉跟老和尚歇一夜。她说,他跟这里啥嘛子事都不相干。
船 娘
船娘是个爽快人,也是明白人,有屁就往裤裆里放,有话就开口讲,从不遮遮掩掩。之前,当然不全是这样。男人没死之前,做事讲话还是讲究个分寸尺度的。有人说,男人没死之前,白日夜晚的总是有个人讲讲话。男人死后,没人说个话。遇到个人,不讲话,会憋出毛病的。
说的也对。
船娘爱讲大实话,明白话,或许和后来跟了她那个老男人有关。
老男人住在渡口后面大崖腔里。原先各自为家。
船娘是七十多岁才跟九十多岁的老男人领结婚证的。那段时间下大雪,先是雪米子,后飘雪花,之后又落毛毛冻雨。先后半个月,雪上一层厚厚冰凌壳子。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雪。贵林组织村里青壮年追山打野猪。封山育林后禁枪禁猎,树林子慢慢长起来,飞禽和走兽渐渐多起来。最烦人最恼人的还是野猪,大白天的也成群结队出来糟蹋庄稼。贵林多次提出来要打掉一些。乡政府准许每年打掉十头。十头就十头。商量定了打大的公猪和母猪。请大公也参加,他枪法准,听说他之前一枪还打死过一头五百多斤的野牛。
大公九十多岁,眼不花,身体还好,也乐意,只说,好久不摸枪,不晓得准不准?
枪是乡里发放的。两杆,子弹二十发。火力不足自己想办法。优选二十个人,分两组。一组一杆枪,子弹每组十发。大公牵头一组,贵林领头一组,分东面山林坡和南面山林坡。
那天船娘没事,主动申请作为监督员参加,还说,她要看看大公那老狗日的是不是真有准枪法。贵林领头在东面坡,一无所获,白白浪费两粒子弹。事后,大公说,主要是掩蔽得不够好,出门披蓑衣,还是应该用白塑料布包裹好。大公就是这样安排的,他在南面坡,两声枪响打到两头野猪。一公一母。公猪体大一点,有三百余斤,睾丸有粗碗口大,正放肆地和一头母猪交配。船娘小声对男人说,等它俩交配完再打它。猛一声枪响,公猪就从母猪背上倒下。母猪似乎不晓得发生了啥嘛子事,侧过身子极其不满意地看了一眼,又听得一声枪响,母猪在雪地上不过跑出五十米远,也倒下。
之后五天打掉六头野猪。
东面坡打掉一只。是头母猪,个也不小,废掉五发子弹。南面坡一共六头,用掉子弹七发。其中一头公猪,中了弹后还在疯跑,立起前脚,原地打转转,似乎在跟谁跳舞。老男人就立起身子,补了它一枪。
七头野猪,齐刷刷地躺在村子的雪地里。
贵林安排,最大一头公猪,跟枪送到乡里,也让乡里跟着打一次牙祭。剩下六头,其中五头按户数人多人少分了,各自拿回家要炖要炒各行其便。那么剩下的一头母猪,体量也不算小,二百斤或许还要多一点,大公出力最多,就全给他办他和船娘的婚事了。
大家都无意见。
贵林说这话时,大公和船娘根本就不在现场。打掉六头野猪后他俩就回到渡口的茅屋里烧柴火。事实上,老男人根本不愿去渡口的茅屋。是船娘硬把他拖进茅屋去的,一面拖一面还对老男人说好话:你枪法准,一枪一头猪。准得有点像我年轻时跟的那个团长。团长枪法准。
当然,船娘的男人死后——,他不只一次听船娘说过,她并不是大蒜老二的婆娘。大蒜老二只不过是团长的勤务兵,除了跟班,在团长家里也只是洗洗衣裳和娃子的尿片。她本人可是团长用大花轿子抬进门拜过堂的。尽管是第三房,夜里,团长可高兴和她睡一床。之后又说,要是共产党不打败国民党,她就不只是团长太太,至少,团长都升了师长或军长,我才不会被大蒜老二骗到这里来!
老男人图清静,不愿听,就说:
你又翻出你那几张老黄历。
之后,就赶忙出门拉一泡热尿,要磨蹭长一段时间才回来。船娘有时会跟了出来,话也说得很直白:
你屙的尿白花花的,清亮清亮的,太素,一点尿骚味都没有。我就不行,一餐不见肉,就是腌肉腌鱼或者蚂蚱也要油煎了几只吃的。
男人回答得也简单:
你口福。
大公是吃的简单,几乎不见油。一只陶罐,放进米或少许豆,加适量水,把面上的沫吹掉,就放近火边煨,煑沸,移开,待脱水,盖上瓜叶或芭蕉叶,再靠近火慢些烤。香味溢出时,把周遭嗤嗤锅巴烤得焦黄,再移开,坐一下水,过小许时间,才动嘴。蔬菜或野菜有时生吃,有时熟吃,糊辣椒就盐。有时就烤几只红薯,就算一餐。也不去哪家里大碗喝酒大碗吃肉。在外饿了时,就给人打声招呼,拔几个萝卜或红薯生吃。
船娘不行。如哪家真诚邀请,会坐下来吃得大汗淋漓。站起来后,用袖子抹一抹油嘴,才叭嗒叭嗒迈着大片光脚板子回到她渡口的茅屋去。之后,如果不是大白天,或是寒冬腊月,她就在早晨黑来时脱光了衣裤,下到河里滚一滚水。就是七十多岁了的这把年纪,也是这样个习惯。她甚至说,大蒜老二骗她来的这几十年间,唯一的好处,就是学会了滚水和大碗喝酒大碗吃肉。
大公嫌吵,不愿养那群鸡时,大部分是船娘捉去或炒或炖或煮。
大蒜老二生前,其实也大多顺着跟前的女人,甚至跟人说,女人能跟他到这里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一道躲躲藏藏,前后走了一个多月。之前,还抱着一岁多的娃——是个女孩,半路上生病死去的。说到这事时,两口子都忍不住伤心落泪。只是男人死后,船娘才说,其实娃子也不是她和大蒜老二的,是他和那个背时的团长生的。要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跟大蒜老二生下一儿半女。不过,船娘还是有信心,她说,如果崖腔里的老男人愿意,说不定她还能给大蒜老二怀个娃子。
大蒜老二是被抓兵抓出去的。
回来时,父母已双亡,原先的木屋已垮架。之前,大蒜老二在渡口撑船——回来后,他说,还是撑船吧。
茅屋前面的渡船是用椿木新打造的。料好,上了好几遍桐油,白里透着红。之后,每年都要在六月里油刷一遍,至今都完好无损。不渡船时,大蒜老二就钓鱼或用网捕鱼,也养了几只羊和一些鸡。婆娘嘴馋,这些都是她进嘴的美味。弄上岸的鱼也很少卖,吃不完,就腌进坛,想吃时就煎一条。女人爱吃,也喜欢作菜作饭,也可口,饭菜熟了,就站在茅屋前亮开嗓子不断吼几声:大蒜老二,大蒜老二,你龟孙子吃饭。大蒜老二应了,或是没应,女人都要狠狠重复几句:我操你先人哟,大蒜老二吃饭。你听没听见呢,操你先人哟赶快回来吃饭!
男人生前是这样,死后也是这样。只要饭菜好了,就要站在茅屋面前,还亮开嗓子,重复吼几句。不晓得大蒜老二是不是已经听见。
大蒜老二是浑名,从小被叫惯的绰号。年纪大一些时,上下左右寨子中人一律叫他二伯,叫船娘为二伯娘。两口子为人其实都随意。当然,渡口也有渡口不成文的规矩。常过渡的人家,每年每家是一升子(约八市斤左右)苞米或稻谷,哪时送来都可——茅屋的右面有两只木斗,拿来就分别倒进去。不拿也不见两口子说过嫌话。年岁好时,也有人家提一刀猪肉的,尽管只有一两斤重,两口子都很满意。
大蒜老二前后病了三年时间。叫大公的男人住进崖腔后还没死,只是病得很厉害,白日夜晚叫得有些凄惨。后来他婆娘听得心烦,就说,大蒜老二,你娘希匹的,想死就早点死呀,不要叫得这么难听!男人就忍住,呻唤的声音就小了些,可身上的汗就直往屁股沟子里溜。女人又说,你要是难过,就放声叫唤。男人就大声叫唤,大公在崖腔里都听得见。
当然,大蒜老二原先也不叫大蒜老二,小名叫溜子,大名朱青山。人可是长得标致,有一米八的个,小时就喜欢玩水,弄鱼。不见其他人时,就说,他两胯间的那个东西,有点像长好的大蒜头子。之后,就叫开了浑名大蒜老二。大蒜老二被捉去当兵时,二十岁。后来跟团长时,挨过枪伤。枪伤不过是断了一截骨头,问题不大。要命的是五十多时肝上长了肿块,人就消瘦得厉害,发作时,全身都是汗。大公去他茅屋看过,之后说,主要是肚里有淤毒,要用药打理一下。船娘就说,也是缘份,看来老二有救。大公就去阴湿地,抓了几只癞蛤蟆,越大越好,越老越对劲,活生生把它剖开,顺手就贴在肚上包住。一次三只,每日早晚一次。那些天,老二肚腹上全是蛤蟆,血淋淋的,或许因为毒火太大,贴上去不到一袋烟功夫,癞蛤蟆就逐渐变干凅。三日以后,老二就不再大声叫唤。又抓了几只甲鱼,用整魔芋头炖汤,不放盐,小火慢炖,三小时后把汤全喝下,坚持三月,病根就会松动。那段时间,大公每天要来渡口两次。早晚各一次,不捉癞蛤蟆,就抓甲鱼。老二和船娘都很感动,说大崖腔里有个活菩萨。
老二好些后,对婆娘说,夜里作一梦,肚子上的癞蛤蟆在走动,走着走着的就开了红——花上有露珠。船娘说给大公听,大公沉默良久,说,命该绝他,你就给老二准备后事吧。
老二去得很平静。
过后不过三天,就听见他婆娘在茅屋前扯着嗓子吼叫:
老二,大蒜老二,我操你先人哟,你把我骗到这个地方,就不管我啦不是哈老二?操你祖宗八代先人哟!
后事也是村里的贵林牵头办的。
作后事时,大公不在现场。他说,病人是他用药医的,也算是死在他手上的。他如果去现场,会增加老二的痛苦。又说,老二半辈子漂泊,不能硬埋,最好软埋。硬埋要用棺材,软埋只用草垫和草席。老二睡去,这样安逸一点。当然,草垫和草席是大公用心编织的。后来,又编织一件蓑衣,很宽大,披在坟头上的。
之后,就听见老二他婆娘中午或晚上独自在渡口喊叫:
老二,大蒜老二,吃饭。操你家先人,你听见了没有?
一个人的日子,似乎也没多大改变。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有人过渡时就渡船。老二死后,早上或晚上滚水的时间要长了些,有时甚至不想从水里起来。滚水当然是老二教的,基本算狗刨,手在水底,两脚拍——由浅入深慢慢学会,淹不死人就是好水性。
船娘滚水有些像她本人的脾气,人在水里不断滚翻,弄得浪花很大,声音很响。不像老二,在水里静静的,或游,或潜在水里,很难看到他的身影。
渡口离后面的石壁崖腔不远。直走,不过三里路,只是没路,坡很陡。要到崖腔大公那里去,得往左走,沿着石板铺的路到半坡,右转,横过去,上坡就到崖腔里。夜里,有时就到老男人大公那里坐坐,说说话,心里要舒服一点。只是改不了放屁这习惯,让它响一点就响一点,让臭一点就臭一点。有时去崖腔里,就专为放屁去的。两片光脚片,走路蹬蹬的,脚步是叭嗒叭嗒的。大老远都听的见,老狗日的说不雅观。说要编一双麻底的草鞋送给船娘,走路不伤脚的。于是就去时才把鞋穿上,回来出了石门就脱掉。有时也在他草垫床上过夜。身边有一个人,你说话他总不能不听,他不听就说给马听,也说给那三条狗听。
白日——他老狗日的有大半时间不在崖腔里。喜欢跟那帮放牛娃子放马蹓狗,或者蹲在旁边看娃子下五子棋。逢场集时,有时也渡过河去,卖几只他捉来的活的野兔或野鸡。
后来的那条路,是船娘专门去崖腔铺的。一共三百六十级,虽然陡一点,但直。全是一色的青石板。花钱请人用钻子钻磨的,平整,宽大,材料全备齐。不急,一年铺十级。多了不铺。十年百级,三十年三百级。料备好后,铺陈石块全是船娘一人消消停停做的。村里人要帮忙,船娘说,不急,到她真的老去时,就铺完了。别人不走,看了也安逸。
每年十级。已经铺了二百级。船娘不只一次给老狗日的说过,你要是愿意走直一点,剩下的由你来铺,找人帮忙也可以。老狗日的说:路不是铺出来的,是人走出来的。走完就算完。
被村寨里叫着大公的老男人在崖腔里活过九十八岁,以为他还能活过一些年岁,不知突然之间就没了气息。落气前,船娘在现场,笑着对船娘说,贵林其实是他亲孙子,他死后——要软埋。后事办完时,是这一年有艳阳的秋天。四面平静安详,当然没下雪。
没铺完的石级,全由船娘铺上。之后,船娘有时住崖腔里,有时还住渡口的茅屋。
碾 房
七上八下九归塘,还是鱼们生活的基本习性。大蒜老二这样说的,爹也是这样说的。妹晓得。妹喜欢在河里弄鱼。多时,一年要弄几百上千斤鱼。
他爹一辈子在河边守水碾房。
爹不喜欢弄鱼。
他爹喜欢在山里悬崖间下套弄山羊和獐子。山羊剥了皮,把肉割成条,烧柴火烤了抹椒盐,好吃。獐子有麝香,拿到街市能卖好价钱。他爹每年弄得最多的还是山鸡。家里养得有三只山鸡婆子,每年入春到进冬前那段时间,他爹都要带了鸡婆子去方圆几十里的山间转悠。山鸡婆子出了门,见山青水绿野花花开,也很兴奋,亮了嗓子,就乐意把公鸡们邀请。妹他爹这时是躲在暗处的,只见公鸡们不时张开翅飞来,驻足,还不成跟鸡婆交配成功,就被箭刀射杀了的。有时,在一个山头或山坡,要猎杀三五只公鸡。因此,妹他爹把鸡婆子伺候得好,冬日里住草垫,出门前喂一粒麝香。听说,鸡婆子吃拌了麝香的口粮,出门会叫得温柔叫得欢实。当然,妹他爹到了那山头或崖壁间,选好地,同样下套弄山羊或獐子。如果不是暴雨洪水季节,有时就去得远,一月两月才回来。
发洪水,容易冲毁碾房的堰坎。离不开碾房,其实就是这段时间,那就只能在周边近一些的山岭转。
碾房离渡口不远。只有三里地,一锅烟功夫,地点就在马脑壳山嘴那段河滩。平时水浅,好扎堰坎,其它地方多是深潭。在渡口茅屋前,能看见那片白花花翻着浪子的河滩,只要站在堰坎中间,也能看见能听见船娘扯着嗓子呼喊大蒜老二吃饭的身影和声音。
妹他爹和大蒜老二是前后一年生的,也是一起长大的。这片山里的男人从小就有一个狭隘的坏习惯,喜欢比试谁长得高长得矮,也喜欢比较谁两腿间的那条烧火棍是长是短。比较而言,大蒜老二喜欢水,妹他爹更喜欢山。后面山有一片白杨树,长得笔直伸展。树上有虫,啄木鸟贴在树干上啄了好些个旧洞和新洞,妹他爹说,老二,你说你那条烧火棍子长,你说你那条烧火棍大,你就爬上树去把你那条火烧棍伸展树洞里看看,是短还是长。老二不信邪,说,他那条烧火棍能把树洞捅破。其实,那颗洞里有鸟窝,老二把烧火棍正要往洞里钻,洞口就伸出两只小鸟的嘴正吱吱叫。手一松,身子就从树间滑了下来,事后很多年间,两男人想起来都还忍不住好笑。
比较而言,老二两口子在渡口渡船,没儿没女,日子多少有些孤单。妹他爹就不一样,没有女,但有儿,儿娃子还不少,十多年间,生了九个。九个都长得好,没病少灾,能吃能做。他爹说,关闸了,不生了。生下的全都是儿娃子,难养,要房间多,媳妇也难得找。大的都已经三十多岁,还有四个儿子都打单身。原先,妹他爹的确是热爱姑娘的。妹排行老五,他娘之后生下来的也都是儿娃子,就把老五叫着妹算了。
妹的脾性赶他爹。
妹他爹出门逛山时,碾房大多是妹跟他娘照看。他娘就是他爹出门逛山逛回来的。事实上是私奔,娘家离得远,有十年没回过家。生了老五时,才由大蒜老二出的主意,把大小五个娃全带上,去认个家。送礼也不要多,一头二百斤重的猪,一头山羊一头獐子,三十只山鸡。进了院子,齐刷刷跪下,该叫爹叫爹,该叫娘叫娘,儿们齐刷刷地叫外公外婆。人心都是肉长的,还能不让人进家?
想想也是个好办法。
其实,妹他爹不愿再要儿女时,婆娘也不过四十岁年纪,要生还可以接着生。婆娘也听话,每次和男人颠过床后,就在肚脐处贴上用麝香配制的药包。这办法很灵,之后就没再怀上。有时,大蒜老二的婆娘也乐意到碾房坐一段时间,唠唠家常,说说话。有一次船娘说,你不想生,肚子闲着也是闲着,娘的,跟你商量个事,把你肚子借我家老二用一下?一个月也行,半年也可以,如果老二跟你也怀不上,就证明他狗日的真没这个本事。
妹他爹逛山回来,妹他娘如实跟男人说过这话。男人说,他虽然跟老二从小亲如兄弟,但要借肚皮,其实还是不妥当。比如借地皮,还算好说。借了地皮种一季,还回来就行。比如借牛借羊,生了牛崽羊崽,养到三月五月,还回来还是母牛母羊。借女人肚皮,从来还没听说过。不过妹他爹也认为,老二他婆娘想的这办法,其实也算好主意。毕竟,老二是好兄弟——自己的婆娘,肚子闲着也是闲着。
男人之间的事,最好是两个男人相互交接。问问老二,是他本人的想法,还是他婆娘自己的主意。那天,老二在河湾里弄到一条大鱼,是一辈子都难看见的黑壳鲭。三十多斤重,全体乌黑,离水即死,全身冒白汗。剖开没有点滴血。听说人吃了得长寿,两人在河湾里砍下尾巴一段,烧了吃得也高兴。之后说,老二你是不是真的想借你嫂子的肚皮,说实话,想了几夜,我也愿意。
当大蒜老二弄清楚了事情的原由后,沉着脸说,都是婆娘想儿想女想疯了,他自己,则从来没想过这主意,何况嫂子如母万不可有歪主意。
回到碾房后,妹他爹不言语,半夜时和婆娘又颠了一次床。之后第一次跟婆娘说了假话。他说他问明白了,事情是老二他两口子的主意。把话说明白了,借个肚皮不是好大一点事。有儿不知无儿的苦,就成全他。不过,求人脚短,你要是想明白了,就主动一点,热情一点,不要让老二觉得非求你不可。他要是来碾房,或者你跟他去河湾,都要避开别的人影。生了孩子以后,就过房给他。这一二年间,我就少来碾房。出门去逛山,说不定三月五月才回来一次,要是发大水,把堰坎冲垮了,就喊老大带他身后的弟兄,早些弄好就行啦。
之后,妹他爹有两年时间都没去碾房。更多的时间,是四乡八里逛山,就是偶尔回家一天两天,都住在寨子的老屋里。
只是一点风声都没有。
后来听婆娘说,一切都是照他说的做的。老二有时来过碾房,当然是在夜里,把妹也支回老屋。没其他人时碾房也清净,也说过老二,不要慌张,更不必害怕。到了这把年纪,也应该帮你生个娃子。之前老二的确有些慌张,后来做房事还算用心。为人也比较体贴,不像你那样毛躁。之后,也跟他去过河湾,他婆娘夜里不在家时,也去过他渡口的茅屋,都没能怀上。没怀上不能怪我肚子有问题,看来是老二的火烧棍在哪时有了毛病。
男人叹了口气,说:
这是命,不能怪你,也不怪他。
日子一如先前一样过。
妹他爹一年间还是出门去逛山,有时就近,有时去得远。同样下套子套山羊套獐子,放出去鸡婆子猎杀公鸡。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帮四个还不曾成家的儿子早些娶到媳妇。只是好心做成坏事,这一年也是冬天里下大雪,妹他爹卖了野物要回家。半路遇上一有残障的孤女,试着领回家能不能让单身儿们看上作婆娘。
大雪,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让姑娘避寒。姑娘也听话,跟在大男人身后,一面走还简单的说话。只是走到一村子边,被后面追赶上来的一群人猛然打翻在地。妹他爹被打得很凄惨。脚打折,腰打断,脸肿得像猪脑袋。
之后瘫在床。大蒜老二去看他。他说,是我的不对,打了就打了,瘫了也就瘫了。主要是不能出门去逛山。你要是我兄弟,要想方设法堵住老大老二他们兄弟和寨子里的人去寻仇。打出了人命烧了别人家的房子,就要出大麻烦。
那场灾祸倒是没出人命。上百人去,村里人都跑光。点火烧了一片木房子。之后政府追究下来,判罪领头的十三个人,坐牢三年或五年不等。也还公正。
老二没病重之前,不时要到他老屋侍候妹他爹一段时间。妹他爹也不只一次说过:
老二,你也老了。如果看得上,就叫老五去伺候你。他叫你爹。
老二下葬时,的确是妹在之前举的幡。
大山梁子
领头的是老三,点火的是老三,出主意的也是老三。他说他是单条子,不怕。出了事由他承担。
老三平时少说话,人蔫,只晓得实干。上下左右寨子百多号男人,每人一碗酒,两只烤红薯,吃了就出发。话说死了,打完了架回来杀一条二百斤的猪。他爹瘫在床,没能堵住。大蒜老二在渡口也没能堵住。有的坐船,有的干脆就从碾房堰坎那里过的河。雪还是下的大,全操着家伙,全披着蓑衣。原先他爹把残障女领回来,其实首先考虑的就是老三,只是话没这样说。他晓得老五妹看女人比较挑。妹是说过,他要的女子得像他娘,能生,还能干。不能像大蒜老二的婆娘,只养着好看。妹没同去,他另有事做,安排杀猪,买酒作饭。最好是弄些鱼。回来的人好好地吃一餐。这些事妹都能做。安排好人后,妹就回碾房等鱼下滩进箭船。
到了冬天,特别是下雪大冷天,鱼们都要从上游逐步回到下游深潭。碾房前面的堰坎是个坎。其中有一大缺口,堰槽水满,河水就从那里流出去。妹他爹和妹就在缺口安置一条箭船。箭船用木棒木条竹片编的,结实牢靠,一端笼住水口,船尾支摆在河滩。鱼们往水口出去,白花花就成了一道好菜。
七上八下九归塘这话一点不假,那些年间河里的鱼的确不少。进冬后遇霜天,鱼开始下行。之前鱼不大,单行,收获三五条。到了雪凌天,大都集体出行,一早一晚,大都是白甲鱼,也叫猪嘴,头大尾短,多时有三五十斤。大的有六七斤重。
这日里雪大,四面雾沉沉。
水口上则白花花。妹在碾房,看得大气都不敢出。鱼们前追后赶,有的还飞起来。天黑尽时,鱼还在下。一次收获有百十斤。出门的男人是夜半时回来的,同样披着蓑衣,家伙一件也没丢失。雪停,四面白。回来时看得见。
老三说,没遇上人,只烧了一片房子。后来老三又说,猪肉吃一半,留一半,鱼也吃一半留一半。似乎都不解气,也不解恨。喝酒吃肉。吃了各自回家。
事实上老三说得有些夸大。
没遇上人,全躲了,这是事实。房子烧了一处,也只是一处柴房。后来看阵仗大,大蒜老二和大公也跟着去的。大公说,事情不出也出了。要出气,也不能烧掉房子。后来就把烧着的柴房也带头把火灭了个干净。
只是那段时间政府组织严打,还是判了十三个人。只是老三一个人坐牢,其他人监外执行。后来,还和那家人成了亲家。第一,他爹想把残障女带回家给儿子作婆娘,其实是好心不是歹意,何况把人打瘫在床。第二,烧了一处柴房,损失也不大,何况他爹安排人搭建了一处新柴房。
残障女嫁的老四。
老三从牢里出来后坚决不住寨子。他说,他要上大山梁子养羊,开荒种地。
之后就找了大公,说:
原先那里是你的家,问你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是不是也该给你一点钱。大公在放牛娃子堆里看人下五子棋,头也不曾抬,说:那里和他不相干。要问就问朱发子,那里有他娘有他妈。
就去问了贵林他爹朱发子。
朱发子说:
茅屋里好些年都没人住了,你要住就好生修补一下。旁边的菜园子要种菜你就种,只要不挖到我娘的坟边就可以,过年后清明节要给她老人家立块碑。到时我走不动了,也去山上,陪老人一段时间。
之后,山梁子上又见炊烟。
山大。之前有老虎,有野牛,站在日头崖,看见山下有田土有人家。
养羊,也养鸡。山高水长,右面石牙里出水,围了一池水,汪汪的够羊们喝。
也开荒种粮种菜,跟老三一道坐牢的牟大叔说,他有个孙女,从小不怎么听话,出门在外打工。她回来后来看他,一定动员孙女嫁给你老三。
牟大叔为人还算随和,只是肠子花,快七十岁了还讨小老婆。娘家人死活不干,打了他。他也是烧了人家的房子才坐牢的,他刑期比老三长,后来女方告了他,说不到十六岁就弄她上的床。老三还到牢里看过他。
牟大叔的孙女,是这年的秋天上山来的,二十多岁的年纪,穿的漂亮,是由老五妹带她来的。在山上茅屋住了一月时间,她说,她出门在外不干活,不打工,主要是跟有钱的老板作二奶。出门坐车,进门住大房子。其实日子也过得不开心。如果想跟她上床,是要花钱的。老三说,他无钱,只有羊。住的一个月时间,老三杀过四只鸡一只羊招待她。离开时,她说,老三和她上过三次床,每次三只羊,一共九只羊。之前杀了一只羊,吃了四只鸡。一道吃的,就当招待你老三。优惠价,她只牵走五只羊。
看牟大叔的孙女的确不肯嫁给他,还要牵走五只羊,老三也愿意。只是到山腰时,老三一声哨响,五只羊就全回到山顶茅屋边。
牟大叔的孙女走得孤独,走得也很失望。
牟大叔也是第二年的秋天上山来的。他说他出了牢房,就不想再回原先的家。上山来跟老三打伙过日子。他要求不高,帮老三放羊,有饭吃就可以。何况他手上还有一门手艺,从年轻时四处转悠,帮人劁猪骟猪。没事时,还可以下山找几文钱花。只是到第三年后,老三的羊,每百只里他要牵起一头,下山卖了换成钱,他想回去时做盘缠。
老三答应了他。
不放羊时,也帮忙开荒种地。那天吃夜饭时,牟大叔说,他有门路,弄点鸦片烟种子来种。春后开花。花开的也非常好看。果入药,也能卖个好价。
老三也赞成。
挖的地,大部分种了鸦片烟。
花的确开得好看。
鸡长大了每年都卖鸡。羊长肥了也不卖羊,让羊们繁殖小羊。计划以后每年出栏五百只羊,出栏五百只羊,该到牟大叔名下五只。老三想想,还是亏了他。就说,你孙女走时,留下五只羊。有公羊有母羊,繁育多少都算你的。另外,百只里你再牵走一只羊。
牟大叔不同意,说之前讲好了的,咋嘛说就咋嘛做。说话不算数,日子过得不长久。
还说,孙女要是再上山来,你老三还跟她上床。这点事,他当老辈子的说了同样算数。要是你看不上,我下山去重新帮你找个好一点的姑娘。他说他亲戚中有不少个好看也能干的姑娘。
羊们的节育手术是三百只后开始做的。阉割后的公羊或母羊都长得快长得肥。羊群中只选留四十只公母种羊。一公配十母,公羊少了也少斗架。
老三他爹每年入秋后,都由几个儿子用担架抬到山上来住一段日子。当然他那三只山鸡婆子死后就不想接着养。
儿们都不愿逛山,怕逛山惹祸害。
老五妹已经有了婆娘。
也就是老三上山养羊的第三年,县畜牧局有三个人也来山下发展养羊。以户养,最多的人家有三百多只。几年之后,满山里四面都是羊。草根刨光,只能上树啃树叶。引的外来品种,头大耳长,个头似牛一样。只是不耐寒,有一年大雪,凝冻一月有余,死去不少羊。
老三在山上建有专门的羊房。羊是麻羊和黑羊。鸡有鸡舍,只是要提防野猫和黄鼠狼。
这一年,牟大叔的孙女是冬天上山来的。她说,她可不是来看风景的,也不是跟人来上床的。主要是来养病的。牟大叔和老三都不言语。之后,她祖父说,他晓得孙女得的啥嘛子病。好生医好后,男女还是可以同床。
事实上,孙女病得不轻。带来的有针药,还有不少口服药。穿得倒也漂亮,只是面象不像之前那样活泛。后来才晓得,孙女染了性病,戒不掉的还有毒瘾。
这一年春暖花开时,三人一道下的山。后面还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跟着。
神色都是凝重。
朱发子一直说要在他娘坟前立块碑。
可这事情也一直没个着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