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 像(之二)
2013-12-29陈丹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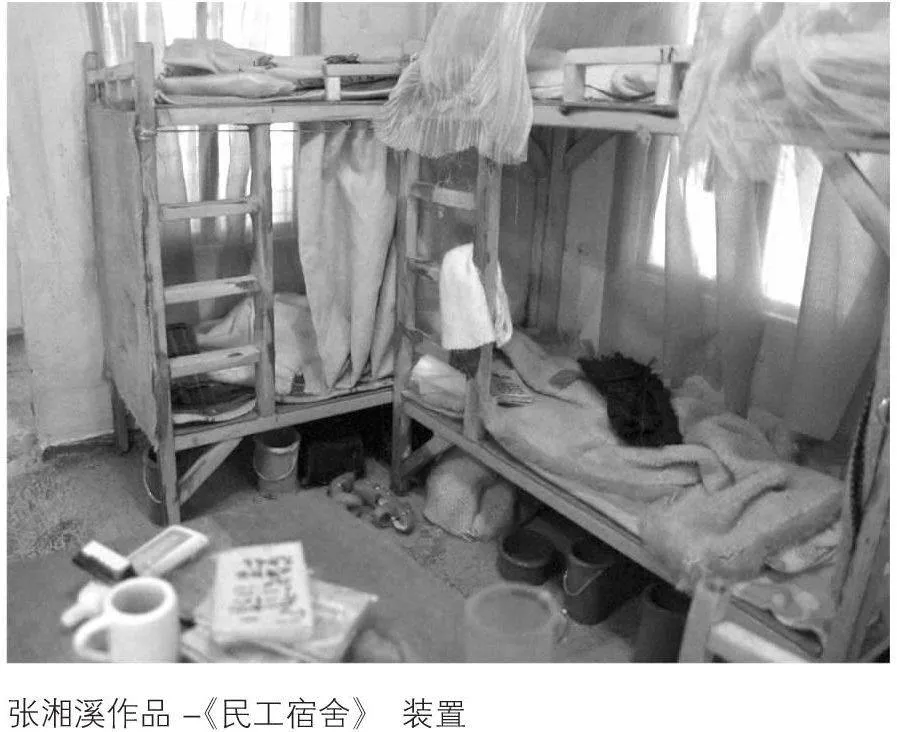

3.1996年的柏林东:黑泵
开往黑泵咖啡馆的那路地铁是又老又旧的,经过了罗莎·卢森堡广场站,这个将近有一百年历史的地铁站,座落在原来东柏林的地下,纪念与列宁同时代的著名德国社会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罗莎·卢森堡夫人,地铁站的墙壁上,有她大幅肖像,她有一张德国人苦苦思索着的脸。
经过亚力山大广场站,那是原来东柏林著名的广场,离开不远,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在广场的中央,竖立着社会主义奠基人的铜像,马克思若有所思地坐着,恩格斯若有所思地站着,凡是去到那里去看他们的游客,总会站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中间去,拍一张“马克思、恩格斯与我”的照片。到了1990年,站在革命导师中间的人,脸上的笑容里总能看到一点悻悻然,无论那个人是美国口音,还是中国口音,或者是下萨克森州的东德口音。
开往黑泵咖啡馆的地铁路过亚力山大广场的繁华区以后,就走到了地面上。傍晚时分,阳光也是一样的金黄,让人想起印象派的画,它们一束束地照耀在老房子上,常常它们不如西柏林的老房子漂亮,因为它们已多年失修,即使是在金黄的夕阳里,也显出了衰弱。许多原来是阳台的地方,只剩下了封死的落地长窗,看上去很不合适梦游者居住。因为失修,阳台已经不能站人,于是,原来东德的房管部门就将阳台拆除了事。常常还能看到老房子上巴掌大小的洞,据说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弹洞。那一个个碗似的弹洞里,盛满了初夏时分金色的阳光。从西柏林过来,很快就可以感到这些街区里的一种隐约的凄凉。
长长的,无人的街道上,也能看到许多绿色的树,草,只是没有西柏林那么多的花,更没有慕尼黑街道上那么茁壮的郁金香。树和草看上去也不是照顾得很精心的样子,有一点乡野间的恣意。
在绿色的阴影里,能看到三三两两停着东德时代生产的简陋窄小的汽车,这种马力不大,价钱便宜,没有富贵气的小汽车,常常可以在苏联、波兰看到。在两德统一以后,在原西德的高速公路上要是出现这样的汽车,会被后面跟着的汽车嘀喇叭,要它让路,所以,它们常常是知趣地开在最慢的那条车道上。挂着西德牌照的车刷刷地擦过它们的身边,用140迈的速度远远把它甩在后面。而它们,在70迈掠过窗前柔和的风里向前,虽然它们如愿地自由行驶在西德的高速公路上,随便可以在任何一个出口下高速公路,进入纽伦堡,斯图加特或者汉堡。但它们反而变得局促而不快,与德国知识分子常开的老牌捷达车在高速公路上从容而讥讽的70迈有很大不同。从车窗看到东柏林街道绿荫里的小汽车,斑斑驳驳的阳光安详地包容着它,像一只狗在它的藤条篮子里。
地铁列车经过生了锈的高架桥,在空旷的街道半空隆隆地响着,停进月台。月台上也看不到人,木条椅子上放着别人看完扔下的报纸,被晚风吹得哗哗响,东德原来的报纸已经销声匿迹,这是一份当天的《时代报》。在这个有一百年历史,铸铁构架的老式车站里,继续向东柏林深处开去的地铁车厢里面的人,在白色的灯下,脸上有些更朴素,更坚硬,更沉默的德国表情,近乎于严厉。
黑泵咖啡馆就在地铁站边上的一条小街道上,在西柏林,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家咖啡馆,它门口的牌子就是从煤炭厂里拆下来的招牌。里面的墙上挂着原来的工厂牌子,还有原来在东德报纸上对这家国营著名大厂的介绍,从前的照片印刷得相当粗糙,让人联想到经济的困顿和生活品质的马虎,可是那上面的工人宽大的脸,洋溢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强烈的骄傲神情。四处放着一些很大的机器零件,有些看上去像齿轮,有些看上去像是铲斗,天棚上,挂着简单的吊扇,像是从职工食堂里直接拆来的。
在没有什么客人的时侯,这里并没有多少咖啡香,更像是煤炭厂的厂史室。
两德合并以后,国营煤炭厂因为生产工艺落后和原有的体制崩溃,失去支持而倒闭。听说这家国营大厂关门以后,从厂长到工人,大部分成为领救济金的失业者,少数年轻的技术人员,改行做其它工作,或设法进入大学,重新选专业进修,以求得日后的发展。不少人选择了几十年前西德青年就很普遍的商科。从前,这些青年更渴望自由,他们中许多人愿意为自由而死,现在他们更渴望挣钱的本领,它能帮助一个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自己的尊严与自尊。
昔日的一个国营大厂,现在成了开在东柏林街上的一家安静的咖啡馆。
他们提供的咖啡是普通的咖啡,桌上的糖罐不那么好使,怎么晃,也晃不出砂糖来。他们的酒保默默坐在用一堆不知道是什么机器做的吧台里,并不怎么照顾客人。
吧台前的高凳上坐着一个剃光头的青年,穿黑色夹克和黑色皮靴。不知道是不是右翼光头党,光头党是原东德地区兴起的新纳粹组织,用暴力攻击在德国的外国人。德国市民解释他们是因为东德的高失业率,东德青年认为是外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所以仇视外国人。德国知识分子解释他们是因为东德人经过柏林墙倒塌的兴奋和幻想以后,社会上弥漫的失落和愤怒。东德的知识分子曾说过:“我们并不是合并,而是西边把我们吃了。可我们就卡在他们的喉咙口,让他们吐不出,咽不下。”说这话的人,在冰凉的蓝眼睛里闪烁着蛮横,耻辱,不屈和恼羞成怒。
临街的窗上,伏着最后一缕夕阳,那种灿烂而悲伤的金色,只有临死前的梵高能用得出来。那里的一张桌上,独自坐着一个男人,在喝一瓶慕尼黑产的啤酒,他坐在那里,几乎不怎么喝,只是看玻璃杯子里从底下不断升起的如线的气泡。他有一个沉思的背影,肩膀软哒哒地靠在椅背上,可头像眼镜蛇一样高高地直立。在这个宁静的咖啡馆黄昏,他在想什么呢?这个咖啡馆里的一针一线,都带着那么强的暗示和情绪,他还能自由地想与它全然没有关系的事情吗?
太阳已经落山,打开的窗前一股股地涌进了充满阳光气味的温暖气息,天光柔和而明亮。一个非常美的年轻女子经过窗前,走了进来,她的眼睛又大又圆,睫毛像向日葵似地张开,带着与西柏林的女子不同的淳朴与诗意。那是更接近东欧的美。她找了靠窗的桌子坐下,要了晚餐和用蓝色大陶杯子装的牛奶咖啡,是通常用来吃麦片的杯子。她应该是个从事艺术的人,因为她手上的手镯,是用一把叉子弯成的。
吃完盘子里的东西,她拿出一本书来,翻到折过的那一页,接着看了下去。
4.2010年的布达佩斯:一道蓝边
到达布达佩斯的晚上,我住在链子桥对面的大楼里。楼下热闹得很,都是新兴的西方式酒吧,这条街上,连从前那些门楣高大,装饰沉郁的旧咖啡馆,在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就赫赫有名的,现在晚上也开始卖酒了。旅游书上介绍说,聪明的旅游者到别具风味的纽约纽约酒吧享用完布达佩斯最著名的古拉绪浓汤,而且,要问侍者要多多的红辣椒面才算正宗的懂得,然后就到酒吧区来过夜生活。
秋天最后的温暖空气里,人们坐在室外,说话声如山谷里的云雾般,带有些清晰的齿音却整体轻柔含混地蒸腾上来,偶尔还能听到玻璃杯子相碰撞清晰的轻响。我打开了窗子,晚风轻柔凉爽,像普希金诗歌里面写的那样拂动着窗帘。从大楼之间的缝隙里能看到一点点链子桥上的灯光,还有对岸城堡的影子,这就是伊丽莎白皇后最喜欢的城市,她是它的保护神。在慕尼黑时,她曾是茜茜公主。
这是秋天最后的温暖时光,让人怀着惆怅想起夏季。古老的公寓大楼,长长的木窗子连接着高大的天花板,在东欧我总有机会住在这样短期出租的公寓楼里,从前人们叫它出租公寓,在布达佩斯有个更时髦的名字,公寓俱乐部。
这高高的天花板让我想起许多东欧的城市,波兰的华沙,卢布林,克拉科夫和扎莫什奇,以及东普鲁士的旧城格旦斯克,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和皇村,捷克的布拉格,东柏林,魏玛,德累斯顿和波斯坦,甚至还有某些奥地利的城市,林茨和因斯布鲁克。还有从窗子里浸入的声响,更多的人声,电视或者收音机发出的播音员的声音。那都是一种与一切都在秩序之中的资本主义世界有着微妙不同的声音,云一样飘浮在高高的世纪初的天花板上方。
我到厨房里去为自己做一杯茶。
橱柜里整整齐齐排列着各种杯子,刻花的葡萄酒杯,厚厚瓶底的啤酒杯,陶瓷的茶杯画着一道蓝边,看上去像是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带着一股乡野地主农舍里的乐观气息,与时代消亡带来的惆怅。我取下它来,准备装上我的茶。
在布达佩斯郊外的另一个小城,有个名叫“在斯大林靴子的阴影下”的雕塑公园,是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那里冷清的草地上陈列着从布达佩斯街道、广场和学校中清除出来的各种社会主义遗迹,斯大林铜像,马克思恩格斯一体像,列宁像,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苏联军人像,工农兵浮雕,以及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群像,高大的苏式街头雕塑,按照一颗五角星的形状排列在公园里。门口的红五星商店里卖出当年的货币,红旗,废弃的党旗与党徽,以及各种勋章,还有洋铁皮做的牛奶罐,以及带有一道蓝边的茶杯。当一些旧有的生活遗迹集中在斯大林高高地踏在红砖台上的靴子旁边,它们散发出一股监狱般的气息。下午好不容易找到那里的时候,有一队小孩子与我一起参观,带着他们的是小学的历史老师。
我将热水注入放好了立顿茶包的杯子里,来自斯里兰卡小英伦茶产区的earlgrey旋即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柠檬草气味,在蓝边茶碗里散发出世界大同的异国情调。在厨房中央的柚木小圆桌上,安放着一只笨重的收音机,我过去打开它,上一个使用者将波段调在音乐台的频道上,所以,它接着播出古典的钢琴曲,已经好久没听到收音机里传出的音质平扁的音乐声了,恍若年轻时代。我想这曲子应该不是《忧郁星期天》。但电影里那个故事,似乎就应该发生在我住的街区里,现在想起来,它更像是个抒情的城市漫游电影。
我在小圆桌旁坐下,然后看到在小圆桌旁边的墙上,褐色镜框里挂着一首手抄的小诗,匈牙利语。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就是匈牙利诗人吧。但我希望这里抄写的不是这首政治化的诗歌,而是更为柔软的,比如《悲哀吗,是一片汪洋大海》,或者《我愿意是激流》。“只要我的爱人是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的游来游去。”那样赤诚的奉献与爱,在我看来就是典型的东欧,连莱茵河畔穿着短大衣赴死的维特都会黯然失色。
1968年,捷克有布拉格之春和《嘿,裘德》,1956年,布达佩斯有裴多菲俱乐部。在我少年时代,从道听途说的窃窃私语中听说过那些耸动的事件,才记住了这两个充满诗意与哀伤的城市。回想起来,我这一代人竟是用这种方式学到了世界历史地理。当然,还有华沙1945年的屠城,卡廷森林的惨案,俄罗斯的古拉格群岛以及叫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女诗人,伯林在《俄罗斯的心灵》里描写的圣彼得堡的夜色,他在堆着肮脏的雪的街道上匆匆而过,去拜访那些噤若寒蝉的诗人们和音乐家们,八十年代优美的拉拉之歌,那是《日瓦戈医生》的插曲,纪念一个纯洁的俄罗斯女人,她在压力与精神追求之间的选择展现了俄罗斯式沉重的诗意。
我从来对政治历史没太多兴趣,我只是被那些在特殊的历史地理里蕴含的温柔的哀伤,与不论如何都不屈服的精神打动,只是一直都认定它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动人的奉献。
在我没什么阅历时,就被这样的故事深深打动,至今没有太大变化。这是我经历了岁月洗礼的感情。每次我住在这样安静的,有些荒芜的高天花板的东欧街巷中的一间房间里,心里都为自己还是保有着少年时代的价值观而有点自豪。
高高天花板下,我只要有机会安静地独自坐着,这种来自东欧的诗意就如一种柔和的光线一样将我的心笼罩住了。这是我在伦敦,纽约,巴黎,罗马,马德里和维也纳以及阿姆斯特丹和旧金山这些伟大的城市都找不到的感觉,我也是爱这些大城的,但这爱不同,在东欧高高的天花板下,那是一种非常深切的,似乎能融化其中的感情。
我只是在那里能感觉到自己内在,有一部分属于它。
只是这样的感情渐渐淤塞了。我知道它并未干涸,只是无从给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