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格局中的知识人格
2013-12-29张大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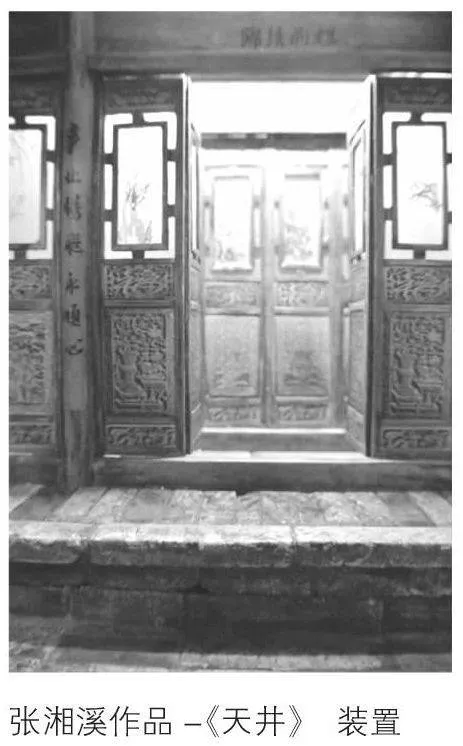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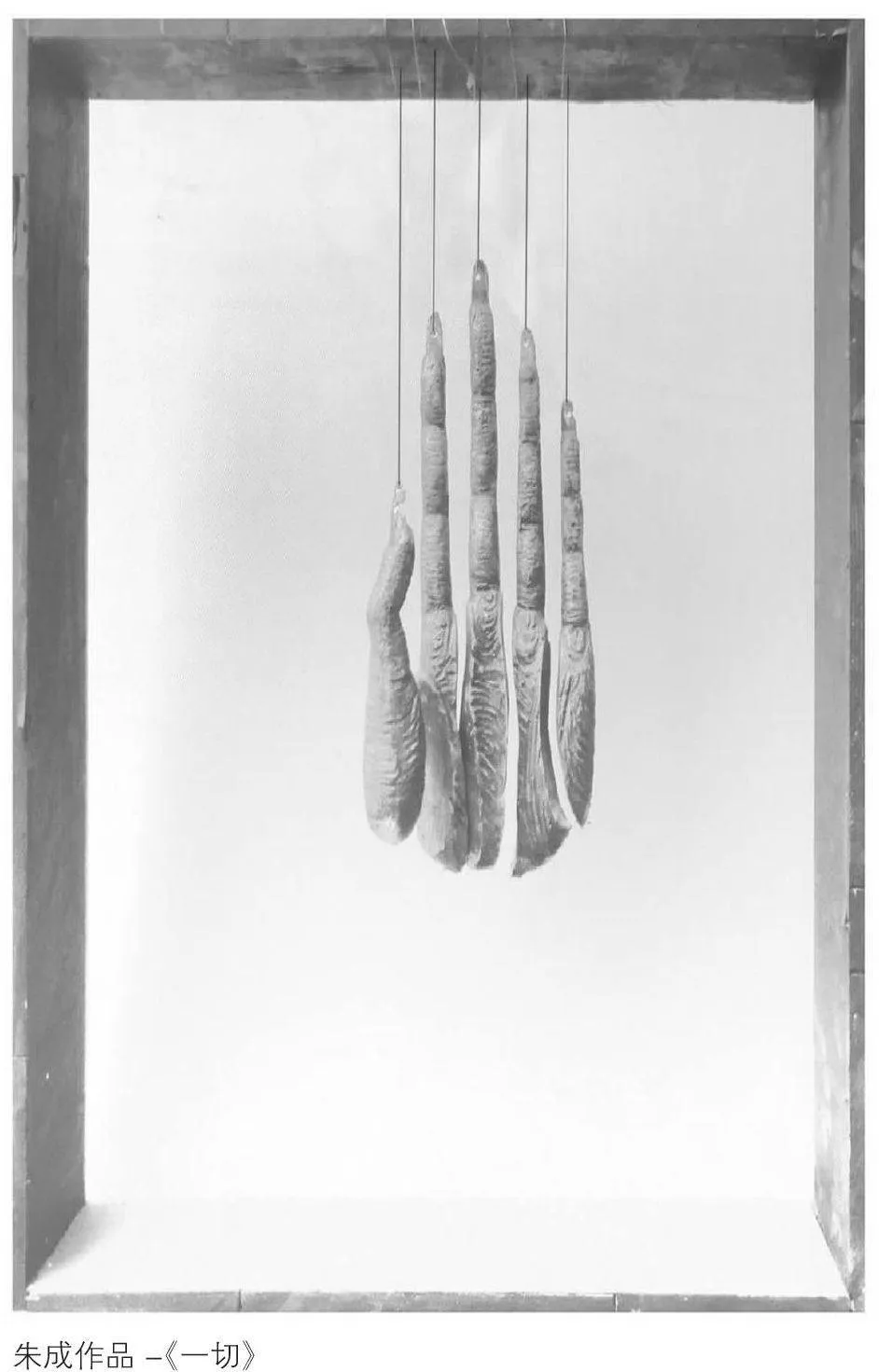
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于东方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人们已经说了太多,人们心目中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道德画像早已定型:他们的突出特征就是其附赘悬疣式的“道德”化特征,因而是一种迂腐和可笑的特征。但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本身就潜藏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新的道德。正因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核心已经被这种意义上的“有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调延宕、肢解了它的直接性与透明性,那它是否能在“知识分子”的新道德当中获得合理公正的评价,那就肯定是一个问题。但在没有道德感的前提下,用“道德”反对“道德”却又无关乎道德,这确实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景观和道德谱系……在这样含混的语境条件下,甚至连概念用语都是一个问题,因此,本文使用的“知识人格”这个含糊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一方面要意指那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并不在其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人格构成,另一方面要让它兼容“知识分子”一类概念,或者能够与之产生一定的意义联系。
一、超越性存在秩序中的东方传统圣人人格
现代“知识分子”最不应该发生的错误,就是在潜意识或者显意识当中,将自己比做古希腊哲人——将哲学的沉思生活视为最高幸福的古希腊哲人。而像康德这样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似乎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尤其是苏格拉底,更符合人们心目中的“哲人”形象,上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哲人。这其中包含了一种哲人自身的幸福伦理学,或者一种哲人的道德,或者一种以哲人的道德为最高样板的伦理学和道德体系:“亚里士多德只是把超越政治的生活、高于政治的生活或与政治生活相对的精神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某种界限。人不仅仅是公民或城邦。人还超越于城邦;然而,人只有借助于他身上最好的东西才能超越城邦……人只有追求真正的幸福,而非追求随便怎么理解的幸福,才能超越城邦。”[1] 是否超越城邦,取决于“他身上最好的东西”,而不是取决于现代各种“主义”之争当中的左中右划分,不是取决于“知识”货色本身的“品质”。这与现代“知识分子”把从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学究性研究进入所谓“公共领域”视为一种道德上的提升或优势,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种结构性的“堕落”与“螺旋式下降”当中,我们不可能设想现代“知识分子”与同其隔了两层的古希腊“哲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
但在这其中,我们同时也看到,即便是亚里士多德,也放任了某种抽象性的蔓延——亚里士多德自己(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相比)体系化的“伦理学”至少是这种放任的间接后果,而这最终又是因为他放任了哲人对于自身的特定“幸福”的欲求:
与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完全一样,对于柏拉图来说,认知是人的最高可能性。决定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待这种可能性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让这种可能性放任自流;毋宁说,他让可能性保持其自然的自由。与此相反,柏拉图不允许哲人们做“现在允许他们做的事情”,亦即不允许把在哲学思想中生活当作在哲学思想中、在对真理的直观中打坐。柏拉图“强迫”哲人们“为其他人操劳,看护他们”(《王制》,519d-520a)。这是为了国家实际上是国家,是真正的国家(520c)。[2]
在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哲人的道德得以凸显出来。哲人有义务思考道德伦理问题,有义务为世俗的生活世界进行道德立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当道德体系变得因为抽象而无用时,哲人有义务将道德具体化。这既包括思考一种更加具体的道德和道德体系,但也包括通过他的思考和思想行为,使得道德体系变得具体适用,因而哲人的这种思考或思想,有可能是一种更加具体的道德思想和道德思维,但也可能是一种更为抽象的思辨和更为玄远的思想乌托邦——只要它有利于道德的“具体”实践和应用。哲人的道德不是取决于对于他自己、或其他哲人所秉持与建构的“超验世界观”和“道德形而上学”的信奉,哲人自身的道德,更不能从他自己的道德哲学和道德思想当中理解,而要从他与其道德哲学和道德思想的关系中来定位,或更准确地说,要从他与其道德实践的关系中来考量——在这其中,他的道德思想只是这种实践关系的一个方面、一个层次甚至一种工具。可以肯定的是,哲人的道德超越政治社会和民众生活的伦理实体,但哲人的道德首先包括对于这个伦理实体和道德世界负有道德义务。哲人的道德,也许与人们的想当然正好相反,它具有一种极度的反体系化、反概念化的透明性和直接性,即便人们很难理解和看清楚它。
这样的一些表述其实终究也是勉为其难。哲人的道德根本上不能用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概念来理解,这是因为在面对政治社会、民众生活的道德世界的同时,它确实维系于一个超越性的存在秩序,而不是因为它渊源于这种秩序,尤其不是渊源于哲人在其“哲学体系”当中表述的那种“存在秩序”。(但我们看到,康德本人的道德,乃至康德所理解的道德,大概不会超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表述,因此在施特劳斯也许会觉得,大名鼎鼎的康德根本算不上哲人,而只能算是学者。)在这里发生的误识,导致人们将现代的“知识分子”当作“哲人”来认识,而这在西方传统当中也是其来有自,因为即便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将“认知”当成“人的最高可能性”。但在东方和中国古典传统的圣人人格那里,消除了认知理性的轩轾隔碍,对这一切的理解就要更加圆融、通透得多。与西方传统当中的哲人的“认知”倾向相比,中国古典传统中的圣人,更像一种“实践性”人格:“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周易·系辞下》)。圣人的这种实践人格所最初面临的,是自然与人事、政治的相互交错、牵引的双重压力:“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尚书·洪范》)这其中的核心,是一种生存的无根基的惶惑和不确定感。自然经验既然不可以人为地主宰,中国古人的措施和方略,因此就是更加深入地投身于自然之中,这反过来也内在地扩展和提升了人的经验领域,将人事与自然错综穿插在一起。人们对于自然的法则和规律的最初揣测和琢磨,就是卜筮,卜筮所代表的是一个镶嵌、交织在自然法则当中的经验和生存系统。在此基础上,东方和中国古典传统很难发展出一种全身心面向自然的、纯粹概念思辨的形而上学,因而在自然和人性、人事之间,包含在圣人人格身位当中的枢转、中介性作用更加增大了。
将这样一个经验系统和自然法则提升为一种“哲理”和“哲学”式的理论系统,人们认为这就是《周易》这样的经典所力图完成的任务。但如果仅仅从“哲理”和“哲学”理论的意义上看待《周易》这样的经典,那它也仅只是一种参差不齐的“哲学”,或者说只是通过《易传》《中庸》等的“道德形而上学”视野看到的《周易》或者《易经》。如果中国古典传统当中的圣人只是《易传》《中庸》这样的形而上学著作的作者,那他最多也只能算是“哲学家”,甚至只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天地设位”的自然秩序、形而上学的哲思与道德义理涉及的人性化领域之间,东方传统和东方圣人选择了使它们相互循顺、叠加的肯定性文化模态和价值情态,也就是说,把它们理解为一个连续性的、相互支持的圆融领域。东方传统和圣人不是把自然法则本身当成是“道”,而是把在这种连续性的圆融境地当中对于“道”的寻求、实践、尊奉称之为“道”。“圣人成能”,圣人起到了沟通这两个层次或领域的作用:“上观河图文,下察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参合考三才。动则循卦节,静则因彖辞,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后治”(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天符进退章》)。圣人因此可以看成是筮人与哲学家的统一:筮人生活在人民中间,与民同患,有神奇、灵秘的先知先觉,但却没有太大的视野和智慧;哲学家有思想、有理论甚至有智慧,却没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将这样的思想智慧施之于伦常日用的实践途径、方略;唯有圣人能够将这两者统一于一身,圣人因而是前者的先知先觉、忧患情怀与后者超然的理性、智慧的统一。
仅仅停留于“道”本身的“道”,是平面的和抽象的,圣人使其成为立体的和实践的格局。圣人捋顺了天地自然与人事、政治之间的关系,于是圣人由面向自然而转身为背靠自然、面对民众,成为率性、顺天、循道的人格化典范。圣人面对民众需要比面对自然时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也意味着他对于自然秩序、自然之道的一种扩大和超然、升华了的新的理解方式,或正因为有这一理解,他才是圣人。因此,一方面,圣人以人格化的形态将“道德形而上学”性质的道德义理本身给具体化了,这种“具体化”,是使道德哲学和道德教义本身,得以下达和肉身化为一种人格化形式,成为可以供人遵循、易于被人尊奉的样板。这也成为东方和中华文明史的起点。这其中并没有太多的神秘主义的因素,而只不过是一种贯通于人事和政治领域的、被升华和重置的、更高一层次上的自然法则,以及对于这种法则的寻找、叙述、实践和遵循。“上观河图文,下察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参合考三才”,这就是对于《周易·系辞》当中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一种更为详尽和具体化的阐述;而“动则循卦节,静则因彖辞”,则是圣人在证得《易》道或天地自然的形上之道之后,所抵达的自由境地。它是圣人仰观俯察、取法天地自然之道同时,在经历艰苦的修为和磨练之后,其人格构成与天地自然之道二者冥契无间、参合统一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自由境地,或许也就是所谓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境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圣人人格与自然之道相互之间,上通、下达的通道均已经建立。这样,通过天道自然与圣人人格的同构关系的达成,在具有“向上一路”的目标指向和价值理想的同时,也具备“向下一路”的引导与门径作用:这也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的信念(在道家就是人人可以成神仙,在佛家就是人人可以成佛),成圣成贤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打开的。这其中包含的道德原理和道德理想就是,既然自然之道不过就是天地自然法则的升华,而圣人又只是自然之道的遵从者和实践者,那么,既然每个人都是自然的产物,只要通过正确的途径和付出足够的努力,圣人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境地。因此,东方传统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入口和门径,就是人人可以成为圣贤的理念或信念,这同时也是其道德意义上最高境界与终极理想。
但另一方面,圣人之道的格局的阔大和恢弘,也始终不能掩饰圣人的一种更深层或深沉的道德情态,这就是“忧患”。这一点在《周易·系辞》当中体现得非常集中:“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吉凶与民同患”……当然,圣人的忧患肯定不是“小人常戚戚”式地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小惠而忧愁烦恼。这种忧患,从圣人面对世界的主体性机制来说,它所体现的是圣人智周万物、心怀天下的“空心”人格:圣人以放弃其私心、私我层面的方式,使其人格的具体构成本身,成为天道自然的全方位的实践载体;而从道德内容和价值实质来说,圣人的忧患所指向的,终究是对于“道”本身的忧虑。圣人知道,超越秩序并非仅仅是天地自然,礼崩乐坏、人心颓危,同样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秩序,同样是自然而然,圣人能够为道德世界树立具体的样板,却不一定能控制道德的颓败。因此,圣人的核心忧患也许就在于,东方传统包括东方圣哲的这种肯定性的文化模态和价值情态,终究抵挡不了尼采所说的“人本身的堕落”[3] ,它指向一种肯定性的、向上的价值,但如果这个世界不向上,那它也没有什么太有力的办法。圣人所信奉的“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思辨体系,也不是挂在嘴边的幌子和招牌,在自然洪荒的原始莽力面前,圣人要循顺着这种力量创制秩序和规则,包括伦理秩序和道德法则;但当这样的秩序和法则在特定情形下变得抽象、飘浮而不适用时,圣人必须将道德变得具体化,或者说,总是需要具体地考虑和处置道德问题。因此,《周易》的《易经》系统层面所沟通的自然经验的不确定性和卜筮式的神秘性,倒是东方传统当中的一种积极的因素,而与此相应,“忧患”当中包含着圣人的道德的本体论,圣人和圣人的道德,在缺乏自然合法性根据和实证政制的荫蔽的混乱的“超验秩序”面前,即便是作为一种乌托邦或者一种隐喻,也始终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意义的,而不是将其与种种“落后”的“超验世界观”一起革除。
循顺和尊重自然之道,是东方和中国古代传统的基本特征,这一点圣人本身就是典范和样板;但既然人人都可以遵循自然之道,圣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圣人之为圣人,不可能仅仅是对自然之道的遵循;正因为超出自然之道来考虑自然之道,才使圣人成为圣人,而这也才使“自然之道”成为真正的“自然之道”……圣人的道德只能是这样的一种展开格局。圣人的“忧患”的道德机制和道德核心,一方面使圣人的道德远远超出现实的道德和政治社会秩序的范畴,另一方面又使其与这一现实秩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引子贡言)。只不过到汉代以后,作为超越性秩序的具体化承担者的圣人人格,基本让位给了作为现实的政治秩序统治者的君主:“《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这也就是说,儒家的素王之法、天子之事,已经被实证性的政治制度彻底统合其间,通过儒家学说和“政治儒学”,已经不能够通达实证政制之外的超越性的自然秩序。道德本身有了现实的国家和政治秩序的规范、塑造和惩戒、干预的手段,但我们不能确定,这是否就能够实现和完成圣人本身的道德理想。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样的实证性的政制秩序内部,圣人已经不复存在,而“知识分子”诞生了。
二、启蒙知识分子的“知识社会学”人格
中国传统知识人格是独立于天地之间,谛视和守护着大化运作、天道周行,而不是独立于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西方古典哲人的情形大同小异。这需要面对真正旷古的孤独和寒彻骨髓的落寞,现实的政治秩序和道德伦理并不是他的终极的生存根据,他充其量是与前者共生、共存而已,其价值理想和人生目标不可能在前者当中完全实现,这是一开始就清楚的事情;而启蒙之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立法者”还是“阐释者”,抑或还是“批判者”,其安身立命之所离不开的现实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也是一开始就清楚的事情。“知识分子”也许会说,我的知识比我的生活高尚,我的思想比我的身体高明,现实的情形也许有这样的时候,但究竟能“高尚”和“高明”到什么程度,却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为这种“人格”的分裂和扭曲做过一点什么,有过些许的反省。默然的态度已经显得有些高贵,不少人也许正自鸣得意于自己的机变和机巧之才。随着古代世界观的被“终结”,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在最为“关键性”的一点上恰恰继承了古典世界中的“传统”,那就是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与现实的存在秩序和现世的生存格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关系——而不认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和道德理想是两回事,才对得起“知识分子”这个名号。只不过,这一存在秩序和生存格局的最终根据,在古典世界中首先是天地大道的大化周行,是上帝的创造,在现代则是民众生活的意见秩序和现实的伦理政治建制。这样,“知识分子”无论是“立法者”还是“解释者”,是“批判者”还是“建设者”,所着眼之处,都逃不脱自己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知识人的幸福和福报只能来自于这个社会秩序:在体制内得不到“回报”,可以从社会大众、民众意见那里邀宠,最后再被体制认可;在这个社会“批判”过了头,恰恰拥有了在另一个社会当中生存的资本。在现代社会当中,邀民意、民众之宠,是一种更高明的邀宠之举:拿出一副民众道德的代言人和民众理想的代理商的姿态,以一种批判“现实”、针砭“时弊”、发掘“真相”的面貌出现,恰恰是一种更为夸张的邀宠之举。
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德问题,道德“知识”、道德修养、道德身份问题,即现代“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道德”概念,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怎样对自身之外的道德领域和道德世界负责的问题,也就是古典圣人和哲人的道德问题:“由于直接关涉政治生活,古典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另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往往自称政治‘理论’,这绝非偶然。古典政治哲学首要关注的不是描述或理解政治生活,而是正确引导政治生活。”[4] 像康德这样的“哲人”,他的书无论如何晦涩难懂,从其本意来说却肯定不只是写给“哲人”看的,或者说,在他的心目中,根本就再也没有哲人和普通民众的区别,只有一个个抽象和平均的“道德”个体。“哲人”只是这样一个写书、授课和传播知识的“道德”个体。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前提,就是哲人的道德知识和哲人的道德身份再也没有了道德力量,而启蒙知识分子的经验性知识拥有了锤子、锄头一样的工具性“力量”。古典哲人所做的,要远多于按照道德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应该做的,而且根本上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道德”:“古典哲人把最佳政治秩序理解为在一切时空都最佳的政治秩序。这并不意味着他把这个秩序设想为必然有益于每个共同体……”[5] 古典哲人的道德行动、道德协调和道德实践,恰恰在民众生活的道德世界和道德领域之外。对于一种“超验世界观”或者自然秩序、自然之道的知识性的刻意的循顺和彻底的遵从,只有在一种纯粹的“哲学”中才能做到,或者说那只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思维,这就是像康德这样的用后脑勺面对民众的启蒙“哲人”的身影:康德在震惊于“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时,一定是背对民众、拧着眉头作苦思冥想状……用后脑勺面对民众,这意味着,第一,其道德身份不再超越民众;第二,哪怕其思想传遍世界,其道德职责不再超越他的道德身份。而这些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谦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尼采所描述的“学者”的含混背影[6] 。像现代启蒙世界观那样认为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尽职尽责的个体,都是道德的个体,这只能是一种对于秩序的纯粹是“哲学”的思维;而即便真的如此,那由这些个体所组成的社会,也不必然就是一个完善与美好的社会。恰恰相反,如果能够有一种具体的思维和实践性的道德思维,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这个社会至少需要对于这个社会的总体和整体负责的尽职尽责的“个体”,而这个“个体”的道德本质上必然不同于平均化、原子化的道德个体的道德,也不能根据这个社会总体的道德体系来理解。
圣人人格和古典哲人认为自己的存在根据不在现实的伦理生活和政治社会当中,但他对于后者负有道德义务,或者说,他的道德就包括对于道德社会负有道德义务;而“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在道德上并不高于民众及其伦理和政治秩序,但自己在“知识”和思想上高于民众的生活世界。“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的“知识”就具有道德意义,而是首先在于他把道德“知识”化了,把道德变成可以理解、可以掌握的道德“知识”,变成甚至可以用无言和否定的状态就能够维护和赞助的一种道德:“道德今天在欧洲是群体动物的道德,因此,像我们对事物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人的道德的一种,在它旁边,在它前面,在它后面,许多其他的道德,首先较高的一些道德的可能的,或应该是可能的。但是这一道德用一切的力量抵抗这一‘可能性’,抵抗这一个‘应该’,它顽固和无情地说:‘我是道德本身,此外没有什么东西是道德!’”[7] 道德像“知识”一样,可以理解、可以掌握,当然也就可以教授、可以传播。哲人变成了“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教师,而且首先是道德教师,虽然他自己也知道,他在道德上并不高于人民:
尼采面临的哲人与“人民”这一古老关系的新问题是,哲人成了“教士化”(“主义”)的人民(自由知识分子),这号人要让全体人民都成为道德化的“教士”——这就是启蒙的理想。“教士化人民”出现之后,哲人消失了,只有学人、文人——民主知识人畜群。随后,这个“我们”畜群中间发生了长达数百年的“人反对人的战争”——“主义”之间的战争。[8]
这就首先需要考察“宗教世界观”的整体格局的变动。“知识分子”成了道德传教士,他想把“道德体系”像传教一样传布给人民,让人民自己因为这套道德的形而上学体系而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或变得像他自己一样成为“教士化的人民”:道德既然成了科学知识,那就可以学习,也可以不学习,可以认同,也可以否定,更重要的是,可用“道德”来批判“道德”,用“道德”来否定“道德”,却不用承担任何的道德负荷和道德负疚——这恰恰是现代性道德正当性危机的症候。因此,为了挽救这种现代性道德的正当性,所谓“教士化的人民”就是要求每个个体都像康德一样,经过一番实践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而变得有道德。这种道德机制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现代的自由社会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成了道德的旁观者和看客,但却又都认为自己很有“道德”,而在这其中,又以最具“批判”和“反思”能力的人民——“知识分子”为甚。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已经不是孔圣人和柏拉图的时代,传统知识人格的那种人格理想已经不合时宜。但恰恰因此,才更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圣贤心术和道统担当,以使我们的社会生活不至于被“意见秩序”所窒息。中国传统知识人格和圣人心态的根据之所在,恰恰是民众生活的意见秩序和政治社会的边界,也就是“专制”的边界所在。现代以后的民众的“道德秩序”不是民众自己创造的,而恰恰只是启蒙知识分子的某种道德专制,是康德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杰作。在启蒙知识分子那种恰恰有一种道德专制,或者说对于道德的一种抽象的概念专制、理念性专制:他们认为道德是一个单数词名词,世界上只有一种如他们那样被“抽象”地理解的道德。随着启蒙主义的传播,这种启蒙道德的抽象性概念专制,不仅使得每个潜在的道德个体成了被“道德”概念和“道德”知识外在地强制的麻木对象,而且也让“知识分子”本身的心性窒息。启蒙知识分子就是凭靠道“道德形而上学”机制和道德知识对自己的心灵的自觉自愿的、“道德”的自我“专制”,建构起了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德身份”。
“知识分子”的优越之处也许首先在于心性本身的灵明觉悟,在于其因此对于心性之“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的领悟,道德之为道德,正需要这样灵敏、圆通的心性,道德的起点,首先就在于培养和激发这样的心性。对于道德个体、尤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知识”也许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但却并非必然如此,甚至有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我们在启蒙知识分子那里看到的,就是“知识”令其心灵更加抽象、更加僵硬、更加“专制”:
有一次,冯友兰往访熊先生于二道桥。那时冯氏《中国哲学史》已出版。熊先生和他谈这谈那,并随时指点说:“这当然是你所不赞同的。”最后又提到“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冯氏木然,不置可否。这表示:你只讲你的,我还是自有一套。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9]
这是启蒙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知识人格之间的一次现代对话,也许是最后一次对话。冯友兰当然不至于像牟宗三所描写的那么不堪,不过至少在那一瞬间,启蒙心性占据了上风和主位。冯友兰在自己晚年的哲学史著作中,将自己的哲学体系归入“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而将熊十力的哲学命名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当中的心学”[10] 。不过“理学”也好,“心学”也罢,都还只是“宋明儒者”的视野,它们还都只是抽象地谈论心性:理学抽象地谈心性,是因为它将心性范畴发展为一套道德形而上学的教义,心学抽象地谈论心性是因为它只谈心性本身,而不谈知识人格的道德。而这样的“宋明儒者的层次”受到推崇,可能又恰恰是启蒙哲学的影响,是康德式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思维:“与佛法东来相比,西法东来对儒家的职责带来更大的多的压力……尽管如此,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已经为面临西法东来压力的现代儒生提供了抵御的学理基础。因此,十力虽然清楚地知道,宋儒既临丧乱,又临‘出世之教’蔓延,复兴儒学功不可没,他仍然要说,‘惜乎宋儒识量太浅,只高谈心性,而不知心性非离身家国天下与万物而独存……’(《读经示要》卷二,《全集》卷三,页803)”[11] 。心性如果是圆融灵明的道德之心,那它就不可能“离身家国天下与万物而独存”,但如果是高谈“心性”概念的宋明儒者的知识化的“启蒙心态”,那就另当别论。因此,冯友兰、牟宗三如何这里暂先不论,要说熊十力,他不是王阳明式的人物,而是孟子式的知识人格。
三、现代知识人格的“获救”之途
古典哲人构造和表述出来的那些“道德形而上学”很可能只是用于道德伦理用途:不是抽象地构筑“道德形而上学”(这是典型的“学者”的思路和做派),而是将“道德形而上学”以“形而下”的方式施用于道德伦理领域。而现代“知识分子”却以为,古典哲人只是因为自己信奉这些“道德形而上学”,所以才拥有和遵循那种迂腐的哲人道德:他们把古代圣哲当成了埋首于学究式的“自然哲学”研究的腐儒,他们认为,古代圣哲是根据“天上的星空”得出“心中的道德律”——这简直是愚昧不堪,所以既然表达古典的“超验世界观”的“道德形而上学”已经不攻自破,那这些哲人的道德也就可以弃如敝屣了;而他们的偶像康德的“聪明”和“进步”之所在就在于,将“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分离开来,却只是从形式上让实践理性模仿理论理性,道德理性模仿认知理性——至少是一种反向的模仿。在此前提下,鲍曼等人提供了一个根据特定的社会特征来确定“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典型范例[12] 。但特定的社会特征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这其中是一种必然的联系吗?即便有“必然”的联系,这是一种道德理解和道德实践本身,还是仅仅只是一种理论认知的对象、并进而成为确定“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根据?“知识分子”个体及其佩戴的理性知识装备,仿佛就再现了现代世界观自身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结构:“知识分子”的个体“单子”,是现代世界观立论的思想原型,也是现代道德机制的楷模。这一点,倒不是“知识分子”自封的,而是“知识分子”们“知识社会学”的存在结构所给出的“结构性”的地位和位置。现代性的道德机制如果真的能够实现,那也不能算是最坏的结果,但问题在于,把民众设想成思维和知识机器,这本身就不是道德思维,而只是“知识分子”的知识理性和知识学意义上的抽象设计。“知识分子”反过来因此占据了一种道德人格原型的位置,却把一个巨大的道德空洞留给了现代社会。因而,在现代社会,“道德”只能是一种偶然的运气。
孟子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特征,似乎与现代“知识分子”有些相似,面对的确实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与春秋以前的时代相比,不要说什么“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超越秩序的玄谈没有市场,就算孟子想以其“先王之道”“尧舜之道”做一个汉代以后的董仲舒式的“知识分子”,一心只想着争霸天下的利益的战国诸侯们的实证政制秩序,也恐怕连一天都容忍不了他。因此,除了狂狷之士以外,孟子时代有些鲍曼式的“知识分子”认为,“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孟子·尽心下》),这样“谨厚”(《孟子集注》朱熹注)地待在“斯世”存在的道德身份之“坑”中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可以今天主张不吃狗肉,明天主张煤气涨价,但孔子还是亲切地称之为“乡愿”,孟子则称更为形象地之为“原人”: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式的知识人格,一方面将自身的出处进退与“道”进行了紧密、直接甚至有些“机械”的联系:“身出则道在必行,道屈则身在必退”(《孟子·尽心上》朱熹注),这意味着孟子首先就割断了现实的伦理格局、政治秩序与知识人格的道德义务、伦理身份之间的联系。他一开始就将知识人格规定为“天民”(《孟子·万章下》),将知识人格的幸福规定为“天爵”(《孟子·告子上》),但同时,这个所谓的“天”,乃至像孔子这样的“集大成”的圣人(《孟子·万章下》),似乎有些抽象、玄远,于是知识人格只能从低到高地得到自己的福报。孟子的焦虑很具体,因此孟子似乎更接近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像是更多地为“知识分子”着想,孟子将知识人格的起步身段放得比较低:尼采将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称为“教士化的人民”,而孟子给“知识分子”规定了一条“得救”的道路——“知识分子”是人民中的犹太人(孟子是从低到高地考虑“犹太人”问题,而尼采是从高到低地批判“犹太人”,这是他们二者不同的“犹太人问题”)。“知识分子”虽然是“天民”,但他却站在民众中间,他的伦理身份是为民众生活的道德伦理秩序服务。他自身的道德似乎至少不与民众道德冲突(“三乐”),有可能冲突的部分,似乎也被表述为一种“负道德”(“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既意味着其对于“斯世”生活终不抱希望,但也是对于“斯世”的道德伦理和政治秩序的维护和认可。
但另一方面,孟子对于“道”的理解、尊奉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复杂的多。正如前面讲过的,人们往往会将这种传统知识人格与那种超越性或超验性的“世界观”联系起来——因而孟子这样的“亚圣”只能是一个更加不切实际的滑稽形象,于是,这类论述的必然结论就是,随着那种超验世界观的解体,传统圣贤人格不再可能。而身处战国乱世的孟子面临的困难实际不仅仅是这些,在比之“礼崩乐坏”更进一步的战国时代,不仅所谓的“超验世界观”本身并起不了什么作用,就连孔子《春秋》经教也真的成了“空言”,那些“善善恶恶”的微言大义,战国时代的“乱臣贼子”们根本不在乎、不想听也听不懂。但孟子之为孟子,并不是因为他秉持和贯彻什么超验世界观和性善的形而上学,他也不是简单地模仿尧、舜、周公、孔子这些圣人,孟子早就知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孟子自觉秉持的“先王之道”(同上),是发明“王者之迹”(《孟子·离娄下》)的《诗》教之政治教化传统:
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君无父,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自觉继承的更主要的是教化、激发、感染人心的《诗》教传统。孟子的理想主义的非现实性,恰恰是为了现实地用运于人心和政治教化,所以它是乌托邦的,它因此是与《诗》教相近,而非“道德形而上学”的义理相近。孟子倾力所为是现实政教,而非“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辨。
因此,孟子的心性概念是一个具体的、却又非现实的心性概念,因而是一个心性的乌托邦的概念,而非心性的道德形而上学概念,或是说,还没有像在宋明儒者那里一样被充分形而上学化。“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孟子·告子上》),可以说是孟子学说中最有力但又最无力、最薄弱的论证环节和关键转捩之处:说它最有力,是因为它从人性之现实的、实然的层面作了一种事实情状的认定,从价值层面进行了一种对人性本身的“性善”认信;但说它最无力,是因为它从逻辑上、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毫无根据,从经验和概率的意义上毫无定性。孟子自己非常清楚这一点,或者说,正因为他的道德知识和“道德形而上学”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的,所以,在孟子那里,有着非常圆融而又具体的道德理解或道德知识:孟子式的知识人格之为“知识”人格,就在于在他那里,具备一种由心性的灵明而来的元道德知识,而这种元道德知识恰恰将道德理念和道德体系具体化了,使其能够“从低到高”地讲道德,能从非道德处讲道德,而非抽象地讲“道德形而上学”(由此可见,宋明理学家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理解孟子,以把孟子的心性概念形而上学化的方式借重孟子,可以说是完全南辕北辙)。“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人们也许经常会将孟子当成是怀抱乌托邦式幻想的堂吉诃德,但与其说孟子心中存在着一个乌托邦,不如说,孟子力图将一种心性乌托邦的理念感染、传导给每一个个体,将每一颗心灵锻造为自身装配着一种具有自我启示、提撕作用的乌托邦式装置的灵魂圣殿:“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特别重视的就是在心性隐微之际引发、校正善性和良知、良能,而非用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说教,这与“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过程平行共振,也是诗教“感发兴起”作用的具体体现。
这样,孟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道”是具体的“道”,而并非源于形而上学的超验秩序:他知道世界上并非只有一个作为抽象单数名词的“道德”,他知道道德是一个等级秩序,或者说,正因为道德是一个等级秩序,才使道德成为道德,成为具体的道德。一个抽象、孤立的美好概念,一个玄远和匀净的道德图谱,一种喋喋不休的抽象道德言谈,甚至不一定具有道德教化意义,更不是道德的具体性本身,虽然“知识分子”可以以此获得紧贴和拥有“道德”的傲慢和优越感。孟子总能够很清楚地将具体的道德和具有道德感召、教化作用的乌托邦式的道德景观、道德影像分开,通过此,他将道德理念和道德秩序具体化了。这其中,尤其“知识分子”的道德在此间得以定位。“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一个道德具体化的领域,抽象的道德理念和道德体系,有助于“知识分子”的瞒天过海地隐蔽、掩藏自己道德缺陷:如若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抽象道德言谈确能与天地大道感通合拍,那他就是圣人,但如若不是,这样的情形就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虚伪和伪善所在。正因此,现代“知识分子”特别喜欢抽象的道德,喜欢抽象地谈论道德,但其实现代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种抽象道德的结果:借着这种抽象性,“知识分子”在现代早期获得了鲍曼意义上的社会“立法者”地位;在后现代的社会,还可以当法官和陪审员,捞得一个“解释者”的工作。
所以,作为孟子式的“知识分子”个体,一方面只能从基于个体自然生命的道德之气、从“浩然之气”的修养和培植当中,获得个体人格和心性的完满:“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同时也从符合于心性自然的、乌托邦式的道德天国当中获得其道德动力和生存的价值根据:“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同上)。但这种“浩然之气”更多地是一种生命之气、情感之气,因此所谓的道德动力和价值根据更多地是一种道德激情层次的认同,个体的自然生命既是“浩然之气”的起点又是其终端,而这样的“浩然之气”既是道德责任和道义担当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是一种十字交叉的关系:“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在这种十字交叉的双重压力中,他最终将道德安装在生理机制之上。实事求是地讲,这一点只是“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的具体化和复写,它无可论证,也无从否认。但“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式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逻辑上“同一性”强辩,同时体现的也是对于心性、人性问题由于乌托邦式的伦理激情所带来的同一化和同质化推论,一种经验被激情浓缩的抽象。孟子式的“知识分子”自己是否从理智上相信这一切,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但他肯定从这其中感受到强烈的道德感,也清楚地感受到这些确实有着强有力的道德传导和感染教化作用。因此,孟子的学说不是像牟宗三所说的价值循环的道德形而上学[13] ,而是“心性乌托邦”和心性天国的启示神学,知识人格只能从由“不得已”的道德义务中升腾起的、基于个体自然生命存在的道德感本身和合于天道的幸福感(“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中得到回报。这才能符合圣贤人格“三乐”中的一乐,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孟子式“知识分子”的道德与幸福的圆融与圆善,恰恰是因为它们没有进入形而上学的概念式循环。就此而言,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人,把民众生活的“意见秩序”看成一潭死水、看成一个封闭固定的结构,他们能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吗?能够做到完全避免“行有不慊于心”(《孟子·公孙丑上》)吗?他们的“知识人格”能没有馁陷和缺失吗?牟宗三先生用“道德主体的自我坎陷”来描述认知主体和近代知识人格,牟宗三先生是诚实而仁厚的,我们相信他并无言外之意;但如果我们能将此读出一种反讽意味来,就能够得出启蒙之后的知识人格和“知识分子”在东方文化传统格局和价值体系当中的道德画像。
但另一方面,在孟子那里,知识人格的道德和民众道德之间,并没有断裂和鸿沟,“知识分子”的道德根本上说虽然不同于、甚至高于民众的道德,但并不与后者相冲突。这不仅是因为,知识人格的道德顶点,是在民众道德的通道(“三乐”)里得以抵达的,而且他也给普通民众的道德升华留出了门径和空间,所谓“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不仅说的是君子,也可以通之于普通民众,甚至就是从民众道德之“低”处着眼的。“民为贵”(《孟子·尽心下》)不是空说的,在孟子的道德实践中,也有着具体的体现。所以,孟子的“独立之精神”,很像今天的“知识分子”所自我标榜的那种样子,但孟子的“独立之精神”主要的说给“顽夫”“懦夫”“薄夫”“鄙夫”听的,希望他们听闻伯夷、柳下惠这样圣人的事迹而“莫不兴起”(《孟子·尽心下》)。孟子同时表示,“君子”学习的真正榜样是孔子,“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他们并非“君子”的学习和仿效榜样。然而,对于民众道德来说,尧、舜、孔子这样的“行仁义者”站在道德世界和伦理实体外部,而伯夷、柳下惠这样的有道德瑕疵的“行由仁义”(《孟子·离娄下》)者,也许更重要,因为他们恰恰站在民众的道德领域和伦理实体的内部,并且维护着这种伦理体系的实质性和完整性。他们也可以认为是“性者也”(《孟子·尽心下》),但更代表了“若乃其情,则可以为善矣”的层次,以及心性之曲折精微的现实性与存在实相,因此他们是道德人格和人心、善性的具体样板,也是“斯世”道德世界的终极目标。
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混沌世界里,在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里,知识人格确实有必要、有责任重申普遍性,有必要为天地立心,知识人格应该是对于普遍性的本身的启蒙。但知识人格本身应该是现实生存秩序之外的普遍性,是天地之心,而不仅仅是“特定社会”的“良心”。知识人格的特定道德举措和道德实践与作为“特定社会”的“斯世”有关,但那恰恰是因为其并非立足于“斯世”立场而负有的对于“斯世”的道德义务。所以与“斯世”的关系本身不是问题:作为“集大成”的圣人孔子,恰恰是因为他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而孟子面对的“特定社会”与孔子不同,但道德用心与义务则同,孟子所继承的,恰恰是圣人之为圣人、道之为道的层面,从而孟子相信“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然而,现代的“知识分子”说到底只是用自己的生存论证了现代世界观或现代性的“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不仅是现代道德试图掌握的一种说教方式,同时也是其现实的存在方式,能够以知识学的角度掌握这套“道德形而上学”的知识分子,结构性地成为现代道德机制原型和道德人格楷模——这是鲍曼等立论“底气”的来源。然而,如果现代“知识分子”在此种“知识社会学”的存在结构当中,实际上并不高于民众生活和政治社会的道德,那么他无论怎样富于“独立之精神”,那也并没有什么高尚之处——因为卖烤白薯的小贩同样、甚至更加富有自力更生的“独立之精神”,倒是应该首先感恩这个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和“宽容”;而如果“知识分子”仅仅通过现实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来设想自己的“责任伦理”,仅仅通过建立在碾平了的原子化个体基础之上的抽象的道德身份之“坑”,来理解和定位自己的道德理想,那他的道德便不可能高于民众的政治秩序和生活世界的道德平均数。对照孟子式的知识人格,现代“知识分子”如果确实不知道自己的存在的根基何在,至少应该知道自己的存在没有“根基”:在学术规范和科研考评体系之外,我们自己时代所面对的“超验秩序”是什么?知识分子应该怎么考虑自己的道德身份和道德实践?这些问题应该常存心中,即便只是为了在“现代人”的繁华世界和人间天国当中,照见自己的身相模糊的影子。
注 释:
[1]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危机》,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刘小枫编,彭磊、丁耘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2] 施特劳斯:《柯亨与迈蒙尼德》,见施特劳斯《犹太哲人与启蒙——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一》,刘小枫编,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3][7] 尼采:《善恶之彼岸——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程志民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08页。
[4][5] 施特劳斯:《论古典政治哲学》,见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潘戈编,郭振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109、106页。
[6]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8] 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见刘小枫《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页。
[9] 牟宗三:《五十自述》,鹅湖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10] 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 刘小枫:《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辩证》,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97页。
[12] 见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解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
[13] 牟宗三:《圆善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8~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