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方式就是看世界的方式
2013-12-29贺绍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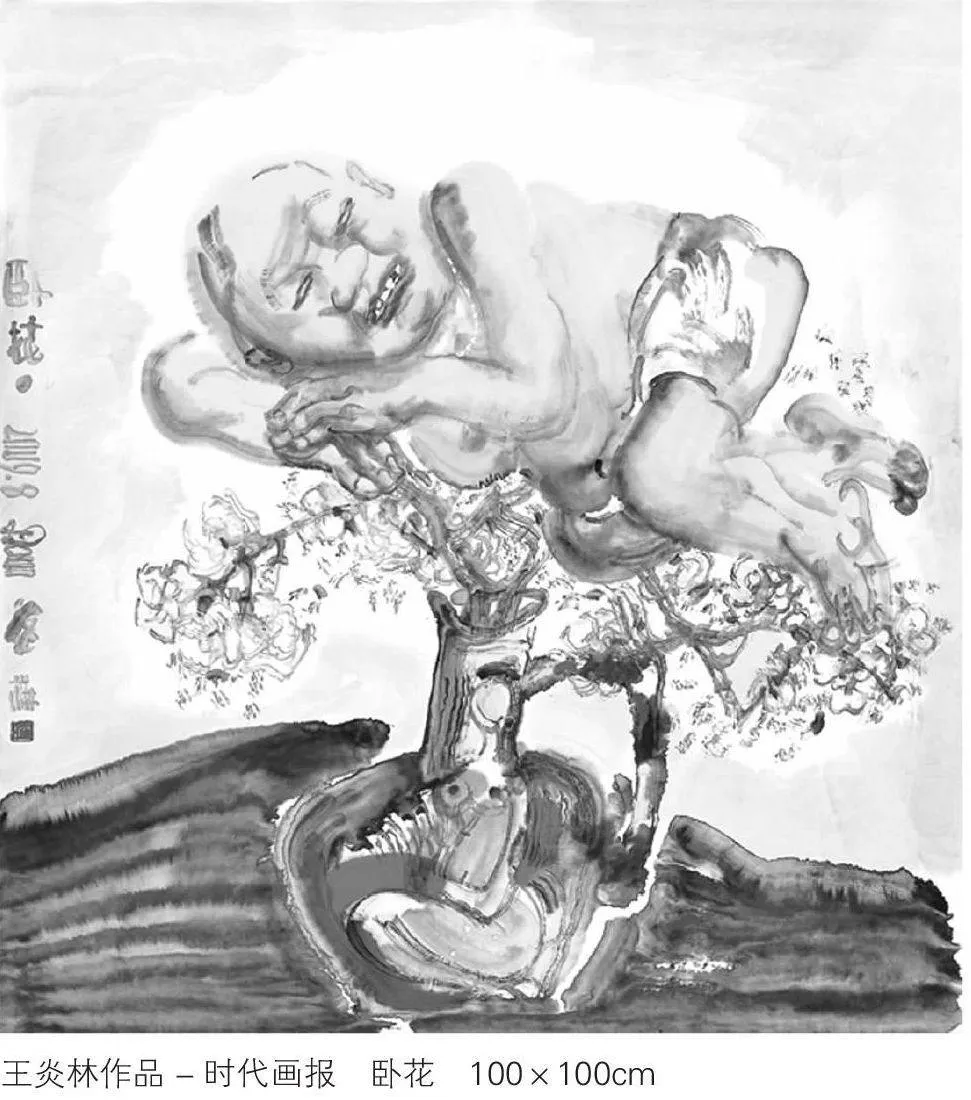
我很喜欢贺奕的小说,尤其喜欢他的认真劲。他以一种认真的神情讲故事,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认真倾听。当我准备为贺奕写这篇评论时,不知为什么就想到了认真这个词,我的这个想法竟然也让我自己惊奇了起来,怎么会把一位作家的小说与认真联系起来了呢?认真也是评论小说的一个方式吗?以前评论小说从来也没有想到小说写作也是需要认真劲的。我不得不放下笔再理清一下自己的思绪,想一想,贺奕的小说中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有了认真的感受。是他的结构严谨吗?或者是他的语言精准吗?或者是他的故事讲得滴水不漏吗?这些都可以说是贺奕小说的特点,但当我从别的作家的小说读到这些特点时,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认真带来的特点。唯有贺奕的小说是认真的。认真是一种态度,是指一个人严肃对待自己所处理的事物,那么我的意思是想说,贺奕真的把文学当成文学来对待,他要通过文学很严肃地告诉大家,他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我以为,这是贺奕最可贵的地方,他对文学太认真了,而他对文学的认真来自于他对世界的认真,他仿佛就是一位哲学家,或者是一位思想家,他要对世界追寻到一个究竟。然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多半是把小说当成是一种消遣,作家似乎也对这个社会多半采取一种妥协的姿态,妥协的结果也就是满足于把小说当成一种讲故事,满足于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莫言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题目也是“讲故事的人”。莫言自然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但显然他决不仅仅是因为他会讲故事而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的青睐。莫言只不过很善于将他的思想非常隐晦地藏在他的故事后面而已,当然莫言对故事的兴趣也大过他对思想的兴趣,他的狂放不羁、想象奇诡的风格不是由他的思想形成的,而是由他的故事形成的。在这一点上贺奕明显不同于莫言。贺奕同样很会讲故事,但他并不放纵自己的叙述,套用一句最流行的娱乐用语,就是贺奕讲述故事时绝不忽悠人,莫言的特点恰是一种忽悠人的特点。这也就是为什么阅读贺奕的小说会给人一种认真的感觉。贺奕特别在意故事背后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指向世界的意义,因此,当贺奕对故事的意义还没有理解清楚时,他是不会轻易动笔的。这就决定了贺奕的风格是一种明晰的、沉稳的、也很流畅的风格,同时也就决定了贺奕讲故事的方式也就是他看世界的方式。
最早读到的贺奕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身体上的国境线》,小说写一位某大学教对外汉语的老师庄祁与不同国家的女孩子的来往和情感纠葛。小说带有自传色彩。贺奕本人就是一所大学的对外汉语老师,也曾到国外从事汉语教学。据说他曾有过没有结果的跨国恋。作者的切身体验无疑融入到了小说人物的塑造中,因此作者本人曾说这是他的一本成长小说,从情感的角度说,小说或许带有一丝青涩的味道,这是一个年轻人在进入心理成熟期时不可避免的阶段。但即使如此,小说也没有像一般的自传体小说那样任其自我情感的发泄。从这部小说起我们就可以发现贺奕的认真,恰是这种认真使得贺奕从进入到小说创作时就有了清醒的理性,他不会像大多数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那样一头扎进密密的丛林里没有方向地乱撞。这种认真使他在动笔前非常冷静地清理了一下自己的情感体验,从而带着清晰的反省来结构和书写与自己有所关联的故事。“身体上的国境线”,它作为小说的标题具有极强的诱惑力,然而它作为作者的一种思想发现,我以为可以成为一句哲理名言,甚至比小说本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贺奕从性爱的体验进入,从生命的哲理出来,他才刻画了庄祁这样一位看似非常擅长男女情事的汉语老师,但实际上,每一个女人对于他来说犹如一个国家,他有很长的时间只能在国境线上游走,而读到他的情爱经历,再联想到国境线的比喻,便发现这个比喻是多么地贴切,完全可以把他的这些情爱经历看成是一次次地越过国境线,有时是偷渡,有时是千方百计办下了签证,有时则是被拒签。贺奕把爱情描述成一个漂泊者,一旦越过国境线,不过是在异国他乡寻找慰藉,那种只有自我才能体味的漂泊感反而愈加浓烈。贺奕的这部小说不妨看作是关于身体政治学的形象阐释,不仅涉及到性别,也涉及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法国思想家福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系统提出了身体政治学的问题,他认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贺奕则从爱情出发,延展了福柯的论述,他告诉人们,身体并不是一个被动的物体,它像一个国家,具有清晰的国境线,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往时,就像两个国家的交往,便具有了政治学的意义。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我对小说的一种过度阐释,人们情愿把它当成一部好看的爱情小说来读。但我想强调的是,这是贺奕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正是从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贺奕作为一位小说家的理论素质,他在进行小说思维的同时,一直开启着另一个理论思维的头脑。这是贺奕的特点,也是贺奕的长处。
在贺奕的叙述中我们能够捕捉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信息,这就是全球化。这是一个覆盖了全球的WIFFBDzENy22PyG+jfRwWSJZg==I,城市化则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路由器,人们只要愿意,轻易就能接受到它的信息,它以它独有的语言形式,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思维。贺奕较早就获得了全球化的觉悟。人们一定以为这与他的工作环境有关系。我以为还是与他的认真有关系。事实上,他在大学期间就对最新的西方理论充满了兴趣,但他永远是认真的,他并不跟随潮流,这从他对后现代思潮的认识就能看出。后现代是全球化的衍生物,也是全球化的思想原则,看看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那些带有创新意味的元素,几乎都有后现代的影子。贺奕的小说同样吸收了后现代,但难得的是他并不迷信后现代。我读过他的一篇讨论后现代的文章,发现他对后现代的认识是内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学者大佬们远远不及的。他认为,后现代正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逃避历史责任的护身法宝。他说:“借用‘后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确实具有巨大的冲击和瓦解作用,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种作用甚至必不可少;然而,由于缺乏某种终极性的价值体系作为依托,这种作用最终将流于短促狭隘和浅薄。中国后现代论者鼓吹的某些观念,诸如拆除深度,追求瞬间快感,往往包藏着希求与现实中的恶势力达成妥协的潜台词,主张放弃精神维度和历史意识,暗合着他们推委责任和自我宽恕的需要,标榜多元化,也背离了强调反叛和创新的初衷,完全沦为对虚伪和丑恶的认同,对平庸和堕落的骄纵。令人可悲的是,这些观念于他们不仅是文化阐释估评的尺码,更上升为一种与全民的刁滑风气相濡染的人生态度。”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是:“他应抱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立足于社会从事文化建设,既关心现实而又不与现实认同,既超离现实而又不与现实脱节。”我之所以引用贺奕文章中大段的话,是因为想以此证明我对他的认真的判断是有依据的。贺奕的认真在一切方面都表现了出来。他对后现代的认真,使得他即使在后现代之风把人们都吹得陶醉了的时刻,他仍能保持清醒。因此他一方面能够搭乘上后现代的思想快车,另一方面又不失去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健康积极的心态”。这种心态反映在他的小说中。他用小说表达了他是如何“既关心现实而又不与现实认同”的。
贺奕写的小说并不多,甚至已有好多年我都没有读到他的小说了。也许他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整理,既然他是把讲故事当成看世界的方式,那么我相信,当他觉得还没有把世界看到很清楚时,他是不会贸然地把故事讲出来的。
这就该说到贺奕最近的“五道口”系列了。
贺奕最近接连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均冠以“五道口系列小说”的副题。五道口是北京的一个地名,贺奕所工作的大学就在五道口,以身边熟悉的生活作为基本写作资源,这大概是很多作家采用的方式,比如人们都爱引用的福克纳的话,他说他只写他的像邮票大小的故乡。但贺奕并不是因为他生活在五道口,就要写个五道口的系列,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五道口这个地区的特殊价值。五道口毗邻中关村,这一大片地区都属于北京的大学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七八所重要的大学都聚集在这里。显然这里成为了那些期待得到最新最高教育的学子们格外钟情的地方。竟然有人把五道口称为“宇宙中心”。贺奕应该很在意这个称谓,立足于“宇宙中心”,还怕对这个世界看得不真切吗?五道口的特殊性还在于,这里本来是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尽管全球化时代的迅猛扩张,逐渐把这里变成了大学教育和科技开发的核心地带,但它曾经的卑贱身份仍然在这里留下了痕迹,因此在这里更容易触摸到现实生活的肌理,特别是那些人烟密集之处,如廉价的咖啡店、拥挤的出租房,仿佛就是后现代的柔软的褶皱,是菌落最活跃的地方。
贺奕的这两篇小说写的都是柔软褶皱里的故事。《五道口贴吧故事》是说的一个出租房内发生的凶杀案的故事。俄罗斯姑娘柳芭租住在王庄小区,房东是一位独身老人,年轻时曾为援华的苏联专家工作过,因此愿意将房子出租给一位俄罗斯姑娘,老人也非常照顾柳芭,这一天老人上楼去找柳芭,发现柳芭赤身裸体被绑缚在床架上,阴道里倒插着一只啤酒瓶,身下的床单被鲜血浸透,老人赶紧报了案。案子最终告破。凶手是一个外号水哥的年轻人。他在酒吧里认识了柳芭,趁柳芭酒醉与她发生了性关系。这次来找柳芭想与她再续前缘,却遭到拒绝,于是就发生了强暴的凶案。《一个故事的两面》是说的一次修理电脑时发生了交接错误的故事。两个陌生人分别将自己的电脑交到一个修理店修理,一个是美发店里的美发师边俊,一个是设计事务所的女白领晏妮,但两人去修理店取电脑时各自拿错了电脑,他们打开电脑发现了这个错误后,设法联系上了,并约定了交换电脑的方式。没想到因为一次电脑事故让两位陌生人认识了,并有了交往,并影响到各自的情感生活。
从我的复述来看,这两个故事并没有太多新鲜之处,类似的凶杀故事,类似的陌生人巧遇后的情感纠葛故事,在当代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中说得上是比较常见的故事模式。问题是讲故事的方式。贺奕这两篇小说最让我惊讶的便是他的讲故事的方式,他的讲故事的方式大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他转换了故事的主体,《五道口贴吧故事》中的凶杀故事将其叙述主体转换成了网络,《一个故事的两面》中的情感纠葛故事将其主体转换成了电脑。因为叙述主体的转换,故事所揭示的思想内涵也发生了转换。有意思的是,这两篇小说的叙述主体,一则是网络,一则是电脑,都是代表着最新科技的传媒工具,是信息化时代的标志性物件。显然,网络和电脑,是与“五道口”这个宇宙中心最相匹配的叙述主体,它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但贺奕并不刻意渲染其象征性,因为作为叙述主体,它将引导我们通往幽深的曲径。在《五道口贴吧故事》里,凶杀案是通过一份网上的帖子而展开的,一位叫随处是终点的网民在帖子上介绍了王庄小区的凶杀案,引起网民的讨论,网民对案件的猜测,对作案动机的分析,以及对案情的调查,也随着案件侦查的进展而不断使网上的讨论发生分歧。即使案件告破,网上的讨论仍未停止,甚至网民又发现案件的破绽,转而又猜测发帖子的楼主是什么身份……血淋淋的凶杀案在网上变成了一桩社会新闻,在一个城市里每天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光怪陆离的社会新闻,人们对这些社会新闻早已见怪不怪。小说通过一桩凶杀案件所引起的网络讨论,揭示出凶杀如何成为了网络上饶有兴趣的谈资,也揭示出人们被一桩凶杀案刺激下的种种心态,让我们看到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是如何与一个活生生和现实对接的。城市的面目也由此变得更加隐晦。《一个故事的两面》具有更强的形式感,小说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分别以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作为叙述者,左右两个部分组成的矩形平面,仿佛就像两个电脑的屏幕。虽然两个主人公从此相识并有了交往,相互之间有了关心和帮助。但事实上他们彼此并不信任,他们更愿意相信电脑,从电脑上获取对方的信息以窥视对方的内心。小说揭示了人与人的隔膜,这正是城市的顽疾。而人们只能把信任寄托在高科技的电脑上,这也许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危机。我从小说中读到了这样的暗示。
英国批评家克莱夫·贝尔曾经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有意味的形式。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各部分、各素质之间的独特方式的排列、组合起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它主宰着作品,能够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贝尔的这个观点启发了我们,在今天,对小说形式的强调,完全是内容表达上的需要。为什么当下小说的城市叙事总是遭到人们的责难,认为城市叙事不如乡村叙事?也许原因就在形式上。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与城市的审美情感相对应的小说形式。如果说乡村的故事是线性的话,城市的故事就是非线性的。传统的讲故事是线性的叙述,我们的作家基本上是在用传统的线性叙述来讲述城市的故事。这种线性的叙述显然难以充分展示一个非线性的城市时空。贺奕的“五道口系列小说”完全放弃了传统的线性叙述,他在尝试着一种有“城市意味”的形式。我以为,贺奕的尝试是成功的,因为他的形式不是一种脱离内容的纯形式,而是与他看世界的方式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