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
2013-12-29姚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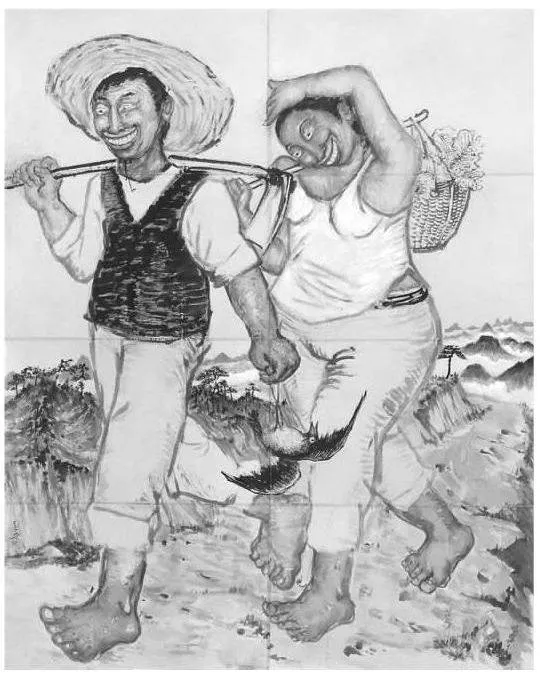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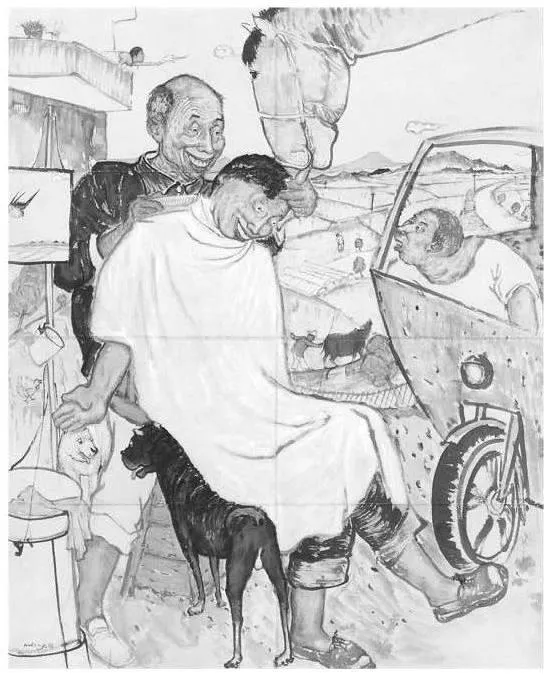
波尔在纽约上城居住了十二年。他居住的小区刚刚绕开著名的“黑人区”哈雷姆,离一片宁静的树林有十分钟的路程。同居十年后,莎莉告诉波尔:她又爱上了,要搬到长岛和女友南希在一起。波尔的寓所凌乱依旧。卧室的墙上依然挂着莎莉五年前拍的黑白照。莎莉的长发撑住了整个镜框。她的脸在镜框内若隐若现,鼻尖挺拔,耳朵上显着两只银色的叶子状耳环,对关注她的人秀着一种挑战的姿态。当莎莉拿到文学博士,当上助理教授后,她的脾气变得愈加猛烈。波尔提出和她一起晨跑。开始的时候他们跑得一样快慢。她的长发惬意地搭在他的肩上,她的耳环和他左耳上的耳环相撞,打出响声。当她的头发掠过他的肩膀,她便超越了他。
“放松,这不是比赛。”他在后面喊。
她停下来,很不满意他声音里的权威性。“我只是在想今天需要做的事情。”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明年要去读博士了。”他突然说。
“为什么?是不是企图证明什么?”她问。
“不是。就是有点烦自己,想干点别的。”
波尔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认识了同学汤姆。汤姆二十五六的年纪,面颊上绣着两朵中部来的男孩才有的红晕。他在东京的一个电脑公司当过两年工程师。
莎莉搬出去的那天是个周五,波尔的心有点软。他没有回去,把办公桌上的白纸一张张的撕碎。他决定在办公室住一夜。
汤姆在酒吧喝完酒后,路过学校去拿他的橘橙色背包。他开门进了办公室,看见波尔坐在灯下,翻着一本画册。他问他是否一切安好?波尔点点头。
“你在读什么?”
“一个墨西哥女人的画,她叫芙烈达·卡罗。也许我不是那么懂女人。她们的内心总比男人更丰富。”波尔的牙床和舌头相撞了,嘴里有一股血腥味。
汤姆问他能不能翻一下他的画册。波尔把书递给汤姆,说:“这本来是莎莉的。今天她要搬出去和她的女友同居了。”
“女友?”他张大了嘴巴,没再合上。
“陪我去喝一杯?”波尔说。
“好,反正我没什么事情。”
在一个爱尔兰酒吧,波尔口齿不清地告诉汤姆,莎莉是英国种,有个愚蠢的父亲和一个任劳任怨的母亲。母亲生了四个孩子,一直是父亲泄愤的工具。母亲在四十五岁那年过世后,父亲一直找不到工作。她和三个姐妹都是领救济金长大的。波尔一直都知道,莎莉从小就有点喜欢女孩子的。波尔相信男女平等。他觉得自己可以帮助莎莉实现她当文学家的梦想。他们曾经过得不错。他说自己不明白一段美丽的关系为什么就此告终?
汤姆听了说:“如果我是你,我不至于这么伤感。至少,抢走她的是个女人。她可以给她你不能给她的东西。”
从此,汤姆成为波尔的好朋友。
不久,莎莉大方地邀请波尔到她们在长岛的公寓玩。南希是个财务师,常在家里上班。公寓里有很多颜色反差极大的画,画中的主角以动物占多数。波尔看到南希给予莎莉的东西:整洁的客厅,窗前的兰花。当莎莉随便说了句什么,南希的头像自动的机器一样摆动着。当莎莉咆哮的时候,南希把目光投向波尔,似乎在问:你是否感觉到我在感觉的东西?
汤姆听完后说:“你该注意其他的女人了。生活总要向前走的。”“是啊。”波尔点点头。“大概是时候了。这次晚间课的班里有个ABC,看着很可爱。”
“什么是ABC?”汤姆问。
“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她叫Lily。二十出头的样子。”
“我在日本上班时曾经有个日本女友,我们同居了一阵。公司发现后就把我开除了。这是为什么我回到美国。其实我喜欢东京。”汤姆说。
“就这样简单?”
“细节是有的,但不那么有趣。她是个简单的女孩子。”汤姆打了个哈欠。
波尔说,“Lily也是个简单的女孩子,头发剪的极短,穿的裤子像男人那么窄。走在曼哈顿的街上,她是很难不被当成‘同志’的。”
学期结束前,波尔接到Lily的电子邮件:“亲爱的波尔,您能不能把我的分数选择从打分改成及格或者不及格?我真的不需要这个分数,修着玩玩的。等学期结束,我会想你的。”她提到她的梦想是当个电影导演。波尔回复说:如果她真的成为电影导演,他会感到自己因为认识她而幸运。
学期结束后,他约她出去看电影,是麦可·戴蒙主演的《心灵捕手》。看完电影,波尔问她的感觉。她说:“不错。戴蒙很有才,没想到他写的剧本都这么厉害。”
他们在59街的地铁站等车,车很久没来,她朝一个正在拉二胡的中国男人脚下的盒子里扔了一块钱。
“这种乐器很好听啊。”波尔说。
“嗯,在一双合适的手里是这样的。”她说。“他拉的曲子叫《江湖水》。很悲伤。”
“打动人的曲子总有点悲伤。昨天我要去献血。”波尔说,“时代不同了。他们让你做各种各样的化验,还问你一堆涉及隐私的问题。”
“这样啊?”她的脸作出动漫女主人公的表情。他们上了地铁。她在一百十几街下去了,向他挥手告别。
教师莎莉开始骑摩托车了。她开车到波尔的家来取自己的东西。
“关于我们的公寓,”波尔犹豫地说:“我是说,我的公寓,是不是该把你的名字拿掉了。”
莎莉用鄙夷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你现在也开始谈钱了,你不是崇尚社会主义的吗?”
“这跟社会主义有关吗?不过,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下次谈吧。”他的灰绿色眼睛里,闪着微笑。
不久,波尔也迷上了摩托车。有一天,他在校门口撞见lily,问她是否愿意坐在自己的摩托车后面,她的耳环晃了好几下,“好的。”
他载着她,从一百二十街开到一百八十街。
“感觉好吗?”
“很好。我想去看看你的公寓,好吗?”她说。他们面对面地坐着。波尔给她煮了一种叫“银针”的茶,往里面洒了一些蓝莓干。
“你戴耳环看着很有气质,以前为什么不戴?”
“这种事情,随心吧。”
“我们要不要挪到沙发上去?”他问。
“你的沙发很硬啊!是从大街上捡的吗?”
“是的。我喜欢回收那些东西,为绿色世界做出贡献。”他用手撩一下她的鼻子。
“什么都可以回收,就是爱情不能。为什么不把墙上的那张照片取下来呢?”
“我还没有准备好。”他说完便吻起她的眼睛来。
“这可是校章上不允许的。”他一边吻一边说。
“你早就不是我的老师了。”
他把她压在身下,问:“你在那里呆得还舒服吗?”
“还好。你不算太重。”她说。
“什么时候你也学会恭维男人的话?”
“她在瞪着我们呢。那个墙上的。她叫什么?”
“莎莉。”
“很不难看。”
“是很不难看。这张照的不好,她的脸不够清楚。我们再来一圈吧。”他把她搬到上面。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大峡谷?”她突然问。
“再说吧,我已经不是那么年轻了。”
暑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一起开车去了大峡谷,那是一辆紫色的车。她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纵横千里,深不可测,广阔无垠。她顺着情绪一奔一跳地下去了。
“悠着点,回程路不容易走。”他的声音在她头上飘。
他们很快走到谷底,看见了卡罗拉多河和一座小吊桥,她发现他的面色苍白。
“我们往上走吧。这里没有我要找的东西。”她的脸上显出一种失望。
她往上窜了几下,往回看:“你这么慢哪?不是跑过好几次马拉松的吗?”
他的脚步放慢,一步三停。她独自向上走。快到顶的时候,她才想起他来。她回首一看,不见他的踪影,“波尔——”她只听见自己的回声。
路过她身边的几个人说,他们看见一个男人躺在一块石头上。她怕了,脚步飞快地下去了。波尔果然躺在一块大石头上喘气,眼皮泛白,像一条被捕上岸的鱼。
“你还好吗?”
“觉得胸口闷。”
“你有心脏病吗?”
“没有。”
“我扶你上去好吗?”
他说:“等等吧,实在不行,可以叫直升机救。”
“我陪你。”她把没有喝完的矿泉水洒在他的脸上。他慢慢坐起来,呼了一口气,一步三停,面色苍白。她在他的后面,胸口填满一种神圣。
“你喜欢跟我在一起吗?”晚餐前,他在旅馆躺了一会儿,洗澡,换上干净的白衬衣。
“我有点喜欢你的样子,眼睛里有鱼的悲哀,手臂动起来有鸟的活力。”
他哭笑不得。
回纽约后,他跟汤姆说起他在大峡谷的经历。汤姆建议他看了医生。波尔做了心脏张力试验。在踩踏板的时候,他感到深度的累。他在一个船形的仪器里睡了个下午。心脏张力试验显示一切正常。他告诉了Lily。她回信说,她最近功课忙,等有时间再找他。
波尔继续骑着摩托车去长岛找莎莉和南希聊天。莎莉说教书是浪费她的智力。她开始写女性小说,要一鸣惊人。
初春,Lily在《纽约时报》上看见波尔的一张照片,头发蓬松,手里举着一个被电脑控制的手。他的目标是让那只手达到名医做手术般的精确。他脸上的线条温柔无比。她便约他到哥大一个匈牙利风格的糕饼店吃夜宵。
她问他最近好吗?
他说不好,刚刚有过一次焦虑性休克。
“为什么焦虑?”
“大概是毕业临近了吧?”他回答。
她说自己也想早点毕业,然后去大陆给一个导演当助理。
“你会离开很久吗?”他问。
“几年吧!”
“够久的。这样也好。我们来往太多不好。我也想找一个真正的女友了。生活总是向前走的。”
“你说的对。你原来是一只鸟,碰到她,就成了一条鱼,因为她是一个池子。”
“那你是什么?”
“一根银针。”
波尔毕业了,想去西雅图工作。但他受到一个老朋友的邀请,专门为人工心脏的安装调控写程序。他留了下来,几年后升了主管。这时,他的朋友欲把公司卖掉,做其他的生意。他独资把公司买下。
Lily从大陆回纽约,拍了一个关于大陆女同性恋的小电影,口碑不错,但没有赚到钱。Lily邀请波尔参加了宣传活动。在苏荷区一个餐厅的院子里,他恭贺她。她对自己的前程并不看好。“艺术家是要养着的,我又不要被养。”
他看了她一眼,问:“那以后我们算什么?”
“朋友。”她说。
春末的夜晚,他和莎莉在东村吃饭。喝下几杯啤酒后,莎莉说自己同意放弃公寓拥有权,但因为公寓涨价了,她向他要了四万,他同意了,举起酒杯:“为了我们有过的快乐。”
夏天,Lily穿着极短的裙子出现在波尔的住宅附近。她的头发变长了,瀑布般的浪漫。她依旧记得公寓的门号,却忘了大街的名字。她在那里转悠了很久,找不到他那颀长的身影。她想导演的一个惊喜效果失败了,有点沮丧。她连着给他发了几个电子邮件,没有收到回复。两周后,她接到一个老妇人的电话,说话带着纽约口音。她问她是不是Lily小姐,是不是认识她的儿子波尔?
“认识的,可是我最近一直联络不上他。”
“他去世了。几天前,在中央公园跑步的时候,他大概自己都不知道,他所有的动脉都被胆固醇阻塞了。我在他的笔记本上看到你的电话,我想请他所有的朋友到我家,参加他的追思会。”
“我一定来的。”她的鼻子里流出浑浊的分泌物。
老妇人的家在布朗士的富人区。别墅不大,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Lily在那里看见了莎莉和南希,还有汤姆。当汤姆看见Lily,忍不住抱住了她。“你很难过,对吗?”他问。“很难过。我不知道我跟他到底干了什么?我一直在做一个梦。”
追思会上,莎莉谈了她和波尔的十年交往,声调冷静,她说他是她认识的最温和的男人。莎莉说:他一直想离开纽约,但一直没飞出去。Lily一直在看天花板顶上的那个白色灯罩,她觉得被浓缩了的波尔就躲在那里,窃窃发笑。
半年后,Lilly到了法国,她在里昂第二大学读文学艺术的硕士。一月,汤姆来到里昂。他背着一个竖琴盒一样长的黑色行李包,脸上还是挂着两块红晕。法国的天空是灰蒙蒙的,偶尔有夹着沙的雪粒偷袭他的脸。他告诉她,自己在共和国街上订了一家旅馆。
她带他在街上随便走。汤姆说:“我开了自己的广告公司,用编程设计动漫广告。”
“你们都很有商业头脑啊。”她看着百代电影院顶上的那只大公鸡说。
“你们?你还没忘记波尔?”他欣赏着那只姿态高昂的公鸡。
“有些记忆是永恒的!”
“有点意思。你不是那么简单,是吗?”
“你以为我很简单吗?”
“是波尔说的。”汤姆回答。
“他什么时候说的?”她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大概是你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吧。晚上我请你吃饭,地方你选。”
“那选麦当劳吧?”锁骨在她瘦骨嶙嶙的胸前显得很突兀。
“法国竟然有这么多的麦当劳?”汤姆的蓝眼睛转了几圈。
“这是新一代的法国人,我们先去老里昂的爱尔兰酒吧。”
酒吧里烟味浓烈,站在汤姆身边的一个阿尔及利亚男人,用粗短的食指和拇指夹着烟,小口小口地抽,像是滋味无穷。
“你喜欢Guinness吗?”汤姆问。
“喜欢那层泡沫的味道,但泡沫下面的不好喝,我的身体里大概没有那个我记不住名字的酒精消化酶。”
“那种消化能力好像和亚裔的遗传背景有关。你从来都不喝完吗?”汤姆问。
“我舔掉泡沫,然后倒掉。”她说。
“你虽然是在美国出生的,但基因还是中国的。”汤姆说。
“我不是出生在美国的,我妈妈是福州人。我三岁那年,父亲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死了,后来,家里常有男人进进出出的。”她说。
“后来呢?”
“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到我们家乡探亲的台湾老人,到了美国。那人有养老金,给她买了婚戒,上面有个三克拉的金刚钻,六岁那年,她把我接到美国读小学。那男人已经做不动工了,家里的钱不够,她就出去做。然后那个老头非礼了我。后来她跟他离婚了,自己去了加州赌城。”她的鼻子开始呼呼作响。
“听上去很不幸,你哭了?”汤姆看了她一眼。
“没有,她把我托给一对朋友夫妇。我上初中时,她常来信说,你要学好,要学会一门求生的本事。”
“那你没有试图联络她?”汤姆问。
“试过。她在赌场发牌,跟很多的男人拿过钱,然后把钱寄给我。不太想见我。我高中上了寄宿学校,那时候就开始喜欢电影。”
“你为什么对波尔说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呢?”汤姆说。
“他突然问了我。谎言像烟雾从脑子里冒了出来,波尔把它吸了进去。就是那样。”
“我们都会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隐瞒一些私有的经验,你喜欢他什么呢?”他问。
“也许是他的不确定感,他像一个在机场等飞机的人,总在起始地和目的地之间。”
汤姆说:“我对他也有这种感受,只是不能像你那样精确地表达出来。”
“我们去那个叫印度支那的饭馆吃饭吧?他们有好吃的越南春卷。”
在餐馆,汤姆问:“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在这里念完书,回美国找工作。我觉得对不起我妈,她一直想让我读会计,可我看到数字就头痛,常常逃学。后来我自己当模特赚钱,她不开心,她几年前出了车祸,被送进疗养中心,每天靠鼻饲管喂食,我很少去看她。”
“为什么很少去?”
“她根本认不出我,那里的空气很闷,我每次一进去就想离开了。”她说。
“纽约的空气本来也不怎么样,我们去外面偷点空气吧?”他说。
在去旅馆的路上,他们看见一个水池和里面的喷泉。她说:“奇怪,现在晚上也喷水了。”
他脱下靴子,扔掉袜子,跳进水池里。
“你不怕冷吗?会感冒的!”她对他喊。
“听说得感冒后会增加抵抗力。”
“那我也进来了。”
他把她拎起来,在空中转了几圈。她的耳环拨弄着空气,耳边时而有响声。
到了旅馆,他们都醉了,挤在一张窄窄的床上,两个脖子靠在一个像法国棍子面包的枕头上。
“你认真地抱我一会儿。”
他把她放到手里,有点怕她的身体从他的手里滑出去。“我就在你手上睡吧!”她的身体蜷缩起来。
他抱着她,目睹她入睡,他的手持续地发抖,不愿打断她的鼾声。
早晨,阳光射进了百叶窗,他们尴尬地对视着,她想不起昨晚的事情。但他身体里的部件,仍然在她的眼睛里摇晃着。
“你和波尔有过高潮吗?”他突然问。
“高潮是个蠢东西,跟不同的人做,感觉是不同的。你问这个有点晚熟。”她说。
汤姆说,“我们一起吃个早饭吧。”
当她把一只绿苹果咬得只剩核时,她起身说:“我要走了。”
他说:“随时到纽约来找我。”
“我会的。”她消失了。
两年后,她出现在他的公司里,在苏荷区。“给我一个工作吧?我把妈妈从加州的养老院移到纽约来了。”
他蓄着一撮嫩嫩的胡子,看着她:“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吧。”从公车上下来,要走三条马路才到养老院门口。她母亲住的是624号。门号旁边标着一个“梅”字。
汤姆在房间里看见一个容貌清秀的妇女,面无表情。“妈!”她的声音像小女孩一般清澈,女人的眼神没有变化,Lily不停地揉着她的右手。
“她在感觉着你。”他说。
“你确信?我觉得,我对她一直都可有可无,如果没有我,也许她不会那么惨。”她说。
“她能听见你在说什么,我觉得。”汤姆的眼睛盯着老女人看。
他们坐电梯到了楼下,电梯口贴着一张餐巾纸,上面画着一个鸡蛋,鸡蛋露出一张笑脸。
谈妥了工资后,Lily为他的公司设计广告,用软件做出生动的彩色小龙在洗衣机的盖子上跳来跳去。
“你对颜色的敏感没有体现出来。”他走过她身边的时候,轻轻地说。
“不要告诉我做什么?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连着设计了五个动态广告,他采纳了两个,顺利地把它们卖了出去。
周六的晚上,他们去东村的Thompson街吃寿司,他们的身体后面坐着两个女同性恋,身体粗壮的那个说:“当我不想有性高潮的时候,她逼着我达到高潮,那就是强奸。”
Lily回头看了她们一眼。
“你搬进来一起吧。”他说。“你很吸引我。”
“你是说,我们可以继续假装吸引对方?”她扔过去一个嘲讽的眼神。
“你从来没有跟男人同居吗?”
“没有。”
“那么我们就给彼此一个机会?”
在她搬进去的那天,汤姆说:“厨房我来打扫,你做饭,这样还算公平吧?”
她从网上下载了很多又东又西的菜谱,吞拿鱼配芦笋是她常做的菜,接下来他们接到很多的订单,他不再打扫厨房,他们的洗手间溢满硫化氢分子的气味。
周日,她洗完澡,穿上一件黑色的衬衣和溜细的牛仔裤。她想去现代艺术馆看看。汤姆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用一条破领带拽住她的脖子。“留下,让我们装出一点暧昧。”
“今天玩什么?”她问。
“游戏是这样的。”他到厨房去了,从冰箱里找出最后一个鸡蛋,当着她的面,他把鸡蛋打碎,把蛋黄含在嘴里,把她扔到床上,他把自己装入她的身体,把蛋黄轻轻吐到她的嘴巴里,她的喉咙被蛋黄封住,口水流了出来。他猛烈地撞击她的敏感点,她把蛋黄吐到他的嘴里,蛋黄散了一半。他撑不住地射了,蛋黄汁从他的嘴里淌到地板上。
厨房里,在做西红柿汤的时候,她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里长了个东西。一个月后,她从一个叫“爱”的药店买了测试怀孕的试剂,结果呈阳性。
“亲爱的,是我该走的日子了,我接到了一个活,是帮一个有名的编剧扩写一个剧本。我妒忌她的才华,但甘愿为她服务。”当他们躺在榻榻米上的时候,她闭着眼睛说。
“那种生活是没有任何保障的DzRo6zCsfbcd0pQH3WD4R4f10xfzWmSXaNtC9nY8ZPM=。”汤姆说。
“我不要保障,我想挣脱。我总觉得被一只手拷锁住了,那只手,是我妈嫁的那个老头的手,那天她上班去了,他把我绑了起来,用一壶凉水从我的头上冲下来,逼着我撒尿,我尿不出来,他把我的一只手上了手铐,用我的另一只手摸他的全身,我挣扎,他一拳把我打到地上,我尿了。”
“你为什么不去告他?”他问。
“我怕,也不要我妈知道。”
“那你就永远活在过去?那时你不过是个孩子。”
“不知道,我突然很想要孩子,你说,女人生孩子是为了欲念,还是为了爱?”
“提这些事情很扫兴,我对结婚或生子的事情早就产生了怀疑,世界末日都要到了,我们只是在狂欢!”汤姆神情严肃,在黄昏的光里,显得苍老。
清晨,她提着一个红色小箱子出去了,她在纽约上城租了一间小公寓,她的腹部微微隆起。
小龙年的年尾,她躺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产科医院里,男医生熟练地把她的肚皮剖开,散开了的内脏扭曲着,形状朦胧,像莫奈画的水莲,她尖叫着,肚子里的水汹涌起来,被粘液裹着的婴儿鱼一般跃了出来,哇地哭了。
Lily穿着宽腿的牛仔裤,抱着婴儿在街上走,上身裹着大红的绸缎披肩,当走进苏荷区,她忽然明白,她不是鱼,也不是鸟,她是一棵早熟的树,尚未开花,便结了果儿。
她紧紧地抱着她的果儿,走过报摊,走过咖啡店,走过法院,走过一家杂货店。在店门前的阴沟里,她认出一付被遗弃的黑手铐,上面标着2013。
雪花在她的头上飘,让她觉得置身于梦境,她通过那副手铐,看穿了自己,忘了男人。
她终于明白,她就是她,一个中国人的女儿!手中的孩子携带着她一半的基因。她们的基因会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