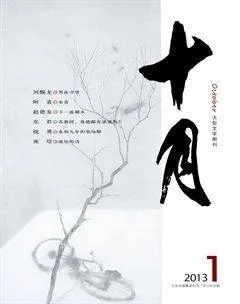苏教授,我能跟你谈谈吗?
2013-12-29东君
一
现在,苏教授不得不惊异于三年前做过的一个梦:那晚,他竟梦见自己一直在跨门槛,跨到七十四道门槛时,他一头栽倒在地。有人解梦,说七十四道门槛就代表七十四岁。也就是说,七十四岁是苏教授的关煞。苏教授听了,一笑置之。懵里懵懂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从未感觉那个梦有什么异样,也不加措意。苏教授以为,死亡是迟早要来的——他不知道自己将会在哪一天去世,但他知道自己每过一天就离死亡更近一步。现在,他刚好过了七十四岁生日,那个梦竟变成了现实。一脚跨到了死亡的边缘,反倒让人有了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
昨天上午九点钟的阳光是很难得的(之前都是可憎的阴雨天),苏教授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死亡的阴影。有人经过,跟苏教授打了个招呼,说一声“晒太阳”啊。苏教授跟一群老人坐在墙角晒太阳却像是做了亏心事似的,讷讷地回了一句。但苏教授很快就变得坦然了。他甚至觉得野人献曝的做法一点都不蠢。早春的阳光确乎是样好东西。老人们都像驱光动物似的,随着阳光一点点移动。人都是这样,苏教授不无自嘲地想,年轻时喜欢跟自己所爱的人坐在月光下聊天,到了晚年,就喜欢跟人在太阳底下扎堆了。好的阳光就仿佛来自上天的祝福。
那天上午,他还记得,女儿塞给他一个热水袋,他却不要。他走到墙角下,抱起那只正在晒太阳的虎皮猫,就像是抱着一个暖手的火钵。猫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只流浪猫,还是自家那只死去多年的猫?为什么抱它的时候有一种如遇故人的感觉?苏教授早年爱养狗,晚年爱养猫。其实不是爱猫,而是爱猫身上那种宁静的气息。这只毛绒绒的猫安静得让他忘掉了它是一只猫。
有个年岁相仿的老人挪过来,跟他聊开了。老人问,你是教书的?苏教授微笑着说,我是个杀猪的。老人说,一点也看不出你是个杀猪的。苏教授说,我上辈子是杀猪的。老人笑了起来,跟他说起小时候村上杀年猪的事。苏教授感到身上的血气一点点鼓荡起来。当他看到眼前的太阳突然落到墙外时,他知道,自己已经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然后他就感到黑夜漫过了自己的眼睛。
苏教授不能动弹的时候,依然能听得清人们惊叫的声音、猫尖叫一声跑开的声音、慌乱的脚步声以及呼啸而至的救护车的鸣笛声,然后就是医生说话的声音、手术刀碰撞的声音。在寂静中,他甚至听到了血液流动的声音。
过了许久,他听到女儿在一旁轻声抽泣。女儿问医生,父亲是否还有挽回生命的迹象?医生说,他身上的机器差不多都坏掉了,他们只能让他暂时苏醒过来,但不能保证他还能活下去。像他这种状况,医生断言,最多活不过三个月。这些对话,苏教授都听在耳里,但他不能发声。手也不能动。哪怕是一根手指。身体像是被一块冰冻住了。
大约是过了一个夜晚,苏教授就“醒”了过来:先是睁开眼睛,其次是张开干裂的嘴唇,然后是连手指和脚趾都能动一下了。最初映入眼帘的是女儿的面庞。仔细端详,脸上泪痕未干。苏教授伸出手来,在空中寻找着女儿的手。女儿迅速握住他的手,放在自己的下巴。她的下巴还在不停地抖动。
女儿说,昨天早上,她一觉醒来,总感觉耳朵里有什么细微的杂音。于是转到厨房、洗手间仔细检查了一遍,没发现有什么异样。回到床上,躺了一会儿,还是不放心,又爬起来,东看看,西看看。她总觉得有什么事好像就要发生了。结果,是父亲这边出事了。
这些年来,苏教授的身体变得益发孱弱。一旦天气发生剧烈变化,就会有过敏的可能性。这种病,医生说,叫天气过敏症。因此,苏教授查看天气预报时,总是特别关注过敏气象指数。阴雨天一来,他的浑身关节就会出现酸痛;若是刮点风,飘些花粉,就会引发老慢支。总之,随着年岁变大,他对天气变化的适应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差。就像他置身这个时代,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常常不知道如何去适应。有很多新鲜物事,身边的人都趋之若鹜,苏教授却怎么也看不惯。有时心情不好,他还会化个名,写篇文章骂几句,算是解气。学生们深知他的古怪脾气,都把他当孩子一样哄着。人老无好相,何况是病了。
苏教授说,我生病的事,你不要跟外人说起。
可是,女儿说,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你住院了。等你精神稍好一些,他们就会过来探望。
苏教授忽然沉下脸来说,我住在医院里难得清静几天,你就不必让他们过来了。等我死了,就让他们跑到殡仪馆跟我作遗体告别好了。
苏教授见女儿泪水盈眶,也就不再往下说,只是别过头,闭目休息。窗外雨声如故。每逢雨天,他总是变得特别脆弱。仿佛这种低落的情绪跟他身上的关节炎一样也是坏天气带来的。
午睡初醒。人还是有点恍惚。打开灯,一片白光驱散了梦境里的阴影。老钱和老姚都来过了?他看见女儿正坐在床头削苹果,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说的是哪位老钱和老姚?女儿问,是不是钱逸君和姚鸿年两位教授?苏教授怅然地点了点头。女儿说,钱教授和姚教授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你还主持过他们的追悼会呢。苏教授拍拍了脑袋说,我一定是睡糊涂了,把梦话也带了出来。不过,我在迷迷糊糊中好像还听到有人说我家乡话。听得很分明,一点儿都不像是在梦中。女儿说,你一定是想念老家了,所以就在梦中听到了乡音,就像你太怀念老朋友了,醒来后就问我钱教授和姚教授来过没有。苏教授突然坐起来说,没错,我是听到有人说我家乡话。你去隔壁看一下,也许住着我的一位老乡呢。说完这话,他又拍了拍自己的前额说,我又说胡话了,我的老家离这里实在太远太远了,怎么可能会在这地方碰到老乡?我不是睡糊涂了,而是老糊涂了。
二
一只山羊爬上老甘的饭桌。他就知道,这是他死去多年的儿子。山羊的眼睛分明就是儿子的眼睛,老甘从它的瞳仁里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儿子。老甘抚摸着山羊的耳朵说,儿子你回来了,一定是饿坏了吧,来来,桌子上有什么,你就尽管吃吧。但山羊在饭桌上静默了一会儿,就拉了一坨屎,然后跳下来,扬长而去。老甘追了出去,却被门槛绊了一跤,一惊,醒来,发现自己竞躺在重症室门口。一名护士把他扶起来说,刚才你还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的,怎么突然间喊一声就往门外跑了?老甘听不懂护士的普通话,就对躺在病床上的小孙子说,她刚才跟我说什么?小孙子把护士的话重复了一遍。老甘抹着惺忪的眼睛说,我刚才在追我的儿子。小孙子又把老甘的话转述给护士听,护士惊讶地问,你不是说儿子坐了牢?他什么时候来过?小孙子又把护士的话转述给老甘听,老甘说,坐牢的是我大儿子,也就是孩子他爹,我刚才追赶的是我小儿子。护士听完转述说,我刚才就在这儿,没看见谁来过。你不信问问你的小孙子。这一回,小孙子没有转述护士的话,就直接跟老甘说,是的,我刚才也醒着,没看见谁来过呀。老甘说,我小儿子跟他这般大的时候就死了,他是不可能来的。我刚才梦见他变成了一只山羊,那双眼睛泪汪汪的,分明就是他小时候被人欺负后的可除相。小孙子知道爷爷又开始说胡话了,也就没有把这话说给护士听。护士正忙着要给其他病人做例行检查,大约也没兴致听他说话。
老甘的小儿子是被村上一个小地痞用石头砸死的。那时正是春耕时节,老甘的小儿子赶着几只山羊来到山坡上吃草,忽然看见村上的唐三站在山坡上东张西望,似乎在急着找什么。老甘的小儿子问他,你丢了什么东西?唐三说,我丢了一头驴。你看见我的驴了吗?老甘的小儿子摇了摇头。唐三看着那几只低头吃草的山羊说,你的羊是我的。老甘的儿子说,你明明是丢了驴,怎么又赖上我的羊?唐三说,没错,我之前说我丢的是驴,但我现在丢的是羊。我说这几只羊是我丢的,就是我丢的。二话没说,他就去赶那几只山羊。老甘的儿子问,你要把我的山羊赶到哪里去?唐三说,我要把它们赶到畜牧场卖了。老甘的儿子上前去阻拦,唐三就把他使劲推开。老甘的儿子毕竟是小孩,没法跟他拼力气。唐三一脚踹中他的肚子,他就瘫软在地上了。唐三想走,老甘的儿子抱住他的腿,死死不放。唐三甩不开,就从地上拿起一块石头砸了下去。老甘的儿子哼了一声,就不动了。唐三探了探他的鼻息,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就把他抱起来,抛进溪流里。傍晚时分,有人在一个清寂的小水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老甘把儿子抱回家,放在门板上。他没有哭,只是不停地跟他说话。谁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老甘出来说,杀我儿子的人现在正赶着三只羊去畜牧场。有人去畜牧场一打听,果然,有人把三只羊卖给了屠宰场。那人就是凶手唐三。老甘的大儿子抄起一把家伙去找唐三,但唐三得了钱早已逃往异地。后来,唐三就再也没有回来。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老甘的大儿子从未放弃寻找凶手的决心,他去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后来据说是被什么高人点化,不想寻仇了,就在这座被称为首善之区的城市居住下来,以打工做力气活为生。再后来,老甘的大儿子又娶妻生子,生活也就慢慢地有了起色。大儿子一直想把父亲接到城里来,但老甘说,他上头还有一个老母,不能远行(老甘的母亲说,她已经活得太久太久了,走动的时候都能听到骨头摇动的声音)。谁也没料到,老甘这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出门远行跑到大城市来,竟是为了照顾生病的孙子。
孙子住院,病得不轻;儿子偏偏又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事,连个音讯都没有;儿媳妇已经偷偷怀上了二胎,为了躲避孕检只好回乡下娘家去了。所有的重任都落到了老甘身上。但老甘只能在医院里陪伴孙子,无暇他顾。整整一个月来,老甘最大的快乐就是教会孙子说一口地道的家乡话。老甘所操的方言是小语种中的小语种,出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没人听得懂了。老甘出门五十里,那些人听他说话就有些费劲了;出门百里,会话时就得附带手势;到了这座城市,老甘才知道,从老家带过来的方言差不多要作废了。还好,孙子没有忘掉乡音,他原本只是偶尔用生硬的方言土语跟父亲聊上几句,经老甘一调教,很快就能活学活用了。孙子反过来教老甘说普通话时,老甘说,我老了,舌头硬了,怎么也转不过来了。但祖孙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孙子跟他讲述城里发生的事,老甘跟他讲述乡村生活。孙子觉着,乡下的各种物色听起来十分新鲜、有趣,禁不住要念想了。他跟爷爷拉了勾,说是病好了之后一定要去老家走一趟。
三
苏教授寂寞的时候就会用家乡话跟自己说话。他记得父亲曾跟他说过,你出门在外的时候要记得把家乡话带在身边,如果你忘掉它,就等于是忘掉回家的路。苏教授自说自话时,就像是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女儿进来,听到苏教授嘴里念念有词,就问,爸,你跟谁说话来着?
苏教授答,跟我自己。
女儿说,我刚才经过隔壁那间病房,听到有人说话的口音跟你还真的很像呢。
苏教授说,你一直以为我在说梦话,连我自己都怀疑那是一种幻觉。现在好了,你可以把隔壁那人请过来聊一下,或许真的是老乡呢。
女儿很快就把那人带了过来。站在她身后的是一位老人,身形瘦小,面容枯槁,衣裳旧兮兮的,头发灰蓬蓬的,两眼无光,只剩下两点寒灰般的东西,一切看起来都像是燃烧过后的模样。
苏教授试着用家乡话向他问候一声。老人十分惊讶地看着苏教授问,你是——
我们是老乡,苏教授说,你只说出两个字,我就知道你是哪里人了。
老人的目光在苏教授的脸上停留了许久,突然喊出了三个字:苏教授。
苏教授愣了一下,扶了扶镜框,仔细端详那人的面容,迟疑地问,你是——
老人说,我是老甘呀,你忘了吗?小时候我们还一起掏过鸟窝、摸过鱼哩。不过,那时候人家是管我叫小甘的。
在苏教授听来,老甘的话音里有着亲切的味道。他看着眼前的老甘,脑子里蓦然浮现的,却是老甘的祖父。老甘老了,竟然跟祖父长得很像。回想往事,苏教授也是百感交集,他让老甘坐到身边来,向他打听一些故乡的人与事。老甘一一相告,便像说起了天宝遗事。在那边,苏教授还有几位亲戚和父执(大都是父亲那所学校里的同事),“文革”时断了联系,后来也就没再来往。现在打听故人消息,倒是有点像异地问路。苏教授问老甘,村里跟外界通车了没有?老甘摇摇头说,只有火车从我们村外经过,但从来没有停留过。我们出远门,还得翻过几座山。
沉默少顷,苏教授说,山里面缺医少药的,你若是生了病如何是好?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还好说,就怕得了什么急症,送医院不及时,兴许就会白白搭上一条命。
老甘说,我这辈子从来没生过什么狗马病。有一回,我感冒了,身子发软,鼻涕直流,于是拎了把椅子走到屋外晒太阳。过了一阵子,我去田头撒了一泡尿,感冒就好了。
苏教授说,也许你身上有过什么病,只是没发现而已。有些病,你不去理会它,它就会很没趣地走开。
老甘说,小时候,我母亲常常跟我说,我们穷人生不起病,千万别把自己的身体娇生惯养了。有时候即便病了,也要多笑。笑跟药物一样能治病,是世界上最便宜、最养心的药物了。
苏教授说,我还记得你母亲的样子,她老人家现在还健在吗?
老甘说,托你的福,她老人家好像越活越有劲头了。有人问她年纪,她就是咬着舌头不回答,说是怕自己的岁数报出来,让阎王听见了,就会派牛头马面来拘她。可是,前段时间她听村上的人说我孙子生病了,就开始不停地诅咒自己,还说我的小儿子之所以夭折,也是因为她阳寿太长的缘故。
苏教授问,你孙子生了什么病?
老甘说,脑子里生了一块肿瘤,我都叫不出名目来。总之是一种怪病,在小孩子当中是极少见的。
苏教授问,很严重吗?
老甘叹息一声说,医生说的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我说的话医生也听不懂。我只是听孙子说,他的病很快就会好了。等病好了,他就可以去学堂念书了。那天我还跟孙子说起你,我让他好好念书,将来也当个大学教授。说到这里,老甘竖起大拇指说,苏教授,你尽管在外头生活,但你的名声在我们家乡可是很大的。问问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他们可以不知道现任的县长是谁,但都知道苏教授是谁。
苏教授少小离家,跟随父母迁居大城市,后来又在这座北方的大城市扎下根来,长达六十年间,他都未曾回过老家,与家乡父老也谈不上什么乡谊,但他们都还惦念着从偏僻山村里走出来、名声在外的苏教授——从老甘的话里,他可以掂量出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这比学界的任何一种嘉奖都来得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时刻,他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故乡,还有像老甘这样的故人,心头便涌起了一股暖流,眼眶一热,差点要掉出一把老泪来。
苏教授说,我很想回老家看看,可我已经走不动了。
老甘说,等你病好了,我就陪你一道回老家走一趟吧。
苏教授说,我已经回不去了,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可能的话,我要把骨灰的二分之一撒在老家那座山上。
老甘听了这话,缓慢地转过身去。过了片刻,他又转过头来,眼泡益发显得红肿。
苏教授看着外面铅灰色的天空说,老甘,我真羡慕你,你明天醒来还能看到太阳升起。
老甘说,我看过天气预报,明天仍然没有太阳。
苏教授微微一笑说,你不识字,怎么会看天气预报?
老甘说,我孙子告诉我,看到天气预报上画个太阳就是晴天,画些乌云和雨点就是阴雨天。
苏教授指了指窗外说,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一声。可是,我怕是等不了太阳出来的那一天了。
四
早晨醒来,拉开窗帘一角,天色似有转晴的迹象。这半个月来,太阳只是十分吝啬地露过一次面,其余时间都是阴雨不断,很容易让病人脸上出现阴郁的神色。苏教授也不例外(他总是抱怨这鬼天气让他的心情都坏透了)。刚吃过早餐,天色旋即又暗了下来。苏教授感觉自己吃的不是早餐,而是晚餐。他对女儿说,他这一顿饭吃完了,怕是吃不到下一顿饭了。
老甘在不在隔壁?苏教授问女儿。女儿答,听护士说,他每天这个时辰就准时出去了。苏教授说,躺着无聊,就想找老甘聊聊天。他每天这个时辰出去做什么?唔,他做什么又关我什么事?这些话,他是用家乡话说的,在女儿听来,他是在自言自语。
阴雨天里,苏教授的腰背又开始胀痛。护士分析说,这是在床上躺卧太久老毛病复发的缘故,从临床经验来看,这还不是病变所带来的那种疼痛。苏教授问,病变会带来怎样的疼痛?护士一边换盐水,一边略显谨慎地回答,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医生。护士挂好了盐水,就轻轻掩上门走了。苏教授斜靠在床上,细数了一下,每天大约要打六瓶大小不一的吊针(还好,护士已经在他的手臂上放置了留置针,手臂也不至于被针扎得跟马蜂窝似的)。望着吊瓶里缓缓注入皮管的药液,他就想起窗外没完没了的春雨。这情形,苏教授微笑着对女儿说,似乎有点像宋词里写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没过多久,医生就过来做例行检查,苏教授顺便向他打听一下老甘那个孙子的病况。医生说,他们也是首次在小孩子身上发现一种多发于中老年人的恶性肿瘤,一线治疗已经不见成效,接下来,医院方面已经征得病人家属的同意,给他服用一种全球第一时间获准上市的新药。苏教授问,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点把死马当活马医的意思?医生说,他们这也是为病人争取最后一线生机。况且,医院方面还承担了病人所有的医药费。
不过,医生看着苏教授说,你跟他不同,我们对你采取的是一种保守治疗。
苏教授想了想又问,我想知道,像我这种病越到后面疼痛是否会变得越厉害?
医生说,也许会,也许不会。这种病在最后时刻出现的状况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会出现发热,有些人会出现昏迷,也有些人会出现如你所担忧的剧烈疼痛。总之,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医生十分坦率地告诉他,很多人临死的时候脑中会分泌出一种类似于吗啡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医学上称为内啡肽,它会缓释一个人对死之将至的恐惧,从而使人的内心与面目都变得很平静。
我对死亡并不恐惧,苏教授微笑着说,至少我现在并没有恐惧。我所害怕的是自己最后会被疼痛折磨致死,到了那个时候,医生,你们会怎么做?
医生说,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尽可能控制病痛的情况下,用最好的药物延长病人的生命。
不,苏教授说,你用药物延长我的生命,也就是延长我的痛苦。与其让我痛苦地活着,不如安静地死去。
医生说,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教授,如果一个论文还没通过的博士生让你开绿灯,你恐怕也不会答应的。
苏教授问,医生难道不允许病人选择痛快的死法?
你说的是安乐死吗?医生像背书似的说,关于安乐死,正确的叫法应该是自愿安乐死亡。所谓自愿,就是病人可做自主选择;所谓安乐死,说白了就是求得一种好的死法。
苏教授听了医生的话,忽然间情不自禁地用家乡话说道,这末后的一节过得从容,也是前辈子修来的福气,但疼痛要是真的来了,想要故作淡定也难。
你说话的口音跟隔壁那个老人很像,医生说,我不明白你刚才在说什么。
苏教授意识到自己的心思又飘到了很远的地方,便收回目光说,医生,如果那一刻真的来临,我就得用得上吗啡了。
医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然后退出病房。
这一晚,苏教授怎么也睡不着。他已经意识到,有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要对他下手了。这东西,也就是苏教授所说的“病痛”。因为他亲眼见过钱逸君教授被病痛折磨致死的情景。深夜,苏教授坐起来,摁亮床头灯,望着窗外,但窗外除了浓重的夜色,似乎也没什么可看。玻璃上映现出一片黝亮的灯光和一个模糊的面影。他静静地注视着,仿佛要看穿黑暗,一直看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但他看到的,只是一片荒芜。
五
晨起,胃纳不佳,苏教授仅吃一点小米粥。女儿给他敲了一会儿背,就拿起梳子帮他梳头。苏教授的头发已经全白了,长长地披下来,十分轻柔地堆在肩头,微微有些卷起。女儿在慢慢梳理着头发,苏教授在静静地梳理着往事。病房静极。窗帘上簇拥着毛茸茸的白光,似有阳光照射进来。苏教授眼前一亮说,好像是出太阳了。女儿起身拉开窗帘,一片浩大的阳光便涌进了病房。苏教授微微闭上眼睛,伸出双手,近乎贪婪地享受着每一寸阳光。女儿说,院子外面的梅花都已经开了,有红梅,也有白梅,让人真正感觉到春的气息了。苏教授微微地点着头。女儿说,趁这天气好,我用轮椅推你去院子里转转,也好欣赏一下这迟开的梅花吧。苏教授挥了挥手说,一头白发,满脸憔悴,很难应这春景了,不如不看。
正说话间,那扇虚掩着的门推开了一点。老甘探进头来,向父女二人问好。苏教授向他招了招手说,进来坐坐吧。老甘进来了,但没有坐下,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苏教授说,老甘,原来你是识字的。老甘面露愧色地说,我是个文盲,认识的字还不满十个手指呢。苏教授问,那你手头拿的是什么书?老甘说,我刚刚去教堂做了祷告回来,赵牧师顺便送了我一本《圣经》。苏教授“哦”了一声说,原来你是信奉基督教的。说起宗教信仰,老甘便问苏教授信奉的是什么教。苏教授说,我母亲是信奉基督教的,但我父亲是信奉佛教的,我在他们中间,哪边都没有信靠,结果就落进水里面了。现在临时抱佛脚,佛会拿脚丫子踢我;给耶稣洗脚,耶稣也会嫌弃我。老甘说,话也不能这样说,你虽然没有信靠,但你有知识,我们乡里那所学校的大门口就写着:知识就是力量。你有知识,所以有力量。我呢,一没知识;二没钱,哪儿来的力量?我要是没有耶稣,我就什么也没有了。苏教授觉得,老甘虽然没有读过书,却是个明理的人。他指着老甘手中的《圣经》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信教的?老甘说,也就一个月前,我的孙子动手术前突然发起了高烧,烧得连医生都没法子。这时候,赵牧师带着三位信徒从病房门口经过,他们听到呻吟的声音就走了进来,按住我孙子的手,跪在地上,给他做了一个祷告。祈祷刚结束,我孙子的高烧竟奇迹般地退了下来。打那以后,我每天都要去医院附近那家教堂做祷告。老甘说起耶稣,说起赵牧师,眼睛里就放出一层柔和的光辉来,把脸上的黑气冲淡了些许。每回跟老甘用家乡话聊天,苏教授就感觉自己回到了老家,仿佛正赤脚坐在田头晒暖闲聊。
苏教授,老甘清了清嗓门说,我想跟你谈谈——
老甘想说什么,但那句话滚到喉头,又咽了回去。苏教授也没有追问,他们面对面坐着,沉默了很长时间。但苏教授感觉自己还在跟老甘说着话,尽管这些话是没有声音的。
傍晚时分,有人敲门。苏教授答一声,请进。进来的,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身后还跟随着三名中年男人。老人轻声地问道,你是苏教授吗?苏教授点了点头。老人说,今天下午,老甘找到了我,让我过来给你做个祷告。苏教授问,你就是老甘说的那位赵牧师吧?老人点了点头。询问病况之后,赵牧师就按着苏教授的手,跪地做起祷告来。念完主祷文,苏教授拍拍床边的椅子,示意赵牧师坐下来。
苏教授:《圣经》这部书,我是断断续续读过一点,有些疑惑,我还解不开,所以要借这个机会向你请教。
赵牧师:跟苏教授相比,我不过是一个浅薄无知的人。《圣经》这部书我读了半辈子,也只是略知一二而已。
苏教授:你知道这世上第一个人是多大年纪去世的吗?
赵牧师:你指的是亚当?
苏教授点了点头:是的。《圣经》上应该有记载亚当享年多少?
赵牧师:《圣经》上记载,亚当活到九百三十岁就死了。
苏教授:也就是说,从亚当的生到死,中间相隔了整整九百三十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漫长的等死的过程。
赵牧师:这世上的第一个人并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亚当之前还没有人体验过慢慢变老直至死亡,所以,以我来看,亚当是只知生,未知死的。死是在亚当出生后过了九百三十年才开始出现的。亚当死了之后,他的子子孙孙们才晓得人终归是要死的。
苏教授:如果我记得没错,在亚当之前,曾有人死过。
是的,那就是亚当的儿子亚伯,赵牧师说,亚伯并非老死,而是死于凶杀。《圣经》里记载说:自从亚伯死后,亚当又与夏娃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意思是说,这是上帝所赐,代替死去的亚伯。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好吧,我们言归正传,苏教授又接着问,亚当出生之后,或者说,亚当和夏娃结婚之后,上帝有没有告诉他,他是终归要死的?
赵牧师: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他们就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上帝曾对亚当说: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苏教授:这九百三十年间,亚当有过病痛吗?比如风湿痛、偏头痛之类。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从事医生这个职业,他是靠什么来治病?或者像我一样,当他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要自杀?
赵牧师:我所知道的全来自于《圣经》,至于《圣经》上没有记载的,我不敢妄言。我只知道亚当的肋骨曾被上帝抽掉过一根,似乎也没有感觉过什么疼痛。书上只记载亚当劳苦的事,并没有记载亚当病痛的事。他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并非疾病所致,而是因为自己的长子该隐在田间杀死了次子亚伯。不过,苏教授,现在轮到我来向你发问了:你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打探亚当的消息?
苏教授:这些天,我躺在床上老是琢磨这些无聊的问题。从第一个人的诞生到我的诞生,从第一个人的死亡到我的死亡,凡是出生过的人都要经历死亡。亚当和我,无一例外。
苏教授看着赵牧师,又重复了一句:亚当和我,无一例外。
六
老甘做完祷告回来,顺便拐进苏教授的病房,说自己今早也特地为他做了个祈祷。苏教授便像回礼似的说,等我病好了,就上教堂给你们一家人也做个祷告。说起老甘家人,苏教授就问,这些天怎么不见你的儿子和儿媳妇?老甘听了这话,眼眶一红,嘴唇抖动了一下,正想说什么,外面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是一群看望苏教授的学生找过来了。老甘赶忙欠身让位,悄然退出人群。学生们把苏教授团团围住,都急着想看一眼老师这一阵子的气色。这些日来看望苏教授的,除了学校里的同事,学界的同行,更多的是一些学生。这回过来的学生中,大的已年过花甲,小的也年近而立。有一部分学生一直追随老师,逢年过节,都不忘给老师送点礼、请一顿饭。这些学生,素以“苏门弟子”自称。跟老师一样,烟酒诗牌,样样都能拿得出手。苏教授虽然脾气古怪,但平常很喜欢板起面孔说笑话。酒喝多了,学生们就让他仿效古人以乡音吟诗。苏教授能将普通话里面早已失传的入声念出来,韵味很足。所以,学生们听到老师病危的消息,都情不自禁地感叹说,苏教授要是走了,我们耳边还会响起他朗吟古诗的声音呢。
学生们问他睡得如何,吃得如何。他也照实说了,这个漫长的雨季里,他压根就没睡过好觉。至于吃饭,素多荤少,有时甚至不沾油腥,以为这样胃不吃力,更好一些。说着说着,苏教授又情不自禁地说起家乡话来。学生们都听不懂,感觉他是在跟自己说话了。
学生们不问病况,不谈故人,不提死字,就怕老师伤感。他们还记得两年前,地理系主任姚鸿年教授得了血癌,苏教授曾带着他们去医院看望。闲谈中,苏教授提到了给姚教授出全集的事,姚教授突然大哭起来,他说自己还要多活几年,怎么这么快就给他出全集呢?跟姚教授相比,苏教授倒是显得坦然得多了。
苏教授说,我要走了,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学生们笔直地站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苏教授说,河要向东流,人要向西走,你想挽留也挽留不住。我的遗嘱已经拟好了,放在我女儿那里,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们就把遗嘱附在我的全集后面。
苏教授抓住其中一个学生的手说,你给我拍摄的那张抽烟的黑白照片我很喜欢,灵堂上的遗照就放这一张。
苏教授又抓住另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的手说,你是大师兄,追悼会上的学生代表发言就非你莫属了。说到这里,苏教授环顾四周,嘿嘿一笑说,你们这些小浑蛋,千万别在我的葬礼上说我的坏话。
学生们想笑,但又不敢笑。有几个还转过身来,悄悄抹去了眼角的泪水。
大家向苏教授告别时,苏教授躺了下来,然后说,你们当中凡是戴帽子的,就预先向我脱帽行个礼吧。
戴帽子的人果然摘下了帽子,毕恭毕敬地向老师行了一个礼。然后退出病房。
等学生都走了之后,老甘又进来了,轻轻地问一声,苏教授,我能跟你谈谈吗?苏教授点了点头。老甘坐在床边,沉默一晌说,这件事跟我大儿子有关,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苏教授说,反正我也没什么事,你就当成是闲聊吧。苏教授这么一说,老甘才打开了话匣子。从老甘口中,苏教授了解到,老甘的大儿子甘大钳出了事,而且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去年,甘大钳进了一家酒店做勤杂工。到了年终,酒店以各种理由拖欠底层员工工资,甘大钳的儿子刚住进医院,急需一笔钱,因此就去找那位从未见过面的大老板讨个说法。他打听到,大老板很少来酒店,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办公。甘大钳去了那家房地产公司,才发现那个大老板就是杀死弟弟、潜逃在外的唐三。但唐三改换了姓名,叫唐善,手下的人则一律称他唐董。时隔这么多年,唐善到底还是认出了甘大钳,心中惶然,立马打电话叫上了三名保安。唐善装作不认识甘大钳,请他坐下来喝杯茶。保安一到,他就从抽屉里掏出一把刀,说甘大钳方才持刀入室,想谋财害命。甘大钳已经没有退路,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经过一番缠斗,甘大钳被他们制服了。唐善意识到,这次如果放走甘大钳就会毁掉自己的后半生,咬了咬牙,索性就把刀子交给其中的一名保安,命令他往死里捅。保安接过刀,双手抖个不停。刀还没有碰到甘大钳,就掉落在地。甘大钳迅速从另外两名保安的手中挣脱,弯腰拾起刀来,怒吼一声,向唐善猛扑过去。唐善躺在地上,只露出半截刀柄。三名保安害怕甘大钳会转身对付他们,吓得赶紧跑开。但甘大钳没有动,他一直坐在唐善身边,对唐善说,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没有想过要报仇,我心中的仇恨早已经化解掉了,是你非要逼我出手的。唐善闭上眼睛说,你捅我一刀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你弟弟的影子,他还是没有放过我。说到这里,他喘了一口气,重重地哼了一声说,一定是你弟弟借你的手向我索命来了。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卖掉了你弟弟那三只羊之后,我的好运就来了。我这辈子也算风光过了,也知足了。唐善断气之后,脸上还挂着一缕微笑。
老甘一口气讲完儿子的事,又清了清嗓门,调整了一下呼吸说,我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原本不想跟你说起,但憋在肚子里让我一直很难受。昨天,有消息传来说,我儿子那起案子过两天就要开庭审判了,我儿子托人带来口信,说是让我找个律师为他辩护,也许他能免去一死。
苏教授想了想说,我有位学生在法律援助中心做事,我给他打一个电话,不晓得管不管用?
老甘说,你每天讲的都是北京话,只要你开口说一句,一定是管用的。
在苏教授的老家,人们管“普通话”叫“北京话”。北京是首都,是权力的象征,天天说“北京话”的人,自然就被人瞧得起。在老甘眼里,人分两种:一种是会说“北京话”的;一种是不会说“北京话”的。像老甘,即属后者。
苏教授拿起手机,给那位在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学生打了个电话,用一种老甘听不懂的“北京话”说明情况。打完电话,苏教授又不放心,特意写了一张便条,让老甘带过去。老甘接过便条,用十分别扭的普通话说出了三个字:谢谢您。苏教授微微一旺,问道,你这句普通话是孙子教会的吧。老甘露出一脸憨笑说,是的,每回护士给我孙子换完盐水,他就会说这句话。次数多了,我也就学会说了。苏教授说,我们不是外人,以后就不用说“谢谢”了,也不必称“您”了。“您”是地道的北京话,在我们家乡,人人平等,没有“您”和“你”的区分。老甘,你说是不是?
七
随着病情的恶化,苏教授感到身上出现了一股愈发强烈的胀痛,服用那些理气止痛的纯野生中药(老甘从老家带来的偏方)已经不管用了。医生给他服用一种吗啡缓释片,但效果也不见佳。在苏教授的请求下,医生不得不给他注射吗啡。但吗啡的镇痛效果仅有六个小时。药性一过,胀痛如故。苏教授时而坐起来,时而躺下,一直无法入眠。他让护士把医生喊过来,请求医生再给他注射加大剂量的吗啡。
医生说,我给你注射的吗啡都必须是限于药典许可的范围,现在不能再增加剂量了。苏教授说,我说过,我可以面对死亡,但不能面对疼痛。现在我感觉这一丁点吗啡已经无法缓解我身上的疼痛了,求求你,医生,请再给我增加一点剂量。苏教授说这话时,流露出恳求的神色,仿佛一个小孩子要向大人再讨一颗糖果。医生告诉他,他现在所用的吗啡剂量已经达到了上限,再增加剂量的话就有可能抑制呼吸。这样做,就等于是医患同谋,让一名医生和病人联起手来杀死一个被病痛折磨的人。但苏教授说,这时候,杀死一个被病痛折磨的人就等于是拯救他。
医生递给苏教授一张纸,上面画着一条10厘米长的直线,两端标示着“0”和“10”(前者代表无痛,后者代表剧烈疼痛)。医生让苏教授用铅笔选择一天二十四小时内的疼痛等级。苏教授放下铅笔对医生说,我的疼痛在这条直线之外,它是无法描述的。在苏教授的反复恳求下,医生也只好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这样,他身上的病痛也就缓解了一些。
这一天上午,老甘又托人从老家寄来了中草药。苏教授知道,这些药物已经不管用了,但他还是吩咐女儿拿去煎熬。喝了几口药汤,苏教授突然侧过身来,哇的一声吐掉了。
注射吗啡不久,老甘又过来了,问苏教授吃了中草药感觉如何,苏教授点点头说,好一些了。老甘说,药效好的话,我让家里人再寄一些过来,苏教授摇摇手说,老甘,不瞒你说,我已时日不多了,现在,我已经对吗啡产生了依赖。除此之外,任何药物不管用了。我希望自己是在平静中睡去,而不是在疼痛中离去。苏教授缓了口气说,医学发达的好处就是,让你死得更舒服一些。
苏教授的愿望并没有落空。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他身上可能出现的剧烈疼痛解决掉了。而他接下来需要独自面对的,是没有痛苦的死亡。那一刻,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决定死在春光里、深埋在雨中的幸福感。
一大早,老甘在教堂做完晨祷回来,刚走进病房,就发现孙子的床位已经清空了。老甘问护士,我的孙子?护士听不懂老甘的方言,但大致明白他的意思,就说,他已经送到停尸房去了。老甘又问,我的孙子呢?他究竟去了哪里?护士说,你还听不明白?你孙子已经不行了。他一直在等你,可他已经等不及了。护士咬着嘴唇,似乎刻意不让那个“死”字说出口。老甘说,你不要跟我说北京话,你就告诉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死”这个字,无论用方言还是普通话来念都是同一种读音,它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夹带一股冷飕飕的尾音。护士的眼圈一红,看着老甘说,是的,死了,死了。老甘这回听明白了,突然跪下来说,求求你们,让医生再给他看一看,也许他还能活过来呢。护士说,很抱歉,大爷,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样吧,隔壁那位苏教授是你同乡,你有什么话直接跟他说,让他再转述给我们听。护士意识到老甘也听不懂她的普通话,就给他做了个手势,把他带到苏教授的病房。老甘站在门外,犹豫了片刻,不敢进来。护士走到苏教授床前,跟他作了一番简单的交代。苏教授抬起头来,朝老甘招了招手。老甘挪进几步,讷讷地说,苏教授,我一大早跟你说起我孙子病死的消息是不是有点不太吉利?苏教授的嘴唇猛地颤抖了一下。他不敢确定,小孩子的猝死是否跟试用新药有关(报纸上也曾刊登过一些国际知名医药公司拿中国农村孩子做“试药者”的消息)。这些话,苏教授没敢跟老甘说,以免他再度受到刺激。
老甘在脸上抹了一把说,我儿子欺骗了我,他说自己判个十年八年就可以出来的,可最后的判决竟然是无期徒刑;我孙子也欺骗了我,他说自己的病差不多就要好了很快就可以出院了,但他说走就走了。
苏教授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老甘,只是低声问,你以后该怎么办?
老甘说,我原本是可以留下来照顾你的,但昨天下午,我们村上的人打来电话说,我母亲也要走了。可她就是断不了那口气,分明是等我回去替她送终。等我的孙子火化之后,我要带他的骨灰回老家去。以后,我就不来这大城市了。我就想待在乡下,哪儿也不去。
苏教授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
苏教授,老甘说,一个人死后……死,唔,我怎么可以跟一个病人提起死字?
苏教授说,这些日,我跟医生和赵牧师也都在探讨死亡的问题。以前我很忌讳跟人谈到死,现在我差不多是两脚踩进棺材里只差平躺下去伸直两腿了,所以,我不再害怕有人跟我说到死以及死后的问题。我已经把临死前可能碰到的问题解决掉了,把死后的事也交代清楚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我跟你不同,老甘静静地注视着苏教授说,你知道自己怎么死,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活着。一个人知道自己怎么死总比不知道自己怎么活着要强吧。
老甘的话有点沉重,苏教授不知道该怎样让谈话继续下去。他想说什么,但只是动了一下嘴唇。他的声音在嘴唇里凝固了,变成了干枯的叹息……
责任编辑 伊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