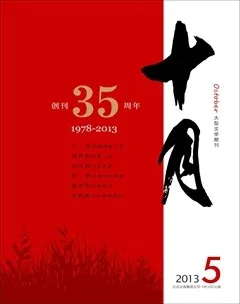木黄,木黄,木色苍黄
2013-12-29贺捷生
一
站在那棵遗世独立的大柏树下,我抬起头往上看:两根硕大的树干并驾齐驱,直直地插向空中,到达十几米处,它们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彼此亲热地向对方靠上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如同两个失散已久的兄弟。再往上看,是茂密的蓬蓬勃勃的枝叶,根本分不清树枝和树叶是从哪根枝干上长出来的,一群群鸟儿在枝叶间飞进飞出,发出叽叽喳喳欢快的叫声。在墨绿的树冠上面,天空高邈,湛蓝,一望无际,飘浮着一朵朵轻盈而素净的白云,仿若盛开在天空的一簇簇白玉兰。接下来,往云朵里看,我便看见了那支不倦的在天上行走的队伍,他们衣着破烂,脚蹬草鞋,身影若隐若现,几乎听得见他们甩动手臂的声音,枪托叮叮当当地敲击水壶的声音,弹袋里可数的几颗子弹在哗啦哗啦晃动中被磨得金光闪闪的声音。
眼睛一阵灼烫,我知道我在流泪。那是我总也止不住的泪。
到1975年9月13日的此时此刻,我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从江汉平原、四川盆地往云贵高原走。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我们从夏天启程,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顺走一段,逆走一程。先去了湖北洪湖,然后翻过二郎山,从雅安进入阿坝;再从青草长得比人还高的大草地踅转身子,顺岷江而下,跨过大渡河、金沙江和乌江,沿阶梯般步步登高的山脉进入云遮雾罩的乌蒙山。走到贵州的时候,已是秋风浩荡。眼看就要万木霜天了,进了贵州省城贵阳,几个人累得东倒西歪,人困马乏,都想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
我是三人中唯一的女性,当然更累,两条腿沉得像深陷在沼泽里。可我不想停下来,还想继续走,往黔东的印江、沿河和四川的酉阳走。我对我的两个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事万钢和何春芳说,你们在贵阳歇几天吧,剩下的几个地方我一个人去。我没有说出的另一句话是,黔东那片偏僻而蛮荒的土地,于公于私,都是我不敢遗忘的地方。我发誓此生必须亲自去寻访,就像有什么东西丢在了那里。
离开同事,我直奔省府找李葆华。他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儿子,在贵州当省委书记,说起来,我们是心照不宣的老熟人和老朋友了,到了贵州没有理由不见他,何况我还有事要求他。但那一年,跟着小平同志出来“促生产”的这批老干部,被那批热衷于“抓革命”的人揪住不放,日子很不好过。听说北京来人要见他,正在开会的李葆华一脸疑惑地走出来。我像在黑暗中找到了党,开门见山,提出请他从省博物馆派个同志陪我去黔东。他说这事他还能办到。当时正是午餐时间,会开得差不多了,他回去简单做了交代,然后对我说:“捷生,你来得真不是时候,我没法招待你,跟我去吃食堂吧。”
省博物馆派来陪我的谭用忠同志,是个党史专家,学问很深,对黔东革命史了如指掌。他建议我先去印江,因为印江的木黄非去不可,那地方太重要了。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说我最想去的就是木黄。
那时我虽然还年轻,但也经不起折腾,当我们沿着惊涛拍岸的乌江舟车劳顿地走到木黄这棵千年古柏下时,我已是脸色枯黄,头发蓬乱,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的。从附近挑着担子走过的土家族人和苗人,都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不知道一个外乡人为什么会对着一棵树流泪。
肯定是李葆华的特别叮嘱,印江派出一个副县长接待并陪同我寻访,不过那时叫“草委会副主任”。副县长和我一样,也是个女同志,叫张朝仙,是很朴素也很泼辣的一个人。许多年后,她以县政协文史委员的名义在县里局域网上撰文回忆,她在印江县招待所第一眼看见我,都不敢相信我是贺龙的女儿,“像一个女知青。”她说。
二
木黄是因为那棵千年古柏而闻名,还是那棵千年古柏因为见证过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而闻名,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反正当我寻遍那几条简陋的街道,最后站在那棵古柏下时,我发现木黄唯一能作为那段历史和我面对面的,也就剩下这棵树了。
这让我无语而泣,悲从中来。
当着漫山遍野又要飘落的落叶,我们怎么能忘记木黄呢?
党史和军史都应该记载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木黄会师,迄今都过去41年了,新中国也建立26年了。我想,我们可以不知道历史的每个细节,但应该知道在红军的三大主力中,有一个红二方面军。而红二方面军的源头,就是1934年10月,从湘西发展壮大的红二军团与从湘赣边界跋涉而来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这个叫木黄的小镇上胜利会合。两支劲旅从此合二为一,生死与共,开始了让世人称奇的全新征程。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地点,就在木黄的这棵大柏树下。
许多红二方面军的老同志回忆,41年前,就是在这样一个木色苍黄的秋日,父亲贺龙亲自带着红三军主力,站在木黄的这棵树下焦急地等待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等待他们带领的那支远道而来的筚路蓝缕的队伍。
这是1934年10月24日,层林尽染,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白霜铺地,在黔东逶迤起伏的山岭里吹荡的风,已经像藏着刀片那般凌厉了。
9天前的10月15日,父亲在酉阳南腰界获悉由任弼时、萧克和王震带领的红六军团号称“湘西远殖队”,从江西永新出发,试图深入湘西,与我父亲的队伍会合。经过一路恶战,此时已进入黔东印江和沿河一带寻找我父亲率领的红三军,这让我父亲喜出望外,因为到这时,他在湘西拉起的这支队伍已经有整整两年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在这两年里,由于“围剿”的敌军蜂拥而至,夏曦又在红军内部大搞“肃反”运动,把许多忠心耿耿的指挥员和地方干部残忍地杀害了,闹得人心惶惶,军心涣散,把父亲在湘鄂西好不容易建立的根据地给弄丢了。父亲惨淡经营,站出来收拾残局,他把我怀孕在身的母亲丢在湘西的山野中苦苦挣扎,自己带着由红四军改为红三军的部队退到黔东的印江、沿河和酉阳等地,建立新的根据地。黔东一带虽属贵州军阀王家烈和川军的地盘,但因地处湘黔川三省边界,山高林密,河流纵横,敌人鞭长莫及;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地的民众也和湘西一样,多为土家族和苗族,与父亲这支在湘西土家族和苗族地区拉起的队伍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因而逐渐被当地号称“神兵”的民族武装接纳,使这支伤痕累累的部队勉强站稳了脚跟。
那天,部队报告说抓到了一个探子,但几番审问,最终弄清是个普通邮差。父亲说,既然是个邮差,就把他放了吧,把信件和汇款单还给他,让他继续去送信,但必须把报纸留下来。如果没有路费,再发给他路费。就是从邮差留下的那摞报纸里,父亲看到了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经湘南向黔东“流窜”的消息。
红六军团同样是一支苦旅。1933年10月,蒋介石调动几十万精锐部队步步为营,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因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占据上风,中央红军屡战失利。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命令在湘赣边界作战的红六军团开始西征,挺进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策应中央红军突围。这支由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的部队,1934年9月从湘黔边界进入贵州,立刻遭到王家烈联合三方会剿。部队原想冲破敌人的防线,西渡乌江,进军黔北,中央军委却命令他们奔向江口。10月7日拂晓,第六军团在辗转中到达石阡甘溪,准备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色越过石阡、镇远进入江口。谁知敌人在甘溪设下埋伏,一场让红六军团在须臾之间损失3000指战员的惨烈战斗在此打响,军团十八师师部及五十二团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团长田海青阵亡,师长龙云被俘后遭杀害。军团参谋长李达引领前卫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各一部突围后,意外得知贺龙的部队在印江、沿河一带活动,毅然率部奔赴沿河地区。
在获悉红六军团主力行踪的同一天,前方传来消息,李达在突围中带出来的部队与红三军七师十六团在沿河水田坝会合。父亲兴奋不已,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6日,率领红三军主力从酉阳进入松桃,在梵净山区纵横交错的峡谷里寻找中央红军。
在山里整整转了7天,22日,当红三军主力到达印江苗王坡时,红六军团主力已先他们一步经苗王坡向缠溪进发。看见红六军团踩过的青草还没有直起腰来,父亲一挥马鞭说,快!抄近路追赶,不能让中央红军再吃苦受累了。
22日深夜,随红六军参谋长李达突围、先期与红三军会合的郭鹏团长,率侦察连穿插到印江苗王坡,忽然听到后面发来一阵“嘀嘀嗒嗒”的军号声。仔细一听,是他极为熟悉的红六军团四十九团的号谱!郭团长欣喜若狂,命令司号员吹应答号。霎时一问一答的军号声此起彼伏,就像两股泉水在空中欢快地碰撞和交缠。号音未落,两队人马已在溪谷的一块坪地上泪光闪烁地抱成一团。
23日,红六军团从印江缠溪出发,经大坳、枫香坪、官寨、慕龙,宿于印江落坳一带。红三军从印江苗王坡出发,经龙门坳、团龙、坪所,宿于芙蓉坝、锅厂、金厂。从地图上我们就能看清楚,两支部队其实是向一个中心靠拢,这个中心就是木黄。
24日中午,按照事先约定,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主力经落坳、三甲抵达木黄。父亲贺龙、关向应和先期到达的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红三军,提前在木黄的大柏树下列队迎接。
虽是满身战尘,衣衫破旧,还拖着300多名伤病员,但在枪林弹雨中跋涉而来的红六军团,精神百倍,指战员们该刮胡子的刮了,背包里还有换洗衣服的都换上了。队伍走近大柏树的时候,正生病躺在担架上的任弼时,一见父亲的身影,立刻从担架上跳下来,坚持要自己走;父亲连忙迎上去,想让他继续躺在担架上。任弼时激动万分,紧紧握住父亲伸来的手,说这下好了,我们两军终于会师了!
父亲也非常激动,连连说好!好!好!我们终于会师了!
站在各自首长身后的队伍,顿时欢呼雀跃,掌声如雷。在两军领导人历史性握手之际,双方拥上来热烈拥抱,相互通报姓名,又相互捶打着对方的肩膀。后面的人挤不进去,急得朝天放枪。
木黄的这棵千年古柏,就这样见证了两军会师的伟大时刻,见证了红军中几个湘籍领袖久久地把手握在一起。
两军会师后,双方领导人在镇上的水府宫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下一步行动。会议根据中央的部署和黔东的敌情,作出了迅速向湘西发展的决定,而且事不宜迟,第二天便拔寨启程,实施战略转移。
10月25日,两军到达酉阳红三军大本营南腰界。这里鸡鸣三省,群众基础稳固,暂无敌人追击之虞。部队驻下后,用红六军团的电台及时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会师情况。26日,在南腰界一块坪地上隆重召开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作为中央代表,任弼时首先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接着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整编后正式称为红二、六军团,设军团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其中红二军团下辖四、六两师4个团共4300余人,贺龙任军团长、关向应任政委。红六军团的军团长仍为萧克,政委仍为王震,下辖3个团共3300余人。
父亲尊重中央红军,信赖中央红军。他虽然担任两军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总指挥,但他在大会上说了一句话,让后人交口称赞。父亲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中央红军就是我们的老师!”
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挺进,拉开了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序幕,有力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熟悉中国红军史的人都知道,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意义重大,它使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汇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
1936年7月,在紧追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中央军委发来电文:“中央决定,从7月1日起,红二、六军团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三
是的,我寻访木黄的时候,正值如今我们已不堪回首的年代,那时“十年动乱”还没有结束,在人们的期待中艰难复出的小平同志又面临着被打倒的危局,中国大地正处在火山爆发的前夜。
自然,那时人们对父亲贺龙的名字还讳莫如深。都知道他作为共和国开国元帅,在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尽管中央在1974年已作出为他平反昭雪的决定,召开了有周总理参加的追悼会,但有关方面规定不准见报,不准宣传。正因为如此,在那个骚动不安的秋天,我是怀揣着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上路的。在这片写满父亲的光荣,每个人都说得出他名字的土地上,我每到一地,每遇到一个当地领导,都要拿出那份红头文件给他们看,让他们眼见为实。我对他们说,毛主席都说话了,贺龙是个好人,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贡献。在中央为父亲举行的追悼会上,带病出席追悼会的周总理连鞠了7个躬。我还说,我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以中国革命博物馆文物征集组副组长的名义,沿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足迹,来寻访和收集革命文物的,请多多包涵。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怯懦,就像鲁迅笔下那个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其实大可不必,当我第一站到达印江,县里的领导就倾巢出动,甚至在我住着的县招待所安排了岗哨。这让我大感意外,又大为感动。我想,天下自有公道,原来老区人民并没有忘记我父亲,没有忘记他们这一代革命老前辈。还有什么比这片土地上的人,在那样一个错乱的年代,在心里深深地铭记着他们的功德,更让人感到激动和欣慰呢?
路途遥远又崎岖,第二天一早,县草会主任和副主任、木黄所在的天堂区草委会主任,还有县公安局负责安全保卫的同志,近十人前呼后拥,一起陪着我去天堂区兰克公社的毛坝寻访。那儿有红三军一个师部的旧址,并有经常随该师行动的我父亲的旧居。户主是个叫陈明章的老人,当年给我父亲做过饭,放过哨,至今还能说出他的音容笑貌。
走进那栋年久失修的房子,楼下的一间厢房洞开,我心里一惊,仿佛闻见从里面飘出来一股熟悉的烟草味。陈明章老人说,我父亲当年就住在这间厢房里,在夜间,他声震屋瓦,常听见他累得像打雷那样打鼾。听见这句话,我一头往厢房里钻。屋子里逼仄、幽暗、潮湿,微弱的光线从一扇不大的开得很高的窗口射进来;两条长凳架着一块薄薄的床板,想必就是父亲睡过的床了,靠近头部的位置明显有松明火熏过的痕迹。那时还没有开放参观一说,更不敢提贺龙曾在这里住过,我一眼认定都是原物,而且几十年都没有人动过。我趴在留有父亲汗渍的床前,想起他睡下后又撑起身子来够墙壁上的松明火点烟斗的情景,止不住失声痛哭。父亲苦啊!但当年他苦,是他心甘情愿的选择,苦中有乐,有他能远远看到的光明和希望。可后来呢?后来革命胜利了,他当了人民赞颂的元帅,却在那场黑白颠倒的运动中,死在了一间同样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而且那是一间钢筋水泥屋子,墙壁比这还坚硬,还冰凉;而且父亲去世的时候,重病缠身,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上……
全程陪着我的县草委副主任张朝仙,后来在她自己整理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贺捷生抚摸着父亲曾经睡过的床,睹物思人,想到父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革命一辈子,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都度过来了,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含冤而死,不禁悲从心起,泣不成声。看到她的哀伤,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我想还是让她痛哭一场宣泄一下为好。从陈明章家出来到公路有三里左右路程,贺捷生边走边哭,一直到上车才止住哭泣。这次恸哭,是我陪她在整个寻访过程中哭得时间最长的一次。”
接着我们去了青坨红花园。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叫何瑞开的老乡家,进门便看到板壁上保留一条巨大的红军标语:“反对川军拉夫送粮,保护神兵家属。红三军九师政治部宣”。字迹古朴,醒目,散发出一股在那个年代红军和民众心心相印的感召力。从红二、六军团几个幸存的老同志嘴里,我听说当年负责往墙上刷大标语的,是后来长期主政新疆的王恩茂。我不敢断定这条标语就是他写的,但我说,这是一件难得的珍贵文物,征询主人何瑞开愿不愿意让中国革命博物馆征用。怎么不愿意?何瑞开拍着胸脯说,只要给我一个屋顶避雨,需要这栋房子都可以征去。又说,贺同志,你父亲当年为我们打江山,生生死死,图个什么?还不是图我们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现在真太平了,没有人欺压我们老百姓了,我怎么舍不得这壁木板?还说,我懂,不是这壁木板有多么金贵,是红军写在上面的字,字字千金。
这天,我们还去看了铅厂黔东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枫香溪湘鄂西分局会议会址。两个地方都是穷乡僻壤,需要翻山过坳,累得人筋疲力尽。令人痛心的是,因为父亲蒙受冤屈,这些理应受到保护的革命旧址,已无人问津,显得破败不堪,岌岌可危,有几处墙壁开始坍塌。
从枫香溪会址出来,已过傍晚7时,黑下来的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满世界回响着雨打山林的声音。下一站去耳当溪,还要走6里山路才能坐上车,只能冒雨前行。走在杂草过膝的山路上,衣服很快便湿透了。天又冷,浑身起着鸡皮疙瘩。走到耳当溪,水漫进了吉普车里。车往前开,看不见一盏灯光。走着,走着,耳边传来轰轰隆隆的流水声。
张朝仙说,贺处长,这地方叫沙坨,前面就是乌江,就是红军突破乌江的乌江。今晚我们也得突破乌江,到对岸的沿河县投宿,但江上没有桥,必须摆渡过去。又说,贺处长,沿河是印江的邻县,条件可能还没有印江好,要有思想准备哦。在路上,张朝仙自作主张,总是叫我“贺处长”,我多次纠正她说,我不是处长,是文物征集组副组长。她固执地说,国务院“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也叫组长,那是多大的官啊!你们中央来的人,组长都比我们县长大,叫你处长还不应该?听她一路对我表达歉意,说贵州穷,贵州的老区更穷,让我受委屈了,我又忍不住说,你们能这样接待我,已经让我感激不尽了,还讲什么条件?你以为我有多么娇气啊,其实我也为人妻,为人母,吃的苦和受的罪,不比别人少。她没话说了,惊愕地看着我。
在江边等船的时候,夜色漆黑一团,深夜的雨打在肌肤上冰凉刺骨。登上渡船后,湍急的浪涛噼噼啪啪地撞在渡船上,明显感到船身在震颤。站在甲板上,比我高大的张朝仙用双臂护着我,好像怕我被浪涛卷走似的。我在想,当年父亲他们反反复复过乌江,有多难啊!
到达沿河县招待所,已是下半夜了。服务员在半醒半梦中从窗口扔出来一把钥匙,让我们自己去客房。打开门一看,这哪里是县招待所?分明是北方的大车店:房间里摆着八九张硬板床,没有被子、褥子和床单,也没有蚊帐,简陋的床板上铺着满是破洞的粗席子。虽是初秋,但山区的雨夜很冷,加上在山里跑了一整天,又淋了雨,睡过去肯定要着凉。我对张朝仙说,就这样凑合一夜吧,反正天快亮了。张朝仙说不行,丢咱老区人的脸,转身去找服务员。只听见她对服务员说,这是北京来的领导,你们得给她换一床干净的被子和床单,把领导招呼好,我们无所谓。没多久,她抱回来两套破旧的被褥,给我铺好后,说贺处长,您好好休息,今天太累了,早点睡,有什么事叫我。说着往隔壁走。我知道隔壁的条件比这还差,一把拉住了她。我说朝仙同志,你就住这里,我们在一起说说话。
这个晚上窗外雨水滴答,空中蚊虫飞舞,我和张朝仙在各自的床上靠墙而坐,扯着被子盖住双腿,聊了很久。我把我父母怎么结的婚,母亲是个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父亲带领红三军到黔东后,母亲怎样怀着姐姐红红在湘西的山里打游击,姐姐红红又是怎么死在她手里的;还有我姨骞先佛怎么嫁给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怎么在长征途中生的孩子;我的童年怎么寄养在湘西,大学没毕业又怎么去青海支边等等,都给她说了。听得她泪光闪闪,连连说想不到,真是想不到。我还对她说了我父亲当年在黔东的一个生活细节:那时候战斗频繁,居无定所,父亲为了养精蓄锐,养成了在扁担上睡觉的习惯。他在两条凳子上放一根扁担,又在手指上绑一根点燃的香,躺下就能睡过去。当那根香烧疼他的手指,马上就能醒来。因此,他每次睡觉的时间,掌握得就像钟那么准确。我讲完这个细节,张朝仙已在黑暗中抽泣。她说,当年打江山有多苦啊!我弄不明白,现在为什么要整那些老干部,这不是过河拆桥嘛。
从这个晚上开始,我和张朝仙成了朋友,以后常有来往。
四
我再次站在木黄那棵千年古柏下的时候,是10月2日。这时我在黔东的崇山峻岭中前后跋涉了近10天。中途张朝仙送我在乌江上船,回贵阳参加了一个文物会议。正想着下一步往故乡桑植走,北京打来电话,说中央准备开展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活动,要我在当地请一个摄影师,重回印江木黄和酉阳南腰界去拍组照片。我重新出现在印江县招待所时,张朝仙大感意外,以为我把魂丢在了印江。
我说我的魂真丢了,但没有丢在这里,丢在了木黄。
还是张朝仙陪我下去。到了小镇上,摄影师只顾得取景拍照,我独自在大柏树下盘桓,心里有个莫名的念头在不住地翻涌和缠绕,却捉不住它,说不清它。之后,我拨开树丛,攀上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一面山坡。这里居高临下,能一览无余地看到木黄的全貌——
远处的梵净山主峰,虎踞龙盘,在奔涌的云雾中岿然不动。脚下的木黄镇,夹在一道深深的峡谷中,两岸的青山雄伟,俊秀,一派苍茫。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正在变色的树叶泛出一片片金黄,如同漫山遍野散落的金箔。与镇子同名的河流穿峡而过,像一条玉色飘带逶迤而来,又逶迤而去。三三两两散落在田野里或山路上的农人,小得像一只只各自在为生活奔忙的蚂蚁,好像日子天长地久,谁都是匆匆的过客,即使哪年哪月发生过什么事情,也不过如此,渐渐地就会被遗忘。
想到我两次来木黄,无论在两军会师的古柏下,还是在两军会师后召开会议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水府宫,都没有一块像样的标牌,更别说作为历史见证开辟出来供人瞻仰了,心里不禁有些苦涩。
10月3日,我们经松桃、秀山去酉阳的南腰界,过县过省的旅途峰回路转,险象环生。不仅是近日下了几场大雨,把多处的路桥冲断了,车开着开着就得下来步行,而且还有不明身份的人出来捣乱。
那是我们从酉阳去南腰界的路上,途经金家坝休息,忽然有人对前来陪同我们的酉阳县委孙副书记说:“孙书记,你要小心,有人要杀你。”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威胁恐吓领导干部是常有的事,因此孙书记并未理会。但稍过片刻,还是在金家坝,忽然又有人贴上来问:“孙书记,你们晚上还回来吗?”孙副书记还没在意,说当然回来。我们在南腰界拍完照片回酉阳,天色已晚,开着大灯的两辆车在夜幕中缓缓行进。可是,当我们的车驶进一片密林,公路上突然横着一根巨大的木料,路中央堆着一大堆石头,无法通过。此时黑夜沉沉,两边的山林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几声夜鸟的惊叫。张朝仙说:“坏了,看来真有人破坏!”然后对孙副书记说:“孙书记,不能再往前走了,不如折到李溪先住下。”孙副书记想起在金家坝的遭遇,也觉得事情蹊跷,同意改道往李溪走。
后来证实,那天晚上真有人要闹事,并且是冲着我来的。原来,1934年,红军在南腰界猫猫山开过一个大会,当场杀了几个恶霸。那几个恶霸的后代听说贺龙的女儿来了,跃跃欲试,暗中组织了几十个人拦路,企图趁乱报杀父之仇。
第二天,孙副书记调来一辆救护车开路,料想那些人不敢在大白天胆大妄为。车开到头天晚上断路的地方,那根横着的木料和路中央堆着的石头依然还在,公路上散落一地燃烧过的柏木皮火把,到处是新鲜的屎尿;两块石头上分别写着:“到此开会,彭?菖?菖”和“我们到了”等字样。我们下车把木料和石头搬开,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路打通。
虽是虚惊一场,但回到印江,我的心里仍然五味杂陈。倒不是感到后怕,我是想,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会出现当年被惩治的恶霸后代寻衅报仇?而且公然把目标对着贺龙的女儿?这说明历史被淡忘到了何等地步!也说明红军和贺龙的威名,被时间,尤其是被“文革”的倒行逆施,渐渐地磨灭了。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啊!
就在这时,那个几天前在木黄莫名缠绕我的念头,忽然变得清晰起来,明确起来。我想我知道该做什么了。
离开印江那天,我鼓足勇气,含蓄地对张朝仙,其实是对她担任的县草委副主任的职务说,红二、六军团1934年9月在木黄会师的历史地位有多重要,无须我多言。但我去过洪湖,也去过遵义,前些天又和你一起去了南腰界,这些地方都有历史纪念碑,你们想过木黄也应该有吗?
张朝仙沉默许久,认真地说:“贺处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是一件大事,偏偏我们又是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容我慎重报告县委。”
五
1977年,我收到张朝仙写来的一封信,告诉我说木黄两军会师纪念碑已经破土动工,碑址就选在我攀登过的那座山下面。现在这座山取名为将军山,那棵大柏树,取名为会师柏。张朝仙还说,纪念碑的碑文,他们请1975年陪同我去木黄寻访的省博物馆党史专家谭用忠同志撰写,但碑名至关重要,必须请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留下字迹,问我能不能找到当年率部会师的红六军团政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题写。
我心里一高兴,马上回答说,这个任务包在我身上了。
事后印江的朋友告诉我,我离开木黄后,张朝仙立刻向县委书记瞿大国汇报了在木黄建碑的想法。“我知道县里穷,但可以先拿出万把块钱来建个简单的纪念塔。”她说:“有总比没有好啊,不能被后人戳我们的脊梁骨。”瞿大国完全同意张朝仙的提议,并在县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有意思的是,在考虑主管纪念碑建设的人选时,大家都想到了张朝仙。
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志感情淳朴,认准的事情按照自己的习惯干了再说。张朝仙不负众望,卷起铺盖一头扎进木黄,动员群众土法上马,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建碑。设计图纸还没有出来,他们就开始平地基,修公路。木黄区更是积极响应,从各公社抽调一个民兵排上阵;又从全区选调了一批石匠,进山提前采集石料。县里经费紧张,常委会决定下拨的一万元迟迟没有到账,木黄区的同志们说,给红军盖碑,是我们多年的愿望,我们不要县里的钱,给大伙记工分。工地上生活艰苦,没有水,便发动机关干部职工和学校师生前来挑水,让各部门负责拉沙。他们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山里的石料用手掰不开,县里得提供雷管和炸药。
木黄虽是老区,又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闭塞,但红军烈属和亲属多,群众觉悟高,有许多见过两军会师的人还健在;甚至还有跟随过红军战斗,因伤或因其他原因没有跟着走的老游击队员,听说要建红军会师纪念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拥来助阵。
将军山下,大柏树旁,一时人声鼎沸。
我后来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张朝仙站在张家沟采石场向大家宣讲建碑的意义,人群中突然有个老汉高声回应说:“这个同志讲得好,为红军建碑是我们木黄的责任。”张朝仙寻声望去,只见那人满脸皱纹,背像弓那样驼着,头发稀稀疏疏地全白了,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张朝仙走过去问他:“老伯,你是谁?在办哪样?”老汉说:“我叫张羽鹏,天堂区陡溪公社茶坨村人,贺老总在印江闹革命的时候我当过游击队长。听到要为红军修纪念碑,我特意赶来出力,连口粮都带来了,不信你来看嘛。”张朝仙朝他身后背着的背篼一看,果然有一包米,一包饭,一些蔬菜。张朝仙当众表扬老汉说,你这个认识很好,很有代表性,大家要向你学习。因为县城与天堂公社同路,那天回县城时,张朝仙特地请张羽鹏坐她的车走,老汉说:“我不跟你走,我是来修碑的,又不是来看热闹的。碑还没建好,我走哪样?”最后,张老汉硬是坚持到纪念碑完工,才背着背篼回家。
这个叫张羽鹏的老汉我还见过,在北京接待过他。那是多年后,张朝仙给我打来电话,说那个背着背篼去木黄修碑的老游击队员,你还记得吗?现在他的眼睛不行了,看不见了,想来北京治病,能不能帮帮他?我说,怎么不记得?你让他来吧,我来管他。那时我的老伴李振军还在世,张老汉到了北京,我们一起去看他,一起把他送进医院。老汉的住院费和治疗费,全部免除。当然,这是后话。
印江在木黄土法上马建会师纪念碑的消息,很快传到省里,省文化厅、省设计院和省博物馆迅速派人来查看。他们既为群众自发纪念红军的精神感动,又觉得按此办法建碑太简陋,与两军会师的重要地位不相称,必须重新设计并把碑挪到半山腰,那儿视野开阔,也更庄重,更气派。省里的同志说,给红军立碑,那是千秋万代的事情,不能垒几块石料竖一面碑了事,像盖一个土地庙。印江的领导听得频频点头,从心里感到省里的人就是比自己站得高,看得远。可他们接着说,那么钱呢?那得要多少钱?我们拿不出来啊!省里的同志说,这样吧,我们给你们设计图纸,再拨给你们四万元,只有那么多了,你们得精打细算。县委和县草委的人笑了,说四万元不少了,我们勒紧裤带,再自筹两万。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收到张朝仙的来信,让我想办法请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题写碑名。我知道王震叔叔很忙,但再忙他也不会推辞的。因为木黄会师不仅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我父亲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包括萧克和他在内——他们个人革命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何况他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对父亲和那段历史感情深厚。所以,当我向他报告木黄正在建造红军会师纪念碑时,他马上说:“好啊,需要我做什么?”
这已是1978年,听说我拿到了王震的墨宝,张朝仙在电话那边激动得哭了,马上让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代表大会的县妇联主任上我家来取。妇联主任开完会立即赶回印江,到了县里得知张朝仙在铜仁开会,又马不停蹄赶到铜仁,当面把墨宝交给张朝仙。
1979年夏天,由王震题写碑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就要落成了,县里挑选7月1日建党58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举行揭幕仪式,并来电来信郑重邀请我参加。不巧的是,我刚做完一个手术,行走不便,未能成行。但是,我字斟句酌地给印江县委写了一封贺信,表达我难以平复的喜悦:
印江县委负责同志:
你们好!收到你们的来电和来信,心情非常激动,木黄会师纪念碑终于落成了,这是一件政治上的大喜事,我万分高兴。记得1975年,我两次走访印江,那时正是乌云压顶,“四人帮”横行之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给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讲话消息尚不能公开见报,印江县委的领导瞿大国、张朝仙等同志就提出要修建木黄会师纪念碑,对我的鼓舞和教育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印江不仅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还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根据地,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这些都是值得我学习的。总之,1975年的两次印江之行,感受很深,受益甚大。也非常感激县委对我的热情接待。这次我非常想去参加木黄会师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但因我患甲状腺功能亢进,刚动过手术不能参加,甚感遗憾,请你们原谅。不过,我一定要争取第三次去印江看望老根据地的人民……
责任编辑 谷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