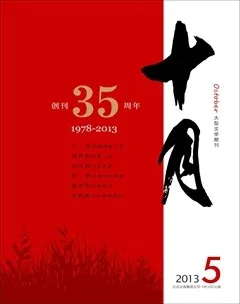四季调
2013-12-29吴文君
他喜欢人去楼空后的静寂,喜欢消毒水盖过一切的强悍的气味。在那种强悍的气味里,任何别的气味都是单薄的,无用的,被彻底地掩盖掉。那种强悍也潜伏在他身上,潜伏在他臂膊的肌肉里。虽然大部分时候,他只是一个文弱的少年。即使他母亲也并不了解他。
这一天的课结束了。别的学校放学的喧哗这里是看不到的,人到了这里,再喜欢玩笑的也会肃穆起来。他们将来都是医生。他们必须尊重病人,或者说尊重病着的肉体,这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
这些未来的医生一个个肃穆地离去了。终于只有他了。梧桐树的叶子在窗外沙沙响着。天好的时候,叶影投到墙上,水门汀的地板上,微微颤动着。那一刻,人世的跃动和屋里静寂的死气在抗衡,也往往以叶影的消失告终。没有哪个无关的人愿意走近这儿,虽和其他房间连在一起,却自成着世界,静得僻远。
这几乎是他的天堂了。尽管起初并不是出于他的自愿,由不得己,直至习惯了一个人在解剖室和存放尸体的库房之间忙碌,把没有用完的尸体刷洗干净。刷尸体有专门的台子。他刷得很认真,先刷正面,翻过来脸伏倒朝下再刷一遍,没有污迹了才放回池中,等待下一堂课再用。这需要相当的体力和耐心。收拾废弃物则容易一些。把课间用过的皮、肉、内脏塞到医用的罐子里,与别的罐子摞到一起就可以了。
他勤勉地做着这些,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他牢记着那些供他们学习而零碎了的身体的年龄,性别。他总以为别的同学只是把皮、肉、内脏一股脑儿塞进罐中就结束了。而他呢,如果把肌肤白嫩的青春少女与干瘪老头装到一个罐子里,某种不安会折磨得他坐卧不定,心思恍惚。倒不是为了他们的尊严,那个时代,活着的人尚没有尊严,何况尸体。他对自己的行为究竟没有说得出口的理由,也许只想单纯的以他的标准做着分类,是他的私心,不喜欢别人看见。总以为让别人知道他这样,是很怪异的。
因为这额外的工作,有解剖课的这一天,他很晚才回来。家里习惯了不等他就开始吃晚饭。孩子多,也没有人给他留菜。他吃惯了剩菜,连剩菜也没有了,就倒点酱油,撅一小块猪油,拌到饭里。他端着饭碗,那微温的饭粒并不足以抵消先前的冰冷。那是从尸体的深处浮上来的冰冷,直到夜很深很深了,还留在他手上。
很多东西他都淡忘了,就像曾经拉得熟得不能再熟的小提琴曲。没有记错的话,那年他是十七岁,与同学打了一架之后,他的医学院预科班的生涯从此结束了。他拎着小提琴坐上火车,永远离开了家。这里的永远并不是说他再没有回来过,而是以户籍制度来讲,他把自己永远驱逐了出去。
几经辗转,他在淮河边一个盛产煤炭和稀有金属的小集镇落下了脚。他似乎是安心留在那里了,以他的聪明,没几年便升到了管理岗位上。他工作得很顺手,把他负责管理的机器当成他的孩子一样。他就像一个家长,坐镇在属于他的院子里。院子一角堆满了零件,有用的,没用的,精光锃亮的,生锈的,堆得小山一样,散发着浓重的机油味和铁腥气。大太阳底下白花花的,到了阴天,或是夜里,又变得乌沉沉的,有些阴森可怕。
机器的零部件犹如人的器官。只不过一个肉质,一个铁质。就像他熟稔地记住了肺叶,肝,大肠小肠,动脉血管,子宫,他也把这些名称不同尺寸不同的零件熟记在了脑子里。当然,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有一摞本子,用不同颜色的彩色铅笔画着横线竖线,标着数字,这些看着像五线谱的东西只有他自己看得懂,于别人,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
黄昏时分,他掀开琴盖,拿出小提琴来拉,并未意识到自己对家里有多少想念。虽然他几乎经常想起那幢临街的楼房,父母和弟弟妹妹。
对于他,他的母亲是极其恼怒的,他这一走了之的举动令她在医院里颜面尽失,还有这举动里藏着的对她的反抗。她很少,或者从不去想这个十七岁的儿子为什么这样,既然他先斩断和家里的关系,盛怒中她表示出放手不管的态度,让他去,他想走,就让他走。兄弟姐妹虽然不解,然而他的不回来,使得分到手的吃食比原先多了,倒成了一件幸事了。
这琴也算他的家了。遗憾的是,他的小提琴练习曲并不讨人喜欢,不仅没有优美的旋律,还太聒噪了。对那刚得温饱的身体来说竟是难以忍受的刺激。更何况还吵了三班倒的工人的好梦。被人骂过几次,他渐渐不再拉琴了。他的话音也渐渐不再有南方的柔和了,与这个集镇的人一样操着侉气十足的土音。他的胡子坚硬了,脸孔黑了,他不再是一个少年,成了一个青年了,又因为整日在露天里来去,他的青年期变得极短,一晃就过去了。还是青年的他有了中年人才有的成熟稳重,甚至于过早苍老了。
然而,他身上仍有着南方人的特征。在他落脚的北方的小集镇里,也有不少人是从南方来的。他们彼此来往,聚会,彼此沟通信息。毕竟不是这块土壤上出生长大的,不用说什么就能辨别出来。他参加过几次这种聚会,地点是更换的,往往选在朋友多,人缘好,家里条件也好的某一个人那里。聚会短不了酒菜。这小集镇虽贫瘠,在吃上竟可算豪阔,各种各样的面食,天天换着吃,吃上一个月也不重样,还有大盆的凉菜,大盘的肉菜,肉是绝不吝啬的,浇着蒜泥,辣油,各种名堂的香料,倒上酒,围着小桌子齐齐地一凑,人和人就贴得近了,各人的底细摊了出来,说话也推心置腹了。
难得,他也会滔滔不绝起来,辩论英国美国好,还是中国好;过去的政府是剥削人民的,现在的政府呢,是不是也剥削人民;台湾到底要不要解放,怎么解放。都是极敏感,甚至违禁的话题。平日说这种话几乎没有机会,气氛自然热闹。然而大家说到最后都是回去。不管有多少话题,说到最后总是回去。仿佛那世上的路,多了又多,然而走到末了,总归只这一条。和他一样出于自愿来这里的人不少,他们一样憧憬着有朝一日回去,他却是特别了,不管这一步棋是不是错着,他自己下了,就再不能反悔似的。他的兴致低落下来,不大响了,心里也越来越孤单了。
渐渐,这种聚会上不大能看见他了。
他们聚起来总要谈起他,他的落落寡合,他有时相当暴躁的脾气,对弄错他意思的手下粗暴地喊叫。他们派和他交好的人去找他。对这同乡共谊的热情,他存心冷淡似的,谁也不能再把他拉到这个圈子里来。久了,大家习惯了他的不来。他甘愿与这个群体脱离了。
他回过家,千难万难地上了楼,装作出差顺便回来转转的样子。母亲并未说什么,淡淡地问他在那边怎么样。他的话多了起来,平常在那边不屑的事,也拿来说给母亲听。一毛钱剃一个头,五分钱一个馒头,有一个北方的女的,脸孔胖得鼓起来,南方人都叫她“癞疙疤”,还有人简称她“疙疤”,那女的不知道“癞疙疤”就是“癞蛤蟆”,应得还很起劲。他自己说着也笑了。说到饿了,母亲给他盛了饭,叫他吃,关照他桌上的菜是给他弟弟留的,他便识相地不去碰那盘菜,看也不看,筷子只管往盛着咸菜的碗里伸。心里却咸涩起来,不觉跟母亲怄起气来。
他怄气的开端常常并不让人以为他在怄气,只是走路重一点,话突然少了。家里几个小的回来了,看见大哥来了,一边奇怪一边也觉着兴奋,捉着他问东问西。他的兴致恢复了一点,陶陶地感觉到回家的快乐。然而到了饭桌上,他们依然是争抢的。弟弟倒是让他吃,然而有了先前母亲的话,他绝不肯去碰那盘菜。要是第二天,母亲专门为他准备一盘菜,他的气或许就消了。母亲一早出门买菜去了,这一天他都怀着指望,然而并没有。他勤快地拖地抹桌子,打扫卫生,闲下来坐在门槛上闻着外面飘来的烘奶油面包的香气,坐着坐着,心里竟是没着没落了起来。那盘菜起先只是一个很小的引子,然而渐渐把过去那团黑漆漆地塞在他心里的东西拖了出来。说好待三天走的,待了两天就说要走。母亲问他为什么要走,他看着她脸上的惊诧,愈加坚决地要走。母亲不说什么了。父亲除了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也没有别的话。
他又坐上了回小集镇的火车。不知为什么,竟只有这小集镇才是他可以去的地方了。要不是这小集镇,他甚至不知他还能去哪里。他坐在车上,看着火车风驰电掣朝着小集镇跑着,懊丧地想着以后还不如不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下了火车。往宿舍区去的小路歪歪斜斜,有一半荒芜着,两边长着高高的茅草,远处有几间低矮的泥坯的房子。他闻着潮湿的泥腥气,这里和他刚刚离开的地方太不一样了,不一样得心里生出疑惑来,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要去哪里。然而他还是径直回了宿舍。同伴上班去了,房里还剩余着一些隔宿的暖热,他拧开水龙头,直接把头伸到龙头底下,伸手大力地抹着脸,耳根,挖了一小块肥皂粉,蘸了水抹到头上,搓出泡沫,复又低下头去冲。这浇头的冷水让他心里舒服了一点,往两边甩着头,甩干脸上的水,擦了身,换了衣裳,把自己里里外外弄了个清爽。这一个早上他存心晚一点上班去,从床底下拖出琴盒,想也没想就拉了起来。他的情绪变化着,琴声也跟着变化着。有时流畅,有时又变得极生涩了,在不曾睡醒的耳朵里,仿佛一支钝了的柴刀在木柴上苦苦摩擦着。
这一天没有人闯进来骂他,嫌琴声打搅了好梦。他拉够了,握着弓,坐在床沿上,垂头坐了半晌,把琴放到琴盒里,上班去了。这一天他格外暴躁。也格外消沉。他坐在那里,退避到很远似的,不希望别人看见他,叫他,跟他说话。他的手下无所适从,走了,走不了的也静了,心里跟他怄着气,就像他跟母亲怄气。他踱出去,踱到他种的鸡冠花、一串红跟前,他看着花,看够了,踱到角落里,到了那堆散发着机油味和铁腥气的零部件跟前站着,只有它们才懂得他似的,面朝着它们站了好一会儿,压在他心头的乌云飘散了,他心里释然了。
也不知是他到了这里第几个年头了,他身边多了一个柔顺的女人。饭后,他常常领着她去小集镇四周散步,去村里养鸡的人家买些便宜的鸡蛋。那女人温顺地跟着他。他不在时,邻居们问女人是哪里人,家里还有谁,才知道她住在隔着几个县的另一个小镇上。有一段时间,他和女人都不见了,过了一阵,又同时回来了,也是问了女人,才知道他们是去女人娘家那边结婚去了。他父母那边,先写了信,寄了女人的照片。这桩亲事他们极力反对,一个小镇上的女人,乡下的,没有文化,没有家世,由父亲执笔,写信劝他不要结婚。然而这阻止来不及了。他自作主张结了婚,把女人带到家里,住了几天。见他父母并没有替他们操办婚礼的意思,便回小集镇了。
因为结了婚,他分到一间带厨房的单间,领了张双人床,他又去集市花了些钱,添了桌椅,碗橱,女人在厨房间门口挂了碎花的门帘,很像—个家了。邻居自然换过了一批,有时听见女人在家里哭,哭声极细,幽幽咽咽,等她出得门来,却看不出什么,脸盘儿依旧像太阳花。女人尽心管着家里,再后来,女人就走了。她有了孩子,回去生孩子了。隔了几个月,女人抱来一个小孩。到小孩四五岁的时候,女人又回去了,她在那边找了个工作,又因为舞跳得好,是厂宣传队的骨干,整天忙着上班,排练,竟是难得来这儿了。
从此,这个小集镇便常常出现这一对父女的身影。
这是一对不大与人来往的父女。吃了饭,父女两个去小镇附近散步,父亲有时拉着女儿的手,有时不拉,让她在前面蹦蹦跳跳。
这女孩生得粉妆玉琢一样,父亲不会修刘海,把她额前的头发剪成一刀齐,也很好看。邻居心疼女孩,做了包子,馒头,腌了鸡蛋,照例要拿过去给她。那女孩不大会谢人,也不大喜欢叫人,不过知道冲着别人笑,笑得很甜。走在路上,常有人上来拉她的手,看看她。有时在她脸上看见手指印,通红地印在雪白的脸上,又有时,她急急地在路上跑着,不知要跑去哪儿,很急的样子,嘴噘起老高,竟像重重地挨了一巴掌,噘得两个嘴唇一般厚,让看见的人心里冷不丁冒出一股寒气。
女人走后,他又跟人打过两架。
正好是吃饭时间,吃饭的人都从家里出来了,大人小孩,捧着碗,边看,边往嘴里塞着,有的人中途菜吃光了,回去添菜,添完了再出来看。
北方的人都好打架,两句话不对,拔出拳头来就要打了。南方人更喜欢用嘴皮子。也因此南方人嘴里的话有时真的好听,有时只是表面好听,实则却阴险毒辣。那阴险毒辣的便是南方人的拳头,保护自己,战胜别人,全仰仗它。
他却不谙此道。讲不过人家,和北方人一样拔出了拳头。有人上去拉架,反而被他一拳头挡开了。看着他瘦小,力道竟是很大的。
然而他的耐力究竟不足,又竞要讨打似的,一拳一拳,直往人要害攻,惹得对方也性起了,直往他要害攻。
两个人都没好结果,打到鼻血流出,衣服破烂,脸孔青紫,疲弱中被轰上来的人拉开了。
北方人打架多不记仇,打完了一道喝酒去了这样的事也是有的。他的脾气更像北方人,也没有跟谁结下仇。有些南方人嫌他野蛮,塌南方人的台。看他的神色便有了些瞧不起,或者干脆只作不认识他一样,把他归到了下等人的一群里。他也无所谓。也有些人忌他好动手,和他打着招呼,心里畏惧着。然而他多数极谦和,极讲道理,喝酒不藏不掖,极坦率,又让他们觉得这畏惧并无必要。他棋下得好,常被人拖去下棋,或上门来切磋讨教。有一个人刚调到邻镇,也是南方人,听说他会拉琴,兴致所至,干脆拎着琴找上门来了。
那个人个子高,穿着又讲究,那讲究不是明里的讲究,而是暗里的讲究,是在衣服的质料上,剪裁上,而不是衣服花里胡哨的装饰上讲究,又拎着琴,便很器宇轩昂的样子,朴素中见着不凡的气度。见了女孩,例必在她头顶上轻轻地按一按。似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疼爱在里面。
女孩欢喜着他,然而她不大会谢人,也不大会叫人,不知道怎么叫,见他来了,便闪开去了,或是搬只小凳坐到门口。
本来他已久不拉琴了,没了拉琴的兴致,然而有人上门来找他拉琴,他还是很高兴的,把琴从床底下拖出来,两个人合奏几曲。其时正流行一支青海民歌,便把这支青海民歌用小提琴拉了出来。在邻居看来,便是他的到来使得他也拉起了这样旋律优美的曲子,路过,便朝屋里看一看,恰好撞到他也抬头,彼此就笑一笑。他穿得好,人也温和,倒和他天上地下一般,很让人奇怪这样的两个人能成了朋友。对邻人眼里藏不住的疑问,他是一概的不管,也不问,只来他自己的。等他收起琴走了,女孩回到屋里,屋里又静了下来,邻人还在哼着那曲调。这样的下午是令人愉快的,而且颇能让人回味的。他不来的下午就异常的单调了。
他不来,他也不拉琴,有时把琴拿出来,似乎要拉了,然而只拉出几个音符,一个归一个,断的,连不起来,仿佛他只是要试试看这琴有没有走音。琴经常要调音,保养的。他拿着细软的布,细细地揩着琴面上的灰。这琴是父亲从旧货商店买的,是战败的外国人逃走前三钱不值两钱贱卖的。价格极便宜。琴自然是好琴。他读书的小学有小提琴课,父亲做主给他买了下来。七岁起就跟着他,到他十七岁离开家,也算半生了。
拎着琴来找他的那人后来日趋来得少了,直到再不来了。一个南方人,突然在小集镇上不见了,便是回去了。对他来说值得庆幸。说到底,这里并不是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父母亲人都不在这里,就像折断的枝条,硬生生地要在另一块土里生出根来,未免是孤独的。
他却是一心要在这里生根了。这个小集镇上的南方人日趋少起来,这对父女的身影依旧在小镇四周出现着。女孩脸上偶尔仍有通红的指印,只是她的脸不那么雪白了,身上的肉也多了,厚实了,她似乎在强悍起来,与潜伏在他身体里的强悍暗暗做着抵抗。
冬天天乌沉沉的一个晚上,他夹着几个馒头回到家里,见她少有地倒在床上睡着。衣服也没有脱。也没有洗脸。他替她脱去衣服,把她在床上摆正,无意中摸到她的额头,竟是滚烫的。
他没有体温表,不知道烧到了几度,绞了毛巾敷在她额头上,怪她调皮,跑得热了出了汗,吹了冷风。在床上看书直看到后半夜,摸着她额头没有先前烫了,便也睡了。
第二天早上,他起来了,喊她起来吃早饭,她勉强起来了,面颊上通红的两团,吃了一口就放下了。他强令她吃,也仍吃掉了半个馒头。中午他带了退烧药回来,叫她吃了。小孩不会诈病,只要还有一点点气力,是不肯倒下的。她在家闷了一天了,吃了退烧药,稍微好一点便要下楼玩。他先是不许,想想出一身汗说不定病就好了,看她玩性实足,他便放心地上班去了。
想不到第三天晚上,她复又倒下。直到天亮仍是滚烫的,额上生出几粒晶亮的水疱,再看身上,倒没有。他原懂得一点医术的,在预科班并没有很用心地学,到了这小集镇,那点医术更是早扔光了。看她这情形,是一定要去医院了,大力地牵着她的手带她去镇上的医院。她做着梦似的,眼睛似睁未睁,踉跄地跟在他身后,手被牵住那个肩膀耸着,另一个肩膀则耷拉着,这走姿引得认识的人走过来看。懂一点的看看她的脸,拨开她额前罩着的头发看看,断定她是出水痘了。他听得出水痘反而松了口气,他倒是担心着她是不是出麻疹,甚至得了伤寒。在他心里,水痘几乎算不得是病,人人都要出一次,出过一次,便终身免疫了。
依旧是那个懂一点的人,关照他出水痘不能吹风。或许她自以为样样很懂的语气他听了极不舒服,不耐烦地从包围他们的圈子里挤出来,夹了她往医院去。一大一小过了河,那河原是被化工厂放出来的水污染过了,颜色碧绿,且发黏,散发着浓重的氨味,整个小集镇便是浸泡在这氨味里。河边几株树,枝条被风刮得忽左忽右晃动着,他迟疑一下,脱下衣服兜在她身上,自己蹲下去,把她负到背上。
到了医院,医生一看,果然是出水痘。医生也是南方人,住的地方和他家相隔不远,配了炉甘石和龙胆紫药水,叫他带回去给她搽。他唯唯诺诺答应着。不防她醒过来,问医生,她是不是要死了。医生听了笑了起来,这么小的人,哪里就会死了。她问医生能不能保证,医生说当然能保证。
她得了医生的保证,回到家里,振作地吃了半碗饭,又躺下了。下午起,热度又升了上来。
他依医生说的,在未破皮的水疱上搽了炉甘石。炉甘石淡淡的粉红色,和她的肤色一样娇嫩,搽过了留下一个白点,掩住了那水疱原本的鲜红,看上去不那么可怕了。他下午要上班,临走把门反锁了。这一去,又忙到了夜里七八点,回去的路上忽地想起她还在床上。
他开了门,她仍侧身朝墙睡着,没有动。摸着像一小团火炭。她在同样年龄的小孩子里算生得高大了,然而躺在床上,仍只一点点大,是一小团正在烧着的火炭。
他的心里温柔起来,摩挲着她的头,唤她的小名,问她要吃什么吗?她并未醒,却知道摇头,眉头微皱着,也许因为烫得难受,皱着的眉头仿佛要告诉他,她正在受着苦。
他只以为世上的苦他样样尝过了,样样无所谓了,她这眉间的一点苦因为还稚嫩着,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芽苞,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让他愕然无声。
他倒了些许水,给她嘴唇润润湿,她舔了舔嘴,不期然地唤了声“姆妈”。
这小集镇的人喊母亲都喊作娘,她说别的话与这小集镇的人一般无二,只有喊她母亲,和南方人一样喊“姆妈”。仿佛那大片的红海洋里的一点点白,于她是根基的东西,即使把她带到这里,她的根基也不在这里。
他心里一动。这一夜几乎没有睡着,只在两三点钟打了个盹。虽然医生保证她不会死,然而她咻咻地喘着气息的样子,那一口小小的气息似是随时会走,没有留给他半点可拖拽的东西。
他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
熬到早上,他给她喂了水,搽了药,检索着她身上冒出来的水疱。
上了班,他头一件事就是给女人打电话。女人那天恰好厂休,不在,接电话的人答应转告。他是急得只想骂人,也没有办法。下午他决定休息,把椅子搬到床边,坐着看着她。
到了晚上五点钟,门忽而推开了,进来的正是孩子的母亲。他的女人。他心里一宽,嘴里却责怪她怎这时才来。
女人辩解,宣传队下乡,她出去几天了,下午才回来,立刻买了票赶过来。她辩解着,放下手里的包裹,就去床前看那烧得火烫的孩子,先在额头上探了探,又跟他一样摩挲着她的头,唤着她的小名。
她睡梦中仿佛知道母亲来了,未合严的眼皮下眼睛眨着,手脚也动了动,然而睡得更沉了。
隔了一天,她身上的水痘排山倒海般涌出来,也预示她快要好转了。只是遍身搽着炉甘石,仿佛一只斑点小狗,让夫妻两个心痛。
又过了四五日,她身上的烧退了,最早一批出的水疱也开始结痂了。水痘会传染,她出水痘楼上楼下全都知道,所有的小孩都在家里被大人关照过了,不许到她那儿去,连门口也不可以去。小孩好奇心重,越不让他们去,越是想去,趁大人不在,难免脚痒,真去了,又还是胆怯的,只敢站在离门口半步远的地方,透过门缝看着她。
她听着他们在门口,却不被允许出去,在床上逗留了那么多日,恨不得马上到楼下跑一圈,也只得老老实实听大人的,不可以见风,免得染上邪气;不可以吃生酱油,将来留下疤痕,嫁不出去。
身上的痂脱去一半多时,她再忍不住了,央求出去。这一回,他答应了,电影院里放的那部片子他早想看了,提议出去看场电影。女人虽觉不妥,看她欣然要去,只得依允,拿一块透明的红纱巾,兜头把她罩住,放到他肩膀上。
她被父亲驮着,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多日未见她的人围过来,一边赶开孩子,不让他们聚过来,又为她熬过这一场苦欢然。她坐在父亲肩上,如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骄傲。所幸因为罩在红纱巾里,不便说话,他们问她的话都由她母亲答了。她一路受着注目礼,到了电影院,父亲仍把她放在膝上,她也不下来,有时朝母亲那边挤过去攀着母亲,一会儿又缩回来,安心地坐在父亲膝上。
电影开始了。剧院里黑了下来,嗡嗡的说话声小了,她很有兴味地睁大眼睛看着,毕竟刚刚痊愈,没看半场便在父亲膝上睡着了。父母也不去动她,让她睡。所以她是睡意蒙眬被父亲驮回到家里的。母亲开了门,把她从父亲身上接过去,忽而发觉纱巾不见了,在随身带的东西里翻了几遍还是没有。他断定纱巾落在电影院了,或是落在了路上。他可惜着那块结婚时买给女人的纱巾,说他去找,出了门,打着手电筒,细心地留心着脚下,朝着电影院走去。
路并不长,—会儿就到了电影院。只隔了这一会儿,电影院里只剩一个人,正弯腰扫着地。扬起许多灰。他依据灰的位置找到扫地的,问他是不是看见一条红纱巾。是他孩子罩在头上的,他孩子正在出水痘,吹不得风,到家里发现不见了。
扫地的直起腰看看他,说没看见,不相信他自己找,又弯下腰。他踩着卡卡作响的花生壳瓜子壳,从第一排找到最末一排,果然未见红纱巾的影子。扫地的劝他不要找了,谁捡到了,也多半拿回去了,落掉的东西哪里还能捡得回来。
他空落落地出了电影院。回去的路上,仍留心着脚下。说不定就找到了呢?他抱着这个念头,慢慢地迎着那排亮着灯的,低矮脏败得几近猥琐的房子走去,玻璃窗上印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贴在一起向外张望,他加快步子,心里那一股坚硬的东西退潮一样迅速地退去了,整个人温热了起来。
责任编辑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