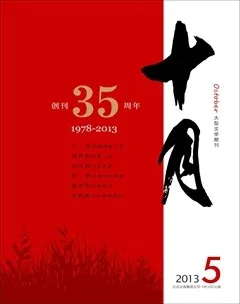小维娜和猫
2013-12-29吴文君
王弗说小维娜很美。他的腿抵着桌子的一条腿,把她横放在桌上,低头看着她,说,“小维娜,你真美,真美。”像一棵枝叶稀少的高大的树。
小维娜很满足。看着王弗的眼睛,沉浸在“此刻自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意念中。
等到两个人都静下来,小维娜说了楼下新来的猫。昨天晚上看见猫的一刹那,小维娜心里突地一跳,想起王弗的猫。虽然王弗的猫是长毛的,这一只是短毛的,毛的颜色也不一样。刚起了养一只猫的念头,楼下就来了一只猫,她的脑子闪电一样划过一个念头——这只猫跟她有关。
王弗靠在窗台上抽烟,没有对这只猫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猫也没有成为他们的话题,小维娜有点惋惜。“它太大了点。我担心养不熟了。”她说。
王弗穿好衣服,小维娜已经拿出木梳梳头了。
王弗说,“我来给你梳?”看着镜子里的小维娜。
小维娜扭过脖子笑了一笑,慢慢地把头发梳好了,穿上棉大衣,扣上扣子。
走到门口,回头又笑了一笑,拉开门,顺着走廊悄悄回到厨房。
还不到忙的时候。小维娜漫不经心地把盘子、酒杯从消毒柜里拿出来,心里依旧很满足,“刚才那一刻自己跟那个人在一起。”
如果现在轮滑俱乐部门外有一队游行的人,她马上会丢掉手里的盘子、勺子,加入到那支队伍里去,摇着旗帜高声喊一喊,唱一唱。
一头大蒜飞过来,惊醒她的春梦。她眯起的眼睛睁开了。是阿灿扔的。只有他绷着脸没笑。他是她们这帮人的头儿。
小维娜拾起大蒜照着阿灿扔回去,甩了甩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很长,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时候就甩甩头发。
小维娜是轮滑俱乐部餐厅的服务员。
过去老莴苣没有死的时候总说小维娜太啰嗦了。
她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在整理床铺上,她有两把刷子,一把软毛,一把硬毛,她先用软毛的刷掉头发碎屑,再用硬毛的刷平。出门前她还要花一个半小时化妆。如果这一天没有化妆,黄着脸就出门了,又正好碰到一个认识的人,她会懊丧死的。
小维娜从不懈怠自己的脸,她花很多时间涂粉底液,再涂上粉,再涂上口红,站到橱窗后面,有时她会笑一笑,虽然只笑一笑,那一瞬间她的嘴眼鼻子变得很生动——她就是往王弗的不锈钢餐盘里放进一只鸡腿时及时地笑了笑,才让王弗记住的。
早两三年,她用光了钱,不知道到哪里去,倚着电影院门口的大柱子,一个人看电影的老莴苣也是因为她很及时的笑把她带去喝了通茶,吹了通牛。老莴苣要回家了,老莴苣说,“怎么办呢?”丢下她太不人道了,不如跟他一起回去吧。
老莴苣不算太老,他就是一个不大多跟人交往的单身汉,住在一套很小的房子里,他有床,桌子,椅子,一个电唱机,一百多张碟片,几十本书,一个种过兰花,现在长满酢浆草的花盆。
小维娜跟着他穿过已经关了门的瓷器交易市场,摸黑走到楼上,在他肩膀上方望到一扇垂着的百叶窗,印在窗上的酷似郁金香的阴影,心里莫名其妙颤了一颤。
老莴苣过去很有钱,现在他的钱都在前妻和儿子那里,为了这些再也拿不回来的钱,老莴苣在一九九六年的冬天没有目的地在马路上连续走了四十几个小时。老莴苣经常说,人最重要的财富是自由地支配自己。这样说来,他现在还是个富翁。
有了小维娜,老莴苣不再一礼拜刮一次胡子,换一次衬衣。他干净了很多,他很满意小维娜,虽然从不去教堂,老莴苣作为老基督徒很感谢上帝把小维娜赐给他。
——如果老莴苣没有死,这样冬天的晚上,会戴上一顶蓝绒线帽,围上格子羊毛围巾,穿得厚厚的,和小维娜去江边吃饭,吃完再散一会步。他让小维娜挽着他的胳膊,像夫妻那样亲密地走在一起,谈谈他喜欢的巴赫,舒伯特。小维娜也喜欢巴赫,小维娜说巴赫的音乐像把刷子,刷遍她身体里的每个角落,老莴苣哈哈大笑。可是老莴苣确确实实死了,小维娜看着他进焚化炉的,亲手把他的骨灰装进云白大理石骨灰盒的。
小维娜只想到这里,她没有再想下去,机械地把刚蒸熟的热腾腾的饭铲到铁桶里。这些黄铜色的铁桶一会儿要运到前面餐厅去。铲着铲着,小维娜手上的劲不知不觉大了,这样她就不想老莴苣了。她也不想王弗。到了别人,特别是阿灿眼里,便是那个蒜头很有用,她要打一打才肯出力,就像不听话的小孩要刮几下头皮,她就是这么一种人。
还是那个时间。小维娜下了班,走到那里,又看见了猫,还有一个老太婆。
地上竖了块牌子,写着:我无家可归,请好心人来领养我。右下角画了一张笑容可掬的猫脸。
小维娜忍不住笑了,问也在看猫的老太婆这是谁写的。
老太婆也不知道。她吃完饭把剩饭剩菜拿过来,牌子已经竖在这里了。
“不如你把它抱回去吧。”小维娜说。老的女人,老的猫,是一对好伴。都爱打盹,都爱偎着暖炉,寂寞了,还可以跟猫唠叨几句,反正猫不会泄露人的秘密。
老太婆立刻说:“不行。猫的毛会四处乱飞,我家老头子有哮喘的。”小维娜这才知道她不是孤老婆子。她还有一个老头子,除了去医院从来不出门。
“不如你把它抱回去吧。”老太婆说。
小维娜看着猫。它仰着脸,也朝她看着。它一点不像西北角那群野猫,天一黑就仓皇地到处跑动,个个都会掀垃圾桶盖,做出倒吊金钟的姿势叼点鱼头碎骨出来饱餐一顿。
“给它饭都不要吃,嘴也太刁了,饿死活该!”一个出来散步的女人踢了猫一脚,又踢了一脚。
小维娜的心疼了一下。她真想说,“不要踢了!不要踢了!”她知道这个嘴唇厚厚的女人就住在老太婆楼下,养了一群鸡,一天到晚播弄闲话,她不想跟这种女人说什么,她知道她们背地里议论老莴苣怎么死的,她们早有一种联想——老莴苣是在小维娜住进来之后死的,老莴苣的死是小维娜害的。
小维娜不想看这样的女人,她看的是老太婆的饭——山芋皮,老头子和老太婆两个嚼干的骨头渣,这碗饭让小维娜不舒服了一个晚上。她想到了包厢的剩菜,她已经倒得麻木了,满盆的鱼肉哗啦哗啦往泔水桶里倒也不会心疼了。她心疼的是猫,而且心疼这猫的时候想到的是王弗家里那只肥嗒嗒的猫。
第二天小维娜用一个盛豆腐的塑料盒装了两块晚饭省下的鸡块回家,顺道去超市买了猫粮,把这两样东西同时摆到猫面前。
猫犹豫一下,头迅速地扎进猫粮。
“你心眼真好。”老太婆啧啧地叹着。
这句话小维娜听进去了,不过她不想说话,慢慢慢慢地挨着猫蹲下,抱住膝盖。
中午,阿灿出去转了一转回来了,告诉小维娜这个月做包厢又是她最多。一个包厢一块五,她做了八十六个,又多了一百多块进账。
“买草莓!买草莓!”小铃铛喊了起来。
小维娜看见过小铃铛去王弗那里。说不定,小铃铛也是躺在那张蒙着厚牛皮的大桌子上分开自己的。还可能在地上那张桃红的新疆大地毯上,那个大得放得下一个屁股的窗台上。
小维娜木木地站着,排风扇扇出的热气让她喘不过气来。
阿灿笑着摆摆手:“来盒烟吧,草莓你们女人吃。”
这儿他是头儿。有一天也有人叫小铃铛请客,因为老板点了小铃铛,把小铃铛叫去陪他们跳舞,吃夜宵。阿灿说:“算了,别为难小铃铛了。”
这潮汕小子,替小铃铛挡,却不替她挡。小维娜只能舔了舔嘴唇说:“我去买。”甩着头发去了。
一会儿,一盆草莓端了进来。这是冬天的草莓,红彤彤,水灵灵。小维娜从衣袋里摸出烟。十来只手快活地伸了过去。
小维娜看着小铃铛玉米须一样的鬈头发,脸色白里透红。在小铃铛面前,小维娜不由得感觉到自己的老,土气。
可是王弗说了她美的。他把她放在窗台上,让她更大地分开自己,朝着他袒露出自己。窗帘金黄的流苏搭在她腿上,如同给她穿了漂亮的裙子,王弗说:“小维娜,你真美!真美!”小维娜又骄傲了起来,她真想告诉小铃铛,“王弗说我美。”可她是不会说的。因为谁都会说她看上王弗的钱了。为什么她不能爱上他呢?他是她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啊。他总是穿着深色的衣裤,趁他洗澡的时候她偷偷摸过他的裤子,那么滑爽柔软,他的头发总是剪得整整齐齐。她除了他没有别的男人。她也不打算再要别的男人。她以前的一个女朋友曾经说过富人脾气都很奇陉,总之他们的举动并不像平常人,他不一定非要找个富有的女人做自己老婆。他爱上她也未为可知。
满满一盆草莓塌了下去,所剩不多时小维娜走开了,她还去了厕所,洗了洗手,理了理头发。她对自己很满意。她做包厢做得最多,这表示她不仅能干而且受欢迎。
她从厕所出来,看见门口扔着几个摔烂的草莓。天哪,她才走开一会儿啊,小铃铛和阿灿就打了起来,小铃铛手里高举着一个草莓要往阿灿身上扔。不过小维娜随即明白他们是在闹着玩,否则小铃铛不会笑得这么开心,她也没有真的扔,阿灿嘴里嘀咕着:“你疯了?疯了?”跳着躲闪的时候,草莓落到了他脚底下。
“扑哧”一声,地上又多了一摊淡红的浆水。像是踩烂的一坨肉。
小维娜的脸一瞬间空白了一下。
小铃铛察言观色地说:“你生气啦?”扯了扯她的头发,“不就是几个草莓嘛。”最后,小铃铛把一张俏脸搁到她肩膀上,说:“小气!”她的声音就像庙檐挂的铜铃。小维娜绷不住了,“去!”她说,甩甩头发,甩开小铃铛的头和手。
小维娜拖干净地,把沉甸甸的两只铁桶搬到拖车上,推到餐厅卸下,推着空拖车往回走。
在厨房门口,她听见一个声音说:“她干吗请客?拿到钱了?算她有钱?”
“谁知道。”是小铃铛的声音。又是“扑哧”一声。
九点半,小维娜下班了。
这夜她做了三个包厢。倒水,倒酒,添菜,陀螺一样没停过。近年夜了,餐厅的包厢间间客满。还好今天没有赖在包厢里不走的人,总有那样一些人,忘了这里是吃饭的地方,连酒也忘了喝了,只管没完没了地说话。她是没有春宵的,没有男人在家里等着她,夜里的时间长得让她发蒙,可她还是急着想早点回家。她甩着头发,在微微发红的夜色里走着。街两边的店铺慢慢稀少了,穿过关了门的瓷器交易市场,就只剩下一排排灯光暗淡的住宅楼了。
到了那里,小维娜看了看,昨晚的饭仍旧在那里,看来那只猫从昨晚到现在还没来过。
她犹豫了一下,掏出一小袋拌了肉的饭,解开绳结,一股香味迅速在寒凉的空气里飘散开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再唤上几声,它就会从灌木丛里跃出来。它跃得那样快,像道雪白的光,还没看清从哪个方向过来的,已经在她脚边了,亲热地用头蹭着她,她心里不免涌起一股温热的感觉。
老太婆说猫是最馋的,谁有吃的就跟谁走,没有良心。
小维娜无所谓它有没有良心。她并不要它感激她。它也不像有一种猫,看见一个人就跟上去黏着不肯走了。每次吃完它都会抬头叫一声,仿佛说:“我吃好了。”“我要走了。”“再见。”而不是:“谢谢你!”“你太好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小维娜把饭放在灌木旁边,拿走昨天的饭,扔进垃圾桶。她想走了,却不甘心地唤了几声,然后,她听到了微弱的叫声。
猫在围墙外新扔出来的一堆建筑垃圾上,挨着一棵树,费力地朝她扭着头,却没有朝向她跑过来。
小维娜费力地爬上去,她想抱起它,发现它的一只脚被一根长长的铁钉钉在树上。
老莴苣的照片依旧搁在柜子顶上,手交叉着盖住肚皮,看着小维娜推开门,抱着猫走进来。
“我只能把它带回来了。不然它会死的。”小维娜换了拖鞋,把猫放在地毯上,倒了杯茶,一口气喝掉,觉得气息缓和了下来。
钉子是宠物医院一个年轻的男医生用钳子拔掉的,顺便给猫打了一针,说可以消炎止痛。小维娜再三说明猫不是她的,她只是个打工的,没多少钱,男医生还是要了个高价。
送她到门口时,男医生说:“你心肠真好。”
虽然有一阵猫叫得很惨,它的痛苦远没有人的脚被铁钉钉穿那么大。它瘸着腿,好奇地闻闻沙发、茶几,舔干净半碗牛奶,来到躺椅边,观察一下后,跳了上去,眯起眼睛睡了。
小维娜看着它。
它并没有真睡着,只是向她表示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无可奈何的认可。它受伤了,它今晚没办法去往常去的地方了。它谈不上喜欢这里,它也没向她求助,是她要救它的。它没有感谢她的意思。
它让小维娜想起自己。跟着老莴苣第一次走进这里的自己。
此一刻,她成了老莴苣,猫则是她。这是一刹那钻入脑中的念头。另一个念头里,她还是她,猫成了老莴苣。他投了猫胎回来了。过去他救她,现在她救他。这样他们扯平了。这个念头实在太怪了,小维娜随即丢开不想了。她洗了澡,换上睡衣,揿着电视遥控器,盘腿坐在沙发上。
小维娜的每个夜里都是差不多的。老莴苣还在的时候也是这样,她看电视,老莴苣坐躺椅上看书。八点半老莴苣要喝一杯热牛奶,老莴苣不难服侍。他喜欢笑着说:“我是根老莴苣了,离死不远了。你还小,小维娜,你还小。”不过老莴苣不许小维娜喝咖啡,不许她在沙发上盘着腿,说女人那样不好看,而且沙发很快会坐塌掉。
现在老莴苣管不着她了。除了躺椅,柜子顶上的照片,老莴苣的东西都在一只旧纸箱里,被她推在柜子最里面。
好几次,小维娜拿掉照片,丢在旧纸箱里、放杂物的抽屉里、垃圾桶里,不管放到哪里,他都在那里呜呜地尖叫,吵得她头痛,睡不着觉,只能拿出来,放回到柜子顶上。
他要待在那儿就待在那儿吧,小维娜由着他在镜框里和蔼地看着她,跟他解释:“等它的脚好了就放它走。”
老莴苣不喜欢猫狗,动物他都不喜欢,嫌它们的毛到处乱飞,还有寄生虫。
这当然不是小维娜放猫走的理由。她看着猫,她还不习惯跟一只猫住在一起。她没有跟猫一起住过。可这个时候她不管,它会死的。她关掉灯,在窗帘透进的亮光里钻进被窝。
她今天很累,非常累。
人的身体真是奇怪,五个小时前王弗还和她在一起,现在她闻不到他的气息,听不到他的声音,也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小维娜睁着眼睛想着王弗,他的头发眼睛,他身上很好闻的味道,他在她身上动起来屁股和腰形成的波浪。他咬紧牙关,痉挛着说:“小维娜,你真美!真美!”
那一刻她是跟他在一起。
午休时分小维娜隔着玻璃看一支业余轮滑队训练。她看不出谁领先谁落后,只有一个人从队伍里退出来滑到一边,才知道他出局了,他失败了。她真想给他们来段音乐。他们背着手就像在滑道上跳舞。
小维娜看够了,回到厨房,在冒着热气的大铁锅子旁边坐下。白气里,影影绰绰露出锅盖银白的尖顶。
小铃铛丢下手里剥着的洋葱说:“我真不想干了。又累,钱又少,还不如回去干我的老本行。”
小铃铛的老本行是在酒馆卖啤酒。一个男人欺负她,阿灿替她解了围,介绍她来这里。阿灿待她就像待自己的妹妹。
小维娜问她:“你真这么决定了?”
“当然真的。”小铃铛发誓道。
“怎么跟阿灿说呢?”她多余地问。
小铃铛用手剪着额前的刘海,眼睛一眨眨地说:“我只是空想想的,我只会空想想,我不像你,小维娜,你真能干,我真羡慕你呀。”
“你羡慕我?”小维娜听了只有笑了。小铃铛是在胡说八道吧。一个人寂寞无聊了,有了秘密不想让人知道,还有对以后怎么样不知所措的时候都会胡说八道。
小维娜不知道小铃铛羡慕她什么。她应该妒忌小铃铛,因为小铃铛分走了王弗给她的东西。可是她也不妒忌小铃铛。
她渴望王弗给她一样什么东西,一样称得上礼物的东西,她很久没有这样的愿望了,她也是空想想的,机械地往不锈钢餐盘里一勺勺舀着菜。王弗的脸从众多的脸里面探露出来,小维娜就像一只准备充足汽油的小火炉轰地点着了,火把她整个撑满了,满得她像要飘浮起来。在她低垂的眼光里,他一步一步走近了,他在跟人说话,他的脸那么愉快,连唇边的那颗痣也带着笑意。她爱他的脸,他的嘴,连他的胡子头发还有那颗痣,她也觉得爱。她真怕手里的不锈钢餐盘会不听使唤失手掉到地上,里面的菜一瞬间四分五裂。
他稳稳地从她手里接过盘子,看了她一眼,转身走开了,一直走到餐厅西侧一根大柱子那儿。
小维娜看不见他了。她晃来晃去,从第一盆菜跑到最后一盆菜,问吃饭的人要吃点什么。眼前始终是那根柱子。
老莴苣的女儿终于来了。
小维娜看到她,就明白了。猫探出脸,打量着这个不怀好意的来客。
她有一张酷似老莴苣的面孔,白白的大理石一样的脸。不客气地斜了她一眼,说,“这是我爸爸的房子。”
走到屋子当中,左右打量几眼,说,“你没有权利住在这里。我的话你听得懂吧?”
小维娜把老莴苣写的“协议”拿出来。她看完了,半天没有说话,然后警告她不许带别人进来住,结婚了,就算自动放弃这里的居住权。到时不要怪她不客气。
小维娜听她下了楼,开动楼下的车,发动机轰鸣中,跟随她一起降临的黑影风一样席卷而去。
“没事了。”小维娜说。小维娜没有想哭,她才不会为老莴苣女儿的警告哭呢。这不是有人的良心的女儿。哪个女儿爸爸死都不来,却想来收他的房子。
“来,我们听音乐。”她打开桌上的迷你音响,猫坐在老莴苣的躺椅上很有滋味地舔着脚掌。沮丧的情绪在水底盘旋着盘旋着升上来,打破了她的宁静。她还是哭了。为老莴苣的先见之明。老莴苣说过这个地方他是一定要给她的。
睡梦中,小维娜听见猫在呜咽。
她披上衣服开了门,看见猫独自站在沙发上,两只前脚搭在窗台上,凝神望着窗外。
“你怎么啦?想外面了吗?”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一个晚上,猫突然发出让她惊怖的叫声。同时它走路的姿势变得很怪,把身体拉得很长,两条后腿屈起来,它就那样不满的不耐烦地用两条屈着的后腿满地爬着。
小维娜只好把它带到宠物医院的男医生那里。
小维娜很不喜欢那个男医生脸上的笑。等到他开口,她更觉得讨厌了,问男医生,“会不会因为拉不出大便?”男医生的两只眼睛在镜片后面深邃地看着她说:“没有,它是在发情。你可以在这里给它选配一只公猫,五十元一次,也可以五天后过来给它做一下结扎手术。”
小维娜思索一下,干巴巴地问医生,“它的发情期是五天吗?”
“不——我的助手结婚去了,不然现在就可以做。你知道做这种手术我必须有一个助手。”
付五十块钱,在男医生的安排下眼睁睁看着它跟一只公猫做一次爱?小维娜把猫抱了回去。
回到家,猫继续发出可怖的叫声,屈着后腿满地爬动。
现在小维娜已经能看出男医生没有说谎,猫摆出的是一个准备迎接的姿势,跟女人准备迎接的姿势一样。
不是春天才发情吗?现在还是冬天。
难道现在猫也跟人一样不分季节?想到就要?
她头痛地看着猫哼哼唧唧叫着,绝望之极后闷闷不乐趴在窗台上看着外面,用它的头,它开始愈合的伤脚试探着去推阳台上的窗。要不要送它去医院呢?她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它做了爱,会不会生一窝小猫?
但是猫好像等不及她做决定了,随后的一个黄昏,它成功地逃掉了。那天是那样的,小维娜清理完猫舍,拉开窗通风,就是那时,她的手机响了,她过去听,等她挂断电话回到猫舍边,猫已经不见了。她呆了片刻,穿上大衣,拿着手电筒下了楼。
所有的楼道都没有猫,猫也不在那片空地上。
第二天早上,小维娜又找了一遍。
小维娜扩大了搜索的范围,紧邻的两个小区也去找了。她听到两个对她的猫很不利的消息,一个是一个小区的门房吃猫,一个是此地专门有打猫的人,把活猫贩到广东去。她给两个门房都留了电话。一有猫的消息就给她打电话。她会重谢。她想吃猫的门房也许会为了钱放弃吃那只猫。
夜里,天下起了雪。
小维娜看着电视,想着这样的雪夜,猫说不定会冻死,饿死。谁叫它自己要走呢?
五天后,小维娜接到一个门房的电话——是吃猫的门房打来的,告诉她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她的猫很可能被人捉去做了皮件了。这样毛色雪白的猫可以做成一顶很漂亮的猫皮帽子,或是一只猫皮袖筒。他看到那家店里新挂出一张新鲜的猫皮。
挂断电话,小维娜呆呆地站着,看了一会儿窗外,裹上围巾,穿上棉靴,先付给门房一百块钱,随后踏着残雪去找门房告诉她的那家店铺。风把她的头弄得又冷又疼,心里摆不脱一个念头——门房吃了猫,把皮卖给皮件店,然后打电话给她,从她手里拿到一百块钱,现在她需要再花一点钱,把只剩下皮的猫买回去。
她这是在做什么?
她每一点钱都来得这么不容易。
她在做什么?
铺子开在朝着街面的一间自行车库里,小维娜下了两个台阶,走进店铺。门房形容过的墙上果然挂着一张新鲜的猫皮。
这就是她的猫吗?
小维娜在猫皮上摩挲抚摸了许久,她很想弃皮而去,却做不到,问店主多少钱她可以买下来。
店主虽然长得又粗又胖,不过她把帽子和袖筒做得很秀气。可见她手艺很好,生意也很好。她已经在这里做了七年了。她会自己硝皮子。她说这儿都是她自己干。说完这些她不说了,矜持地看着小维娜。
小维娜说她不要帽子也不要袖筒,她只要那张皮。店主说她不卖皮,但最后还是嘀咕着,把皮卖给了她。她卷起带回家,挂在老莴苣视线之外的墙上。
那个夜里,从来不做梦的小维娜做了个梦,她梦见自己坐在一辆开动的汽车里,汽车每转一个弯都会把半个车身开到路基外,让她看见下面深不可测的悬崖。下车后,她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走一步,地上现出一张猫的脸。
她告诉王弗,王弗没说什么。他的腿抵着桌子的一条腿,低头看着她。这一次他没说:“小维娜,你真美!真美!”他有点不耐烦,草草结束了,拉开窗帘,他的汽车停在外面,下午他要开着这辆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顺利的话,他要从那儿赚回四百万。再用这四百万赚回八百万、一千六百万。小维娜很后悔,不过王弗说这跟她没关系,不是她的缘故。看来他根本不在乎她的梦——反正,但愿他不要把车开出路基。最后,他摸着她的头发说,“梦是相反的,不是吗?”
小维娜轻手轻脚顺着走廊走到外面,她没回厨房,而是回了家。脱掉鞋,盘腿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着墙上的皮。
一只猫和一张猫皮还是很不一样。尽管小维娜很熟悉她的猫,还是不能百分之百肯定皮就是它的。这就给了她一个感觉,猫没有冻死饿死,没被人掳去吃掉,它自由自在地在一个地方跑着跳着,尽情地玩着,她这么想着,恍惚自己成了那只猫。
她等着阿灿打电话把她从遐想中叫回去,她会跟他说:“我就来。”“我这会儿马上来。”可是手机搁在桌上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也许阿灿还没有发现她不见了。后来她觉得饿了,于是从昏暗中站起来,准备去厨房弄点吃的。
责任编辑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