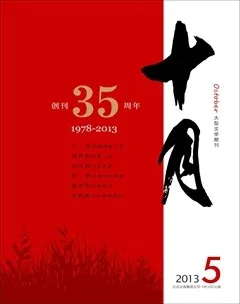果可食
2013-12-29刘照如
地瓜属桑科,落叶匍匐小灌木;茎棕褐色,有乳汁,节略膨大,
触地生细长不定根:
隐花果有短梗,簇生于无叶短枝上,埋于土中,球形或卵球
形,红色;产于我国中部和西南部;果可食。
——摘自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
我们全家人都知道很多年前发生在家里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我父亲在1949年深秋,从当时的平原省湖西区驻地单县出发,跟随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到了安徽省砀山县之后,脖子上忽然长了一个大疮。无奈之下,父亲的南下不得不半途而废。此后几年,父亲一直待在老家,甚至一生都没能再出去工作。
我奶奶说起父亲的事往往身临其境,好像父亲南下的时候她就跟在身后。奶奶说,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是在深秋里一个大霜后的早晨起程的。那天早晨父亲穿着奶奶托人捎给他的棉靴子,新靴子有点儿小,在白花花的霜地里走起路来,使他显得蹒跚或者犹豫不决。同时,走在长长的南下队伍里,父亲的脖子也有点疼。父亲认为是落枕了,他不停地扭着脖子,以为这样慢慢地就会好起来。可是往南行走了一天一夜之后,父亲的脖子上长起了大疮。到了安徽砀山县,他脖子上的大疮已经长得像馒头那么大,溃烂化脓,并且发起了高烧。这种情况下,南下大队的指挥官作出决定,让我的父亲离开队伍,返回老家。
以后的年月里,当父亲已经年老的时候,他还时常提起自己南下掉队的事。比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个冬天的黄昏,我和父亲一起走在从人民公社驻地返回村子的土路上,父亲就再一次提到了他的“南下”。那次是父亲因为修自行车被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他们这些“尾巴”们被集中到人民公社参加为期一个多月的“斗私批修学习班”。学习班结束之后,我到人民公社去接父亲回家。父亲被这个学习班弄得脸上脏兮兮的,头发蓬乱,很多天没有刮胡子,而且双眼迷离,脚步踉跄,好像他一下子就变老了。父亲说,在学习班上,他们这些人根本就吃不饱。再说了,他们吃的那叫什么?简直是猪食!除了地瓜还是地瓜,他们根本吃不上粮食。父亲说,还不如从前打仗的时候吃得好,打仗的时候,他还能吃上玉米面窝头呢。其实平时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家也都是吃地瓜,吃不上玉米面窝头,也吃不上其他的粮食,吃地瓜的时候父亲吃得也挺香。父亲说学习班上吃得不好,只不过是发泄发泄罢了。
从人民公社驻地返回村子的土路旁是一条沿路大沟,沟里还堆着一些发乌的积雪,父亲走在前头,我跟在他的身后。有一段路程,父亲一直在踢一块鸡蛋大小的砖头,他把小砖头踢到前面,等走过去的时候,再把它往前面踢。他足足把那块小砖头往前踢了一里多路。父亲是在踢砖头时提到南下的,他说得不多,声音也很低,其实是在自言自语。父亲说:“如果不是我脖子上长了那个大疮,现如今我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不管是我母亲还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于父亲南下掉队的事都耳熟能详,同时我们也对父亲、对我们自己的处境充满了同情。离湖西区干部南下的日子越是久远,我们就越是觉得那个大疮并不是长在父亲的脖子上,而是长在他的心里。当然,父亲脖子上的大疮更是长在我的心里,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不是父亲脖子上的大疮,如果他跟随南下大队去了南方,他的一生会很辉煌。尤其是想一想父亲落难的那些日子,比如说想一想他害怕被打成右派而仓皇逃往西宁、想一想他因为修理自行车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而到“斗私批修学习班”上去挨饿、想一想他在村子里为了跟人争一点自留地的边角被打断一根肋骨的那些日子,我忍不住就会想父亲的一生被耽搁了。父亲当时在湖西区的时候,是区里最靠得住的文书,而且他还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字;即便是当年跟在他屁股后面的一个小文书、他的部下,到了“文革”前,在南方做官也都做到市长了。
有一年,当年父亲的部下、后来的市长姜勇开着绿色吉普车和警卫员到我们村子里来过一次,他是专门来看望父亲的。据我奶奶说,这个姜市长当年不仅仅是父亲的部下,在他成为父亲的部下之前,父亲还曾经救过他的命。可是这两个人,都已经快20年没见面了。那天吉普车就停在我家院门外的街边,父亲迎出了大门,那个姜市长一下车,刚刚看到我父亲,就扑到父亲的怀里,抱着父亲的头哭起来。在我家大门外,街上的人都过来看热闹,父亲和姜市长两个人像孩子一样哭得不管东西南北。我知道,故友重逢,除了各奔东西、往事艰险而引起的百感交集之外,姜市长的哭声中满含着对于父亲处境的同情;而相比于姜市长的成就感和优越感,穷困潦倒的父亲在那一刻肯定又想到了南下时自己脖子上长的那个大疮。
不过有一点让我疑惑不解,姜市长和我父亲都没有提到父亲脖子上长疮的事。姜市长在我家里待了半天,吃了一顿饭,和我父亲说了很多话,天南地北,世事沧桑,却唯独没有说到父亲在南下的路上脖子上长的大疮。我非常希望他们说一说父亲脖子上的大疮,我是这样想的:也许和南下老战友说一说自己的脖子,半生对自己的脖子耿耿于怀的父亲,也许就会对那个大疮释然了。可是对于父亲的脖子,姜市长和我父亲一句也没有说。那天他们两个人坐在我家院子里的一棵大杨树底下喝了很多酒,我父亲越是喝酒,话就越多,他的脸变成了猪肝的颜色,说话的时候喉结一上一下地滚动着,但他还是不停地和姜市长碰杯。父亲每次和姜市长碰杯之后就说一大段话,每段话之前他都是这样开头的:“我这一辈子……”后来父亲喝醉了,躺在院子里不省人事。
我奶奶在瘫痪多年后于1984年秋天去世,终年84岁。我父亲1997年夏天因肺癌去世,终年73岁。父亲去世之后,我时常感到奶奶和父亲共同带走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长在父亲脖子上的大疮。在过去的那些年里,虽然母亲常常听父亲和奶奶说到父亲脖子上长疮的事,但她不一定真的知道父亲南下掉队的真相,因为她是在父亲南下掉队之后才嫁过来的。真相很可能只有奶奶和父亲两个人知道。
父亲咽气前,母亲和我们姐弟几人都在他眼前,当时我格外注意了一下父亲的脖子。有一个疑问藏在我心里,那就是父亲的脖子上到底有没有长过一个大疮。这个疑问不是父亲咽气的时候才有的,它很久以前就有。以前姜市长到我家来的时候,父亲和姜市长两个人坐在大杨树底下喝酒,我一直待在他们身边,那天我一直盯着父亲的脖子看,我没有发现父亲脖子上的疮疤。按照奶奶的说法,父亲跟随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到了安徽砀山县,他脖子上的大疮已经长得像馒头那么大,溃烂化脓,并且发起了高烧。这种情况父亲脖子上怎么会没有留下疮疤呢?
1998年春天,就是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姜市长已经回到了他的老家、我们的邻县成武县养老。他在成武县县城的东关建了房子,和老伴儿两个人安度晚年。按照我的推算,姜市长也已经至少70岁了,他肯定早已经从市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当时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犹豫再三要不要给姜市长报丧,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不让他知道。我们的顾虑一是姜市长位居高官,见过大世面,认识的人太多了,是否真的会把我们的父亲去世当回事;二是姜市长年事已高,再加上路途遥远,如果他回来给我们的父亲吊唁的话,身体会吃不消。现在姜市长从南方回来居住了,我决定去拜访他,给他说一说我父亲的事。
姜市长的房子建在县城的最边缘,院子很大,里面种满了各种花草和蔬菜,有一些花正在开,有蝴蝶和蜜蜂在上面飞舞。姜市长穿着一身淡蓝色的睡衣,手里拿着喷壶,正在侍弄那些花草。我知道姜市长已经认不出我了,就告诉他我是谁。很显然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去看望他,所以显得很意外也很惊喜,他握着我的手不松开,问我:“你父亲身体还好吗?”他的话让我无法对答,我只好顿了顿,嗫嚅着说:“我父亲,他已经去世了。”姜市长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说不上我父亲的去世对他来说很意外还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又问我:“什么时候?”我说:“去年夏天。”姜市长把喷壶重重地放在旁边的一块石板上,然后沉默了一阵子,眼睛望着院子外面的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他责备我说:“怎么不告诉我,让我好去送送他?”我解释说:“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姜叔叔已经从南边回来了。”姜市长把手按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然后引我到屋里去。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他又说:“你父亲这一辈子很不容易。”姜市长的这句话,竟让我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那天姜市长留我吃饭,我们喝了一些酒。我们一直在说我父亲的事。姜市长回忆起当时在湖西区的一些经历,好像是在说昨天的事情。那时候我父亲在湖西区做文职,姜市长和一个姓梅的女子是我父亲的部下。后来做文职的这三个人,一个去了南方(姜市长);一个落在了农村(我父亲);一个生病死在湖西区人民医院里(梅女子)。当时,他们三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墙皮,然后往墙皮上写标语。虽然我父亲只上过一年半私塾学堂,却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整个区里的所有干部都比不上他;他的文才也很好,大部分的标语都是他自己编的。总之,湖西区的干部们都喜欢我父亲。
据姜市长回忆,一开始准备南下的时候,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的名单上并没有父亲的名字,原因是父亲是独子,而我的爷爷又死得早,当时我奶奶一个人生活在离湖西区驻地单县大约180里远的农村。区里领导考虑父亲家庭的特殊情况,所以才把父亲的名字从南下大队的花名册上抹了去的。可是父亲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心里非常纠结,他曾经背着人偷偷地在河边坐了一夜,翻来覆去地考虑南下的事。虽说各种各样的情况似乎不允许父亲南下,但父亲又觉得不能跟随南下大队一起去南方巩固政权,问题很严重,同时自己也心有不甘。那时候父亲已经在队伍里混了好几年,对于一些事情的利弊权衡还算明智,于是第二天他找到区里领导,表明了自己南下的决心。就这样,父亲的名字才又被重新写进了南下大队的花名册。
我父亲南下掉队之后,却没有回到湖西区工作,而是回了老家,不久即与我母亲结婚。几年之后的1953年,平原省撤销建制,湖西区的几个县划归山东;另外几个县划归河南。这个时候,父亲原来的一些同事,忧心父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过于艰难,他们就想为父亲做一件大事。这些人又联系了原湖西区另外的几个同事和几个老上级,写了一封联名信,共同为父亲证明他当初南下掉队实属迫不得已,建议上级部门重新考虑为父亲安排工作。姜市长就是这次联名信的发起人。但是这些人为父亲的事跑了两年多,最终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了了之。
在姜市长家里吃的那顿饭,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席间,我们把我父亲的一生所经历的比较大的事情说了一遍。姜市长对我父亲的前半生比较了解,他主要是说父亲的前半生;而我则对父亲的后半生比较了解,当然主要是说父亲的后半生。在我们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姜市长两次说了我奶奶和我父亲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如果南下的时候你父亲不掉队的话,他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你们这几个孩子也不用吃地瓜长大了。”说这话的时候,姜市长的酒喝得已经有些多,他的脸、眼睛和脖子都被酒精烧得通红。
自从离开湖西区和南下大队之后,实际上父亲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为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找饭吃”。他先后到过山东的成武、菏泽、鄄城、冠县,河南的商丘、南阳,后来是安徽的蚌埠、毫县、砀山,还有山西运城、甘肃酒泉、青海西宁、江苏徐州、河北邢台,等等等等。父亲在他到的每一个地方都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们姐弟七人都还没有长大成人,奶奶年事已高,生计所迫,父亲只好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在那些数不清的陌生之地,父亲做过淘粪工、汽车修理工、卡车司机、仓库保管员、砖窑工、搬运工、过磅员和看门人,还开过自行车修理铺、杂货铺、熟肉铺以及废品收购站。
用姜市长的话说,我父亲像一只雁一样落在了农村,他落在了一片盐碱地上。我们村的土地过于贫瘠,不生庄稼,生产队每年夏季打下的小麦,分到我们家里只有一小口袋,就是这一小口袋小麦,我们也只有看一看摸一摸的份儿,那些金灿灿的麦粒子永远也不会磨成白面让我们吃,隔不了几天,我父亲就会扛着那口袋小麦到集上去,换来几大口袋地瓜干,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一家10口人才能吃得饱。一年四季、一天三顿吃地瓜,吃得我课间或者放学的路上蹲在地上吐酸水。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打嗝,课桌底下的地皮上,都被我胃里的酸水弄湿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把胃里的酸水吐在路边的沟里。
我不停地说着父亲的事,说着因为父亲南下掉队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不得不吃地瓜长大,目的是想启发姜市长,让他说出父亲南下掉队的真相。可是姜市长的话似乎总是在有意回避这个关键的地方。最后,在我和姜市长两人的饭局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只好问:“姜叔叔,那个时候,我父亲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脖子上就长了一个大疮呢?”姜市长被我问得愣了一下,他反问我:“你父亲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什么时候?”我赶紧说:“南下的时候。”姜市长皱着眉头想了一阵子,然后摇着头说:“我不记得你父亲脖子上长疮的事。”我说:“这么大的事,您怎么会不记得了呢?这事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姜市长还在沉思中。我追着说:“我父亲跟着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到了安徽砀山县,他脖子上突然长了一个大疮,像馒头那么大,溃烂化脓,并且发起了高烧。”姜市长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说:“你父亲是这么说的?”我说:“我父亲还有我奶奶,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姜市长咂咂嘴,不说话了。我盯着姜市长,希望他说一说我父亲南下掉队的事。我追着姜市长说:“姜叔叔,难道说我父亲他是犯了什么错误,被南下大队开除的吗?他脖子上根本就没有长过什么大疮,是吗?”
姜市长慢慢地低下了头,他似乎是在寻找什么恰当的言辞来应付我的追问,渐渐地,他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但是我等了好一阵子,姜市长并没有说话。于是我又说:“我父亲脖子上根本就没有长过什么大疮,他是因为什么事情偷偷跑回来的,用你们那个年代的话说,他这叫自行脱离组织,是这样吗姜叔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几年之后,你们一些人写联名信要求上级有关部门为我父亲恢复工作,事情为什么又会不了了之?上级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给一个说法呢?”
看看姜市长还是不说话,我又说:“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有很多次我父亲早晨一觉醒来,会把日子记错;这个错误也很奇怪,他总是把日子记错七天,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三天四天,是整整七天。每一次他都是这样。”我望着姜市长的脸色,他的头低得更深了。我说:“一定发生过什么大的事情,让我父亲这个样子的,是在南下的时候,对吗姜叔叔?”许久之后,姜市长说:“你父亲他,脖子上是长了一个大疮……”这么说着,姜市长的嘴唇哆嗦起来,慢慢地,他的眼里流下了泪水。我知道,姜市长和我父亲的感情很深。
父亲去世前,曾花了五六个月的时间写过一本近20万字的回忆录,题目叫《流离》。这本回忆录一直由我来保存,但我却一直没有看过它。从姜市长那里回来以后,我非常想看一看父亲的回忆录。在一个阴雨天里,我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一口气看完了父亲的回忆录《流离》。说实在的,父亲把他的回忆录取名叫《流离》,是对他一生生活状况的高度概括,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叙述他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以及在那些地方如何精打细算地挣钱,为家里10口人找饭吃。在回忆录的结尾部分,父亲对自己进行了评价,其中最让他自豪的是,他认为自己具有极强的“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的能力”。
但是就像姜市长有意回避我父亲南下掉队的事一样,在父亲的回忆录中,对于1949年深秋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的事也少有涉及。在这20万字的篇幅里,父亲倒是常常会提到南下以及从安徽砀山县返回的情景,但他始终不说明南下掉队的真正原因,仍然还是那一句:“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最终,我在父亲的回忆录中一无所获。实际上那个时候,关于父亲南下掉队是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的说法,已经被我否定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托词,父亲南下掉队一定另有隐情。
父亲去世两年以后,母亲因脑溢血后遗症瘫痪了,她只能一整天一整天地躺在床上,脑子也开始有些糊涂。我觉得,母亲离到那边找父亲的日子不远了。我还记得父亲咽气之前对母亲说过的话,老年的父亲手头宽裕了一些,他临走的时候为母亲留下了几万块钱,他的话就是对那几万块钱说的,当时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说:“你不要舍不得,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地养那些钱,等你把钱养没了,我就来叫你走。”父亲对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流着泪,他接着又补了一句:“你这辈子跟着我没过上好日子,光吃地瓜了。”母亲躺在床上脑子有些糊涂的那一年,她有时候突然就会对我说:“你去大门口看看,是不是你爹回来了?”她反复地催我离开她的床边,到大门口去看看,是不是父亲回来叫她走。母亲的一生对父亲非常依赖,父亲的每一句话她都会很当真。同时,母亲没有认为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她只当是父亲出远门去了,有一天就会回转来。
但是终于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母亲要我到大门口去看看的时候,并没有认为是父亲回来了,而是认为大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母亲还详细地描述说,那个年轻女人个子不高,身材细瘦,面目白净,穿着一身青蓝色的衣服,剪着齐耳的短发,臂弯里挎着一个蓝底白花的小布包袱。那个年轻女人站在大门外叫了我父亲的名字,问我父亲的家是不是在这里。母亲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只是觉得她脑子糊涂产生了不着边际的幻觉。可是过了一些日子,母亲再一次说,那个身材细瘦、面目白净的年轻女人又站在了我家大门外,叫了我父亲的名字。母亲的说法对我形成了刺激,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父亲的回忆录中一些零碎的片断,那些片断散布在回忆录的很多个章节里,看起来毫无关联。是母亲让我把这些片断串联起来了。
父亲的回忆录中写到了一个人。当时在湖西区做文职的父亲,手下有两个人,一个是后来当了市长的姜勇;另一个是姓梅的年轻女人。父亲在通篇回忆录中对姜市长少有提及,却有多处写到了梅姓女子。如果把父亲提到梅姓女子的片断联系在一起,是这样的:梅女子自幼父母双亡,她的叔叔把她卖到了巨野县柳林镇的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但柳林镇的这家人对她很不好;后来梅女子一个人跑到了湖西区,和养父母再无联系;到了湖西区之后,我父亲曾教会梅女子认识了一些字,所以梅女子就到父亲手下去做文职;全国解放不久,梅女子在湖西区人民医院死于伤寒并发症。
回忆录中对梅女子的具体描述只有两处,一处出现在前半部分;另一处出现在后半部分。出现在回忆录前半部分的这一处描述,却仅仅是父亲和梅女子的一次碰面。1949年的秋天,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开拔前一个月左右,一个清爽的上午,我父亲骑了一辆从区里借出来的自行车,离开湖西区的驻地单县,到邻县成武去开会。一出单县县城,在西关外意外地遇到了梅女子。梅女子是我父亲的部下,但那一天他却不知道她的行踪。两人遇到之后,相互询问对方去做什么。原来那一天梅女子是去城外的印刷所,催印区里交给印刷所去印制的年历画,本来印制年历画的事一直是父亲亲自经办的,而且他还是那幅年历画的绘画作者,但那一天他把这件事忘记了。然后他们停下来,父亲把自行车靠在小路边的一棵树上,而梅女子则倚在另一棵树上和我父亲说话。他们说了很长时间,但父亲没有写他们说话的内容,不知道他们说话的内容是不是和父亲的南下有关。
就像小说里常常出现的段落一样,父亲在回忆录的这一页详细描述了梅女子的长相、身高、穿戴打扮、神情举止等等。梅女子倚着一棵树,父亲站在自行车旁,一只手扶着自行车的车座,他们相距大约三尺远。那一阵子没有人从路上走过,四周很安静,近处的庄稼地里,有一些秋虫子在叫。在回忆录的这一页,父亲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字是,他写道:那一天梅女子穿了一件大红底衬鹅黄细格的粗布夹袄,一条藏蓝色的粗布裤子,一双黑色的千层底布鞋。那件红色的夹袄是新做的,还没有洗过水,布料精细,颜色纯正。梅女子身材娇小,肤色细白,这样的一件夹袄更是把她的脸颊衬得白里透红。梅女子的身后是一大片枣树林,当时所有的枣树上都结满了枣子,枣子把树枝压弯了,看起来摇摇欲坠。
在回忆录的后半部分,我父亲在叙述他的老年生活时,突然插入了他在湖西区工作时的经历,他在这里曾回忆到1949年深秋梅女子死在湖西区医院的情景。当时梅女子患的是伤寒并发症,在医院里已经治疗了多天。她临死的前几天,因为持续高烧及至昏迷,大部分时间她都痛苦得低声呻吟,但有时候也会清醒。无论昏迷或者清醒,梅女子临死前长达七天的时间里一句话都不说,只用极其留恋而又极其绝望的眼神看着守在她身边的人。那个时候梅女子身上和脸上起了很多的玫瑰疹,尤其是脸上的玫瑰疹,她非常在意,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看见,所以她时常抬起手来,做着无力的手势,要求护士把她的脸用手巾盖上。梅女子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她想把自己姣好的形象留给她跟前的人。我父亲没有说梅女子临死那几天他在不在她跟前,但他的描述身临其境,悲伤和绝望也在他的文字中显露出来了。
我父亲的回忆录中有关梅女子的文字只有这些。在与“湖西区”和“南下”有些关联的文字中,父亲还写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从湖西区驻地单县回家看望我奶奶,回家有180里路要走,步行的话需要两天。那一次父亲就是步行回家的。在回忆录的这一页中,父亲写到他在路上行走的双腿,他说那双腿好像不是他的,好像是两截木桩,它们不紧不慢,在机械地往前走着。这天傍晚还在路上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在雨天中行走的父亲突然发起了高烧。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父亲只好躺进了一座破庙里,他竟然在那座破庙里昏迷了七天七夜。七天之后,我父亲被一个拾粪的老头从破庙里背了出来。
重看父亲的回忆录,我看到了父亲南下掉队的真相,或者说我对父亲南下掉队的真相有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断:1949年深秋,我父亲跟随平原省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到了安徽砀山以后,无奈之下不得不半途而废,重新返回湖西区;可是父亲的脖子上根本就没有生过大疮,那时的父亲年轻、生龙活虎,他返回湖西区,是因为一个姓梅的女子突然生病住进了湖西区医院,父亲回去是要照顾她;20天以后,梅女子因伤寒并发症死在湖西区医院里,而我的父亲则因为过度悲伤和疲劳,在梅女子病逝后一连昏迷了七天七夜;等父亲醒来时,梅女子已经入土;父亲从安徽砀山离开南下大队,并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他是偷偷跑回来的,从此,父亲“自行脱离组织”。
梅女子死后,父亲直接回到了老家农村。父亲回家那天,雨已经下到第八天了,院子里的一截圆木上长满了黑木耳。几只鸡趴在鸡窝里,咕咕地叫个不停。因为满地泥泞,再加上好几天的行程,我父亲在路上走掉了一只鞋,他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站在了我家的堂屋门口。
过了三天,雨还没有停下来。奶奶和父亲两个人坐在堂屋当间,望着屋外纷纷扬扬的小雨。奶奶问父亲:“你真的不能再回湖西区了?”父亲说:“娘,我不能回了。”奶奶说:“不回湖西区,你一辈子打牛腿,吃地瓜。”父亲说:“娘,我知道。”停了一阵子,父亲开始慢慢地用双手抱住了头。奶奶又说:“前些日子,大王庄你二舅来给你提亲了。”父亲双手抱着头,眼睛盯着外面,没有说话。随后,奶奶把女方的情况说了一遍,再问父亲:“你见见那闺女不?”父亲说:“娘,你见了吗?”奶奶说:“我见了。”父亲说:“娘,你见了就行了。”奶奶又问:“那你同意这门亲了?”父亲反问奶奶:“娘,你啥意见?”奶奶说:“我没意见。”父亲抱着头,说:“娘,你没意见,我也没意见。”奶奶和父亲两个人说的是我的母亲。那一年年底,我母亲就嫁过来了。
1999年秋天,就是在首次拜访姜市长一年半之后,我又一次来到姜市长的家。这次拜访姜市长的目的,是想在姜市长那里印证我对于父亲南下掉队真相的推断。我觉得,这次当我把梅女子的事情说给姜市长听的时候,他一定会配合我,甚至还会说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有关我父亲的事情。但我去得不巧,我到了姜市长的家,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两个多月。姜市长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我去的那一天,他的亲人正在给他过“十七”。我和姜市长的亲人一起祭奠了他。
从姜市长家里回来,我的心里有些空落。关于我父亲南下掉队,知道真相的三个人,我父亲、我奶奶和姜市长都去世了,而我的心里却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情。于是我再次翻出父亲的回忆录《流离》,利用一个双休日的时间重读了一遍。这次读《流离》我有一个大的发现,我发现父亲的回忆录写得零乱、含糊其词,甚至于有些扑朔迷离,原原本本的一件事情,他却要这里写一笔,那里写一笔,像是把一捧豆子撒在簸箕里。或者说父亲的回忆录像是一副扑克,每一次打开它,它好像都被洗过牌,它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我面前。我知道,父亲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很可能是在尽力回避着什么,或者言不由衷。
从父亲的回忆录中可以读出,他从湖西区回来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寻找两样东西。父亲首先写到他莫名其妙地丢掉了一样东西,然后就是寻找,找了大半生。他没有说明那是一样什么东西,按照他的描述,那东西像是一块布。但多大的一块布呢?一块布可以是一块手帕,也可以是一条床单。父亲也没有说明那样像是一块布的东西是怎么到手的,又是怎么丢掉的,他写的只是他在不停地寻找那东西,很多时候他找它的时候心神恍惚,像是丢掉了自己的影子。有时候,比如说阴天下雨的时候,父亲待在家里没有事干,他就会利用一整天的时间翻箱倒柜地找。父亲找那丢失的东西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它不可能丢掉,它跑不远,它就在家里,我能闻见它的味儿。”我小时候常想,父亲要找的东西有味儿,那么它很可能是一块饼子。
父亲的回忆录中说,他在梦中常常会找那个东西,他写到了其中梦境非常清晰的一次。梦中的那一天,天空飘着小雨,地上满是泥污,在泥污和水洼上面是一些稀稀拉拉的稻草,那些稻草好像是有人故意撒在泥污上面的。是在一条河的岸边,父亲拿着铁铲在田地里刨地瓜,刨了一阵子,就刨出了要找的那个东西。那东西被一层布包着,但布和里面包着的东西都已经被泥水浸透了。打开来看,却又不是他要找的东西,而是一沓冥币,冥币都被泥水浸烂不能使用了。在梦中和在清醒后,父亲都认为这个梦很不吉利。
父亲要找的另外一样东西是我爷爷的尸骨。在父亲很小的时候,我爷爷到东北逃荒,结果饿死在吉林省梨树县境内的一条河边。一同去逃荒的我二爷爷没办法把爷爷的尸骨带回家,只好把爷爷埋在河左岸漫滩的一棵柳树下。几年之后,当我父亲和我二爷爷再次来到梨树县的那条河边时,却再也找不到我爷爷的尸骨了,因为在这之前梨树县发过大水,当时河水漫溢,田野和农舍都被大水淹没了,河道、河漫滩、河岸、长在河岸和河漫滩上的树以及周边的田野和农舍都大变了模样,我二爷爷认不出掩埋爷爷的尸骨时作为标记的那棵柳树了。他们两个人沿着那条河的左岸走了几十里路,见过很多模样相仿的柳树,每见到一棵柳树,父亲就问二爷爷这一棵是不是,但在每一棵柳树跟前二爷爷都点头,随后很快又摇头。他们还试着在二爷爷模棱两可的几棵柳树下挖了深坑,却没有挖出人的尸骨。在此后的很多年里,直到父亲老年,他一直在偷偷地攒钱,钱攒够了,每隔三五年他都要去一次吉林省梨树县的那条河边,去寻找一棵柳树,而每一次都是空手而归。
每一次从吉林省梨树县回来,我父亲都要病一场。他的病程是半个月左右,唯一的症状是发低烧,不耽误吃饭,也不耽误睡觉。父亲发起烧来,喜欢去我们村子前的万福河边蹲着,如果他是早晨去万福河,就在那里蹲到吃中饭,如果他吃了中饭去万福河,就在那里蹲到天黑。我们都不敢去河边叫他,因为逢到这种时候,他一句话也不会说,任凭我们站在他身后喊破嗓子,他连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的。到了吃中饭或者到了天黑,我父亲自己就会乖乖地回家来吃饭,他的胃口也不差,一块地瓜三五口就下肚了。
父亲一生中一共去过吉林省梨树县七八次,他回来后发低烧蹲在万福河边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经历了七八次。头两次,我母亲曾要求父亲去看一看医生,但父亲不愿意去看医生,他说发低烧不会死人,只有发高烧才会死人。母亲就不再催父亲去看医生。后来的几次,父亲从吉林省梨树县回来,母亲知道他又要发低烧了,而且他发低烧又不去看医生,母亲就在地瓜面里面掺进去一点粮食面,单独做给父亲吃。但我父亲不吃母亲单独做给他的饭,他说他自打湖西区回来之后,就是吃地瓜活过来的,现在为什么又要吃一顿不同的饭呢?难道说吃了这一顿不同的饭,以后就不用再吃地瓜饭了吗?
父亲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几次吉林省梨树县之行,其中有一次写得很详细。他写那一次如何坐火车来到吉林省四平市,从四平火车站步行到四平长途汽车站,然后倒长途汽车到梨树县。到了梨树县已是傍晚,父亲花一分钱买了一碗大叶茶,就着自己带在身上的地瓜面窝头吃了一顿晚饭。饭后在夜色中,父亲又步行赶往20多里以外的一个名为黄岗的小镇。当晚,他住在黄岗镇的“供销社招待所”。这个名为黄岗的小镇境内,就是那条让我父亲牵挂了一生的小河,小河的名字叫“古柳”。
像过去很多次一样,父亲沿着古柳河的左岸走了几十里路,也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一无所获。父亲写道,当时正是暮春,没有风,柳树上的枝条纹丝不动,但有很好的阳光照射下来,阳光让人的后背暖洋洋的。那时候河岸和河漫滩上的柳树正在飘飞着柳絮,按照父亲的说法,那些柳絮大朵大朵地像棉花一样飘飞在半空中,地上也有厚厚的一层。不长时间,父亲的头上、身上都沾满了柳絮。父亲从河堤或者河漫滩上走过,地上的大团柳絮被他带起来,在他的脚下打着旋儿。
父亲不知道在哪儿能够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他的心里毫无目标,一眼望去,地上白花花的一片。河漫滩上尽是青草和小树,那些青草和小树的枝叶上也都沾着柳絮。父亲就在一片青草里躺下来,望着天,一躺就是几个时辰。后来,柳絮渐渐地把父亲埋了起来。在回忆录的这一页中,父亲写自己躺在河漫滩的青草里并且被柳絮埋起来的时候,提到了当地的一个民间传说。传说说的是很久以前一个名叫白娥的姑娘、一个名叫赵明诚的青年和一棵柳树的故事,父亲的回忆录中并没有复述这个民间传说,只说因为这个传说,当地人管柳树不叫柳树,而是叫作白娥树。
父亲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几次吉林省梨树县之行,每一次都描述了躺倒在河漫滩的草丛里的情景,就连1992年的那一次也不例外。1992年夏天,父亲曾带我去过一次梨树县。和父亲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很相似,我们坐火车来到吉林省四平市,然后倒长途汽车到梨树县,住在县城北边的一个小镇上。那个小镇的前面,就是我们要找的河。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在小镇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我们去那条河边。我记得那一次父亲也在河漫滩的草丛里躺了一个时辰,回旅馆的路上,父亲对我说起了爷爷。他是这么说的:“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我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长啥模样。”停了一会儿,父亲又说:“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一个人很孤单。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这几十年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回旅馆之后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返回了。
但是1992年夏天的那次梨树县之行,我能够记得梨树县县城北边的那个小镇名字并不叫“黄岗”,而是叫“太平”。我们去的那条小河,名字也不叫“古柳”,而是叫“茂川”。父亲错把“太平镇”写成了“黄岗镇”,把“茂川河”写成了“古柳河”。当时在阅读父亲的回忆录时,我并没有在意他的这个错误。我觉得父亲一生去过太多的地方,那么多地名会像蚂蚁一样在他的脑子里乱爬,弄错一两个地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过了两天我的想法就改变了,我又觉得父亲一生去过那个叫“太平镇”的小镇和那个叫“茂川河”的小河七八次,每一次他都躺倒在茂川河河漫滩的草丛里,寻找不到我爷爷的尸骨,他的一生不能释怀,怎么又会把他铭心刻骨的一个小镇和一条小河的名字记错呢?
这次重读父亲的回忆录之后不久,我因公出差去单县。单县县城是当年平原省湖西区的驻地,所以县里的博物馆陈列着大量有关湖西区的资料,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张湖西区的行政区划图。在这张湖西区行政区划图上,在县城正南大约十里的地方,赫然标着“黄岗镇”和“古柳河”的字样。也就是说,我父亲回忆录中提到的“黄岗镇”和“古柳河”并不在吉林省梨树县,而是在湖西区的驻地单县。我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当年的湖西区医院就在黄岗镇的古柳河岸边。这让我再一次想到了梅女子。当年,梅女子因伤寒并发症死在湖西区医院里,而我父亲在梅女子死后昏迷了七天七夜,因此没有能够送梅女子入土。最有可能的是,古柳河的河漫滩曾经掩埋过梅女子的尸骨,而后来我父亲却怎么也找不到它。
那天处理完公事之后,我让单县当地的陪同人员带我去了一趟黄岗镇的古柳河。我站在古柳河的岸边,看到河岸上、河漫滩上甚至河道里,到处都长满了柳树。只是这次我来到古柳河的季节正是冬天,柳树的叶子都已落尽,满目的柳树都只剩下树干和枝条。河道里也没有水,却堆满了厚厚的一层枯叶。那天我站在枯枝败叶满目萧条的河岸边,尽力想象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的河岸暮春景象。那个柳絮飘飞的季节,父亲的世界白花花一片,那些大朵大朵的柳絮被父亲赋予了生命似的,贴住他的身体或者跟随他的脚步飞舞。有一刻我甚至感觉到,站在父亲的河岸边,在父亲的世界里我难以回归现实了。
在古柳河的岸边不远处,隐约可以看见几间旧房子。当地陪同人员告诉我说,那几间房子就是当年的湖西区人民医院,1950年以后医院就废弃不用了。后来房子拆掉重建,改为养马场。再后来养马场承包给一户村民,现在承包人在那里改建成了苗圃。我看了看那个苗圃,离古柳河的河岸大约不到两公里的样子,那里的确是一片一片的比庄稼高不了多少的树苗。我问那个陪同人员:“听说当地人叫柳树不叫柳树,叫白娥树,有没有这回事?”那个陪同人员笑了笑,指了指河岸上那些柳树说:“有这回事,他们都管柳树叫白娥树。”我接着说:“对柳树的这种叫法来自于一个民间传说,说的是很久以前一个名叫白娥的姑娘、一个名叫赵明诚的青年和一棵柳树的故事。”那个陪同人员又笑了笑说:“前几年文化馆印了一本书,《单县民间故事集成》,那里面就记载了这个故事。”
离开单县几天之后,我突然想到在我很小的时候,村子里流传着有关我父亲的一个笑话。说的是有一年深秋父亲被抽调,随村子里的其他人一同到外县去挖河,结果父亲实在吃不下那个苦,挖河的时候累哭了。见到他哭的人说,父亲蹲在河岸边哭了很长时间,他的泪水把两只裤管都打湿了,他的声音像牛犊子在叫。后来挖河的人回来了,父亲的这个笑话又被他们带回了村子里,他们把父亲挖河累得蹲在河岸边哭的事添油加醋,传得有鼻子有眼。但那时我不相信他们那些人说的话,我认为把父亲的裤管打湿的是露水,而那声音真的是牛犊子在叫,因为如果父亲蹲在河岸边的话,河岸边就有耕地,耕地里就有牛犊子。
父亲的这个笑话还有一个版本,说的是父亲在挖河的时候哭,那并不是累哭的,而是吓哭的。因为他们挖河的那些人,在河漫滩的某一段,挖出了很多尸骨,骷髅满地都是,腿骨和肋骨横七竖八。在这个版本中,他们说父亲是躺在有尸骨的烂泥里哭的,他哭的时候浑身打着哆嗦。有几个人想安慰一下父亲,让他爬起来,可是发现父亲的身体完全不听使唤,父亲的身体也像是一摊烂泥,根本扶不起来。在场的一个上了些年纪的人指着烂泥里的父亲说,这样的事情他以前见过,“这个人可能是胆子太小,他是被那么多的孤魂野鬼吓着了”。
有关父亲的这种笑话,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说一说听一听也就过去了,没有人过于当真,也没有人过于追究它的真实性。可是我母亲好像相信父亲是蹲在或者躺在万福河岸边哭了,她在街上听到有人说父亲挖河累哭或者吓哭的事,回到家里脸色通红,骂那些人是“孬孙”“不得好死”。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浑身打着哆嗦,就像父亲躺在河漫滩有尸骨的烂泥里打着哆嗦一样。
正是那一次,父亲挖河回来不久,被村子里的二柱打断了一根肋骨。那个时候我们家的自留地和二柱家的自留地挨在一起,有一天父亲发现二柱用铁锨翻地的时候,把两块自留地之间作为界线的田埂往我们家的自留地里弯了一个大肚子。父亲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两个人就发生了口角。本来平时父亲和二柱的关系还不错,发生口角也不至于动手。在双方激烈的言辞中,二柱突然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而且他还在父亲的追问下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是二柱这句话让父亲忍无可忍。二柱说父亲的那句话是:“你个孬孙,你挖个河都能累得躺在烂泥里哭。”父亲说:“二柱,有种你再说一遍。”二柱又说:“你就是个孬孙,你看见个死人骨头都能吓得躺在烂泥里哭。”是父亲先动的手,“二柱,你不得好死!”父亲一边这么喊着,一边用铁锨朝二柱拍了过去。但是二柱年轻,身体灵活,他侧身一闪,躲开了父亲的铁锨。接着,二柱的铁锨朝父亲拍过来。
吉林省梨树县太平镇茂川河的河漫滩上埋着我爷爷的尸骨,山东省单县黄岗镇古柳河的河漫滩上埋着梅女子的尸骨,这两个人的尸骨父亲一生都无法找得到,这让他无所适从。父亲一生中的七八次吉林省梨树县之行,有几次或者至少有一次是一个谎言,那几次或者那一次他并没有去梨树县太平镇的茂川河,而是去了山东省单县黄岗镇的古柳河。去古柳河的那几次或者那一次,他找的不是我爷爷的尸骨,而是梅女子的尸骨。又过了一些年,那一年深秋,我父亲随村子里的其他人一同去挖河,他们去的正是单县,挖的河正是黄岗镇的古柳河。他们挖古柳河的时候,挖出了很多人的尸骨,但父亲分不清哪一个是梅女子。
2003年年底,瘫痪多年的母亲再次突发脑溢血,昏迷18天后去世。好几年的时间里,母亲一直躺在床上,脑子也一直有些糊涂,但她发病前的几天,脑子突然清醒了。母亲不愿意让我离开她的床边,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她想和我说说话。母亲对我说了很多,她的这些话时断时续,并且不断地重复,但整体上看又充满逻辑性。她说了差不多一天一夜,说累的时候,我就让她睡一会儿,但她睡不安稳,只要有一点轻微的响动就会醒过来。
那天,母亲对我说了三层重要的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她死后,希望我们再也不要说“如果不是我爹南下的时候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我们也不会天天吃地瓜”之类的话。这样的话,以前我奶奶说过,父亲本人说过,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说过,只有母亲从来不说。母亲认为我们的父亲南下掉队是被迫无奈的,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继续跟着南下大队往南走,他人一辈子根本就活不好;再说了,母亲反问我说:“你知道当时南下的那些人,到了南边之后活下来几个吗?”如果父亲死在南方呢?哪里还有这个家?
母亲说父亲一辈子对她都很好,这是她要对我说的第二层重要的意思。母亲说,父亲一生到过很多地方,那些地方多得数也数不清,但是无论父亲走到哪里,母亲都愿意跟着他,一步也不愿意离开。母亲认为,父亲的一生失去了很多,他需要人好好地疼他,而母亲一步一步地跟着父亲,就是想好好地照顾他。在母亲的印象中,除了父亲几次去吉林省梨树县寻找爷爷的尸骨之外,其他逃荒糊口之类的远行,她都跟在父亲身边。只有两次,父亲是孤身一人出远门的。
一次是1957年夏天至1958年夏天,父亲只身一人在青海省西宁市待了一年。1957年夏天反右派开始之前,父亲提前得到口风,知道有人想把他搞成右派。父亲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以前他在湖西区工作的那几年,让他明白只要是政治的问题一律非同小可,所以父亲知道自己要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很害怕。当天晚上,父亲脸色蜡黄,他的手也有些发抖,在床沿上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无奈之下,母亲出了一个主意,她鼓动父亲连夜跑掉,跑得越远越好。这一次父亲出门连行李都没有带,他像一只被追打的老鼠一样一头撞进了黑夜。
半个多月的行程,几经周折,我父亲来到了西宁市,经朋友介绍进入青海汽车制造厂做临时工。两个月之后,父亲受到厂长的重视,让他带着厂里的六个家属开了一间自行车修配门市部。还是在1955年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在安徽省砀山县拜过一个年老的自行车修车匠师傅,学过半年修车,没想到来到西宁又派上了用场。虽说父亲只学过半年修车,但他的技术却很精,不长的时间里,几乎全西宁市的自行车有了毛病都到父亲的门市部去修理。这个自行车修配门市部不但为厂里养活了六个家属,每个月还向厂里上交一些钱。
和我奶奶一样,我母亲说起父亲的事往往身临其境,好像父亲在西宁的时候她就跟在他身边。母亲说那间自行车修配门市部开在西宁市的东门附近,离汽车制造厂很远。门市部店面不大,父亲的吃住都在店里,而汽车制造厂的那几个家属一到下班都回家了,所以父亲一个人很是孤单。为了把挣的钱攒下来寄回家里,父亲舍不得吃好的,他经常跑到农贸市场买一些地瓜干,回到店里一个人用盐水煮了吃。在西宁的那一年,父亲很少说话,为人低调,害怕言多有失。他最不愿意说的是自己的来历,如果让人知道他是谁,在西宁也会被打成右派的。
西宁的气候温差很大,白天干活的时候汗流浃背,到了晚上却很冷。父亲只有一床薄被子,就连这床薄被子,也还是他从家里跑出来的那天,母亲追了半里路硬塞给他的。在西宁的那些日子,因为舍不得买被子,晚上父亲只好和衣而睡。很多个夜晚父亲都因为害冷睡不着觉,他脑子里经常有差点成为右派的恐惧和盘算着如何攒钱寄回家里。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家属去敲门,那个家属是一个寡妇,她就在自行车修配门市部里跟着父亲干活。那天晚上寡妇在门外站了很长时间,找借口让父亲开门,可是父亲就是不给她开门。此后还有两个晚上,那个寡妇又去敲过父亲的门,父亲还是不给她开门。就是这样,父亲在西宁度过了一年。
关于这个寡妇和那天晚上她去敲门的事,父亲的回忆录《流离》里面也有描述。父亲的回忆录中说,那天晚饭他多吃了半个窝头,结果胃里有些不舒服,寡妇去敲门的时候,他已经睡下了。后来有一个声音在门外叫他,他一下子就听出了那个人是谁。父亲的言外之意,好像对于这么一个晚上那个寡妇去敲门的事早有预感。父亲的额头上冒了一层细汗。
父亲躺在被窝里,隔着门和她对话。那个寡妇说:“老刘,你睡下了吗?”父亲在被窝里动了动身子说:“我睡下了。”那个寡妇说:“我觉得你很冷,我拿了一床被子过来了。”父亲说:“我不冷,谢谢你。”那个寡妇说:“可是我觉得你冷。”父亲说:“我真不冷。”那个寡妇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又说:“老刘,你把门打开,我把被子给你。”父亲说:“谢谢你,不用给我被子,我不冷。”那个寡妇没了动静。父亲折起身听了听,仍然没有动静,他就以为她已经离开了。可是那个寡妇并没有离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老刘,你开门,我把被子给你,我老是在外面站着很冷。”父亲说:“我不冷,用不着被子。你要是觉得冷就赶紧回去吧。”那个寡妇说:“你这个老刘,你真是一个不知道冷的人。”说完,她又恶狠狠地补了一句:“你个老刘,冻死你活该!”
母亲要说的父亲第二次单身出门的事发生在1969年冬天,那一次父亲是去了安徽毫州,时间也只有6天。那一年冬天,父亲用两张野兔皮意外换得15斤豌豆,正巧,那几天我家里来了一个亲戚,听那亲戚说,当时在安徽毫州有一个关于豌豆的传说,这个传说搞得毫州人拿一碗豌豆烧香磕头,顶礼膜拜,所以毫州的豌豆在黑市上居然卖到了5毛多钱一斤,几乎和猪肉一样贵。而那个时候毫州的地瓜干,一斤却只卖到3分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父亲暗自高兴了一阵子,他很快算好了一笔账:如果把这15斤豌豆带到毫州卖掉,然后拿这个钱再在毫州买地瓜干带回来,地瓜干居然能买到260多斤。这样,再算上家里已经储备好的500多斤地瓜干,剩下的大半个冬天,一家人的口粮全有了。
但是父亲的这笔账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毫州之行来回的路上不能产生任何盘缠。无论是15斤豌豆还是260多斤地瓜干,它们统共就值8块多钱。一般情况下,空手去一趟300里地开外的毫州,8块钱只作为盘缠都不够,更不用说这样去讨一次荒了。不过父亲有自己的主意,他是这样规划毫州之行的:第一,骑自行车去,一天骑300里,当天赶到,第二天变卖豌豆并且购买地瓜干,第三天返回。这样可以不必乘坐长途汽车,不用花车票钱。第二,自带一床棉被,当天的晚上和第二天的晚上都可以睡在免费睡觉的毫州汽车站候车室里。这样就不用住旅店,省去了住宿费,自带的那床棉被回来的路上还可以盖在几麻袋地瓜干上遮挡风雨。第三,自带足够多的地瓜面窝窝头,不在饭馆吃饭,不会因为吃饭花钱。如果时间耽搁在回来的路上,也不会饿着,从毫州带回来的那260多斤地瓜干想吃就吃。这样盘算好了之后,父亲骑了一辆“大金鹿”自行车,踌躇满志地去了毫州。
父亲用自行车驮着260多斤地瓜干从毫州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那场雪下在傍晚,下得很急,大约只用了一个时辰,地上的积雪已经有一尺多厚了,但是大雪仍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当时父亲被大雪围困在河南商丘以北、山东曹县以南的黄河故道里,那个地方离家只有不足一百里路了。父亲的自行车骑得快,一开始下雪的时候,他脑子里全是尽快赶路、在雪下大之前赶到家的想法,但是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父亲的想法还是赶不上老天爷的想法快。黄河故道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上已有一尺多厚的积雪,积雪下面又是土质松软的淤沙路面,结果父亲的自行车比一辆老牛车还要沉,他一步也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晨,父亲被曹县仵楼人民公社前郭庄大队的郭老九遇到,他把父亲救回到他的家里。郭老九遇到父亲的时候,父亲的自行车已经歪倒在地上,并且大雪已经把自行车和那几麻袋地瓜干掩埋起来了。郭老九扒那些麻袋,扒出一床棉被,棉被里面裹着我父亲。当时父亲全身僵硬,动弹不得,也不会说话,只能轻轻地哼哼几声。郭老九一看就明白了,冻僵在这里的这个人,是去南边的毫州讨地瓜干的,因为前些天常常有一些从毫州回来的人骑着自行车驮着麻袋从这里路过。郭老九把父亲背回家,一路上不停地重复一句话:“你这个人,你不要命了吗?为了吃你就不要命了吗?”后来在郭老九的家里,父亲醒过来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说这句话:“你这个人,你不要命了吗?你一个人出远门,不要命了吗?”在郭老九家,他们给父亲烤火,喂他喝姜汤,给他盖三床棉被。四天之后,父亲才缓过劲儿来,最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在郭老九家的第二天,父亲曾向家里拍过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才是母亲叙述父亲毫州之行的重点。在郭老九家的第二天,父亲已经能够含糊不清地说话了,他把郭老九叫到身边,费了好大力气才终于把他的愿望表达清楚。那时候父亲的手还不能屈伸,所以他的手抚摸着郭老九,就像板刷子在刷着郭老九的胳膊。父亲是求郭老九到仵楼人民公社驻地的邮电所去一趟,帮他拍一封电报。后来我母接到的那封电报的内容是:“曹县,仵楼,平安。”可是同样是因为大雪封门,电报也不能及时送达,母亲接到那封平安电报的时候,父亲已经先于电报到家了。
父亲在郭老九家里住了四天,四天之后,他在雪地里推着一辆空白行车,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回到了家里。父亲在郭老九家里吃了四天饭,还花了人家两块多的电报钱,再加上救命之恩,所以父亲把260多斤地瓜干全部送给郭老九,一点儿都不为过。父亲到家那天是个大晴天,积雪开始融化,屋檐上往下滴着雪水,院子里已经积水成片。也不知道在路上摔过多少个跟头,父亲满身泥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父亲进门之后在院子里叫了一声母亲:“羔子他娘。”然后,他的身体像面条一样软软的,和自行车一起倒在一片雪水里。
母亲说完父亲的西宁之行和毫州之行之后总结说,父亲一辈子心里都装着她。如果心里装着一个人,那他做很多事情就都不一样了。母亲反问我说,如果父亲心里没有装着她,他在西宁的时候会不肯给那个寡妇开门吗?要知道,那个寡妇抱着被子去敲父亲的门,敲了三次,三次父亲都是用同样的话回答那个寡妇的。母亲说,像父亲“这样的男人很少见”。还有,父亲为了260多斤地瓜干去毫州拼命,那260多斤地瓜干统共才值8块钱,父亲舍不得吃,舍不得住,舍不得坐汽车,却舍得花两块多钱给母亲拍电报。说到这里,母亲哭了,她的泪顺着眼角滴在耳窝里。
母亲去世前要对我说的第三层意思,说的是父亲一生都在寻找的那块像布一样的东西。那块东西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拥有过,后来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父亲找它找得心神恍惚,像是丢掉了自己的影子。父亲闲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他会利用一整天的时间翻箱倒柜地找,他在晚上做梦也在找那个东西。母亲说,父亲找了一辈子的那个东西,并没有丢失,而是在她和父亲都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她藏起来了。母亲一直觉得她这样做很对不起父亲,但是又没有别的好办法。随后母亲告诉了我那个东西藏着的地方,并且嘱咐我,等她死后,她和父亲合葬的时候,把那个东西找出来放在父亲的身边。母亲的意思,这一辈子是没有办法,所以只好藏了父亲的东西;到了那边,她不想让父亲再一辈子去找它了,让父亲随他的意吧。
按照母亲的提示,我在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下挖出了那个东西。那东西被母亲埋得很深,我挖了足足三尺深才把它挖出来。东西装在一只釉面陶罐里,陶罐的盖口那儿还被蜡封着。我打开釉面陶罐,轻轻地从陶罐里外往掏。拿在手里的东西像是一本薄薄的书,最外面包着一层厚厚的桐油纸,是那个年代用来制作雨伞的那种桐油纸。由于在地下埋得时间太长,那层桐油纸已经发黑了。第二层包装还是桐油纸,只是比第一层桐油纸薄了一些,呈现出的是一种黄灿灿的颜色。最里面的包装是一层淡绿色的缎子布,布面上绣着一些深绿色的花草。以前母亲常说,她和父亲的一生过的都是“穷得恨不得啃泥、一分钱掰成八瓣花”的日子,可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她居然用釉面陶罐、缎子布和桐油纸这些值钱的东西把她要藏匿的东西封包起来,从这一点也足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在母亲心里有多么重要。
被包了三层的东西,是细心折叠起来的一张年历画。这是一张由当年的平原省湖西区在1949年发行、1950年使用的年历画。年历画的上半部分是日历,日历的最上端印着一行大字“一九五0年(夏历庚寅)”,上端右侧印着另一行大字“国历节气”和“夏历节气”。年历画的下半部分是一幅水粉画,画面上共有男女老少一家八口人,他们正在包饺子过年,每个人物都喜气洋洋,安乐祥和。水粉画的绘画水平不算很高,但作者让画面洋溢出了大喜,让人很容易进入画面所呈现出的氛围里,理解到那些从1949年走过的人,每一个人都将会在1950年过上平安和富足的日子。水粉画下端正中印着两行小字,第一行是“平原省美术协会美工组绘制”,第二行是“平原省湖西专署人民文化馆监制”。这两行小字的右边,也就是在整张年历画的右下角,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印的是我父亲的名字:刘元魁绘图。但是印着父亲名字的这一行小字,比起整张年历画上面的其他字迹来,显得模糊不清,原因是父亲的名字被人用自来水笔涂抹过。可是自来水笔迹更加模糊不清,那些墨水快要褪尽颜色了。我仔细辨认了一下,自来水笔迹竟然是另一个人的名字:梅香。很显然,这一张由父亲绘图、湖西区1949年印制发行的年历画,曾经被父亲和梅女子共同拥有过,可以想见,他们有可能曾把这张年历画铺在桌子上,盯着上面的节气,对1950年的某些日子进行过规划。可是在1949年深秋,父亲跟随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来到安徽砀山的时候,留守的梅女子突然身患伤寒并发症,死于湖西区人民医院。
责任编辑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