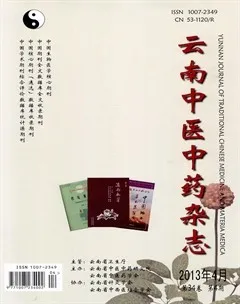从温病学说论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2013-12-29张平吕文亮刘林
关键词:温病学说;风温;湿温;温毒;荨麻疹;湿疹;药疹
中图分类号:R75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3)04-0009-03
温病学是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学说,它的斑疹辨证、湿热证治法、伏气学说等特色理论和方法对过敏性皮肤病的病因、诊断、辨证论治、处方用药以及用药禁忌、预后转归均有指导意义。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又称过敏性皮肤病,是由过敏原引起的一组炎症性皮肤病,是皮肤病中极为复杂的多发病和常见病。中医认为其发病在内为体质因素(体质禀赋不耐、正气多少);在外与风、寒湿燥、火热之邪,以及被广泛称为“毒” 的致敏物(虫、尘螨花粉等)密切相关;六淫邪气中,除寒与湿外,皆为广义的“温邪”。而寒邪久郁、入里皆可化热,湿邪郁久也能生热,湿热之邪也是温邪[1]。其中寒邪作为诱发因素在过敏性皮肤病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温病学家将斑疹的病因归于“热”,如吴鞠通认为“太阴温病,不可发汗,发汗而不出者,必发斑疹……”(《温病条辨》);叶天士亦认为“斑色紫,小点者,心包热也;点大而紫,胃中热也。黑斑而光亮,热胜毒盛”。
1 以“风温”认识荨麻疹
叶天士:“风温者,春月受风,其气已温。”荨麻疹又名瘾疹,好发于春夏交替季节,病因复杂,是多系统、多器官受累的过敏性皮肤疾病。《内经·四时刺逆从论》“少阴有余,病皮瘅瘾疹”。《金匮要略》“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本病病因病机多与风、毒、湿热有关。急性荨麻疹起病急,初起可见卫分证,但卫分证存在的时间很短,随即病邪入气分,而见高热、汗出、烦渴,咳喘气急,腹泻、腹痛,舌苔黄,脉数等典型的气分证,气分证存在的时间较长,肺经郁热波及营分,内窜血络可见肌肤红,皮肤上出现水肿性紫红斑,此起彼伏。
治疗原则方面,根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火郁发之”的治则。银翘散是驱散手太阴风热之基本方,使用中处理好清热与散风、清热与祛湿之间的关系,叶天士说:“夹风则加薄荷、牛蒡之属,夹湿加芦根、滑石之流。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以红斑疹、红丘疹,红色风团,咽痛或咽充血,无明显寒热,无出血斑,舌红、苔薄白或薄黄,脉浮或浮滑或弦为主,辨证属风热袭表者,用银翘散去荆芥、豆豉、薄荷,加生地、丹皮、赤芍、大青叶倍玄参方;以红斑疹、红丘疹,红色风团,咽痛或咽充血,发热,微恶风寒,伴有紫癜,便干或不干,或有腹泻,舌红或绛红、苔薄白或薄黄或花剥或黄或黄腻为主,辨证属卫血同病者,用银翘散合犀角地黄汤加减。赵炳南治急性荨麻疹的一首常用经验方“荆防方”(《赵炳南临床经验集》):荆芥穗、防风、僵蚕、金银花、牛蒡子、丹皮、紫背浮萍、生地、薄荷、黄芩、蝉衣、生甘草,基本是银翘散的加减方,即从卫营同病证角度治疗急性荨麻疹。其中荆芥、防风、薄荷、蝉衣是赵老治急性荨麻疹的一线用药,卫分证疏散、清透的治则,再加丹皮、生地和营药,与吴鞠通方非常吻合。治疗的总原则仍以卫气营血辨证为准,强调“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
2 以湿温认识急慢性湿疹
薛生白说:“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急慢性湿疹是典型之湿温病。急性湿疹是一种具有多形性皮疹、渗出倾向,伴剧烈瘙痒,反复发作,易于发展成慢性的皮肤炎性反应。本病主要与湿邪、过敏体质、接触的过敏源、季节有相关性。但由于病程发展的阶段、患者中焦阳气的强弱等因素,有湿偏重或热偏重的差别,而辨清湿热证湿与热的孰多孰少,直接关系到能否感人,感染后能否发病及用药。急性湿疹如治疗不彻底极易发展成慢性,反复发作。这跟湿邪易于生痰、化热、湿热兼夹,易伤脾胃致内湿停聚有关。
华云岫总结叶天士治湿病的经验可以很好的指导急慢性湿疹的治疗用药。“今观先生治法,若湿阻上焦者,用开肺气,佐渗湿、通膀胱,是即启上闸,开支河,导水势下行之理也;若脾阳不振,湿滞中焦者,用术朴姜半之属,以湿运之;以苓泽、腹皮、滑石等淡泄之,亦犹低湿处,必多烈日晒之,或以刚燥之土培之,或开渠以泄之耳。” 急性湿疹初期常为湿邪极盛,尚未化热。《温病条辩》第12条:“湿热证,舌遍体白,口渴,湿滞阳明,宜用辛开。”湿浊盛治当以化湿为主,薛氏“辛开”药选用“厚朴、草果、半夏、菖蒲等味”。这4味药是薛氏治疗中焦湿热证湿浊极盛的主要用药。对湿疹反复急性发作常常为湿伏中焦,湿渐化热。《温病条辩》第10条表现及证为“舌根白,舌尖红。湿渐化热,余湿犹滞”,治疗用“藿梗、蔻仁、杏仁、枳壳、桔梗、郁金、苍术、厚朴、草果、半夏、菖蒲、佩兰叶、六一散等味”。这是急性湿疹最常使用的方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疗效。急性湿疹如治疗不及时,极易发展成慢性,湿热化燥,其证治同于温热类温病。如邪热在气分,或清或泻;在营血分,或凉或散。湿病后期,病邪深入下焦,真阴耗损,虚热内扰,水亏木旺,则见皮革样肥厚,瘙痒、皮肤干燥、手中心热甚于手足背,口干,舌燥等阴虚内热之象。
薛生白认为由于湿热所引起的发斑应遵“湿热证,壮热烦渴,舌焦红或缩,斑疹,…。热邪充斥表里三焦,宜大剂犀角、羚羊角、生地、玄参、银花露、紫草…等味”(《湿热病篇》)”。“湿热病属阳明、太阴者居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故当内外兼治,外为太阴阳明之表,皮毛肌腠,以辛散祛风胜湿为治;内为太阴阳明之里脾胃,以辛温苦通燥湿渗利为治[1]。
3 以“温毒”学说认识药疹
温病学说中温毒主要是指感受温热时毒而发生的急性感染性疾病,即所谓“诸温夹毒”。临床以高热、头面或咽喉肿痛、出血性斑疹为特征。温毒学说对药疹的发生、发展、辨证、治疗、转归规律能做很好的指导。其发病急,初可见发热,微恶风寒,微咳,咽痛等类似于上呼吸道感染的卫分证,很快出现发热(高热)不解、皮疹、红斑隐隐的气营同病之证,气营同病证存在时间很短暂,病邪即已完全入营,而见斑疹密布,舌质红绛或杨莓舌,此间最易逆传,一旦出现热毒伏邪逆传至心包,心包络代心受邪则见神昏烦躁、谵语、头痛、抽搐为主的精神、神经系统损伤症状。此为属温病极期阶段的证候,陆子贤说:“斑为阳明之热毒”;叶天士说:“斑属血者恒多”。
化斑汤是清代吴鞠通所创,“阳明主肌肉,斑家遍体皆赤”,因此以白虎汤清阳明之热,犀角咸寒(以水牛角粉代替)“救肾水以济心火,托斑外出”,玄参清热凉营。清瘟败毒饮是大清气血的代表方,由白虎、凉膈、犀角地黄、黄连解毒诸方组成,其中生石膏、生地黄、犀角、黄连四药为主,石膏大剂量者可用六至八两。正如余师愚所说:“重用石膏,先平甚者,而诸经之火自无不安矣。”其他药有山栀、桔梗、黄芩、知母、赤芍、玄参、连翘、甘草、丹皮、竹叶,皆是感染性皮肤病或其他皮肤病急性炎症期治疗的常用药。
如周身皮肤潮红,层层脱屑,如糠似秕,隐隐作痒,肌肤干燥,伴口渴欲饮,便干溲赤。舌绛少苔,甚则龟裂,脉象细数,多为热盛伤阴型。本证多为疾病后期,热毒未除,阴血已伤,阴血不能荣润肌肤,则肌肤干燥,层层脱屑。疾病后期,舌象辨证极为关键。舌红少苔,是阴液已伤,正气难复的表现。此时“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观舌有无津液,常可预见转归。此时宜以大剂甘寒之品滋养胃阴;若用咸寒之品常滋腻碍胃,适得其反;亦不可以大剂苦寒之品,否则伤伐脾胃,更损正气。本证治疗时,当酌加活血凉血之品,如丹参、赤芍、丹皮等,以活血化瘀,兼清血中余热,所谓“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3]。
4 伏气温病与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荨麻疹、药疹、湿疹都是属于变态反应性皮肤病类型,此类疾病多因为素体阴精亏虚、先天不足、内伏蕴热等内因,复感温邪发病。病例发病多在春季及春夏之交,春季正是阳气升腾之时,春夏之交及夏季地气炎热,均易引动伏邪而发,非常符合《内经·素问》“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记载。《素问·金匮真言论》中有“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之说。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特定物质过敏、特定环境导致全身性炎症性反应,急性发作期病情重,发病急,瘙痒剧烈,全身中毒反应明显,容易导致慢性病程经过,出现皮肤的干燥、脱屑、肥厚等。过敏性皮肤疾病和伏气温病有很多吻合之处。在临床认识和治疗上我们可以参考伏气温病理论指导此类疾病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疗效。清代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指出“伏温之邪,冬时之寒邪,其伤人也,本因是肾气之虚,始得人而据之”。刘吉人在《伏邪新书》中说“感六淫而不即病,过后而发病,总谓之伏邪”,提出“有已治愈而未能尽除病根,遗邪恶内伏。后以复发,亦谓之伏邪”。大凡具有起病隐蔽或少有卫分证表现、病邪内陷而反复发作特征的疾病,均可从伏气温病辨治。
过敏性皮肤病要重视预防及潜伏期和初期治疗,病程中注意存津救液、保护元神。斑疹的用药禁忌:吴氏提出斑疹忌升提,禁用升麻、柴胡、当归、防风、羌活、白芷、葛根、三春柳;斑疹亦忌攻下。温病学家提出发斑之病在治疗及后期调理时应注意的要点,大抵用药性凉之品占十之八九,不宜偏于温燥以免耗伤阴血,不宜过于苦寒以免败胃。以上只是点滴肤浅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以提高对这类疾病的疗效,减少复发。
参考文献:
[1]宋乃光.温病学说在皮肤病诊治中的应用[D].第九次全国中医药防治感染病学术交流大会论文集,2010:20.
[2]刘明江,王丽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湿疹2例[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15(6):793.
[3]宋坪,杨柳.药疹的中医辨证施治[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0,6(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