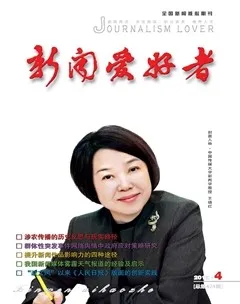试论中国传媒及新闻人法治理念的完善
2013-12-29薛中军
【摘要】新闻话语并非无章可循,尤其是具体到语用实际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要求与规范。某些传媒关于著名歌唱家“李××”之子涉嫌强奸犯罪的报道却存有一定的偏颇,有损于客观、真实、公平与公正。本文仅就相关新闻语用的把握问题展开一定的分析探讨,进而强调传媒及新闻人法治理念的完善。
【关键词】新闻语用;专业;完善
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也是强化法治社会建设阶段。中国传媒及新闻人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新近发出的关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1]的指示精神,就必须把握一定的新闻语用规范。因为毋庸置疑,中国传媒及新闻人审慎新闻语用,加强新闻语用的严谨、准确、专业、规范正是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只有如此,才有益于社会家庭安定和谐,有助于减少更多的家庭伤痛与社会裂痕。
两年前,诸多海外中国人曾因为美国Internation Herald Tribune(《国际先驱报》)头版头题的那篇China’s bitter joke:My father is Li Gang[2](《中国苦味笑话:我爸是李刚》)的报道而唏嘘。而2013年新春刚过,许多受众又无不为新闻传媒发布的关于著名歌唱家“李××”之子有关强奸犯罪的各种报道而惊愕。笔者注意到,关于此内容的报道,个别传媒及新闻人甚至带有某种“欢炒”的喜悦,全然忘了新闻传媒应有的客观、中立态度和身份,更有牵强附会的许多不当与不宜的隐私曝光,由此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值得商榷。
一、倡导公平,新闻语用不可失“理”
我们知道,“语用就是语言的实际应用。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又是思维的工具,所以语言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言语交际应用之中[3]”。可见,新闻报道和语言实际应用密不可分。然而,众所周知,新闻语用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忌用语浮躁、泛泛失真;忌主观臆断、弄虚作假;忌人云亦云、炒作起哄;忌空话套话、言之无物。[4]156可见,作为贯穿、存在于新闻传播整个过程的新闻语用不可乱来,务必保有一定的理性,力求严谨、准确、客观。诚如美国著名新闻专家Bruce(布鲁斯)和Douglas(唐拉斯)撰写的专著所言,“不管传媒老板是谁,新闻人务必不断采集信息,发掘最重要的相关信息元素,并形成新闻报道即新闻故事,然后迅速有效地将其按相应的传媒规范、要求传播出去。此时,无论多少人接到信息而且无论信息在被传播过程中已经发生怎样戏剧性的变化,该信息的出处是新闻领域的新闻人,尽管最初的传播通道可能是电话或电脑等,但新闻人中的他或她通过句子、段落反映着生活万象和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故事梗概,但即使是在非常紧迫的截稿时间的情况下,严谨准确仍是报道的根本所在”[5]4。
综观新闻语用交际方式,我们可以主要总结为口头方式、书面语言及电子图像等,这些皆与内容相关联。方式为交际内容服务,内容依赖方式活动。而新闻语用要素与范畴与新闻要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闻要素体现与新闻价值标准相关,比如与时效性、接近性、影响性、显著性和重要性、结果和影响性、情趣性等相关。新闻要素体现与新闻编辑对文字的把关不可分割,比如相关文字的特殊性、简洁性、情绪性以及传媒影响力等等”[5]10-23。但是在新闻传播交际主体向交际客体受众传播时,注意强化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强化新闻语用规范则是遵循新闻报道原则和新闻传播规律使然,是认真对待把握新闻价值的具体体现。
然而,反观有关著名歌唱家“李××”之子涉嫌强奸犯罪的个别中美传媒报道,却并非如此。比如,在报道导语中,有用“据说”“据传说”“据网传”等含糊用语的。我们知道,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严谨准确的新闻报道,要有明确的记者采访的新闻源告知,不可用传闻方式发布所谓新闻。而关于此事,个别中美传媒报道却少有准确的新闻来源交代或传媒记者亲自采访所得的新闻源告知,不能不说一定程度上有失“理”的水准。不仅如此,更有个别中美传媒及记者的相关报道,在没有得到任何确证司法判定结果的情况下发出判官之音,直接说“著名歌唱家李××犯罪之子……”或“李××的强奸犯儿子……”,情绪宣泄不仅直指“李××”本人及其儿子,甚至直指“李××”其他事情及其家人,其表现大失新闻传媒及新闻人应有的理性姿态与定位。
伴随当代传媒资讯发展的国际化、迅捷化等多元发展,任何新闻事件、现象的信息掩盖都近于掩耳盗铃,所以对敏感新闻事件、现象的信息传播,各新闻传媒都尤其重视,以便更好地倡导公平,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传输率,满足受众信息、心理等多方需求。然而,无论对哪家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媒而言,丢弃新闻理性不该也绝非应当是上述种种情况下的衍生品。更何况,某种“欢炒”的背后,有时往往是某些传媒和记者无端追求某种新闻效应的直接结果,与倡导公平已相去甚远。
可见,新闻语用要以“理”服人、“理”之先行,就要力避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不良:一忌严谨度缺失;二忌为某种目的而进行鼓噪、喧嚣、“热炒”;三忌情绪化导致有失客观中立态度。当然,在资讯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当下,个别新闻传媒报道关于新闻源交代含糊,已并非新鲜事儿。比如,美国新闻人关于新闻源头的捕捉较为宽泛,其中包涵的10种出处是:“其他人;其他出版物;新闻公告或发布;社会服务指导部门;政府公报;你拥有的纸媒上的故事;广告;电子复件;当地新闻摘要;你自己的目击或亲历。”[6]新闻源头宽泛,这当然与各方面因素有关,比如与当代新闻市场激烈竞争有关,与新闻报道要求的新闻价值要素有关,与个别传媒无端追求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等有关;凡此种种,似乎都有一定的可以解说的原由,但是新闻源交代含糊却是真正持有专业精神的传媒及新闻人不应提倡或应禁行的。
不言而喻,以传闻为新闻源可能导致新闻报道失“理”,有违真实性原则。而新闻一旦脱离客观真实,一切都无从谈起。更何况,新闻语用不当不宜,与中国法治社会建设不相匹配。由此可见,个别中国传媒及新闻人法治理念的完善不可拖延,要马上做起、立即做起。
二、伸张正义,新闻语用不可失“规”
不能否认,新闻语用显现一定的倾向性和文化观,主要体现为通过一定有代表性、有刺激性的新闻话语形成一定的效果。由此,传媒新闻报道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对社会文化舆论一定的导向作用,表达着一定社会大众的好恶心理。正如科恩早就指出的,“传媒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有效地决定人们的思考,但能非常成功地告诉读者应该想什么”[7]。这说明议程设置作用产生的新闻导向效应不容忽视。所以,传媒通过报道伸张正义,体现了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一定的正当之责。
何况,当下“正能量”一词颇热,它充分显示了社会上下正直善良的人们寻求正义的心态,以及人们对坚持真理的期许和热望。所以,新闻传媒通过报道伸张正义,是弘扬正能量的具体体现,体现了新闻传媒及新闻人坚持正义的倾向性,无可非议。然而,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伸张正义、坚持一定的倾向性不可失“规”而为。因为,关于新闻倾向性常常体现为客观性与公正性的一体。在此,且不说美国新闻记者道德公约对此方面早有约束,仅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就通过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其中第五条规定“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这个原则这样表述:客观公正,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新闻报道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到客观公正。采写和发表新闻,不从个人和小团体私利出发,不论关系亲疏、个人好恶,不抱任何偏见。新闻工作者与其他组织、个人发生纠纷,不得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发泄私愤,或作不公正的报道。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对于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以及有争议的人和事,不主观臆断,不作偏袒报道。[8]所以,对中美传媒及新闻人而言,在新闻报道中,任何捕风捉影的某种主观臆断或情绪化、妄语断言等,都是与新闻倾向性初衷相违的,是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相悖的。尽管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然而又有谁能说规范冷静的关于新闻倾向性与客观性、公正性的一体显现不是真正大爱、大情的体现呢?也许,后者才更是新闻之“规”的本质所在。
不言而喻,嫉恶如仇、伸张正义,秉持客观、公平的新闻报道,是中美传媒及新闻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然而,在实际新闻报道传播中,却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规”,不能不令人遗憾。笔者认为,关于“李××”之子涉嫌强奸犯罪的个别传媒报道,尤其是有关花边新闻,就有失“规”之嫌。诚如众多人士表示的,此相关报道的中心眼应该重在探讨孩子成长和教育问题。因为,避免更多像“李××”之子一样的孩子触犯法律,不重蹈覆辙,也许才更有意义,更有益于社会家庭的和谐安定。所以,传媒新闻语用当中出现炒“星”“性”“腥”等不当的语用泛滥问题,并非只是新闻语用错位、不协调、混沌等问题的表现,也是个别传媒及新闻人法治理念缺失的表现。关于这一点,尤其对中国传媒及新闻人而言,在当代强化依法治国的历史特殊发展阶段,更值得反思。
综观当今中美社会个别传媒报道,新闻语用的文化承载与传播,已不能不被商业利益所驱动。因为不可争议的事实是,个别传媒新闻语用的文化观显现,已被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所取代。所以,真正秉承新闻专业精神正直正义的新闻传媒与新闻人,无论如何都要坚守把握新闻语用之“规”。何况,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当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均致力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由此,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何不抱着正能量之胸怀,怀着一颗人文关怀之心,更多地报道反思如何强化家庭教育呢?因为犯罪预防及降低青少年重新犯罪率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大工程,它需要社会的综合治理。而这其中,良善的传媒及新闻人尤其不能缺位。
常言道:“凡事应有度,过犹不及。”倘若新闻传媒及记者只为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而使报道语用失“规”,则是背离了新闻报道维护客观公平主张伸张正义的宗旨所在。由此可见,传媒及新闻人法治理念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鞭笞罪恶,新闻语用不可失“律”
综观围绕著名歌唱家“李××”之子涉嫌犯罪的中美某些传媒报道不难发现,有揭隐私的,也有“大嘴巴”传谣的,更有谩骂、攻击的,等等,新闻语用颇有情绪化占主导之势。科学地讲,“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不能画等号,两者属于不同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新闻事实”必定含有一定的主观因子,而“客观事实”则不然。任何将两者等同的认知和行为都是可笑而无知的表现。[4]37
“新闻事实”与“客观事实”不能等同,决定了新闻采写是主客观融而为一的工作,即具有主观、客观相结合的特性。所以,即便是相关鞭笞罪恶的新闻报道,新闻语用也要注意一定的自律与他律,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新闻传媒及记者的媒介素养和品位。更何况,关于法律案件的报道常常并不简单,不仅需要传媒及新闻人具有足够的法律基本常识,也需要传媒及新闻人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素养,使报道新闻语用具有一定的适度性、合法性等。
众所周知,按新闻媒介素养要求,新闻传媒及新闻人必须客观、公平、中立,反对以判官、法官等身份出现,或者发表具有情绪化、倾向性等不适当的观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传媒及新闻人可以不鞭笞罪恶,不挖掘事实真相。也就是说,新闻传媒及新闻人通过报道传播鞭笞罪恶的过程中,不可不顾法规“禁区”任意而为。美国历史上不乏因新闻报道失当而造成判案偏颇的事实,在此不必赘述。而对中国新闻报道而言,中国法律也早有明确要求,要力避“禁区”,以法律为准绳,不可失控与失度。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司法保护部分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第五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在第五十五条中则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同时,第五十九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与犯罪行为的预防,依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执行。”[9]
显然,鉴于未成年人的身、心、智等发展特点,从保护他们的成长发展出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有关法律是设有“禁区”的。然而,那些揭隐私者不仅不加任何处理地发布照片,不遗余力地披露家庭背景资料,更有“大嘴巴”传谣、攻击的,等等。这已不仅仅是缺乏媒介素养品位的表现,更有违“律”之嫌。当然,一定程度上这也体现了在传媒激烈竞争态势下,利益驱动传媒报道的某种结果。可见,为“炒”的需要而导致虚妄语用泛滥,不仅有悖新闻规律,不利于新闻传播,也是失“律”而为,不利于犯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是不负责任的无良、无仁的某种表现。
从法律专业角度而言,且不说“李××”之子的年龄等等,单单仅就案件侦查刚刚开始,一切尚未有结果和结案等定论之时,个别新闻传媒和记者就大肆不当地“热炒”并跟风,不能不说是有所失“律”与失“衡”的。其实,即使案件定案或结案,法律认定“李××”之子有罪并判罪,这种“热炒”跟风和过于情绪化的新闻表达,对当事人及当事人家人也是不公平的。更何况,一切未明了之时,按《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隐私的明确规定,即使提及其真实身份及家庭背景的表述,也是不适宜的。
诚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传媒或百姓嫉恶如仇,反感特权,愿意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以及呼吁民众平等的心愿皆可理解。但是,“人人平等”难道不同样适用于名人之后吗?所以,传媒及新闻人不可“越位”,也不可先入为主做定论有罪的判官,等等。因为,司法自有司法的程序,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不可以笔代之。只有如此,新闻传媒及新闻人才可能真正做到新闻语用的有法可依,做到新闻传播自律与他律的“律”之有度。
毋庸置疑,当代社会受众知情权等公民权益的觉醒,呼唤更多的新闻传媒报道的自由空间,新闻人在诸多事宜上满足受众更多对新闻报道透明度的需要,倡导公平、伸张正义、鞭笞罪恶均无可非议,但是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也要莫忘新闻之“理”、之“规”、之“律”,因为坚持新闻原则和新闻规律,把握适宜的中立身份立场,不被情感左右,不盲目使用新闻语用也是实现受众知情权等公民权益觉醒的重中之重。一定意义上讲,仅就中国而言,新闻传媒及新闻人直面事件发生,担当社会责任,并不仅仅针对一家一户一人,而是整个社会。因为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也是强化法治社会建设阶段。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曾强调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1]
总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关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指示,对中国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提出了努力发展的方向,它对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然,它也应该是中国新闻传媒及新闻人铭记在心并进而践行的。所以,中国新闻传媒及新闻人把握一定的新闻语用,要有所言有所不言,这也是新闻传媒及新闻人保持中立、独立的具体体现,是体现传媒新闻报道客观、真实、公平、公正非常关键的环节。何况具体到该案而言,司法程序刚刚开始,案情尚未定案明了,新闻传媒及新闻人最好本着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适当采取一定的规避策略,因为此分寸的把握以及导向,也许更有利于该案的司法公正,有利于推动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从这一点而言,它与新闻传媒及记者满足受众知情权等公民权益的觉醒,践行舆论监督权利的行使并不矛盾,也不存有任何悖论。何况,新闻语用的浮躁、泛泛、失真,以及主观臆断、人云亦云和炒作起哄等,皆不可取,而无良无品的新闻语用更是令真正的传媒及新闻人所不齿。
综上所述,中国传媒及新闻人是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所以尽快不断地加强传媒及新闻人法治理念完善,必须落实到具体新闻报道工作中,不可忽视与放松。因为它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安定奔小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价值。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新华社北京2013-02-24电稿.
[2]China’s bitter joke:My father is Li Gang,Internation Herald Tribune,First p,2010-11-18.
[3]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247.
[4]薛中军.新闻采写研究[M].上海交大出版社,2010.
[5]Bruce D.Itule,Douglas A.Anderson:News Writing and Reporting for Today’s Media.McGraw-Hill Education Press,2003.
[6]Brians.Brooks,George Kennedy,Daryl R Moen and Don Ranly,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Bedford and St.Martin’s.2001,p99.
[7]Cohen,Bemard: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3.
[8]出版常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新编[G].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79.
[9]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46.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访问学者)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