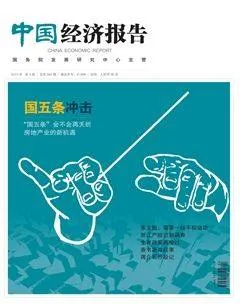新型城镇化虚实
2013-12-29彭真怀

今年元旦过后,我在河北省宁晋县、广东省高州市、安徽省五河县和山东省垦利县等地调研,当地干部群众对我说,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有一段时间了,但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有些明显是跑偏的。他们特别想有个说法,讲明白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里?与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关系?坦率地说,这些疑惑也是我最近一直苦苦思索的。为了找到答案,我把自己关起来,对新型城镇化的各种意见进行了一次集中的逻辑梳理。
新型城镇化要闯过深水区
在这样一个近乎面壁修佛的过程中,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回归常识,努力把真相和全貌搞清楚,把本质和规律弄准确,把思路和对策想透彻。我注意到这样一件事,早在十多年前,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就反复强调要搞“城镇化”,要搞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但具体操作层面的官员更喜欢推行自己的“城市化”,而且是特大城市、国际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之类的“城市化”。一字之差,后果完全不同。于是大家就看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要“趋利避害”。但究竟避什么害?为什么避害?害到了什么程度?
2012年12月17日晚,我应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之邀,解读当天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当时说,所谓“避害”,就是要避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三沙市属特殊情况)新一轮扩张之害,要重点改造这些城市的老城区、棚户区和城中村,把累积的历史遗留问题清理干净,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从面上看,这些城市都在透支国家的土地、水资源承载能力,三次产业结构中二产占大头,二产中又以钢铁、石化和建材为代表的资源型落后产能占大头,并同时陷入交通、环境和就业等多重困境。这就意味着,必须有针对性的举措闯过深水区,不宜一拖再拖直至没有退路。
新型城镇化敢碰真问题
当代中国,恐怕没有一个词像“城镇化”这样歧义百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人都在似是而非的概念上绕圈子,有时甚至脱离了公认的普遍规律。调子高到天上去了,就是不着边际,不敢面对已经存在的尖锐矛盾。近平、克强同志都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一些人却自有另一类的空话、套话,前几年的“城市化”发言也居然拿到现在用。如此没有针对性,新型城镇化还怎么深入讨论下去?在我看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谈真问题,要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劲头,要有把自己的见识、主张,尤其是逆耳忠言说出来的勇气。
既然叫新型城镇化,那就是与当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化不同,而且这个城镇化一定是撞到南墙了,否则就没必要提什么“新型”的。其实,2010年就有专家对我说,当前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半截子城镇化”或“不完全的城镇化”,过激的观点甚至认为是“病态城镇化”或“畸形城镇化”。我一直注意倾听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从中学习、借鉴和体会了很多真知灼见。我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可以大体上梳理出当前城镇化的十大积弊:
一、制造了城镇化率的数字泡沫;二、放大了户籍壁垒的制度缺陷;三、暗藏了土地财政的隐性风险;四、侵蚀了耕地资源的保护红线;五、引发了攀比冒进的失控开发;六、催生了商业贿赂的高发多发;七、扭曲了干部考核的评价导向;八、漠视了城市自身的弱势群体;九、割裂了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十、恶化了生存发展的环境空间。
新型城镇化要先调研后决策
记得小时候种地,长辈总是先把地里的石头、树根和杂草清理干净,然后再播种。我想,治国与种地是一个道理。新型城镇化能不能成为未来30年的经济主载,关键在于能不能把这些批评意见暴露的问题一一加以解决,以苦干续写中国辉煌,用实干托起中国梦想。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正本清源,就能矫枉纠偏。我建议在全党、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调研,对当前的城镇化进行全面彻底反思,采取不破不立、边破边立和先破后立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看准了的就下决心干,明摆着是错的就赶快改,不能总是在深水区里“摸石头”。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度过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全党就一些重大问题同时开展调研,很快就形成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决策。我听到消息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已基本定稿,今年上半年可能正式出台。从我个人角度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规划应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后再公布,特别要增加对新型城镇化的最新理解和认识。包括破解新型城镇化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和地向哪里用三大难题,拿出几条看得见、摸得着和感受得到的可操作性实施意见。
新型城镇化要盘活三农全局
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出现过农民贫困、农业凋敝和农村没落的现象。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农民富则国家盛,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村稳则社会安。新型城镇化不应当造成新一轮农村环境的大破坏,农民更不应当成为整个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成为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流民群体。如果新型城镇化以牺牲农民、农业和农村为代价,就会成为经济风险的重要根源,成为社会稳定的主要引爆点。一个国家的城镇化走向,对农民保持应有的尊重,必须对农业保持应有的敬畏,对农村保持应有的清醒。
我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大量耕地被抛荒,很多村庄的房屋常年无人居住,断壁残垣,荒草丛生,拆又不能拆,卖又卖不出,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山东省乳山市樗树崖村约有600处宅基地,其中荒废多年的房子有200多处。除了正常生育之外,村里的人口几乎只出不进逐年减少,加上人口自然死亡,空置的房子越来越多。湖北省阳新县姜福村现有耕地3,169亩,人均耕地不足1亩,村民用打工挣来的钱建新房,每年减少耕地十几亩。2002-2005年,这个村减少耕地170多亩,相当于一个村民小组的耕地面积。
这种由人口空心化演变的涉及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域空心化现象,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点,但也是希望所在,承载着13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蕴涵着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梦想的信心与能力。我的综合测算表明,按照分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情景,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1.5亿~3亿亩。再加上打谷场、村边林、取土坑塘等村庄附属用地,保守估计可有效利用耕地4.5亿亩以上。这本帐算清楚了,就可以找到新型城镇化开门的钥匙,形成农村宅基地的退出与盘活机制,破解建设农村新型社区的土地供需矛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按照我的理解,新型城镇化是未来30年的一次制度革命。为什么这样讲呢?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当时的人口分配耕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造成了3.5亿农民从一出生就没有土地,其中2.5亿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大迁徙大流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触及农村产权制度,占人口总数65%以上的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新型城镇化所承接的,是过去30年留下的最难啃的硬骨头,“老百姓越来越难管”,“维稳成本高”,所有的改革议题都充满着分歧甚至严重对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一种革命性的超越,并以这种超越体现历史进步。
过去十年,我始终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新型城镇化一定是一个可持续的国家战略,能够把国家的梦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就业梦”、“上学梦”和“安居梦”……但我也时时刻刻地感受到,当前城镇化的推动者与改革的对象多数情况下是同一个主体,他们在城镇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并已经从容地掌握了话语权。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早就暴露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制度积弊,为什么一直推不动、改不了?新型城镇化所呼唤的所有改革内容,既得利益者在经历短暂的观望后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面对他们的集体阻挠又该如何破局?
比如特别敏感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已经想到了“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有些人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呢?日本、韩国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增值部分都要拿出来分享,我们国有、集体土地的增值怎么被少数人装进腰包了呢?今天的矛盾,有一多半都是土地带来的,群体事件也有一多半是因为土地纠纷导致的,贪腐也大多跟土地连在一起。我主张,新型城镇化先从土地制度入手,现在就动手下狠刀,逼地方政府下决心放弃倒卖土地的财政。当然,大家都会觉得疼,但现在不动,越晚动越疼。农村土地增值的主要收益,从道义上必须归进城的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突破了,农民进城的信心就有了,既得利益者就不得不让步。没有这一条,新型城镇化就是白扯。
从人类历史长河俯瞰,类似于新型城镇化这样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由最早感受到危机的知识分子首先表达诉求,最终由明智而有能力的执政者下决心形成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样一个上下呼应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阻断革命的过程。我最近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从何而来?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推动新型城镇化?关键的问题是,近平、克强同志在获得应有的权力后,如何把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改革动力,从而引领历史走向代价较小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有人说,新型城镇化一旦推进,就会触动既得利益的守护者,这种情况下还有可能达成共识吗?但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否则城乡两极分化到最后就是社会撕裂,谁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
我仔细分析了最近三个多月来的新型城镇化讨论,整体上虚的多、实的少,看不到究竟怎么干的思路。我很担心这样的高谈阔论,不利于中央下最后的决心。人们通常说,十八大开启了新10年。我的看法是,把十八大看作是新30年的开端应当具有更高的立意。今天所做的,是我所能做的初步尝试。我努力把零散的观点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期待与所有关心新型城镇化的人们共同思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